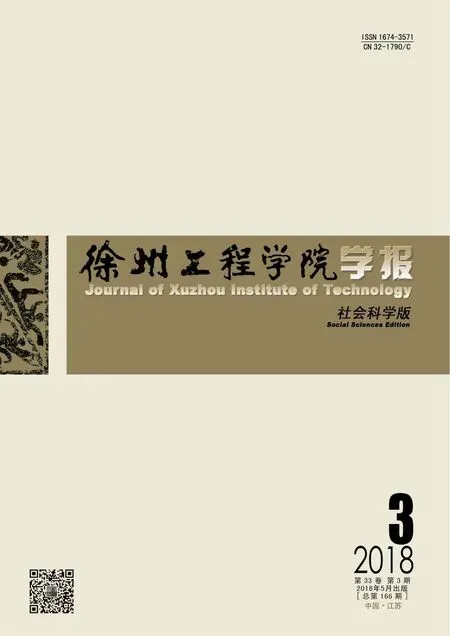圆融思维与意象诠释:阳明哲学的理论纲脉
李煌明
(云南大学 哲学系, 云南 昆明 650500)
阳明强调为学须有头脑与纲领,批判后儒之学没有头脑,故茫茫荡荡,全无着落;纲领不明,故迷于傍蹊小径,陷入断港绝河,通不得,行不去。于是,辨析之纷纷、争论之哓哓,而圣学日以支离,益以残晦[1]14、15、38、10、48。故钱穆指出,讲王学,首先须超脱训诂与条理,直透大义,全其精神;其次,须摒弃争道统与闹门户,依其气脉文理,述其大纲流变[2]序1-2。不明其头脑与纲领,则终难超越训诂与条理之境界;不解其思维与结构,则终难突破概念与命题之窠臼。头脑与纲领透显出阳明哲学之精神特质——大道的浑沦性与思维的圆融性。头脑者,本体也,旨趣也,哲学观也;纲领者,思维与结构也,条理与脉络也,本体之开显也。此二者,一似规矩与方圆。非规矩,方圆无以立;非方圆,规矩无以见。规矩者,方圆之微之本;方圆者,规矩之显之用。故曰:“体用一源,显微无间。”概而言之,“知行合一”是阳明哲学之宗旨与总纲。分而论之,“道即是良知”[1]105是其哲学观、本体论,是头脑*阳明对良知心体即道的表述,遍见于《全集》,如“知是心之本体”(第6页)、“这心体即所谓道”(第14页)、“见得自己心体即无时无处不是此道”“心即道,道即天。知心则知道,知天”“诸君要实见此道,须从自己心上体认”(第21页)、“道即是良知”(第105页)等。;“一三三一”是其内在之思维与结构,是纲脉。由月印万川、一多相摄、理一分殊故,总体是一三三一,各各亦一三三一。本体原无内外,大道不分物我。故以道观之,当下哲学诠释之理路即阳明理论建构之心印,皆一乎良知本体开显之纲脉。理路、心印、纲脉,似三而一,共通的思维-结构之“象”是贯通本体之“意”与诠释之“言”体用显微两端的桥梁,故曰:“意以象尽”“象以言著”,“体用一源,显微无间”。通过良知本体原义的追问,本文进一步阐释了以“意象”为核心的哲学观念与诠释方法——“意象哲学”与“意象诠释”*“意象哲学”与“意象诠释”相关阐述,参见李煌明:文化意象、民族精神与少数民族哲学[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13(6);宗密一心二门思维模式与濂溪宇宙本体论建构[J].广西师范大学学,2014(6);价值观念、思维模式与中国哲学的人格诠释法:以李贽哲学与人生的诠释为例[J].徐州工程学院学报,2014(6);“先立乎其大”:张载的虚气本始论及参两模式[J].哲学研究,2015(1);意象哲学与民族精神:少数民族哲学的本原论建构[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15(6);一而二,二而一:朱子哲学的思维结构与理论纲脉[J].哲学研究,.2017(4);中庸之道与意象哲学:中国哲学的重构与诠释[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17(4)意象言:意象哲学简论[J].云南大学学报,2017(5);核心价值观的体用结构与思维方式:基于中国哲学本体论的思考[J].广西师范大学学报,2017(6).下文常涉及其中相关内容,为简洁故,不再一一注出。。
一、圆伊三点与本体三性
阳明关于“本体”的表述各不相同,大致可分二类:离相言体与即相言体。阳明说:“太极生生之理,妙用无息而常体不易”,“心之本体即是天理,天理只是一个,更有何可思虑得?天理原自寂然不动,原自感而遂通。”[1]64、58离相乃就其“常体不易”“寂然不动”而言;即相则就其“妙用无息”“感而遂通”而论。由体用一源故,良知无前后内外,无寂然感通,而浑然一体者也。然要得分明,又须分而别之。事有本末,言有先后,此处先就其不易之常论之。
概而言之,良知本体实熔心、性、气于一炉,集公、寂、中为一体。心、性、气是本体三性质,公、寂、中是本体三性用。此二者实构成了“自性体用”结构:三性质是自性体,三性用是自性用。然就自性体与自性用分别而论,心、性、气与公、寂、中皆为“圆伊三点”结构。就思维而言,自性体用是“一而二,二而一”,而圆伊三点则是“一三三一”。圆伊三点者,伊字三点也。三性成伊,一心为圆。非方非圆,亦方亦圆;似三而一,似一而三;举一含三,相即相入;非一非异,一三三一。故佛家以“∴”象之,明其一三三一之理,显其心性不二之论。南岳天台之“三谛一境”“三智一心”,此之谓也。 理学先声、华严五祖,宗密更以“空寂知”释之,曰:“但云空寂知,一切摄尽。”[3]127有且只有“空寂知”三者圆融一体,方可尽显本体之用。于此,阳明论曰:“性无不善,故知无不良。良知即是未发之中,即是廓然大公,寂然不动之本体,人人之所同具者也。”[1]62可见,阳明良知心体亦有三性用:中、寂、大公。以思维-结构观之,良知本体之建构亦不出圆伊三点、一三三一。阳明之“心即理”正与宗密之“真心即性”相契,“公寂中”正与“空寂知”相照。
所谓“空”,指本体之虚无而言。虚无者,湛然非有、无声无臭、无方无所、无形无象也。宗密释之曰:“空者,空却诸相”,一如瓶空之空,非谓无瓶。故曰:“言无者,心中无分别贪嗔等念,名为心空,非谓无心。言无者,但为遣却心中烦恼也。”[3]124-127空者,虚也,无意无念、无是无非、无为无相。于此,阳明说:
仙家说到虚,圣人岂能虚上加得一毫实?佛氏说到无,圣人岂能无上加得一毫有?但仙家说虚,从养生上来;佛氏说无,从出离生死苦海上来。却于本体上加却这些子意思在,便不是他虚无的本色了,便于本体有障碍。圣人只是还他良知的本色,更不着意在[1]102。
阳明指出,“虚无”便是良知本色即心之本体。于此而言,儒释道三家并无差别,故说,无上不能加得一毫有,虚上不能加得一毫实。此即所谓良知本体之形上性,是对一切有形有对的超越,故亦为超越性。由此,阳明说:“无善无恶是心之体”“心之本体原无一物”是“廓然大公”[1]117、34。由上,所谓“空”便是虚无,无有障碍而廓然大公,是良知本色,指示本体的形上性、超越性。
所谓“寂”,指本体之实有而论。实有者,窅然非无也,至虚之中有至实者存焉,乃至善之性、至实之理也,是万有之本源,故阳明说,良知是乾坤万有之基,是宇宙万化之源[1]790。如果说“空”是“空瓶”之“空”,那么“寂”则是“空瓶”之“瓶”,故宗密说:“空者,空却诸相,犹是遮遣之言,唯寂是实性不变动义,不同空无也。”可见,“寂”者,指不变之性、不动之实而论。由性即理,故又说:“理即寂也”,是“象外之理”[3]127。于此,阳明亦说:“至善是心之本体”。既为“至善”,故又说“光光只是心之本体……此便是寂然不动”[1]2、22。所谓“光光只是心之本体”即是“离相之体”“象外之理”。因其至善,故完满自足;因完满自足,故寂然不动。由此,寂然便是至善,包含了自足性与完满性,是从性理上说本体,故阳明说:“心之本体原自不动。心之本体即是性,性即是理,性元不动,理元不动。”至善者,自涵有规矩、准则之义,故阳明说:“尔那一点良知,是尔自家底准则。”[1]24、93然而现实总是偏于一隅,总是残缺不全,完满至善只能存在于理想之中,故至善性实指理想性。由上,所谓“寂”便是“寂然不动”,是从性理上说,指示本体之至善性与根源性。
所谓“知”,灵知也,灵明神妙也。灵明神妙者,灵动而明觉,能知能辨,能生能显。宗密说:“唯空寂知也。若但说空寂而不显灵知,即何异虚空?……何名摩尼?何能现影?”故说:“知是当体表显义。”[3]125、127如果说空无、虚无是遣其非,那么灵明能觉之知便是显其是,指示本体的灵动性。由此,阳明说:“心之虚灵明觉,即所谓本然之良知也”,“未、发之中即良知”,“良知即是未发之中”,“所谓恒照者也”[1]47、64、62、61。故阳明所谓“中”者即“未发”也,“灵明”也,“恒照”也,指“知”而论。“江右王门”王塘南(时槐)亦就此指出:“故知之一字,内不倚于空寂,外不堕于形气,此孔门之所谓‘中’也。”[4]468正因“知”便是孔门之所谓“中”,而“中”乃对“和”而言,是能发而未发、能应而未应者。此于本体之“知”的理解至关重要,若将其误解为已发之知、感应之动、实现之生则是形上形下不分,体用混为一谈。于此,阳明说:“知是心之本体”“良知者,心之本体”,是天植灵根,生生不息,是造化精灵[1]6、61、101、104。可见,所谓“知”便是“自然灵明”,乃就“心”之“虚灵明觉”“未发之中”而论。由灵动性,故有贯通性;由贯通性,故有普遍性。为此,灵动性便包含了自然性、贯通性与普遍性,故宗密说:“知之一字,众妙之门。”[3]38综上,“知”者,便是“未发之中”也,就其“神灵”“妙觉”而言,指示本体的灵动性与未发性。
由上,阳明心体之公寂中与宗密真心之空寂知确然相印相契。由“空寂知一切摄尽”,故良知公寂中亦摄尽一切,故阳明说:“心之本体无所不该,原是一个天。”“除却良知,还有甚么说得!”[1]95、204此三性用者,实为良知本体之三义,可谓“一名三义”。析其用而言有三,合其本而言则一,故曰“一三三一”“一名三义”。“廓然大公”是其遮遣义,指其形上性与超越性;“寂然不动”是其不变义,指其至善性与根源性;“自然灵明”是其不断义,指其灵动性与未发性。
公寂中三者,各有其用,不可或缺。《起信论》曰:“解释分有三种。云何为三?一者显示正义,二者对治邪执,三者分别发趣道相。”[5]15此乃指示空寂知三者各自之用,阳明本体之公寂中亦如是。形上性与超越性,乃对治世儒之邪执,超越意必固我,从世俗泥潭中超拔出来,从个体私我中脱洒出去,故曰“廓然大公”。至善性与理想性,旨在立本显宗,本乎“立人极”。若破而不立,则沦空堕无,故须立此爱根与孝心、天理与准则,方显儒家本色、圣人理想,故曰“寂然不动”。灵动性与未发性,意在彰显本体之灵明性与自然性、贯通性与普遍性,所谓“能生能显”。万物自此出,万事由此生,由体达用,应事接物,莫非良知也。得此良知道体,故造化在手,天地我立,万化我出。良知本体不是凝然不变者,若是枯槁之物则何足道哉?以其可以妙万物,故名之曰“神”,称之曰“灵”。
圆伊三点者,一三三一,廓然、寂然、自然,湛然、窅然、本然,浑沦一体,一似《老子》所谓:“此三者不可致诘,故混而为一。”[6]53故阳明说:“良知底用安排得?此物由来自浑成。”[1]785知其有三,而不知其一,则方而不圆。明其分别,而不知融会,则失之乖离。由即心即性故,不可以“心体”“性体”析之;由即天即人故,本体即境界,良知即天道,不可以“存有”“境界”分之。一三三一者,相即相入,互收互摄,故举一含三。换言之,说“寂”便有“空”与“知”在;举“知”则有“寂”与“空”存;言“空”则有“寂”与“知”俱。阳明拈出“良知”二字,便是以自然灵明统摄廓然大公与寂然不动,至善性与根源性、超越性与形上性皆融乎其中。卷而藏之,会三归一;舒而展之,一中有三;圆而融之,一三三一,相即相入,一心圆通三性,一性遍含一心。
有是体必有是用,有是用必有是体;无无用之体,亦无无体之用。既然良知本体有公寂中三性用,那么必有其相应之体,必有“附着处”,否则便悬空无实矣。悬空无实,则难免捕风捉影,玩弄光景,求个效验。故公寂中三性用者,不过圣人气象,非道体之真切。若舍道体而求气象,则“如以无星之称而权轻重,未开之镜而照妍媸,真所谓以小人之腹而度君子之心矣”[1]59。当然,此体与用皆就超越本体而言,故称其为“自性体用”。何谓“自性体用”呢?宗密说:
真心本体有二种用:一者自性本用,二者随缘应用。犹如铜镜,铜之质是自性体,铜之明是自性用。明所现影是随缘用,影即对缘方现,现有千差。明即自性常明,明唯一味。以喻心常寂是自性体,心常知是自性用。此能语言分别动作等,是随缘应用[3]129。
由上,所谓“自性体用”,皆就超越本体而言者。此所谓“用”者便是宗密之“自性本用”,与“随缘应用”相对。公寂中者,圣人气象也,犹铜之明也,是自性用而非随缘用。良知道体之中又有体有用,此便是“自性体用”。那么“铜之质”“道之体”“附着处”,即良知之“自性体”究竟为何呢?阳明说:“盖天地万物,与人原是一体,其发窍之最精处,是人心一点灵明。”[1]107由即心即天,即天即道,故“人心一点灵明”即“宇宙之一点灵明”。由此,所谓“自性体”一言以蔽之,是“真己”,是“主宰”,是“一点”:可以而尚未展开的一个原点,人心本此一点,宇宙亦此一点,万古亦此一息。不过,这一点不是槁木死灰,而是“造化的精灵”,“生天生地,成鬼成帝”,是“与物无对”的“灵明”[1]104, 是三性同俱的“圆点”。
作为本体之原点、圆点是什么呢?简言之,便是心、性、气三者的一体浑融,糅合了宋代三种本体论:以“气”言,谓之“虚无”,是“太虚”,是“廓然大公”;以“性”言,称其“至善”,是“天理”,是“寂然不动”;以“心”言,名为“灵知”,是“神妙”,是“自然灵明”。寂者,以性善而言;知者,以心灵而论。此前已论,无须赘述。以理推之,虚无者便应对气而说。正由此,阳明说:“良知之虚,便是天之太虚;良知之无,便是太虚之无形。”[1]106可见,良知本体涵盖了气在内,此亦非笔者之孤见独发。秦家懿亦就此指出:(阳明)“他也以良知说统摄气说”“他的宇宙论与气论,都属于他的心学或良知论”[7]109。
就超越性而言,本体莫非“虚无”,此儒释道三家之同,故说虚无是良知本色。但是在阳明看来,从真实性论,三家根本不同:仙家从养生上说,佛家从解脱上来,儒家从太虚上论。阳明所谓“太虚”,正是横渠所谓“太虚无形,气之本体”,是超越“阴阳二气”的“形上之气”,所谓“至虚之实”“至实之虚”者。故曰:“良知之虚,便是天之太虚;良知之无,便是太虚之无形。”本体之性即太虚之气,原无分别,宇宙万物“只为同此一气,故能相通耳”,故说:“若见得自性明白时,气即是性,性即是气,原无性气之可分也。”又说:“夫良知一也,以其妙用而言谓之神,以其流行而言谓气,以其凝聚而言谓之精,安可以形象方所求哉?”[1]106、107、61、62“精”“气”“神”只是“一物”即“良知”。良知本体摄尽一切,含融全体,故气亦不外良知,无有一物能超于良知之外,故以未发之体观之:“精”者,天理也,寂也;“气”者,太虚也,无也;“神”者,心灵也,知也。只是本体之“气”不可以“气”名,及其流行方谓之“气”,故说:“圣贤非无功业气节,但其循著这天理,则便是道,不可以事功气节名矣。”[1]96如果“圣贤”便是“本体”,“功业气节”“事功气节”便是“气”,那么便可说:本体非无气,但其循著这天理,则便是良知,不可以气名矣。由此,阳明重视“亲民”“事功”也就有了本体之根。
综上,良知自性用是圆伊三点、一三三一,由“体用一源,显微无间”,良知自性体心性气亦如是。用由体立,体以用彰。体者用之微,用者体之显。故体用显微,同构同源。体之与用,只是一个,而不是分割的,只是因了言说与理解的方便将体与用分开论而已。由举一含三故,良知本体亦可从太虚上论,而心、性、气与公、寂、中皆尽摄乎其中矣。故阳明说:“本体只是太虚”,“夫惟有道之士,真有以见其良知之昭明灵觉,圆融洞澈,廓然与太虚而同体”[1]1306、211。若不明良知本体之圆融洞澈、一体浑沦则必然滞碍不通,偏于一隅,各执己见,于是析理气、心性为二,昧体用一源之理,故“各滞于一偏,是以不相为用”[1]62。由前所论,阳明良知本体之一三三一亦是“体相用”结构。以“体”观之,良知是心性气。以“相”观之,良知是廓然、寂然与自然,合此三者而言便是“本然”“浑沦”。此即“无状之状,无物之象”,是本体之大象。以“用”观之,则有空寂知三者,即形上性、根源性与自然性。
二、妙应随缘与流行三态
上节乃离相言体,此节则即相言体。在阳明哲学中即相言体,便是“妙用无息”、“感而遂通”,乃良知本体的自然流行、当下发现。简而言之,良知即道,一而已矣,而有寂感体用,故其结构便是未发-已发。此便是道之本体与道之流行,亦即“道兼体用”结构,只是此体用不是自性体用而是随缘应用。这一道兼体用结构,实质上便是“易”之“一名三义”。道一而已,故简易;寂然不动,故不易;感而遂通,故变易。就变易而论,良知流行、应感而动,故有“节目时变”,显时位之异,此即心-意-物三态,此三态之结构实质便是《易》之意-象-言。
阳明在《答聂文蔚》中云:“良知只是一个,随他发见流行处当下具足,更无去求,不须假借。然其发见流行处却自有轻重厚薄;毫发不容增减者,所谓天然自有之中也。”[1]85如果离相言体是不变,那么即相言体便是随缘。正由此,阳明之高足龙溪(王畿)明确地说:“良知虚体不变,而妙应随缘。”[8]277所谓“随缘”即“妙应随缘”、“妙用无息”,是良知之发见流行处。如果说“离相”似“真如心”,是至一不二、不增不减,那么“即相”便如“生灭心”,是善恶二分,净染和合。由此,可以说不变是良知之真如义,是“非异”,是理想;随缘是良知之和合义,是“非一”,是现实。
良知本体之流行发用实其自然固有之性,一似水之就下而川流不息。因其自然无为,故流行变化全在“应”、“时”二字,所谓“应感而动”、“顺时而化”者也,所谓“良知之于节目时变”者也[1]50。阳明诗云:“无声无臭独知时,此是乾坤万有基”、“良知却是独知时,此知之外更无知。”[1]790良知本体妙应随缘,因不同时位而呈现不同状态,此便是“节目时变”。那么,本体如何流行变化呢?在《答顾东桥书》中,阳明释曰:
心者身之主也,而心之虚灵明觉,即所谓良知也。其虚灵明觉之良知,应感而动者谓之意;有知而后有意,无知则无意矣。知非意之体乎?意之所用,必有其物,物即事也。……凡意之所用无有无物者,有是意即有是物,无是意即无是物矣。物非意之用乎[1]85?
阳明以本体之“自然”(灵明)统摄“寂然”(至善)与“廓然”(无善),故说:“良知,心之本体,即所谓性善也,未发之中也,寂然不动之体也,廓然大公也。”[1]62*至善者,有也;无善者,无也。以举一含三故,良知者叩此有无两端而竭,故曰“中”。由此,“良知”(知)、“心体”“道心”,名三而实一,皆指本体而言[1]52*《传习录》云:“道心者,良知之谓也。”。。阳明指出:“有知而后有意”,“意之所用,必有其物,物即事也”,故良知之道的流行过程可概括为“心(知)-意-物(事)”。此即良知之“节目时变”,是心体流行所呈现的三种状态,故本文称其为“流行三态”或“本体三变”:本态、意态、物态,或本然、或然与定然。只是阳明对此有二种回答:以“意”为中心则说,“知者意之体,物者意之用”;以“心”为原点则曰,心之所发,便是意;意之所在,便是物[1]47、6。显然,三态之间乃性相体用、本末源流、未发已发关系。
于本体三变或流行三态,应从同与异两面观之:以非异观之,三态莫非一心,同一本体,只一良知便括尽一切。道一而已,岂有前后内外哉?故说:“心外无理,心外无事。”[1]15此谓虽三而一,乃以体观之也。以非一观之,心一也而有体用之殊;道一也而有时位之异。心意物者,三也。此谓虽一而三,乃以用观之也。故合同异,兼体用而言,一三三一也。由即心即性故,本体三态可用阳明对“性”的论述加以说明。
问:“古人论性,各有异同,何者乃为定论?”先生曰:“性无定体,论亦无定体。有自本体上说者,有自发用上说者;有自源头上说者,有自流弊上说者。总而言之,只是一个性,但所见有浅深尔。若执定一边,便不是了。性之本体,原是无善无恶的;发用上,也原是可以为善,可以为不善的;其流弊也原是一定善,一定恶的。……孟子说性,直从源头上说来,亦是说个大概如此。荀子性恶之说,是从流弊上说来,也未可尽说他不是,只是见得未精耳。”[1]115
阳明从体用、源流上和会诸性论:“只是一个性”也就是“但惟一心”。所谓“道,一也”,贯天人,彻古今,通变化,只此一良知,此乃以同摄之,非异也。分体用与源流则以异论之,非一也。阳明强调:不可执定一边,而应圆融贯通。以分别观之,至善是从源头上说来,无善则就本体上说来;以同一观之,“无善”“至善”与“灵知”,乃涵三为一,只是一个本源,本体与源头为一,生成论与本体论不二,此即“本-源”论。为此,“中寂大公”即为“本态”。“可以为善,可以为不善”即“可善可恶”乃发用,是意之动,是“意态”;“一定恶”乃就流弊即负态上说,而“一定善”则是就正态上论,然莫非物之成,事之定,是“物态”。
众生之心即宇宙之心,个体良知即天地之仁,故阳明曰:“良知即天道。”[1]986良知之心意物的流行也就是“易”之意象言的大化,良知与易无非道也,心意物与意象言无非道之变易也,“节目时变”也。《易》曰:“在天成象,在地成形”,此言“易”之流行,“易→天→地”便是其内在结构。为此,王弼说:“夫象者,出意者也;言者,明象者也。尽意莫若象,尽象莫若言。言生于象,故可寻言以观象;象生于意,故可寻象以观意。意以象尽,象以言著。”[9]609可见,易天地、意象言、心意物三者在结构上是相通的:自幽而明、由微而著、渐形渐固。此即天人合一,同构同源,莫非一道,不外一三三一。
作为形上之道,是对阴阳动静的超越,故曰“非阴非阳”“无动无静”。与之相应,“良知即道”则是对善恶、是非的超越。然都是“未发”,一如《老子》(简本)所谓:“有状混成,先天地生。”因其未发,故此先天地生之状,只是一个能现而未现的原点、圆点,阳明所谓“先天未画前”,乃“无状之状,无物之象”。此便是良知中寂大公之本然,即本来面目、原本状态,乃超乎形象,不杂声臭,不落方所,故曰,“无善无恶心之体”。由“心即理”故,阳明自然得出这样的结论:“无善无恶者,理之静。”[1]29此即所谓“本态”,思虑未萌而事物未接也。细细品来,阳明良知道体有统天地人三极,摄儒释道三家之意。其《白说字贞夫说》曰,贞者,三极之体,诚而神者,全乎理而无所容其心焉[1]906。良知即道;道者即贞;贞者,备天地人三极之体而诚之至焉。虚者,太虚也,以天言之;寂者,至善也,以人观之;知者,贯通也,以成物也,以地论之。虚空者,佛家之超越;至善者,儒家之根本;自然者,道家之旨趣。然阳明从大道之全出发,认为兼取释道之说便不是,儒家之大道本与天地民物同体,何物不具,何理不摄,故说“儒、佛、老、庄皆吾之用”。若儒家之道不能涵盖佛老之理,“与二氏成二见”,便是见道不全,执滞一端,自私小道[1]1289。
“在天成象”者道之动也,就阴阳二气之象而言,乃分阴分阳、有动有静者。与之相应,阳明则谓“其虚灵明觉之良知,应感而动者谓之意”即“意”者“知之动”。此“意”便是“阴阳二气”,故阳明说:“有善有恶者,气之动。”[1]29“意”之“能用”亦有多义:“分善分恶”是其分别义;“有善有恶”是其和合义;“可善可恶”是其转化义;“能善能恶”是其趋向义。如果说“本态”是“本然”,那么“意态”可称“或然”。
“在地成形”者道之著也,就刚柔二质而论,乃天地位而万物形者。与之相应,阳明之“物”也就是“心”之“著”,是形质已具,故说是“一定善,一定恶”。所谓“意以象尽,象以言著”即“言以尽意”,由此,“言”是“意”之“尽”。同理,阳明之“物”亦是“心”之“尽”,即良知本体的真正实现,由理想而现实,由应然而实然。虽阳明强调“一念发动即是行”,要人在“意”上做工夫,但意念之善恶毕竟不是事实而是可转化的,因可转化所以才有做工夫之必要,只有落实在物事上才是成形。由此,亦可称良知之物态为“定然”“实然”。
有学者认为,阳明所谓“物”是“意向对象”“意识指向”“意识对象”“良知外化”。这些解释或许是“科学的”,然本质上却是物我有对、两分对立的思维方式,终与阳明“心外无物”之旨似隔一尘。须明白阳明之“意”与“意向”、“意识”并不是等同的二个概念。良知摄尽一切,何尝有一物能超乎良知之外?又何来“外化”“对象”?若依此解,阳明应说“物”是“意之所指”或“意之所向”,然阳明却释之曰:“意之所在”“意之所用”“意之所着”“意之所著”“意之涉着处”[10]77。言虽不同,其意则一:既有显现、显发、显著义,更有下落、成就、结果义,一如“春根夏苗秋着子”之“着”。
综上,心意物三态便是良知之妙应随缘,是心体之应感而动、顺时而化,是良知之节目时变,乃就其大化流行而论。意-象-言便是其内在结构,象者意之显,言者象之著。以体观之,三态各别而莫非一心,此虽三而一;以用观之,同为一心而三态各异,此虽一而三。此三者相即不离,互通互摄,一以贯之。以心观之,意者心之动,物者心之著;以意观之,心者意之体,物者意之用;以事观之,心者事之本,意者事之始,物者事之成。故从三态中任一出发皆可一以贯之而统摄余二。然此三态无非一个良知而已,故以良知观之,心者知之体,意者知之动,物者知之成。故阳明说:“但指其充塞处言之谓之身,指其主宰处言之谓之心,指心之发动处谓之意,指意之灵明处谓之知,指意之涉着处谓之物。只是一件。”“只要知身心意知物是一件。”此即“即体而言用在体,即用而言体在用,是谓体用一源”[1]91、90、31。
三、知行合一与工夫三法
三性乃揭示良知本体;三态是彰显良知流行;三法则展现致知工夫。此三者层层深入:由本体而流行,由流行而工夫。故“致良知”是阳明整个哲学的贯通,是本体与工夫的融会,是其思想真正圆熟的标志。为此,阳明“致良知”的工夫论最为圆融、最为简易,也最为复杂,故而也最难理解、最难表述,同时又最能体现阳明哲学之精神与宗旨——知行合一与圆融浑沦。阳明工夫论之要,可一言而尽,曰“致良知”,故说:“致良知是学问大头脑,是圣人教人第一义”,是“真圣门正法眼藏”[1]71、1279。致良知工夫乃彻上彻下:彻上者,复得本体完完全全;彻下者,扩得良知充天塞地,直止于万物一体而无一物不得其所。前者是体认,后者是扩充。具体而言,致良知之要有三:一是合着本体,二是意上立根,三是不离事物。阳明工夫论之难,则在其圆融浑沦。圆融浑沦者,非一非异,相即相入,一三三一也。其工夫三法之一三三一既是正心、诚意、格物三种工夫的熔融,也是本体、流行与工夫的一体。
其一,“正心”。所谓“正心”,乃就本然上说,重一个“悟”字。“正心”工夫之要有三:一是“合”,即“合着本体”,阳明强调说,“合着本体的,是工夫”,“合得的便是,合不得的便非”[1]1167、93;二是“减”,即“做减法”,故说,“吾辈用功只求日减,不求日增”[1]28;三是“顺”,即顺应良知之自然天则,故修行工夫便如饥食渴饮、困来即眠一般。
正心并非说本体有正不正,心即性,心即理,莫非纯粹至善、大中至正。故说,“至善者,心之本体。心之本体,哪有不善?如今要正心,本体上何处用得功?”[1]119既然本体上用不得工夫,那么何由正心?阳明说:“不要着一分意思,便是心体廓然大公,得其本体之正了。”[1]99由此,正心工夫便是“不着一分意思”,与本体之廓然大公相应。故正心乃就“去蔽复明”而言,一如云雾遮天蔽日,正心便是去其云,散其雾,复见天日,显此良知,此亦所谓“明明德”。故说:“着实致其良知而无一毫意必固我,便是正心。”[1]83欲除其私而去其蔽,岂能无心?须用心著力,方显虚无本色。故正心也就是除妄去蔽,只一个“减”字,与“损之又损”异曲同工。
然减损去蔽只是正心之有心有为一面,还有自然无为的另一面。用心著力、有心有为,意在“减”,与本体之“廓然大公”相应;不须著力、无心无为,则意在“顺”,与本体之“自然灵明”相应。故阳明说:“久久成熟后,则不须著力,不待防检,而真性自不息矣。”[1]123但无论工夫之“减”与“损”都不能忘却宗旨所在——良知本体。减者,旨在超越以悟道;顺者,旨在因顺以行道。为此,阳明强调说:“天理原自寂然不动,原自感而遂通,学者用功虽千思万虑,只是要复他本来体用而已,不是以私意去安排思索出来。”[1]58良知本体,原自寂然不动,原自感而遂通,本自灵明自在,本自生生不息,故说:“吾儒养心,未尝离却事物,只顺其天则自然,就是功夫。”[1]58如果于良知本体之自然灵明、真性不息上勘不破,那在正心工夫的理解上便难免“着”而不通。为此,若将“致良知”之“致”诠释为“推行”“使之”,便是“助长”之病,阳明所谓“引犬上堂”“添燃一灯”。此节一失,全盘皆错,难免以心治心、先污后洁,失却虚无本色,工夫反为本体障碍。
至善良知不可无,言心体之有,如空瓶之瓶也;意必固我不可有,言心体之无,似空瓶之空也。工夫之有无却与之相反相应:“工夫之有”合“本体之无”,乃用心以去蔽,着力以去私,而后方显良知之虚无本色,此便是“做减法”。故说:“有心俱是实,无心俱是幻”,此时之工夫乃对本体之超越性、形上性说。“工夫之无”显“本体之有”,乃因顺自然,不着意在,而后能彰本体之自在灵明。阳明《答人问道》诗云:“饥来吃饭倦来眠,只此修行玄更玄。说与世人浑不信,却从身外觅神仙。此正是“无心俱是实,有心俱是幻”,此时之工夫则对本体之自然性、未发性说[1]791、124。用心着力,才识廓然大公之体;无心无为,方显自然灵明之性。云开雾散而红日自照,障尽蔽除而大道自彰,私欲剥落而良知自显。诗云:“人闲桂花落”“鸟鸣山更幽”,正表达了此中滋味:心闲无事,方悟大道自然;鸟鸣蝉噪,更显山空林静。
由上,正心工夫包含了“有”与“无”两面:“去私蔽”与“顺自然”,此正与天台所谓“止观”相应。《摩诃止观》云:“发菩提心即是观,邪僻心息即是止。”[11]4a06“止”与“观”,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故阳明说:“止之,是复其本然而已。”[1]25而“观”者正是良知自然流行。若总体观之,本体有“空、寂、知”三性,故工夫亦有“戒、定、慧”三法,如此方完整、圆融。“空”与“止”、“戒”相对,意在除蔽、破执,无意必固我而廓然大公,重在“减损”。 “知”与“观”“慧”相契,本于发趣、道用,原乎自然,重在“现照”。“寂”与“定”“诚”相应,旨在显性、立宗,以良知为真己、主宰,阳明所谓“须是有个深爱做根”[1]3,此亦张载所谓“为天地立心”。若就工夫上看,这便是“定”。无论平澜浅濑,还是颠风逆浪,只信良知之是非,只依良知行将去[1]1278-1288。此即阳明之所谓“信”与“狂”也。只是这个“立定”工夫,要从事上呈现即在形下中见本体,故阳明说:“人须在事上磨,方立得住,方能静亦定,动亦定。”[1]12
其二,“诚意”。阳明所谓“诚意”有二种内涵,以正心为分界,可作如是观:诚意→正心→诚意。为区别此二种“诚意”,称前者为“去有诚意”或“离念诚意”,称后者为“存有诚意”或“正念诚意”。理解阳明之“诚意”,其要有三:一是上悟下达之枢纽;二是正心与诚意之不同;三是人有习心之现实。
阳明说:“为学工夫有浅深。初时若不着实用意去好善恶恶,如何能为善去恶?这着实用意便是诚意。”[1]34由此,“诚意”便是“好善恶恶”“着实用意”。既然工夫有浅深、初时应着实用意,那么可以认为:以着实用意为特征的好善恶恶之“诚意”只是初浅工夫。由上,阳明的工夫路线已然明了:由浅而深,由修而悟,由工夫见本体,即由现实的“意态”渐进于理想的“本态”。正因此,阳明说:“欲正其心在诚意,工夫到诚意,始有着落处。”[1]119显然“诚意”在此处只是“明本”或“正心”的一个初始工夫,旨在“明心见性”之“悟本”,其核心在于“去有之蔽”,故称其为“去有诚意”。
然阳明接着又说:“然不知心之本体原无一物,一向着意去好善恶恶,便又多了这分意思,便不是廓然大公。《书》所谓‘无有作好作恶’,方是本体。”[1]34此正指出“正心”与“诚意”之不同:“诚意”是初浅工夫,是用意;而“正心”则“非初学时事”[1]16,却是无意。若在心体上依然“存个善念”“用意于善”,那此“善”便“横在心中”,遂成“理障”,便是“日光中添燃一灯”,便不再是“无善无恶心之体”。阳明作了个比喻,说:“心体上着不得一念留滞,就如眼着不得些尘沙。些子能得几多?满眼便昏天黑地了。”继而补充道:“这一念不但是私念,便好的念头,亦着不得些子。如眼中放些金玉屑,眼亦开不得了。”[1]124由此,从“诚意”到“正心”乃一重大飞跃:从用意到无意、由离念而无念、自“思虑分明”至“何思何虑”。从“悟本”这一意义上可说:意绝于心地,理显于心源。因此“诚意”核心在于“离念”,故称其为“离念诚意”。
对于利根之人,一正心工夫便足矣,“一悟本体即是工夫”,“人己内外,一齐俱透”,故曰:“若良知一提醒,即如白日一出,而魍魉自消矣。”“有如烈火之燎毛,太阳一出,而魍魉潜消也。”[1]117、219-220、260但“利根之人,世亦难寻,就是颜子、明道亦不敢承当,岂可轻易望人?”若只停留于正心,就将引来二个严重后果:一是“难免失人”;二是“养成虚寂”[1]118。于此,阳明引入了一个重要预设即“不免有习心在”“不能不昏蔽于物欲”。这是从现实出发,其旨在“中人上下皆可引入于道”[1]117*人有习心在之根源自然也在心本身,宗密指出:“但以此心灵妙自在,不守自性”,但是必须明白,此“迷悟凡圣在生灭门”( 《禅源诸诠集都序》,第76-77页)即真妄迷悟、善恶净染并非就“无善无恶心之体”上说,而是就“有善有恶意之动”上论。即人有习心在必须放在阳明的“意”“气”上论。就工夫上说,正因其不守自性,故悟之与修,相间相成,缺一不可。。由此阳明说:“圣人之心,纤翳自无所容,自不消磨刮。若常人之心,如斑垢驳杂之镜,须痛加刮磨一番,尽去驳蚀,然后纤尘即见,才拂便去,亦自不消费力。到此已是识得仁体矣。”[1]146正因其有善有恶而可善可恶,故应知善知恶、明辨是非,进而存善去恶,此即所谓“正念头”,亦即“修”也,此即“正念诚意”也。
由上,此“正念诚意”与前论上达悟本、由修见性之“离念诚意”不同,是知本达用过程,是悟而后修。如果说由修而悟是离念绝意、自有而无,那么由悟而修则是实其心而诚其念,乃自无而有、由微而著。此谓悟修相间,理行相参,解证相须。可见,诚意是工夫的枢纽所在:上可悟本,下可达用。
前文乃就诚意与正心、格物之分别上说。若相通相入观之,正心与格物皆为诚意。“知者意之体,物者意之用。”[1]1193此是三态流行上以意统摄心与物。与之相应,在工夫上则以“诚意”统摄“正心”(致知)与“格物”,这便是“在意上立根”。故说:“工夫难处,全在格物致知上,此即诚意之事。”[1]25综合诚意之悟本与达用双重功能,工夫次第之先后顺序应如此:诚意(离念)→正心(无念)→诚意(正念)→格物(实念)。
其三,“格物”。阳明“格物”之说历来颇受误解,往往道着姓名人不识。阳明好友湛若水(甘泉)与罗钦顺(整庵)都质疑之,认为“格物”与“正心”“诚意”三者义意重复,无非都是“正念头”,而整庵更是批评阳明“沉溺于枯槁虚寂之偏,而不尽于物理人事之变”。这是天大误解,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不明阳明哲学之圆融浑沦,不识格物工夫之“一三三一”。概而言之,格物便是正其不正以归于正,便是为善去恶之谓[1]972。然要得详密,则又须明其分别义与贯摄义。分别义,乃就格物与正心、诚意三者作用之不同而论;贯摄义,则就格物包罗统括三者,贯通整体而言。
阳明答罗整庵少宰书云:
格物者,《大学》之实下手处,彻首彻尾,自始学至圣人,只此工夫而已。非但入门之际有此一段也。……凡某之所谓格物,其于朱子九条之说,皆包罗统括于其中,但为之有要,作用不同,正所谓毫厘之差耳。然毫厘之差而千里之谬实起于此,不可不辨[1]76-77。
以举一含三之互摄观之,格物亦是彻首彻尾,自始至终,包罗统括所有工夫,自然含摄了正心与诚意,故说:“修齐治平,总是格物。”[1]181故此时所谓“正其不正以归于正”,自然同时包罗统括了心意物事,既是正心也是正意,既是正意也是正物。此本非分别义,并不是阳明糊涂。若于此处分别所“正”者究竟是念头还是事物,这种强索才是真糊涂。
以“为之有要,作用不同”之分别观之,正心、诚意与格物三者各有用力处,故阳明亦强调此三者“纤毫不可得而缺焉者”[1]972。阳明指出:“工夫难处,全在格物致知上,此即诚意之事。意既诚,大段心亦自正,身亦自修。但正心修身工夫,亦各有用力处。修身是已发边,正心是未发边。心正则中,身修则和。”[1]25故以分别义观之,格物乃真正落实在行上。如果说正心是潜在的理想,是未发之中,那么格物便是理想的实现,是已发之和。而诚意则是理想与现实之间者,即濂溪所谓“动而未形,有无之间者,几也”[12]17。为此,格物全在“行”字上,是良知心体的运用,是万物得其所之仁的实现,故说格物非影响恍惚而悬空无实之谓,是必实有其事。正由此,阳明说:“只说明明德,而不说亲民,便似老佛。”[1]972、25
若以工夫之整体性、格物之贯摄义观之,格物与正心、诚意又是相即相入者。故说,格物乃是“全其正”而“至其极”,即全乎良知本体之正而达乎万物一体之仁。故“全其正”与“至其极”并非格物之二义,而是格物之贯摄义。《大学问》曰,致良知之修身者,必先正心;正心者,必在诚意;诚意者,必在致知;致知者,必在格物[1]971-972。此便是相即不离的贯通义。正因为“只是一个功夫”,所以阳明说:“就物而言,谓之格;就知而言,谓之致;就意而言,谓之诚;就心而言,谓之正。正者,正此也;诚者,诚此也;致者,致此也;格者,格此也。”[1]1273此乃一即一切,一切即一,是互摄义。
正由此,阳明答罗整庵少宰书云:“若语其要,则修身二字亦足矣,何必又言正心?正心二字亦足矣,何必又言诚意?诚意二字亦足矣,何必又言致知,又言格物?惟其工夫之详密,而要之只是一事,此所以为精一之学,此正不可不思者也。”因举一含三、摄贯一切,故语工夫之要,格致诚正修,任一皆自足,工夫只是一个,总是一般,岂有二乎?然要得详密,三者各有其用而不可得而缺焉,不可混而不分,故曰:“此正不可不思者也。”
由上,致知的工夫论充分体现了阳明哲学的浑沦性与圆融性。正由于其浑沦性与圆融性,故对于工夫论的理解与诠释不可脱离其“立言宗旨”——“知行合一”[1]96,此乃其头脑与总纲,始终之一贯者。龙场悟道次年,阳明便在贵阳书院提出了“知行合一”,自此之后,皆不出乎此,只是对此进行丰富与完善。所谓“知行合一”,阳明明确地说:
知犹水也,人心之无不知,犹水之无不就下也;决而行之,无有不就下者。决而行之者,致知之谓也。此吾所谓知行合一者也[1]277。
水之就下者,知行本体也,良知自然之流行也;决而行之者,知行工夫也,除障开塞,为善去恶,所以复其本然者也。简而言之,知行合一便是本体与工夫的统一:本体就是工夫,工夫就是本体,故说:“知行二字即是功夫。”[1]111这是自然工夫或本体工夫。本体不离工夫,工夫不离本体,故说“合着本体的,是工夫;做得工夫的,方识本体”[1]1167。这是修治工夫。分而言之,则有三个层次。其一,就“知行本体”上说,是本体良知与大道流行的统一,此便是“体用一源”之意。这是良知天理自然之流行,即所谓“理行”,故阳明说:“此已被私欲隔断,不是知行的本体了。”“此便是知行的本体,不曾有私意隔断的。”[1]4-5只要不隔断它,良知自然生天生地,成人成物,如水之就下,自然天则。其二,就“知行工夫”上说,此所谓“行”不是“理行”而是“修行”,指“格物”而言;与“格物”相应,此“知”是指“正心”而言,是“悟”。故仅工夫上说,知行合一便是悟修相资,一内外,合有无。其三,合本体与工夫而言,是“性修不二”之意。所谓“致良知”,便是以良知为明师、真己、主宰、指南针、试金石,只依良知行将去,一切工夫只是复他本来的体用。故阳明说:“天理原自寂然不动,原自感而遂通,学者用功虽千思万虑,只是要复他本来体用而已,不是以私意去安排思索出来。”[1]58
可见,知行合一既是工夫论的前提,也是归宿,故说:“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若会得时,只说一个知已自有行在,只说一个行已自有知在。”“君子之学,何尝离去事为而废论说?但其从事于事为论说者,要皆知行合一之功,正所以致其本心之良知。”[1]4、52这是“理行”与“修行”、本体与工夫的统一。由此,阳明“知行合一”乃将体与用、悟与修、性与修“两端”融会贯通,从而形成了体用一源、悟修相须、性修不二、浑沦圆融的哲学体系。
四、本体工夫与王学三分
或谓阳明后学于本体原无异议而诸家所争实在工夫[13]345。此说或昧于本体工夫:如果本体是哲学观,那么工夫便是方法论。于中国哲学而言,一如阳明所说,“合着本体的,是工夫”,“合得的便是,合不得的便非”。有什么样的哲学观,便有什么样的方法论。工夫是本体的展开与实现,本体是工夫的头脑与根基。由此,王学分化、后学之争的根本,在于良知本体的理解不同,此即所谓“良知异见”。所谓“良知异见”实质便是各人所悟之道不一,故龙溪说,后学同门虽于良知宗说不敢有违,但各以其性之所近,拟议搀和,纷成异见[8]26-27。正由于所悟之道不一,故而有了工夫之争;由于哲学观不同,故而有了方法论差异。
既然王学分化之实质是本体论的差异,是哲学观的不同,故而本体论理成为其派别划分之依据,而不应是工夫论,更不应将本体与工夫混为一谈。同时,后学派别之划分不能离开阳明哲学而论。王学分化是“流”,皆一于阳明之“源”,故划分理应以阳明所悟之道即良知本体为观察点,这是理解、认识后学之背景与框架。若没有背景与框架,也就无法认识;若离开了阳明哲学这一源头,也就无法正确理解。由上,理解阳明后学及其分化应当遵循二个原则:本体与源头,即以本体为依据,以阳明为根源。
如前所论,阳明良知本体有心性气与空寂中三性,流行有心意物三态,工夫有正诚格三法。由此,无论以本体三性还是以流行三态或是工夫三法为视野,王学分化理应是三分格局,故确切地说王学分化便是王学三分。阳明哲学,源也,一也;后学分化,流也,三也。自源而流,便是一而三;自流而源,便是三而一。然而问题也是复杂的:以本体为核心,并不意味着只论本体而舍弃流行与工夫,而是以本体差异察照其流行与工夫之不同;以阳明为源头,也并不意味着以此框架生搬硬套在后学之上,而是以源头为背景彰显后学的发展与变化。然而阳明后学乃一庞然大物,此处非专论阳明后学,而意在由源照流,因流显源;源流相照,终始相印,前后相证。故而舍繁就简,不求全责备。
据《明儒学案》“浙中王门学案五”,当时最盛者有莫过四人,其曰:“阳明殁,诸弟子纷纷互讲良知之学,其最盛者,山阴王汝中、泰州王汝止、安福刘君亮、永丰聂文蔚。四家各有疏说,骎骎立为门户,于是海内议者群起。”[4]329-330而在“江右王门学案四”中有这样一段评说:“阳明亡后,学者承袭口吻,浸失其真,以揣摩为妙悟,纵恣为乐地,情爱为仁体,因循为自然,混同为归一。”[4]437此外,浙中王门胡瀚(字川甫,号今山,年十八从阳明游),对各立门户、异说纷纷则有这样一段评述:
先师标致良知三字,于支离汩没之后,指点圣真,真所谓滴骨血也。吾党慧者论证悟,深者研归寂,达者乐高旷,精者穷主宰流行,俱得其说之一偏。且夫主宰既流行之主宰,流行即主宰之流行,君亮分别太支。汝中无善无恶之悟,心若无善,知安得良?故言无善,不如至善。天泉证道其说不无附会。汝止以自然为宗,季明德又矫之以龙惕。龙惕所以为自然也,龙惕而不怡于自然,则为拘束,自然而不本于龙惕,则为放旷。良知本无寂感,即感即寂,即寂即感,不可分别。文蔚曰,良知本寂,感于物而后有知,必自其寂者求之,使寂而常定,则感无不通。似又偏向无处立脚矣[4]330。
在《明儒学案》中黄黎洲以为,后学之盛者惟“二王”、双江与师泉,而胡今山则不论师泉而论彭山(季本,字明德)。无论黎洲与今山似皆四分王学,然就本体而实究之则三也。阳明后学之所以能自立门户而异说纷纷,根本就在于他们有各自的本体论即哲学观,此即所谓“显性立宗”。但是,这些各具特色的本体论又无一不是源自阳明,故龙溪曰,他们于阳明良知宗说不敢有违,但却俱得其说之一偏,并以各自所理解的良知说评判诸家。
既然如此,我们亦以我们所理解之良知说观察、评判后学。也正由此,我们对阳明后学的观察乃以本体为核心,以阳明为源头。阳明本体具有心性气与公寂中即“空寂知”三性,即廓然、寂然与自然,此三者互收互摄、举一含三。就逻辑观之,有三种可能:以“空”摄“寂知”、以“寂”摄“空知”、以“知”摄“空寂”。此三者正是阳明后学展开的内在逻辑和本体依据,故而也是王学三分之理论依据。
其一,以“知”摄“空寂”。此即阳明以良知自然为本体,统摄廓然与寂然。由自然灵明故,有贯通性;由贯通性故,有普遍性;由普遍性故,有当下性。由此,泰州学派从自然性、本觉性与当下性出发,宣称:日用即道、自然即天理、凡夫即圣贤、良知现成,故力倡“率性而为”“自然顺适”“现成自在”。由此胡今山称“汝止以自然为宗”,而龙溪之“直心以动,无不是道”所实指,并斥之为“凌躐之病”。在罗近溪看来,生活日用之中最根本的便是“赤子之心”,是“孝弟慈”的亲亲之爱,故建构出以“赤子之心”为核心,实质是亲亲之爱的仁本论。此便属于黎洲所批判的“情爱为仁体”。由日用即道,李贽便自然可得出这样的观点,“穿衣吃饭,即人伦物理”[14]8;由直心即道,李贽便将“赤子之心”等同于“童心”,从而建构出以自然真心为实质的“童心说”。
其二,以“空”(即“虚无”)摄“寂知”。此即龙溪以无为道、无念为宗,虚无为本,故曰:“空空者,道之体也。”[8]132但龙溪所谓“无”“虚”“空”都是含寂知、寂照者,故说:“予谓虚寂者,心之本体。良知知是知非,原只是无是无非。无即虚寂之谓也。” “良知不学不虑,寂照含虚,无二无杂。”[8]464、273以其“空无”,故称“虚体”;以其“未发”,故谓“寂体”;以其“灵知”,故名“灵体”。[8]227、78、214阳明所谓“虚无”是从太虚之气上说,同样,龙溪也如此,故曰:“其气之灵,谓之良知,虚明寂照,无前后内外,浑然一体者也。”[8]182
其三,以“寂”摄“空知”。寂者,天理之性也,故此一派多以性理为核心融摄心与气,而于“公寂中”三用各有侧重,于是又一分为三。合性与寂为一者,主张性寂说,如双江;合性与灵为一者,主张性灵说,如塘南;合性与公为一者,主张性虚说,如师泉。至于彭山则多承袭朱子理气二分说,《明儒学案》云:“先生之学,贵主宰而恶自然,以为‘理者阳之主宰,乾道也;气者阴之流行,坤道也。’”黎洲评曰:“先生之理气非明睿所照,从考索而得者,言之终是鹘突。”[4]271而胡今山则以之和泰州相对,二个极端:一则放旷,二则拘束。
综上,王学的三分格局可以从本体、流行与工夫三方面观之。以本体观之,三派各有所立:龙溪立于“空”,双江等立于“寂”,泰州立于“知”;以流行观之,三派各有所重:龙溪重“心”,双江等重“意”,泰州重“事”;以工夫观之,三派各有所主:龙溪主“悟”,双江等主“修”,泰州主“证”(或觉)。在阳明那里,形上形下、本体工夫是差异的同一,存在着合理的张力,所谓“不离日用常行内,直造先天未画前”。阳明之良知有心意物三态,是一种圆满的形态,故说:“谓日月风雷即天,不可;谓人物草木不是天,亦不可。”[1]21于此,阳明在天泉证道中便对绪山与龙溪谆谆告诫,二君之见正好相资相取,不可各执一边;若执定一边,便于道体各有未尽,切不可失了其的宗旨[1]117。但是“执定一边”、见道一偏正是后来王学的分化的路径,不能不令人感慨。
五、余论
知行合一是阳明之立言宗旨、一贯之道、头脑总纲,是本体与流行的一源,正心与格物的交融,本体与工夫的一贯,而良知浑沦则是这一切的根本所在。浑沦者,摄贯一切,圆满自足。龙场悟道,所悟所觉不过“吾性自足”;忠泰之变后,所揭所信亦为“良知无不具足”;至其55岁,答南元善所示所教不出“良知之昭明灵觉,圆融洞澈”[1]1228、1278、211。故就特质上说,良知之学便是浑沦之学,舍浑沦无以明良知。故阳明说:“良知底用安排得?此物由来自浑成”,“白头未是形容老,赤子依然浑沌心”,“人人自有,个个圆成”,“不假外慕,无不具足”,“完完全全,增减不得,不假修饰”[1]785、790、31、37。由此,“浑沦”实乃良知本体之根本特征,阳明哲学之核心精神。
由本体浑沦,故而简易直截,洞见全体;然亦由本体浑沦,故而难以理解,不易表达。于阳明则不得已与人一口说尽,于学者则苦于无入头处。[1]1575为此,阳明在《别诸生》一诗中指示曰:
绵绵圣学已千年,两字良知是口传。欲识浑沦无斧凿,须从规矩出方圆。不离日用常行内,直造先天未画前。[1]791
浑沦者,规矩也,良知也,本体也;方圆者,圆融也,思维也,结构也,方法也。浑沦者道之体,方圆就道之用。由“体用一源”故,本体浑沦性与思维圆融性二者相通相应。思维者,结构之微;结构者,思维之显。由“显微无间”故,思维圆融性即结构整体性。由“象生于意”,故本体浑沦性必然表现为思维圆融性与结构整体性,故说“须从规矩出方圆”;由“象以尽意”,故惟思维圆融性与结构整体性方识本体浑沦性,故说“欲识浑沦无斧凿”。换言之,舍圆融思维、与结构整体性别无善法,其余皆为斧凿,难免陷于枘方圆凿之困境。如前所论,一三三一是阳明哲学内在的思维-结构,而一三三一亦即∴,故阳明称其为“方圆”。方圆者,莫非象也。由此,便形成了本体(意)-结构(象)-诠释(言)这一融贯圆通的一三三一结构,亦即意象言结构。可见,阳明所谓“欲识浑沦无斧凿,须从规矩出方圆”,已明显具有了本体论与方法论的双重含义,彰显了本体、思维(结构)、方法的统一。
以本体论观之,意象言结构在阳明哲学中体现为心-意-物三态流行,三态者不过本体之“节目时变”。故阳明说:“即体而言用在体,即用而言体在用,是谓体用一源”;“未发之中即良知也,无前后内外而浑然一体者也”,“未在已发之中,而已发之中未尝别有未发者在;已发在未发之中,而未发之中未尝别有已发者存”[1]31、64。体者,未发之意也;用者,已发之象也。以意观之,意中有象;以象观之,象中有意。意之与象,浑然一体者也,故阳明谓,良知浑沦。
事实上,整个中国传统哲学亦如是。以内容观之,本末源流、未发已发、有无显微、性相体用,不外“意”之与“象”;以特质观之,由“体用一源,显微无间”故,意之与象,相即相入。意不离象,象不离意;意中有象,象中有意;以形态观之,由内容之意象性与特质之意象性,自然表现为形态的意象性。由此,无论内容、特质,还是形态,中国传统哲学只“意象”二字便括尽无余,故称其为“意象哲学”。
以方法论观之,只有思维圆融性与结构整体性方能与本体浑沦性“打得对同过”。故于理解而言,中国哲学之本体,只有置于其自有之思维-结构中才能获得全面的理解;于诠释而论,唯有藉思维圆融性与结构整体性方能彰显本体浑沦性,浑圆之学必由整体观照方能全其精神,透其大义。此谓“尽意莫若象”“寻象以观意”,故这种诠释方法便是以“寻象”为切入点,以“尽意”为宗旨的方法,即缘象以尽意,为此,称其为“意象诠释”。这也是由本体与方法的同一性所决定的,乃与“意象哲学”相应者。
所谓“意象诠释”,就是以意为本源,象的中介的诠释。它不是以概念-命题为核心,而是以思维-结构(象)为核心,通古今而一内外,联结言意本末,融合哲学观与方法论,强调本体-思维(结构)-方法三者的一致性,突出本体的浑沦性、思维的圆融性与方法的整体性,从而彰显出“体用一源,显微无间”这一中国传统哲学的民族性。思维-结构的同一性与贯通性是意象诠释客观性的保障与依据。
如果说概念思维是强调“排中律”的确定性思维,那么圆融思维则是突出“取中律”的灵动性思维。故欲明方圆之法,须先识取中之道。于此,阳明说:
孔子有鄙夫来问,未尝先有知识以应之,其心只空空而已。但叩他自知的是非两端,与之一剖决,鄙夫之心便已了然。鄙夫自知的是非,便是他本来天赐,虽圣人聪明,如何可与增减得一毫?他只不能自信,夫子与之一剖决,便已竭尽无余了。若夫子与鄙夫言时,留得些子知识在,便是不能竭他的良知,道体即有二了[1]112-113。
所谓“取中”便是《论语》之“叩其两端而竭”,故阳明说“叩他自知的是非两端”。这并不是阳明于识取良知有两法,取中便是圆融的基础,没有取中便没有圆融。而“取中”并不是不要两端,相反两端是取中的基础、前提,惟有叩其两端且至其极,阳明所谓“竭尽无余”,方能取其中。为此,宗密指出:“至道归一,精义无二,不应两存;至道非边,了义不偏,不应单取。故必须会之为一,令皆圆妙。”[3]23综上,圆融者,非一非异、不离不外、相辅相成。实则虚之,虚而不空;虚则实之,实而不固。寂则动之,动而有则;动则寂之,寂而能感。方则圆之,圆而不流;圆则方之,方而不滞。由此,将有无、动静、虚实、方圆熔为一炉。
意象哲学与意象诠释对于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学科之发展具特别之价值。从意出发的哲学观,强调哲学的抽象性,认为许多少数民族没有哲学,从而质疑这一学科的合理性;从象出发的哲学观,强调哲学的文化性,甚至认为文化即是哲学。然从意象哲学出发,由意象不同故,民族哲学不是民族文化;由意象不二故,民族哲学不离亦不外民族文化。民族哲学,道之体;民族文化,道之用。其之为道,一也,民族精神也。以意象哲学观之,浑沦性、圆融性与意象性便是中华民族之精神,而这也正决定了中华民族具有稳健的性格。
参考文献:
[1]王守仁.王阳明全集 [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2]钱穆.阳明学述要[M].北京:九州出版社,2010.
[3]宗密.禅源诸诠集都序[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8.
[4]黄宗羲.明儒学案[M].北京:中华书局,2008.
[5]高振农.大乘起信论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2.
[6]朱谦之,撰.老子校释[M].北京:中华书局,2000.
[7]秦家懿.王阳明[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
[8]王畿.王畿集[M].南京:凤凰出版社,2007.
[9]楼宇烈,校释.王弼集校释[M].北京:中华书局,1980.
[10]吴震.王阳明著述选评[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11]智者大师.摩诃止观(卷一)大正藏(T)第46册No.1911 [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12]周敦颐.周敦颐集[M].北京:中华书局,2009.
[13]劳思光.新编中国哲学[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14]张建业,张岱.李贽全集注(第一册)[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