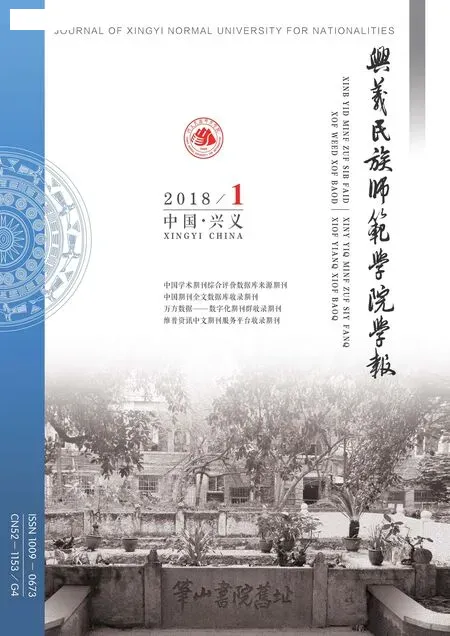小角色与侗戏的当代传承
——基于侗族戏师口述的调查与分析
黄守斌
(兴义民族师范学院,贵州 兴义 562400)
传承是侗戏当下面临的最大困境,这是戏师的困惑,也是学界的关注。为改变这一现状,普虹、吴定国、梁维干、吴国夫、吴贵元等都关注着侗戏的当代命运。他们一生与侗戏为伴,并较为深入地对侗戏进行研究,较为一致认为对侗戏剧本、音乐、“八字步”进行改革,侗戏才会有明天。而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侗戏传承人的张启高、吴胜章、吴尚德,三者分别善表演、善编剧和善音乐,都不计个人得失全力组织戏班的演出。他们为侗戏的传承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可是他们忽略了极具表演性质的小角色丑角。
因为丑角是侗戏生命的内动力,为侗戏困境突围的一把钥匙,关联着侗戏的当代命运。通过丑角的舞台表演的合理炫张,侗戏在表演方面多有了“戏”的本质,至而为自己族群的民歌注入了“娱乐”气象和体悟的深刻,为“歌”向“戏”的生发修筑基础性的台阶。侗戏丑角的集中发力,也许就是侗戏传承发展的一个基础所在,也是无专业剧团的村落戏剧突围的核心智慧。在正角与丑角聚合的整生图式中,[1](P210)重构侗戏的文化生态,有助于生发侗戏更为强健的生命力,为侗族文化的集体出场提供一个宜态的场域,从结构上体验侗族文化的整体性魅力。
一
侗戏是一种较为特殊的戏,其中之一是戏师中心制。戏师从剧本的创作、排练到演出的组织乃至登台演出,都是最为核心的和关键,所以对于角色等戏剧文化的理解和阐释也是最具代表的。他们认为侗戏在行当上仅有正角和丑角之分。其中具有共性的是,正角为善良、勤劳、忠诚、勇敢等寄予美好人性的正派而严肃的正面人物,并且戏份较多常为一簇戏的主要角色。
丑角有的村落戏班称之为“Nahganl”(那干),有的村落戏班叫“Nahwal”(那花),有的直接用汉族丑角称呼他,只是与汉戏丑角在本质和内涵上存在差别。侗戏丑角在类型上有三种:一种为笑丑,是喜剧中逗人发笑或是戏中调节气氛的角色,主要运用的表演策略是幽默和滑稽,外在表现为形之怪、言之谬、动之迂;另一种为恶丑,是从人物的道德层面上所作出的一个角色类别,其判定的标准是演员所演剧中人物的所作所为不符合伦理道德的规范,给代表人类正义、美好人性的正角带来灾难与不幸,主要在侗戏悲剧中出现。第三种为正丑,正丑最为复杂,其内在本质和外延的确定也比较模糊,概括起来主要是社会地位卑微心地善良无心使坏的戏剧配角。
村落是侗戏展演的生态场,村落戏班对正角和丑角的阐述也不是完全的一致,丰富性和多样性是其特征,至而也使我们难以用比较精准的概念和原理对其进行归纳、定义。吴文彩的家乡黎平腊洞村目前还是主要根据其作品进行角色分类,像梅魁、梅良玉、李旦等代表正面人物为正角,卢杞就是丑角的代名词。丑角用得最多是在恋爱戏中,扮演恋爱的破坏者以丑角扮。细心分析腊洞的传统剧目,几乎没有笑丑这一丑角,至于正丑他们把他归于群众演员了。从江龙图贯洞对正角和丑角本质内涵的理解与上述一致,其特殊性在这里的正角和丑角只是针对男演员而言,丑角在这里称之为”Nahganl”(那干),那干直译是花脸的意思,但是与汉戏的花脸在本质内涵上是有明显的区别,也包含笑丑、恶丑、正丑三类只是没有这一叫法。直至目前戏班中女性演员尚无角色行当的说法。从作为本地演出的第一部剧目吴宏干的《金汗》,其历史几乎于侗戏这一剧种的产生同龄,从侗戏的盛行以及侗戏的贡献来说,龙图贯洞是名副其实的戏窝,六十年前本地侗族女演员就走上了侗戏舞台,而其角色习惯还是沿袭没有女演员的年代的称呼。是否这就是民间侗戏角色划分法的原生地,因无文献记载尚难以考证。
二
村落对丑角有着他们的自己的阐述方式,也意识到戏剧也需要这样一个角色,但是配角的地位使丑角没有得到应有的地位和重视。侗戏是以戏师制作为核心的戏剧,戏师是戏剧的灵魂与核心。那么戏师对丑角的关注如何?戏师侗语称“Sanghxik”(桑戏),桑戏是剧本的创作者和传承者,戏班的组织者和领导者,编排和演出的导演,戏台上的演员。他们对侗戏的理解可以说是最为真切和深入的了。在笔者近十年的田野调查中,从国家级侗戏非物质文化传承人张启高、吴胜章、吴尚德到村落公认的著名桑戏梁安敏、吴秀华、秦文璋等,对于丑角他们比较一致的看法是配角,难以或是很少能作为侗戏戏班的台柱子,正角的重要性远超丑角。笔者认为主要的原因在戏师的前身几乎都是歌师,不是歌师而作为一个纯粹的戏师那几乎是不可能的。从历代的著名戏师吴文彩、吴宏干、梁绍华等到现在的张启高、吴胜章、吴尚德等,都是当地有名的歌师。戏师与歌师的一体共在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歌与戏的联姻,侗戏成了歌化的戏,侗戏演出有明显的特征“戏台行歌”[5]的倾向性。正角歌唱的重要性和在时空上的所在的比例一定程度上遮蔽了丑角表演的特殊意义与价值。编戏类同编歌,演戏如同唱歌。《戏师传》中说道:“吴文彩,读过好多汉文书籍看过许多汉家戏。他心中苦闷,硬是不服这口气。为何我们侗家没有戏?我们的琵琶歌那么动听,我们的牛腿琴歌那么悦耳,我们的笛子歌那么悠扬,我就不信编不出戏……《珠郎娘美》歌一本,梁绍华他把嘎锦细啃慢嚼变成戏……贯洞大寨吴宏干,他拿金汉长歌来改戏……高增有个吴昌华,歌才哄得天上雁鹤飞落地,名声传到丙妹城,相公秀才也称奇……”可见对戏师来说歌是戏的基础的基础核心的核心,至于以表演为其特别的丑角被列在了核心之外,以致为戏班的边缘了。1984年黔东南州举办了第一届侗戏调演中,《蝉》、《善郎美娥》、《丁郎龙女》的出现,使人感到振奋和喜悦。“《蝉》发掘侗戏深层内涵中的民族文化的优势,广采博收其它侗族艺术精华,吸收侗族大歌等多音部唱法,以情动人,以歌动人,来重新构成自己的艺术优势。”[6](P143)“以歌动人,来重新构成自己的艺术优势。”间接道出丑角的边缘性地位。戏师从歌出发,淡化了行当表演的同时也冷落了丑角。
丑角演员对丑角的经验体会是更具代表性。丑角演员多是因为其貌其行或是不善歌而被选作丑角,固然是不得已而演之。女性演员对丑角的排斥程度更高,因而丑角成了男演员的专利,直至上世纪九十年代这一状况才有所改观。贯洞戏班演员陈爱行是三江贯洞大寨戏班的一员,以演“陈世美”闻名。年纪轻轻他有了“贯洞陈世美”的俗称。人生大事找对象就因有“贯洞陈世美”而成了基于演丑角而带来的障碍。如他已是三江著名的琵琶歌手兼木匠师傅,每每与其提起这段“陈世美”的戏台经历。陈师傅常常送以微笑或是保持沉默。倒是其妻爱说爱笑,她所说的:“‘我的陈世美’只是长相一般,心还是很好的,她们不嫁我就嫁给他了。”这一句话不长,其意味是无比的深长。从外在的长相到内在的心灵这一份对丑角演员的误读有几人会热衷于丑角演员呢?丑角虽然是侗戏审美性的心情情愫的直接营造者,但是从根上它还是与“丑”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故而演员不敢、不想也不愿演丑角,成了具有普遍性的情绪。简言之,具有主体性的丑角演员默认了“我丑所以我演丑角,”这是没有情感热度的无奈选择,没有一定的承受能力是难以承担这一角色的扮演。这样的例子很多,限于篇幅不在列举。
戏民作为剧场的最大主体,他们聚集于戏台下首要的理由是娱乐,体悟的深刻主要是来至娱乐的不经意中的收获。他们是爱看丑角的表演,对于其中逗乐式的滑稽语言与动作很是喜爱。但是如果要他自己演丑角,他又是不情愿的。在他们心理这一角色有的虽是好笑,并很有趣味,但是从语言动作舞蹈装束来说是丑的,并且认为丑角是不重要的配角,是正角的陪衬而已,一簇戏的成功与否主要看正角的唱得如何。从黎平的腊洞、地扪、岩洞……,到从江的龙图、贯洞、小黄……,到三江的八江、贯洞、高亚……,到通道的皇都、新寨、独坡……戏民和戏班对丑角较为一致的看法是戏份少不是戏班的重要的角色,用个比喻就像菜里放的味精,仅作佐料而已。对于丑角中的恶丑,那是更是难以接受,有的戏民甚至说为什么要有那么一个令人心情苦痛的角色,大家本来去戏场就是为了放松放松,寻找乐趣,可是结果却泪流满面,不欢而散。他们没有理解这正是戏剧的魅力所在:痛苦的快乐。戏剧不仅仅是娱乐,也收获这深刻的体悟。
三
戏师、演员、戏民到戏班,在认识层面丑角是一个倍受冷落的角色,而在演出之际尤其是戏剧的高潮丑角又成了激发情感的核心焦点。听腊洞老人讲,侗戏祖师吴文彩带戏班在外村演《梅良玉》,扮演奸臣卢杞的演员被戏民当场吐口水解恨,谩骂之声很是难听,至而戏后的“劝戏”成了文彩戏班的必修课。散戏后“抢演员”到家休息吃饭,正角、乐师以及群众演员一抢而空,而扮演丑角的演员,越是演技好能把丑恶人物演活的,多是无处可去,只有曾经演过丑角的村民喊上几个“丑角”,在“理解万岁”的共同经历的共鸣中回忆曾经相似的经历。难以想象侗戏“同时天涯沦落人”的戏外之悲剧,在生活的实际中还会如此延续,对于扮演恶丑类型的丑角,他们在台上的虚拟性的凶恶在现实中得到真实的“回报”。更有甚者是吴文彩带戏班在梅寨演出《梅良玉》时,那个寨子的人从未看过戏,一青年看到卢杞如此谄害梅家忠良,竟以戏为真,情绪失控,持刀上台将卢杞的扮演者砍死,以致引发一场款约无法界定的官司,政府当局立即禁演《梅良玉》。吴文彩以忘我的精神历经三年的疯疯癫癫写下《梅良玉》,在腊洞首演却无人愿演丑角卢杞。侗戏祖师爷吴文彩上台扮奸臣卢祀,演得活灵活现。台下乡亲都是第一次看侗戏,有个莽后生看到好人遭奸臣欺侮,跳上台去要打文彩。急得培闹大声呼喊:“那是文彩师傅呀!打不得呀!他是好人呀!”
吴宏干(1779-1839年)五十岁带着两个儿子到八洛开荒。年老力衰加之家境贫寒生活很差甚至连饭都吃不饱,他每天拖着疲惫的身体一边挑土开田,心却在编《金汉》一剧。日复一日,整个心思都在故事里,他也就变得整天不说话了。有时挑着土到田边没有倒,又挑了回来。大伙觉得奇怪,家里人也以为他精神有了问题,请鬼帅来看“米挂”。他舅舅听说鸿于傻了,拄着祸杖前来探望外孙,此时宏干才不得不说话。他也因为说了几句话打乱了思路,一下就忘了几十首歌。宏干编完《金汉》到鼓楼传唱,遭到村里几个大户人家的反对。后来吴宏干只好带着戏本《金汉》离开家乡从江贯洞来到黎平佳所,排演《金汉》,故而《金汉》的首场演出在黎平佳所。后来贯洞有人来到佳所砍木头,到了年关下起大雪,难以回家过年,看到佳所演出《金汉》。这几个贯洞人纳闷《金汉》故事本是自己村的,不知这戏竟在这里上演,问了才知是自己村里的吴宏干来教的。吴编了《金汉》后,本想在本村排演《金汉》,但是《金汉》故事主人还在,并且家大业大很有势力,要想《金汉》能在本村演出是不可能的。其中的秘密就是因为戏中丑角人物,与地主有着类似的历史故事。这与丑角对号入座的热度影响戏剧的文化生态。
梁绍华(1893~1978)所编的《珠郎娘美》,仅在1917年就演出了四十余天,取得了空前的成功,因其有反地主而一度被地主恶霸禁演。[3](P24)不是当时的侗族地主恶霸不喜欢侗戏,而是戏中的丑角人物为他们不能接受。在1920年,从江龙图新安的陆克强、梁卜先娇顶着的压力分别扮演丑角银宜和蛮松,他们基于对侗戏的热爱演上了他们自己也不喜欢的角色。1955年三江林溪侗剧团吴岩美扮演吴居敬改编的剧作《秦娘美》中丑角银宜,几十年中难忘自己演过银宜,本着对侗戏的爱他演了别人不愿演的银宜。三江林溪戏师杨平义演过丑角银宜管家,一说起这段经历,他都不太愿意多谈,其中奥秘只有演过丑角的演员才能体会。
值得深思的是银宜同为侗戏《珠郎娘美》和黔剧《秦娘美》的极为相似的丑角,可演员命运却完全不同。贵州省黔剧团1959年把侗剧《珠郎娘美》改编为黔剧《秦娘美)》作为国庆十周年献礼节目到北京演出,得到好评,她第一次向全国介绍黔剧这一剧种。一部《秦娘美》写下了黔剧艺术的最高峰,直至今天还是一座难以超越的黔剧艺术巅峰。2012年6月29日,中国贵州省黔剧院仍以《秦娘美》赴澳大利亚墨尔本参加“2012年墨尔本中国戏剧节”。从1960年6月贵州黔剧团带《秦娘美》于6月11日在民族文化宫进行了首场演出后,在7月1日到中南海怀仁堂为朱德、陈毅、叶剑英、罗瑞卿等中央首长演出,《秦娘美》轰动了首都文艺界,郭洙若、梅兰芳、欧阳予倩、马少波等观看演出后,或发表文章,或题词,予以高度评价。余重骏的名字与剧中的“坏人”——心狠手辣的地主银宜,从此走进千家万户。当时的外交部长陈毅元帅看完演出后,高兴地上台接见全体演员,他握着余重骏的手问:“你今年多大了?”余重骏回答:“十七。”陈老总说:“17岁的娃娃能演地主,演得好!演得好!国务院请你们吃饭。”梅兰芳在《大众剧场报》上撰文称“演银宜的余重骏才十七岁,把无恶不作的地主刻画得淋漓尽致。”著名戏剧家欧阳予倩也发表文章赞扬:“扮银宜的演员才17岁,学戏时间不过两年,但他能够恰如其分地表达角色的性格和感情,十分难得。”1961年,黔剧《秦娘美》被上海海燕电影制片厂搬上银幕,余重骏扮演的地主银宜给全国的电影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珠郎家象蛤蟆毛都没有,你跟他吃尽苦哪天才出头?”他的这代表唱段让观众耳熟能唱。当时在贵州文艺界,“银宜”几乎成了余重骏的别名。四十多年后的今天,一些长点年纪的观众见了他还亲切地称呼他为“银宜哥”。[7](P151-152)只是可惜的是在侗区村落,很少有人知道黔剧《秦娘美》。
黔剧的丑角是“喜剧”而侗戏的丑角是“悲剧”。侗戏从演员到戏师丑角是他们演出经历的一个痛苦的心结,主要在戏民对丑角人物中丑角演员过热反应,冷却了丑角演员对于丑角的热情,特别是对于作为村落戏剧的侗戏,演员几乎是没有报酬。善待丑角给予丑角一个宜态,还原侗戏“真善美”的舞台影像生态,确实需要学界、戏师、戏民的大力支持,如今侗戏丑角的生存生态虽有了很大的改善,但是需努力,尤其是在认识层面给予丑角一个应有的重视。
四
丑角表演的较大的自由性,突出演员的主体能动性,既为戏师减负的同时,也为侗戏减轻了排演的难度,增加一簇戏的丰富性,有助于缓解戏师的历史的面面俱到带来的面面难到的历史困境。丑角表演突出宾白和动作,宾白与生活的对接提升了戏剧魅力的同时也有助于缓解“难听懂歌”的当下的历史现实,尤其是对于当下不进歌堂进学堂的侗族后代。丑角动作的变形与夸大与正角所需的舞蹈的程式化和精致化相比较,前者的完成是较为容易并且带来的效果不亚于后者。故而后者在歌,突出歌的精致化,前者在演突出演的戏剧化、喜剧化乃至悲剧化。丑角是侗戏中特别的部分也是重要的组成,丑角有助于侗戏戏剧本质的生发,而这需要构建一个有利于侗戏丑角生长的村落文化生态。
不可否认,在戏剧危机的时代,侗戏也步入了危机的时段。戏师、侗戏爱好者、学者乃至政府都在思考,如何能够让侗戏这一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活在人们的生活之中,传承和发展成了最大的诉求和焦虑,可是遗憾的是,大家的关注的重心主要局限于剧本和音乐以及政府如何进行扶持,或者是利用侗戏进行旅游开发,这些是都很重要,可是忽略了侗戏最为核心的两个要素:其一侗戏是表演的艺术,其二侗戏是侗族戏民的戏剧。这对少数民族戏剧侗戏的“切脉”,建立在望闻问切的“田野基础”,目的就是更好地更为科学的“开方”,以期侗戏在黔湘桂的侗寨中换发时代的新生命。
这不仅是侗戏的问题,也是陷入困境中的少数民族戏剧的共同关注,这也许还关联着中国戏剧的未来走向和命运。
参考文献:
[1]袁鼎生.生态艺术哲学[M].北京:商务出版社,2007.
[2]吴琼.侗剧调查札记[A].中国少数民族戏剧研究[C].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63.
[3]李瑞崎.贵州侗戏[M].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1989.
[4]方晓慧.表演[A].湖南地方剧种志[C].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88.
[5]黄守斌.戏台行歌—关于侗族戏剧语言艺术的研究[J].遵义:遵义师范学院学报,2009(5).
[6]贵州剧作编辑部.贵州剧作[Z].贵阳:贵州剧作出版社,1990.
[7]傅汝吉.余重骏:为所热爱的事业奋斗[A].贵州省老艺术家委员会编,黔岭星空[C].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