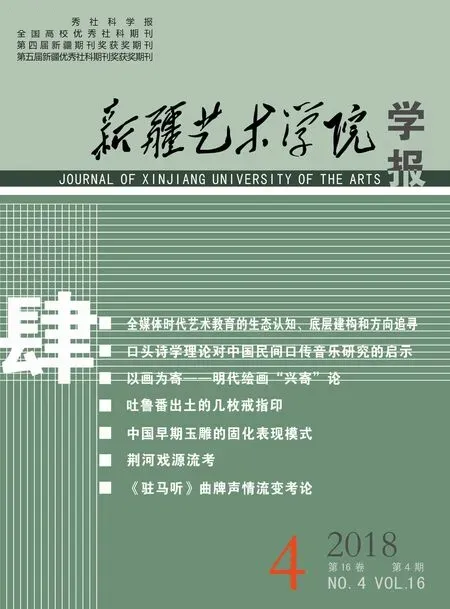论李龙云与老舍的作者意识
——以《小井胡同》与《茶馆》为例
邹卓凡
(中央戏剧学院 北京 102209)
一、两部作品的主题比较
《茶馆》的终结与《小井胡同》起点属于同一个时代背景下,虽然两部作品涉及的具体年份不同,却存在关联和重叠的部分。《茶馆》第三幕描绘的是“抗战胜利后,国民党特务和美国兵在北京横行的时候”,而《小井胡同》则是“北平和平解放前夜”,前后相差不过四年,北平的战况和人们的生活却不可同日而语。我们对历史的考察总依赖于对重大时间节点前后变化的推测,殊不知历史早在起点之前就已经开启,而在终结之后仍萦绕不去。基于两部作品对同一时代的描绘,能够看出作者在浩瀚的历史素材中进行选择的出发点是什么,从而更具体地寻找出两部作品主题上的差异。
《茶馆》第三幕一开始,作者简单交代了茶馆的现状“不像前幕那么体面”,“莫谈国事”的纸条更多字也更大,旁边还贴着“茶钱先付”的新纸条。这一提示告诉我们的是,在前两幕中作为一个公众集会场所的裕泰大茶馆,其开设的可能性最大的障碍在于,它是否成为便于人们谈论政治、抒发对当权阶级不满的场所。这说明尽管政局倾覆、时局混乱,城中仍然有能够消费茶歇或住店的客人,不管是从前吃铁杆庄稼的旗人,还是后来铁打不动的学生。可当抗战胜利后,当侵略行为不再威胁个人生命时,国人面临着国家内部将如何被重新分割,当权者重新洗牌需要重新取得资格的局面。北平城内几乎所有人都以一种末日暴徒的心态搜刮着最后的资源,以惶恐又麻木的心态应对即将到来的“新生活”。此时,威胁茶馆命运的因素不再是“国事”,而变成了“茶钱”。茶馆的落魄预示着这个时代的基调与之前相比更为灰暗而绝望,生存似乎彻底丧失了可能性。
在这样凄惶的背景下,老舍通过饥饿和逃命对这个时代做了更具体的说明。一大清早少掌柜王大拴垂头丧气地收拾屋子,女儿小花想吃一碗热汤面,媳妇周秀花却说“可谁知道买的着买不着呢!就是粮食店里可巧有面,谁知道咱们有钱没有呢!”①老舍《茶馆》,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40页。一句话将眼下的困境说得清清楚楚,物资短缺、粮食不足,人们持续挨饿;同时货币贬值、物价飞涨,拿着钱也买不着东西。然后王大拴再三叮嘱小花不能向任何人透露身为八路军的逃犯康大力的消息,其养母康顺子意识到自己的存在或会给王利发一家带来麻烦,犹豫自己是否要离开茶馆投奔西山游击区,同时也劝说王大拴和周秀花好好考虑一下自己的出路。对康大力及其母康顺子的存在,王利发的态度一直是含糊而不大情愿的。
第二幕康顺子离开庞家再次来到茶馆时,内掌柜王淑芬出于同情及对茶馆人手不足的不满,自己做主留下了她帮着打杂,对此王利发颇有怨言。直到第三幕小宋恩子、小吴祥子四处抓捕康大力,康顺子不得不离开的时候,王利发虽然对于儿媳妇周秀花去送她面有难色,可嘴里仍是说不行就还回来。作为一个生意人,王利发有他圆滑计较的一面,可对于康顺子和康大力这对与他毫无关系的苦命母子,他已经十分慷慨了。王利发见证了康顺子是如何在自己家的茶馆被十两银子卖给庞太监做媳妇,到最后隐瞒康大力的下落以致危害自己辛苦多年经营的茶馆的命运。康顺子并不是王利发卖给庞太监的,可最终却还是因她受到了牵连。作者设置了一个看似没有因果关系的“因果循环”,试图展示其中的荒谬和无理。而更无理的是,当小宋恩子、小吴祥子逼迫王利发交出康大力的时候,王利发却知道这不过是“交人还是拿钱”而已。在见证了三个时代中各种人借着各种名义在茶馆抓人犯事,王利发已经彻底看透了这个社会运行的规则,那就是永无止境地去尽可能抢占别人的生存概率,就等于扩大了自己的生存概率。
秦仲义称自己富国裕民的事业被政府当碎铜烂铁卖了,常四爷感慨自己凭良心了一辈子落得卖花生米,王利发则做了一辈子顺民,见谁都请安、鞠躬、作揖,变尽了方法不过是为了活下去。秦仲义、常四爷和王利发代表了对待命运三种截然不同的态度,可无论是变革、抗争还是顺从,最终都无济于事。作者展示了普通人在乱世中为了求生存的全部可能性,却没有一条是行得通的。在这里唯一能做的就是抢夺,作恶和害人变成了一种职业。
相似的是,《小井胡同》的第一幕也是由饥饿开始的,作者同样隐藏了一个关于“逃犯”的线索,带出了一段重要前史。刘家祥看着杨半仙的年画脑子里想的却是画上的小驴腿,这只是人物对生存状况的调侃。等刘家祥说自己跑去北海期盼着能碰上飘过来的空投物资时,饥饿的窘迫已经无处可藏。刘家祥在小年下出院门打算祭灶王爷,正好碰见准备去敛份子的警察巡长吴七。两个人通过对前夜里响了一夜的枪声,交换了对最新战况的看法。吴七虽为国民党警察巡长,却与胡同内的平头百姓建立了超越身份的情感关系,也同样对八路军进城结束兵荒马乱有着某种期许。在刘嫂准备带着小结实去庙里许愿时,丈夫指责她把收养来的男孩当女孩儿养的迷信行为,于是刘嫂突如其来地提起了“吴巡长,听说这孩子是您从监狱里给抱出来,搁胡同口的?”①李龙云《小井胡同.小井风波录》,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48页。这一前史。这里刘嫂的动作是有点奇怪的,后文提到小结实被搁胡同口那阵儿他也就三四岁,可知小结实抱回家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而吴七作为小井的老交情,刘嫂认识他的时间也不短了,对小结实的身世真有疑问不必等到现在才问,应该是抱回家的第一时间就问了。作者全剧一开场就安排刘嫂说出这一重要前史,是为了在第一幕结尾春喜喝取灯时小结实被人贩子抱走这一动作显得更有力量,这样设置对于快速展开情节、保证叙事节奏十分有利,却在人物合理性上做出了牺牲。
交代小结实是八路军遗孤,被吴七出于良心从监狱抱出来放在胡同口这一前史是有重要意义的,因为这是全剧所要表达的主题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后来的情节发展我们可以得知,吴七救小结实这一行为既是证明其人物性格的主要戏剧动作,也是小媳妇得以诬陷他从而霸占吴七的房子将他强行遣送回乡的前提。小结实的下落不明是小井遭受苦难、丧失希望的象征,小井胡同作为一个生态空间其真正的意向是大家庭,小结实作为这个家庭的孩子象征着光明和希望。在第一幕中,刘嫂为了让他摆脱不幸的命运遵从迷信把他当成女孩子养育,同时将他带往娘娘庙由道士摸头并取名为僧保,以期得到庇护和保佑。可这两件事最终的结果是小结实在第一幕结尾时便被人贩子毕五拐走。而吴七在小媳妇的指控下,一辈子背着国民党警察的罪名,流离失所。在这里,真正造成小结实和吴七不幸的,既不是战争也不是制度,而是毕五和小媳妇的个人行为所致,更多的是人物品质上本身的恶劣,与时代无关。
这并不是一种偶然。第四幕的整体基调都是灰暗、悲痛的,因为作为小井主心骨的刘家举家罹难,同时承受了来自各方面的不幸。可当我们仔细分析这些不幸却发现,不幸的本身并不是最可怕的,真正让刘家人不能承受的都是由同一个人造成的。刘丫头和小妮儿的大喜之日在哀伤中度过,因为刘家祥在地震中砸伤腿住了院,工资停发家里的状况捉襟见肘;二妮儿纪念周总理被抓走,丈夫与她离婚带着儿子小六九回到包头生活,小六九离家出走;二妞即将被当作反革命在小井胡同批斗,当着自己亲生父母和全院街坊的面。但细究其中原委发现,刘家祥之所以会被砸折,是因为“把防空洞挖在刘嫂屋底下”,工资停发是因为“电车公司上街道来的时候已实求实地反映了情况”,这都是小媳妇故意为之的。而二妮儿被抓虽然让人悲痛,却不丢人也不耻辱。真正伤害了刘嫂及全院人的心的,是专门把二妮儿带回到小井,当着所有人的面批斗她的这种做法,而这仍是拜小媳妇所赐。几乎小井所有人的悲剧都与小媳妇及其所代表的居委会有关。
时间来到“文化大革命”之后,作品渐渐丧失了对人物和时代相对客观的把握,而是任由个人的情感推动,进入到一种类似“私人恩怨”的纠缠中去。小井胡同里的人们的确因为时局的动荡遭遇了不幸,可人们似乎更多是在宣泄积压多年的不满,以一种“算总账”的方式向这最大的反派小媳妇进行反抗。如果说小媳妇所代表的居委会是趁着混乱彻底改变了自己的阶级和地位,那么小井的居民们也是通过这次动荡狠狠地享受了一次苦情的催泪。而在回顾矛盾的真正出处时,只是因为作为有资产者的石掌柜所在的阶级属性触怒了曾经一无所有的小媳妇。《小井胡同》中最根本的冲突来自于在阶级的层面对人进行宣判,阶级的属性决定了人物的性格、品质和命运。而作者所要讲述的时代的演变规则,则仍然是找出人群中的那一个或一些坏人,通过打倒他们来洗清队伍。因此,历史的面貌在此变成了全然的二元对立,只有道德的正确性和不正确之分,少了《茶馆》中生存完全不同的可能性以及这些可能性被一一抹灭的动态过程。
正如老舍自己所说:“我所爱的北平不是枝枝节节的一些什么,而是整个儿与我的心灵相粘合的一段历史,一大块地方。”①老舍《想北平.老舍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4卷第48页。在老舍说的这“一大块地方”里,有全不一样的人物和各不相同的悲惨,茶馆作为一个历史的取景器而不是万花筒而存在,呈现出作者对历史的态度更多的是一种思考而不止于表达。
二、两种不同的作者意识
李龙云将写看作是一种生命存在的方式。他选择作家作为职业的原因是“因为这种职业的自由。”对他而言,“一个用自己头脑写作的作家,工作本身就是享受,他的自由闲暇时间是生命的百分之百。”②李龙云 剧本《乡土、母亲、畏天知命及其他》,2007年8月,第60页。李龙云从他创作之初起就一直都为维护这种“自由”而斗争,强烈的自由意识给他带来痛苦和孤独,同时也深刻地影响着他的创作观。
从李龙云的早期作品《有这样一个小院》和《小井胡同》来看,他所谓的自由主要指的是一个作者能够以个人的方式表达自己对现实和历史的观感。而对于现实的思考和表达在他的作品中实际上包含了两个层面:生活的现实和政治的现实。这二者在《小井胡同》中有着清晰而又割裂的表达,在作品中呈现出一种矛盾的状态。《小井胡同》从排练到上演几经波折,最终还是被迫停演。作者在《小井风波录》中专门书写了《为〈小井〉洗三》一文,来纪念这一段心酸而又无奈的“生产”过程。《小井胡同》一共有过两版第一幕和四版第五幕,在此仅以第五幕的修改为例,试图从中找出李龙云作为作者渗透在作品中的个人意识体现。
我们现在较为熟知的分别是作为文学台本的1983年第二版第五幕,和作为演出台本的1984年第四版第五幕。通过比较得出,不管情节走向和人物结局如何修改,作者都坚持保留了居委会改选这一情节线。虽然最终第四版第五幕的演出台本的结尾,打点打在居民排队投票上,并没有交代选举的最终结果。但舞台提示中北京站越来越响的钟声,带着人们的憧憬与希望播向远方,实际已经暗示了选举的最终结果,同样是一个欢欣鼓舞的结局。而与第二版第五幕相同之处在于,从这一幕一开始水三儿、石掌柜和刘家祥三位老人在为吴七家的新房建地基开始,关于改选的讨论就一直贯穿始终,而内容则仍然是对小媳妇这个“万恶之源”的控诉,同时包含了一些通过“假换房启事”,让不断上门又被赶走的愤怒的来访者折腾死小媳妇这样的情节。
矛盾之处在于,一直以善良、淳朴的形象出现的小井胡同的可爱的老街坊们,从第五幕起渐渐变成了正义与道德的裁决者,而裁决的方式除了改选,就是控诉和报复。小井胡同的居民开始以一种与小媳妇类似的“整人”方式,来将小媳妇打倒。改选在此除了有助于蒙受冤屈的吴七夺回清白的意义,更多是小井居民对自己常年来遭受不幸和压迫的集体清算。改选的价值本应该在于重新选择一个能够代表小井人民利益的代表,却衍生出了以一个新的“领导人”代替集体讨伐旧的权力象征者的意味。我们很难说清刘嫂在满足居民们的需求和意愿外,会不会有将个人情感和私人恩怨带入新的管理过程中的可能。小井的“民主”选举,有着民主的事实,却难以预见是否能有民主的结果。因为对一切事物的判断标准并不基于客观事实,而是基于道德和所谓“正义”。
这样的人物塑造跟作者自身的个人经历,尤其是他的伤痛有很大关系。在他回忆自己童年往事的文章中,曾反复多次地提到过自己出生时“十字披红”和由于夜夜哭嚎差点被装进粪桶的经历。尤其是他对房东小妮子哭嚎却不被人在意的仇视,为后来作品中一系列的人物形象埋下伏笔。在李龙云的作品中始终存在的一个问题,就是将自己对底层市民深切的情感化为对剧中正面人物的道德认可,而将自己对不同阶级或社会身份的不满化为反面人物的政治不正确。两种同样偏离现实的“现实”彼此矛盾,造成了他如《小井胡同》这一类现实主义题材的偏离和困境。
李龙云曾经这样写道:“这几年,对于戏剧作品的长远美学生命问题,是我想得最多,和朋友们讨论得最多的问题。通向永恒之路到底有多少条?《莫扎特之死》写了人性中普遍存在的东西,‘阿Q’靠的是‘这一个’典型;而《茶馆》是熔工笔与写态于一身,用气度恢宏的三幅民俗画准确地描绘了三个时代……在大师们的‘碑林’面前,我们怎么办?我很担心,我们写出的戏都是些短命儿。问题在哪里?我很焦灼……”①李龙云 剧本《学习·思索·追求》,1985年,第3期。他与老舍一样,在作品中以塑造市井底层的小人物为主,通过他们的生活侧面透露社会政治形态。但他误将老舍对戏剧人物塑造的典型,当作了生活现实中的典型,这才是他在作品审美上的真正局限。通过第二版第五幕的结尾,水三儿、石掌柜、刘家祥、吴七四个老人围到抬夯面前,唱着号子一起抬夯,唱着唱着就笑了的情节可以看出,李龙云想要试图模仿《茶馆》最后三位老人给自己撒纸钱的戏剧场面。老舍并没有刻意去渲染一种悲凉的氛围,只是让他们客观地陈述各自生存尝试的失败,但荒诞的现实反差让悲剧意味不言自明。而《小井胡同》的结尾虽然通过惩恶扬善获得了新的希望,让类似大团圆式结局的回归变成了剧中人口中的光明,却未能形成真正的触动。
李龙云在他的创作早期试图师承老舍式的文字风格,沿袭写实的京味话剧传统,将剧作的重点落在再现那段时间人物的风貌上。作品中的人物都带有着很强的政治性,没有从个体自身全面展现人物,只是一个外在的真实,底层人民生活的一个缩影。但老舍的剧作并不完全局限于政治意识形态中,他要表达的是人在不同时代中的生存状况,以一个独立知识分子的身份去反思这个社会出现弊病的根源,同时也指出个人在这种病态社会中的无力。他对小人物秉承的是一种悲悯的情感,即使是行为上作恶多端的苟且之徒,也不是他所要正面批判的对象。
两剧在剧终处都试图让剧中人物总结出当时的社会面貌,但要表达的内容却截然不同的。老舍通过让社会上坏人当道,裕泰茶馆被腐恶势力强占,好人王利发、秦仲义及常四爷没落悲哀的晚年描写,反映了当时中国旧社会腐败的政治局势。老舍是以忠顺的小民们希望的破灭甚至是生命的灭亡,来表达自己对社会和历史的态度:换汤不换药的政治改良不可能彻底改变旧社会的弊端,腐朽的恶习依然世袭传承,腐败的政治局势将逐渐腐蚀社会而最终导致灭亡。而在《小井胡同》中,李龙云则通过社会上善良的小井街坊们最终战胜了常年使坏的恶势力小媳妇等人,反映政治黑暗结束后中国步向欣欣向荣的新政治光景。全剧最后以小井居委会改选成功,几个老人畅谈中国一路走来的艰辛路程的感想,以及街坊们的搬迁作为结局,反映的是终于迈向正确道路的政治局势。
如果说《茶馆》只是侧面表现政治对人们生活及生存的影响的话,那李龙云则是正面在表达自己的政治态度,从创作出发点上来说是有根本性不同的。李龙云在话剧史上争议不断,除了时代和社会对他的不公,根本上的原因还是要归结到个人对于自己命运的愤懑上。这种愤懑使他不能独立于作品之外,难免要把自己对于命运无法想通的痛苦,借人物的口舌反映到作品中去。作为一名剧作者,独立的创作人格很重要,独立的创作境界更直接决定了作品的价值。这或许是在深入研究李龙云剧作的得与失之外,我们能够从这位剧作家身上探寻到的更值得深思的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