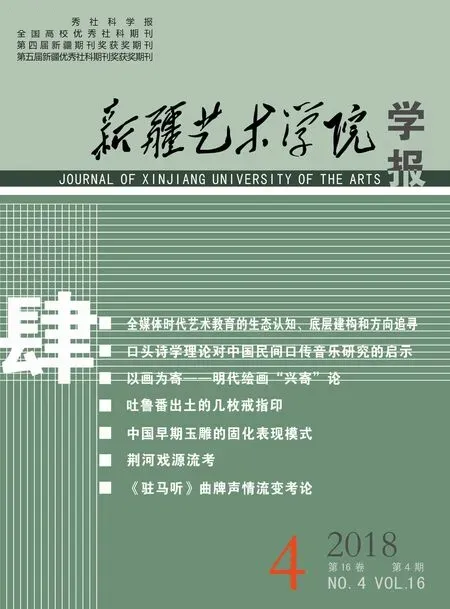口头诗学理论对中国民间口传音乐研究的启示
——评《口头诗学:帕里—洛德理论》
王 丹
(新疆艺术学院 新疆 乌鲁木齐 830049)
口头诗学理论也被称为“口头程式理论”“帕里—洛德理论”,自产生之日起,便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普遍的推广,对民间口头文学研究具有一定的意义。20世纪90年代中期,在民间文学研究学者的推动下,口头程式理论引入我国,主要集中在民间文学研究领域中的口头史诗研究,颠覆了原有民间口头文学研究的思维模式和研究范式。民间口头文学之所以能够代代相传,究其原因离不开民间讲述者的代代传诵,“音乐”是口头文学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没有文字记录的口头文学,靠有韵易于上口,便于流传,顾大多是采取歌唱的方式,靠曲调韵律传诵下来,离开曲调韵律,诗歌如同是去了灵魂。”①马学良《素园集》,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出版,1989年版,第126页。目前我国有部分学者在研究中接纳和吸收了口头程式理论的研究方法,并将其应用于口传音乐研究中,如蒙古族学者博特乐图(杨玉成),成功地将帕里—洛德理论引入蒙古族口传音乐研究,在他的博士论文《胡尔奇:科尔沁地方传统中的说唱艺人及其音乐》和《表演、文本、语境、传承——蒙古族音乐的口传性研究》中都有充分的体现。但从总体来看,这一理论方法并未受到音乐学界的普遍关注。
美国学者约翰·迈尔斯·弗里所著的《口头诗学:帕里—洛德》一书1988年由印第安纳大学出版社出版,2000年由中国著名民间文学研究学者朝戈金先生将其翻译为中文,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发行。本文以此书为研究切入点的主要原因是,首先作者约翰·迈尔斯·弗里作为美国密苏里大学“口头传统研究中心”的创始人、《口头传统》杂志的创办者,该学派自洛德之后的主要代表人物,将口头程式理论的学术背景、帕里和洛德的主要观点、学科的影响和未来发展方向进行了系统的梳理,成为系统、详细介绍口头程式理论的最重要的研究专著。其次,作为中文译本,在忠于原著的基础上,朝戈金先生从中国视野中对口头程式理论进行了关照,他对原文中各种术语概念如“程式”“程式句法”“口头传统”“主题”等的汉译,已在学术界达成了共识,促进了不同文化间的对话和沟通。并且译者结合中国史诗研究和其他口传样式研究,阐述了这一理论在中国得以运用和发展的现实意义和学科未来发展趋势。因而,笔者欲通过对该书理论和方法的提炼和归纳,为如何将口头程式理论和中国民间口传音乐研究相结合,如何在口传音乐研究中借鉴和运用这一理论提出了一定的思考。
一、该书是对口头程式理论的系统、全面的介绍
美国学者米尔曼·帕里是口头程式理论的开创者,1923年以古希腊“荷马史诗”作为研究对象,发现了荷马史诗中“会出现重复地、循环地诗行和场景,提出在“口头表演中会采用‘常备片语(stock phrases)’和‘习用的场景(conventional scenes)’来调遣词语创编他的诗作,这些循环出现的语言被看作是口头诗人创作诗歌的工具。”①[美]约翰·迈尔斯·弗里 朝戈金译《口头诗学:帕里—洛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2-3页。但仅书面文本分析,还不能印证荷马史诗所拥有的口头诗歌传统,1933至1935年,帕里与艾伯特·洛德一起前往南斯拉夫地区,对当地盛行的活态口传史诗演唱传统进行实地调查,将书面文本分析的结论通过田野实践进行验证,录制了数百首史诗的演唱,之后通过对照和比较发现它们与荷马史诗一样,“都是由‘大词(large words)’构成的,这是种易于变通使用的修辞单元与叙事单元,用以帮助歌手在口头表演中进行编创。”②[美]约翰·迈尔斯·弗里 朝戈金译《口头诗学:帕里—洛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4页。在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语境和传统中,帕里和洛德找到了它们之间交集,印证了他们关于荷马史诗为口头诗歌的推断。1935年帕里去世,洛德继续对研究扩展和深入,1960年出版专著《故事的歌手》,被称为“口头理论之圣经”③[美]约翰·迈尔斯·弗里 朝戈金译《口头诗学:帕里—洛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97页。,在两位学者的共同努力下,口头程式理论发展成为一门自成体系的学科。
该书由五个章节构成,第一章为语文学、人类学和“荷马问题”,作者对口头程式理论的来源,形成背景和学术源头进行了阐述。第二章主要介绍帕里的学术成就,及理论形成和发展的脉络。第三章为洛德理论形成的发展脉络,重点介绍了其著作《故事歌手》的研究思路和方法,以及之后的理论创新。第四章为学科的形成,阐述了帕里—洛德理论形成之后,在主要的三个领域,即古希腊传统、古英语传统、更小层次传统(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西班牙等国家)中的接受和发展情况。第五章为近期和将来发展的走向,是弗里对口头程式理论在过去发展状况的思考,以及这一理论在发展中所面临的挑战和发展方向。
译者朝戈金先生一直致力于对口头程式理论的引进和介绍,他的专著《口传史诗史学:冉皮勒〈江格尔〉程式句法研究》“则是以蒙古族英雄史诗《江格尔》的口头程式研究为出发点对口头诗学理论的一次开掘.”①王佑夫《开创在中国民族史诗研究新局面——论朝戈金口传史诗研究》,载《新疆社会科学》,2016年第1期,第154页。之后,口头程式理论在朝戈金以及尹虎彬、巴莫曲布嫫、陈岗龙等中国学者的共同努力下,得到了学界的广泛认可。
帕里—洛德理论主要研究对象为民间口传文学,程式(formula)、主题或典型场景(theme or typical scene),以及故事形式或故事类型(story pattern or tale—type)”为口头程式理论的核心概念,书中重点对“程式”和“主题”进行了详细的阐述。帕里最先提出了程式概念,即“一种经常使用的表达方式,在相同的步格条件下,用以传达一个基本的观点。”②[美] 约翰·迈尔斯·弗里朝戈金译《口头诗学:帕里—洛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57页。洛德进一步发展,认为“程式是思想和被唱出的诗句彼此密切结合的产物,强调节奏和韵律的构形功能。”③[美] 约翰·迈尔斯·弗里 朝戈金译《口头诗学:帕里—洛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98页。主题为“观念的组群,在传统的各种常常被用于以程式的风格讲述故事。”④[美] 约翰·迈尔斯·弗里 朝戈金译《口头诗学:帕里—洛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99页。总体来看,帕里—洛德理论是一门具有方法论性质的学科,其意义在于“很好地解释了那些杰出的口头诗人何以能够表演成千上万的诗行,何以具有现场创作能力的问题。”⑤[美] 约翰·迈尔斯·弗里 朝戈金译《口头诗学:帕里—洛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15页。
二、对中国民间口传音乐的启示
(一)对口传音乐文本的再认识
口头程式理论对中国民间口传音乐而言,最重要的影响在于对“文本”的界定。“文本”和“本文”这一对概念是由语言学“能指”和“所指”演化而来,“能指是表示物质实体或抽象概念的一系列语音或文字符号,即声音的心理印述或音响形象。所指表示成分、概念,即用一系列语音或文字符号表示的具体事物或抽象思想。在民族音乐学中‘文本’与‘能指’相对应,表示用符号记下来的乐谱和用文字记下来的歌词,‘本文’与‘所指’相对应,表示事实上存在的音乐。”⑥杜亚雄《音乐的文本和本文》,载《中国音乐》,1997年第3期,第15页。
艾伯特·洛德在口头传统的比较研究中,提出了对口头文学中“文本”的认识。他认为“每次表演都是一首特定的歌(the specific song),而同时又是一首一般的歌(the generic song)。我们聆听的歌是“这一首歌”(the song),因为每一次表演都不仅仅只是一次表演,它是一次再创作。”⑦[美] 约翰·迈尔斯·弗里 朝戈金译《口头诗学:帕里—洛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100-101页。从这个角度看,口头文学和书面文学的“文本”具有一定的差异。主要表现在:首先,口头文学的“文本”不存在“标准”的版本,“这一首歌”指具有相同叙事情节的故事,“特定的歌”表明每一次表演都是一次创作的过程。“一般的歌”表明“这一首歌”与“特定的歌”之间存在的联系。而在书面文学中,是存在“权威本”或“标准本”。其次,口头文学是付诸听觉而存在,既然付诸听觉,每一次呈现,都具有不可重复性,其目的是为了聆听,洛德进一步解释“恰恰流变性才是传统诗歌的生命,只有当没有固定的文本横插在歌手和传统之间时,传统诗歌才得以存在;一旦‘一次’表演(a performance)成为‘这一首歌’(the song),传统那多重易变的本质才会终止其作用的发挥。”①[美] 约翰·迈尔斯·弗里 朝戈金译《口头诗学:帕里—洛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102页。而书面文学则付诸视觉而存在,借助文字符号传达信息,具有可重复性,不受时间空间的限制,其目的是为了阅读。第三,口头文学会依赖于程式化系统,即“一组具有相同韵值的片语,并且它们彼此之间在含义上和用词上至为相似,以致诗人不仅将它们视作单独的程式,而且也视作一组特定类型的程式,进而掌握它们并毫无迟疑地记忆运用。”②[美] 约翰·迈尔斯·弗里 朝戈金译《口头诗学:帕里—洛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66页。而书面文学,则不依赖于程式化系统,力求灵活的表现力,构思的巧妙和结构的新意。二者之间的这些差异,使得在口头文学研究与传统的书面文学研究具有不同的研究路径,口头文学研究更需其放入所属的生活和文化语境中进行全面的考察。
在口头文学传承、流布的过程中,音乐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若将音乐考虑其中,口头文学的文本应由两个部分组成:一是用文字记录下来的语言,即“唱词文本”;二是用符号记录下来的音乐,即“音乐文本”。帕里—洛德理论是开放、发展的理论体系,虽然主要针对民间口头史诗研究,但对口头史诗音乐部分,乃至口传音乐研究同样具有借鉴价值。口传音乐与西方以乐谱为主要承载工具的音乐有着截然的区别。目前,针对口传音乐的研究更多地是停留在对“表演后”产生和形成的音响作为研究对象,对其进行传统音乐形态学分析,缺乏对口传音乐本质属性的关照,因而帕里—洛德理论可以为口传音乐研究能够提供一个新的视野和方法。
在借鉴和应用口头程式理论时也应考虑到口传音乐的“文本”与口传文学的“文本”之间的共性和差异。共性表现在“文本”均无“标准本”或“权威本”,每次表演都是一种创作行为。差异表现在:首先,音乐文本就自身特点而言是非语义性、非对应性、抽象的,只有借助于诗歌(唱词)才会被赋予语义性和对应性,使之具体化,更易于和不同的诗歌文本相结合,形成“同曲异词”现象。部分音乐文本也会由于旋律朗朗上口的特点,在后期的发展中逐渐独立存在,被赋予某种特定的“语义标签”,成为曲牌的概念,形成“同词异曲”的现象。其次,文学语言的“文本”(能指)和“本文”(所指)之间的关系是任意的,而音乐的“文本”(能指)和“本文”(所指)的关系是相对固定的,“文本”(乐谱)是对“本文”(实际音响)的记录,虽然相对固定,但“文本”不可能忠实的反映“本文”。第三,就口传文学文本而言,在研究中民间活态留存的文本,可以和已有的被书写保留的文本之间进行相互的参照。但对于音乐文本而言,很多民间音乐形式缺乏对音乐进行精确记录的手段,即使有记录,也是较为宽泛的规定性记谱(prescriptive)③1958年,规定性记谱(prescriptive)和描述性记谱(descriptive)由查尔斯·西格提出,即为一首将要演唱的歌曲绘制的一幅蓝图和关于一首实际上已经完成了的歌唱表演的书面报告。,内特尔称之为“为表演者提供的一张蓝图。”④杨民康《以表演为经纬——中国传统音乐分析方法纵横谈》,载《音乐艺术》,2015年第3期,第112页。与口传文学文本相比,要需将“文本”置于所属的社会和文化语境中进行考察,突出对音乐“文本”形成过程的阐释。蒙古族音乐学者博特乐图对“口传音乐”文本做出了重要的探索,提出适用于蒙古族口头传统的“曲调框架”的概念,认为“曲调框架是一种结构,是口传音乐的思维方式和音乐建构手法,是潜藏在具体曲调背后的关于曲调的音响形象,并通过口头表演与曲调相连。”⑤博特乐图《表演、文本、语境、传承——蒙古族音乐的口传性研究》,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12年版,第38页。每个民族的音乐文化都有其不同于其他民族的独特性,就其构成方式而言,口传音乐存在某些共性因素,但每个民族口传音乐的生成、创造、实践都无法脱离本民族传统的生存土壤和口头形成的传统,因而在研究中应充分考虑不同民族口传音乐生成的历史、社会、文化等多种因素而加以区别对待。
(二)传统与个体创造之间的关系
“表演中的创作”是帕里—洛德理论针对口头史诗文本研究所提出的核心概念,即口头传统的文本需置于赖以生存的表演语境中进行研究。这一概念的提出给口头史诗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洛德立足于个体研究,选取了南斯拉夫具代表性的史诗歌手,观察描述了歌手的三个学艺阶段“第一阶段为单纯的聆听和吸收叙述的节奏与修辞;第二阶段,确立形式的基本要素,即旋律和节奏开始尝试演唱;第三阶段,从头至尾表演一首以上的歌,并能够根据听众和当时的场景,在表演中进行增加或删减。”①[美]约翰·迈尔斯·弗里 朝戈金译《口头诗学:帕里—洛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97页。并对不同歌手如何处理口头程式理论的“程式”“主题或典型场景”等进行了详细的阐述。音乐属于表演艺术,其本质是第二度创作。“表演中的创作”在西方音乐话语体系中也同样适用,但在西方音乐话语体系中,创造行为是以乐谱为存在形式的音乐作品(音乐创作的产物)作为出发点和归结点的基础上的创造。而对于口传音乐而言,表演中的创造并无某一特定的音乐创作产物作为依托,因而“表演中的创作”则表现为传统和个人创造的关系。
“传统是人类行为、思想和想象的产物,并且被代代相传,这种代代相传事物涵括一个特定时期内某个社会所拥有的一切事物,包括一种哲学思想、一种艺术风格、一种社会制度,在代代相传的过程中既发生了种种变异,又保持了某些共同的主体、共同的渊源、相近的表现方式和出发点,从而它们的各个变体之间仍有一条共同的链锁连接其间。”②[美] E.希尔斯 傅铿 吕乐译《论传统》,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16页。传统具有延续性、同一性、持续性的特点。对于每一个口头史诗歌手而言,“他不是一个有意识逆传统惯例而动的人,而是传统的创造性的艺术家。他的传统风格仍然有其个人的特性。”③[美]阿尔伯特·贝兹·洛德 尹虎彬译《故事的歌手》,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6页。
赖斯在梅里亚姆“概念、行为、音声”三重模式的基础上,结合格尔兹针对仪式研究所提出的“历史构成、社会维持、个人创造”,提出新的民族音乐学研究模式,即“四级目标模式”,回答了“人类怎样按历史构成音乐、有社会维持音乐并通过个人创造、体验音乐”④[加]蒂莫西·赖斯《关于重建民族音乐》,载《中国音乐学》,1991年第4期,第121页。的音乐生成过程。第一级中,他将“概念、行为、音声”分别置入“历史构成、社会维持、个人创造”中进行分析,第二级中,辩证地、互动地看待“历史构成、社会维持、个人创造”之间的关系。第三级中,提出音乐学的目标,解决人类创造音乐的问题,第四级中,达到人文科学的终极目标,即“音乐作为文化”的研究。这一研究模式的提出“不仅使民族音乐研究中保持了音乐与文化互补的学科基本形式,而且还明确了其中的层次关系,并为此制定了具体的实施步骤。”⑤杨民康《音乐民族志方法导论——以中国传统音乐为例》,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2008年版,第29页。传统作为被代代相传的人类行为、思想和想象的产物,存在于“历史构成”和“社会维护”“个人创造”的互动中,“历史构成包括两个重要过程,随时间变化(即历时)的过程和当下时刻重遇、在创造过去的形式与遗产(即共时)的过程。”①[加]蒂莫西·赖斯《关于重建民族音乐》,载《中国音乐学》,1991年第4期,第122页。在“历史构成”研究中,除了运用传统的文献证据和实物证据外,还需结合口述文本、音像文本等材料。就口传音乐而言,特别是缺乏用文字记录历史或音乐习惯的某些民间音乐,大多数情况下很难推测,谁最先使用了这些音乐,谁在前,谁在后,谁传承给谁、体裁之间谁影响谁的问题,传统发生在不同时代、不同地域之间的传承关系之中,不同的个体创造在传承链条中均占有一定的位置,在口传音乐中,个人创造的发挥必须建立在“传统”的基础上,是在和传统的不断碰撞中,确立自身的表达方式和风格特色,若这种表达方式和风格特色在历史的传承链条中受到了群体的认可就形成了传统,“历史是过去的承传:当文本、遗迹、艺术、表演风格和习惯等日常生活的构成部分被归类、固定或‘文本化’,历史便形成了,因此,历史既远又近;他同时属于现在,又属于另一时空。”②[加]蒂莫西·赖斯《愿它充满你的心灵——体验保加利亚音乐》,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14年版,第21页。个人创造形成的表达方式被群体认可所形成的传统,也应看作是历史的一部分。个人创造与传统之间始终相互依存、相互制约,传统是不同个人创造积淀的结果,个人创造离不开传统的土壤,因而,在对口传音乐进行研究时,应将个人创造置于首要的位置,将其作为探究历史构成和社会维护的重要因素。
中国民间口传音乐既属于民间文学范畴,也属于民间音乐范畴。在口传音乐中,唱词和音乐是不可分割的整体,最终以统一的声音符号呈现,但长期以来由于学科之间的分界,往往各自归入所属的研究范畴。口头程式理论作为一种分析方法,不仅对文学领域、民俗领域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也应借鉴运用到民族音乐学研究领域中,这种方法的运用对于解释口传音乐中人的行为以及思维模式都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当前,中国民间口传音乐在经历着不同程度的发展和变迁,需要在研究中拓宽思路,吸收借鉴不同的研究方法和视角,用动态、发展的眼光看待和研究民间口传音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