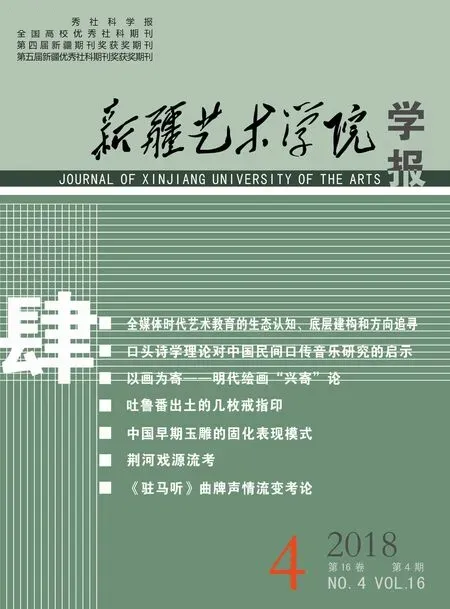以画为寄
——明代绘画“兴寄”论
郭青林
(安庆师范大学 安徽 安庆 246011)
从画史上看,重视绘画的“兴寄”作用可上溯到南朝刘宋时期。宗炳在《画山水序》说道:“披图幽对,坐究四荒,不违天励之藂,独应无人之野。峰岫嶤嶷,云林森眇,圣贤暎于绝代,万趣融其神思,余复何为哉?畅神而已,神之所畅,孰有先焉!”①俞剑华《中国古代画论类编》,人民美术出版社,1998年版,第584页。这里,宗炳从审美接受的角度来阐释山水画的“畅神”——娱情适意的作用。同时代的王微也说:“望秋云,神飞扬;临春风,思浩荡。虽有金石之乐,珪璋之琛,岂能仿佛之哉!披图按牒,効异山海。绿林扬风,白水激涧。呜呼!岂独运诸指掌,亦以神明降之。此画之情也。”②俞剑华《中国古代画论类编》,人民美术出版社,1998年版,第585页。王微抉发“画之情”,观点和宗炳相类。唐代王维开创的写意山水成为除诗词以外,文人寄情适兴的重要方式,绘画的寄兴功能在文人画的创作中得到充分的体现。至宋,苏轼在《跋汉杰画山》中指出:“观士人画,如阅天下马,取其意气所到。”③俞剑华《中国古代画论类编》,人民美术出版社,1998年版,第629页。文人画以表现画家主观“意气”为目的,不能以“似”和“不似”来评价。在《书朱象先画后》一文中又写到:“能文而不求举,善画而不求售,文以达吾心,画以适吾意而已。”①俞剑华《中国古代画论类编》,人民美术出版社,1998年版,第49页。作文为发抒心灵,作画为畅适情意,不存在为了什么功利而作画。元代是文人画创作兴盛时代,画家更重视绘画的“兴寄”功能。“元四家”之一的倪云林,在谈自己的绘画创作时说:“仆之所谓画者,不过逸笔草草,不求形似,聊以自娱耳。”②俞剑华《中国古代画论类编》,人民美术出版社,1998年版,第706页。倪云林的画以其“逸笔”写其胸中之“逸气”,达到“自娱”之目的,显示出对绘画的娱情功能的重视。明代画论家特别是文人画家,尤为推崇倪云林的“聊写逸气”及“自娱”之说,他们针对画坛模拟雕琢之习,强调“以画为寄,以画为乐”③董其昌《容台集》,西泠印社出版社,2012年版,第676页。,视“兴寄”为绘画之本,并对此作了多角度的阐释。
一、画本予漫兴
明代画家在朝为宫廷所用,置身画院,所作稍不称旨,即遭酷刑,思想受缚,创作多墨守成规,精严工整,继承南宋院体画风。在野则志在丘壑,栖居在山水之间,思想自由,创作上不求形似,遣怀写意,承续元代文人画风。画家身份、地位及生存环境的不同,是影响他们画学取向、并各自成派的重要因素。此外,明代画家所拥有的绘画资源,较唐、宋、元三代更为丰富,流传下来的大量名作,为明人创作提供可以借鉴的范本。画者以临摹古迹,逼似古人为上,复古气息极为浓厚。在绘画思想上,文人画家在对院体画风以及只知临摹,不知创新的画坛陋习的批评中,竭力倡导绘画的兴寄功能,这既是对明初宋濂倡导的“助名教而翼群伦”④俞剑华《中国古代画论类编》,人民美术出版社,1998年版,第95页。的反驳,又是明代心学思潮流布在绘画领域的体现。
明初政权刚建,有待稳固,政治上有借助文艺维护统治秩序之需要。在绘画领域重新倡导政教功能。如被推为“开国文臣之首”的宋濂,在《画原》中就指出“至于辨章服之有制,画衣冠以示警,饬车辂之等威,表旟旐之后先,所以弥纶治具,匡赞其政原者,又乌可以废之哉!”⑤俞剑华《中国古代画论类编》,人民美术出版社,1998年版,第95页。认为画家创作应当为现实政治服务。至明中叶,名臣吴宽也重弹此调:“古图画多圣贤与贞妃烈妇事迹,可以补世道者,后世始流为山水、禽鱼、草木之类而古意荡然。然此数者,人所常见,虽乏图画,何损于世?乃疲精竭思,必欲得其肖似;如古人事迹,足以益人,人既不得而见,宜表著之,反弃不省,吾不知其故也。”⑥俞剑华《中国古代画论类编》,人民美术出版社,1998年版,第105页。重视的仍然是绘画的“补世道”“足以益人”的政教作用。宋濂和吴宽身为朝臣,承担辅国之责,强调绘画的政治功利性是与其身份地位相符的。
但是,吴宽所处时代已与明初迥然不同,明初文禁森严的状况已发生了改变,士人的思想较为自由。绘画上以写意为特征文人画已主导画坛,而工整精严的台阁体画已趋于没落。吴宽虽强调绘画的政教价值,对画家的影响不再像明初。从其本意来说,他是针对画坛中专事临摹一派,以逼似前人为旨归的不良习气,从画史的角度进行批评的,旨在揭示这些只知临摹的绘画行为的实质——无用的浪费生命的活动。这也是在蛰居民间的文人画家常持的看法。与吴宽有过深入交游的,吴派绘画开创者沈周就认为绘画之道在于“意到情适”,而不是“拘于形似之间”。(《桃熟花开图》题记)和吴宽不同的是,沈周的批评注重绘画的主观表现,把画家的“情”和“意”的传达视为绘画之关键。他在论自己的画时说:“画本予漫兴。天下事专至精,岂以漫浪而能致人之重乎?”①沈周《跋杨君谦所题拙画.沈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229页。所谓“专至精”就是指像画院里那些以精雕细琢为能,追求逼真效果的画工作风,沈周是反对这种匠人习气的。他把绘画动机归结为个人的“漫兴”活动,重视绘画的兴寄功能。在他看来,绘画主要是画家个的“寄兴”行为:
老夫弄墨墨不知,随物造形何不宜。山林终日无所作,流观品江开大奇。明窗雨过眼如月,自我心生物皆活。傍人谓是造化迹,我笑其言大迂阔。(《花果杂品二十种》题记)
我于蠢动兼生植,弄笔还能窃化机,明日小窗孤坐处,春风满面此心微。戏笔此册,随物赋形,聊适闲居饱食之兴,若以画求我,则在丹青之外矣。(《写生图》册题跋)
水墨因戏事,山水偶流形,辍笔信人卷,妍丑吾未明,模拟亦云赘,所得在性情。(题旧作《匡庐新雪图》)
在这些题写在画册之上的诗中,可见沈周对绘画所持的主要观点。其一,绘画是表现画家生活情趣的创作活动,不是机械地图写物象描摹行为。在图写“造化迹”之外,还有画家寄寓其中的主观情兴。其二,绘画是“适兴”活动,若无兴致,不可妄作,若“以画相求”,就不是绘画了,而是在“丹青之外”,绘画是无功利的。其三,绘画是“戏事”之作,重在表现性情,不是纯粹的模拟活动。这三点的核心,就是强调绘画的“兴寄”功能。文嘉在论其父亲文徵明也说:“先待诏喜画,明窗净几,笔砚精良,得佳纸辄弄笔作小幅,以适清兴。”②俞剑华《中国古代画论类编》,人民美术出版社,1998年版,第715页。文徵明的绘画,冠绝当代,其创作目的也是为了寄托个人之“情兴”。绘画是为了“寄兴”,反之,若无“兴”可寄,绘画活动便不能进行,“兴”成为绘画活动中决定性的因素。顾凝远(1580-1645)在《画引》中指出:
当兴致未来,腕不能运时,径情独往,无所触则已,或枯槎顽石,勺水疏林,如造物所弃置,与人装点绝殊,则深情冷眼,求其幽意之所在,而画之生意出矣。③俞剑华《中国古代画论类编》,人民美术出版社,1998年版,第118页。
“兴致未来”就会导致“腕不能运”,绘画活动终止,这时画家应以“径情独往”,在顽石、勺水、疏林中,以“深情冷眼”来“求其幽意”。“幽意”即是“兴致”,“求其幽意”就是触发兴致。“兴致”是绘画得以进行的动力因素,也是绘画艺术表现力的产生根源。
明人视绘画为个体的寄兴行为,表明对绘画的价值的认识由强调功利性政教意义转向非功利性的审美意义,这是明代画家特别是在野的文人画家的普遍的价值取向。这种观念的转变既与画家对山水画艺术本质认识的深入紧密相关,又与画家对画坛形式主义倾向的模拟风气的批评联系密切。
二、笔墨之间,无非兴也
本质与功能是体与用的关系,对绘画兴寄功能的认识,要从绘画艺术的本质来把握。沈周在论山水画时指出:山水之胜,得之目,寓诸心,而形于笔墨之间者,无非兴而已矣。是卷于灯窗下为之,盖亦乘兴也,故不暇求其精焉。观者可见老生情事如此。①俞剑华《中国古代画论类编》,人民美术出版社,1998年版,第711页。画家眼中有所“得”,心中即有所“寓”,笔墨便有所“形”。沈周以极简洁的话语描述了绘画的创作过程,指出“兴”是绘画表现的对象,它不是外在的客观的,眼睛所见到的山水形象,而是主体的内在情感。绘画的本质就是主体情兴的物化,绘画创作就是画家情兴的传达过程。画家运用笔、墨,通过空间结构的营造,赋于情兴以感性的形式,这是绘画区别于其他艺术的本质特征。由此所决定,绘画活动只能是主体的“兴寄”行为,是画家表达个体生活体验的重要途径之一。大凡作画,必有兴寄。岳正在《画葡萄说》中指出:
画书之余也,学者于游艺之暇,适趣写怀,不忘挥洒。大都在意不在象,在韵不在巧,巧则工象,则俗矣。虽然其所画者必有意焉,是故于草木也,兰之芳,菊之秀,梅之洁,松竹之操,皆托物寄兴以资自修,非徒然也。②孙岳颁《佩文斋书画谱》,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4年版,第416页。
“适趣写怀”是画家绘画之目的,因此创作时用力处在情兴的表达,而不是物象的再现,即“在意不在象”,所画必有寓“意”,有“兴”可寄。“托物寄兴”是画家陶冶性情,提高自我修养的重要方式,窥其旨趣,也有视“寄兴”为绘画艺术本质之意。唐志契在谈到山水画时说道:
山水原是风流潇洒之事,与写草书行书相同,不是拘挛用工之物。如画山水者与画工人物花鸟一样,描勒界画粉色,那得有一毫趣致?是以虎头之满壁沧州,北苑之若有若无,河阳之山蔚云起,南宫之点墨成烟云,子久、云稹之树枯山瘦,迥出人表,皆毫不著象,真足千古。若使写画尽如郭忠恕、赵松雪、赵千里,亦何乐而为之?昔人谓画人物是传神,画花鸟是写生,画山水是留影。然则影可工致细描画乎?夫工山水始于画院俗子,故作细画,思以悦人之目而为之,及一幅工画虽成,而自己之兴已索然矣。③俞剑华《中国古代画论类编》,人民美术出版社,1998年版,第736页。
这段话所表达的观点同岳正相近,山水画的创作同草书、行书一样,主要是表现作者的主观情兴,创作时不必拘泥于对象形体,进行精细的描摹,否则会破坏“趣致”的表达。唐志契视山水画的创作为“风流潇洒之事”,就是在强调山水画的创作是表现主体情兴这一本质特征。他批评院体画家对山水作精细描绘,并不是为了表现自己的情兴,而是为了“悦人之目”,画虽工,兴却无。对山水画的创作,唐志契还认为:
凡画山水,最要得山水性情,得其性情:山便得环抱起伏之势,如跳如坐,如俯仰,如掛脚本,自然山性即我性,山情即我情,而落笔不生软矣。水便得涛浪潆洄之势,如绮,如云,如奔,如怒,如鬼面,自然水性即我性,水情即我情,而落笔不板呆矣。④俞剑华《中国古代画论类编》,人民美术出版社,1998年版,第742页。
所谓“性情”不外乎指山水的自然情态及所呈现出的生气,它们通过画家审美感官内化为画家主观的“性情”,所以说山水之“性情”即“我”之“性情”。山水画的创作,“最要得山水性情”,就是说山水画创作关键在于要表现出画家之“性情”。王肯堂(1552-1638)在论画时也说:“前辈画山水皆高人逸士,所谓泉石膏肓,烟霞痼癖,胸中丘壑,幽映回缭,郁郁勃勃不可终遏而流于缣素之间,意诚不在画也。”⑤孙岳颁《佩文斋书画谱》,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4年版,第418页。“郁郁勃勃不可终遏”是指画家主观情兴,山水画的创作就是画家主观情兴的表现,目的确实不在于为了再现外在的、客观的山水形象。
从明代画论家重视绘画的寄兴功能来看,他们对绘画艺术本质的把握,不再是从客体的一端,关注绘画所再现的对象,而是侧重从主体角度,关注绘画所表现的情感。体现了中国古人对绘画艺术本质的认识经历了一个由外向内的转变过程。其发端始于对绘画娱情功能——“畅神”认识,中经苏轼等文人对“意气”的强调,最后在理论上给予明确界定的则是沈周,这是明人对传统画学所做的重要贡献,具有重要的绘画史意义。它对明以后的绘画,特别是文人画的创作和接受产生深远影响。在绘画创作中,“形似”受重视程度退居其次,画家更关注的是绘画对主体情兴的表现功能。在绘画批评上,画论家更注重从主体的内心感受出发,来对画作进行鉴赏,“传神”让位于“生趣”,对笔墨形式运用的研究,也立足于主体情兴的表达。
三、品高寄托自远
既然“兴”是绘画表现对象,画家就要“乘兴”进行创作。王绂在《书画传习录》中说道:
高人旷士,用以寄其闲情;学士大夫,亦时彰其绝业。凡此皆外师造化,未尝定为何法何法也!内得心源,不言得之某氏也。兴至则神超理得,景物逼肖;兴尽则得意忘象,矜慎不传。亦未尝以供人耳目之玩,为己稻梁之谋也。惟品高故寄托自远,由学富故挥洒不凡,画之足贵,有由然耳。……辗转摹倣,无复性灵。①俞剑华《中国古代画论类编》,人民美术出版社,1998年版,第99页。
从绘画创作过程来说,“兴至”则神情超迈,道理自得,所作“景物逼肖”;“兴尽”则意味着情感活动停止,此时画家只有对对象的理性把握——“得意”,不能妄作。情兴既是绘画创作的动力因素,又是绘画表现的主要对象,情兴的深或浅,取决于画家本人品格高或低。画家因为“品高”,“寄托”自然深远,也是“画之足贵”的“由然”。这里以“情兴”的表达为媒介,把画家的品格与作品的价值相联系,颇有一种“画品出于人品”之意味。王绂把绘画视为是“高人旷士”为“寄其闲情”而进行的活动,是从创作目的角度来揭示绘画的艺术本质。“闲情”是寄寓在笔墨形式之中的,本质上绘画是“闲情”的传达,而不是笔墨形式所营构的形象本身,观念同沈周一致。这里所讲的“高人旷士”是指那些品格高尚,不同凡俗之人,也被称为“雅人胜士”“高明不俗之友”“高人逸士”等,如:
画之为艺,世之专门名家者,多能曲尽其形似,而至其意态情性之所聚,天机之所寓,悠然不可探索者,非雅人胜士,超然有见乎尘俗之外者,莫之能至。②俞剑华《中国古代画论类编》,人民美术出版社,1998年版,第98页。
古之高人逸士,往往喜弄笔作山水以自娱,然多写雪景,盖欲此以寄其岁寒明洁之意耳。若王摩诘之《雪溪图》,郭忠恕之《雪霁江行》,李成之《万山飞白》,李唐之《雪山楼阁》……乃与履吉索素缣,乘兴濡毫为图,演作《关山积雪》。一时不能就绪,嗣后携归,或作或辍,五易寒暑而成。但用笔拙劣,虽不能追踪古人之万一,然寄情明洁之意当不自减也。③文徵明《文待诏题跋》,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6年版,第48页。
画须从容自得,适意时对明窗净几,高明不俗之友为之,方能写出胸中一点洒落不羁为之妙。④俞剑华《中国古代画论类编》,人民美术出版社,1998年版,第738页。
“超然见乎尘俗之外”,即超越世俗,不以世俗风尚为趋向。画家如不能免俗,在创作上便被外物所牵,最多“曲尽其形似”,作品成为外物形象的机械记录,缺少生命的气息,无法传达出对象的“意态情性”和“天机”。“雅人胜士”能超越世俗的羁绊,保持自由的心境来感受外物,体验其“意态情性”和“天机”,并将感受通过笔墨形式传达出来,这样,作品就不再是外物形象的记录,而是主体心灵的表达。一般来说,记录须忠实外物形象,以“逼似”为特征,画家为此要“精雕细琢”,笔墨的运用为外物形体所约束,无法自由创造。这样的作品充满了工匠之气,是没有生气的。而表达是画家主观情兴的感性呈现,“情兴”来自画家对外物的审美观照。外物通过主体的审美感官(“得之目”)进入画家的心灵世界,成为灌注主体主观情感的“意象”(“寓之心”),在情感的推动下,画家借助想象对外物进行自由创造,最后通过笔墨形式传达出来(“形于笔墨”),这样的作品实际上是心物交融的结果,它将主体的情兴与外物的生机结合在一起,构造成一个充满生命气息的艺术形象。较之以“逼似”为特征的临摹作品,自然更具艺术魅力,为画家所推崇。可见,画论家重视主体人格对绘画创作的重要作用,源于其对绘画“兴寄”功能及艺术本质的思考,这既是对元代文人画创作精神的继承,又是与其人生际遇相联系。他们往往借山水以“自娱”“适意”“明志”,使得绘画成为其精神生命存在的重要方式。因此,明代画论家对绘画“兴寄”功能诠释从不脱离画家主体的人格因素,特别重视画家的胸襟怀抱与绘画“兴寄”功能之关系。这是明代绘画“寄兴”理论的重要特点。
需要注意的是,明代画论家所重视的人格,不是指道德意义上人格,而是指一种与世俗相对、超越功利的审美人格,落实在绘画创作中,体现为画家本人的胸襟怀抱。这种审美人格对绘画创作来说,往往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这与绘画作为审美活动的基本属性是一致的。据此,明代画论家强调绘画的非功利性的特点,认为绘画既不为“耳目之玩”,也不“稻粱之谋”①俞剑华《中国古代画论类编》,人民美术出版社,1998年版,第99页。,是画家纯粹的“兴寄”行为。“兴寄”就是绘画作为审美活动的重要体现。从“兴寄”实现的途径来看,“兴”之所以能“寄”,取决于主体胸襟怀抱。为此,明代画家都重视审美心胸的营造,追求一种不为物役的自由创作环境。李日华指出:
姜白石论书曰:“一须人品高。”文徵老自题其米山曰:“人品不高,用墨无法。”乃知点墨落纸,大非细事,必须胸中廓然无一物,然后烟云秀色与天地生生之气,自然凑泊笔下,幻出奇诡,若是营营世念,澡雪未尽,即日对丘壑,日摹妙迹,到头只与髹采圬墁之工争巧拙于豪厘也。②孙岳颁《佩文斋书画谱》,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4年版,第425页。
文徵明所说的“人品不高,用墨无法”,将“人品”与创作直接相关联,就是强调“人品”对创作的决定性作用。这种“人品”不是指道德境界而言,而是指画家“胸中廓然无一物”心灵状态。正如苏轼所言,“静故了群动,空故纳万境”③苏轼《送参寥师.苏轼诗集》,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905页。,因为“廓然”,所以自由,因为“无一物”,所以心静,只有这一状态下,画家才能“写气图貌,既随物以宛转”④刘勰《文心雕龙》,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693页。,形之笔墨,尽得山水情性。反之,若被“世念”所牵制,胸中还有它念留存,心物只能两隔,而不能交融,画家所见只是对象的形体,而不是对象的“生生之气”,形之笔墨,得形似而无情性。
唐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说:“自古善画者,莫匪衣冠贵胄,逸士高人,振妙一时,传芳千祀,非闾阎鄙贱之所能为之也。”①张彦远《历代名画记》,人民美术出版社,1963年版,第15页。虽也认为绘画是“逸士高人”之所为,但他把绘画活动与画家的身份地位联系起来,把“闾阎鄙贱”之人排除在善画者之外,这与文人画的平等意识是不相符的。明代画论家关于绘画与人品关系的讨论是以绘画主体的平等观念为基础的。画家可以是“衣冠贵胄”,也可以是“闾阎鄙贱”之人,与其社会地位没有必然关系。从明代画家生存状态来看,既有在朝的“贵胄之士”,也有在野的,甚至靠卖画谋生的“闾阎鄙贱”之士,他们的社会地位并没有妨碍各自成为名家。从根本上说,强调画家的身份、出处,与绘画作为审美创造活动是相违背的,这一点,明代画论家是非常清楚的。
综上所述,明代画论家从三个角度对“兴寄”与绘画活动间关系进行了深入的讨论。从创作动机看,寄兴是画家从事绘画活动的动力因素,绘画成为画家个人的寄兴行为、抒情方式;从绘画艺术的本质看,绘画的本质是画家情感的物化形态,画家将情感诉诸笔墨形式是“寄兴”行为的实现途径;从创作主体看,画家的人格品质是“寄兴”活动能否展开的决定性因素,这体现了绘画活动的非功利性,绘画是画家进行自由自觉的审美创造活动。这些认识深刻影响了人们的绘画批评方式和笔墨形式的创造观念,使得自苏轼以来重主体情感体验的批评方式在理论上得到正式确立,绘画情兴有效传达成为绘画活动的出发点和批评的主要依据。“传神”不再是人们对绘画批评的唯一标准,而是对画学史上关于绘画与情感之间的关系的系统总结和发展,是明代画论家对传统画学做出的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