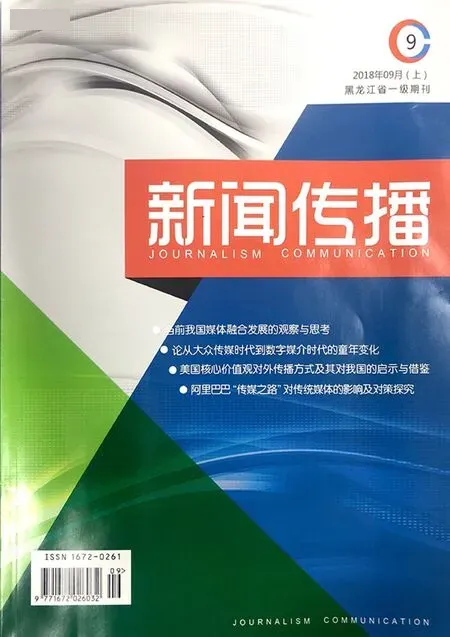浅析互联网后真相时代被污名化构建的真实
(南京师范大学中北学院 江苏 210000)
2016年11月22日,牛津词典将“后真相”(post-truth)一词列为年度词汇,对它的释义为:它指的是这样一些情形,即诉诸情感和个人的信念要比客观事实对形塑公众舆论的作用更大。[1]
造成后真相时代的深层原因在于,社交媒体的发展在某种程度上将个人心理或是社会心理集中放大投射在网络上,而这种投射根植于网民本身的心理特质,但同时也存在不自觉为人所操纵的成分。媒介环境是传播发生的实际情境,而后真相时代则伴生于社交媒介。
一、社交媒体伴生的“后真相”时代
社交媒体的出现真正意义上实现了新媒体“去中心化”的特质。内容生产的门槛降低甚至消失,使得网络传播中的信息量空前暴涨,然而无论是囿于部分信息生产者本身水平的限制,还是一些人为追求流量经济、迎合部分网民猎奇心理,刻意夸大、隐瞒或歪曲信息内容,都使得信息本身的质量良莠不齐。面对大量碎片化模糊化的信息内容,人们很难基于事实本身进行精确的判断,而信息生产者在提供信息中蕴含的情绪与观点,则伴随着模糊的事实不断扩散。随着扩散范围和程度的不断增加,情绪和观点的传播逻辑下将默认信息的真实,随之观点和情绪则取代了事实成为网民集体表达的核心。从信息到情绪观点的置换,这是后真相时代运行逻辑的最初一步。
2017年11月22日晚开始,有十余名家长反映朝阳区管庄红黄蓝幼儿园(新天地分园)国际小二班的幼儿遭受到园内教师的扎针和喂不明白色药片,并提供孩子身上多个针眼的照片,同时有自称孩子家长和知情人士者,在网上编造传播有关园长勾结“老虎团”猥亵幼儿园儿童的信息。事件一出,网民们纷纷示以极大的愤慨。从最早的网络曝光,到警方公开案件的侦破结果,红黄蓝幼儿园虐童事件持续的时间不足10天,然而网络上有关“虐童”“性侵”“老虎团”等几个关键词“热搜”度和讨论程度却远超之前的诸多事件,成为2017年度最引人关注的事件之一。
遍观整个事件在网络上的发酵,我们可以看出网民们的愤怒点集中在“老虎团”猥亵幼童的虚假情节上。而从其叙事框架来看,造谣者刻意将园方、军方、猥亵、幼童几个关键词联系在一起,制造了一个群体对立的矛盾框架,从情绪与观点上刺激网民的神经,最终引发了舆论场巨大的反响。在公安部门尚未辟谣之前,整个舆论场呈现一种被网民主宰的病态狂欢。从信息置换成情绪,再到公开表达的舆论,在社交媒体的发酵中,所谓的“真相”不再是客观的,而只是被建构出的情绪和观点。
后真相时代是随社交媒体而伴生的,但将后真相时代产生的问题完全归咎于媒介技术的发展显然也并不合理。从整个社会信息系统来看,在短期、可视化的信息失真长期发生后,则会对社会总体认知产生较大的影响,而“群体污名化”的大量增加正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一点。
二、从“框架”到“污名”——网络后真相时代被建构的真实
“污名”(stigma)一词最早是用来指代罪犯、奴隶、叛徒等被烙下的身体印记,以“暴露携带人的道德地位有些不寻常和不光彩”。[2]美籍加拿大裔社会学家戈夫曼首次将“污名”的概念引入到社会学中,从具体的实物拓展到抽象层面,包括性格、家庭背景、越轨行为等,并开始将个人层面的污名外延到群体层面,而上文提到的“群体污名化”正是基于这样的意义之上。
“污名化”本身可以视作一种社会总体认知的偏差,而在后真相时代,这种偏差的趋势愈发明显。后真相时代的社会议题,往往并非由传统媒体所抛出,而是由社交媒体用户在网络曝出。不同于传统媒体时代的议程设置,网络后真相时代议程设置的主体呈现多元化趋势,甚至在某种意义上公众议程会反向设置媒介议程,或者与传统媒体“互设”议程。但是,在网络每日庞大的信息量中,能够从中凸显并引人关注的议题,除与网民切身利益相关的部分,更多的是一些足以引起网民震惊的事件,对此类事件,我们姑且称之为“极端化议题”。
在考察人的认知和传播行为中,经常会使用“框架(frame)”这一概念,戈夫曼将其定义为:“人们用来认识和阐释外在客观世界的认知结构,人们对于现实生活经验的归纳、结构与阐释都依赖一定的框架,框架使得人们能够定位、感知、理解、归纳众多具体信息。”[3]个人框架的存在从一定程度上为人认识世界决策事件提供了经验性参考,但从另外一个层面来讲,这样的框架更容易让我们产生长期的刻板印象,从而对于某一类事件有预设立场和预设判断。
2017年8月31日20时左右,在陕西榆林市第一医院绥德院区妇产科,一名产妇从5楼分娩中心坠下身亡。事发后,围绕“究竟是谁拒绝为产妇实施剖腹产”和“究竟是谁该为产妇跳楼负责”,医院和家属各执一词。微博上一些千万粉丝大V开始转发此事件,引起广泛讨论。该议题将“产妇”“被拒绝剖腹生产”“跳楼”几个关键词连接,极端性的情节给网民以极强的冲击力。从该议题在网上被曝出伊始,网民便将舆论压力投向医院或孕妇丈夫一家,网民们此时更多是基于自身的“框架”而对事件进行“脑补”定性。而随着事件的真相大白,人们开始重新谴责医院,并将脑中对于医院认知的框架进行修改,本有偏见者加深偏见,无偏见者也会多少有质疑,尤其如医院这类特殊议题主体,负面性的消息更容易影响受众认知框架。
虽然基于受众认知的主观性,受众框架下“同向解读”“对抗式解读”“妥协式解读”等各种情况均存在,但是网络后真相时代以情绪和观点的迅速传播,舆论场间以一致的声音,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受众解读的高度同质化,因而一旦媒介议程被公众议程所采纳,极易扩大媒介框架对受众框架的影响力,而一旦媒介框架本身涉及对某一群体的负面报道,则更易形成负面刻板印象,随着时间推移和印象的积累,则有可能自然发展为群体“污名”。如“女司机”“坏老人”“新疆人”等群体逐渐蒙受污名,虽还有诸多历史、社会原因,但就大众媒介的信息传播而言,除了网络信息的失实外,社会议程的偏颇、媒介框架的固化也是这些“污名”形成中相当关键的因素。
三、重塑后真相时代崩塌的真相信仰
首先,媒介框架的存在是无法避免的,这是由新闻信息产品的特性决定的,但是在互联网媒体信息容量的解放下,媒体实际上可以将某一事件的所有相关信息以超链接的方式放在一篇文章内,以尽可能全面的方式报道新闻,从而避免因媒介框架的冲突而有意无意间造成社会群体的“污名化”。
其次,随着市场化进程对各类网络信息传播平台的大浪淘沙,幸存下来的平台大多获得了稳定的受众群体,舆论传播在经过了一轮“去中心化”之后,出现了“再中心化”现象。在“再中心化”的趋势中,我们可以因势利导,建立起以“新型主流媒体”[4]为核心,其他专业媒介组织与专家机构为辅的新型互联网信息体系,并借此机会提供给社会公众更多的媒介接近权。这不同于普通用户在社交媒体生产内容传播,而是公众生产新闻或提供线索给新闻媒体,通过新闻媒体的巨大流量寻求关注,当然这样的行为显然要在事实核查制度内进行。
最后,从互联网受众自身的角度而言,不断提升网民的网络媒介素养,提高对个人框架的全面构建能力,是自媒体时代重塑真相信仰的重要保障。媒介素养的提高要求网民充分利用参与、使用媒介及其信息的权利,这种赋权使人在心智上能够穿透媒体所建构的拟态环境,不被媒体左右,更能促使民众进行社会参与,使用媒体表达对公共事物的关心,形成社会共识。拥有较高媒介素养的人,在面对纷繁复杂的网络环境和形形色色的媒体信息时,就可以拥有一副“火眼金睛”,其理性思考有利于净化民间这个大舆论场的风气,为最终社会认知的修正起到积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