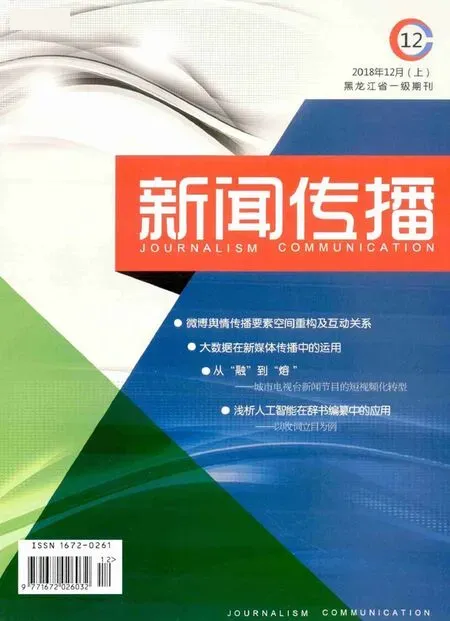符号学视阈下中国文化对外传播的策略研究
(安徽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芜湖 241000)
一、符号学相关理论概述
符号学是研究符号表意的一门科学,国内符号学著名学者赵毅衡认为,“符号是被认为携带意义的感知,没有意义可以不用符号表达,也没有不表达意义的符号,没有意义可以不用符号来解释,也没有不解释意义的符号,符号学即意义学。”[1]索绪尔认为符号由“能指”和“意指”组成,罗兰·巴尔特同样认为“符号是一个包括能指和所指的复合词”[2]。皮尔斯提出了著名的“符号三元论”,他将符号分为“再现体”、“对象”和“解释项”,其中“再现体”就相当于索绪尔“二分法”中的“能指”,他将索绪尔“二分法”中的“所指”分为了“对象”和“解释项”两个部分,强调了符号接受者对于符号意义的影响。后来的内涵符号学将“元语言”和“内涵概念”结合起来,叶尔姆斯列夫提到的“外延”与“内涵”也恰巧对应了皮尔斯所提出的“对象”和“解释项”。艾柯指出,外延是“所指物在文化上得到承认的潜在属性”,而内涵“未必对应所指物在文化上得到承认的潜在属性”[3]。
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茨在《文化的解释》中说道:“我所采纳的文化概念本质上属于符号学的文化概念。”[4]他认为符号学“提供一种语言,是符号行动所必不可少的自我表达-即文化在人类生活中的角色-得到实现”。[5]符号学在传播学的发展过程中也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传播学家马歇尔·麦克卢汉的许多传播学理论中多处使用符号学的相关理论,符号是人类传播的一个介质,人类通过符号交流信息。
二、中国文化对外传播面临的困境之符号学分析
(一)符号“任意性”下西方媒体对中国文化的“神话制作”
长期以来,世界传播领域始终由西方主导着话语权,西方长期以来对中国进行着“神话制作”。赛义德在《东方主义》中曾经说过:“东方被东方化了,不是因为它通过19世纪一般的欧洲人所认为的普通方法被发现‘具有东方色彩’,而是因为它可以被东方化,也就是说,它经受了东方化。”[6]“任意武断性”是符号所普遍适用的,符号的能指与所指既是基于社会习俗的规定,又是没有理据的,符号和意义的结合方式不需要进行论证。西方媒体通过各种符号组合向国际社会传达着中国文化,他们将自己意图的意义置于文本之中,把自己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融入这些文本之中,将选择过滤后的中国文化传达给世界,这种神话制作的方式一定程度上歪曲了国际社会对于中国文化的理解,中国故事常常被妖魔化。
(二)不同社会文化语境下国际社会对中国文化符码的无效解码
克利福德·格尔茨认为只有在一定的社会文化语境中,才能了解交际行为之后的意义,才能使得文化符码能有效解码。文化符号作为一种能指优势符号,能指不需要明确地指向所指,而是独立形成一种自身的价值,如果置于另一种不同的文化体系中,这种能指所创造的价值和意义可能就不复存在了。国际社会传播领域里,中国文化符码的解码深受多元文化的社会文化语境影响,各国文化、社会和个性结构等都不尽相同,形成了非常复杂的意义语境,这加剧了不同国家和民族的人民对中国文化解读的难度。
(三)“解释项”下中国文化符号“接受度”问题的亟待解决
传播过程是信息“编码-译码-解码”的循环过程,传播最终的效果与解码的过程密不可分。拉斯提埃尔认为,对于符号表意来说存在接受原则,即愿意或者不愿意接受符号所携带的意义,这是一种基于受众个体差异性的原则,对符号传达和表意效果有至为关键的影响。中国的对外传播中存在很多仅仅是进行宣传而没有进行传播的现象,一味的宣传式和灌输式的传播并不能使中国文化被国际社会所接受和认可,这种不足一定程度导致一些受众对了解甚至接受中华文化产生负面情绪,从而导致中国文化符号的“接受度”下降。
(四)“符号载体”多样性下对外传播中文化符号载体的不足
符号载体作为发送者意图的承载者,是符号过程中充当中间环节的存在,任何符号都需要符号载体,文化符号亦是如此。赵毅衡在《符号学原理与推演》中举例,“文字是载体,印刷是媒介,图像是载体,电视等是媒介。”[7]中国的对外传播活动其实非常多,但是没有将中国文化充分地载入这些文化符号载体中,这些文化符号载体的能指所能体现的所指十分有限;另一方面在对外传播中,我们缺少更多类型的文化符号载体,很多情况下是官方发声,缺少民间社会的文化符号互动,这也限制了中国文化的对外传播。
三、从“符号三元论”看中国文化对外传播策略的完善
(一)从“对象”到“解释项”——确保国际社会对中国文化的正确解读
“解释项”在符号的过程中直接影响到符号传达和表意的效果,文化符号的解码直接关系到对“对象”的解释,我们要重视从“对象-解释项”的过程。全球化浪潮下,意识形态作为文化的元语言是纷繁复杂的,文化符码的有效解码必须要深入社会文化语境,中国文化的对外传播需要更多关注受众个体的差异性,要考虑到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选择适合某一地区的方式进行传播。
刘建明曾在《全球化语境下中国媒介对外传播的策略》一文中建议采用西方的叙述方式去讲述中国故事,在中国媒介对外传播从业人员队伍中更多地引进外籍人员以减少跨文化传播受众的心理排斥感。[8]除此之外,笔者认为,还可以利用中国文化与其他文化的共性进行中国文化的宣传,在相似的文化语境之下,对中国文化的接受度会大大提高。除此之外,我们还要提高自身文化符号载体以及其携带意义的可信度,媒介的公信力需要提升,不要刻意去隐瞒负面的内容,要做到公开、公正、公平,及时、准确、客观。
(二)从“对象”到“再现体”——加快对中国文化符号载体的优化
“对象”到“再现体”的过程是一个符号化的过程,这个过程与人的主观能动性密切相关。中国在对外传播文化的时候,应该赋予中国文化符号载体以更多的文化意义,体现出自己的一套文化价值观,增强这些文化符号载体的文化内涵。作为中国文化符号的发送者,我们要将意图意义尽可能地转变为文本意义,同时要减少文化符号载体中的“噪音”成分,使得对外的文化传播能够传递更多赋有意义的文化符号。
洛特曼注重阐明“再现体”和“对象”之间的关系,认为叙述文本主要有两种途径,一种是语言符号的形式,通过文本篇幅的扩展来叙述,另一种是图像符号的形式,通过变形和内部成分的换位来叙述。中国文化对外传播的过程中要注意叙述的方式和方法,遵循国际公认的客观真实性和新闻专业主义,外交场合里用词用句的精准和恰当,中国文化纪录片从拍摄到后期制作都经过仔细地斟酌等,从而能将我们想要传递的中国文化更好地融入它的符号载体中,使得中国文化能够更好地被感知。
詹姆斯·罗尔认为,商业社会语境中的文化就是一种资本,可以被消费。正如罗尔所认为的一样,在资本全球运作的环境下,文化可以成为一种全新的资本形式。中国文化也可以成为一种资本,除了各种文化产品外,中国的文化风格、文化理念也可以被“消费”。如同张碧认为的那样,“文化生产相对于此前的任何一个时代,都更加依赖各种科技手段的促进和推动。”[9]全球化浪潮下,中国文化想要成为一种资本,需要依托先进的科技手段,我们需要借助新的媒介技术向全球传递中国的文化符号、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把中国文化送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