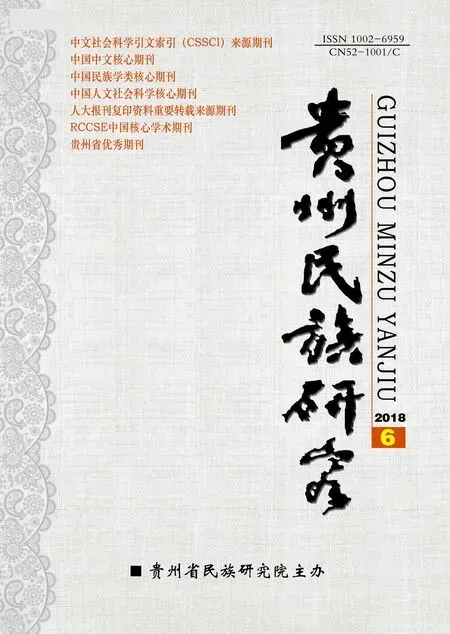西域佛教美术文化历史与贡献
董馥伊
(新疆师范大学 美术学院,新疆·乌鲁木齐 830054)
西域处于中国最西部与中亚腹地,因为独特的地理位置,自古迄今,西方祆教、景教、摩尼教、佛教、伊斯兰教等宗教相继入驻此地。其中要数印度输入的佛教最为盛行,并以其独特的美术造型形式,彰显其文化内涵,深受西域各族人民的爱戴与支持。
据佛教文化学者陈世良为“丝路佛光丛书”所写“总序”提及:新疆在地理位置上位于“丝绸之路”的中段,其中有大量的受到中外学人、游子、释门弟子极大关注的佛教文物。《中国美术全集》 《中国石窟》等大型类书的“新疆卷”中均公布了珍贵的佛教文物图片,与此同时,国外一些国家如德、法、英、日等学者们均先后刊布出各国从新疆掠走的与佛教相关的部分文物照片。这些文物佐证,更是引起了学界对新疆的更多关注。
陈世良先生认为:作为中国佛教中重要组成部分的西域佛教,其目前的研究现状令人堪忧。整体研究包括其脉络的整理以及基础材料的搜集;佛教文化和佛教艺术的体系化研究等方面相对滞后,与西域佛教应具有的历史地位相差甚远。[1]
我们追寻古西域佛教美术中的珍贵遗产与文化基因,可通过国内外多年来的诸多研究成果,尤其是对西域佛教艺术(美术)与丝绸之路文化的研究,梳理西域美术的研究重点与解决的问题,确认西域美术研究在中外经济、文化交流中的历史价值与现实作用。
一、丰厚的西域佛教美术文化遗产
据《新疆百科知识辞典》记载:“西域,意即中国西部的疆域。最早见于《汉书·西域传》。此后,以迄于清,历代著作,多以西域呼之。其界定范围有广、狭义之分[2]。按照狭义与广义西域的史地文化概念,古代新疆为“我国历代中央及地方政权所管辖的地方。”一般为“西域三十六国”,此论始见《后汉书·西域传》。三十六国分别为:乌孙、龟兹、焉耆、若羌、楼兰、且末、小宛、精绝、戎卢、扞弥、渠勒、于阗、皮山、西夜、子合、蒲犁、依耐、莎车、疏勒、尉头、温宿、尉犁、危须、墨山、狐胡、车师、劫国、依耐、无雷、难兜、大宛、捐毒、休循、桃槐、蒲类、西且弥。历史上西域诸国均在匈奴以西,乌孙之南,多在天山南北,葱岭一带。分布于中西文化交流的丝绸之路沿线。
此文所涉猎的西域为狭义所指,是古代新疆旧称,在两汉至宋元时期这里的佛教文化占有绝对优势。解放以后,党和人民政府尊重新疆各族人民的意愿,可以自主选择宗教信仰,佛教文化仍具有一定的份额。
令人深思的是,20世纪末21世纪初,在印度输入的佛教基本消失的新疆,却一次次掀起了发掘、整理、研究古代佛教文化,特别是探索与研究佛教美术的学术热潮,这为我们研究古代新疆的佛教文化带来机遇。
西域佛教美术包括古代新疆地理历史时空中所产生的佛教绘画、雕塑、建筑、器物与相关的佛教文化遗产。在遗存的无论是数量与质量都很大与高乘的西域佛教文化宝库面前,佛教美术仅是佛教艺术的一个组成部分,它包括佛教雕塑艺术、绘画艺术、石窟艺术和建筑艺术等门类。[3]
相比于林林总总的宗教与世俗文化著述之中,在研究西域佛教美术的学术成果中,如中国美术全集新疆分册、及其此地佛教绘画、雕塑、建筑画册与学术论集中,要数对西域美术文化遗产的介绍与研究成果的比例较大而广。就拿在当今丝绸之路与西域文化产生广泛影响,享有盛誉的《丝绸之路造型艺术》[4]一书所显示的重要学术数据,就能掂量出西域佛教文化的重量。
按照其佛教文化总论与分论来审视:总论文章共四篇:阎文儒《新疆天山以南的石窟》,贾应逸、赵霄鹏《艺苑妙境—灿烂的新疆石窟寺艺术》,黄国强《西域壁画的视觉形式剖析》,吴焯《从考古遗存看佛教传入西域的时间》。分论包括西域佛教美术所在地高昌、龟兹、和田、中亚文章共十八篇。
其中高昌佛教美术文章四篇:李铁《高昌乐舞图卷》,谭树桐《阿斯塔那唐墓俑塑艺术》,邵养德《高昌掠影—兼谈〈女娲和伏羲图〉》、贾应逸《吐峪沟石窟探微》。
龟兹佛教美术文章十一篇:张光福《库车的壁画艺术》,霍旭初、王小云《龟兹壁画中的乐舞形象》,姚士宏《克孜尔的佛传四相图》 《克孜尔175窟的生死轮图》 《龟兹佛教与石窟》 《叙利亚画家在克孜尔》。王伯敏《克孜尔石窟的壁画山水》、贾应逸《克孜尔17窟壁画艺术特色》,霍旭初《龟兹舍利盒乐舞图》,徐建融《龟兹壁画的人体画法》,袁廷鹤《龟兹风壁画初探》。
和田佛教美术文章两篇:张光福《尉迟跋质那和尉迟乙僧》 《尉迟乙僧的绘画及其成就》。中亚佛教美术文章一篇:吴焯《来自中亚的北齐画家曹仲达》。从中显示的西域佛教文化我们可以发现,其中相关论文以天山以南佛教石窟艺术研究为主,并以龟兹佛教石窟艺术研究为主,其他地区佛教石窟及其美术家与作品研究为辅。
据黎蔷先生《新疆美术概说》一文将古代西域与新疆美术分为四大部分:(1)史前原始宗教美术,(2)佛教时期美术,(3)伊斯兰教时期美术,(4)新中国建立前后美术。相比其他宗教与世俗造型艺术而言,西域佛教时期美术较为繁荣与发达,遗存的佛教石窟绘画与作品比较多,西域佛教文化旷日持久地影响着中国内地的石窟艺术发展。[5]
贾应逸、祁小山著《佛教东传中国》一书亦考述:佛教于公元前后传入中国。传播路线,主要以沟通东西方陆路交通的大动脉——‘丝绸之路’为主。地处祖国西部、位居东西方陆路交通——丝绸之路要冲的新疆较早接受了佛教,尤以距印度、罽宾最近的于阗为最早。此书“概述”阐释了古代新疆是印度佛教经西域输入中原地区的天然孔道,并论证了西域佛教东传在丰富中国传统美术文化过程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印度、希腊、波斯和中亚文化中的精粹艺术如绘画、音乐、工艺以及艺术理念等方方面面、五方杂俎,都借助着佛教东传而来到中国。
同时此书还指出在古代新疆佛教美术文化区域,所酝酿、形成的“西域佛教画派”的独特艺术风格:“古代的于阗人将流传于自己人民中间的传说与佛教联系起来,往往还把这些传说表现在佛教艺术中。如鼠王、传丝、毗沙门天等。于阗的造像风格,早期与犍陀罗的石雕相近,也曾吸收了马图拉艺术的成分。但其突起的面型、绘画中的铁线却独具风采”。后者大大影响了我国中原地区的佛教艺术,以尉迟父子为代表“于阗画派”的“用笔劲紧如屈铁盘丝”“用色沉着,堆起素绢而不隐指”和“匠意特险……身若出壁”特点在我国绘画史上享有盛誉。“于阗画派”的美术特点,在现存的龟兹壁画中表现最为明显。[6]
二、西域佛教美术史学研究
在我国,关于西域佛教美术史的研究与探索兴起于20世纪初,成熟于20世纪末与21世纪初。最早的综合性论著如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汤用彤《隋唐佛教史稿》,黄文弼《新疆考古之发现与古代西域文化之关系》,王子云《从长安到雅典》,常书鸿《新疆石窟艺术》,阎文儒《中国石窟艺术总论》,金维诺《龟兹艺术风格与成就》,苏北海《丝绸之路与龟兹历史文化》 《新疆天山以南的石窟》,沈福伟《中西文化交流史》等。
后来产生的则是较具体的相关论文与著作,如宿白《克孜尔洞窟阶段划分与年代问题的初步探索》,谭树桐《龟兹菱格画与汉博山炉》,霍旭初《西域佛教文化论稿》,贾应逸《高昌石窟壁画精粹》,林梅村《汉唐西域与中国文明》,柳洪亮《高昌石窟概述》,朱英荣《论新疆克孜尔千佛洞形成的历史条件》,沈康身《丝绸之路与源远流长的石窟艺术》,吴焯《克孜尔石窟壁画画法综考》、《佛教东传与中国佛教艺术》,赵丰《美术考古概论:丝绸之路》,张俊《龟兹石窟壁画之宗教文化研究》等。
西域佛教美术有着特殊的史地文化与艺术特色,故此,需要从文化宏观与艺术微观方面进行综合考察。其理论则倡导从西域历史文化与美术艺术角度予以全面、系统、科学的构建。
阎文儒先生在解放初期对新疆佛教石窟进行实地调查与研究,撰写了一系列学术考察与统计的长篇论文,如在《新疆天山以南的石窟》中所统计有:(1)拜城克孜尔石窟,(2)森不塞姆石窟、(3)玛扎伯哈石窟、(4)克子喀罕石窟(克孜尔尕哈)、(5)库木土拉石窟(库木吐拉)、6、焉耆七格星明屋与石窟、(7)柏孜克里克石窟、8、胜金口的寺院遗址、(9)吐峪沟石窟、(10)雅尔湖石窟、(11)石窟造像等。还撰写《龟兹境内汉人开凿汉僧住持最多的一处石窟——库木土拉》。1999年新发现的位于库车县城北面,天山支脉克孜利亚山的库木鲁克艾肯沟谷内的“阿艾石窟”。开凿时间为公元八世纪安西大都护府设龟兹之时。如洞窟中的“观无量寿经变”“说法图和观音”“卢舍那佛像”“药师佛像”等很有学术价值。
据阎文儒在《中国石窟艺术总论》[7]中论述:“天山以南各石窟群中的塑像,由于宋、元以来,新疆佛教一蹶不振,因而佛教造像俱遭破坏。清末,外国考古学家进入新疆各地,将还残存的一些造像又全部劫走。近年来,新疆文物工作者在库木土拉石窟新发现了两个洞窟,其中新2号窟尚有一尊佛像,是新疆石窟中保存至今的唯一塑像……还有库尔勒那克沙特拉石窟出土的半身菩萨像……以上造像,最早的当四、五世纪,最晚之作品约当八、九世纪的精美的造像作品……至于各期壁画的画风,不只可以说明龟兹诸地的绘画艺术发展过程,而且也可以补证中原地区佛教艺术的发展规律”。
上述历史文献与资料基本囊括了新疆境内古代佛教美术主要文化遗产与学术理论基本观点。当然较为完备的是后来集全国美术学术理论工作者之力编纂的《中国美术全集》 《中国美术分类全集》等大型类书的“新疆卷”。
仲高在《西域艺术通论》一书专设“西域佛教艺术”,提及西域佛教美术的内容、形式与重要历史地位。他指出,因自然与人为原因,于中世纪“天山以南诸绿洲城郭佛教先后走向衰亡,千年西域佛教艺术的踪迹也只能在那些毁坏殆尽的佛教石窟、寺院和雕塑、壁画遗址、遗迹中寻觅了。这些遗址、遗迹主要是:于阗热瓦克,丹丹乌里克,约特干佛寺遗址,鄯善米兰佛寺遗址,龟兹克孜尔石窟,疏勒莫尔佛教遗址,焉耆佛寺遗址,高昌吐峪沟石窟等”。西域佛教美术以强大的生命力“不仅存在汉化的诸如于阗、鄯善、龟兹、高昌等区域性佛教艺术,还存在汉传佛教艺术、藏传佛教艺术等形态。……汉传佛教艺术也是与中国传统的绘画、雕塑、音乐、舞蹈相融合的产物。汉传佛教艺术以其巨大的能量足以在西域的佛教艺术中占有重要地位。”[8]
论及西域鲜为人知的佛教美术家与代表性绘画作品,我们可以参阅张彦远《历代名画记》,以及张光福《尉迟跋质那和尉迟乙僧》 《尉迟乙僧的绘画及其成就》与吴焯《来自中亚的北齐画家曹仲达》等学术论文。
其中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卷九记载:“尉迟乙僧,于阗国人,父跋质那。乙僧国初授宿卫官,袭封郡公,善画外国及佛像,时人以跋质为大尉迟,乙僧为小尉迟。画外国及菩萨,小则用笔紧劲如屈铁盘丝,大则洒落有气概”。另外,《历代名画记》中记载曹仲达:“本曹国人也。北齐最称工,能画梵像,官至朝散大夫。国朝宣律师撰《三宝感通记》,具载仲达画佛之妙,颇有灵感。僧倧云:‘曹师于袁,冰寒于水,外国佛像,亡竟于时’。
吴焯先生指出,曹仲达的“曹衣出水”式画法,是“中国佛像画艺术发展和中外文化交流的必然结果”。还说,“东汉末年,印度佛经由中亚传入我国新疆,继而进入内地,至南北朝时代,佛教寺院已盛行,图绘寺壁的佛画得到空前的发展,许多来自印度和中亚的画家参加了绘制佛像的活动,北齐曹仲达即其突出的代表”。
魏长洪在《西域佛教》一书“绘画艺术”之“尉迟乙僧的佛画”中写道:“尉迟乙僧的画法对唐代及唐以后的绘画有重大影响,并且其影响远及朝鲜、日本,为中国美术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9]
陈兆复主编《中国少数民族美术史》谈到“西域民族画派”勃兴原因与历史文化影响时指出:“西域民族画派与唐代美术交融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是唐太宗对各民族一视同仁的思想起到了重要作用。二是唐在贞观十四年(640年)到长安二年(720年)间把天山南北归于唐朝版图中,设四镇,号称安西四镇。但在这里设立了两种行政机构系统,其一即与内地相同的州县制。另一是专设于边区的护府领都督府,对兄弟民族内部社会制度给予保留,而使其同新的行政组织结合在一起,因此对西域各族经济文化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三是西域各族民族文化得到进一步发展。以上因素促使西域画派艺术得到繁荣发展。”[10]
三、西域佛教美术文化关系探索
著名学者季羡林先生在《佛教与中印文化交流》一书中论断:“新疆是全世界上惟一的一个世界四大文化连接的地方。它东有中国汉族文化,南有印度文化,西有闪族伊斯兰文化和欧洲文化。连古代希腊的雕塑艺术,都通过形成于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一带的犍陀罗艺术传入新疆,再传入中国内地。……新疆这个地方实在是研究世界文化交流的最好的场地。”这里汇聚了不同的西域宗教文化,对此我们应该综合性比较研究,并且还应追溯西域佛美术文化与国内外相互影响的艺术关系。[11]
王子云在《新疆拜城赫色尔石窟》一文中曾发现,天山南麓“赫色尔石窟”(即龟兹克孜尔石窟):“壁画的一般造型和技法,属于犍陀罗的艺术样式,即希腊—波斯—印度式。这种样式的特点,主要是表现在衣褶的紧窄和人体肌肉的晕染。以及部分裸体的形象。但在赫色尔,它又结合了地方成分,并吸取了中原民族的样式,即有多民族传统的具有新鲜气质的艺术。它与中原文化、新疆地方文化,中印度笈多文化,北印度犍陀罗文化,波斯萨珊朝文化,以及希腊罗马的文化成分,都有着直接的关系。……它蕴含着崭新的形式,这样就更值得我们在研究遗产和中西文化交流的问题上对它特别加以珍视”。
王镛先生主编《中外美术交流史》在“东渐中国西域”一章中考察发现,在塔里木盆地疏勒地区图木休克的木雕《佛陀坐像》,“具有笈多萨尔纳特样式佛教的特征。这尊佛像以禅定姿势端坐,袈裟下摆一任犍陀罗旧制呈半圆形在双膝之间垂落……佛像拇指与食指之间的缦网(三十二相之一),亦属于笈多式佛像的造型特征。”从而得知“印度、犍陀罗佛教美术相继输入于阗、疏勒、龟兹、高昌等地”。另外此书还以龟兹、高昌地区的佛教美术代表作为例指出:“龟兹地区的佛教遗迹以石窟为主,包括克孜尔石窟、库木吐拉石窟等十余处,其中克孜尔石窟规模最大,早期克孜尔壁画深受犍陀罗艺术和印度传统绘画的影响。高昌地区的吐峪沟石窟、伯孜克里克石窟和吉木萨尔高昌回鹘佛寺遗址等地的泥塑、木雕、幡画和壁画,亦受到经龟兹、焉耆传来的犍陀罗艺术与笈多艺术的影响,而中国内地艺术的影响更为强烈。西域南北两道最终总凑敦煌、犍陀罗艺术与笈多艺术的影响与中国内地艺术交相汇合”。
说到西域佛教美术文化与唐代艺术发生的关系,及其“西域画”在“中西文化交流”中所具有“重要的地位”时,陈兆复主编《中国少数民族美术史》指出:“在唐代,出现来不少有成就的绘画艺术家。其中尉迟乙僧为代表的西域画派尤为突出。西域画是中西文化交流的结晶,民族艺术的奇葩,不仅在中国美术史上有其重要的地位,而且对今后如何吸收外来艺术融化于民族艺术之中,提供了非常有益的借鉴”。
当然上述“西域画”在中国美术史上是一个大概念,不仅在古代新疆,亦在中原、江南地区流传而形成重要流派。西域佛教美术包括西域人士绘制,人士创作的反映西域古族生活场景的绘画作品,如由梁萧绎所作的描绘西域与外国贡使的《职贡图》画卷,据吴升《大观录》记载,其原画:“绘入朝番客凡二十六国,今仅存十二国,如西域龟兹、波斯、胡密丹,以及滑国、狼牙修、邓至、周古柯、百济、倭国、呵跋檀、白题、末国等胡夷古族国度”。
再有需指出的是西域佛教不仅包括由印度输入的大乘教、小乘教与密教等,亦包括在中国生成的汉传佛教与藏传佛教,后者俗称“喇嘛教”的藏传佛教亦为中国民族佛教的一个重要分支,与新疆佛教发生密切关联。关于藏传佛教及其美术文化输入西域历史,据魏长洪等著《西域佛教史》一书指出:藏传佛教传入西域的时间,至今仍未发现文献的具体记载。今在新疆和田地区发现的“欢喜佛”塑像,属于藏传佛教的塑像。“欢喜佛”是藏传佛教密宗的本尊神,即佛教中的“欲天”“爱神”。经专家考定,“欢喜佛”塑像约为10世纪末或21世纪初的文物,表明藏传佛教此时已传入和田地区。近代在新疆吐鲁番地区发现的11—13世纪期间的藏文佛经,进一步佐证藏传佛教在新疆传播地区的扩大。
意大利著名学者马里奥·布萨格里在《中亚绘画》一书对西域佛教美术甚为赞赏,他特别指出:“在所有的中亚艺术中,库车绘画实实在在可划入其高水平之列”。根据国内外所刊布的大量研究成果,在中亚、西亚与西域宗教艺术之中,不仅龟兹佛教绘画,天山南北历代的佛教美术文化亦“可划入其高水平之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