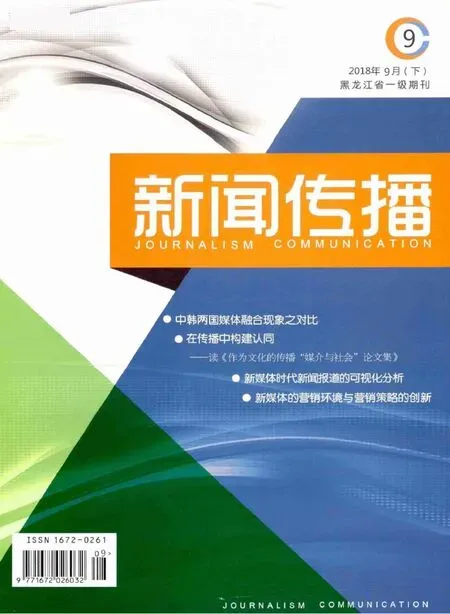文化传播视域下的文化史重构
——评余辉《隐忧与曲谏——清明上河图解码录》
(复旦大学 上海 200433)
一、创作背景与书目概况
2005年的北京《清明上河图》研究峰会将张择端版《清明上河图》的研究带向了新一轮的高潮。在1960年至2000年的第一,二轮研究浪潮中,国内外的《清》卷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核心问题上,即1.张择端版《清》卷是否为实景绘画,2.卷中表现的季节是否为春季清明时节,3.张版《清》卷的绘制年代到底是宋亡之后,还是之前。
如果说前两个浪潮中,国内研究与国外研究基本呈现齐头并进的样式,那么2005年以后的第三个浪潮中,国内研究学者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2005年至2015年十余年间,国内的《清》卷研究长篇著作的数量是前45年著作数量的三倍有余。如果说以往的《清》卷研究框架更像是传统意义上基于考古的传统史学研究,即王国维与陈寅恪的“考古证据与文献彼此印证”[1]的研究框架,第三次浪潮中的《清》卷研究明显呈现出了传统史学向新文化史的转向。《清》卷的研究不再是拘泥于对古本的考据,而更多的是将此卷作为一个起点去还原北宋的一段文化社会史。
在这样的契机下,余辉的《隐忧与曲谏——清明上河图解码录》以一个修正者,更是建构者的身份出现了。仅从这个题目便能见出其文化史研究的样态,即以张择端作《清》卷的意图作为全书的逻辑脉络与纲要,重新有机地整合考古与文献证据,从而达到以《清》卷作为一个支点,还原北宋末年危机四伏的社会生态与一个具有文人理想的宫廷画家在面对这种危机之时的责任感与勇气。
全书在第一章便着力讨论张择端的故乡与其“习绘事”之前为应对科举的努力,这在以往《清》卷研究中并不常见。紧接着的二,三,四,六章则对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清》卷研究中的核心问题逐一做出了自己的回答,如《清》卷到底是实景绘画还是理想城市,画的到底是清明还是秋季,到底是画于宋亡之前,还是之后。而第七,八两章则是整本书的最精彩的部分。作者通过有意识地提取了《清》卷中12处细节,对应了12处宋末危机,道出张择端藏于《清》卷中的12个恳切谏言。而第八章更是通过分析印证自宋太祖以来的“文德治国”的谏言体系到了北宋末年时的境况,来反证张择端以画谏言的可操作性与可能性。而全书最后对于张版《清》卷与后世的明代仇英版《清》卷与清代陈枚等人的《清》卷的比较,将张择端殊于明清宫廷画家的儒生良心与责任表露无余。张版《清》卷长期以来由于受到金人跋文影响而被忽略的深切用心也终于在一次次的努力之下被层层展开。
二、从余辉著作看文化传播视域下文化史构建的转向与趋势
纵观全书,最可贵之处除去作者的严谨详尽之外,更重要的是作者突破了《清》卷之传统史学研究的条框,将其拓展到新文化史层面上的研究。众所周知,传统艺术品的研究在国内研究中多出现在两个研究框架下,一是历史学,特别是考古研究中,二是艺术史研究中。余辉却进一步将《清》卷的研究顺着史学研究转向的大趋势推向了下一个阶段,即放弃传记式的编年考或者精英范式的传承考,转而寻求对一个历史片段的多维还原。
对于历史片段的多维还原在第六次史学转向时,直接波及了考古、人类学与艺术史研究。在中国历史中,社会主流的意识形态在很大程度上被直接表述为精英意识形态。如果仅仅通过文献去印证考古发现,那处在边缘地带的寻常人的思想与生活多少会被忽略。历史并不是精英史,而历史的文化史转向正是努力将新鲜的血液注入到价值观单一的传统历史中。正像20世纪80年代理查德布昂纳克在总结新文化史、对以往史学研究的反抗中所说的,“这是一场对既成社会史、经济史和人口史的一种突发批判”[2],在这种爆发的批判中,传统文化唯精英的偏见也将被以一种更广泛的文化概念所代替。
突破这种框架的方法是一种几近浪漫的新文化史学。反映在余著上,便是其通过既大胆又小心地推测张择端作画的意图去重新结构证据的努力。余著对于《清》卷证据链的组织与考证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对于传统文献中主流文化观与精英对于《清》卷的评价的批判与疏离。由于科举的失败,张择端作为儒生的身份远不及其作为宫廷画家的身份来得引人注目;又由于徽宗好大喜功,奢靡无度,且众所周知的喜欢吉利,加之北宋末年发达的商业社会所导致的审美世俗化倾向,使得主流艺术审美的意识形态便因此而好浪漫精致,喜祥繁盛。这也是《清》卷被徽宗阅完即转手赠人的重要原因。最后再纵观《清》卷研究长达60多年的历史,2000年以前的主要参考文献除去《清》卷前后的题序与跋文,便是南宋孟元老的《东京华梦录》。而偏偏北宋亡之后,南宋诸公颇有思乡之念,邓之诚在《东京梦华录注自序》中坦言,“绍兴初,故老闲坐必谈京师风物……《清明上河图》卷至镂版以行。”[3]宋朝遗老们对于亡宋繁荣生活的追思和偏安一隅劫后余生的庆幸,使得《东京梦华录》读来竟也只衬出《清》卷与梦中故都的繁华喧嚣,一片唏嘘之中,一众掩卷思乡的人又怎么愿意去顾得深藏其中的笔笔恳切之谏?余著正是整合起了一个又一个不那么主流又刻板的标签,将张择端的儒生身份,徽宗虽奢靡但依然受谏的事实联系起来,并对《东京梦华录》及《清》卷中后人,特别是金人的跋文保持批判与惊醒,才能最终以张择端画谏的线索,重现一个丰富的北宋末年。
与余著同时代的《清》卷研究中,亦有一本关注到了《清》卷中呈现的社会矛盾,即曹星原女士的《同舟共济——〈清明上河图〉与北宋社会的冲突与妥协》。在曹星原看来,《清》卷的主题是北宋末年王安石变法所导致的社会紧张和同舟共济的“协作”。然而正如在上文论述中所提及的,曹著正是对居于主流的审美意识形态的过于信任,仅凭借“徽宗既不具备欣赏带有强烈平民意识的对下层社会的描绘,更无法忍耐李成、郭熙一派画家的风格”[4]就断定作为宫廷画家的张择端不可能于徽宗年间绘制此画。这个结论也正是同样的信任使得她就没有立体参考其他证据,如徽宗的听谏和张生的儒学教养所致。又如,在颠覆性地将卷首即将遇难的船解释为对于北宋末年社会危机的隐射并无什么不妥——这甚至正是政治文化史的浪漫之处,即大胆地假设。然而,最后将船夫试图救船的行为理解为整个社会的在应对危难时的同舟共济,便多少有些欠妥。那一船垂手而立的乘客和一桥继续赶路的行人呢,又在曹著的同舟共济的隐喻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但凡曹女士撇去一些徽宗的刻板印象,亦或相信一个未中举的宫廷画家也能在特定的条件下做一件不那么主流却也合乎逻辑的事——勇敢地画谏;并且放弃对于君臣齐心君民共勉的理想政治的幻觉,其著作中对于证据的梳理与证据链之间的逻辑便会更为清晰与丰满。
三、文化史重构对于文化传播的影响
新文化史对于文化史的重构为文化传播带来了诸多影响。而其中最重要的便是多维的历史建构重新定义了历史学意义上的“真实”。背离与主流意识形态的文化史在传统史学研究中常常被忽略。然而,以这样的文化史为切入点往往能够对单一维度的史学“真实”进行有机地修正。以微观史为例,阿尔夫吕德科曾做出这样的归纳:“日常生活史即利用文化和社会人类学的手段,努力重建和解释个人的行为与经验同物质生活、机制、过程等之间的相互关系”[5]。放在余著中,便是从张择端的儒生身份到其不顾风险而向徽宗进谏之间的逻辑环节。1.张生曾学儒并应试,2.徽宗年代社会的确有艺谏之风。亦有两个间接依据,一是元代李祁做“忧勤惕厉观”[6],二是后世明代邵宝跋文中“令人反复展卷,触与目而警于心”[7]的跋文。不管是张生的儒生身份还是李祁与众不同的跋文,均不是主流的意识形态。然后,以这两处证据为支点,余辉构建了一个新的《清》卷阐释系统,并对原来的系统进行了有机地修正。也是因为通过余辉的建构,以《清》卷为基础的宋史呈现出了新的可能性。
也正是在一次次对主流意识形态的梳理中,历史的“真实”变得愈发丰满。这种丰满也保证了文化传播过程中话语权的平等与叙事的多样性,而历史的多元叙事性在这种建构意义上受到了有效地保护。文化传播过程中的由资本和政治意识形态所带来的文化霸权主义的权威与影响在这种多元建构中得到消解。而在保护文化多元性这种行为的本身,也就意味着参与建构了平等且开放的社会公共话语空间。张择端《清》卷研究在对主流叙事背离的基础上又呈现出了一种全新的宋末社会史解读模式,而这种重构终将通过对历史的不断重构而更迭整个文化传播的模式。
——《宋代徽宗朝宫廷绘画研究》评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