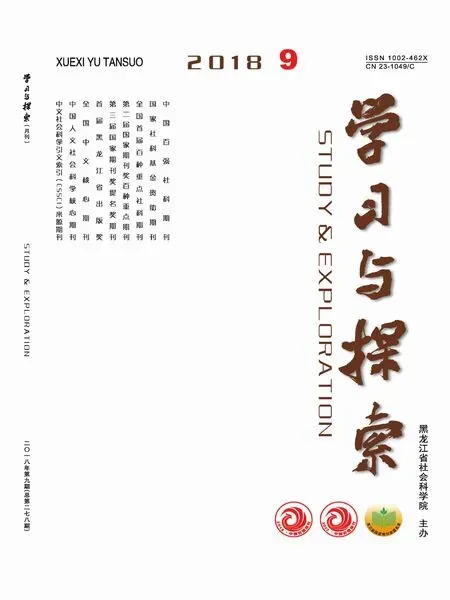激进主义的突围与挫败
——斯托克利·卡迈克尔的“黑人权力”思想探析
安 然,陈至清
(北京师范大学 历史学院,北京100875)
美国黑人民权运动大体呈现出温和主义和激进主义两种潮流,前者以马丁·路德·金和南方基督教领袖会议(Southern Christian Leadership Conference,SCLC)所倡导的非暴力行动和融入主义(Integration)为代表,后者以马尔科姆·X、黑豹党等主张的暴力抗争和分离主义(Separatism)为典型。激进派在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掀起的“黑人权力”(Black Power)运动,成为黑人民权运动和举国媒体关注的焦点。时任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Student Nonviolent Coordinating Committee,或简称 SNCC、“SNICK”)主席的斯托克利·卡迈克尔(Stokely Carmichael)作为这场运动事实上的代言人,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
20世纪80年代以来,聚焦于重大事件、著名人物的民权运动研究经典模式被打破,以地方性组织、运动和个人为主题的长时段叙事模式兴起,美国学界出现了一系列关于“黑人权力”运动和卡迈克尔的重要研究成果。克莱伯恩·卡森(Clayborne Carson)的《在斗争中: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和60年代美国黑人的觉醒》一书梳理了“黑人权力”运动的来龙去脉,并对其做出了有保留的历史评价:“黑人权力口号具有一定的模糊性,因而它更像是一种情绪的宣泄而不是思想的表达”[1]218。与此相反,彭尼·约瑟夫(Peniel E.Joseph)对卡迈克尔的激进性及其历史意义给予了充分肯定。他认为卡迈克尔的思想是连接民权运动温和派(如马丁·路德·金)和激进主义者(如马尔科姆·X)的纽带[2]319,同时他的实践触及了底层与精英、政治与社会、地域和性别等丰富的维度,最终将年轻一代激进派争取民主的斗争推进到了新的阶段[3]。斯图尔特(Charles Stewart)大致认同约瑟夫的观点,认为“黑人权力”的表述具有双重激进性,同时挑战了现行体制和民权运动旧有的框架[4]。加拉赫尔(Victoria Gallagher)的观点较为中立,认为卡迈克尔充分意识到了意识形态动员的战略意义,但同时将黑人的自决与自由推向了一种没有实质的逆反[5]。此外,还有学者从不同角度探讨了卡迈克尔的“语言激进主义”(Linguistic Activism)[6]及其所领导的黑人权力运动的国际性[7]和地方性等[8]。
相比之下,国内研究多集中于卡迈克尔曾任职的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及其所领导的“黑人权力”运动,例如谢国荣的《1960年代中后期的美国“黑人权力”运动及其影响》[9]、《美国联邦调查局对民权组织的监控——以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为中心》[10]、梅祖蓉的《美国“黑人权力”运动:公民权运动中的极端主义》[11]、杨云志的硕士论文《“从非暴力到黑人权力”——美国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SNCC)研究》等[12],并未深入探讨卡迈克尔的生平和思想。
卡迈克尔是20世纪60年代美国民权运动中的流星式人物。他以“黑人救星”的形象高调进入公众视野,最终同时为民权运动的温和派和激进派所不容,被主流媒体拒斥,以致终老国外,其戏剧性的人生轨迹并非偶然,为我们认识民权运动激进派的共同命运提供了一个独特又典型的视角。下文拟通过对卡迈克尔思想构成及其逻辑结构的梳理和分析,探究其大起大落命运走向的思想根源及其背后的制度因素。
一、“黑人救星”的崛起与陨落
斯托克利·卡迈克尔1941年出生于特立尼达岛(Trinidad),11岁时随家人迁往纽约。在纽约多元族裔背景下成长起来的卡迈克尔最初具有温和的民权倾向。早在高中时代,卡迈克尔就对马尔科姆·X、卡尔·马克思、后殖民理论家弗朗兹·范农(Frantz Fanon)的思想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与一些社会主义者往来,参与“非暴力行动组”(Nonviolent Action Group,NAG)的活动。大学一年级时,他受黑人青年“入座运动”的风潮鼓舞,参加了自由乘车运动,从此屡因参与民权运动被捕。1964年,卡迈克尔大学毕业后成为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的全职工作人员,投身到密西西比州各县黑人争取选举权的运动中。当地种族暴力泛滥的现实使卡迈克尔对非暴力途径的怀疑渐渐增长。1964年的“密西西比之夏”(Freedom Summer)成为卡迈克尔思想转向的转折点。目睹该运动的失败,尤其是黑人组成的密西西比自由民主党(Mississippi Freedom Democratic Party,MFDP)作为民主党在该州唯一合法代表的诉求被否决后,卡迈克尔等人对民主党的希望彻底破灭。
随着卡迈克尔的思想日趋激进,他明确提出建立黑人独立政党的主张,并来到阿拉巴马州的朗兹县(Lowndes County)践行这一思想。此地种族暴力频发,许多民权组织都难以立足。卡迈克尔先组织了一系列提高黑人参政能力的工作坊,到1965年10月,已有将近一半符合资格的黑人选民登记选举。时机成熟后,卡迈克尔等人利用阿拉巴马州法规的模糊之处,在当地黑人的支持下建立起政治上独立的“朗兹县自由组织”(Lowndes County Freedom Organization,LCFO)。卡迈克尔在阿拉巴马州的初步尝试得到了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总部的关注,委员会许多成员将建立第三党视为该组织未来发展的希望。
1966年,随着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的激进化倾向愈演愈烈,卡迈克尔逐渐从基层组织者上升到委员会核心,并以其出色的组织才能被推举为该组织的全国主席,任期一年。同年6月,年仅24岁的卡迈克尔在格林伍德(Greenwood)的演说中凭借“黑人权力”口号成了全国媒体的焦点。这次集会上,卡迈克尔振臂高呼:“这已是我第二十七次遭到逮捕,我不会再进监狱了!阻止白人打倒我们的唯一办法就是把权力夺过来。我们已经为自由呐喊了六年,仍然一无所获。现在我们要说的就是黑人权力!”卡迈克尔精力充沛、不知疲倦,发表了大量的演说和评论文章,与电视访谈相结合,大大提高了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的媒体曝光率,自己也迅速成为美国政治舞台上的一颗耀眼明星。
就在卡迈克尔的事业达到巅峰之际,危机却接踵而来。首先,卡迈克尔与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成员间的内部矛盾日渐显露。多丽丝·罗宾森(Ruby Doris Robinson)、费·贝拉米(Fay Bellamy)等核心成员在暴力手段的使用和组织纯粹性等问题上与卡迈克尔发生分歧,对其擅自以集体名义发表的演说非常不满,讽刺其为“斯托克利·咖迈克尔”(“Stokely Starmichael”),委员会甚至决定禁止卡迈克尔的电视亮相,一些成员亦因卡迈克尔言论日渐失控而离开组织。1967年,失去信任的卡迈克尔离任,担任以暴力手段著称的黑豹党(Black Panther Party)的名誉主席,并因此受到联邦调查局局长埃德加·胡佛反谍报项目的严密监视。然而不久之后,卡迈克尔又不满于黑豹党与白人激进组织结盟而主动离开了黑豹党。其次,卡迈克尔的现实处境不断恶化。1968年以后,一些受激进思想影响的黑人不断在全国各地制造骚乱,卡迈克尔作为公众人物不断被牵扯其中,加上黑豹党成员的诽谤和中情局控制的收紧,最终卡迈克尔被迫离开美国前往几内亚定居。
在非洲,他成为几内亚总统艾哈迈德·塞古·杜尔(Ahmed Sekou Toure)的助手和加纳前总统克瓦米·恩克鲁玛(Kwame Nkrumah)的学生,并将自己的名字改为“克瓦米·杜尔”(Kwame Ture)以纪念两人。不同于埃尔德里奇·克里夫(Eldridge Cleaver)等许多70年代以后渐渐回归正常生活的激进派民权运动者,卡迈克尔在后半生仍然积极为激进派黑人事业奔走,如时常回到美国发表演说,并担任“全非人民革命党”(All-African People’s Revolutionary Party,A-APRP)的领导人。然而,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美国种族状况明显改善,卡迈克尔的影响力已一落千丈。黑人以黑人党团等形式在政治体制内占有了一席之地,在70年代中期,已有约1500名非裔美国人通过选举进入了全国各级政府任职[13],美国种族主义政治的局面有所缓和,促使黑人建立第三党的热潮渐渐退去。同时,约翰逊、尼克松政府的联邦援助计划缓解了黑人的就业压力,美国垄断财团也向黑人就业、黑人资本伸出了援助之手,黑人的经济民族主义思想渐渐被主流社会吸纳。斗争的目标渐渐消逝,本人又远在国外,卡迈克尔逐渐隐没在民权运动的历史中,最终于1998年因癌症在几内亚逝世。
综上所述,卡迈克尔的人生轨迹呈现出反差明显的两个阶段。在前一个阶段,卡迈克尔凭借激进的反种族主义思想跃上美国政治舞台,成为万千受压抑的底层黑人心目中的“救星”;在后一个阶段,卡迈克尔在不断激进化的同时,其个人地位却不断被边缘化,终成黑人民权运动中的一颗“流星”。笔者认为,卡迈克尔人生境遇的重大反差来自其思想的两面性:一面是以“黑人权力”为中心的激进反种族主义思想,另一面是杂糅了多元视角、不同流派的左翼思想。在民权运动转向激进的重要节点,他凭借前者迅速崛起;随着民权运动激进派的分化,他又因后者而被主流社会乃至民权运动本身所拒斥。
二、“黑人权力”:激进反种族主义的突围与局限
卡迈克尔思想体系中最为外显的部分是激进的反种族主义。不同于马丁·路德·金,他提出的“黑人权力”主张将批判的锋芒指向整个现行制度,而非制度的局部不合理现象。卡迈克尔断言:“这个国家并非依靠道德、爱和非暴力运行,而是权力。”[14]18因此,他放弃通过非暴力与爱感化种族主义者的期盼,直接对整个制度发起挑战,这是卡迈克尔激进思想的基点。
卡迈克尔认为,现行制度的最大问题在于存在一种根深蒂固的“白人权力结构”(White Power Structure)[15]23,对黑人形成了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全方位殖民包围。他区分了个体性种族主义(Individual Racism)和制度性种族主义(Institutional Racism),前者加害方与受害方都是具体的个人,其行动和结果往往公开、立时可见,会受到媒体报道和道德谴责,而后者则更为微妙和隐蔽,其危害甚至远大于前者。例如在伯明翰,由于制度上的不公,每年有500名黑人婴儿因缺乏食物、住所和医疗保障而夭折[15]2-3。由于“白人权力结构”及其代表的制度性种族主义当道,黑人在政治上无声、经济上无力,最终陷入贫困和自我矮化的恶性循环之中。
“白人权力结构”根深蒂固,一直深入到社会文化层面,种族主义作为其典型体现,已经成为主流意识形态的一部分。卡迈克尔曾提出,“种族主义最主要的工具就是神秘化(Mystification)”[14]79。黑人长期以来被主流媒体塑造成“懒惰”“冷漠”“沉默”“不思进取”“寻欢作乐”的典型[15]37,这实际是一种文化殖民策略,通过宣扬白人至上和非白人群体的低下来完成自身的合法性建构[14]106,使得种族压迫更加无所顾忌。更令卡迈克尔感到痛心的是,黑人竟然纷纷向主流文化靠拢,如黑人妇女以漂白肤色、拉直卷发为时尚潮流。受弗朗兹·范农的启发,他认为正是制度化的种族主义使黑人受困于自我厌恶的情感之中。
该如何打破制度性种族主义的包围呢?卡迈克尔提出,最有效的解决方案就是构筑“黑人权力”。温和派对此极力反对,认为这个口号可能点燃黑人的种族主义情绪,还会对白人造成心理压力。马丁·路德·金直言:“黑人权力”是个“不幸的词语选择”[1]210,会削弱公众对民权运动的支持。但是,卡迈克尔寸步不让,甚至毫不讳言:“我们无法、也不应该保证,‘黑人权力’,如果能够达到的话,会是非种族主义的。”[15]49黑人应该“使用他们想要的语言——而不是白人想要听到的”[14]18。对于可能引发的白人恐惧,卡迈克尔的答复是:“让他们处理好他们自己的事情和负罪感吧。让他们去找自己的心理医生。”[14]52在这里,卡迈克尔以“逆向种族主义”的强硬姿态赋予了反种族主义口号以意识形态对抗的冲击力。
“黑人权力”的第一步是弘扬黑人的文化主体性,抵制由白人定义的“融入主义”(Integration)。卡迈克尔提出,必须检查由白人精英书写的黑人历史,以黑为美,重构文化认同与文化自信,提高黑人的文化创造性,“将我们的肤色用作自由的武器”[14]107。只有这样,黑人才能自尊自信地参与权力竞争,避免在社会地位的提升中迷失自我,渐渐被白人中产阶级主流价值观同化。
在此基础上,卡迈克尔构想了更根本的制度改造。首先,黑人必须形成独立的政治力量,实现“黑人自决”(Self-determination),如提高黑人的实际参选人数、组织独立的黑人第三党等。这是迫在眉睫的现实要求。一方面,虽然1965年约翰逊总统签署了《选举权法》(The Voting Acts),黑人还是因为财产限制、文化水平等借口被大量隔绝在选举体系之外,参政情况不容乐观。另一方面,他观察到美国的“种族大熔炉”远非宣传中那样开放、融合,各族裔都为了利益努力把自己的代表送进权力机构,因此,黑人若不自立,势必在竞争中落于下风[15]45。唯有抛弃不切实际的幻想,提高参政能力,选举出真正为黑人社群说话的代表,从而控制地方政府,黑人才能拥有决策权,才能变得强而有力。
进而,黑人还需要构筑独立自主的社会经济权力,达到黑人自治(Black Autonomy)。一方面,“只有黑人可以表达出这个革命性的想法:黑人有能力独立完成自己的事情”[15]47;另一方面,黑人也只有证明自身能够独立生存,才能保全本族群的人格完整性(Integrity),无所顾忌地发表意见。为确保“独立”的彻底性,他反对任何形式的白人参与,拒绝白人加入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的申请,批判联邦政府反贫困项目对黑人社区的援助,提倡建立黑人自己的银行、商店、企业等,还曾多次表示,白人的任务是回到他们自己的社区里,组织反对种族压迫的活动和宣传非暴力思想。
最后,手段上的行动主义(Activism)和必要暴力是“黑人权力”的实现路径。卡迈克尔大力呼吁黑人不再被动地等待,而是要行动起来,打破现有权力结构。卡迈克尔将“虚伪的自由主义者们”视为美国自由社会的隐患,因为他们总是试图维持现状,减少压迫双方的正面冲突。受弗朗兹·范农用暴力哺育斗争精神的主张影响,卡迈克尔试图建构一种反抗意识,由此不可避免地触及暴力问题。在卡迈克尔看来,暴力的使用与道德无关,关键在于谁掌控了合法化暴力的权力。“白人权力结构”对暴力的垄断是黑人暴力行动的前提,无数无辜的美国人和越南人死于越战战场,就是美国白人政权粉饰战争机器的证明,因此黑人使用暴力是正当防卫。他公开呼吁黑人持枪权:“我们要拥有枪支、坦克和手榴弹!”[14]1241968年,在马丁·路德·金遇刺后,卡迈克尔对黑人大声疾呼:“如果你没有枪就不要上街,因为那里总会发生暗杀。”[16]
卡迈克尔“黑人权力”口号在黑人中乃至美国社会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主要源自其激烈的表达风格与时代需要之间的碰撞。“黑人权力”的主张正式诞生于非暴力民权运动频频受挫的环境下:1963年伯明翰暴动、1964年“密西西比之夏”将紧张的种族关系推向流血暴动的边缘,马尔科姆·X被暗杀与越战升级更使现实危机显得刻不容缓。“我们已经为自由呐喊了六年,仍然一无所获”“我们别无选择”[15]177正是黑人对民权运动陷入僵局的焦虑心态的写照。在此背景下,“黑人权力”作为一种全新的思路,有力地表达了受压迫黑人,尤其是“城市贫民区(Ghettos)里的年轻黑人和南部聚居区黑人(the Black-belt South)”无处安放的失望[15]50、“此前尚未被明确阐发的愤怒”[1]244,以及对积极行动的渴求。
作为代言人,卡迈克尔的辩才功不可没。“他的热情、雄辩及其起到的效果”从迈克尔·特尔维尔听过演讲之后情绪激动、几近失态的表现中可见一斑[17]544。联邦政府甚至将“黑人权力”视为导致1967年夏季以来大城市黑人区中出现的暴乱潮流的原因之一[9]44。卡迈克尔简短有力、富于感染力的言辞形成了巨大的社会影响,推动了民权运动的进程。
然而,卡迈克尔及其“黑人权力”口号虽完成了情绪宣泄的使命,却并未形成一套明确自洽的激进派思想体系,正如历史学家埃里克·方纳(Eric Foner)所言,“‘黑权’是一个定义非常不精准的概念”[18]1286。卡迈克尔思想中的模糊与矛盾之处十分突出,令其自身的激进性大打折扣。
首先,卡迈克尔的黑人权力主张呈现出明显的前后不一致。卡迈克尔曾尖锐地批判其他民权运动家们只关心餐馆、酒店等一些公共设施的准入权,对选举权的重视不够[14]102。但是选举权斗争遭到打击后,卡迈克尔又发泄道:“有人说‘黑人权力’就是选举权……选举权不过是白鬼们的诡计。”[14]115-116这体现出他本人的挣扎和怀疑。
卡迈克尔的暴力思想更令人捉摸不定。卡迈克尔主张行动与力量,也发表过宣扬暴力的情绪化言论、担任过黑豹党的名誉主席,但他强调的仍是暴力作为种族残杀频发情势下的正当防卫。正如他对黑豹党标志的诠释:“(黑豹是)一种有力量却通常隐遁(Reclusive)的动物。除非被激怒,它总是回避人类。”[17]463-464他曾多次表明,他已“厌倦了向白人解释我们并没有伤害他们的意思。我们只想取得我们想要的东西。”[14]59卡迈克尔想以暴力的话语对抗暴力的现实,从而激发反抗意识,然而,作为符号的暴力与现实中暴力行动之间的模糊界限和复杂关联很难澄清,在与激进派和温和派双方的辩诘中,卡迈克尔的思想变得更加犹疑反复、矛盾含混。
模糊性与不一致只是端倪,其深层的问题在于卡迈克尔反种族主义思想的矛盾性,这在“隔离”与“融合”的问题上表现得最为明显。卡迈克尔一方面坚持“反向隔离”的激进立场,主张维持黑人社群的纯粹性,排斥白人的救助和介入,另一方面又不排斥融合的远景,只因现有的政治、经济条件和族群关系下,与其他族群平等联合远远无法达成,反而沦为实际上的剥削、殖民,所以才以自决为第一步。“因此,‘黑人权力’并非暗示着单打独斗。‘黑人权力’仅仅意味着:在你有能力自力更生以后再谈联合。”[15]79此处卡迈克尔的逻辑是:通过激进的手段达成温和的目标,借助暂时的隔离方能实现真正的融合。且不论这能否真正消解激进与温和、隔离与融合逻辑上的对立性,仅就这一努力本身而言,它无形中暴露了卡迈克尔思想的温和底色,至少黑人自决的激进行动需要借助于种族融合的温和目标自我辩护。
追根究底,卡迈克尔思想上的矛盾性来源于其内在未被充分表达的融入趋向。虽然媒体不断渲染马丁·路德·金与“黑人权力”运动的分歧,但卡迈克尔在晚年出版的自传中明确写道:“他(马丁·路德·金)真的更了解我们,更能感同身受,而且在精神上和我们比人们想的都要接近。”[17]511“我们拥有的唯一差别仅在于策略和方法上(他说我们太不耐心了),从来都不在目标或价值观上。从来不。”[17]512可见,卡迈克尔对融入主义隐蔽的认同构成了其激进性的先天障碍。
这种潜在的融入趋向并非无源之水,而是受到黑人精英文化传统影响和民权运动不同流派渗透的结果。20世纪初,黑人精英布克·华盛顿大力倡导黑人自我改良,“放下水桶,就地取水”,以脚踏实地的平凡劳动融入美国社会,获得信任;略晚于华盛顿的黑人思想家W.E.B.杜波依斯(W.E.B.Du Bois)则以黑人选举权的呼吁迈出了更为激进的一步,但他的意图亦是将黑人塑造成符合美国社会主流价值观的“真正的人”;进入20世纪60年代,马丁·路德·金以非暴力、爱与和平的口号表达了对美国现行制度与主流价值的认同与捍卫,并比“融入”更进一步,提出了新时代以温和手段实现种族融合的诉求;与此同时,主张分离主义的激进派黑人领袖马尔科姆·X在60年代中期亦转向体制内斗争,提出了著名的“子弹或选票”口号,号召黑人以独立身份积极参与选民登记,提升自身政治地位,从而使黑人群体成为各党竞相拉拢的制衡力量[19]133。
可以发现,融入主义始终存在于黑人的精神传统之中,也始终是民权运动绕不开的主题,差别仅在于这种意识在实际宣传中是被着力表述还是刻意回避。就此而言,卡迈克尔对种族关系的矛盾态度,也代表了黑人民权运动本身的内在难题和矛盾症结。
综上所述,言辞的激进性成就了“黑人权力”思想的影响力,使其成为一面旗帜,汇聚了民权运动激进派形形色色的诉求。然而,卡迈克尔虽能凭借自己的热情与辩才承担起公共发言人角色,却无法建立一套完整的思想体系,因而缺乏实质性要求来切实应对现实中的复杂困境。例如,除了以黑为美的信条之外,黑人文化主体性的依托何在?黑人如何在“白人权力结构”的政治框架下通过选举实现自决?黑人自建的经济网络如何与主流市场脱钩?为了寻求答案,不同于其他民权领袖的回避态度,卡迈克尔将目光投向了反种族主义之外的激进思想。
三、多元视角的左派“异端”:在激进中滑向边缘
彭尼·约瑟夫指出,卡迈克尔身上有一种多变性(Protean),在黑人领袖中处于一种奇怪的地位[20]。的确,卡迈克尔思想中交织杂糅了多重视角、不同形态的左翼理论,成为反种族主义之外的另一条主线。
为了摆脱理论上的困境,卡迈克尔首先引入了“新左派”学生运动(the New Left)的思想资源,尤其是“个人分享式民主”的标志性理念。不同于号召“回到非洲”的早期黑人领袖马库斯·加维(Marcuse Garvey),被迫远走非洲前,卡迈克尔始终以美国作为战场,关注美国的社会现实,痛陈美国已经沦为一个窃贼、杀手的国度,希望通过积极斗争改变美国政治和族群关系。他支持反越战游行,呼吁青年人自觉承担起改变美国现状的责任,“我们这一代人必须拯救世界”[14]76,“我们不要下地狱!”(Hell no!We ain’t go!)这些言论体现出卡迈克尔的双重认同标准:“我们”既是“黑人”,也是积极行动的“美国人”。此处左翼导向的政治认同与以黑人为中心的族裔认同并存,并大有超越之势。
此外,卡迈克尔还充分吸收了新左派提出的意识革命、从观念上瓦解现行制度合法性的主张。他大胆使用“黑人权力”这样充满意识形态冲击力的口号,甚至不惜引发白人对于“反向隔离”的恐惧。他还身体力行地实践自己的“语言行动主义”。早年间在朗兹县进行基层组织时,卡迈克尔在课堂上反思美国社会对黑人英语(African A-merican Vernacular English)的规训:“谁决定了何为正确的英语,何为不正确的英语?”[14]4引导学生思考文化背后的权力逻辑。
卡迈克尔对新左派思想的吸收源于两者之间共享的某些基本价值观。从源头上看,“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具有强调个体价值、积极为个体权益斗争的传统。卡森认为,“到1965年,SNCC在很多支持者和批评者的眼里,已不单单是一个民权组织,更是‘新左派’的一部分”[1]175。其次,两者相互借用对方的社会意识,丰富自身的批判维度。“正是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而不是其他群体,塑造了早期新左派的意识”[21]。例如,“白人权力体系”概念明显吸纳了新左派体制批判的成果。
然而,在如何从个体自觉走向群体意识、如何确认革命主体与斗争目标的问题上,卡迈克尔与新左派出现了分歧。新左派的精神领袖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将斗争矛头导向了技术理性对个体人格的异化,寄望于以知识阶层政治意识的提高、“新工人阶级”(New Working Class)的塑造、尚未被体制俘获的亚文化群体的唤醒和对体制的“大拒绝”推动革命[22]。这些都与卡迈克尔的反种族主义和黑人群体主导斗争的要求格格不入,最终分道扬镳。
归根究底,最终的分化来源于两者社会意识的形成基础不同。新左派的队伍来自体制中心,无论是作为新左派精神导师的C.赖特·米尔斯(Charles Wright Mills)和马尔库塞,还是作为主力的中产阶级白人大学生,都具有鲜明的中产阶级属性和精英倾向,“它不是产生于贫困而是产生于富裕”[23],是物质丰裕、科技革命、发达工业等多重“文明的压抑”下追求极致的自由、平等的文化逆反。对此,即便作为黑人文化精英的卡迈克尔心存认同,但对于被排斥于主流社会流动体系之外的下层黑人来说,这些都是生疏和难以理解的。卡迈克尔要将下层黑人的激进情绪导入社会变革,就必须放弃新左派这些脱离民权运动实际的虚玄理论。
为了填补新左派的理论缺陷,卡迈克尔求助于老左派的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卡迈克尔少年时就被马克思主义所吸引,高中时期曾加入社会主义者的读书小组,阶级意识曾在他的思想中占据了基础性地位。在1966年发表的《谁能胜任?》(Who is qualified?)演说中,他认为社会是排他性的,资源掌握在少数人手中,只有通过金钱、关系或者教育能够达到阶层流动[14]9。阶级问题凌驾于种族问题之上,黑人不幸因肤色沦为被剥削阶级,种族主义为阶级剥削服务。即使在黑人群体中,也存在精英人士马丁·路德·金与草根运动者芬妮·娄·哈默(Fannie Lou Hamer)的天壤之别。因此,他批判现有的民权运动带有中产阶级倾向,没有联系黑人无产者。
然而,鲜明的阶级视角不但拉开了卡迈克尔与新左派之间的距离,也令其与民权运动激进派产生了隔阂。在60年代左派思想风行的背景下,黑人激进派领袖马尔科姆·X也曾对社会主义产生过兴趣。他表示,“出于好奇,我无法抵御自己的欲望,去做一些小小的调查,了解那些这种特殊的哲学碰巧存活下来,或是通过努力成为现实的地方”[19]65。他认为资本主义总是与种族主义相关联,也曾对激进劳工论坛(Militant Labor Forum)、社会劳工党(Social Labor Party)发表演说。但总体看来,马尔科姆·X对老左派思想并未抱过多期待。他清楚地意识到,即使体制是所有被压迫者共同的敌人,争取其他群体对黑人斗争的认同仍十分困难。他思想的底色是强烈的身份政治意识,以黑人的权益为头等大事,“我们是中立的。我们只为我们自己。什么对我们有好处,我们就对什么感兴趣”[19]132。被强迫带到新大陆、曾经为奴的非裔美国人必须“始终铭记在心,我们之所以在西半球,是与任何人都不同的”[19]120。1964年以后,马尔科姆·X转而强调更加跨越地域、阶级的“人权”问题[24],试图联合广大第三世界国家、殖民主义的受害者,尤其是非洲黑人。他声称“我们的问题就是你们的问题……除非我们的问题解决了,否则你们的问题永远会悬而不定”[19]74-75。即便将美国本土的黑人民族主义扩大为泛非主义,种族的视角仍然处于优先地位。
与之相比,卡迈克尔显然在理论上走的更远,对共产主义的兴趣也更为浓厚,还曾被其在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的同事尤里乌斯·莱斯特(Julius Lester)评价为“准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左派言论家”(Quasi-Marxism-Leninism and New Left Rhetoric)[25]。左翼倾向的阶级视角使卡迈克尔突破了单一种族视角的局限,具有更加宽阔的批判视野,形成了超越于同时期其他民权领袖的激进性、批判性。然而,在实践中,他的阶级视角又是犹豫动摇的,受到黑人民族主义的极大牵制。
这首先体现为阶级视角对种族视角的让步和回归,尤其是当种族关系持续紧张、黑人民族主义(Black Nationalism)情绪高涨时。他为了唤起黑人民族性(Peoplehood)的觉醒,甚至无视群体内部已经形成的阶级分化。他鼓励黑人青年学生回到黑人聚居区(Ghettos)帮助贫苦黑人[14]73,劝诫他们“个人主义是一种黑人学生支付不起的奢侈品,你应该将你自己视作这个群体内的一员”[14]74;同时,通过“耐心、爱、兄弟情谊和集体,而不是暴力”使已经分化出去的黑人中产阶级重回社区,自觉将财产投入集体的工厂、商店中[14]29。
卸任“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主席后,卡迈克尔思想中的种族议题完全占据了上风。不同于黑豹党联合一切反抗帝国主义革命力量的“革命民族主义”主张,卡迈克尔在组织策略上更接近于“文化民族主义”[26],强调民族主体性,这又使他与左派人士产生了隔阂。1968年卡迈克尔发表了《释放休伊》(Free Huey)演说,主张应和墨西哥裔美国人、波多黎各人联合,但没有提及底层白人。在他看来,即使同受剥削,种族、肤色和文化基础仍是两者之间的天壤之别[14]119。当他转向泛非主义后,更是简单地以肤色定敌我,回避美国黑人与非洲黑人的巨大差异,只谈非洲文明的荣光、血浓于水的兄弟姐妹之情等空泛的概念,即使仍不放弃马克思的阶级分析理论[14]192,其最终的理论关怀也在于解释“种族”的成因。最终,卡迈克尔的阶级观在摇摆不定中成了反种族主义的理论工具和附庸。
更深层的问题在于,卡迈克尔基于阶级分析的体制批判,本身是空泛而杂乱的,这体现在他对社会主义粗浅、有限的论述上。卡迈克尔始终认为黑人社区应该是集体所有的,“我们要在黑人之中建立的社区,不是一个资本主义社区”[14]29,这种倾向在他后期投身于泛非主义运动时受恩克鲁玛和塞古·杜尔影响更是愈发坚定,曾在演说中将社会主义作为泛非主义的基础;但是他始终没有清晰地阐释“社会主义”的内涵,在公共场合提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次数远不及“反对资本主义”的表述多。可见他脑海中的“社会主义”仅是对现行体制的否定性概念,充当反种族主义的象征和口号。
在卡迈克尔的思想中,还混合了社群主义的成分。在他看来,理想的黑人社区应是“社群精神(the Spirit of Community)和人道主义的爱广泛传播”之地[14]29,重视黑人社区内部的手足情谊与互帮互助,同时社群也拥有自己的财产;后期倡导泛非主义时,他更是明言,“泛非主义以社会主义为基础,后者以社群主义(Communalism)为根源”[14]221,他将社会主义简单归结于社群主义,这不知不觉间又回到了美国的社群主义传统。美国的社群在19世纪有过发展的高潮,20世纪60年代再度兴起,主流的自由派、保守派以及新左派都有各自社群主义的表达形式,将其视为个人自由和权利的保障、推动精神解放的场域[27]。卡迈克尔将资本和权力之外的社群视为弥合黑人内部阶级裂痕的调和剂,本质上是一种体制内的保守改良方案。此外,社群非但不能如卡迈克尔期望的,有效弥合阶级与种族视角之间的分裂,反而增加了其思想的空想性和混乱性。
于是,卡迈克尔在种族关系问题上的矛盾态度,进一步延伸到阶级视角下的体制批判中。一方面,卡迈克尔出于对种族现状的悲观和绝望,激进地宣扬反体制思想;另一方面,他又无法摆脱体制内思维和斗争框架,包括饱受非议的建立第三党和黑人武装,及其所设想的各种补救方案。由此,卡迈克尔陷入了拒斥抑或接受体制的困惑之中。
为了突破这一困境,他尝试将现实政治与民主制度剥离。即使痛斥“制度性种族主义”,卡迈克尔针对的仍只是现实中运行的体制,而非民主制度本身。在《黑人权力》一书中,为了抛弃旧有体制、寻求政治结构和参与的新形式,卡迈克尔和汉密尔顿提出了他们的“政治现代化”构想,对“制度”(System)和“结构”(Structure)进行了区分,认为“黑人权力”意图推翻的是与种族主义如影随形的现行政治、经济架构,唯有如此才能完成对制度的更新和改革[15]39-43。这一尝试并不成功。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内涵上,其民主构想都只是现实政治的翻版和提纯,终究无法突破对于美国自由主义体制和价值观的深层认同,这注定了他对体制的斗争一开始就不可能是“彻底”的。
同时,理论上的自救无法使卡迈克尔免于现实中的尴尬境地。对民权运动激进派来说,卡迈克尔的犹疑和妥协无法满足其理论和实践需求;对于主流社会和民权运动温和派而言,卡迈克尔对黑人自治言辞激烈却模糊的宣传使大量不安的白人乃至大部分黑人只读出了种族分离的信息,不仅事实上将黑人再度隔绝于主流社会之外,还刺激了白人的恐慌情绪。1968年的一项民调显示,80%的人认为黑人“前进的太快”[28],方纳亦指出,激进派黑人引发了“白人对‘反向歧视’发生的担忧和恐惧”[18]1282。不仅如此,卡迈克尔的阶级视角还使他本人命途多舛,不但遭受主流社会和其他民权运动者的排斥,更受到行政当局的打压。1967年卡迈克尔赴古巴访问菲德尔·卡斯特罗、共同宣扬武装革命,却险些被美国领事馆没收护照,即与联邦政府的反共产主义倾向有关。
至此,卡迈克尔思想的空虚性和两难境地显露无遗:种族自决与隐藏的融合认同相冲突;新左派的个人主义与老左派的阶级立场无法融合;族群内部阶级分化使以社群为纽带唤起黑人群体凝聚力成为空想。最终,卡迈克尔试图将激进思想推向极致时,这些杂糅并处的思想成分却陷入相互割裂的冲突和混乱,并使其人同时遭到了多方孤立。
四、结语
卡迈克尔集多重身份于一身,既是为黑人解放事业奔走的活动家,又是富于思考的思想者;他的个人命运大起大落,一度成为“黑人救星”,此后却迅速淡出公众视野,甚至客死他乡。他的多重身份和命运起伏,很大程度上是其思想体系内在矛盾的作用及其与社会现实相互碰撞的结果。
一方面,卡迈克尔试图发挥马尔科姆·X以来的分离倾向和激进的黑人民族主义思想,将反种族主义从文化层面推向制度层面,通过黑人自治、黑人自决达到种族平等;另一方面,为了维持激进性,他的思想中又杂糅了多种当时的激进思潮。然而无论是反种族主义还是激进主义,卡迈克尔的思想都陷入了激进性和妥协性的矛盾挣扎:首先,反种族主义始终在独立与融合之间摇摆不定;其次,个体的、阶级的和社群的多重视角不但各具缺陷,而且彼此冲突;最后,其试图维持激进性的多元视角最终让位于种族的单一视角,其理论内部的矛盾并未得到克服,反而进一步深化了。
正是这种矛盾的思想特性使他遭遇了“多重边缘化”的命运:外在的激进反种族主义、分离主义倾向使他不容于温和派民权运动家;内在的种族问题妥协性最终又使得下层黑人逐渐挣脱他的思想框架,走向更极端的情绪宣泄;阶级视角下的左翼倾向令他与民权运动激进派和新左派同时隔离;缺乏普世性的反种族主义又令他被放逐于白人主流价值观之外。
最后,作为一套存在严重缺陷的思想体系,卡迈克尔黑人权力理论的风行是民权运动特定阶段的时代产物,因社会改革滞后造成的情绪宣泄风潮而生,注定随着体制改革突破、社会思潮的变化而消逝。更为重要的是,黑人虽然在美国社会中处于不平等地位,但随着社会的发展、体制的改良,已逐步内嵌于体制之中,形成了与体制日益同构的社会分层和观念分化体系,试图使黑人抱合成团再连根拔起的激进主张,在思想上和现实中都是不可行的。卡迈克尔反种族主义和激进主义的时时自相矛盾,除了其自身理论素养不足外,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其缺乏理论创新的现实基础。虽然卡迈克尔一直为革命准备着,他斗争的对象到60年代末、70年代初已渐渐被分化、消解,卡迈克尔的抗争姿态不免显得不合时宜,无可立足。
究其根本,“边缘人”卡迈克尔的命运,正是民权运动激进派试图自我突围、另寻出路,却终究难以破除自身矛盾,在体制强大的压力下走向消解的典型象征。可以说,体制的弹性和思想吸纳能力赋予了反体制力量以活动空间,也约束了其活动边界,潜在地塑造了其思想的基底。
时至今日,黑人的文化主体性得到彰显,爵士、摇滚等音乐风格席卷全美,越来越多的黑人精英在各个社会领域大放异彩。历史学家乔伊斯·贝尔认为,正是“黑人权力”的口号而不是种族融合的思想,最终成了非裔美国人的主流[29]。不过,显而易见的是,“黑人权力”的内涵经过实际发生的多重阐释,早已弱化了卡迈克尔等人最初的激进设想与反体制倾向,成了非裔美国人争取权利、发扬种族自信心的象征。但不论如何,“黑人权力”思想及实践以其特有的形式改写了20世纪下半叶以来美国的族群关系,一度对自由主义机制产生了冲击,最终促成了体制的自我完善,其自身也经过体制内部的淘汰成为革新的推动力量,使美国的自由与民主价值观向更广阔的群体敞开。这是卡迈克尔所代表的激进主义的历史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