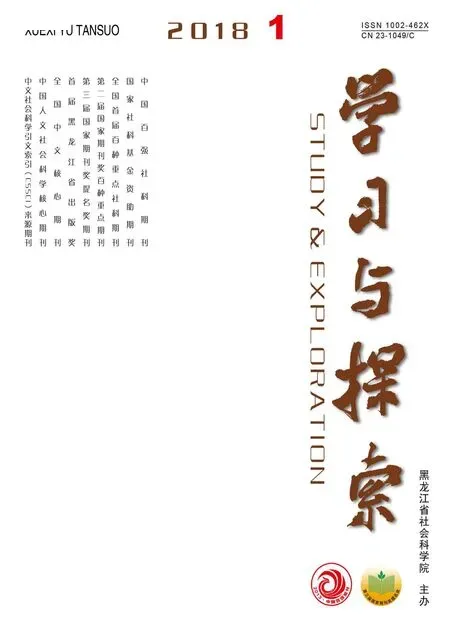中日恩文化之比较
杨 春 时
(四川美术学院,成都 401331)
在中日文化体系中,“恩”的理念始终处于核心或重要的地位,因此中日文化都可以称为恩文化。但中日恩文化之间又具有重要的差异,不能等同。因此,就需要对中日恩文化进行比较研究,以深入地把握中国文化和日本文化。
一、中华文化的核心——恩
生存体现了主体与世界之间的关系,人们如何认识和处理这种关系就构成了特定的文化。文化的核心是价值观念,中华文化的性质也决定于其核心价值观念。中华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念是什么呢?对此有多种说法。一般认为是仁,因为仁是以儒家代表的中国文化的最高范畴,它统御了如孝、悌、忠、义等其他范畴。但问题在于,仅仅说中国文化的核心是仁并不够,因为仁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概念,我们对其不应按照儒家的定义来理解,而需要进行现代的阐释,而问题的症结就在这里。在中国文化研究的历史上,由于缺乏反思性的阐释,其真正的含义被遮蔽,导致对中国文化性质的误解。那么仁的内涵是什么呢?仁是被一个更根本的理念规定的,这就是恩,恩是仁的深层意义。恩的观念是中国伦理的核心,中国伦理实质是建立在恩的观念之上的。由于中华文化的伦理本位性质,恩就成为普遍的文化观念。因此,中华文化也可以称为恩文化。
中国人认为,生存就是做人,生存的意义就是做好人,而做好人的内涵就是做好自己的社会角色——在家做孝子慈父、贤妻良母;在外做被乡邻、国人认可的好人;在国家做忠臣良民。这个基本伦理概念就是仁。何谓仁?许多人把它解释为爱,因为孔子说过“仁者爱人”。当然,仁有爱的含义,但它并不等同于现代意义上的爱,因为中华文化中的爱是恩爱,即爱是被恩规定的。在中华文化中,仁就是对他人施恩,也是对施恩者报恩。因为中国人认为,人生而承受恩,包括天恩、国恩、家恩、人恩等,也因此就具有了报恩的义务。同时,人也天生就有施恩和报恩之心,即仁爱之心。总之,这种对恩的自觉就是仁。中国传统社会的人际关系被概括为“五伦”: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而恩的观念也涵盖了五伦。
仁具体体现为各种伦理范畴,它们都以恩为根据。孝是家族伦理的核心范畴,它也以恩为根据。孝的内涵就是父母生育儿女、对儿女慈爱是施恩,故儿女从属于父母,要以奉养、服从父母来报恩。以此为中心,就衍生出悌(兄弟姊妹之间的恩)、贞(夫妇之间的恩)等家族伦理范畴。家族是中国社会的基本地位,因此家族伦理成为社会伦理的基础;而孝成为传统伦理的根源。
社会伦理也以恩为根据。由于传统社会没有形成人与人之间的契约关系,家族伦理就推广到社会领域,形成社会伦理,也就是被狭义化了的义。义本来是与仁相对的概念,仁指内在的天性、良心,义则指外在的规范、行为。孟子曰:“仁,人心也;义,人路也。”(《孟子·告子上》)但后来在实际应用中,我们把非亲属的和非政治的人际关系准则也称为义,也就是民间所谓的义气。
政治伦理也是一种恩的关系。由于中国没有形成人与国家的契约关系,政治关系就被伦理化并形成了忠的观念。忠本指内心的诚恳,后来则专指对君主的忠诚。君主对臣民行仁政是施恩,因此就有了统治的权力,甚至可以支配臣民的生命财产,即“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而臣民要忠于君主,奉献出自己的一切以报恩,否则就是大逆不道。中国的专制与西方不同,君主不是以上帝的名义统治,而是进行家长式的管理,虽然也要借助天子的名义,但它更强调君民之间的亲情关系,即君父对子民施恩,子民效忠君父。作为社会精英的中国知识分子——士与君主的关系也以恩为纽带,君主信用士人,是施恩;士人对君主尽忠,是报恩。孔子说:“君使臣以礼,臣侍君以忠。”(《论语·八佾》)“士为知己者死”是古代知识分子的信条。百姓与官员的关系亦然,官员是父母官,是牧守;人民是子民,是牛羊。官员行仁政,就是青天大老爷,子民要感谢他的恩德;而官员也自认为“爱民如子”,从而有了道德上的优越感和统治的合法性。
中国的礼仪规范也建立在恩的理念之上。《礼记》曰:“太上贵德,其次务施报。礼尚往来,往而不来,非礼也;来而不往,亦非礼也。”也就是说,道德是最高原则,在这个原则之下要讲求施恩报恩、礼尚往来,这就形成了恩文化。董仲舒的三纲即“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君为臣纲”,确定了施恩者为尊,具有支配地位;受恩者为卑,具有被支配地位。他提出的“五常”即“仁义礼智信”,也是以恩的观念为中心建立的伦理规范。
二、日本的恩文化
日本也有恩的观念,也是重要的伦理范畴,因此日本文化在一定意义上也是恩文化。鲁思·本尼迪克特对日本的恩文化做过精湛的研究,她认为日本文化是“各人相互有恩的巨大网络”。日本文化恩的观念体现在等级关系中,不仅有人身依附和等级服从政治关系,也有施恩—报恩的伦理关系。传统的日本社会是贵族等级社会,天皇与贵族之间、贵族内部的不同等级之间、贵族与平民之间都有着不可逾越的身份差别。因此,日本传统社会有人身依附关系,讲求等级服从。同时,为了加强等级间的黏合力,日本文化也有恩的观念,认为上层阶级对下层阶级有恩,下层阶级对上层阶级有报恩的义务,报恩的形式就是忠于等级身份所具有的职责,服从上层阶级。日本的恩文化体现在家庭、社会、政治诸领域,与等级制度融合为一体。在家庭伦理中,父亲的身份最高,母亲次之,子女是底等级,父母对子女有恩,子女要服从父母以报恩。丈夫与妻子的关系也大体上如此,丈夫有恩于妻子,妻子要服侍和服从丈夫。在政治领域,武士、家臣与主君的关系也体现了施恩与报恩的观念。主君对于武士、家臣是施恩者,为了报恩,武士、家臣要忘我舍身,这被看作一种非常崇高的行为。与中国的“赵氏孤儿”故事相似,日本也流传着一个舍子报主恩的故事。日本历史上有一个著名的人物菅原道真,他被政敌流放,政敌还要杀害他的幼子。而其幼子被菅原道真一个名叫源藏的旧臣藏匿了起来。为了保护旧主的幼子,源藏挑选了一个与其相像的孩子做替身,交给菅原道真的政敌。这个替身的父亲家族曾受过菅原道真的恩惠,所以他和孩子的母亲都心甘情愿地献出自己的孩子。更为残酷的是,替身的父亲还被委任鉴定首级是否为菅原道真幼子。替身的生父回家后,对等候的孩子母亲说:“喂,老伴高兴吧,儿子已经效忠了。”[1]52-53
明治维新以后,出于政治的需要,日本统治阶层把以往对于藩主和大名的忠诚转移到天皇身上,建构了“皇恩”“国恩”这一最高恩义形式,国民也以报“皇恩”“国恩”为最高义务。
恩文化有情感的层面,也有理性的层面,后者就是相应的“义理”。所谓义理,鲁思·本尼迪克特称其为做事必须遵循的规则,它包括“报答的义理”,也就是处理恩情关系的准则。鲁思·本尼迪克特说:“在日本,所谓‘义’,就是确认自己在各人相互有恩的巨大网络中所处的地位,既包括对祖先,也包括对同时代的人。”[2]90在其成名作《菊与刀》中,鲁思·本尼迪克特列举了日本文化中恩的种类,有皇恩、亲恩、主恩、师恩等;与恩对应的义务有忠——对天皇、法律、日本国家的责任;孝——对双亲及祖先(含对子孙)的责任;任务——对自己的工作的责任。还有对应的义理,包括对社会的责任、对主君的责任、对近亲的责任、对他人的责任、对非近亲的责任等[2]106-107。由此可见,日本文化恩的观念渗透在社会生活诸多领域,构成了一种恩的伦理文化。
三、中日恩文化的共同性
中日文化都有恩的观念,它们构成了伦理观念的核心,联结了人与人之间的情感。中日文化中恩的观念具有相同的性质,即它们都是人恩,而不是神恩;都构成了一种互动的而又具有支配性的伦理关系。西方文化建立在人与人之间的契约关系之上,其伦理观念的核心是爱,而爱是平等的施予和回报。中日传统社会没有建立契约关系,恩是人恩,体现了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的关系。西方文化中没有恩的观念,只有神恩,没有人恩。西方的恩情(gratitude)是恩典的意思,专指神恩;感恩(grace)是感激的意思,具有平等性,没有报恩的含义。神恩是神对人类的爱,人们要报神恩,就要按照神的教导爱他人。所以,爱是西方文化的核心概念,它具有平等的性质。恩与爱是有区别的:所谓恩的观念,就是一方对另一方施以恩惠,施惠方就具有了支配受惠方的权力,而受惠方则承担了以牺牲自身权利回报施惠方的义务。恩爱也是一种爱的形式,但又是扭曲的爱,是一种以爱获得支配权力的伦理观念:施爱者有恩于被爱者,对其有要求报偿的权力;被爱者要对施爱者报恩,否则就是不仁。仁体现为孝、忠、义等恩的形态,衍生出礼、义、廉、耻、信、智等伦理范畴。在以施恩—报恩为基本结构的伦理关系中,施恩方就获得了支配受恩者的权力。中国古代的爱用“怜”来表示,怜爱是强者(如男人)对弱者的爱,是不平等的,所以后来“怜”就演化为“可怜”的意思。日本的恩也不等同于爱,本尼迪克特说:“但是,‘爱’这个词在日文中特指上级对下级的爱。西方人也许会觉得这种‘爱’其实是‘庇护’(paternalism)之意,但在日语中,它的意识不仅在‘庇护’,而是一种亲爱之情。”[2]95这种对爱的扭曲,源于恩的观念。本尼迪克特又补充说,由于现代以来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爱这个词也用于同辈之间。中日文化以恩情代替爱,以恩义代替普遍的理性,恩衍化为一种普遍的权力,支配了整个社会生活。
中日恩文化要从历史的角度给予评价。从积极的方面说,恩伦理以情感的交往调和人际关系,从而避免了直接的暴力性。此外,施恩—报恩的关系具有互动性,不是单方面的给予,也不是单方面的服从,而是双方的责任。如父母对子女的恩有“慈”的义务,而子女对父母的报恩有“孝”的义务,慈与孝构成了互动。君主与臣民的关系不仅有臣民对君主的忠,也有君主对臣民的“亲”,忠与亲构成了互动。因此,这种恩伦理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社会矛盾,有助于社会稳定。
中日的恩文化具有不同于西方的社会基础,但都构成了恩文化的不平等性。中国与日本的社会性质不同,一个是平民性的宗法社会,一个是贵族性的封建社会。但与西方社会相比又有共同点,就是都缺乏西方社会那种契约关系,都具有不平等性。日本是等级制度,中国是宗法制度,这样人际关系就都缺乏独立性,而具有依附性。在这个社会关系的基础上,伦理观念也不可能是平等的,不是平等的爱,而只能是不平等的恩。
从消极方面说,恩的伦理加固了不平等的社会关系,因为施恩与报恩之间具有不平等性。恩是一种特殊的权力形式,具有情感的支配性。按照福柯的观点,权力无所不在,统治着人和社会的各个领域。伦理就属于这个权力系统,作为集体价值规范,它是对人的支配、规训力量。以恩为核心的伦理虽然有现实的根据和合理性,但像一切意识形态一样,受到历史条件的限制,具有自身的缺陷。从现代伦理关系上看,爱是核心的、最高的价值,它构成了平等、和谐的人际关系。而恩不是纯粹的爱,是爱的畸变、异化。在中国和日本的传统社会里,由于没有爱的宗教,爱作为最高价值缺失,而恩成为一种绝对的伦理法则,一种意识形态,一种支配性权力,于是爱的需求被压抑、排斥和扭曲了。恩是以情感方式对他人的支配,也是对自己的支配地位的肯定方式。这就是说,爱交换了权力,或者说爱权力化、爱异化。当然儒家也谈爱和同情,例如孔子说“仁者爱人”,孟子讲“君子有不忍人之心”,但这种爱和同情却受到了恩的观念的限制而丧失了本源性。特别是在中国文化中,爱是有差等的,这是由施恩与报恩的大小决定的。中日传统文化中的恩,无论是父母对子女的恩爱,还是统治者对子民的恩德,或者是“义士”对弱者的恩义,都在情感上和伦理上把施恩者当作主人,把受恩者降为奴隶,这是一种温柔的奴役。正是在恩文化当中,人失去了自我,失去了自由。中国文化以恩为中心形成了宗法性的伦理体系,在平民社会建构了不平等的社会关系。日本文化以恩为中心强化了等级制度,论证了贵族社会的合理性。
四、中日恩文化的差异
中日恩文化虽然有相同之处,但也有相异之处,而且这一点也至关重要。首先,中日恩的观念在文化体系中的地位不同。中华文化中的恩具有普遍性,不仅适用于一切社会关系,而且也包括人与自然、人与神的关系。中华文化建立在天人合一的基础上,人与神、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都有施恩—报恩的关系,神、自然都被称为天,都有恩于人,所以有天恩,人要报天恩。由于天人合一的观念,天恩就变成了人恩,赋予人恩以合法性。在社会关系上,从家族伦理到社会伦理到政治伦理,都受到恩的观念的支配,孝、义、忠体现着这三个领域的恩的观念,孝为家族伦理的核心,义(狭义的)为社会伦理的核心,忠(狭义的)为政治伦理的核心。可以说,中国伦理以恩为核心,恩的观念支配着一切社会关系。
日本的恩文化也具有相当大的支配力,主要体现在家族伦理和政治伦理之中。它认为父母抚养子女,主君任用家臣,天皇统御臣民都是在施恩;子女孝顺父母、家臣忠于主君、臣民忠于天皇都是在报恩。但是,日本文化的恩并不覆盖着全部的人际关系,它只是在上下等级身份之间存在,如父母与子女、臣民与主君、臣民与天皇之间。而在同一等级身份之间不存在必然的恩的关系,它们之间是平等的、独立的。这与中国人与人之间普遍存在的恩情关系不同。中国人伦是家族伦理的延伸,一般的人际关系也相当于家族关系,如同事、朋友、兄弟(姐妹),年长者与年幼者、师徒之间如父母等,它们之间都有施恩和报恩的关系;即使普通的人与人之间,也有恩情关系,也要施恩和报恩,因为一切善意都被看作施恩和随之而来的报恩。而在日本,同事之间、朋友之间都是平等的,没有恩情关系,也不需要建构恩情关系。因此,日本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是非恩情化的,额外的施恩并不受欢迎,因为它意味着一种需要偿还的债务负担。因此可以说,中国文化中的恩是普遍的,也是积极的、建构性的;而日本的恩是不普遍的、被动的、非建构性的。中国的恩文化是整体性的文化,而日本的恩文化只是局部性的文化。
此外,中日恩文化的情理关系也不尽相同。恩文化包括情感层面和理性层面,也就是既有“恩情”层面,也有“恩义”层面,这一点在中日文化中都是存在的;但在中日文化中两者的关系不同。中华恩文化在理性层面上制定了宗法制度,讲三纲五常,有天理人欲之别。在感性层面,它讲天性人情,制定了礼乐教化。于是情理一体、互相支撑,构成了中华文化的整体结构。中国传统文化的感性与理性未完全分化,道德、政治、法律等意识形态被情感化,因此中华文化重情感。中国恩文化情理未分,它既是一种普遍的伦理关系,又是一种本源的情感状态。恩文化是恩情与恩义的统一,但恩情是恩义的基础。中国文化中的恩首先意味着一种恩情,是一种感性的关系,它源于人的天性。孔子认为人天生就对父母有孝顺之心,如同父母天生就对子女有慈爱之心;孟子认为人天生有同情心即“不忍人之心”,这是仁义的根源。恩的情感层面具有本源性,而恩义建立在恩情的基础上,恩义要依附于恩情。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李泽厚先生认为中华文化是“情本体”的观点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日本文化中的恩虽然也有情的成分,但情并不主导“义理”,义理具有独立性,不建立在情的基础上。这就是说,日本的恩情和恩义是不相统属的,各自独立的。日本文化中没有对恩的本体论式的论证,恩也不以情感为基础。鲁思·本尼迪克特提出,日本文化中义理与人情是分离的,义理是社会的、普遍的,人情是个人的、偶然的,它与义理平行,具有独立性,并不受义理统属。新渡户稻造也认为:“例如对双亲的行为,唯一的动机应该说是爱,但在缺少爱的情况下,就必须有某种其他权威来命令履行孝道。于是人们就用义理来构成这个权威。”[1]24这就是说,在日本恩首先是一种义理,而非感情,不管父母、主君和天皇是否对子女、家臣、臣民有爱心,都不影响他们之间的恩义,都需要报恩。日本也讲恩情,但这不是根本,只是无关宏旨的个人的感情,恩义才是根本。
与此相应,中日恩文化也就有了另外一个不同点,即中国文化中的恩是双向的,而日本则是偏于单向的。中华文化不仅规定了受恩者报恩的义务,也规定了施恩者的施恩的义务,家长、君主等强者有对子女、臣民等弱者施以恩德的义务,而不仅仅是象征的功能。因此,中国的报恩要以施恩为条件,而不是单向的施恩或报恩,如果没有施恩,报恩也就失去了前提。 根据这个原则,就有父慈子孝、君明臣忠等一系列对等的伦理规范。例如在政治领域中,儒家就认为君主不贤德,可以行废立甚至革命。孟子告齐宣王曰:“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孟子·离娄章句下》)当然在传统社会后期,这种对等性发生了偏斜,更加强调了报恩,但并没有根本上改变恩的双向性。
日本的恩文化有单向性的倾向,它认为高等级身份对低等级身份的施恩并不是主动的、实际的,而是名义上的;而低等级身份对高等级身份的报恩则是主动的,要付诸实际的。而且低等级身份对高等级身份的服从和报恩则是无条件的,不以高等级身份的施恩为条件。日本的统治者并不把通过施恩建立与被统治者的情感联系作为维系统治的必要条件,而更直接地强调等级服从,因为他们认为统治本身就是一种恩。所以日本天皇能够“万世一系”,其原因也在于此。中国那种“船能载舟亦能覆舟”的观念在日本并不存在,所以贵族对平民也不须实行仁政。德川家康颁布的法令甚至规定:“对武士无理,对上级不逊的庶民,可立即斩杀。”[2]59
在日本伦理观念中,耻是一个重要范畴,因此日本文化也被称为耻感文化。耻与恩相对,是指下级对上级即被施恩者对施恩者报恩的义务感,如果不能报恩,就是耻辱。从表面上看,耻是一种自尊心,但这种自尊心是建立在恩的观念之上的。“在日本,自尊心是与对施恩者报恩联系在一起的。”[2]119耻感是建立在等级制度和恩文化的基础上的,具有约束性,因此本尼迪克特说:“真正的耻感文化依靠外部的强制力来做善行。”[2]202
正是由于日本恩文化的单向性,所以人们把恩当作一种需要偿还的债务。本尼迪克特认为,由于恩不同于无条件的爱,所以在日本“‘恩’是债务,必须偿还”,“‘报恩’被看作与‘恩’全然不同的另一个范畴”[2]105。这实际上指出了日本恩文化的单向性,即施恩只是一种等级身份的象征性功能,施恩者并没有施恩的义务,而受恩者有报恩—还债的义务。
五、中日恩文化差异的根源
中日恩文化之间为什么具有上述三点差异呢?首先,两者的起源不同。中国恩文化的渊源是祖先崇拜。原始社会先后有三种崇拜形式:自然崇拜、图腾崇拜和祖先崇拜。中国社会在走出原始社会后,并没有以文明宗教取代祖先崇拜,反而使祖先崇拜宗教化,成为普遍的信仰和社会伦理。特别是周代以降,以“德治”主义取代殷商的“鬼治”主义,提倡敬天法祖,祖先被神化,与天一道成为崇拜对象。一旦祖先被神化为崇拜对象,神恩变成了人恩,一切都是祖先所赐、所保佑,就要感谢、报答祖先的恩德。同时,这种崇拜也就延伸到活着的长辈,就要感谢、报答家长的恩德,从而形成了以孝为中心的恩文化体系。因此,《礼记》中说:“礼也者报也……反其所自始……礼报情,反始也。”这里说礼是关于报答人情的规范,根源于对祖先的报恩(反始)。于是,源于祖先崇拜的恩文化,以孝为始基,就具有了覆盖一切人伦领域的特征,也具有了恩情作为本源、恩义奠基于恩情的特性。
日本恩文化的起源是多元的,不只是祖先崇拜。作为政治伦理的恩,起源于神道教,是神崇拜与权力崇拜的结合。日本的本土宗教是神道教,它是一种带有原始宗教性质、缺乏经典和统一的教义。神道教发源于自然崇拜,同时也掺入了祖先崇拜的内容。它崇拜天照大神等神灵,认为它们是日本民族的保护神;同时又认为天皇是天照大神的后裔,神人合一,最后形成了天皇崇拜。日本民族认为天皇代表神灵祖先,所以要效忠于天皇,报神恩和国恩。这样,随着神道教的政治化,神恩就与人恩同一,形成了带有政治性的恩伦理。明治天皇于1882年颁发了《军人敕谕》中,阐述了“恩”和“忠”的观念:“朕赖汝等为股肱,汝等仰朕为首领。朕能否保护国家以报上天之恩,报祖宗之恩,端赖于汝等恪尽其职。”[2]194
神道教是恩文化的重要渊源,但不是唯一的渊源。鲁思·本尼迪克特认为,日本文化中多个理念(义理)各自独立,不存在统一的价值根据,这也体现在恩的理念上。除了神恩、国恩之外,还有家族伦理中的父母之恩、社会伦理中的师恩以及政治伦理中的主君之恩等,这些恩的理念有其独立的文化渊源。家族伦理的父母之恩和社会伦理的师恩以及政治伦理的主恩等应该与神道教无关,这些恩的观念或者来自氏族社会伦理的遗留,或者来源于封建等级制度的政治需要,也可能与儒家文化的影响有关。
其次,中华文化是世俗文化,而日本文化带有宗教性与世俗性混合的性质。中国虽然有宗教信仰,但不起主导作用。孔子讲“未知生,焉知死”“子不语怪力乱神”,可见是把宗教信仰置于伦理之下的。因此中国文化属于世俗文化,没有神恩,不以爱为核心。但社会伦理又需要建构一种情感上的联系以聚合社会人群。于是,不是神恩而是人恩、不是神圣的爱而是世俗的恩构成了基本的伦理观念。
日本有神道教信仰,不是单纯的世俗文化,但又没有形成欧洲那种宗教统治,不是单纯的宗教文化,而是世俗文化与宗教文化的混合。这就决定了日本恩文化具有人恩的性质。由于神道教是原始宗教的遗留,缺乏高级宗教的人道内涵,因此恩作为伦理观念具有神恩与人恩一体化的特点,皇恩即神恩,人恩获得了神恩的名义和绝对权威。特别在明治维新后,神道教与天皇制结合,形成了神权与王权的一体化。所以新渡户稻造说:“神道的教义包含了可以称为我们民族感情生活中两个压倒一切的特点——爱国心和忠义。”[1]19
再次,中日恩文化的社会基础也是不同的。中国恩文化的社会基础是家族制度。中国社会在从原始社会进入文明社会之时,家族并没有解体,家族被保留下来,成为社会的基本细胞。在中国宗法社会,血缘亲情成为基本的社会关系,家族伦理就成为普遍的社会伦理及宗法制度的核心。这一施恩—报恩的伦理模式,蔓延到在整个社会生活中,就形成了中国传统社会伦理关系。因此,从本质上说,恩文化源于中国的家长制。中国伦理中缺少平等的关系,以恩为内涵的伦理关系就成为一种权力的运作、一种支配关系。中国传统文化的伦理信条都是建立在恩的基础上,基本范畴,如礼、义、廉、耻、忠、孝、仁、爱、信、德等,都是恩情关系的凝定。
日本的恩文化的基础不是家族制度,而是封建领主制度。日本社会不是以家族为基本单位的宗法社会,而是以等级制度构成的封建社会,其社会关系不是家族制度的扩展,而是以领主与家臣关系为核心构成的不同的等级身份之间的关系。因此,这种主臣关系直接地规定了日本文化的性质。日本文化包括家族伦理,但不是家族伦理的延伸。日本的社会关系脱离了血缘关系,因此文化体系不是依据血缘亲情建构,而只能依据抽象的义理即等级服从。日本的家族伦理也不是建立在血缘亲情的基础上,而是等级制度在家庭中的体现,如父子关系、夫妻关系等都比照等级制度建立,是一种服从原则。而且,日本人对天皇的忠不能比附于对父亲的孝。因为天皇具有神性。本尼迪克特说:“说天皇是国民之父是不够的,因为父亲在家庭中虽然可要求子女尽一切任务,‘却可能是个不值得尊重的人’。天皇必须是远离一切世俗杂虑的圣父。”[2]114所以说,恩并不起源于血缘亲情,不是家族伦理的延伸,恩的情感性就不具有基础性而只能居于依附地位。
此外,中日恩伦理的文化背景不同。中国传统社会是平民社会,缺乏贵族精神,形成的是平民文化。平民社会没有等级服从,需要建构一种伦理上的主从关系。恩文化构成了实际的依附关系,父与子、君与臣、民与民之间都是一种主从关系。平民社会的社会关系决定了恩文化的双向性和情感性,尽管这也是一种非制度化的不平等的关系。与此同时,平民文化缺乏自律性而需要他律,而恩文化就以互相约束的恩构成了一种他律。
与中国的平民文化背景不同,日本的恩具有贵族文化的背景。在日本的贵族社会,等级制度规定了不平等的社会关系。日本文化的典范是“武士道”,即武士阶级的道德行为规范。耻感就主要发生于武士阶级。等级制度决定了日本的恩文化的单向性和非情感性,它是与等级服从相对应的。这就是说,恩主要指下级对上级的服从,报恩甚至不需要以施恩为前提,它是一种等级制的原则。此外,贵族社会需要一种自律性的文化,这是贵族精神的体现。因此,日本文化讲求以报恩为核心的身份责任,以忠于身份责任为荣,以违背身份责任为耻,形成了所谓“耻”感文化。
恩作为伦理观念,有其哲学根据,需要哲学的论证。中日恩文化的哲学根据不同:中国文化中恩的根据是仁;日本文化中恩的根据是义(义理)。中华文化以恩为核心,覆盖一切社会关系,这是因为恩是仁的体现,而仁具有本体论的地位,是道的体现。中国哲学认为,道既是天道,又是人道,道体现为人性,即所谓“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为教”。人性为何?孔子认为就是仁,这是最根本的人性,也是天道的落实。孔子认为,孝、忠、信、义等都是仁的具体化。仁不同于现代的爱,其核心就是恩,即强者对弱者施恩,弱者对强者报恩。孔子讲“仁者爱人”,何谓爱人?就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这就是施恩于人,就是恩爱。同样,受恩者也必须对施恩者感恩、回报,履行孝、忠、义等义务。所以,在中华文化中,恩不是偶然的、个别的行为,而是天经地义的法则,是人的本性,是核心的价值观念。
日本的恩文化没有本体论的根据,这首先是因为日本文化没有仁这样的核心概念。日本文化中没有一个统摄一切的核心范畴,各个领域的义理并不贯通。它的上面没有西方那种超验的本体,如上帝之爱;下面也没有中国那种伦理本体,如仁。日本虽然接受了儒家文化的一系列观念, 如忠、孝、信、义、诚、勇等,也有仁的观念,但并没有把仁作为核心范畴,它并不支配其他伦理范畴。在日本文化中,仁并不是最高的理念,不是人的本性,也不是根本的伦理法则,仅仅是一种个人化的情感,一种在义理之外的同情心。本尼迪克特认为:“事实上,‘仁’在日本是被排斥在伦理体系之外的德目,丧失了它在中国伦理体系中所具有的崇高地位。”[2]108日本语言体系中的爱,也不具有平等的性质,本尼迪克特说:“但是,‘爱’这个词在日文中特指上级对下属的‘爱’。……它的意思不仅是‘庇护’之意,而是一种亲爱之情。”[2]95新渡户稻造在《武士道》中,就把仁释为“恻隐之心”,是一种“温文尔雅的感情”和“对他人痛苦的同情”。而这只是一种个人的品质,而非普遍的道义。新渡户稻造认为,仁只是对武士的勇猛品格的一种补充,而非根本品格。他引用格言说:“过于义则固,过于仁则懦。”[1]29-35可见,在日本文化中,仁不是绝对的法则,而只是需要适当节制的情感。正因为如此,恩在日本文化体系中没有本体论根据,不具有中心地位,不能形成普遍的伦理范畴,而只具有有限的、局部的意义。
[1] 新渡户稻造:《武士道》,张俊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
[2] 鲁思·本尼迪克特:《菊与刀》,吕万和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