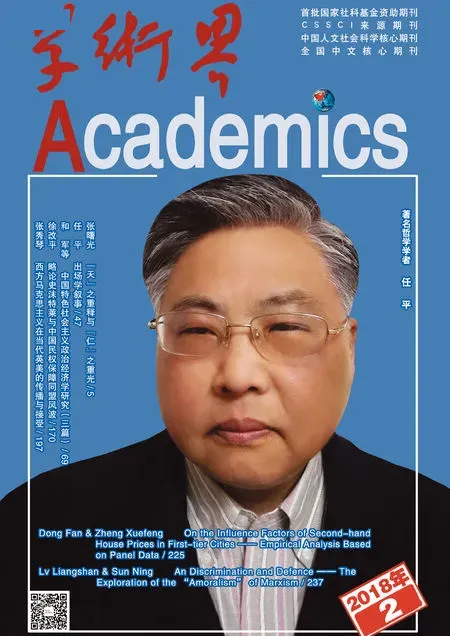以“苏联”“延安”“重庆”为地标的文学构建
——以《苏联纪行》《回忆延安》《离渝前×日记》为例
○ 唐 蕾
(南京大学 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 江苏 南京 210023)
《苏联纪行》《回忆延安》《离渝前×日记》三组散文自1945年10月至1946年4月相继发表在《新华日报》副刊上,连载时间上是相继且部分交叉的,郭沫若的《苏联纪行》发表时间最早,从1945年10月起,延续到次年1月;何其芳的《回忆延安》时间跨度最长,从1945年11月起,断续连载到次年4月;胡风的《离渝前×日记》发表时间最晚,从1946年4月3日起,到4月30日止。从散文内容所指向的时间来看,《苏联纪行》记录了郭沫若1945年6月到8月从重庆到苏联的游历过程,期间经历了抗战胜利;《离渝前×日记》记载胡风1946年2月在重庆接到赴沪通知到开赴前一段的情况,时处内战爆发前夕;《回忆延安》时间性最弱,文章间关联性不强,独立成篇,为何其芳1945到1946年间在重庆时所作。从数目来说,《苏联纪行》文章最多,近百篇,《回忆延安》和《离渝前×日记》均为二十余篇。但是《苏联纪行》与《离渝前×日记》连载紧凑,中间较少停顿,而《回忆延安》虽历时最久,但文章间隔较大。
三组散文最显性的关联就是都在一段历史时间内表达了较为明确的空间意识,并且形成空间上的交叉关系,其中《苏联纪行》是从重庆到苏联,《回忆延安》立足重庆回忆延安。如果从延安、苏联、重庆三者的政治延伸意义来看,三位作者都是立足延安(故乡),直指重庆(敌方),面向苏联(未来中国)的,三组文本之间形成政治上的关联,这当然也是《新华日报》副刊编辑的匠心所在。而从文学层面来看,拥有独立个性的不同主体在“延安、重庆、苏联”的时空关联中形成了既不相融合也不相分割的“和而不同”的状态。
一、三处“圣地”的显性空间观念
《苏联纪行》是郭沫若应苏联科学院之邀参加纪念大会所创作的游记。郭沫若从重庆出发,途经国内外多个城市,到达苏联后去各地参观游览。名为“苏联纪行”,实际在多个空间流转,旅行分为中国境内、经停诸国与苏联境内三部分,而郭沫若的情绪也跟随空间的转换不断发生着变化。在国内各地辗转时,因不忍离别,文章显出抑郁忧伤的情调。离开中国,途经印度、伊朗等国,短暂的客居他乡,作者一方面为异域风情所吸引,另一方面,游子情达到顶点,泛起了“怀乡病”。这“怀乡病”中,有对祖国的深深眷恋,作者在德黑兰(伊朗)受到使馆工作人员招待,喝上了盖碗的中国茶,产生了隽永的感情,“真是奇怪,不喝中国茶也仅仅只有十天,就像阔别了十年的一样”〔1〕,乡愁让作者对于凋敝的重庆产生了恋慕之情,“我对于重庆本是极端憎恨,觉得世界上再没有这样恶劣的地方。闷热,崎岖,不干净,一切都逼榨着人;但我今天离开了它,却不免怀着无限的恋慕。我的朋友,我的家,都陷在那儿,那儿就好像我的天国”,“纵使是热风如火,热汗如汤,我也愿意躺在那儿的垃圾堆上”〔2〕。然而这“怀乡病”中,也有因祖国贫弱而产生的激愤之情。面对衰败的东方文明,郭沫若感慨,“古代四大文明之一的发祥地,为什么今天成为了这样呢?一个始终梗在我心里的问题,我说出了口来。这儿不是美索布达米亚平原,古代巴比伦文明璀璨过的地方吗?为什么成了这样的沙漠呢?——你中国今天又有什么发明呢?出乎意外地那驯如子羔的仆欧这么反诘了我一句,我喝着的凉水好像变成了一瓢热汤”〔3〕。
然而这时而眷恋、时而忧伤、时而激愤的“怀乡病”在抵达苏联之后发生了变化。东方古国衰颓带来的压抑感已然褪去,而“在照片和电影里面久已熟习了的红场,克里姆林宫的尖塔,尖塔顶上的金星红星,都呈着欢喜的颜色在表示欢迎,好像在说:‘老乡,你来了!’”“是的,我来了。我确是到了莫斯科,就好像回到了自己的老家一样。我当然不懂话,但当一个赤子初到他的家的时候,他能懂话吗?”〔4〕在苏联,郭沫若受到家人般的热情接待,在博物馆与各类文化活动中寻找到了失落的故国之美,祖国的凋敝现实已经远去,眼前原本陌生的国度却变得熟悉和亲切了,换句话说,苏联正是“未来中国”。郭沫若感慨道:“我真是很爱慕这样的国民,他们真正了解对于人生必要的娱乐。这自然也是物质条件使他们这样的,他们的生活有保障,工作有保障,做了好多工便有好多报酬,医疗助产是官费,用不着有了今天愁明天。得到甘肃望西蜀,他们所得到的报酬自然便会求正当的享受了。乐天氏之民欤?无怀氏之民欤?这是古人的乌托邦式的想象,而在苏联只是现实。”〔5〕
和《苏联纪行》中空间的流转不同,《回忆延安》的空间是相对固定的,所有的文章都直指“延安”,但是延安并不是文章里唯一的空间,“重庆”作为它的对立面在文章中时隐时现。《回忆延安》是何其芳在重庆时所创作,文章多次采用对比的方式,以“重庆”反衬“延安”。《回忆延安》的“引子”里,何其芳描述了重庆的一幅幅画面:无家可归的人在大街上过夜,曾经的公务员只能当街乞讨,赤脚的小孩子在街上擦皮鞋,在重庆,这一切看起来都那么稀松平常。然而,在这将丑恶黑暗看作平常的重庆,何其芳四次表达“这时候我就想起了延安”,因为“延安没有这样的事情”〔6〕。何其芳损毁了在重庆习以为常的日常感受,把生机盎然的前景灌输给读者,让他们在对比中看到在重庆所看不到的全新的生活方式,试图将人们从麻木迟钝中唤醒,满怀希望地去追求完全不同的延安生活方式。而在此后的文章中,何其芳不断强化这种印象,营造出重庆(有时用“外面”表达)与延安的紧张对峙状态,延安的同志可以立即指出延安和重庆的差别:延安处处都是牛羊猪鸡的富足,外面的老百姓哪有这么多牲口的差别;外面到处是未经开垦的荒山,而延安怎么看得到荒地,到处是“像装满奶汁的乳房”一样的开垦过的黄色山头〔7〕。延安之外当然也有“锦绣江山”,但是锦绣江山养不活人,常常是途有饿殍;延安虽没有如画风景,却用“黄土”和小米养活了所有的人〔8〕。在外面,太太可以对餐馆里炒菜的大师傅指手画脚,不高兴还可以“喊警察来抓他去”,但是在延安,炒菜的大师傅可不听你的指挥,他可以坚持自己的做法……这一切的富足、平等都源自“这里是延安,不是外边”〔9〕。在这种对峙中,何其芳将“延安”作为主体强化突出,而“重庆”在文中则或隐或现,但这并不妨碍它作为对立物的一直在场,并且因为这种在场,何其芳“回忆”的延安对重庆的习惯化过程自觉起到反作用,产生“陌生化”的效果,在二者的紧张关系中烘托出延安。何其芳的“回忆延安”可谓精神还乡,他笔下的延安是素朴明朗的,但这种素朴明朗不是通过平静舒缓的笔调完成的,而是通过对比强化的方式表达的。
《离渝前×日记》从内容来说,仅仅局限于重庆,胡风展现了一个积弊已久的重庆,但是他对这承担着旧中国深重灾难的重庆并不厌弃。在胡风看来,重庆“是一个海,一个兼收并容的大海,里面栖息着各种各样的生灵:有的残暴地喝血,有的阴险地策动,有的勇敢地战斗,有的善良地受苦,有的机伶地变化,有的麻木地苟活……但也有的在逐渐生长,有的在逐渐死亡。你就这样地形成了你底壮观,你也就这样地联系着千千万万的人民底命运,千千万万的劳动者底痛苦,千千万万的受屈者底眼泪,千千万万的牺牲者底血液,千千万万的战斗者底意志”〔10〕。重庆是“兼收并容的大海”,重庆的黑暗不独属于重庆,也不只是政党腐败的产物,这里有残暴,有阴险,有麻木;同时也有勇敢,有善良,有机灵,从一定意义上来说,重庆即中国,即我们的母地,“她会把和平和谷粒预约给人们么?她会的,她愿意的。但如果要和平是普及众生的和平,谷粒是普及众生的谷粒,那我们就还得和她一道接受一个痛苦的锻炼过程”〔11〕。重庆是一个政治地标,但于胡风而言,重庆更是中国的缩影,是鲜花与癣疥并存的完整意义上的中国。
在通常意义上,“苏联”和“延安”被视为红色圣地,但是胡风却将“重庆”看作和“延安”并立的“圣地”,这种说法在当时一些人眼中显然是“石破天惊”的。然而,正因为胡风的“圣地”观点,让《苏联纪行》《回忆延安》《离渝前×日记》所描绘的“苏联”“延安”“重庆”三处圣地串联起来,形成一种空间特色鲜明的文学景观。三位作者的三处“圣地”,其实背后都隐含着“故乡”的概念,在《苏联纪行》中,乡愁连接着故国,行旅中也怀着“他乡是故乡”的期许。而《回忆延安》里,何其芳正是将延安作为“精神故乡”来表述的,所以发出“我又在我的想象里看见了那些我曾经歌颂过的‘像装满奶汁的乳房’一样开垦过的黄色山头”这样的感慨,延安给予的不仅是身体上,更是精神上的哺育。而胡风的《离渝前×日记》则将“重庆”引申为一个死亡与新生、黑暗与光明、肮脏与纯洁并存的“民族共同体”的概念。
虽然三组散文都有明确的空间意识,但是在表达上仍有较大差异。郭沫若在异域发现失落的故国与找寻未来中国,和“故乡”始终隔着一层,借助“游子”的身份,情绪在哀乐间切换,最后达到升华,因此“故乡”在他的笔下具有一定的丰富性。何其芳的《回忆延安》,身处延安之外,情感上、思想上却始终以“局内人”的身份讲述,因为距离太近,破坏了审美观照的力量。在讲述的过程中,作者不断对比、强化,往往是感情率先达到了高点,笔力却无法达到。当作者暂时跳脱出这种对立模式时,内容就会显得深刻一些。至于胡风的重庆日记,“重庆”没有被简单化、政治化,反而超出具体的时空限制,成为更为阔大的概念,连接着民族精神的骨血。
二、三组文本的“外在时间”与“内在时间”
《苏联纪行》《回忆延安》《离渝前×日记》三组散文发表时间和内容指向的时间大致相同,然而更重要的是独立于“外在时间”的“内在时间”。在《苏联纪行》中,郭沫若借助身体在不同空间的漫游,将这种“内在时间”分别表达为:昨日中国、今日中国与明日中国。作为游记,《苏联纪行》写了多个空间,但无论是国内、途经诸国还是苏联,其实这些空间都可以看作“中国”的某个历史阶段,它们或则是中国的过去,辉煌的东方文明举世瞩目;或则是中国的现在,贫弱衰败,在黑暗中摸索,在痛苦中挣扎;或则是中国的未来,国家独立自主,人们安居乐业,重建昔日辉煌。空间虽然变换,但从实质来说,只是“中国”的多面表达而已,贯穿其中的是时间。游记的尾声,郭沫若在苏联迎来了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消息,郭沫若借助苏联所展现的“明日中国”即将成为现实,文本的“内在时间”与“外在时间”合流,文本内在的文学性与外在的政治性也融合一体,结尾迎来了政治性的升华,郭沫若的游记圆满地完成了它在《新华日报》所应担负的“使命”。
同样地,《回忆延安》也有自己的“内在时间”。所谓“回忆”,本身就包含时间观念,但是文本以“延安”为中心的构建并未与作者所处时空构成明显的“回忆”关系,换句话说,作者始终和“延安”处在同一历史进程,并未跳脱出来形成反思,所以这组文章在时间上整体趋于静态,节奏和缓,与外在的时空环境形成反差。胡风在《离渝前×日记》中有一处细节写到“企香”(“企香”是何其芳在文章中的化名),颇有意味。何其芳来找胡风,让他对最近发表的一篇文章提意见,“这真是一个老实人,整个局势是兵荒马乱,我自己的心情也是兵荒马乱,怎样有时间来弄这样不急之务的讨论呢?而且,就是搁下几个月再谈,未必文艺底‘政治性’就睡觉了么?”〔12〕何其芳对于外在慌乱时间的漠视,“有时间”关注“不急之务”,这和他在《回忆延安》中所表现的不疾不徐是一致的。
尽管文本整体呈静态之势,但并不意味着《回忆延安》没有“内在时间”。仔细阅读,就会发现和胡风、郭沫若的文章不同,何其芳作为“回忆延安”的主体,却并不始终承担主体的叙述,有的时候“我”是一个隐藏的叙述者,有时是一个观众,有时又完全消失。《回忆延安》描绘了一幅“人物画卷”,有孙万福、吴满有、冯云鹏这样的边区劳动英雄,有谷老、赵步喜、陈万福等延安普通干部,也有续范亭、王震、贺龙等将领;却几乎没有知识分子的“人物传记”,唯一一篇《记冼星海同志》也是为“冼星海纪念特刊”所作。在《回忆延安》里,“我”不作为主体,主要起记录的作用,但是在对延安生活和人物的描述中却清晰地展现了“我”的变化。比如,“我”在最初的文艺创作中,对于那些曾经是长工的村干部、曾经是贫农的富农、曾经是奴隶的主人们并不关注,相反对于一个曾经是地主的农民十分感兴趣,采访他,参观他过去的生活。〔13〕但是,这样的“我”在与续范亭、王震、贺龙这样一些领导交往之后逐渐改变了。《回忆延安》中有5篇散文记述了续范亭的故事。〔14〕续范亭原是国民党军官,因为反对蒋介石消极抗日政策,而在中山陵剖腹明志,后来到延安。选择续范亭这样的人物作为记录对象,带有鲜明的政治性,何其芳完整地描述了续范亭政治转向的过程,从早年追随孙中山,到失望后转向宗教信仰,直到在延安终于找到了“朝闻道,夕死可矣”的信仰。如果说对续范亭的记述中,“我”还是身份平等的倾听者,那么到了对王震、贺龙等将领的叙述中,“我”就彻底失去了主动性。
《新华日报》在1946年1月16日、17日分两期连载了《记贺龙将军》一文,何其芳在文章中描绘了一个外表威严却平易近人、说话诙谐的革命将领。在何其芳看来,贺龙亲自去文协拜访延安作家,欢迎他们到部队中去表现出的“礼贤下士”令人感动,而贺龙对于鲁艺办学的关心更是达到了“醍醐灌顶”的效果。同样地,《记王震将军》也在对人物的描述中,重申了这种“醍醐灌顶”的效果。王震将军讲述了一个被大家认为“最落后”的战士,怎样从想退伍还乡到重新走回革命队伍的故事,而让他做出转变的正是古田会议决议案、《讲话》,以及毛主席正在做出的决议。听完这个故事,何其芳的感受是:“王震同志这个偶然的叙述就像给我们打开了一个新的世界:仿佛这就是早已应该出现在新的文学,新的戏剧里面的人物、场面。仿佛这就是怎样在创造着世界与历史的布尔塞维克的‘神秘’”〔15〕。政治家创造出了文学家所创造不出的、更加动人的故事,作为文学家的何其芳“甘拜下风”。而王震所说的“对于工农,我们真是应该努力为他们做事情,将功折罪呵”,“这,本来是对同学们说的,但对于我这个旁听者,对于我这个从地主家庭出身的人,这几句话也有些使我毛骨悚然。将功折罪,这是一句听来不大舒服的话,然而这是真理”〔16〕。在对贺龙、王震这样的将领的描述中,成为“忏悔者”的“我”在叙述中完全退缩,失去主体性地位。而“我”在其中的转变,恰恰构成了《回忆延安》的“内在时间”关系:昨日之我与今日之我。
作为“昨日之我”,彼时何其芳刚刚到达圣地延安,亢奋而充满惊喜,他激情澎湃地高呼自己在延安呼吸到了“自由的空气。宽大的空气。快活的空气。”〔17〕然而,《回忆延安》中“我”的情感却变得“平淡”了。“延安”在何其芳的笔下变成了一个符号,当它作为精神上的故乡时,丰满充实,一旦转化成文字,却让人感觉无所凭依。在这样的环境里,“我”不再是随意宣泄自我情绪的个人,而成为集体中无名的一员。在“我”的身边,到处是“无名”的英雄,我甚至“想不起他的全名来”,“名字,有什么重要呢,他来到我心里已经成为一个朴质地忠实地向革命献出了一切的农民干部的代表了”〔18〕。“我”主动承载起集体的记忆,成为“共同回忆”的讲述者,这种讲述过滤了个人情感与体验,因此所谓“回忆”其实是每一个延安人都能“无差异”表达的“共同回忆”。其时,周扬、艾青、丁玲、吴伯箫、陈学昭等为数众多的延安作家都写过边区劳动英雄,他们笔下的“吴满有”“田保霖”们和何其芳所创作的“孙万福”“冯云鹏”们并没有什么区别。这也就是来延安采访的记者赵超构所提到的“思想标准化”现象:“我在延安就有这么一个确定的经验,以同一的问题,问过二三十个人,从知识分子到工人,他们的答语,几乎是一致的”,“他们的思想,不仅标准化,而且定型了”。〔19〕在赵超构看来,《解放日报》上记载的都是些“生产消息”,“半夜就上山开荒”“打破纪录”“劳动英雄”、向某人“看齐”、向某人“挑战”一类火热的消息,“报纸小册子好比球场上的啦啦队,提高嗓子,向劳动英雄不断喝彩”〔20〕。然而在这种“过度紧张的空气”中,作家却获得了“安定”。这种“安定”源自思想的统一,“我”的消失。而从内在逻辑来看,正是《记贺龙将军》与《记王震将军》中都提及的《讲话》在起作用,《讲话》对于文学的规范划分了“昨日之我”与“今日之我”。
然而“昨日之我”与“今日之我”并不是完全隔绝的,在一些篇章中,还是能够窥见“昨日之我”的影子。在《H.同志和监狱》这篇文章中,何其芳描述了一位曾经被敌人关进监狱的H同志,他时常在寂静的深夜低低地哼起异样的悲苦的歌声,白天却显出热情快乐的神色。他的热情快乐让我“相信”他虽然形体受损,精神还是好的。直到从其他同事处得知,长期的失眠实际上已经导致H同志精神失常,时常引起一些“误会”。面对这些“误会”,何其芳和同事们发出“善意的哄笑”,“但是,在笑过以后,我又仿佛看见了他枯瘦的身体,看见了监狱,看见了他独自在深夜里点着亮亮的灯,并且在低声地哼起监狱中唱惯了的歌来”〔21〕。白天的H同志可以假装快乐,自我疗治;但是黑夜来临,当回忆汹涌而至,灵魂深处仍不免哼起“唱惯了的歌”,H同志的“白天”与“深夜”一定程度上不正是何其芳的“今日”与“昨日”。当然,这种回望“昨日之我”的内心探索只是“昙花一现”,文章的结尾,作者又回到了“今日之我”发出感慨,将这种痛苦转嫁于敌人的暴行。
胡风的《离渝前×日记》可谓三组散文里“外部时间”最彰显的作品。在胡风个人,是有记录历史“环节”意识的,“无论是历史行程或个人经历,每一个阶段都是一个环节,通过了它,才由过去走向未来的”。创作《离渝前×日记》“当时是开始了所谓和平斗争的时期,局势在微妙的变动过程中间发展,说话很容易犯错,而无为的日子又不大容易过。那么,就在不相干的小地方和这个社会的头发或指甲之类开一点不关痛痒的小玩笑罢。至多也不过如此而已”,“但就个人来说,当然是什么也说不上,至多至多也不过表现了一点在这样重要的环节里面只是无可奈何地打打滚的窘相而已。窘相就窘相罢,虽然绝对不能从这里看到什么历史的表情,但总也算是枝叶的摆动;虽然不过是枯了黄了的枝叶的摆动,但它们却依然是和历史的主干相连的”。〔22〕所以,尽管只是“枯了黄了的枝叶”,胡风仍让这些枝叶和时空相连,和他的主体精神血脉相连。
胡风在开篇说明自己是模仿了曹白的《离沪×日记》,写作的《离渝前×日记》。1938年曹白曾给胡风主编的《七月》创作了《离沪×日记》,记录了自己被组织“决定”离开上海之前的情况。和诸多注重人生“飞扬”“斗争”一面的文学作品不同,《离沪×日记》呈现的多是卑微琐碎的日常和小资产阶级式的软弱、无奈。曹白当时虽然做着革命的工作,然而却时常在工作中感到难堪的悲哀,生活的琐碎既已磨去工作的神圣性,勇敢的空言也无济于事,在作者看来不过是“忍耐着苦楚,而且忍耐着战斗”〔23〕,于是用敷衍的语调记录下来,激昂与低沉在这篇日记里倒了个个儿,在当时显然与时代力美的主流作品格格不入,然而这篇充斥着空气霉味的作品,却颇受胡风的青睐,成为《离渝前×日记》的“原型”。胡风曾评价曹白的作品:“如果虚伪的叫喊不一定必然得到战斗的感应,那么,真诚的叹息也未始不能引起对于残酷现实的憎恨和对于光明来日的追求,更何况热到发冷正和假到出汗一样,也并非不会有的事情。”〔24〕而在《离渝前×日记》中,胡风就表现了这种“热到发冷”的情绪。胡风在日记中写了自己接受命令即将离渝前的种种情状:去医院看望生病的朋友,才发现无怪乎剧作家们常常以医院为题材,实在是一家公立医院竟然连基本的设施都无法提供,管理上更是漏洞百出;朋友的姐姐在家里打赤脚种地养活自己,同时补助留洋的丈夫,然而丈夫回国后却半哄半吓地离了婚,顺心如意地在某部当着要员,朋友却不敢为姐姐讨公道,“怕去找的时候会遭到暗算,弄到失踪或者被关起”;而身边文艺界的朋友们也都陷在各自的平庸与琐碎中,他们中有中国最早的革命者,而终于在一次次“失势”后,笃信起命运来,早早地须发皓然了;有的在高谈理想之下,迫于生计还是只能主动去结交有权势者;有宣称无路可走,想做隐士而不成者……人人都是“帮凶”,在这历史的特殊“环节”,谋杀着别人和自己。然而,胡风并不诿过于人,他将自己也放在这“帮凶”的一群。孩子不懂为什么自杀也算犯罪,妻子开导他,“做人有义务,自杀就是逃避义务,对政府完粮纳税的义务,所以算犯罪”;儿子不服,“但公民也有权利呀,自杀了也就不要权利了,抵不得么!”胡风脱口而出:“你有什么权利?”本想和儿子开玩笑,“但刚一说出口,我听见我底声音不像开玩笑的声音,我底心情也不像开玩笑的心情”〔25〕。这质问不是对于儿子而是对于自己,自己何尝不是这崩坏的社会的“帮凶”,为着各种不大不小的“恩惠”,陪着笑脸,有时竟连自己都感觉有点“飘飘然”了,承认“在这样的社会里面,我们常常要做些零零碎碎的奴才的”〔26〕。孩子是社会的希望,对他们总要有些真诚。然而在给小朋友们做演讲时,话题既空泛无趣,实则也解决不了任何问题,但为着引起小朋友的兴趣,索性也就“模仿大演说家,加进一些可笑的说明,配以手势。果然时时引起了笑声,脸孔也都开朗了”〔27〕。越是卖力“表演”,获取的笑声掌声越多,情绪越热烈,就越是远离对于血肉的现实人生的搏斗,色调也就越发灰色阴冷。然而,这阴冷又实在是由“热”而来,是一种“热到发冷”的情绪。彼时胡风的“主观论”正受到攻击,在日记里他自嘲为“看不见客观现实的主观大家”〔28〕。在胡风看来,最有价值的斗争,不在社会的表面,而是深潜在带着血痕与泪痕的生活角落里。作家主体只有不断的自我扩张、自我搏斗,才能够与客观对象拥合,去反映这种深刻的斗争。而作家去深入和拥合的人民,“他们的生活欲求或生活斗争,虽然体现着历史的要求,但却是取着千变万化的形态和曲折复杂的路径,他们底精神要求虽然伸向着解放,但随时随地都潜伏着和扩展着几千年的精神奴役底创伤。作家深入他们,要不被这些感性存在的海洋所淹没,就得有和他们底生活内容搏斗的批判的力量”〔29〕。相比那种精神萎缩、流于表面的旁观,胡风要求作家不仅要有思辨的头脑,更要以极大的勇气去正视现实,深入生活的肌理,发现历史的本质,这正是一个情绪从激扬到冷静、由热到冷的过程。在这种“热到发冷”的情绪下,胡风开启了自己的“内在时间”。
胡风在日记里有一处细节,一位太太在路边摆着豆瓣罐子等人来买,自己心里暗笑这能卖几个钱,真是不把时间当时间,随即就回忆起在武汉的一幕。当时武汉形势危急,有办法的人们匆匆离去,然而“一个穷苦的女人拿着油瓶慢慢地穿过马路,好像是到店子去买一点油回去办她照例的晚餐。炮火就要来了,敌人底屠刀就要来了,但无数的穷苦的人们无地可走,因而也就不走,依然听天由命地过着照例的微贱的生活,而我们却丢下他们走了。抬头看一看照在夕阳光辉里的对江的龟山,它依然若无事然地坐在那里,几百年前几千年前它这样坐在那里,几百年后几千年后它也一定照样坐在那里,但在它底下面和周围,有多少生灵忍受了痛苦,遭到了灾殃”。“那以后,我有时会突然记起这一幕,那个女人就拿着油瓶慢慢地从我底眼前走过。胜利以后,开始只想到坐船回去,因而想到在武汉停留的时候就有时将那一幕同时记了起来。心里隐隐地怀着一个愿望,得去看看那马路,从那里望一望龟山,虽然同时也知道,那个女人十分之九不在了,或者流亡,或者被杀,或者汇进了战斗的队伍里面,但总想去看一看,望一望一定依然若无事然地坐在江对岸的龟山……。”〔30〕这个女人的身影深深烙印在胡风心里,乱世里有能力离开的“我们”(包括胡风在内)无情地抛弃了“他们”,然而他们也就自觉接受了这种“抛弃”,以一种照例的姿态走进历史的灰烬。说到底,抛弃“他们”的正是他们自己,他们所表现出的从容与安定正是历史深处的民族惰性。然而这历史的惰性并不单单源于这些无路可走的人,也属于匆匆逃遁的“我们”,这千百年来沉积的历史惰性潜伏、扩展,形成精神奴役的创伤。这个听天由命的女人和匆匆撤离的“我们”组成了整个中国,或者闭目塞听,或者消极躲避,没有反抗。胡风对于这千百年的历史惰性是极端厌恶的,他几乎笃定那个女人十分之九不在了,以时间的凝定不可能对抗变动的时代,听天由命的女人不会获得拯救,她的结果只有3条:流亡,被杀,革命。因此,抗战胜利后,胡风想回去看看这个象征着历史惰性的女人的最后结局。然而,想到那“依然若无事然地坐在江对岸的龟山”又让人绝望,它会让死去的女人复活,重复着几百几千年前一样的生活。这不受“外在时间”影响而永恒凝定的就是胡风在日记中揭示出的“内在时间”,它将在精神奴役创伤没有得到拯救的情况下永世轮回。
“现在我要走了,这街路白天当然是照例的熙熙攘攘,夜里当然是照例的荒凉落寞,不会感到因为我曾经多了一点什么,以后要少了一点什么的罢。这就像我自己,这大宇宙里面的一粒原子,这大中国身上的一个细胞说,在这里曾经给予了什么,又从这里带走了什么呢?然而,不论身外有着怎样的爱爱仇仇,或者说,正因为有着身外的爱爱仇仇,我带走的决不是空虚。真理无处不在,因而随处可以巡礼,反真理的力量也无处不在,因而随处可以赴敌,怕只怕自己没有巡礼的心和赴敌的心而已”〔31〕,临别前的胡风在重庆留下这么一段内心的拷问。一己之身留给一座城市、一个时代的印记几乎可以忽略,如果一定要说留下了什么,不过是借助个体与时空的关系所表达的。肉体置身于不同空间,只要与外在时间保持关联,那么就随处可以赴敌,随处可以巡礼。然而,胡风自己的内在时间却与外在时间错位,他超越了战时重庆,在民族根因的深处延展了他的时空观,他的时空因为主体的思考而化凝定为流动。只是胡风没有想到,若干年后,内外时间的错位会给他带来沉重的灾难。
《苏联纪行》《回忆延安》《离渝前×日记》三组散文在一个时间段内相继连载于《新华日报》副刊,以“苏联”“延安”“重庆”为地标,其政治性含义不言而喻。但是郭沫若、何其芳、胡风却将各自的“内在时间”输入这些政治性的空间,让它们和“外在时间”呈现交叉、并置、错位的关系。将这三组散文放在一起考察,既源自地标上的关联,更是因为在这种关联中所表现出的差异性。这些作品在作者本人都不是代表作,但在组合中却体现出了参照意义。它们的差异首先源于作家在思想、艺术上的差异,但是将它们视为一个整体时,这种差异又超越了具体作家的限制,展现出了超出具体历史时空定位的更为阔大的真实。
注释:
〔1〕郭沫若:《苏联纪行》,《新华日报》1945年10月22日副刊。
〔2〕郭沫若:《苏联纪行》,《新华日报》1945年10月18日副刊。
〔3〕郭沫若:《苏联纪行》,《新华日报》1945年10月21日副刊。
〔4〕郭沫若:《苏联纪行》,《新华日报》1945年10月28日副刊。
〔5〕郭沫若:《苏联纪行》,《新华日报》1945年11月15日副刊。
〔6〕何其芳:《回忆延安·引子》,《新华日报》1945年11月19日副刊。
〔7〕何其芳:《回忆延安·差别》,《新华日报》1945年11月20日副刊。
〔8〕何其芳:《回忆延安·锦绣江山与黄土》,《新华日报》1945年11月22日副刊。
〔9〕何其芳:《回忆延安·一个笑话》,《新华日报》1945年11月21日副刊。
〔10〕〔11〕胡风:《离渝前×日记》,《新华日报》1946年4月29日副刊。
〔12〕〔28〕胡风:《离渝前×日记》,《新华日报》1946年4月12日副刊。
〔13〕何其芳:《回忆延安·人民大翻身了》,《新华日报》1945年11月24日副刊。
〔14〕分别是12月1日《回忆延安·热情的老革命家》、12月2日《回忆延安·续范亭将军的诗》、12月3日《回忆延安·信仰》、12月10日《回忆延安·续范亭谈阎锡山》、12月16日《回忆延安·餐桌上的闲谈》。
〔15〕〔16〕何其芳:《回忆延安·记王震将军》,《新华日报》1945年12月19日副刊。
〔17〕何其芳:《我歌唱延安》,蓝棣之主编:《何其芳全集·第2集》,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41页。
〔18〕何其芳:《回忆延安·谷老》,《新华日报》1946年2月2日副刊。
〔19〕〔20〕赵超构:《延安一月》,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2年,第78、82页。
〔21〕何其芳:《回忆延安·H.同志和监狱》,《新华日报》1946年1月26日副刊。
〔22〕语出胡风《人环二记》“小引”部分。《离渝前×日记》后改名《出西土记》,与《浮南海记》结集出版《人环二记》,参见《胡风全集》(第4卷),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01-102页。
〔23〕曹白:《离沪×日记》,《呼吸》,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年,第77页。
〔24〕胡风:《曹白著〈呼吸〉小引》,《胡风全集》(第2卷),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665页。
〔25〕胡风:《离渝前×日记》,《新华日报》1946年4月11日副刊。
〔26〕胡风:《离渝前×日记》,《新华日报》1946年4月14日副刊。
〔27〕胡风:《离渝前×日记》,《新华日报》1946年4月5日副刊。
〔29〕胡风:《置身在为民主的斗争里面》,《胡风全集》(第3卷),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89页。
〔30〕胡风:《离渝前×日记》,《新华日报》1946年4月9日副刊。
〔31〕胡风:《离渝前×日记》,《新华日报》1946年4月28日副刊。
——兼及一类史料的应用
- 学术界的其它文章
- The Positive Role of Governance in the Way Environmental Policies Impact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Translator’s Style
—— A Corpus-based Case Study of Lianghuiwang〔*〕 - On the Influence Factors of Second-hand House Prices in First-tier Cities
—— 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Panel Data - 日本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研究“理论上的突破点”〔*〕
- 城市治理的差序参与〔*〕
——基于“市民服务热线”的分析视角 -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与实践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