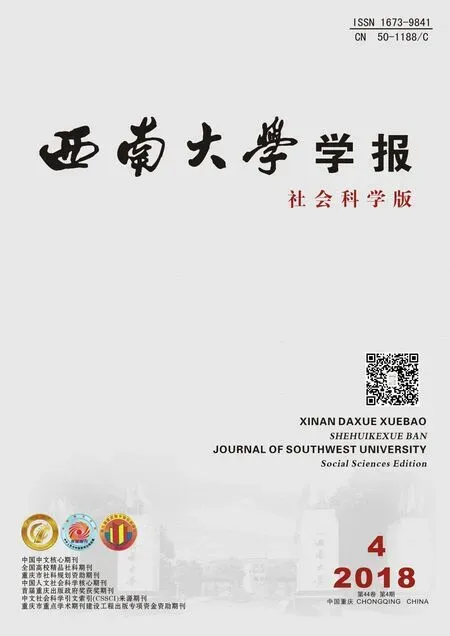明代职官奏请取问制度
周 囿 杉,柏 桦
(南开大学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学院及法学院,天津市 300071)
按照明代法律规定,具有一定级别及正官犯罪,要奏闻请旨发落,简称奏请,这是处理职官犯罪的必然程序。奏请主要有题奏与劾奏两种形式,劾奏可分奏劾与面劾两种形式。奏请取问类似于现代的立案程序,具体交由什么部门审理,则由皇帝的旨意决定。
一、奏请问罪
按照《大明律·名例》“职官有犯”“军官有犯”条规定,京官与在外五品以上文武官及正官犯罪,要开具所犯事由,实封奏闻或奏闻请旨取问,不允许本管衙门擅自勾问,这是文武职官犯罪审理的原则。
在律例中规定,凡是文武官员有犯赃、犯奸、行止有亏、诈伪、逞私争讼、失误等一切赃私罪名,都要奏请,但笞杖罪名不在奏请之列,这是因为文武职官犯笞杖以下罪名,可以处分当之。职官犯罪有公私之别,公罪可以“明立文案,每年一考,纪录罪名,九年一次,通考所犯次数、重轻,以凭黜陟”[1]文武官犯公罪,p284。私罪则“杖一百者,罢职不叙”[1]文武官犯私罪,p286;杖一百以下降等,俱解见任叙用。
按照明代文书制度,“下之达上,曰题,曰奏,曰表,曰讲章,曰书状,曰文册,曰揭帖,曰制对,曰露布,曰译”[2]卷72,职官志一,p1732。“题”是内外衙门的例行公事,“奏”是内外官员的申奏文书,“凡内外各衙门,一应公事用题本,其虽系公事而循例奏报、奏贺、若乞恩、认罪、缴敕、谢恩,并军民人等陈情、建言、伸诉等事,俱用奏本”[3]卷212,通政使司,p1059。题本属于正式公文,按例要钤印署名;奏本不用钤印,仅署名具奏,是非正式的公文。对于文武职官犯罪的奏闻请旨,主要采用这两种方式。在京由各衙门堂上等官,在外由都、布、按三司等具有上奏资格的官员具题奏请。事涉职官犯罪,文官要由吏部或刑部题覆,武官要由五军都督府或兵部题覆,最终请旨定夺,称为题奏。内外各官以个人名义对文武职官犯罪进行弹劾,皇帝下旨移付相关部门核实,再进行题奏,称为奏劾,多为风宪官员所奏,因为举劾是他们的职责。按照明代制度,皇帝要定期举行朝会,接受公卿奏事,不定期召见臣僚议事,若有文武职官犯罪,这些臣僚可以进行面劾;若是“露章”,也就是公开的章疏,也称为面劾。
从文武职官犯罪提出的角度来看,奏劾是主要的方式,这是具有上奏资格的臣子们都能够采用的方式。劾奏主要是列举罪行,提出处置意见,故此措辞都比较激烈。如嘉靖年间,保定巡抚弹劾所属各官时,讲到广平府管马通判张经济,“虽开伍拾有玖,见年实捌拾有壹,耳目聋聩,手足痿痺,牙齿脱落,虽尚能饮啖,但语音含糊,则不辨你我。自去冬拾壹月,潜自到任,通不出见抚按兵备,但率领恶子狞孙及无籍光棍数人,乘知府陈俎之公出,即扛台(抬)本官,私下各县点马,将各马头苦打索银,动称寻死图赖,所至之县,各索银不下数百两,犹同强盗打劫。及知府回日,差人禁止赶回,止救得邯郸、永年贰县不曾被害而已。及臣至该府,其子孙光棍已各逃回原籍,止存本官,坚卧宅内不出,仍欲候臣行后,破死求索银两,盖举世所未见,而一日不可留者也。除行该府,将本官俸粮住支,将马政行令知府带管外,合亟行罢黜,以快人心。”这种欺瞒年龄多达22岁,身边不但有恶子狞孙,还有无籍光棍,索银如强盗打劫,按理说应该予以问罪,但嘉靖帝并没有轻信,下旨云:“吏部知道。钦此。”要吏部予以核实,吏部并没有纠缠于该巡抚弹劾的罪状,却提出:“顺天等捌府,设有巡抚都御史贰员,巡按、巡关御史各贰员,提学、巡盐、印马、管屯御史各壹员,缘此捌府庶官,壹岁之间,被劾者几至十次,不惟事多掣肘,人无固志,抑且迎新送旧,劳民费财,况后者未必胜前者,调者又须别用,似涉纷更,殊非事体”。吏部官员所提出的问题很明白,这顺天八府有八个御史,其职责就是劾奏。除此之外,还有兵备道,按察司副使、佥事,都有巡视考察之责,地方官面对这么多的上司,难免动辄得咎,故此他们不去核实奏劾的内容,却提出让都察院将贪酷已著者按例提问,其余都戒饬供职,嘉靖帝也只好下旨:“是”[4]364-368。
具有上奏资格的臣子之间进行劾奏,是可以互劾的。如洪武时,福建按察使陶垕仲劾奏“布政使薛大方贪暴自肆”,薛大方也劾奏陶垕仲,最终他们一起被逮至京。“事既白,大方得罪,诏垕仲还官,闽人迎拜,为之语曰:‘陶使再来,天有眼;薛不去,地无皮’。”[5]卷170,洪武十八年春正月丙戌条,p2588、2589由此可见,在朱元璋时代,这种处置还是比较得人心的。洪武以后,不鼓励官员之间的互劾,一般称之为“讦奏”,则是两败俱伤。如“巡抚延安等处右佥都御史徐廷章,总兵官署都指挥佥事张杰,互讦奏不法诸罪”[6]卷10,天顺八年冬十月癸未条,p207。“广西总兵官泰宁侯陈泾,巡抚右佥都御史吴祯,讦奏不法诸状。”[6]卷12,天顺八年十二月壬午条,p253“镇守四川总兵官芮成等,与贵州副总李安等,互相讦奏失机事情。”[6]卷24,成化元年十二月戊寅条,p463对于这种互劾,皇帝一般都派遣官员前往核实真伪,然后再由核实官员奏请处置。按照正统四年(1439)《宪纲》规定:“凡都察院、按察司、堂上官,及首领官、各道监察御史、吏典,但有不公不法及旷职废事、贪淫暴横者,许互相纠举,毋得徇私容蔽。其所纠举,并要明具实迹,奏请按问明白,核奏区处。”[3]卷209,都察院·纠劾官邪,p1045明代在短时期还实行科道官互纠的制度,即嘉靖六年(1527),经吏部奏准:“两京科道官,有相应黜调考察遗漏者,互相纠举”[3]卷13,吏部·京官考察,p80。沈德符对此事的始末进行了论说,认为是当年“张璁以兵部左侍郎,为北科道所纠;桂萼以礼部右侍郎,为南科道所纠;虽俱奉旨留用,而心恨甚。萼乃疏谓杨廷和私党犹在言路,引宪宗初年例,于拾遗后,互相纠察”。实际上并没有这种例,却得到嘉靖帝的认可,“命吏部勒科道互相纠拾,时考察内六科已去四人,十三道已去十人矣”。这乃是桂萼“始终引杨廷和及大礼为言,耸动上听,以要必允,心虽狠而识则陋矣”[7]卷3,科道互纠,p883。这种出于政治报复而制定的制度,当然不能够长久,所以在嘉靖十七年(1538)予以废除。
对于相互劾奏有限制,却允许被劾奏人员进行奏辩。按照《大明律·名例·职官有犯》条规定:“若所属官被本管上司非理凌虐,亦听开具实迹,实封径直奏陈。”[8]4这是法律规定职官可以进行奏辩,但《大明律·刑律·诉讼·越诉》条规定:“若越本管官司,辄赴上司称诉者,笞五十”[8]174。正因为法律界限的模糊,对于职官因劾奏问题的奏辩受理与否,也要视情况而定。如四川按察使陈泰,被布政司参议陈敏希劾奏“擅杖武职,殴舆夫至死。逮刑部狱,坐斩。(陈)泰奏辩,大理卿俞士悦亦具状以闻。皆不听。”[2]卷159,陈泰传,p4334对陈泰的奏辩完全置之不理,有时却可以听信奏辩。如山西巡抚秦纮,劾奏镇国将军朱奇涧等罪:“奇涧父庆成王钟镒为奏辩,且诬(秦)纮。帝重违王意,逮纮下法司治”[2]卷178,秦纮传,p4743。无论如何,奏辩是在劾奏提出以后进行的,即便是听信奏辩,也会使奏辩者感觉到不安。如兵部右侍郎万恭,在寇逼通州时引疾,“于是给事中胡应嘉劾恭奸欺。恭奏辩,部议调恭。诏勿问。恭不自安,力请剧边自效”[2]卷223,万恭传,p5872。奏辩必须在皇帝允许的情况下进行,若没有得到皇帝允许,就是违制。如崇祯四年(1631),“御史水佳允连劾兵部尚书梁廷栋,廷栋不待旨即奏辩”,最终结果是“廷栋落职”[2]卷251,钱象坤传,p6493。朝廷对于奏辩并不重视,认为:“伸冤理枉,虽系仁育,但迩来奏辩,俱支吾隐饰,希图报复”[9]卷99,万历八年闰四月甲寅条,p1978。以此之故,职官一旦被劾奏,如果没有皇帝允许自陈的旨意,是很难进行自我奏辩的。
二、核实罪名
有关部门及风宪官奏请问罪之后,皇帝往往根据罪名所及与罪状轻重,交有关部门予以核议,或派相关官员前往核实情况,或直接置而不问,或直接交付有关部门议处与议罪。
职官的劾奏大部分先交吏部进行核议覆奏,吏部根据劾奏所涉及的职官,率先核对考语。明代实行考满制度,即“考满之法,三年给由,曰初考,六年曰再考,九年曰通考。依《职掌》事例考核升降”[2]卷71,选举志三,p1721。因为每三年一给由,吏部有历年的考语,若是被劾奏的职官考语多为称职,就是品行俱优,吏部会提出不予议罪或议处的建议;如果吏部考查与劾奏情况相同,也会提出具体的处置意见,报皇帝核准,即可付诸实施。如嘉靖间,直隶巡按弹劾青州兵备道佥事,今升广东布政司左参议沈沣,“肆志贪墨,不矜行检”;吏部查各年抚按的考语,“俱有清白勤励字样”,所以提出不予处置,嘉靖帝下旨:“是”[4]1111、1113。对于吏部的建议,皇帝也不是完全听信。如河南巡按弹劾提学副使焦维章,“行检不修,廉耻扫地”;管河副使高,“同僚鄙贱,市井传詈”;吏部考查之后,将二人按照“有疾”题请;嘉靖帝下旨云:“这本章内,焦维章、高,御史劾称贪滥昭彰,你部里却拟作有疾,与听调,如何臧否各异!还会同都察院从公定议来说,无纵无枉。其余依拟”[4]1115、1118。吏部为某些职官开脱,即便是没有考语俱优可凭,往往也会在劾奏文里寻找破绽。如嘉靖二十二年(1543),湖广巡按弹劾汉阳府知府应大桂:“德性廉静,虽孚于民情,处事周章,颇欠乎通变”;吏部便以应大桂“府分原已僻小,劾语又称廉静”,题请将其“策励供职”,嘉靖帝下旨:“是。”[4]1293、1298
一般来说,根据劾奏的罪名或罪行,皇帝会交不同的部门进行核覆,也就是说,各部院寺监府都有可能承担核覆的责任。如“巡抚四川左佥都御史李匡,劾奏贵州永宁等卫,及贵州布按二司官佥事张溆等,妄费粮储等罪。事下户部覆奏”[10]卷32,景泰三年三月戊戌条,p4603。“浙江右参政曹凯,劾奏镇守浙江左军都督同知李信,擅令民人舍余投充军役,冒名虚报,妄费粮储等罪。事下户部、兵部议。”[10]卷83,景泰七年夏四月辛亥条,p5633“山西左布政使李益,以潞城县供应细匹,织造不如法。工部劾奏其罪”[6]卷251,成化二十年夏四月乙丑条,p4248。这些都不是专门的法司,劾奏却可以下这些部门议覆。
劾奏多是列举犯罪的史实,故此核实的事务多交法司办理,因为是职官,则以都察院为主。按照《诸司职掌·都察院》规定:“职专纠劾百司,辩明冤枉,提督各道,及一应不公不法等事。”[3]卷209,都察院,p1039都察院不但与刑部、大理寺同为三法司,对文武职官也拥有独立审判权,有独立的都察院狱,故此职官犯罪,基本上都让都察院复核,称之为“都察院具闻”。都察院早期权力较大,如永乐时,陈瑛主持都察院事务,“天性残忍,受帝宠任,益务深刻,专以搏击为能”。他“为都御史数年,所论劾勋戚、大臣十余人,皆阴希帝指”。史家认为永乐帝“以篡得天下,御下多用重典。瑛首承风旨,倾诬排陷者无算”[2]卷308,奸臣陈瑛传,p7910、7911。这乃是采取春秋大义的笔法,为皇帝讳,而将罪归于臣下,实际上陈瑛所作所为,都是在永乐帝授意的情况下做出的。
刑部“掌天下刑名及徒隶、勾覆、关禁之政令”[2]卷72,职官志一,p1755。被劾奏的职官,皇帝命刑部进行究治与核实,也是正常的制度。如“兔儿山东马房仓火,户部尚书王佐等,劾奏主守官不谨罪,上命刑部究治之”[11]卷153,正统十二年闰四月戊寅条,p2997-2998。“陕西纪功兵部郎中杨琚,劾奏都指挥林盛冒报弟林俊、千户刘清等功次。上命刑部移文核实,以治其罪。”[6]卷29,成化二年夏四月丁卯条,p580
在众多劾奏的事件中,有些是皇帝直接命厂卫审鞫。厂是指东厂,明代一度还设有西厂、内行厂,长期存在的是东厂,拥有东厂狱,可以直接关押审讯人犯。卫是锦衣卫,其狱号称“诏狱”,由其属北镇抚司专理。“厂卫未有不相结者,狱情轻重,厂能得于内。而外廷有扞格者,卫则东西两司房访缉之,北司拷问之,锻炼周内,始送法司。即东厂所获,亦必移镇抚再鞫,而后刑部得拟其罪。故厂势强,则卫附之,厂势稍弱,则卫反气凌其上。”[2]卷95,刑法志三,p2339按照一般规则,厂卫鞫实,转交法司拟罪,但也有不交法司拟罪而直接处置的。如“掌锦衣卫事都督陆炳,劾奏司礼监太监李彬,侵盗帝真工所物料,及内府钱粮以数十万计,私役军丁造坟于黑山,会起丁字大券,循拟山陵,大不道,宜寘诸法。上命锦衣卫捕送镇抚司拷讯,下刑部拟罪”[12]卷444,嘉靖三十六年二月戊子条,p7575。这是按照正常的审问程序,拟罪归法司。“六科十三道劾奏五城兵马指挥司指挥李惟新等二十一员,不带夜巡铜牌,事觉,许令回话,奏对不实,俱宜问罪。上命锦衣卫镇抚司鞫之,寻各调外任。”[11]卷291,天顺二年五月丙午条,p6223这是进行了审讯,最后交吏部予以降调处分。“锦衣卫千户安贤,公差辞朝失仪。纠仪御史俞深、刘让,序班望玘,皆不举劾。东厂官校发其事,(俞)深等始请罪。上命锦衣卫各杖二十,释之。”[6]卷270,成化二十一年九月壬子条,p4556这是锦衣卫直接处置,并没有交付法司与吏部议罪或议处。
还有一些劾奏事件采取多官会鞫,或者是皇帝亲鞫。如“太监僧保、金英等,恃势私创塌店十一处,各令无赖子弟霸集商货,甚为时害。事闻。上命锦衣卫同监察御史治之”[11]卷29,正统二年夏四月壬申条,p580。御史大夫汪广洋、陈宁,劾奏太师韩国公李善长,“善长父子免冠待罪”,朱元璋亲鞫云:“善长,国之大臣,不能律身教,子劾之诚是,但念相从之久,宥之勿问。”[5]卷108,洪武九年八月丙寅条,p1805
凡是皇帝亲自过问的劾奏事件,若是不予以追究,或是宥免,皇帝也需要讲明理由,申明是宥免、姑宥、再犯不宥。如“监察御史张骏等,劾奏阳武侯薛禄,以更番操练为名,擅调山海等处守关士卒至京,致边防不固,请罪之。禄闻奏,叩首服罪。上命宥之”[13]卷57,宣德四年八月壬辰条,p1365。这是薛禄认罪态度良好,所以宥之。“巡按直隶监察御史余思宽,劾奏永平都指挥佥事萧敬,纵放所部军士,不严守备,致寇入境杀掠。”宣德帝认为:“闻鸡林颇捷,可赎前过,姑宥之,仍停俸三月。”[13]卷66,宣德五年五月壬子条,p1555-1556这是尚有功可抵,暂时宥免,以后再犯则有记录在案。“四川总兵官左都督陈怀,多干预民事,布政司、按察司官,稍有违误,辄加凌辱,各道监察御史劾奏之。上以怀出于行伍,姑宥不问,但以御史章示之,且敕责之。”[13]卷66,宣德五年五月癸丑条,p1557这是暂时宥免,但进行了申诫。“巡按四川监察御史王翱,劾奏四川都指挥赵得,镇守松潘,贼斫伤旗军,得畏惮不率兵追讨,请罪之。上命姑戴罪捕贼,不获不宥。”这是让其戴罪立功,如果不能够捕贼,将不宥免。皇帝所讲的宥免理由各异,有些在情理之中,有些则是政治权术,其中原因不但值得推敲,而且耐人寻味。
三、取问拟罪
劾奏事件经不同的部门核覆以后,根据罪责,若是皇帝认为应该治罪,则交法司、锦衣卫、巡按御史、巡抚等议罪,或钦派官员前往审理拟罪,便进入审理程序。
劾奏都是列有罪状的,在一般情况下,职官犯罪例由都察院复核,但明代司法审判主要由三法司与厂卫两个系统所构成。三法司是刑部、都察院、大理寺,按照分工,刑部受理天下刑名,都察院掌纠劾,大理寺掌驳正,乃是专门审理刑事案件的中央司法审判机关。厂卫是指东厂、锦衣卫,直接听命于皇帝,进行侦缉和办理诏狱。“除三法司外,也有其他中央机关得兼理司法审判。这些中央机关包括内阁、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宗人府、五城御史、司礼监、锦衣卫等机关。三法司是狭义的中央司法审判机关,三法司之外的其他兼理司法审判的机关则属于广义的司法审判机关。”[14]14正因为如此,事涉职官的犯罪,交与何种司法审判机关审理,皇帝往往有决定权,但也有一定的规律可循,如果皇帝违背规律,臣僚们可以提出异议,并且进行抗争。
据王世贞考证:“永乐十八年(1420)立东厂,命内官一人主,拨锦衣卫官校剌诇大小事情。成化十二年(1476),增立西厂,命御马监太监汪直主之,权出东厂上。正德三年(1508),东厂有太监丘聚,西厂太监谷大用矣。复以荣府旧仓地为内行厂,司礼太监刘瑾自领之,得诇察一切及二厂不法事。”[15]卷15,皇明异典述·三厂,p268-269这些宦官衙门虽然是在皇帝特许下设置的,但毕竟不是祖制,若是皇帝过多地将职官交付这些部门审理,群臣进行抗争,往往也会收到一定效果。如成化十三年(1477),“夏四月,汪直执郎中武清、乐章,太医院院判蒋宗武,行人张廷纲,浙江布政使刘福下西厂狱。五月甲戌,执左通政方贤下西厂狱”[2]卷14,宪宗纪二,p174。大学士商辂率同官条上汪直十一罪,“会九卿项忠等亦劾直,是日遂罢西厂”[2]卷176,商辂传,p4691。虽然是暂时的胜利,却也“人心稍安”[6]卷167,成化十三年六月庚戌条,p3027。刘瑾专权,户部尚书“韩文一发不中,而顾命诸臣斥逐无遗。六给事、十三御史之章再入,而谏官台臣诛锄略尽”[16]卷43,刘瑾用事,第6册p65。虽然以朝臣惨败而告终,毕竟还是前赴后继,尔后士大夫风骨则荡然无存了。谢肇淛认为:“宦官之祸,虽天性之无良,而亦我辈让成之,辅相大臣,不得辞其责也。”[17]卷15,事部三,p458身为辅相大臣,率先阿附宦官,群臣争先仿效,“骨鲠之风,扫地尽矣”[18]卷122,修政弭灾疏略,p1177。在这种情况下,皇帝对于劾奏事件,不交付法司,而交付厂卫审理也为常态。“嘉靖中,内臣犯法,诏免逮问,唯下司礼监治。刑部尚书林俊言:‘宫府一体,内臣所犯,宜下法司,明正其罪,不当废祖宗法。’不听。”[2]卷95,刑法志三,p2341臣僚微弱的抗争,皇帝一个“不听”,也就无可奈何了。
明代中叶以后,宦官参与审讯成为制度,“凡大审录,赍敕张黄盖于大理寺,为三尺坛,中坐,三法司左右坐,御史、郎中以下捧牍立,唯诺趋走惟谨。三法司视成案,有所出入轻重,俱视中官意,不敢忤也”[2]卷95,刑法志三,p2341。在这种情况下,劾奏事件,凡是有宦官与锦衣卫的参与,其余参与取问拟罪的官员,也只有惟命是从了。如弘治二年(1489),南京监察御史姜绾等,劾奏南京守备太监蒋琮,导致彼此更相奏诉,“上命太监何穆,大理寺少卿杨谧,锦衣卫指挥杨纲偕往”,结果,姜绾“及御史金章、刘逊、孙纮、纪杰、曹玉、谭肃、徐礼、余浚皆就逮,而(蒋)琮所占官房酒楼地,悉归之官云”[19]卷31,弘治二年十月癸卯条,p701、702。最终还是“宥(蒋)琮不问”,史家认为是“时刘吉窃柄,素恶南京御史劾己,故兴此狱”[2]卷304,宦官蒋琮传,p7786。刘吉是“纸糊三阁老(万安、刘吉、刘翊)”之一,“多智数,善附会,自缘饰,锐于营私,时为言路所攻。居内阁十八年,人目之为‘刘绵花’,以其耐弹也”[2]卷168,刘吉传,p4529。此案审理三人之中,只有杨谧是朝官,还是属于说不上话的人,也难怪蒋琮“由是益无忌”[2]卷304,宦官蒋琮传,p7786,这也是凡有宦官与锦衣卫参与审理劾奏事件的惯例,也不能够完全归罪于某个人,官僚政治特征在于官僚们只关注自身利益,为了自己的利益,往往采取屈服,不敢履行自己的职责,甚至同流合污,助纣为虐也是在所难免的。
按照《大明律·名例·职官有犯》条规定:“六品以下,听分巡御史、按察司并分司,取问明白。议拟闻奏区处。”[1]明代律例汇编·职官有犯,p268按察司长官按察使,分司即按察副使、佥事,分巡御史即巡按御史,而当巡抚普遍设置之后,抚按被称为“两院”。按照职责,“按察使,掌一省刑名按劾之事。纠官邪,戢奸暴,平狱讼,雪冤抑,以振扬风纪,而澄清其吏治。大者暨都、布二司会议,告抚、按,以听于部、院”[2]卷75,职官志四,p1840。在地方司法方面,“凡死刑,各府州县等衙门自问,及奉抚按批行者,俱申呈抚按照详,仍监候会审。如各道自行批行者,不必呈详抚按,止候会审。其奉抚按批行者,照旧呈详。都司卫所,与府州县事体同”[3]卷211,都察院·抚按通例,p1056。朱元璋“外建都布按三司,实有臂指相使之势”。设置巡按御史以后,“御史之与按察使副使、佥事等,均为风宪,俱名察官”,由于“三司谄佞阿附,要求保荐,以为进身之阶,所以养成粗傲之御史”[18]卷155,正名祛弊以光治体事,p1554。此后,普遍设置巡抚,与巡按分庭抗礼,在成化年间,“各处巡按举劾巡抚及方面等官,因被劾之人讦奏,往往并令御史回籍听勘”[18]卷151,应诏陈言时政以裨修省疏,p1515,巡抚已经处在优势地位。当镇守中官设置之后,地方上形成“三堂”,以至于“国家之制,边防以文臣巡抚,以武臣总兵,而内臣纲维之。事体相埒,职位相等,胜则同其功,败则同其罪”[6]卷90,成化七年四月甲辰条,p1745。在这种情况下,事涉地方官的劾奏事件处置,也发生一定的变化。如正统时,一般职官劾奏事件,多由巡按御史核覆。如福建巡按丁俊,因为考察按察司经历沈文铭老疾,导致其赴部申诉,吏部见其“年方少壮,素无疾病”,结果“事下巡按御史赵奎覆之”[11]卷36,正统二年十一月丁未条,p706。如果事涉巡按,则要下巡抚核覆。如巡按监察御史左瑺,考察嘉兴县县丞赵恭“设施无方,黜罢为民”,赵恭诣阙诉,“事下巡抚侍郎等官廉察”[11]卷43,正统三年六月己卯条,p847。在当时的体制下,即便是事下巡抚、巡按,也要他们会同三司官共同核覆。如镇守延绥等处都督佥事王祯,与陕西布政司右参政年富,相互劾奏,“事下巡按御史同三司会勘”[11]卷80,正统六年六月丙子条,p1590。“巡按山西监察御史吉庆,太原府知府袁海,互以不法讦奏。事下巡抚河南山西大理寺左少卿于谦等覆实。”这里强调“等”,则巡抚不能够独断,而到了成化年间,这个“等”字几乎就不见了,可见此时巡抚、巡按可以独专,但有时也要巡抚、巡按会同。如分守万全右卫右参将署都督佥事孙素,劾奏所部指挥使李贤有罪状,“下巡抚都御史秦纮,会巡按御史验问”[6]卷238,成化十九年三月丁酉条,p4036。由于普遍设置镇守太监,地方事务多有他们参与,如“镇守甘肃太监颜义等奏,游击将军都督同知赵英,擅放备御官军”[6]卷41,成化三年夏四月癸亥条,p851。“命陕西镇守、巡抚、巡按及都、布、按三司等官详议。”[6]卷42,成化三年五月丙子条,p859在抚按发生争执之事,镇守中官的意向往往能够决定胜负,三者之间还能够保持平衡。嘉靖时裁撤镇守中官,地方上少了平衡之人,故此“抚按之争”愈演愈烈。
在多头司法体制下,作为君主偏信厂卫,也是必然的。如正统时,参赞宁夏军务罗绮,被陕西署都指挥佥事陈斌等劾奏为贪酷,正统帝“下巡按监察御史覆之,以为多虚”。再下三法司鞫,也不过是“赎徒还职”。于是改命锦衣卫鞫之,罗绮便“引伏”了。因此正统帝认为:“三法司专理刑狱,而不公至此”[11]卷144,正统十一年八月戊戌条,p2838-2837,也就无怪乎皇帝不信任法司,将职官取问之事交与厂卫办理了。
四、政治分析
君主专制要求君主乾纲独断,太阿之剑不能倒持,权柄之威不能下移,将权力尽可能地集中于上,并且运用各种制度及手段,严厉打击与消弥各种企图削弱君主权力及触犯君主权威的政治行为,职官奏请取问制度理所当然地会成为君主手中的工具。
孟德斯鸠认为:“由于专制权力的性质的关系,施行专制统治的单独个人也同样地用单独一个人去替他行使他的权力。”[20]18在这种情况下,作为专制君主,会充分地利用制度赋予他的权力,进而达到实质上的专权。例如,朱棣以“靖难之役”夺取了帝位,在欢迎他进入南京的人群中,有曾经与他对垒过的李景隆,他是开国第三功臣李文忠之子,洪武十九年(1386)袭爵曹国公,虽然多次到湖广、陕西、河南等地练军,却没有实战经验,建文元年(1399)受命率50万大军征讨朱棣,大败亏输,而当朱棣兵临城下的时候,他却开门迎接,因此被加封太子太师,位极人臣,不但那些从龙的靖难诸功臣不满,就是建文诸臣也对他恨之入骨,其实朱棣也看不上他。朱棣新登大宝,毕竟要安抚降臣,故此对他优礼有加,让他主持修《太祖高皇帝实录》,并下敕书有云:“尔景隆,国之懿戚,自少暨壮,服事皇考,庙谟睿略,多所闻知”[21]卷13,洪武三十五年冬十月己未条,p233。明眼人都知道,这种不给实权的礼遇,实际上不是重用,揣摩上意的臣僚们岂能够不知。永乐二年(1404),先是周王朱橚上疏揭发李景隆受赂,接着刑部尚书郑赐弹劾其“包藏祸心,不守臣节,隐匿亡命”[21]卷33,永乐二年秋七月甲寅条,p577;然后是成国公朱能、吏部尚书蹇义,率文武百官劾奏“李景隆及其弟增枝,阴养逋逃蒋阿演辈,谋为不轨”。面对群臣的劾奏,永乐帝下旨:“逮蒋阿演辈鞫之”[21]卷33,永乐二年秋七月乙卯条,p577、578,并没有处置李景隆,却也让群臣知道不会再重用他了。在这种情况下,六科都给事中张信等再次劾奏:“李景隆心怀怨望,密造奸谋,招纳逋逃,图为不轨,条列其罪”。永乐帝似乎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去勋号,绝朝请,其以曹国公爵归第”[21]卷33,永乐二年秋七月丙辰条,p578。群臣还是不依不饶,礼部尚书李至刚同六部、都察院等又进行劾奏,“乞正典刑,以收国柄”。永乐帝讲:“朕自有以处之。”[21]卷33,永乐二年八月癸未条,p587永乐帝的所谓“处之”,自然引起群臣的猜度,礼部尚书李至刚等便劾奏李景隆的弟弟李增枝,永乐帝将“其庄田佃仆俱没入官”[21]卷33,永乐二年八月丙戌条,p588。痛打落水狗,是官场上的惯例,吏部尚书蹇义等继续劾奏,并且提出:“今陛下乃欲曲庇景隆,圣人之治,去邪勿疑”。永乐帝曰:“卿等所言良是,然朕既宥之,姑寘勿论。”[21]卷34,永乐二年九月己未条,p602可能是火候未到,锦衣卫指挥同知潘谞等接着劾奏,直接称李景隆为“奸臣”,依然是“姑寘之”[21]卷34,永乐二年九月庚申条,p602。永乐帝将李景隆及其弟李增枝等禁锢在北京,没收其全部财产,没有杀他,是为了全亲亲之谊,毕竟李景隆是其妹夫;将之禁锢则以观其变,其后李景隆绝食“旬日”,永乐帝置之不理,却发现李景隆家属,“潜逃沧州诸处,阴结党类,欲行劫狱”[21]卷199,永乐十六年夏四月癸巳条,p2075。可见永乐帝一直关注李景隆的动向,直至其死。从这次群臣奏请将李景隆问罪的过程来看,永乐帝一直把握尺度,既不能够落下杀功杀亲的罪名,也不能够不洞察其奸。从群臣劾奏“包藏不轨”,到“奸臣”的指称来看,永乐帝并没有提出异议。若是依照“奸党罪”来处置,正不知道多少人要被牵连,在群臣急于摆脱“奸党”罪名的情况下,肯定会有所表现。在劾奏过程中,不但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六科等官都参与了,连武职官中的都督、指挥同知等也不甘示弱,永乐帝在文武群臣中发现可以利用的人。无怪史家云:“听言之际,明睿所照,不待其尽,洞见底蕴。”[21]卷274,永乐二十二年八月壬午条,p2476在职官奏请取问制度下,这种“君临之术”的发挥,可以说是不胜枚举。
在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制度下,君主是权力的享有者和供给者,官僚们为了维护自身的权势地位,必须要依靠君主,获得君主的宠信。“专制政体不存在,当作一种社会体制看的官僚政治也无法存在。”[22]39在官僚政治的条件下,官僚们出于利己的意志,参与政治斗争,结成团伙而互相倾轧,也成为难以克服的弊端,而利用奏请取问制度,以达到利己的政治目的,也就成为必然。如洪武三年(1370),中书右丞杨宪,为了排挤中书左丞汪广洋,便“剌求丞相汪广洋阴事,令侍御史刘炳、鄯某等劾奏之,广洋因免官还乡里”。斩草除根,回乡里则难免被再度起用,杨宪便让刘炳再奏,要将汪广洋迁徙海南。在没有得到朱元璋认可的情况下,杨宪又让刘炳“诬奏刑部侍郎左安善入人罪”,以便再度牵连汪广洋,结果被以察察为明的朱元璋发现隐情,将刘炳下狱,经过拷讯,“尽吐其实”。杨宪属于浙东集团,为首者乃是刘基,虽然刘基曾经评价杨宪“有相才无相器”[2]卷128,刘基传,p3780,但与其评价汪广洋、胡惟庸相比,还是出色很多,所以在刘炳招供的情况下,“太史令刘基并发其奸状及诸阴事”,最终导致杨宪与刘炳等人“皆伏诛”[5]卷54,洪武三年秋七月丙辰条,p1071。在这里可以看到官僚们是如何利用奏请取问制度相互倾轧的,而为了摆脱浙东集团之嫌,刘基率先检举揭发,朱元璋则成功地进行驾驭。
孟德斯鸠认为:“行政的妙处,乃在于十分懂得在不同的情况下应使用哪一部分权力,而且宽猛得宜。”[20]209在君主专制政体下,无论是君主,还是官僚,都懂得这种行政妙处,而且应用自如。比如嘉靖初年,大学士杨廷和以拥立之功,居然敢独断专行,“先后封还御批者四,执奏几三十疏,帝常忽忽有所恨”。嘉靖帝的表情,早已被左右看到,“因乘间言廷和恣无人臣礼”[2]卷190,杨廷和传,p5038。兵科给事中史道,因为不满被调外任,便上言杨廷和“为漏网元恶”。杨廷和则一方面上疏自辩,一方面乞致仕,而此时嘉靖帝羽翼未丰,还不能够黜退杨廷和,便以史道“挟私妄言,颠倒是非,巧佞迎合,摧辱大臣,变乱国是”为名,将之下诏狱,而廷臣为杨廷和鸣不平的也不在少数,嘉靖帝只得承认杨廷和是“社稷之臣”,但还是允许科道官劾奏“朋奸党恶,纳贿实迹”[12]卷21,嘉靖元年十二月戊子条,p614、615、616。这无疑是释放一个信号,在杨廷和三疏乞致仕不许的情况下,御史曹嘉上言:“为大臣者真能擅威权以移主柄,党大臣者真能取容悦以惑圣德矣”。嘉靖帝将其“疏下所司”[12]卷22,嘉靖二年正月丙辰条,p639,杨廷和只有再求去,而“数日辅臣无至阁者”[12]卷22,嘉靖二年正月戊午条,p640。嘉靖帝慰留再三,科道官们便极论“大小臣工,互相诋訾”之非,嘉靖帝“下其章于吏部”[12]卷22,嘉靖二年正月乙丑条,p644、645。科道官们则上疏督促内阁大学士入阁办事,且认为他们有朋党之嫌。嘉靖帝曰:“朝廷清明,岂可辄以朋党之说指斥大臣?为大臣者,身任天下之重,岂忍轻易求去?”派人“往廷和宅,宣谕朕意”[12]卷22,嘉靖二年正月庚午条,p648。一场风波暂时过去,但嘉靖帝“然意内移矣”,最终在嘉靖三年(1524),让杨廷和致仕,“责以因辞归咎,非大臣道”[2]卷190,杨廷和传,p5038、5039。从这个过程,可以看到君主与臣下们充分利用奏请取问制度来进行政治较量,而在君主专制政体之下,最终的结果必定是臣下的失败,却会有另外一批臣下从中获得政治利益。以史道、曹嘉而言,他们先是官复原职,之后升为布政使,成为方面大员,算是政治投机成功,但最终也难逃被黜免罢职的命运。
总之,明代职官奏请取问制度在具体实施过程中还是饶有成效的,在相当长时期内发挥了澄清吏治的效用。如成化年间,户科给事中陈寿“劾去镇守中官不检者”[2]卷186,陈寿传,p4933。天顺年间,李纲“历按南畿、浙江。劾去浙江赃吏至四百余人”[2]卷159,李纲传,p4343。巡抚邢宥“奏黜不识者百七十余人”[2]卷159,邢宥传,p4341。正德六年(1511),巡盐御史张士隆,“劾去贪污运使刘愉”[2]卷188,张士隆传,p4992。史称朱元璋“惩元季吏治纵弛,民生凋敝,重绳贪吏”,在高压之下,“一时守令畏法,洁己爱民,以当上指,吏治焕然丕变矣”,以至于吏治澄清者百余年。即便是“英、武之际,内外多故,而民心无土崩瓦解之虞者,亦由吏鲜贪残,故祸乱易弭也”[2]卷281,循吏传序,p7185。其中应该有奏请取问制度的功效,其合理部分应该予以肯定。王亚南从官僚政治层面进行解读,认为:“特殊自然条件和历史条件所造成的专制主义、官僚主义与封建主义混合统治形态”[22]146,虽然没有阻碍中国社会的进步,但也应该看到官僚政治的沉重压力,因为“专制政体的原则是不断在腐化的,因为这个原则在性质上就是腐化的东西”[20]149。腐化则源自这种“事上安下”的制度设计,因为其本身变数是很大的。只要搞好与皇帝及上司的关系,就能够保住和争取更大的利益。在这种情况下,规定细密的职官奏请取问制度,也只能够沦为政治斗争的工具。
参考文献:
[1] 黄彰健.明代律例汇编[M].台北: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七十五.1979.
[2] 张廷玉,等.明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
[3] 申时行,等.明会典[M].北京:中华书局,1989.
[4] 不著撰人.吏部考功司题稿[M].台北:台湾伟文图书公司,1977.
[5] 明太祖实录[M].北京:北平图书馆藏红格本,1962.
[6] 明宪宗实录[M].北京:北平图书馆藏红格本,1962。
[7] 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补遗[M].北京:中华书局,1959.
[8] 怀效锋,点校.大明律[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
[9] 明神宗实录[M].北京:北平图书馆藏红格本,1962.
[10] 废帝郕戾王附录[M].北京:北平图书馆藏红格本,1962.
[11] 明英宗实录[M].北京:北平图书馆藏红格本,1962.
[12] 明世宗实录[M].北京:北平图书馆藏红格本,1962.
[13] 明宣宗实录[M].北京:北平图书馆藏红格本,1962.
[14] 那思陆.明代中央司法审判制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15] 王世贞,撰;魏连科,点校.弇山堂别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5.
[16] 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M].北京:中华书局,1985.
[17] 谢肇淛.五杂俎[M].北京:中华书局,1959.
[18] 陈子龙.明经世文编[M].北京:中华书局,1962.
[19] 明孝宗实录[M].北京:北平图书馆藏红格本,1962.
[20] 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册[M].张雁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
[21] 明太宗实录[M].北京:北平图书馆藏红格本,1962.
[22] 王亚南:中国官僚政治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1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