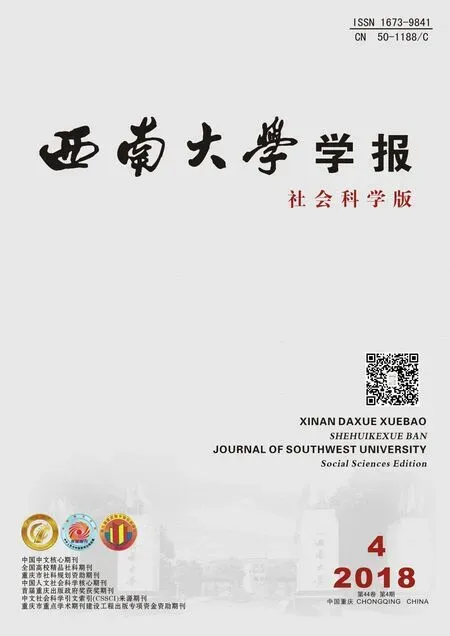儒家与人权的“普遍性”论证
李 秋 祺
(华东师范大学 政治学系,上海市 200241)
在近30年中西学术界关于人权的论争中,总是离不开“普遍性”和“特殊性”这两个对立的概念。人权到底是普遍的还是特殊的?这个问题至今尚未有一个确定的结论。甚至,由于它被认为是无法解决的,提出这个问题的意义也开始受到怀疑*一方面,以米哈伊尔·伊格纳季耶夫(Michael Ignatieff)为代表的一些西方学者,认为国际社会只要有人权法就足够了,哲学上的“普遍性”论证既不清楚也不可靠,所以只会削弱国际人权法的权威。另一方面,“普遍性”这个概念在后现代理论的冲击下,被批评为西方文化将其他文化“他者化”的一个工具。西方文化并不试图认识自己,而是通过将非西方的文化视为“特殊性”的,来完成自身的“普遍性”认同。但是,就像酒井植树提出的,西方这个“假想的统一体”正逐渐被解构。在这个背景下,非西方的社会已经不能够用力争自身“特殊性”的方式将自己和西方社会区分开来了。如果所有的文化都是“特殊的”,作为对立的“普遍性”概念也就自我消解了。参见Michael Ignatieff, “Human rights as Idolatry”, in Michael Ignatieff et al., eds. Human Rights as Politics and Idolatr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1,p.55. 酒井直树:《现代性与其批判:普遍主义和特殊主义的问题》,白培德译,见张京媛主编:《后殖民理论与文化批评》,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86页。。
这里的问题是,难道一定要在“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对立中才能理解“普遍性”概念吗?是否有可能将“人权是普遍的还是特殊的”这个问题加以转化,追问“哪种‘普遍性’更适合用来讨论人权”。在使用“普遍性”概念的时候,许多讨论人权问题的学者就已经假定我们知道这个概念意味着什么,没有必要再对其进行定义和分析了。然而,这个人人都自以为知道的概念恰恰是一个涵盖了多种可能的集合体*在陈嘉映看来,“普遍性”不是一个单独的问题,而是一个题域。因为,从诸多具体的事物中抽象出一个普遍原则,实际上存在多种抽象的可能和途径。生产出怎样的“普遍性”,取决于人的需求。参见陈嘉映:《普遍性种种》,见陈嘉映主编:《普遍性种种》,北京:华夏出版社,2011年版,第3-14页。。“普遍性”概念的多义性并不能说明讨论它是没有意义的,与之相反,“哪一种‘普遍性’”这个问题恰恰可以将我们从“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对立中解放出来。
近30年来,在中西学术界儒家和人权的问题一直是讨论的热点,并且已经发展出了丰富的学术脉络。时至今日,学术界对儒家立场的解读却不尽相同,甚至相互对立。为了区分和比较这些观点,本文试着将海德格尔的前存在论(更广义的存在论)作为切入点,考察儒家内部是否有可能发展出一种支持人权的普遍伦理。
一、儒家与人权的内容:规范性论述层面的比较
在新加坡、马来西亚等东亚社会的语境中,原始儒家对人权概念的个体化原则、法权特征等提出了质疑*参见《曼谷宣言》(1993年3-4月)和《维也纳宣言》(1993年6月)对人权概念中文化“特殊性”以及发展权的强调。。比如,个体权利的实现是否优先于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的权利?权利优先的制度是否会破坏儒家“礼”的社会理想[1]?在这些话题中,儒家思想被用来辩护非西方社会人权概念的“特殊性”。这些社会不但在历史、文化上和西方社会是不同的,并且在历史、文化上的“特殊性”还转变为了一种规范性的论证——在人权概念的解释上,“我们”应当有所不同。
那么,为什么儒家思想会被用来为人权的“特殊性”辩护呢?克雷格·威廉姆斯(Craig Williams)认为这是儒家经典的解释问题,比如,将儒家的“仁政”和权威主义等同起来,乃是一种过于简单化的解读。他梳理了儒家在中国各个朝代的政治实践,发现儒家一直试图限制权力的滥用,而从未真正将这种限制制度化。在现代社会中,儒家思想的权威正式从法律系统中剥离出来,因此约束政府权力就更加成了空谈[2]。在防止权力的滥用上,人权和儒家的“仁”有着相同的目标,而人权的法理意义正好解决了儒家长久以来制度化方面的弱点。
然而,这些在儒学中发现人权概念的乐观主义者很容易受到另一些学者的挑战,他们更忠实于儒家经典的文本。在普遍人权的话语中,通过法律来保障权利是一种积极的政治实践,但这显然不是儒家的理想世界。在《论语》中,孔子道:“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3]178如果在一个社会里,每个人都需要用法律途径才能维护自己的权利,说明这个社会已经陷入了伦理上的无序状态。在这个意义上,克雷格·威廉姆斯认为人权的法理意义可以帮助实现儒家的“仁政”理想,其实忽略了儒家同样期待一个“无讼”的社会。作为一个法学概念,人权不但抽象地规定了个人的应得之物,更重要的是它以法律的形式保证了人如何实现自己的诉求。为了调和人权的法理意义和儒家的“无讼”理想,一些学者试图通过赋予两者不同的价值权重,使它们可以在一个社会中发挥各自的优势。
比如,陈祖为提出,原始儒家“无讼”的理想并不是反对人权概念本身,而是反对人权的滥用。这就是说,当人和人之间产生冲突的时候,先应当提倡以自我约束和相互妥协的方式来解决。只有当冲突没有妥协的余地时,才考虑诉诸法律途径[4]。换而言之,“无讼”乃是值得追求的一个美好前景,它的价值要高于权利。假如这个前景没有实现或者只实现了一部分,人们依然可以通过声明自己的权利来获得保障。
但是,这种价值区分的方式真的调和了人权和儒学之间的矛盾吗?贾斯廷·蒂沃尔德(Justin Tiwald)提出了另一种可能性——在权利概念没有被使用的时候(unclaimed),只要它已经体现在法律中了,就会给人和人的关系造成消极的影响[5]。这种法律形式假设人和人之间是不能相互信任的,以此为基础,为了他人或整个社会的利益来进行自我约束就显得没有意义了。因为,一个人使自己的行为服从“礼”,却不能指望任何人同样如此,一个互惠的循环从一开始就无法形成。
实际上,在这些围绕着原始儒家和人权概念是否可以兼容的讨论中,追问谁代表了儒家的正统解释是没有意义的。这些学者所集中引述的文本《论语》《孟子》,本来就不是以定义的精确性为重点的文本。比如,孔子多次论“仁”,每次都论述了“仁”的某一个特征,很难说清楚哪种“仁”的解释最符合孔子的本意。那么,是否应当等量齐观地看待这些关于儒家的争论呢?为了理清各种观点之间的分歧,我认为可以在两个层面上做出区分,一个是关于原始儒家自身的,另一个在于普遍人权的论证类型。
在考察儒家经典中和人权概念有关的内容时,需要分清楚文本中所讨论的是一种人性的概述还是政治上的规范性论述。这涉及到两个不同的问题,即“人是什么”和“人应当怎么做”。在这个层面上,最明显的区分就是儒家对“平等”的理解。即使在天性上人是“平等”的,在实践上人和人之间仍然有很大差异,这个差异构成了儒家讨论人性问题的起点。这里的问题在于,儒家对人性的概述是如何进入其规范性论证中的?
相对于抽象的人性论,区分长幼亲疏的“礼”则是儒家行为规范对“不平等”的具体表达。“礼”的目标本身并不是为了将人区分开,而是通过区分来提高人的德性。在这样一个因果关系的论述下,“礼”才成为了判别行为对错的一个根据。“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3]13在儒家看来,通过“不平等”的礼,反而实现了“人皆可以为尧、舜”[6]265的“平等”理念。
但是,行为规范上的“不平等”并不能扩大到社会生活的其他层面。孔子亦言:“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贫而患不均,不患寡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3]250经济上的“不平等”会影响社会的安定、“仁政”的实施,因此从规范的意义上来说,儒家主张调节经济上的“不平等”状态。孔子被问道:“既富矣,又何加焉?”[3]191答道:“教之。”[3]191从这里可以看出,社会财富的分配问题最后还是回到了人的德性培养上面。在教育资源的分配上,孔子则根据平等的人性观提倡“有教无类”[3]247,即认为社会应当给予每个人“平等”的教育机会。
原始儒家一方面根据“平等”人性观,推导出了支持现代意义上生存权、教育权的规范性内容。另一方面,以“礼”为代表的儒家规范说明,“不平等”在某些情况下也可以有助于“仁政”的实施、德性的普遍培养。而对于人权来说,“平等”既是手段也是目标,这一点显然不同于儒家“礼”的设想。唐纳德·J. 芒罗(Donald J. Munro)看到了儒家“性相近”的人性观在规范性论证上的局限。他举例说,虽然儒家肯定了人天性上拥有“平等”的潜力成为有德性的人,却没有将这种形式的“平等”用来论证人和人之间在政治参与权上的“平等”[7]。徐复观通过追溯中西的思想脉络,发现西方的“平等”观念最开始只是一种思辨性的学术,在社会的现代转型中才扩大到了政治生活的方方面面。与此相反,中国儒家的“平等”观念最先以激进的人性观出现,在历史的发展中则越来越趋向于保守,缩小到了私人讲学的教育事业上[8]。在这个意义上,兰德尔·纳多(Randall Nadeau)、克雷格·威廉姆斯、陈祖为等学者在讨论儒家与人权概念的时候,将儒家经典中支持人权的文本一概而论,是不合适的。儒家支持人权概念中的某些内容,不等于赞成让这些内容直接成为政治规范[9]。如果引述的经典属于儒家对人性的概述,就要进一步讨论这个根据如何进入儒家的规范性论述。
二、儒家与人权的形式:一个旧方法无法解决的悖论
另一个同样重要的问题在于,原始儒家可以被用来讨论人权概念哪一层次的规范性论证?这里就需要区分人权的内容和形式。近30年来,中西学术界对这个问题的讨论主要停留在儒家学说是否支持人权的内容。但是,在讨论的儒家经典满足这两个条件的情况下,即(a)它在儒家的规范性论证中具有重要作用,(b)它支持人权概念的某一项内容,如言论自由、受教育的权利,这个论证仍然不能说明儒家支持人权。因为,我们所理解的人权总是“普遍性”的人权。
《世界人权宣言》在第一条即宣布:“人人生而自由,在尊严和权利上一律平等。”在第二条中解释了什么是“人人”“生而”和“平等”:“人人有资格享受本宣言所载的一切权利和自由,不分种族、肤色、性别、语言、宗教、政治或其他见解、国籍或社会出身、财产、出生或其他身份等任何区别。”在人权的问题上,它的形式甚至是比它的内容更为关键的组成部分。因为,各个社会传统都在某种程度上规定了共同体内部或某一阶层、某一族群应享有什么样的利益,却没有一种社会传统试图将这种规定无条件地扩大到每个人身上[10]。在每个人都无条件享有人权的条件下,才能进一步确定人权的内容[11]。在这个意义上,人权的形式也就优先于内容了。在讨论儒家是否支持权利的内容之前,需要明确它对于人权“普遍性”的态度。在儒家内部有可能引申出这样一种“普遍性”的条件下,考察儒家和人权内容的关系才是有意义的。
那么,原始儒家中是否有支持“普遍性”的因素呢?如果有,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普遍性”呢?在这个问题上,不同学者之间的观点也大相径庭,比较有代表性的例子分别是新儒家的牟宗三和社会学家费孝通。
在牟宗三看来,原始儒家乃是一常道,只是“外王”之说在新的时代应该有新的表现形式,即民主和科学[12]。民主和科学在儒家“内圣”的“普遍性”进路中是开不出来的,只有在相反的逻辑中探索,才能辩证地开出民主和科学所要求的“普遍性”。在这个意义上,牟宗三一方面肯定了儒家的“仁”是一种超越了时间性和空间性的普遍原则。比如,在形而上学的层面上,儒家的“普遍性”原理“仁”和西方哲学的“理性”是同一的*牟宗三写道:“此具有普遍性之原理,儒家名之曰‘仁’。吾人现在亦可转名之曰‘绝对理性’。此绝对理性在人文的实践过程中彰着其自己。吾人即由此实践而认识其为指导历史或贯穿历史之精神原则,即吾人上文所说孔子经由反省而显之‘意义’。”参见牟宗三:《道德的理想主义》,台北:台湾学术书局,1992年版,第10-11页。。另一方面,他认为“普遍性”概念本身就是多义的,“仁”所依据则是具体的普遍原则,而科学所依据的是抽象的普遍原则*牟宗三在中西哲学的对比中讨论“普遍性”概念的多义性:“‘具体的普遍’是黑格尔所造的名词。西方历来从亚里士多德起,一讲普遍只有抽象的普遍(abstract universal),没有所谓具体的普遍。什么是具体的普遍呢?这在西方人是很难了解的,但在中国人就很容易了解。比如说孔子讲仁,仁是个普遍的原则,但是你不能说仁是个抽象的概念。仁是不能和科学、数学、逻辑里面所谓的抽象概念相提并论的。照孔子所说的,仁是可以在我们眼前真实的生命里头具体呈现的。”参见牟宗三:《中国哲学十九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27-28页。。在牟宗三看来,中国儒家传统注重前一种“普遍性”,而受到科学思维影响的近现代西方社会就只承认后一种“普遍性”了。他从黑格尔哲学的角度推论说,儒家的“内圣”之说虽然直接开不出“新外王”,通过辩证的方式却可以和“新外王”相贯通[13]。理论贯通的前提便是区分“仁”的“普遍性”和民主科学的“普遍性”有何不同[14]。
再者,若是不对原始儒家做一番重构的工作,它就自然而然地落入了反对“普遍性”概念的范畴。在现代思想脉络的背景下提及“普遍性”一词,特别是在人权的语境中,“普遍性”总是意味着普遍的平等。然而,单从理论上来讲,“普遍性”也有可能指普遍的不平等。比如,有一类批评就集中在原始儒家“爱有差等”的观念上面。费孝通将此观念生动地比做“同心圆波纹”,即每一个人都形成了以自己为中心的社会网络,越往外推关系就越疏远[15]42。由于这种差序格局对所有人都是一样的,就不能说它不是一种“普遍性”的形式,只是此形式和人权语境中的“普遍性”概念相差太远。在费孝通看来,如果从自己向外推,推到国家层面已经很淡了,更别说超越国家的国际社会。在中国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中,以“等差之爱”为特征的个人伦理一直处于和“平等”“社会责任”“世界主义”等价值相悖的尴尬地位。
牟宗三和费孝通的观点都涉及到了原始儒家和它在政治实践上的表现形式。这两种观点各执一词,正好说明了理论规范和政治实践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为了对儒家的“普遍性”概念做一纯理论的分析,就有必要忽略作为实践的这一部分,讨论儒家给自己设立了一种什么样的“普遍性”标准。
不能否认,儒家既有“等差之爱”,也有一种不问身份、性别、阶层的普遍之爱。这个“普遍性”的标准内在儒家“仁”的观念中,即:“樊迟问仁。子曰:‘爱人。’”[3]182同时,儒家的确将人的自我作为“普遍性”伦理的起点。孔子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3]241这是从“不应当对人做什么”而言的,从更积极的角度,孔子认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3]83-84这个“普遍性”的标准并不像康德的“道德律令”那么绝对,在具体的情境里,“等差之爱”和“普遍性”标准是可以有先后顺序的。比如,孟子主张在有余力的情况下再努力实现普遍的伦理标准:“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6]291-292
这种普遍伦理和以亲疏远近为基础的行为规范同时出现在儒家经典中,以至于很难让人相信儒家真诚地设立了一种“普遍性”的标准。为什么要将两种全然不同的伦理形式皆视为“仁”的表现呢?赵汀阳认为,儒家对自身缺少普遍原则这一点是自觉的,并且也在为此感到焦虑。对于这个问题的矛盾性,他概括为“行对言的解构”,即儒家的“仁”并不超越它的实践,反而是在特殊的情境下被定义的[16]。这个批评的问题在于,赵汀阳所论的普遍原则是基于西方形而上学而设立的理想标准,即认为“普遍性”必须超越一切特殊的情境。然而,很难证明在孔子的时代,儒家就已经知道这种“普遍性”的形式并且认为它是重要的。笔者在这里试着提出一个更为有效的考察方式,即从儒家的视角来理解它的“普遍性”概念。
三、海德格尔与儒家的“普遍性”进路
为什么对于原始儒家来说,由自身出发的个人伦理可以作为“普遍性”的根据呢?这个问题涉及到了两个方面的讨论。首先,这需要澄清“普遍性”概念是唯一的还是多义的。如果“普遍性”概念是唯一的,就无从讨论这儒家“普遍性”和形而上学“普遍性”的差异,而只能判断“普遍性”概念的真假。其次,为了比较这两种“普遍性”概念哪个更适合用来论证人权,就需要将它们置入同一个理论背景下进行分析,使它们之间的差异成为有关联的。但是,对“普遍性”问题的澄清,既不能从西方的形而上学来解释儒学,也不能从儒家出发来评判西方的形而上学。只有通过引入第三种理论,才能更公正地讨论造成差异的支配因素。在这两个任务的要求下,笔者从海德格尔的前存在论出发,尝试界定这两种“普遍性”的差异,并进一步分析它们和人权概念之间的关系。
海德格尔认为,分析形而上学“普遍性”的理论局限,是在开辟新的“普遍性”进路之前一项必不可少的准备工作。从形而上学出发,最高“普遍性”即“存在”概念本身,它的定义超出了逻辑学能够定义的范畴,“存在既不能用定义方法从更高的概念导出,又不能由较低的概念来描述”[17]。由此,在西方形而上学的传统中,“存在”概念被看作是无法定义的,也即不证自明的。什么是最普遍的概念?这个问题一旦有了答案,就给“普遍性”设置了界限、前提或条件,而“普遍性”在形而上学中应当是无限、无前提、无条件的。在这个矛盾的背景下,海德格尔试图通过提出一种更为原始的前存在论,使“存在”概念成为显明的、可讨论的[18]。
在前存在论的意义上,具有最高“普遍性”的概念之所以能够存在,是因为它已经被领悟了。什么是“存在”?这取决于存在者如何存在的一种事先筹划。这就是说,“普遍性”概念的有效性依赖于它的界限,而无限、无前提、无条件的“普遍性”是不存在的。海德格尔对西方形而上学传统的扬弃并非一种简单的颠倒,他没有说“特殊性”高于“普遍性”——这样一来“特殊性”和“普遍性”依然是对立的。从前存在论出发重新理解的“普遍性”概念,由于其存在的前提、条件有所不同,从而可以相互区分。
由此,海德格尔哲学开启了“何种‘普遍性’”的追问,从而启示了儒家的“普遍性”“特殊”于形而上学的“普遍性”。产生于形而上学的“普遍性”即一个统一的最高原则被设置为根据、标准的结果,所以“特殊性”总是在较低的、被动的意义上被理解。在这里,“统一”意味着这个原则和所有其他原则都发生关联,而“最高”意味着这种关联是支配和被支配、价值上的高和低。如果说儒家是特殊的,它的正当性就面临着“普遍性”的挑战。如果它试图论证自身的“普遍性”,就必然要用一个西方的理论框架进行自我重构。就像张祥龙批评新儒家为了力争“普遍性”,成了西方文化的一个“他者”[19]。所以,一种对儒家思想建设性的解读不能再依赖于“普遍性”与“特殊性”对立的结构,而是要返回它最初设想的“普遍性”形式。
若追问儒家“普遍性”的根据在哪里,可以试想儒家的普遍伦理实际上是建立在“等差之爱”上面的。王阳明对原始儒家有一精辟的阐释:“问:‘程子云:‘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何墨氏‘兼爱’反不得谓之仁?’先生曰:‘此亦甚难言,须是诸君自体认出来始得。仁是造化生生不息之理,虽弥漫周遍,无处不是,然其流行发生,亦只有个渐,所以生生不息……’”[20]在他看来,“仁”是一个生成发展的过程,就像树木生根发芽、长出枝叶一般。人先要考虑自己的欲求和不欲之事,或是先培养自身的修养,然后才能将此外推到身边的人,再从亲近的人推到所有人。
不同“普遍性”概念在前存在论上的特征和它的形成过程息息相关,因此“普遍性”的根据即意味着它的起源*赵敦华认为,“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理论可以追溯到同一种预设,即“关于本质的发生学教条”。普遍主义假设一种价值观在产生的时候便获得了决定性的本质,特殊主义则强调一种价值观在产生时所依赖的是差异而非本质。他批评这种普遍主义往往和西方中心主义联系在一起,但同样不可否认的是,起源问题在“普遍性”的构成上起到了关键作用。参见赵敦华:《为普遍主义辩护——兼评中国文化特殊主义思潮》,《学术月刊》,2007年第5期,第36页。。王阳明认为,墨子“兼爱”的理想缺少最初的发展动力,它只是一个“无根”的空想。这个能够作为“仁”生成动力的根据,必须是切近于人并且容易被大众所分享的,家庭的纽带正好符合这一要求。于是,儒学在它的发展历程中一直坚持着“家-国-天下”一体的原则。孟子言:“君子之于物也,爱之而弗仁;于民也,仁之而弗亲。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6]315因此,“等差之爱”一方面区分了不同层次的爱,另一方面将不同层次的爱看作是起源与结果。
如果同样追本溯源,西方形而上学的“普遍性”则先设立了一个统一的最高原则,其他的原则都是从这个原则向下推出来的。在这个意义上,最高的原则即普遍原则,它支配了各种“特殊性”原则的形成。费孝通以西方形而上学的“普遍性”为对照,认为“等差之爱”不可能成为“普遍性”的根据。一方面,他承认在家庭内部,儒家强调“克己”的无私精神并主张将这种精神外推到“国家”或“天下”层面;另一方面,他提出一旦“家”和“国”之间有了利益冲突,为“家”而牺牲“国”在儒家看来也是合理的。因此,在以个人伦理为基础的儒家社会中,一开始就不可能出现一个统一的最高原则,而只有费孝通所说的“一根根私人联系所构成的网络”[15]47-48。
那么,原始儒家真的不追问各种“仁”的统一原则吗?在程颐的解释中显然不是这样,他说:“分殊之蔽,私胜而失仁;无分之罪,兼爱而无义。分立而推理一,以止私胜之流,仁之方也。无别而迷兼爱,至于无父之极,义之贼也。子比而同之,过矣。且谓言体而不及用。彼欲使人推而行之,本为用也,反谓不及,不亦异乎?”[21]
在这个意义上,儒家的“仁”既讨论“分殊”的特殊原则,也试图在特殊原则中推出“理一”。如果没有这个“一”,私人的偏好和利益就会占据上风。因此,儒家承认作为统一原则的“仁”的重要性,甚至将其称为“体”。这里的问题在于,程颐认为“理一”最后还是要落实到实践上,无法实现的统一原则也就没有意义了。正是为了将“仁”的对象扩展到每个人,儒家才向特殊原则妥协。这个观点正好可以反驳赵汀阳的批评,即儒家的“行”并未解构“言”,统一的普遍原则依然存在,它只是在实践层面“分殊”了。程颐从“体”“用”兼顾的角度来阐释“仁”,而朱熹认为,若不以“分殊”为起点,人根本无从认识“理一”,即:“圣人未尝言理一,多只言分殊。盖能于分殊中事事物物,头头项项,理会得其当然,然后方知理本一贯。不知万殊各有一理,而徒言理一,不知理一在何处。”[22]
进而,不管是在实践还是认识上,“理一”和“分殊”都是一体的。对照形而上学的“普遍性”结构,儒家实际上既讨论“普遍性”,也讨论“特殊性”。只是这两个概念在儒家中并不是对立的,它们被安排在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中,并根据其不同的作用获得了各自不可或缺的价值。
在前存在论的语境中,起源问题解释了原始儒家和形而上学“普遍性”概念的第一个差异,而“分殊”和“理一”的优先性问题则构成了第二个差异。儒家的“仁”中存在“理一”,这个“一”可以被称为统一的原则,因为它和所有“分殊”的原则都产生了联系。但是,儒家的“理一”并不是最高的原则。至少在实践的层面上,它必须依靠“分殊”才能成为惠及人人的普遍伦理。西方形而上学的普遍原则却不同,它既是统一的也是最高的。
四、儒家的“普遍性”:作为人权论证的理论资源
在人权的“普遍性”论证上面,探索一种新的“普遍性”形式是一个尤为重要的任务。为了将不同文化传统的国家纳入国际人权社会,并避免任何从人身上剥夺“权利”的理论可能性,《世界人权宣言》的起草者们特意将西方的“自然权利”(natural rights)概念改成了“人的权利”(human rights)。这个改动得到了来自不同文化传统的代表们的支持——提出《世界人权宣言》哲学根据的《序言》一章和其他部分的文本相比较,引起的争议是最少的(11票支持,5票弃权)[23]。人权概念虽然摆脱了自然法的庞大理论体系,但也给自身的“普遍性”论证造成了一定的困难。
人权理论上的困难也造成了实践上的分歧。当前绝大多数国家都承认了《世界人权宣言》的正当性,但是在缺少成熟理论的背景下,各个国家对国际人权法的解释也就存在任意的可能。这并不是说只有一种解释或几种解释是正确的,问题的关键在于找到一种“普遍性”的理论,来说明人权法的解释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允许多元的差异,以及法律约束力的强弱。例如,为了阻止国际社会中侵犯人权的政治行动,在什么条件下可以采取武力干涉的方法?如果没有一种有效的“普遍性”理论,就无法确定人权政治实践本身的正当性在哪里*在这个问题上,杰克·唐纳利(Jack Donnelly)为了避免一种霸权主义的“普遍性”,借用了罗尔斯的“重叠共识”概念作为普遍人权的根据。参见Jack Donnelly, “The Relative Universality of Human Rights”, Human Rights Quarterly, Volume 29, Number 2, 2007, p.282.。
国际社会在论证人权的“普遍性”时,需要考虑这种“普遍性”是否能够包容不同的文化传统,在求同存异中创造一种普遍的国际规范。在这个意义上,原始儒家“仁”的概念在前存在论上的特征就有助于设想一种包容性的普遍规范。随着更多国家承认《世界人权宣言》的正当性,人权概念的建构需要非西方的文化传统共同参与。然而,正如西方形而上学传统下的“自然权利”论证不能强加给人权概念,儒家的“普遍性”进路也只能作为新规范建构的理论资源,而并不能直接进入正当性论证。换而言之,儒家“仁”的概念之所以有助于人权的“普遍性”论证,不是因为它是圣人之言,而在于它更加适合多元化的国际人权社会。
一方面,“仁”的生成性特征打破了原来“普遍性”与“特殊性”对立的框架,使非西方社会中的个人伦理可以成为普遍人权实践的起点。个人伦理最初并不遵循一个普遍平等的原则,比如儒家就主张“等差之爱”,根据关系的亲疏远近来差别地对待他人。进而,在“等差之爱”的基础上,“仁”的原则也可以逐渐外推到和自己较疏远、甚至无关系的人。在儒家看来,主张“等差之爱”的原因是“仁”需要一个能够生成的动力。在实践中,作为普遍原则的“仁”不是一开始就存在的,而形而上学传统下的“普遍性”则要求人在处理任何特殊情况的时候,先就考虑到处理方法是否符合普遍规范。简而言之,这两种“普遍性”进路的目标在宽泛意义上是相同的,都是为了将“爱人”的行动施与每个人,而达到这一目标的途径则不同。在非儒家传统的社会中,以“等差之爱”为原则的个人伦理也许并不能作为普遍规范生成的动力。但是,儒家“仁”的生成性特征至少可以说明,普遍人权的实践能够依靠地方性的特殊经验来完成。在一开始就将人权概念的“普遍性”凌驾于不同传统下的社会中,人们实际上不能有效地实践人权。
另一方面,在多元化的国际人权社会中,各个国家在价值优先性问题上存在分歧。在最高价值规范无法形成的情况下,儒家的“普遍性”进路提供了一种可能,使各个国家依然可以分享同一个普遍人权规范。儒家的“理一”和“分殊”之间并不是支配与被支配间的关系,它们在不同的层面发挥着不同的作用。“理一”是“仁”统一性的体现,它意味着“仁”实践的对象包括了每个人,而“分殊”是“仁”在具体情境中能够被实践的差别化方法。在这个意义上,原始儒家“仁”的“普遍性”在于它是一个统一的原则,而不是最高的原则。国际共同体由来自不同宗教、文化背景的社会组成,这些社会在存在论上也持有不同的观念。按照形而上学的“普遍性”进路,“普遍性”必须超越一切“特殊性”的原则,这就要求所有的社会都被改造成同一的。比较而言,孔子在人性与天道上的立场也是儒家在存在论上的态度,即绕过什么是最高存在者的问题之后,普遍伦理依然是可能的。
由于原始儒家的“普遍性”并不设立一个最高的存在者,也不试图将所有的“特殊性”都改造成“普遍性”,这种立场就仅能支持一种弱的普遍人权概念。从这个角度来看,儒家实际上无法解决价值的优先性问题。比如,个人权利是否优先于共同体的权利?权利概念是否优先于传统中“善”的概念?只有澄清了什么是存在论上的最高存在者,上述问题才能在理论上得到解决。所以,儒家的包容性在本质上反对一种革命式的普遍人权——这种观念将人权的普遍实践放置在了价值序列的顶端,并且试图为达成这一任务的任何手段进行辩护。
参考文献:
[1] TU W M. A Confucian perspective on human rights[G]//WONG S K. Confucianism, Chinese history and society. Singapore: World Scientific Publishing Co. Pte. Ltd., 2012: 15.
[2] WILLIAMS C.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and Confucianism[J]. Asia pacific journal on human rights and the law, 2006, 7(1): 38-66.
[3] 论语[M].张燕婴,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06.
[4] CHAN J. A Confucian perspective on human rights for contemporary China[G]//BAUER J R , BELL D A. The east Asian challenge for human rights.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226-227.
[5] TIWALD J. Confucianism and human rights[G]//CUSHMAN T. Handbooks of human rights. Abingdon: Routledge, 2012:250.
[6] 孟子[M].万丽华,蓝旭,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06.
[7] MUNRO D J. The concept of man in early China[M].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9: 12.
[8] 徐复观.儒家思想与现代社会[M].北京:九州出版社,2014:143-146.
[9] TAN S. Why equality and which inequalities?: a modern Confucian approach to democracy[J]. Philosophy east and west, 2016, 66(2): 488-514.
[10] DONNELLY J. The relative universality of human rights[J]. Human rights quarterly, 2007, 29(2): 281-306.
[11] PERRY M J. The idea of human rights: four inquiries[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29.
[12] 牟宗三.政道与治道[M].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87:12.
[13] 牟宗三.人文讲习录[M].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0:151-158.
[14] 牟宗三.中国哲学十九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28-33.
[15] 费孝通.乡土中国[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16] 赵汀阳.身与身外:儒家的一个未决问题[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7(1):15-21.
[17] 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M].陈嘉映,王庆节,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5.
[18] 海德格尔.海德格尔选集[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6:164.
[19] ZHANG X L. Is political Confucianism a universalism?an analysis of Jiang Qing’s philosophical tendency[G]//FAN R P. The renaissance of Confucianism in contemporary China. Dordrecht: Springer, 2011: 237.
[20] 王阳明.传习录全鉴[M].2版.北京:中国纺织出版社,2014:80.
[21] 程颢,程颐.二程集:第2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1:609.
[22] 黎靖德.朱子语类:第2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8:677-678.
[23] MORSINK J. Inherent human rights: philosophical roots of the universal declaration[M].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2009: 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