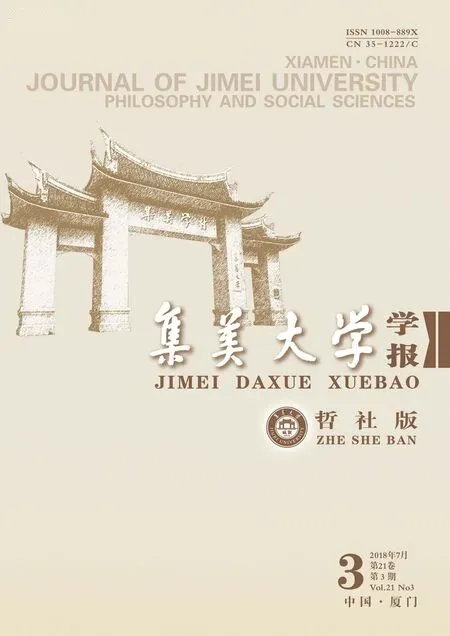罗钦顺对朱熹理气观的误解
赵 玫
(西北民族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甘肃 兰州 730000)
罗钦顺(号整庵)被称为“朱学后劲”,但在理气关系上提出与朱子“小有未合”[1]7。这是对朱子的立论缺陷的敏睿洞见,还是对朱子圆融理气观的误解,是一个亟需澄清的问题。针对这一问题,长久以来存在两种互不相容的主张。一种以刘嶯山、黄梨洲为代表,认为整庵的质疑是对朱子理气关系的超越;另一种以清儒陆桴亭、李光地为代表,认为整庵对朱子理气关系理解未透而生出误解*刘嶯山、黄梨洲代表的“超越说”,陆桴亭、李光地代表的“误解说”,其具体观点见本文第四小节(结论部分)。。和刘、黄相似,当前学界的主流看法认为,整庵修正了朱子的理气关系*冯友兰先生认为朱子确然有将理气分离之论,因而,整庵的就气认理(“事在理中”)的主张是对朱子学说的改造。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85-289页。阎韬先生提出整庵理气一元是对朱子理气二元说的纠正。阎韬:《罗钦顺的哲学思想》,《困知记全译·代序》,成都:巴蜀书社,2000年版,第8-13页。邓克铭先生提出整庵理气观是对朱子的“补充”或“修正”。邓克铭:《罗钦顺“理气为一物”说之理论效果》,《汉学研究》,2001年第2期,第33-57页。。这是需要反思的。
一、朱子理气关系的两个面向
整庵言:
所谓朱子小有未合者,盖其言有云:“理与气决是二物。”又云:“气强理弱。”又云:“若无此气,则此理如何顿放?”似此类颇多。惟《答柯国材》一书有云:“一阴一阳,往来不息,即是道之全体。”此语最为直截,深有合于程伯子之言,然不多见,不知竟以何者为定论也。[1]7
在整庵看来,朱子理气观存在矛盾。因朱子“理与气决是二物”“气强理弱”“若无此气,则此理如何顿放?”一类的言说,有析分理气为二物的嫌疑,这和“一阴一阳往来不息,即是道之全体”的圆融表达完全不同。显然,整庵对朱子类似于大程子的论说是极认可的。
朱子理气观存在矛盾么?朱子理气观的形成可以追溯到对周子《太极图说》的阐释。《太极图说》言:“无极而太极。”朱子作了两层划分,此理在天而言无形象方体可求,故曰“无极”;然而此理同时又作为造化之枢纽,品汇之根柢,是万物生化之源,故曰“太极”。所以,“无极而太极”并非是说无极生太极,“非太极之外,复有无极也”[2]4,二者强调理的两方面性质。
一方面,“无极”表明理无形象方体可求,有别于世间可闻见之物,其在空间上无广延,在时间上无持续,说明其不具经验物的特征,是形而上者。另一方面,凡物皆可以推寻一个肇始者,推到“太极”这里已经是极致,说明“太极”是万事万物的形而上的终极根据。既然理并非为经验存在物,是物之所以为物的依据。那么,在与物的关系上,理并非是被物承载起来的一个实体,但同时,理作为形而上者,它作为物的根据并通过物来呈现。
综上,从形上、形下关系来看,理并非为有别于气而存在的实体,理先于气,故朱子说:“理未尝离乎气。然理形而上者,气形而下者。自形而上下言,岂无先后!”[3]3又从二者的存在方式来看,理是气的根据,气为理的显像,理不离气。所以朱子称:“太极非是别为一物,即阴阳而在阴阳,即五行而在五行,即万物而在万物,只是一个理而已。因其极至,故名曰太极。”[3]2371
总之,朱子是从两方面来强调理与气的关系。一方面,正因为“太极”是万物之形上根据,所以“太极”便成为超越于气者。另一方面,理非别于万物而存在的实体,凡有物处必有理,理气不可分离。
朱子所言之 “气强理弱”“若无此气,则此理如何顿放”“理与气决是二物”一类说法,皆偏重于上述理气关系的第一个面向,强调理作为形而上者的优先地位。具体而言,与形而下之气对待的形而上之理,不仅具有主宰义,亦具有究竟义。整庵未能恰当地理解这一点,导致对朱子有疑。
二、对“气强理弱”说的怀疑:误解了理的主宰义
整庵言:
尝考朱子之言有云,“气强理弱”,“理管摄他不得”。若然,则所谓太极者,又安能为造化之枢纽,品物之根柢耶?惜乎!当时未有以此说叩之者。姑记于此,以俟后世之朱子云。[1]38
整庵认为,若如朱子所说 “气强理弱”“理管摄他不得”,则否定了理具有的“枢纽”“根柢”之地位。整庵有此疑问,在于他未能理会太极之为“造化之枢纽,品物之根柢”的意思,即没有理解理之主宰义。
朱子论理为万化的根源与枢纽,不是说万化之生成受理之宰制,也不是说万物皆按照理的理想生成创造,而是说万化不出乎理之范围。朱子言:
盖气则能凝结造作,理却无情意,无计度,无造作。只此气凝聚处,理便在其中。且如天地间人物草木禽兽,其生也,莫不有种,定不会无种子白地生出一个物事,这个都是气。若理,则只是个净洁空阔底世界,无形迹,他却不会造作;气则能酝酿凝聚生物也。但有此气,则理便在其中。[3]3
在朱子看来,理只是形而上的洁净空间,无形象方体可求,然凡有气处必有其理,凝结造作者是为气,气之所以能凝结造作则由乎理。正如周子所说的“无极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一句,“妙合”是指“无极”与“二五”的混融无间的状态,而非指二者是各自存在的两物。“妙合”方才有“凝”,“凝”是指“二气”与“五行”之凝聚而成形,“无极”是所以能“凝”的前提和依据。
朱子曰:“有理,便有气流行,发育万物。”弟子问:“发育是理发育之否?”朱子答曰:“有此理,便有此气流行发育。理无形体。”[3]1可知,气由于有理,则能发育万物,然直谓理能发育则不可,故对于“发育是理发育之否”的问题,朱子并未回答“是”,而是强调了所以能发育者是理,而流行发育处是气,无形之理只是乘气。反过来也说明了气能凝聚生物,而理却不能如此。
基于此,可以推出气强理弱的意思。“气虽是理之所生,然既生出,则理管他不得。如这理寓于气了,日用间运用都由这个气。只是气强理弱”[3]71。理生气,并非指理能“发育”而生出气,而是指理为气的所以然者。理不但不能“发育”而生出气,并且也不能左右气的生成变化。按钱穆先生的话说,理对于气的作用并非“理想的”,而是“消极性的”(或称为“自然的”)[4]36。这说明,理对气的“主宰”,是作为无为自然的存在者,是气生成、变化的所以然依据。
这一点也可以从万物成形之后的两个方面来理解:首先,性在心中,心能检其性,而性不能检其心,所以《论语·卫灵公》载有孔子语:“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也就是说,在心上可做工夫,工夫非在性;其次,虽然心乃气之精爽,但此心只是气,故而有清浊轻重厚薄,接物应事时可能失去如明镜般鉴照功能,就此处而言,心会对性有所妨碍。因此,朱子讲心性,认为心可能会对人有遮蔽与妨碍,同时,人心亦能实现自作主宰,而有所作为。合此两面,心能积极作用,性则消极范围,亦可曰“气强理弱”。
通过以上论述可知,朱子所言之理并非能安排、管辖事物,并非能动地、积极地生物造物,而是作为所以然者,让气在其范围内活动。所以朱子之理并非作为造物者,让世间万象完美无瑕,因为理若具备如此功能,则世间所有尽成了最好的物事。朱子对理的解释,强调了理作为形而上的“主宰者”的真正意义:是至极、根据、所以然者,而非经验意义上的生成者与造物者,因此,朱子的理并非经验物,也不是有别于气而在的“实体”。
对“造化之枢纽,品物之根柢”一句,唐君毅先生曾解释到:“言其为根柢,乃谓其为至极义说;言其为枢纽,则亦兼自其为在造化之中,而主乎造化说。”[5]426唐先生此意甚明,说太极之为“根柢”,就是推求而至其极,其上别无他物,而并非说太极如造物主般生化万物;说太极之为“枢纽”,是说太极在气之造化之中,而为所以能造化者。所以“造化之枢纽,品物之根柢”一句并非是说太极生物造物。生物造物者是气,所以生物造物者是理。
整庵与林贞孚讨论这个问题,林贞孚给出了较合理的解释,整庵却不以为然。整庵言:
谓“造化枢纽”、“品物根柢”指本原处而言,亦过于迁就矣。岂有太极在本原处便能管摄,到得末流处遂不能管摄邪?是何道理?其以形体性情、君子小人、治乱祸福,证“气强理弱”之说,皆未为当。[1]《答林正郎贞孚(乙亥秋)》,187
林贞孚写给整庵的原信已无从考证,从整庵的回信中可知,林认为“造化枢纽”“品物根柢”是就“本原处”而言,而“气强理弱”是在万物成形之后说,故有“形体性情、君子小人、治乱祸福”等论证。推想林贞孚之论证,大致为:心能遮蔽性之发露,亦能反观自省,这是“形体性情”之证;众人同禀一理,然气却有清明昏浊差异,理不胜气,固有君子小人之别,这是“君子小人”之证;众人所禀之命各有不同*在儒家经典中,命有两义:1.人物生于形气分别,如上智下愚、品节高下、贫贱富贵、死生夭寿之命。2.天命。在天为命,在人为性,在物为理。此处所言为第一义。,所以治乱祸福不一,这是“治乱祸福”之证。
林贞孚对“末流处”“气强理弱”之论证可谓恰当,但并不充分。要应对整庵对“气强理弱”的怀疑,关键在于证明理作为“造化枢纽”“品物根柢”,就本原处与在万物成形之后而言,管摄皆非安排的。理在本原处与末流处皆同样要为气之范围,皆可说“气强理弱”。然林贞孚似并未完全见到这一点。
总之,朱子所说的理不积极造作,却消极自然,理为气之“主宰者”,其意并非是指理操纵驾驭气,而使其按照理的规定而活动。整庵不解此,故对朱子的理气关系存在误解。
三、对“理与气是二物”诸说的怀疑:误解了理的究竟义
整庵认为朱子有将理气视作各在的两物的嫌疑。由此,他对天命与气质之性的划分、“气同而理异,理同而气异”、“理与气决是二物”等言说皆产生怀疑。
整庵尝言:“然一性而两名,虽曰‘二之则不是’,而一之又未能也。”[1]又言:
一性而两名,且以气质与天命对言,语终未莹。朱子尤恐人视之为二物也,乃曰:“气质之性,即太极全体堕在气质之中。”夫既以堕言,理气不容无罅缝矣。惟以理一分殊蔽之,自无往而不通,而所谓“天下无性外之物”,岂不亶其然乎![1]10
可知,整庵认为 “气质之性”与“天命之性”有分理与气,分天命与气质为二物之嫌,不如“理一分殊”说得好。
整庵并非没有理解天命之性与气质之性划分的必要,因为整庵也认可林贞孚“理一即本然之性,分殊即气质之性”[1]《答林正郎贞孚(乙亥秋)》,183的说法,他只是认为用“理一分殊”言性较易于体认,而用气质与天命来说则“疑其词之未莹也”。[1]《答林正郎贞孚(乙亥秋)》,183至于整庵之“夫既以堕言,理气不容无罅缝矣”的怀疑便是多余的,朱子讲形而上之理优先于形而下之气,二者在未妙合之前并非相离各在,以“堕”言,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比喻,强调的是理之全体在气中,并无别于气而存在的意思。
在朱子看来,天命之性与气质之性并非指天地间有两性,就未有天地之前而言(并非在时间上存在“未有天地之前”与“已成天地之后”,而是思辨地抽出形而上的理来讨论),此理并无沾染气质,为纯粹无伪之存在,故名之为“天命之性”;在万物成形之后(即理作为形而上者不离形而下者而存在),一理分散于各物当中,各物所含有虽同为一理,然因气质有清浊厚薄之差别而表现各有分殊,如物有蔽塞而无所知,人能通理而无所碍,就人而言又有偏于仁者、偏于义者等。所以当朱子在回答有人提出《中庸》“天命之谓性”是极本穷源之性还是气质之性时说:
性也只是一般,天之所命,何尝有异?正缘气质不同,便有不相似处,故孔子谓之“相近”。孟子恐人谓性原来不相似,遂于气质内挑出天之所命者说与人,道性无有不善,即子思所谓“天命之谓性”也。[3]69
子思所言“天命之谓性”,孟子所言“性善”,便是极本穷源之性,是从根本上言性,是为究竟处。孔子“性相近”,与小程子 “气质之性”是就人物界而言性。虽然两处对性的言说不同,由理一分殊之旨可知,二者无非一理,天命之性强调根据义,气质之性则是即物而言理,是与物不离之理。故朱子有言:“论天地之性,则专指理言;论气质之性,则以理与气杂而言之。”[3]67
朱子常用理一分殊表明理气关系。有人问理气关系,朱子言:“伊川说得好,曰:‘理一分殊’。合天地万物而言,只是一个理;及在人,则又各自有一个理。”[3]2在未有天地万物之前,只是一理;在既有天地万物之后,此理殊散于各物当中,物物各具一完整的理,万物虽各有不同,而所含之理其实为一。
朱子以上表达都是相通的,而无论从哪一种表达来看,都能理解理气关系的两个方面:究竟意义上的理先于气,在人物而言的理与气不二。“天命之性”就是指天所赋予万物者,即,未有天地之前的“理一”,理虽然不外乎气而存在,然“天命之性”“理一”都是在究竟意义上来说,在此种意义上,必须强调理在气先。“气质之性”是见得天之所赋予人者与万物浑然一体,表现为既有天地以后的“分殊”,所以在人物而言理,当然会说理气不二。通过以上论述,可见整庵未能完全理解朱子究竟意义上理先于气的内涵。
整庵又对朱子“理同而气异”“气同而理异”的说法有疑。整庵言:
“理同而气异”,“气同而理异”,此两说质之《大传》“形而上下”之言,终觉有碍。必须讲究归一,方得触处洞然。[1]139
朱子《答黄商伯书》有云:“论万物之一原,则理同而气异;观万物之异体,则气犹相近,而理绝不同。”[3]57朱子认为在天地万物成形之初,天命之流行无非一理,故虽有二气五行之别,然理则为一,由此而言“理同而气异”;在天地万物成形之后物物各得此理,万物之所以成乃由于二气五行妙合而凝,故气相似,然而理殊散到万物之中而被万物之形气所蔽,故所彰显之理各有不同,由此而言“气同而理异”。
“理同而气异”是就极本穷源之性上来说,物物各有不同,然而其理为一,朱子用碗盛水作比喻:“人物性本同,只气禀异。如水无有不清,倾放白碗中是一般色,及放黑碗中又是一般色,放青碗中又是一般色。”[3]57极本穷源之性犹如水,万物之别犹如各色的碗,水本无不同,然置于不同颜色的碗中,便可见到气质之性的不同。气质之性各有不同,然天地万物创生之初,只是二气五行交感,凝结生聚,万物之形皆由乎此二气五行,故气相近。朱子之解无非为其理气观两方面的内容,整庵有疑恰证明其理解有差。
对“理气决是二物”的怀疑,整庵表达到:
朱子《辩苏黄门〈老子解〉》有云:“道器之名虽异,然其实一物也,故曰‘吾道一以贯之’。”与所云“理气决是二物”者,又不同矣。为其学者,不求所以归于至一,可乎?[1]31
整庵认为,朱子“理气决是二物”的表述与道器“其实一物”的表述有冲突。这也是整庵对朱子理气观两个方面的理解不到位的表现。
朱子《答刘叔文》第一书言:
所谓理与气,此决是二物。但在物上看,则二物浑沦,不可分开各在一处,然不害二物之各为一物也;若在理上看,则虽未有物而已有物之理,然亦但有其理而已,未尝实有是物也。[6]2146
理气并非为各在的两物,二物浑沦不可分;但就形而上下而言,理先于气。后一个意思就是“理气决是二物”的涵义。整庵之前的种种疑问,都由于对朱子理先于气的观点没能恰如其分地理解。
通过分析整庵所理解到朱子之言论,可知,整庵在对朱子理气关系不离不杂两方面的理解上,对“不杂”的理解,多有厥误。陆桴亭总评整庵对小程子、朱子质疑,认为整庵“见犹有未到”,原因在于他对朱子的理“不离乎阴阳,亦不杂乎阴阳”的观点,只看重“不离”的一方面,而对“不杂”的一方面存在误解,所以说:“整庵疑,是知其一、不知其二也。”[7]卷二十三,203桴亭此说是为卓见。
综上,朱子所谓理先于气,是强调理作为形而上者,有究竟、本体、根据的意义,是为极本穷源之性,这并非将理看作别于气而存在的实体。因此,理先于气同时不妨碍从事实层面上的理气不相离。整庵并未理解朱子对理的究竟义的强调,遂质疑朱子,这是他的不足处。
四、整庵在理气观上并非“超越”了朱子
整庵之理气关系,不出于朱子之囿,他对朱子“小有未合”而质疑的言论,实为其见理未透。他过分强调朱子理气不二,而对朱子的理先于气的一些表达未能恰如其分地理解。他误解了朱子语境中理的主宰义与究竟义,从而对朱子“气强理弱”“理气决是二物”诸说存疑。
基于此,需要重新审视以刘宗周、黄梨洲二人为代表的“超越”说。不可忽视的是,这基于对朱学的反对立场,从而导致二人或断章取义,或以“偏”概全,对整庵理气关系的评价有失公允。
黄梨洲学宗刘蕺山,蕺山著有《皇明道统录》,梨洲将此书部分内容节选,编订入《明儒学案》并列于卷首,名为《师说》。蕺山对整庵评价到:“先生既不与宋儒天命、气质之说,而蔽以‘理一分殊’之一言,谓‘理即是气之理’,是矣。”[8]10可见,蕺山首肯整庵“理即是气之理”之说,认为这就是整庵对程朱“天命”“气质”之性的更定,而作出的“理气是一”的表达。然而,“理即是气之理”一句出自于整庵《困知记·续卷上》第三十八章,此章结论部分明言:“愚故尝曰:‘理须就气上认取,然认气为理便不是。’此言殆不可易哉!”[1]89整庵意思明确:一方面理不离气,但理气从形而上下上来看,决是二物,“理即是气之理”强调即气而言理。此章大体上和程朱理气观无出入。由此可见,蕺山为整庵所撰《学案》存在明显的断章取义的嫌疑。后人不辨此间用心,便肯定蕺山的评价,这是有问题的。
黄梨洲言“盖先生之论理气之言最为精确”,[8]卷四十七,1107并引整庵《困知记·卷上》第十一章(即“气本一也”一条),然后评述到:“斯言也,即朱子所谓‘理与气是二物’、‘理弱气强’诸论,可以不辩而自明矣。”[8]卷四十七,1107可知,梨洲奉整庵理气观为至论,并认为由此可以对朱子的“理与气是二物”“气强理弱”提出批评。梨洲在《学案》对整庵的评述中,独引此章以表整庵理气关系之全体,一方面,不解此章和朱子从流行的意义上说理气不离的观点一致,因此并未看到整庵理气关系不出于朱子之囿;另一方面,没能理解朱子“理与气二物”“理弱气强”诸论只是强调理作为形而上者的根据地位,遂认为朱子理气关系之失误乃“不辩而自明”。梨洲的做法,一方面有以“偏”概全的嫌疑,另一方面以整庵之言对朱子提出总体性批评,这显得过于轻率。
与“超越”说截然相反,清儒陆桴亭、李光地认为整庵误解了朱子的理气观。陆桴亭认为:
整庵与朱子未达一间处只是心性、理气,然心性犹可通,若理气则自不识理先气后之旨,而反以朱子为犹隔一膜,是整庵欠聪明处也。[7]卷三十一,289
整庵不识朱子理气关系可合而观亦可离而观,遂以为朱子理先于气有分理气为二物之嫌疑。所以,整庵之学并非为朱子学的歧出或超越,只是对朱子理解未透而已。李光地也认为:
先有理而后有气,有明一代虽极纯儒,亦不明此理……罗整庵谓理即气之转折处,如春转到夏,夏转到秋,自古及今何尝有一毫差错,此便是理……至五十一岁后忽悟得三说之差(笔者注:“三说”指李光地文中提到的蔡虚斋、罗整庵、薛文清之说),总是理先气后不分明耳。[9]卷二十六,396
这说明,整庵正是未明白理先气后之旨,才对朱子有疑。
综上所述,反观长久以来整庵的理气观与朱子关系的争论,我们认为,以黄梨洲、刘宗周为代表的“超越”说,对当前学界的主流看法有至深影响,却是应当反思的;而陆桴亭、李光地为代表的“误解”说,对此问题的深刻洞见,当引起足够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