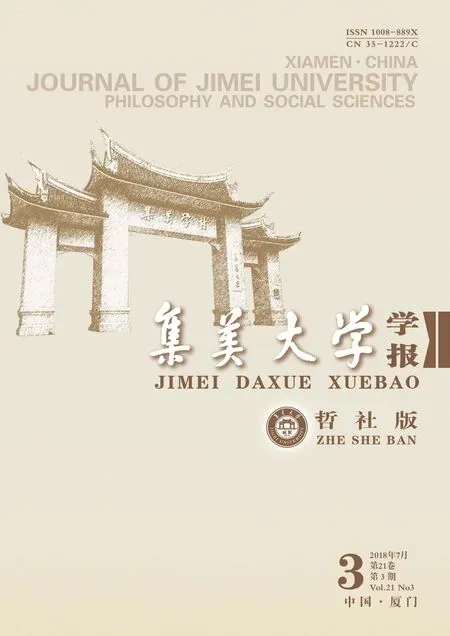理学的发生:一个天人学视域的分析
张 恒
(山东大学 儒学高等研究院,山东 济南 250100)
一、引 言
作为中国儒学发展史乃至中华文化生命的重要一期*关于儒学分期,学界有不同观点。如牟宗三持“三期说”,认为“宋明理学是儒家学术发展的第二个阶段”。牟宗三:《政道与治道》,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87年版,第9页;李泽厚持“四期说”,认为宋明理学是以“心性论”为主题的第三期儒学。李泽厚:《历史本体论·己卯五说》,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154页;黄玉顺则提出了原创、转进、再创“新三期说”,认为宋明理学是儒学第二期转进时代的第二阶段。黄玉顺:《儒学当代复兴的思想视域问题——“儒学三期”新论》,《周易研究》,2008年第1期,第51-58页。不管以何种方式分期,宋明理学都毫无疑问是儒学发展史上的重要阶段。,宋明理学*“理学”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理学”主要指程朱学派,广义的“理学”则涵盖开创于北宋五子、鼎盛于程朱学派、转折于陆王学派等的整个学术思潮。本文取后一种含义。以高度思辨的哲学形态和融会儒、释、道三家的文化形态,开启了中国思想新的范式。20世纪以来,理学的发生问题越来越受学界重视,各个学科的学者从不同角度作出了多样化的探索和诠释。
从哲学角度说,探讨理学的发生问题,实际上就是探讨理学“制造者”的哲学问题意识。冯友兰曾指出:“如果担水砍柴,就是妙道,为什么‘事父事君’就不是妙道……禅师们自己,没有做出这个合乎逻辑的回答。这只有留待新儒家来做了。”[1]216从这一问题意识出发,“新儒家建立了一个观点,从这个观点看来,原先儒家评定为道德的行为,都获得更高的价值,即超道德的价值”[1]226。由此,冯友兰认为新儒家是禅宗进一步的发展,具有超越意义的儒家伦理极类似于“柏拉图式理念”(platonic ideas),这是典型的存在论(ontology)视域。
嗣后牟宗三提出“道德的形而上学”概念。他认为理学的产生不仅与佛老无关,也与秦汉至隋唐间的儒家无关,宋明儒的主要课题是“豁醒先秦儒家之‘成德之教’”,“说明吾人之自觉的道德实践所以可能之超越的根据”[2]34。
李泽厚也曾指出,佛教“既要追求空寂,又不能舍弃血肉之躯;既以为一切皆空,又仍须穿衣吃饭,仍要维持包括自身(身体、生命)和环境(自然、人世)在内的感性世界的物质性的存在,这不是矛盾吗?宋儒的‘心性之学’实际进行的本是这种常识批判”。[3]225在他看来,理学的主题是“重建以人的伦常秩序为本体轴心的孔孟之道”。[3]224近些年的相关研究也大都属于这一思路,即认为理学是儒学为回应佛教而另起炉灶建构以伦理为本体的存在论。
以往关于理学发生问题的研究各有道理,但有两点值得商榷:其一,以存在论为框架的解读视伦理为“本体”,实际上宋儒所谓“理”并不完全同于西学所谓“本体”;其二,无论是牟宗三认为理学的发生与佛老无关、与秦汉至隋唐间儒家无关,还是其他学者认为理学的发生单单是受了佛教的刺激,都不符合思想史逻辑发展的事实,他们普遍忽视了魏晋时期哲学家尤其是王弼、阮籍、嵇康、郭象等人的哲学贡献。而以上认识偏颇之所以出现,主要是因为中国哲学一个独特而重要的视域——天人学被忽视或矮化。在天人学视域下,上述偏颇将不复存在。
二、天人合一:“宋承魏晋”新说
“天人合一”*本文认为,“天人合一”和“天人一体”观念含义相同,只是不同时期在表述上略有差别。是中国传统哲学独特而重要的视域。北宋张载首次明确表述了“天人合一”这一命题,宋明理学家群体也普遍持有“天人合一”观念,有鉴于此,当前学界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天人合一”观念正式形成于宋代。实际上,宋儒的“天人合一”观是承续魏晋学者“接着讲”的。对这一问题的辨明是从天人学视角理解理学发生问题的重要前提。
(一)宋代“天人合一”观及争议
作为中国传统哲学独特而重要的视域,“天人合一”观念为理学家普遍持有,在宋明时期广泛流行,这已是学界共识。如北宋张载曾说:“儒者则因明致诚,因诚致明,故天人合一。”[4]56这是有历史记载的首次对“天人合一”命题的明确表述。张载还曾说:“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4]53以天地之塞为体、以天地之帅为性、民胞物与,这些对“天人合一”观念的阐释形象而又生动。
与张载同时代的邵雍亦曾说:“学不际天人,不足谓之学。”[5]156“事无巨细,皆有天人之理。”[5]174这显然都是对贯通天人的强调。被尊为“理学开山”的周敦颐虽然没有明确的“天人合一”相关表述,但是他通过《太极图说》阐述的宇宙化生图式也隐含着“天人合一”观念。
嗣后程朱和陆王两大学派均深化了“天人合一”观念。如二程曾说:“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莫非我也。”[6]1179“仁者,浑然与物同体。”[6]16朱熹曾说:“盖天地万物本吾一体,吾之心正,则天地之心亦正矣,吾之气顺,则天地之气亦顺矣。”[7]18陆九渊曾说“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8]273,明代王阳明亦曾说“天地万物,本吾一体者也”[9]89,“天地万物与人原是一体”[9]122,等等。
基于理学家群体对“天人合一”观念的普遍接受以及张载对“天人合一”命题的首次表述,当前学界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天人合一”观念正式形成于宋代。
除此之外,还有观点认为“天人合一”观念形成于汉代,其文献依据是董仲舒所说的“以类合之,天人一也”[10]249,“天人之际,合而为一”[10]208。还有观点认为“天人合一”观念形成于先秦,如张岱年曾提出:“天人合一的思想起源于先秦时代,而这个成语则出现较晚。”[11]汤一介认为:“根据现在我们能见到的资料,也许《郭店楚简·语丛一》:‘易,所以会天道、人道也’,是最早最明确的‘天人合一’思想的表述。”[12]张世英亦曾表示:“‘天人合一’的思想在西周的天命观中已有了比较明显的萌芽。周公提出的‘以德配天’,更是‘天人合一’思想的明确表达。”[13]
(二)“天人合一”观念源流新考
对“天人合一”观念源流的相关争议的辨明极有赖于一个前提,即“天人合一”这一命题含义的界定,如若没有含义界定,各种争议只能是自说自话。本文认为,“天人合一”之“天”主要应指涵摄天、地、万物的“自然之天”*冯友兰曾对中国古代“天”概念作了五种意义区分:物质之天、主宰之天、运命之天、自然之天和义理之天。本文认为,上述区分实可进一步归纳合并,最终落实为三个层面,即自然之天、天然之天和宗教之天。其中,自然之天主要是指整全的宇宙世界,天然之天主要是指人性的根据,宗教之天则主要是指一种宗教性的存在和主宰。,诚如邵雍所言“以天地观万物,则万物为万物,以道观天地,则天地亦为万物”[5]9之“观”法,天、地、万物当统一于同一视角下的同一世界,否则,一物阙如,以“天”为代表的宇宙便不够整全,不能臻至圆满。“天人合一”之“人”当然也不是指个体之人,而是指人类全体、人类社会、人类文明。“天人合一”即是整全的宇宙世界与人类世界的一体和统一。这种一体或统一并非机械性的,而是有机的,须臾不可分离。
以此为前提,尽管作为一种文字表述的“天人合一”由张载首先提出,且理学“制造者”普遍持“天人合一”观念,但作为一种思想观念的“天人合一”却并非形成于宋代,也非形成于汉代或先秦,而是形成于魏晋时期。
宋以前,天人关系已历经长期演变和发展。“绝地天通”往往被视为中国天人关系史上第一个重大转变。尽管“绝地天通”并非真实的历史事件,但却是真实的思想史事件,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观射父是春秋晚期人,亦即处在中国轴心时期的第二阶段;他所陈述的与其说是历史事实,不如说是他自己所身处其中的春秋时期的思想观念”[14]。也就是说,“绝地天通”实际上间接揭示了先秦尤其是春秋战国时期天人关系的总体趋向——天人相分(天、神与地、人相分)。这一点也反映在了当时的思想家身上,如孔子罕言性与天道,思孟学派以人性言天(天命),荀子学派也极力强调“天人之分”,这些对“天”的有意疏离和区隔都是为了摆脱“绝地天通”之前的“民神杂糅”状态,以彰显人文之精神。
至汉代,董仲舒对天人关系作出更加具体、深入的阐释,他说:“天、地、阴、阳、木、火、土、金、水九,与人而十者,天之数毕也。”[10]354冯友兰认为这句话中的第二个“天”指的是“宇宙”,因此董仲舒的意思是“宇宙由十种成分组成”[1]163。值得注意的是,董仲舒的这个“宇宙”并非无所不包,他说:“起于天,至于人而毕。毕之外谓之物……”[10]354也就是说,“物”是在上述十个元素之外的。因此,董仲舒创制的宇宙化生图式看似繁复,实则失之粗糙,因为在他那里并没有整全世界的观念。总的来说,董仲舒所谓“天人之际,合而为一”,一方面“天”并非整全世界,另一方面“合而为一”也只是“以类合之”,亦即“人有三百六十节,偶天之数也;形体骨肉,偶地之厚也”[10]265。这种形式上的“人副天数”,或可称为“天人相类”。事实上,董仲舒的真实意图是借“天人相类”提升人的地位:如果人是天的副本、摹本,人间的一切都能从天那里找到根据,那除了天,还有什么能比人更高贵呢?正如他所言:“人之超然万物之上,而最为天下贵也。人下长万物,上参天地。”[10]354
真正符合本文定义的“天人合一”观念实形成于更晚些时候的魏晋时期。
正始玄学首先展现出了一种“以一统多”的整体观念。王弼说:“万物万形,其归一也。”[15]117又说:“夫事有归,理有会。故得其归,事虽殷大,可以一名举;总其会,理虽博,可以至约穷也。譬犹以君御民,执一统众之道也。”[15]622“万物归一”“执一统众”这些观念都意味着王弼已经意识到,世界万物应该可以统一为一个整体。[16]
这种整体观念在竹林玄学代表人物身上同样显化。如嵇康说:“流俗难悟,逐物不还。至人远鉴,归之自然。万物为一,四海同宅。”[17]13-14阮籍说:“天地合其德,日月顺其光,自然一体,则万物经其常,入谓之幽,出谓之章,一气盛衰,变化而不伤。是以重阴雷电,非异出也;天地日月,非殊物也。故曰:自其异者视之,则肝胆楚越也;自其同者视之,则万物一体也。”[18]115“万物为一”“万物一体”这些观念的确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先秦道家的“齐物论”,但是,先秦道家如庄子更多是强调万物之间的无差等性,而竹林玄学更多是强调万物之间的有机统一性,即“万物”是涵盖了重阴雷电、天地日月的整全的自然世界。
至西晋玄学,对于整全世界的认识变得更加具体而明确,如郭象提出:“天地者,万物之总名也。天地以万物为体,而万物必以自然为正。自然者,不为而自然者也。”[19]11郭象也曾直接说“天者,万物之总名也”[19]26,“物无非天也。天也者,自然也”[19]126。以自然之天为“万物之总名”,也就是确立了以“天”为代称的整全世界的观念。而人与天是一体的:“同天人,均彼我,故外无与为欢,而嗒焉解体,若失其配匹。”[19]23
可见,作为一种观念的“天人合一”在魏晋时期就已经基本形成。但是,在随后的隋唐时期,这一观念不但没有引起广泛认同,反而是被不同程度拒斥的,这在某种程度上与佛道的盛行有关。在宋儒眼里,佛道的观念属于典型的“天人相分”。
后文将进一步指出,宋儒对“天人相分”观的批评和对“天人一体”观的接续,是与他们的哲学追求——对哲学之“本原”的追问——密切相关的。这种哲学追求必然要求答案的唯一性和终极性。于厌苦之佛教、求生之道教而言,这一追求或可在“天人相分”视域下完成,但于儒家而言,这样的课题在“天人相分”视域下是无论如何也完成不了的。
三、体用一源:宋代哲学的范式转换
上文已经指出,宋儒的“天人合一”观承续魏晋而来,这种承续背后实际隐藏着中国哲学史上一条更加深刻的主线——“本原论”的逻辑发展脉络。
哲学就是对“本原”的追问。本原(arche),一方面可以指经验的“存在之先”,如“宇宙发生论”(或“宇宙生成论”等,英语cosmology)即是这重意义上的本原论;另一方面,本原也可以指超验的“存在之先”,“存在论”(或“本体论”等,英语ontology)即是这重意义上本原论的典型。具体到中国哲学史,唐宋以前,本原论主要是对经验的“存在之先”的探索,或可称之为“本—末”思考范式(“本末论”);自唐宋开始,佛教启发中国哲学全面转向对超验的“存在之先”的追问,或可称之为“体—用”思考范式(“体用论”)。*沈顺福以宋明为界,将中国传统哲学划分为两个发展阶段,宋明之前的哲学为“本源论”,宋明之后的哲学为“体用论”。参见沈顺福:《本源论与传统儒家思维方式》,《河北学刊》,2017年第2期,第29-34页。本文亦受此启发。从某种意义上说,理学发生的实质正是宋儒对“天人合一”的宇宙生命体之“本原”的追问,这一追问因为思考范式的转换而具有了更强的思辨意味。
(一)“本—末”思维及其理论困境
“性”观念的出现是先民对本原进行理性探寻的第一个里程碑。据徐复观考证,作为由“生”孳乳而来的文字,“性”早在周初就已出现,至春秋时期开始被较多地使用,但是此时“性”字含义不一,有的是“生”字的假借;有的可作欲望、本能解释;还有的可作本性、本质解释;最后一种含义的出现意味着当时的人们“开始不能满意于平列的各种现象间的关系,而要进一步去追寻现象里面的性质”[20]54。“现象里面的性质”也就是现象之本原。换言之,先民从此开始了对本原的探寻。不过早期的探寻多从经验角度出发,属于思辨程度较低的“本-末”思考范式。
孔子极少言“性”,其殁后最有影响的儒家学派之一——思孟学派开始以“天命”言“人性”,所谓“天命之谓性”。孟子以“心”释“性”,由“心善”推导出“性善”,人只要“尽心”便可“知性”进而“知天”。也就是说,主体的道德修养只需存心养性、扩而充之。这实际上是将人类生存之本归结为人生而即有的道德天性。
荀子不同意孟子的“性善论”,提出“性恶论”,但他同时也提出,人与牛马等牲畜禽兽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区别,即“人能群,彼不能群也”[21]98。“能群”也就是能进行共同而有序的生活,正是通过“群”,也就是在后天的道德实践中,人为之“善”得以形成。荀子说:“君者,善群也。群道当则万物皆得其宜,六畜皆得其长,群生皆得其命。”[21]98这实际上是把王道教化作为人类生存之本。
相比思孟学派和荀子学派,《易传》学派*关于《易传》的成书年代及学派属性,自古以来众说纷纭,本文相对较为认可郭沫若、李泽厚等人的观点,即视《易传》成书于荀子之后甚或更晚,《易传》学派受荀子学派之影响多于思孟学派。对本原的探寻多了几分逻辑推演的色彩,如《系辞上》说:“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又如《说卦》:“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可见,《易传》学派更多是从发生学的角度来解释“性”,其从天、地、人三个维度谈“性命之理”隐含着调和孟荀的倾向。
在这些学说的基础上,汉代董仲舒进行了极具里程碑意义的本原探索,他明确提出:“天地人,万物之本也。天生之,地养之,人成之。”[10]119这一观点既可依字面称为“三本论”,也可进一步归纳为“二本论”——一为“天”“地”亦即天然之天,一为“人”亦即人文教化。董仲舒既主张“性出善”又主张“兴王教”,实际上正是对孟荀的调和。不过总体上,董仲舒更加倾向于荀子学派。
然而,无论是三个本原还是两个本原,对于真正的哲学追问来说都太多了。魏晋玄学家的工作即是从中拣选他们认为更加终极性的本原。如王弼借助老子的哲学语言回应了这一问题,他说:“万物万形,其归一也。”王弼找到的那个终极性的因而是唯一的本原——“一”,实际上就是“自然”。此处的“自然”不同于现代意义上的自然界,而是自然而然。但王弼与老子有一根本上的区别,用他自己的话说,老子是“崇本息末”,而他是“崇本举末”,他说“守母以存其子,崇本以举其末,则形名俱有而邪不生,大美配天而华不作”[15]95,还说“绝仁非欲不仁也,为仁则伪成也”[15]199,也就是既要崇尚“自然”之本,又不放弃乃至要利用“名教”之末。
王弼的“崇本举末”思想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二本论”或“三本论”中本原太多的问题,不过仍然内蕴着亟待解决的理论矛盾。具体地说,“崇本举末”仍然不出“本-末”范式的窠臼,而本末论是一种极具经验色彩的本原论,换言之,本末论的“本”是“末”之经验的“存在之先”,既然如此,“末”的消失并不会给“本”带来实质性的影响,或者说,放弃“末”实际上并没有理论上的障碍:“息”之即可何必“举”之?
(二)“体—用”思维与宋代本原论转向
正当“本—末”思维面临理论困境的时候,佛教来了。
佛教哲学当然也要追问本原。如被方立天称为“华严宗佛教哲学思想的基本纲要”的《华严金师子章》即开宗明义,以金狮子作喻阐明了世界万物的起源、本原。法藏说:“谓金无自性,随工巧匠缘,遂有狮子相起。起但是缘,故名缘起。”照此理解,金狮子只是“相”,作为“相”的金狮子是由“金”“工巧匠”等因缘和合而成的。同理,世界万物也都是因缘和合而成的。
可以说,“缘起观”就是佛教的本原论,但是,只讲“缘起”似乎不那么直接、明白,所以佛教还讲“性空”。如上文所述,“性”是中国传统哲学用以追问本原的哲学范畴,佛教在华本土化的过程中向中国传统哲学借用了这一用法。在佛教那里,世界万物(万法)之“性”(或实相、真如、本来面目等,从不同角度来说有不同的表述)皆为“空”。这个“空”并不是真的什么都没有,而是指世界万物因缘和合、非实有、无自性的存在状态。
“缘起性空”观完整地表达了佛教的本原追问,其思考范式可总结提炼为“体—相—用”模式:“体”即是“空”,“相”即是世界万物之“假相”,“用”即是“相”在人心中之显现,体、相、用同源而不二。
按照“缘起性空”观和“体—相—用”思考范式,世界万物并没有实体性本原,皆为因缘和合而成;世界万物并非历时空的经验建构,而是超越时空的逻辑建构。这就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中国传统哲学“本—末”思维的理论困境:“本”不必是经验性的存在之先,也可以是超验性的存在之先;“末”不必是“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经验性的存在之末,也可以是与体同源、依体而起、不可舍弃亦无法舍弃之末。
佛教哲学的思维方式大大启发了儒家学者,宋代理学“制造者”开始自觉或不自觉地加以运用。如被尊为“理学开山”的周敦颐,虽然未明确以“体”“用”二字联用的方式阐述过相关命题,但是其核心命题“无极而太极”实际上就是“体—用”*宋儒在借用佛教“体—相—用”思维范式的时候并没有原样照搬,而是改造成了“体-用”思考范式。之所以会产生如此之区别,显然与两家对于本原问题的哲学追问密切相关,简而言之:佛教崇“无”,儒家重“有”。儒家从根本上否认“假相”的存在,“体”就是“相”,“相”就是“体”。思维的产物,这个命题并不是说“无极”派生出了“太极”,而是旨在说明“太极”依“无极”而起、“无极”依“太极”施用的本原论。
如果说周敦颐还只是理念上的化用,到了二程则直接有了话语的言说。程颐《易传序》说:“君子居则观其象而玩其辞,动则观其变而玩其占。得于辞,不达其意者有矣;未有不得于辞而能通其意者也。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体用一源,显微无间。”[6]689以至微之理为“体”,以至著之象为“用”,“体用一源,显微无间”,这正是佛教哲学思维方式的“翻版”。从哲学史的角度看,“体用一源”相关命题的提出标志着宋儒“体—用”思考范式从实践应用走向了理论自觉。
总而言之,佛教哲学的传入启迪中国传统哲学主动转换了自身的思考范式,即从对经验的存在之先的探索逐渐转向对超验的存在之先的追问,或者说从以“本—末”为思考框架的经验本原论逐渐转向以“体—用”为思考框架的思辨本原论。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有学者指出,“佛教不仅仅给中国人带来了某些观念,尤为重要的是,它带来了真正的、彻底的终极性思维方式。正是这种真正的终极性思维方式给中国哲学带来了里程碑式的发展”[22]。
四、人性即理:宋儒的生存论命题
佛教哲学的思考范式大大提升了中国哲学的思辨程度,但其视本原(性体)为“空”是儒家学者所不能接受的。这是因为,在这之前,儒家哲学所追求的本原——无论是天(或天地,即性)还是人(王道教化或名教等),在“本—末”思考范式下都带有浓厚的经验色彩,佛教对实体性本原、对经验世界的否定实际上便是将儒家的一切都否定掉了。因此,唐宋之际的儒家学者,其核心使命便是在更高的思辨水平上“重新发现”本原。
(一)天人本原的提出:性论复兴与人性二分
如前文所述,“性”的发明是中国哲学本原追问之路上的第一个里程碑,佛教借助这一概念在华本土化的过程中,这个概念从经验走向思辨的同时,也从“实存”走向了“虚无”。“性空”之下,儒家哲学的本原以及建基于这一本原的儒家伦理都面临着无处安放的困境。因此,复兴儒家性论并对“性”进行重新阐释,便成为儒家学者的首要任务。
历史地看,儒家性论的复兴早自中唐便已开始。韩愈承接汉代儒家关于人性的基本观点,重申性、情两个概念的界定:“性也者,与生俱生也;情也者,接于物而生也。”[23]20这一方面肯定了“性”作为人之天赋的至实特点,另一方面也使“情”的来源合法化,二者均显然构成对佛教的反驳。与此同时,韩愈还在董仲舒“性三品”说的基础上,构建了繁复的性情分品说。
与韩愈亦师亦友的李翱更是将“性”作为其哲学的核心范畴。同韩愈视“性”“情”一致的观点有所不同,李翱开始分离“性”与“情”:“人之所以为圣人者,性也;人之所以惑其性者,情也。喜、怒、哀、惧、爱、恶、欲七者,皆情之所为也。情既昏,性斯匿矣。非性之过也,七者循环而交来,故性不能充也……情不作,性斯充矣。”[24]6在李翱看来,只要“情”不从中作梗,先天之“性”足以使一个人成为圣人;如若“情”“作”以至于“昏”,“性”便“匿”而“不能充”。这就意味着,只要情欲控制得当,人人有成圣的潜质。这种“性善情扰”说成为后来理学家“变化气质”说的理论铺垫。
宋儒延续了中唐以降儒家学者的学术兴趣,他们从思孟学派那里重新发现了最有可能与佛教展开“对话”的理论资源。一方面,宋儒继承了思孟学派“天命之谓性”的观念,普遍以“天”(天命、天性)为人性,如邵雍说“言性者必归之于天”[5]117,“天使我有是之谓命,命之在我之谓性,性之在物之谓理”[5]163,张载则直截了当地说“性,即天也”[4]252。另一方面,至于“性”究竟是什么,宋代以前的儒家学者要么没有说明,要么只是给出了经验性的说明。有鉴于此,宋儒试图赋予“性”以新的内涵——这种内涵不仅要区别于佛、道两家的“无”,而且要区别于传统儒家经验性的“有”。
宋儒的这种努力在张载身上体现地尤为明显。张载说:“太虚无形,气之本体。其聚其散,变化之客形尔。至静无感,性之渊源。有识有知,物交之客感尔。客感客形与无感无形,惟尽性者一之。”[4]1此处,张载以“气”释“性”,并创造性地将“性”作了两种区分:“形而后有气质之性,善反之则天地之性存焉。故气质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人之刚柔、缓急、有才与不才,气之偏也。天本参合不偏,养其气,反之本而不偏,尽性而天矣。”[4]15
表面看来,张载分“性”为二——一为“气质之性”,一为“天地之性”——实际上则有意将“性”的内涵规定为“天地之性”。证据有二:一是张载援引并认可部分学者的说法,即“气质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二是张载在其他地方更加明确地提出“合性与知觉,有心之名”[4]3,此处“性”当为“天地之性”,“知觉”当为“气质之性”,实际上也就是“情”。从某种意义上说,张载“天地之性”的提出标志着儒家哲学“性”的超越意义的确立。正是从此出发,后学如张栻发展出了“心主性情”说,朱熹发展出了“心统性情”说,等等。
(二)天人生存的规定:道的理化与性理合一
如果说张载开启了儒家哲学本原论的超验化道路,二程兄弟则使这一探索路径更加清晰。
作为中国传统哲学的核心概念,道为儒释道及其他学派普遍采用并作为最高范畴。“道”的本义是“道路”“路径”,如《说文解字》的解释是“道,所行道也”,《尔雅·释官》的解释是“一达谓之道”。
同“道”一样,“理”也是中国传统哲学一直使用的概念。根据《说文解字》,“理”的本义是“加工玉石”,所谓“理,治玉也”,后来引申为事物发展运化的道理、原理、根据、所以然者等义。对“理”概念较早的深入阐发可以追溯到《易传》学派,如对后世影响深远的命题“穷理尽性以至于命”即出自《易传·说卦》的总结。
如前文所述,相比思孟学派和荀子学派,《易传》学派对本原的探寻多了几分逻辑推演色彩,也相对更加抽象。基于此,宋儒在应对佛教流行而对传统思想资源所作的挖潜中,首先找到的资源便是周易,由此“理”便成为宋儒话语中极其重要的概念。
邵雍说:“易曰:‘穷理尽性,以至于命。’所以谓之理者,物之理也。所以谓之性者,天之性也。所以谓之命者,处理性者也。所以能处理性者,非道而何?是知道为天地之本,天地为万物之本。”[5]9又说:“天使我有是之谓命,命之在我之谓性,性之在物之谓理。”“性”在人而“理”在物,“道”能“处”理与性。可见,在邵雍那里,“道”的地位还是最高的,能统摄“性”与“理”。
到了张载,他提出“由太虚,有天之名;由气化,有道之名;合虚与气,有性之名;合性与知觉,有心之名。”[4]3又说:“神,天德;化,天道。德,其体;道,其用,一于气而已。”[4]9在这里,“天”的地位高扬。“天”是至实之气,是体;“道”是气化过程,是用。张载还曾明确表示:“万事只一天理。”这表明他已经开始强调天理的本原和主宰地位。
至二程,以“理”代“道”的意图则更加明显:“子曰:上天之载,无声无臭之可闻。其体则谓之易,其理则谓之道,其命在人则谓之性,其用无穷则谓之神,一而已矣。”[6]1170“或问:‘何谓诚,何谓道乎?’子曰:‘自性言之为诚,自理言之为道,其实一也。’”[6]1182“惟理为实。”至此,至实之理代替了以往关于道的言说。
“性”与“理”超越意义的确立,为理学的最终出场做好了理论准备。在此基础上,二程顺理成章地提出了“性即理”的命题。程颐说:“性即理也,所谓理,性是也。天下之理,原其所自,未有不善。喜怒哀乐未发,何尝不善?发而中节,则无往而不善。”[6]292对此,朱熹曾大加赞佩:“‘性即理也’一语,直自孔子后,惟是伊川说得尽。这一句便是千万世说性之根基。”[25]2360
朱熹的评价并非谬赞。二程“性即理”这一论断对人之“性”与物之“理”的打通,实在是解决了儒家哲学的大问题。一方面,“性即理”某种程度上解决了儒家哲学自先秦至唐代一直思辨性不高的弊病,这显然构成了对佛道二教的有力回应;另一方面,“性即理”也在某种程度上吸取了佛教哲学思考范式的教训,它并没有像佛教或者西方古典哲学那样预设“人”与“天”、主体与客体的分立,也没有在人的生存世界之外构建一个完全独立的理性世界、精神世界,而是从“天人合一”的视角出发,始终坚持只有“一个世界”,生存世界之外别无其他世界。
由此,对理学发生问题的哲学阐释,存在论视域固然有其道理,但并不准确。理学“制造者”是要借助佛教哲学的存在论思维,承续魏晋“天人合一”观,其终极目的是要探寻人类生存世界之本原,这一本原不仅仅是作为“客体”之“理”,还是作为“主体”之“性”——仁,正如程颢所说:“学者须先识仁。仁者,浑然与物同体,义、礼、智、信皆仁也。”[6]16由此,作为儒家最高伦理的“仁”成为“天人合一”的宇宙生命体之本原,亦即人类生存之本原。“仁”不是思考的对象,而是宇宙生命体生机勃发的行动之源头,宋儒的本原追问因此具有了浓厚的生存论意味。
五、结 语
以“天人合一”为思维视域,以“体—用”思维为新的思考范式,宋儒将“人性”“物理”合二为一——“性即理”。“理”既是自然世界运化发展的原理、根据、所以然者——仅从这个意义上说,将理学之“理”理解为具有存在论色彩的“实存”尚有道理;同时,“理”又是人类社会生存发展的最高法则——在这重意义上,“理”就不仅仅是“实存”,更是关乎人类生存之本原。
理学的发生也内蕴着向程朱、陆王两大学派发展的可能性。二程之后,理学又历经程朱、陆王两大学派的发展和转折,“理”的内涵也渐趋清晰,那就是“天地万物一体之仁”。[9]91也就是说,性、理、心、仁,从根本上说是一回事,这就是宋明理学追问生存本原所找到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