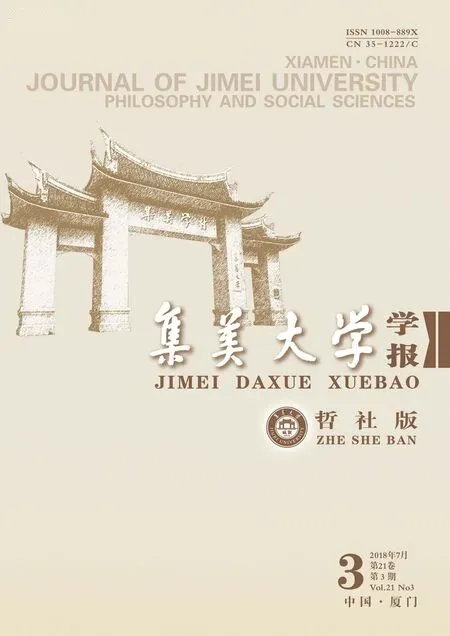理即气
——论罗钦顺对朱子的继承与超越
沈顺福
(山东大学 儒学高等研究院,山东 济南 250100)
作为“朱学的后劲”[1]183,罗钦顺不仅仅继承了朱熹的理学思想,而且发展了朱子理学。在继承与发展朱子学的过程中,罗钦顺面临着怎样的哲学问题呢?也可以说,罗钦顺解决了怎样的哲学问题?或者说,罗钦顺的哲学基本主题是什么呢?本文将通过分析罗钦顺的理与气的关系,试图指出,罗钦顺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其实是朱熹所遗留的难题,即理气二本论问题。罗钦顺在继承了朱熹的理本论的基础上,对理的观念做了进一步的阐释,提出理终究是气,从而形成了具有实在论特征的气本论。理气一体论的实质在于将事物的终极性本体视为客观的实在且统一于客观事物之中,即理不仅在气中,而且理即是气。
一、朱熹的二元论难题
朱熹的核心观点是理本论。朱熹曰:“凡事固有‘所当然而不容己者’,然又当求其所以然者,何故?其所以然者,理也。”[2]414理是事物的所以然者,事物存在的终极性根据。朱熹称之为太极:“所谓太极,则是‘所以然而不可易者’。”[2]415事物的“所以然”,即事物之自性,即是太极。朱熹明确指出:“太极只是天地万物之理。在天地言,则天地中有太极;在万物言,则万物中各有太极。未有天地之先,毕竟是先有此理。动而生阳,亦只是理;静而生阴,亦只是理。”[2]1太极即万物之理。朱熹之所以称之为太极,意在太极的终极性:“太极便是一,到得生两仪时,这太极便在两仪中;生四象时,这太极便在四象中;生八卦时,这太极便在八卦中。”[2]671太极指一。作为一的太极,至少包含三层内涵,即基础性、单一性和不可知性。太极是最基础的单位,具有基础性。这可以从词义本身和朱熹的言语中得到论证。太极之极,本义指栋梁或屋顶之至高处。太即大,表示最、极端等义。太极指极端处。极端处显然指向某种究竟。这种究竟即事物的终极性、基础性内容。因此,太极指称事物的究竟,具有终极性和基础性品质。它不同于一般的事物,而是事物“万化根本”。太极之理是世间万物存在的根本。或者说,理、太极是万物存在之根本。这便是人们常说的理本论:“有是理便有是气,但理是本,而今且从理上说气。”[2]2理是万物存在之本。
与此同时,朱熹又区别了理与气:“理未尝离乎气。然理形而上者,气形而下者。自形而上下言,岂无先后!理无形,气便粗,有渣滓。”[2]3理是形而上者,气是形而下者。形而上之理与形而下之气同时存在。尽管朱熹再三强调二者的相即不离的关系,但是,事实上,由于朱熹完全否认二者之间的内在联系,从而将理与气分为两个实体存在。“也须有先后。且如万一山河大地都陷了,毕竟理却只在这里”。[2]4理似乎是可以独立于气、物而实在,理不同于气或物。
而另一方面,从中国传统气论的立场来看,万物的生存依赖于气:天气与地质。其中,天气提供生命,地气或地质提供形质。气与质也是万物生存的本源:“人之所以生,理与气合而已。天理固浩浩不穷,然非是气,则虽有是理而无所凑泊。故必二气交感,凝结生聚,然后是理有所附着。凡人之能言语动作,思虑营为,皆气也,而理存焉。”[2]65人的存在是理和气共同作用的结果。理是本,气也是本。事实上,在《太极图说注》中,朱熹提出了生存谱系说:“有太极,则一动一静而两仪分;有阴阳,则一变一合而五行具。然五行者,质具于地,而气行于天者也……五行具,则造化发育之具无不备矣。”[3]73万物产生于阴阳之气,最终本于太极。太极是形而上之理,为无极。它并非事物的现实的本源。也就是说,从现实的角度来看,万物生于气。这也基本符合传统中国生命哲学。于是,万物便有了两个本,理与气。这便是二本论。故,很多学者提出朱熹的二元论问题。陈荣捷曰:“形而上与形而下之分为两橛,每易趋于两元论或导致孰为主从。于二程学说中尚未见显明。而于朱子,此种两橛渐较显著,因而两难之困局,亦至迫切。朱子为免于此一困局,乃转而求之于太极观念。”[4]149-150刘述先先生亦曰:“理气虽在实际上不可分,但理自理,气自气,二者决不可以互相化约,这是朱子一贯的思想!故由形上构成的角度看,朱子主张理气二元不离不杂的思想是不容辨者。”[5]222“我们之所以要把朱子说成理气二元论者,一则是因为他高悬其‘理’,赋予无上之地位。”[6]很多人相信朱熹是一种二元论者。这其中也包括罗钦顺。
尽管我们相信,从形而上学的角度来看,事物的存在具有两个本体,即客观本体和主观本体。正是这两个本体的合作,方才形成经验的、现实的存在物。但是,对于某个事物来说,其客观之本体一定是单一的,比如理念(idea)等。如果理是本体性存在,那么气便一定不是本体性存在。朱熹的理气关系说,将理与气分为两节,形成了事实上的双重本体性存在。为了避免这种二元论,朱熹便提出形而上、下的分别,以为理是形而上的存在,气是形而下的存在,似乎因此而解决了二元分立的立场。这种努力显然是徒劳的。他将气视为形而下的存在,鬼神便因此成为形而下的存在。这显然有误。或者说,二元论的立场必然要求他相信鬼神等气的形而下性质。事实上,鬼神等气的存在如何能够成为形而下的存在呢?这一切的原因在于理气关系中的二元论,或者说,朱熹并未正确理解理气关系。这便是朱熹留给后人的难题,即理气究竟是什么关系?或者说,理是不是气?
二、理:超验而普遍的本体
理是朱子学的核心概念。罗钦顺接受了这个概念及其所包含的基本内涵。在罗钦顺看来,万物有理:“‘理一分殊’四字,本程子论《西铭》之言,其言至简,而推之天下之理,无所不尽。在天固然,在人亦然,在物亦然;在一身则然,在一家亦然,在天下亦然;在一岁则然,在一日亦然,在万古亦然。持此以论性,自不须立天命、气质之两名,粲然其如视诸掌矣。”[7]9万物有理。和朱子的观点一样,罗钦顺也将理理解为事物之“所以然”者:“理果何物也哉?盖通天地,亘古今,无非一气而已。气本一也,而一动一静,一往一来,一阖一辟,一升一降,循环无已。积微而着,由着复微,为四时之温凉寒暑,为万物之生长収藏,为斯民之日用彛伦,为人事之成败得失。千条万绪,纷纭胶轕而卒不可乱,有莫知其所以然而然,是即所谓理也。初非别有一物,依于气而立,附于气以行也。”[7]4-5理是事物的“所以然”者。所谓事物的“所以然”者,即事物的自性,或曰,此事物之所以为此事物的决定者。罗钦顺曰:“理只是气之理,当于气之转折处观之。往而来,来而往,便是转折处也。夫往而不能不来,来而不能不往,有莫知其所以然而然,若有一物主宰乎其间而使之然者,此理之所以名也。”[7]68理为主宰者,是事物的“所以然”者。罗钦顺称之为“条理”:“物格则无物,惟理之是见;己克则无我,惟理之是由。沛然天理之流行,此其所以为仁也。始终条理,自不容紊……”[7]10理即条理,乃确定事物性质的东西,即事物的自性。
事物的所以然者或事物的自性,又被叫作性:“夫心者人之神明,性者人之生理,理之所在谓之心,心之所有谓之性,不可混而为一也。”[7]1性即人初生之理。性理一指。“盖受气之初,犬牛与人,其性未尝不一,成形之后,犬牛与人,其性自是不同。叔子所云‘不害为一’,正指本源处言之,而下文若乃二字却说开了,语脉殊欠照应,非记録之误而何?”[7]21禀气为性。同时,作为性或理,它又是犬、牛、人的根据。性、理是事物存在的根据。他以观山为喻,指出:“穷理譬则观山,山体自定,观者移歩,其形便不同。故自四方观之,便是四般面目,自四隅观之,又各是一般面目。面目虽种种各别,其实只是此一山。山之本体,则理一之譬也,种种面目,则分殊之譬也。在人所观之处,便是日用间应接之实地也。”[7]68山之理即山的本体、山的自身。它是确定的。然而,不同的人,从不同的角度却只能见到不同面目的山,而不是山的本体。
这种所以然之理是“静”的:“至理之源,不出乎动静两端而已。静则一,动则万殊,在天在人一也。《乐记》曰:‘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中庸》曰:‘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此理之在人也,不于动静求之,将何从而有见哉?然静无形而动有象,有象者易识,无形者难明,所贵乎穷理者,正欲明其所难明尔……然欲动情胜,虽或流而忘反,而中之本体,固自若也,初未始须臾离也。”[7]8性理之初便是静。这个静并不仅仅指动静之静,而是说它的超越的、形而上的状态。这种状态之一便是无形象。故,本体之理无形。“‘上天之载,无声无臭’,又安有形体可觅邪?然自知道者观之,即事即物,此理便昭昭然在心目之间,非自外来,非由内出,自然一定而不可易。所谓‘如有所立卓尔’,非想象之辞也。佛氏以寂灭为极致,与圣门卓尔之见絶不相同,彼旷而虚,此约而实也。果然见到卓尔处,异说如何动得?”[7]71理在事物之中“约而实”,是真实的,同时也无形体。“性无形,虽有善譬,终难尽其妙”。[7]20或者说,理处于隐微的境地:“乃知圣经所谓‘道心惟微’者,其本体诚如是也。”[7]1隐微或无形者自然难知。罗钦顺曰:“此等皆是粗迹,感应之理便在其中,只要人识得。故程子曰:洒扫应对,便是形而上者。理无大小故也。若于事物上无所见,谈玄说妙有何交渉?”[7]73二程称理是形而上者。罗钦顺虽然未有明示,却引述此语,应该可以证明他的相同立场,即,理也是形而上者,“无大小”。这种形而上的存在便是超验的存在。
超验之理不仅规定同类事物自身,而且是事物的终极性根据:“盖一卦有一卦之理,一爻有一爻之理,皆所当穷,穷到极处却止是一理。此理在人则谓之性,在天则谓之命。心也者,人之神明而理之存主处也,岂可谓心即理,而以穷理为穷此心哉!良心发见,乃感应自然之机,所谓天下之至神者,固无待于思也。”[7]114理是一种终极性存在(“穷到极处”)。所谓终极性存在,即它是一种究竟,具有超越性与终极性:对事物的追问到此为止而不可能继续下去了。它是一种真正的终极性存在。作为超验的终极性存在,事物之理是自在的。“性之理,一而已矣。名其徳,则有四焉。以其浑然无间也,名之曰仁;以其灿然有条也,名之曰礼;以其截然有止也,名之曰义;以其判然有别也,名之曰智。凡其灿然截然判然者,皆不出于浑然之中,此仁之所以包四徳,而为性之全体也。截然者,即其灿然之不可移者也;判然者,即其截然之不可乱者也。名虽有四,其实一也。然其所以如是之浑然灿然截然判然,莫非自然而然,不假纤毫安排布置之力,此其所以为性命之理也。”[7]71性理自然而自在,无需他者为条件,即理是绝对的。理具有绝对性。它表现为“常”:“然窃惟天地之化,消息盈虚而已,其妙虽不可测,而理则有常。圣人裁成之云,亦惟因其时顺其理,为之节度,以遂生人之利,非能有所损益也。”[7]26理有常,即具有绝对性。“夫为人妇,祈子而得子,此常理也,安得谓之‘无人道而生子’乎?然其所以见弃者,意必有奇形怪状,可骇可疑,如宋芮司徒女子之比,其为祥为妖,莫可测也。”[7]102理便是常理。
超验的常理具有普遍性。罗钦顺曰:“夫此理之在天下,由一以之万,初匪安排之力,会万而归一,岂容牵合之私?是故,察之于身,宜莫先于性情,即有见焉,推之于物而不通,非至理也。察之于物,固无分于鸟兽草木,即有见焉,反之于心而不合,非至理也。必灼然有见乎一致之妙,了无彼此之殊,而其分之殊者自森然其不可乱,斯为格致之极功。然非真积力久,何以及此?”[7]3理是一个普遍者。从天地世界来看,世界万物虽然万种,却也分享一个理。比如人与物,罗钦顺曰:“人犹物也,我犹人也,其理容有二哉?然形质既具,则其分不能不殊。分殊,故各私其身;理一,故皆备于我。夫人心虚灵之体,本无不该,惟其蔽于有我之私,是以明于近而暗于远,见其小而遗其大。凡其所遗所暗,皆不诚之本也。然则知有未至,欲意之诚,其可得乎?故大学之教,必始于格物,所以开其蔽也。格物之训,如程子九条,往往互相发明。其言譬如千蹊万径,皆可以适国,但得一道而入,则可以推类而通其余,为人之意,尤为深切。而今之学者,动以不能尽格天下之物为疑,是岂尝一日实用其工?徒自诬耳。”[7]2-3人与万物一般,分享同一之理。所以,罗钦顺曰:“天人一理,而其分不同。‘人生而静’,此理固在于人,分则属乎天也。‘感物而动’,此理固出乎天,分则属乎人矣。君子必慎其独,其以此夫。”[7]8天人同理。“天人物我之分明,始可以言理一。不然,第承用旧闻而已。”[7]14“天地人物,止是一理。然而语天道则曰阴阳,语地道则曰刚柔,语人道则曰仁义,何也?盖其分既殊,其为道也自不容于无别。然则鸟兽草木之为物,亦云庶矣,欲名其道,夫岂可以一言尽乎?大抵性以命同,道以形异。必明乎异同之际,斯可以尽天地人物之理。”[7]73万物一理。“成已成物,便是感应之理。理惟一尔,得其理则物我俱成。”[7]77理是普遍者。或者说,作为一个名词,理是普遍名词,以不同于个体的专有名词。
在罗钦顺看来,“理,一也,必因感而后形。感则两也,不有两即无一。然天地间,无适而非感应,是故无适而非理。”[7]13理是一,即万物一理。这个同一之理,便是太极。“夫易乃两仪四象八卦之总名,太极则众理之总名也。云易有太极,明万殊之原于一本也,因而推其生生之序,明一本之散为万殊也。斯固自然之机,不宰之宰,夫岂可以形迹求哉?斯义也,惟程伯子言之最精,叔子与朱子似乎小有未合。今其说具在,必求所以归于至一,斯可矣。”[7]5太极也是理。或者说,理是太极。作为太极的理无疑具有终极性。故,它不仅仅是一个普遍名词,而且是一个最普遍的名词。它甚至是万物之本。但是这个本原之理,罗钦顺明确指出:“或者因‘易有太极’一言,乃疑阴阳之变易,类有一物主宰乎其间者,是不然。”[7]5理仅仅是基础,而非主宰,以为在气之外还有一个主宰者即太极或理,这是不对的。
万物一理。对于万物来说,这个理便是普遍者(universal),即,普遍存在于万物之中的实在。所谓万物一理,通常具有类的意义,即,它普遍存在于某类物体中,如牛之理普遍于所有的牛的种类中。故,罗钦顺曰:“易逐卦逐爻各是一象,象各具一理。其为象也不一,而理亦然。然究而论之,象之不一,诚不一也,理之不一,盖无往而非一也。故曰:同归而殊涂,一致而百虑。非知道者,孰能识之?”[7]29各个物体有各类的理。这个理最终却可以归为万物之理,即公理、公道、天理,即唯一之理。假如我们将宇宙万物视为一个存在物、一个生命体时,万物之理自然是共同的。这便是公理:“故程子申其义云‘闻道,知所以为人也。夕死可矣,是不虚生也。’今顾以此言为处老处病处死之道,不几于侮圣言者乎!道乃天地万物公共之理,非有我之所得私。圣贤经书明若日星,何尝有一言以道为吾,为我?”[7]42此公道、公理便是儒家之理。
超验的、普遍而实在之理是万物存在的终极性本原。这是朱子学的基本主张。罗钦顺继承了这一基本思想,并对其进行了进一步的改造。
三、气与物
从中国传统生存哲学尤其是张载哲学来看,气是事物或“生物”的终极性本源。同为本源或本体,二者关系如何?对此,朱熹以为二者别为二物。对此,罗钦顺进行了修正,并最终提出:“理果何物也哉?盖通天地,亘古今,无非一气而已。”[7]4理是气。那么,理为什么是气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首先必须回答一个前提性问题,即,气是什么呢?
气概念是中国传统哲学的核心概念之一。仅就宋明理学而言,张载便是其代言人。或者说,张载的气学说为宋明理学中的气论奠定了基础。根据张载的气论,气具备两个主要功能。其一,气为万物的生存提供动力:“《正蒙》有云:阴阳之气,循环迭至,聚散相荡,升降相求,絪缊相揉。盖相兼相制,欲一之而不能。此其所以屈伸无方,运行不息,莫或使之。不曰性命之理,谓之何哉!此段议论最精,与所谓太虚、气化者有间矣。”[7]31张载的气论以为,实体之气乃是生存的终极性基础。这个终极性基础,不仅是终极性本源,而且为万物的生生不息提供动力。
其次,气也是构成事物的基本材质:“《正蒙》云:聚亦吾体,散亦吾体。知死之不亡者,可与言性矣。又云:游气纷扰,合而成质者,生人物之万殊。其阴阳两端,循环不已者,立天地之大义。夫人物则有生有死,天地则万古如一。气聚而生,形而为有,有此物即有此理。气散而死,终归于无,无此物即无此理,安得所谓‘死而不亡者’邪?若夫天地之运,万古如一,又何死生存亡之有?譬之一树,人物乃其花叶,天地其根干也。花谢叶枯,则脱落而飘零矣,其根干之生意固自若也,而飘零者复何交渉?谓之不亡,可乎?”[7]30万物的存在无非气,气等构成了生物之质。或者说,生物一定具有气质材料。没有气质材料的物是不存在的。“‘游气纷扰,合而成质者,生人物之万殊。阴阳两端,循环不已者,立天地之大义。’《中庸》有两言尽之,曰:小德川流,大德敦化。”[7]30气生成质,便成为生成万物的基本材质或材料。“‘气则阴阳五行,理则健顺五常。’欲令一一相对,自不觉其言之多也。然太极乃性命之全体,恐须提出此两字,方见头脑分明。”[7]103气是阴阳五行的根基、本原。罗钦顺曰:“若吾儒所见,则凡赋形于两间者,同一阴阳之气以成形,同一阴阳之理以为性,有知无知,无非出于一本。故此身虽小,万物虽多,其血气之流通,脉络之联属,元无丝毫空阙之处,无须臾间断之时,此其所以为浑然也。然则所谓同体者,亦岂待于采揽牵合以为同哉?”[7]55-56阴阳之气最终成就事物。
罗钦顺引述了邵雍与朱子的几段话:“卲子《观物外篇》有云:气一而已,主之者乾也。朱子《易本义》所谓‘天地间本一气之流行,而有动静尔。以其流行之统体而言,则但谓之乾,而无所不包’,与卲说合。又云‘神亦一而已,乘气而变化,能出入于有无生死之间,无方而不测者也。’如此则神别是一物,与朱子所谓‘气之精英’不合。异同之际,学者不可不致思也。”[7]72第一段话的意思是:万物以气为根本。邵雍与朱熹观点一样。第二段话的意思说二人不同:邵雍以为神、气有别,朱熹则以为神、气为一。这段话的意思似乎表明:罗钦顺赞同气本说。至于神气关系,他以为需要斟酌。
事物的形而上的客观性本原一定是单一的存在,故,气是一,或者说,阴阳二气实为一气:“先天横图最宜潜玩。奇偶二画之中,当一线空白处,着太极两字,其旨深矣。阳奇而阴偶,二气流行不容有纤毫间断,但画而为图.若非留一线空白,则奇偶无自而分,此即邵康节所谓‘一动一静之间,天地人之至妙至妙者也。’偶画亦有空者,盖二气之分,实一气之运,直行去为阳,转过来便是阴,须空一线,方见其转折处。阴之本体,只是后半截耳。只此一奇一偶,每加一倍,其数至不可胜穷。然倍至六画,则三才之道包括已尽。图虽无文,而其理甚显,要在默而识之。”[7]102阴气与阳气实际上是一个气。这和朱熹的观点也是一致的。
单一的、实在的气是万物存在的客观本源。这便是气本论。这本来属于张载的发明。罗钦顺吸收并继承了张载的气本论。与此同时,作为朱子后学,罗钦顺也同样接受理本论的立场, 以为理是天下万物存在之本原:“先天图最宜潜玩,性命之理直是分明。分阴分阳,太极之体以立;一阴一阳,太极之用以行。若玩得熟时,便见得一本之散为万殊,万殊之原于一本,无非自然之妙。”[7]71理是万物之本。于是产生了两种不同的本原论,即理本论与气本论。也就是说,罗钦顺既赞同气本论,也接受理本论。或者说,在罗钦顺看来,理本论便是气本论。
四、理即气
理本论即气本论的前提条件是理是气。这恰恰是罗钦顺的新主张。罗钦顺明确提出:“尝窃以为,气之聚便是聚之理,气之散便是散之理,惟其有聚有散,是乃所谓理也。推之造化之消长,事物之终始,莫不皆然。”[7]38气聚便是理在。“人呼吸之气,即天气之气。自形体而观,若有内外之分,其实一气之往来尔。程子云‘天人本无二,不必言合。’即气即理皆然。”[7]43气理统一。罗钦顺曰:“盖五行,质也,质附于地。庶征,气也,气运于天。以‘润下’、‘炎上’等语观之,谓‘在天为五行’非其实矣。看来庶征一畴,但顺经文解说,便见天人感应之理,似不必过求。”[7]103理便是气。
气理统一并不是说理气完全一致。“愚故尝曰:理须就气上认取,然认气为理便不是。此言殆不可易哉!”[7]68理必定是气,但是我们不能够因此断定:气便是理。理仅仅是气的某个特殊部分、性质或形态。故,“理须就气上认取,然认气为理便不是。此处间不容髪,最为难言,要在人善观而黙识之。‘只就气认理’与‘认气为理’,两言明有分别,若于此看不透,多说亦无用也。”[7]32气与理具有统一性,并不意味着理气完全一样。“‘理同而气异、气同而理异’,此两说质之《大传》‘形而上下’之言,终觉有碍。必须讲究归一,方得触处洞然。”[7]107我们必须同时接受“理同气异”与“气同理异”的观点。理气既统一,又有差异。后者强调了统一性,前者突出了差异性。或者说,理仅仅是特殊的气。我们可以将理与气的关系比作(不可见的)树根与(可见的)大树的关系。树根一定属于树,但是树未必是树根。理是某种气。
这个特殊形态的实在之气便是“所以然”或“规定性”的载体。罗钦顺曰:“理只是气之理,当于气之转折处观之。往而来,来而往,便是转折处也。夫往而不能不来,来而不能不往,有莫知其所以然而然,若有一物主宰乎其间而使之然者,此理之所以名也。‘易有太极’,此之谓也。若于转折处看得分明,自然头头皆合。程子尝言‘天地间只有一个感应而已,更有甚事?’夫往者感,则来者应;来者感,则往者应。一感一应,循环无已,理无往而不存焉,在天在人一也。天道惟是至公,故感应有常而不忒。人情不能无私欲之累,故感应易忒而靡常。夫感应者,气也。如是而感则如是而应,有不容以毫发差者,理也。”[7]68气和理都是感应。但是气属于所有的感应体,而理则仅仅指某些感应体:“如是而感则如是而应”[7]68者,且不容毫发之差。于是,理和气的关系我们可以用哲学上的具体事物与普遍者的关系来说明。气代表了具体的器物或物理实体。理则是某类事物的普遍者。比如马,气代表马的物理属性,即马一定是气质之物、实在之物。作为种类范畴的马,当我们称呼其为一般名词时,这个一般名词描述了一般现象。一般现象则源自一般性的马的理念,即,所有的马都具有的、共有的、客观的存在者。从实在论的角度来看,马的理念是客观而实在的。人们见到它自然会知道拥有这类存在者的物体便是马。故,在每一个具体的马的身上都隐藏着某种特殊的、共有的存在体。这一存在体是此物成为马的基本条件或根据。这个共有的存在体一定是客观的。或者说,从客观性来说,假如我们将马视作某种气的动物,那么,这种能够让此动物成为马的理必然具有气的属性或特点。简单地说,作为普遍概念的马一定拥有一个普遍的、客观的物理实体与之相应,或者说,马的理念也是客观的、实在的。既然它是客观而实在,它便一定是气,即理与气在此合一,理便是气。“杨方震复余子积书有云:若论一,则不徒理一,而气亦一也。若论万,则不徒气万,而理亦万也。此言甚当,但‘亦’字稍觉未安。”[7]43万物的所以然者是终极性的、单一的理。这个终极性的单一的理终究还是物质性的气。理即气。
理即气,故,“盖人物之生,受气之初,其理惟一,成形之后,其分则殊。其分之殊,莫非自然之理,其理之一,常在分殊之中。此所以为性命之妙也。语其一,故人皆可以为尧舜;语其殊,故上智与下愚不移。圣人复起,其必有取于吾言矣。”[7]7人生有性理便是禀气。比如恻隐之心,本来为性,罗钦顺便将其解释为气:“人物之生,本同一气,恻隐之心,无所不通。故‘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皆理之当然,自有不容已者,非人为之使然也。”[7]14理一定是气。性理为一,故,性也是气:“程叔子云:孟子言性,当随文看,不以告子‘生之谓性’为不然者,此亦性也。被命受生之后,谓之性尔,故不同,继之以‘犬之性犹牛之性,牛之性犹人之性欤’,然不害为一。若乃孟子之言善者,乃极本穷源之性。尝考叔子论性之语亦多,惟此章意极完备。同中有异,异中有同,性命之实,无余无欠……盖受气之初,犬牛与人,其性未尝不一,成形之后,犬牛与人,其性自是不同。叔子所云‘不害为一’,正指本源处言之,而下文若乃二字却说开了,语脉殊欠照应,非记录之误而何?”[7]21性、理是气。
理是气,故,知理便和气相关。罗钦顺曰:“孟子之学,亦自明而诚,知言养气是也。自明而诚者,未必便造其极,理须善养……程子尝言‘学者须先识仁’一段说话,皆与孟子相合,但以存字该养字尔。吾儒之学,舍此更无是处。然异学亦有假之以文其说者,不可不明辨之。”[7]88理是气,存理自然便是养气。这是儒家的核心观念。“孟子以‘勿忘勿助长’为养气之法,气与性一物,但有形而上下之分尔,养性即养气,养气即养性,顾所从言之不同,然更无别法”。[7]10存理、养性与养气是一回事。
据此,罗钦顺批评张载等人的二性说:“程张本思孟以言性,既专主乎理,复推气质之说,则分之殊者诚亦尽之。但曰‘天命之性’,固已就气质而言之矣,曰‘气质之性’,性非天命之谓乎?一性而两名,且以气质与天命对言,语终未莹。朱子尤恐人之视为二物也,乃曰‘气质之性,即太极全体堕在气质之中。’夫既以堕言,理气不容无罅缝矣。惟以理一分殊蔽之,自无往而不通,而所谓‘天下无性外之物’,岂不亶其然乎!”[7]7-8理气为一,焉能有二性?
虽然理气不可视为一物,但是,“罗钦顺在绝大多数场合下是明确主张理气不可被视为黄宗羲式的‘一物’(即一回事)的,罗氏所谓‘认理气为一物’,意思应是理气浑融不离”。[8]这等理解却也失之偏颇。罗钦顺的意思并非理气不离,而是理即是气。这基本符合实在论的立场。
五、理气一致
什么是罗钦顺所面临的哲学问题?或者说,罗钦顺解决了什么哲学问题呢?作为朱子后学,罗钦顺继承了朱子思想,同时发展了朱子学。这
种发展便是对朱子学的超越。罗钦顺所面临的问题其实也是朱熹所遗留的理学难题。朱子突出了理的独立性、实在性与超验性,以为理在气先,从而将理看作是区别于气的另一个物体。这在事实上造成了二元论,即万物不仅本理,而且本气。“朱子终身认理气为二物”。[7]29这便是朱子学的不足,至少在这个问题上,朱子并没有合理地解释或处理它。罗钦顺直面这个问题,并提出了一个合理的答案,从而在解决朱子难题的同时,超越了朱子哲学。罗钦顺的解决方案便是理气不二,或者说,理即气。
罗钦顺用气来解释客观之理。罗钦顺认为,万物皆有一个客观的、超越性本原,且这个本原一定是实在的。与此同时,事物的终极性存在,按照气学的立场,乃是气,即气本身便足以成为万物的终极性本原。故,同时作为万物的客观的、终极性的存在根据,理与气必然具有一致性。或者说,二者便有了重合,即作为终极性本原的理和终极性本原的气应该是同一个存在。理便是气。理本论与气本论获得了统一。这也基本符合实在论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