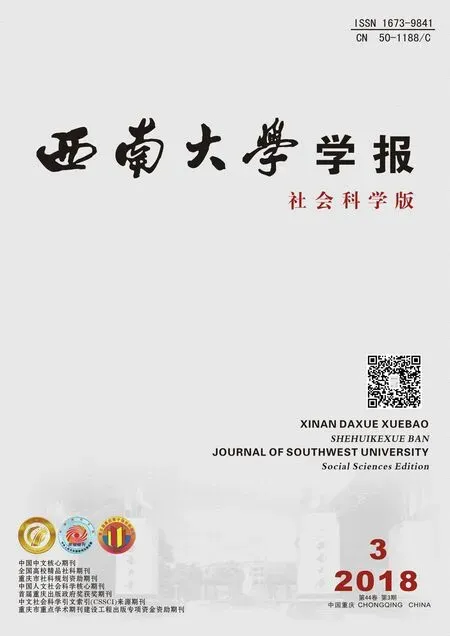斯坎伦的道德契约主义与多余性反对
周 晶
(吉林大学 哲学社会学院,吉林 长春 130012)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应得:正义的维度”(14JJD720023),项目负责人:王立。
一、斯坎伦的道德契约主义
在1998年发表的《我们彼此负有什么义务》一书中,托马斯·斯坎伦(Thomas M. Scanlon)对道德契约主义做了完整的表述:“一个行为如果其实施在某种境遇下会被一般行为规则的任何一套原则所禁止,那么这个行为就是不正当的;这种一般行为规则作为理智的、非强制的普遍的协议的基础,是人们无法合理拒绝的。”[1]153用一句话来概括这个表述,即:不正当的行为是能被人们合理地拒绝的行为;反之,正当的行为就是不能被人们合理拒绝的行为。没有人能够合理拒绝是斯坎伦契约主义的道德准则,这条准则表达了行为不正当所包含的内容,是判断行为正当与否的依据。
人们为什么遵从基本的道德?我们为什么有理由做道德的行为?这是传统伦理学关于道德动机的难题。斯坎伦认为,相对于传统的道德哲学理论,契约主义的优点在于提供了一种更好地说明道德动机的理论。道德动机总是与道德判断联系在一起,所谓道德判断也就是道德对错问题,即什么在道德上是正确的,什么在道德上是错误的。道德动机问题则是解释道德判断如何为行为者提供道德理由的问题。具体来说,当人们判断一种行为是错误的,这种判断如何为行为者提供不去做该行为的理由。以往的契约论者设定的缔约者都是从维护自身的利益出发来寻找行为的动机。与之不同,斯坎伦认识到缔约者还有一个重要的动机——寻求共同的道德原则,这些原则是那些具有相似动机的其他人不能有理由拒绝的。因此,在斯坎伦的契约论思想中,订约者的行为是受寻求自我利益和尊重他人的共同驱使。行为者的道德动机来自于:“我们不得不与他人友好地生活在一起,这是他们无法有理由拒绝的,只要他们也受到这一理想的激发的话。因为我们有这条理由,我们就有理由去注意关于哪些行为是正当的、哪些是不正当的问题,也就是说,去努力确定,什么东西是其他人不能有理由拒绝的原则所允许的,并且,我们也有理由按照这些原则所要求的方式来支配我们实际的思想和行动。”[1]154也就是说,我们与他人共同的,且他人不能有理由拒绝的原则,是道德动机的来源。
斯坎伦认为自己的契约主义有两个目标:其一是为不正当性提出一个一般标准,这个标准解释了那些更为具体的不正当做法的特性,这个标准也就是斯坎伦关于道德不正当的一般规定;其二是解释正当与不正当的道德判断所具有的说服力和动机力,这也是斯坎伦关于道德动机的说明。可拒绝性原则既是判断行为正当与否的一个重要前提,也是对以往契约动机的一种改进。以往的契约论都是以个体自我利益的计算为动机,而斯坎伦的契约主义道德动机理论包含两个部分:“一是寻求自身利益,一是寻求共同的道德原则。”[2]可拒绝性原则是斯坎伦道德契约主义的核心特征和基本原则。
斯坎伦的道德契约论自从发表以来,在当代西方道德哲学界、政治哲学界和伦理学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如哲学家R.杰伊·华莱士(R.Jay Wallace)说:“毋庸置疑,斯坎伦的权威性的论著《我们彼此负有什么义务》在这些年来出现的最成熟的、最重要的道德哲学论著中占有一席之地。该书指明了道德哲学范围内所有主要方面上的根源性问题。我希望并且期待着看到在未来数年中,这一著作对道德哲学的形式和发展方向产生决定性的影响。”[3]罗杰·克里斯普(Roger Crisp)也指出:“正如《伦理学原理》在本世纪初的伦理学讨论中处于中心位置一样,托马斯·斯坎伦的《我们彼此负有什么义务》也将成为争论的焦点,而且会成为二十一世纪伦理学灵感的一个源泉。”[4]
虽然斯坎伦的著作受到很高的评价,但是也招致了很多批判。对斯坎伦契约主义思想的一种标准反对就是:契约主义的可拒绝性原则无论在判断道德不正当上还是在解释道德动机的问题上,都是多余的,这种反对被称为“多余性反对”(The Redundancy Objection)。这种反对最初由菲利普·佩迪特(Philip Pettit)提出,柯林·麦金(Colin McGinn)、西蒙·布莱克本(Simon Blackburn)等人也做了相似的批判[5-7]。
按照杰西·苏克恩(Jussi Suikkanen)的观点,多余性反对可分为两种:程序性多余性反对(The Procedural Redundancies)和动机性多余性反对(The Motivational Redundancy)*参见Jussi Suikkanen, “Contractualist Replies to the Redundancy Objections”, Theoria,2005,vol.71, No.1, pp.38-58。在这篇文章中,杰西·苏克恩对程序性多余性反对做了进一步的划分,所以程序性多余性反对用了复数形式“The Procedural Redundancies”表示。本篇文章没有按照杰西·苏克恩的意思,对程序性多余性反对做进一步划分,但仍然采取了杰西·苏克恩的表达形式。。前者认为契约主义在判断道德不正当问题上是多余的,后者认为契约主义在解释道德动机问题上是多余的。针对多余性反对,迈克尔·瑞金(Michael Ridge)、菲利普·斯特拉顿(Philip Stratton-Lake)等人都依据他们自己所理解的契约主义做了反驳[8-9]。斯坎伦的契约主义,针对契约主义的多余性反对,以及与其相关的反驳,在政治哲学界形成了辩证相争的态势,并促进了契约主义的发展。理清这一“否定之否定”的脉络进程,对于真正理解斯坎伦的契约主义有重要意义。
二、程序性多余性反对和动机性多余性反对
对斯坎伦道德契约主义的反对中,最有代表性、也最值得辨析、辩驳、严肃对待的,即为多余性反对。这种多余性反对首先是以程序性多余性反对的样态出现的。程序性多余性反对的基本观点可以表述为:斯坎伦依据可拒绝性原则来解释道德不正当是多余的,人们往往是根据不正当行为本身所具有的道德理由来理解道德不正当。
契约主义的反对者认为,按照斯坎伦关于道德不正当的规定,人们是按照可拒绝性原则来判断一项行为是道德不正当的,而其拒绝该项原则的理由却是行为本身暗含的道德理由,如这项原则允许的行为本身是不公平的,谋杀是残忍的等。一旦明白了拒绝这项原则的道德理由,我们就明白了道德理由是判断这种行为不正当的真正根源。可拒绝性原则对于判断道德不正当没有增添任何新的东西,因而是多余的。由于持这种观点的反对者认为斯坎伦的契约主义在判断道德不正当的程序上是多余的,所以这类反对被称为“程序性多余性反对”。
以折磨婴儿为例,反对者认为,斯坎伦对道德不正当的判断经历了以下推理过程,可以用以下三个命题表述:
(a)折磨婴儿是残忍的,因此禁止折磨婴儿的准则是没有人能够合理拒绝的。
(b)禁止折磨婴儿的准则是没有人能够合理拒绝的。
(c)折磨婴儿在道德上是不正当的。
其中,(a)命题对于斯坎伦来说是隐含的前提,(c)命题是关于道德判断的结论,(b)命题则是斯坎伦契约主义判断道德不正当的依据。据此,反对者认为:实际上,对(c)的判断是直接来源于(a)中折磨婴儿是残忍的这一道德事实,(b)在判断折磨婴儿在道德不正当性上实际上是多余的。
迈克尔·瑞金对这种程序性多余性反对做了全面的概括:由于一种行为拥有特征F*F是迈克尔·瑞金(Michael Ridge)在其对多余性反对的著名论述中采用的表达方式,F作为一个未知数出现,特征F等同于“某种特征”,用F指代应该意在突出这种特征的负面性,特征F(foul)表征的是一种行为在道德内容上的错误。,无论何时允许这种行为的准则都是能够合理拒绝的。这种行为是不正当的仅仅是由于这种行为包含特征F,不是由于特征F使得允许这些行为的准则得到合理拒绝[10]。
对于这种程序性多余性反对,不少哲学家通过分析契约主义可拒绝性原则性质,以此证明契约主义道德准则不会面临程序性反对。如菲利普·斯特拉顿就认为斯坎伦不会面临程序性多余性反对。他反驳程序性多余性反对的依据在于,他认为其他反对者错误地理解了斯坎伦的理论:斯坎伦的契约主义准则不是告诉我们什么使得某些行为成为道德上不正当的,而是为了说明为什么这些行为是道德上不正当的;契约主义的准则的提出也不是为了说明道德不正当的根据,而是为了描述道德不正当的性质[9]。
但是菲利普·斯特拉顿并不能挽救斯坎伦的契约主义。程序性多余性反对的核心并不在于如何理解契约主义准则的性质,其问题的关键在于斯坎伦提供了一种判断行为正当与否的哲学说明,反对者和斯坎伦的分歧在于判断一种行为正当与否的理由是否在于可拒绝性原则。
不同于程序性多余性反对,动机性多余性反对的基本观点是:契约主义对道德动机的说明是多余的。斯坎伦认为,可拒绝性原则不仅是判断行为正当与否的根据,也提供做或者不做这种行为的理由。但是反对者认为,我们是从行为本身所包含的道德理由来寻找做或者不去做这种行为的理由。例如,折磨婴儿这种行为本身所包含的残忍性就提供了充分的道德理由不去参与折磨婴儿的行为,在这种情况下,把禁止这项行为的理由诉诸于契约主义的道德动机就是多余的。
斯坎伦在《我们彼此负有什么义务》一书中所举的例子更能说明这种动机性多余性反对。斯坎伦指出:“当我首次读到彼得·辛格有关饥荒的著名文章,并感受到其论证的谴责力时,打动我的不仅仅是孟加拉国生活在饥荒之中是一件多么恶劣的事情。我强烈体会到的是一种非常不同的感觉,即考虑到我是多么容易帮助他们,而我没有帮助他们,对我来说这就是不正当的。”[1]152斯坎伦在这个例子中指出,他受到谴责的原因是某些具体的道德考虑:饥荒使得人们处于一种非常恶劣的状态,而在这种情况下我却没有帮助他们。在这种情况下,把受谴责的理由诉诸于可拒绝性原则就没有说服力。而且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不去做某些行为的理由也是某些具体的道德考虑,如这种行为会伤害某人的感情,这种行为要求别人付出的太多,以及这种行为是不公正的。在这些情况下,道德动机都不是来源于可拒绝性原则。
在这种动机性多余性反对提出之后,哲学家菲利普·斯特拉顿提出了一种解决办法,他认为斯坎伦应该放弃不正当具有提供理由性质的这一核心目标[9,11]。通过这种解决办法,我们就可以避免这种动机性多余性反对。菲利普·斯特拉顿的这种观点遭到了诸如迈克尔·瑞金、戴维德·麦克鲁顿(David McNaughton)以及罗林(Rawling)等哲学家的反对[10,12]。迈克尔·瑞金认为,菲利普·斯特拉顿要求斯坎伦通过放弃一些核心目标的方式来避免动机性多余性反对的观点是错误的;斯坎伦如果放弃不正当具有理由给予的性质,也就放弃了契约主义关于道德动机的说明。斯坎伦整个理论的主体部分都依赖于对于道德动机的说明,这也意味着斯坎伦不可能放弃不正当具有提供理由的性质。
上述两种多余性反对如果成立,就意味着斯坎伦的整个理论体系是没有意义的,而它们的共同特点就是以非个人的道德理由来作为判断行为的对错和寻找行为的道德动机的根据,反对者们没有看到斯坎伦是从个人理由出发来回答上述两个道德哲学基本问题。如果从个人理由出发理解斯坎伦的道德契约主义,就会发现契约主义作为一种实质性道德理论足以依其自身反驳上述两种多余性反对。
三、对多余性反对的反驳——基于“个人理由”
坚持多余性反对的人有一个共同观点,即认为斯坎伦可拒绝性原则的根基在于行为本身的道德价值,柯林·麦金在《理由与非理由》(Reasons and unreasons)一文中将这层意思表达得最为清晰,他指出:“当我说一种行为是不正当的时候,我可能暗示这项行为不能向其他人证明其正当性。但这种行为不正当唯一所表达的意思是它在道德上是不能得到合理证明的,道德价值是判断这项行为不正当的唯一根据。”[6]在麦金看来,斯坎伦的可拒绝性原则实质上是以这种道德价值为根基的,因此,这种道德价值才是判断行为正当与否的最终根据。但是麦金实际上误解了斯坎伦的理论,斯坎伦的契约主义实质上走的是一条不同的线路,即为了判断一种行为正当与否,我们必须从相关的个人观点(而非行为本身的道德价值)出发来评判。斯坎伦指出:“为了判定在环境C中,做X是否是不正当的,我们就应该考虑支配一个人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如何可能的原则,并且追问,允许一个人在这些环境下做X的任何原则,由于那条理由,是否有理由被拒绝。”[1]195在这里,判断做X是否正当的根据必须从支配个人的原则出发,也就是说契约主义可拒绝性原则的根据在于拒绝该项原则的理由必须是个人的,否则这项原则就不能被用于判断行为正当与否的根据。斯坎伦指出,契约主义的主要特征在于“它坚决主张道德原则的可证明正当性仅仅取决于不同个体拒绝该原则的理由以及可以替换它的另一种选择”[1]230。“拒绝一条我至今为止考虑过的原则的所有根据,都出自于一个占据了该原则应用于其中的那些境况中的某一个位置的个人会拥有的一般理由。”[1]229斯坎伦强调的是要从生活在不同环境下的个体(包括行为者和可能受行为影响的人)来考虑有理由拒绝的原则问题,我们考虑拒绝该项原则的依据在于行为广泛实施在孤立个体中所产生的不同效果。
对此,迈克尔·瑞金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迈克尔·瑞金认为斯坎伦坚持判断行为正当与否的根据是一项原则对孤立的个体(personal)所产生的不同的效果,而反对者则是从非个人(impersonal)的理由出发来寻求判断道德正当与否的根据。斯坎伦在《我们彼此负有什么义务》中划分了这种个人理由(personal reasons)和非个人理由(impersonal reasons),他对二者的区分是通过对一般理由(generic reasons)的论述来完成的。他指出:我们是基于一般理由来反对一项原则。一般理由首先必须是个人理由,这些理由反映的是,一个个体在某种环境下,有理由想要什么。但是由于无法确切知道在各种不同情形中个体所占据的不同位置,因此在考虑承认或拒绝某项原则的理由不是特定个体所拥有的精确理由,而是处于某种环境的个体普遍所拥有的理由。因此一般理由同时也是一种普遍的理由,它是“我们可以看到的,人们由于他们的境遇而拥有的理由,用一般的词语及诸如他们的目标、能力和它们所处的条件来表现其特性”[1]186。这种一般理由实质上就是个人的一般理由,是从个人立场出发提出的普遍理由。个人根据这种一般理由从相关的立场出发,拒绝接受某项原则作为他们自己实际思考的根据,也拒绝承认它是其他人可以用来证明行为正当性的根据。而非个人理由是对象自身所具有的价值,这种理由并不涉及我与其他人的关系。
这种个人理由和非个人理由也分别被迈克尔·瑞金称之为主体相涉(agent-relative)的理由和主体无涉(agent-netural)的理由[8]。例如,一个主体有理由通过自己的努力提高自己及家人的生活水平是主体相涉的理由,而每个人都有理由去提高社会总的福利水平就是主体无涉的理由。其中斯坎伦注重的是前者,而持多余性反对观点的人则根据后者对其进行反驳,这样就形成了对斯坎伦的一种缺少根基的因而也是错误的批判。非个人理由并不提供可拒绝性原则的根据。例如,人们没有理由破坏原始森林,仅仅是由于破坏原始森林的行为本身是错误的(这种行为会导致生态环境的破坏),而不是由于破坏原始森林与个体的权利和利益相矛盾。但这种主体无涉的理由可能会在确定有理由拒绝的其他根据时确实起到一定作用。例如,对于个体而言,一个人可能会去考察原始森林,从而为科学发展做贡献,那么从他个人的理由来看,就有理由拒绝只考虑经济利益而破坏原始森林的行为。但是这些表面上的个人理由来源于对非个人价值的判断,这些非个人价值就是原始森林是珍贵的,其能够为科学发展提供素材。契约主义的反对者认为这种非个人的理由和我们应该帮助自己的同胞,不去做伤害他们的行为的理由一样。他们给出的理由就是这些行为会导致一些人被伤害。因此,在契约主义的反对者看来,在这种情况下,把不去伤害同胞的理由诉诸于该行为不能被合理拒绝的原则所允许就是多余的。
四、“个人理由”与“我们彼此负有什么义务”
这两个领域之所以有着不同的道德理由,是由于二者所涉及到的价值本性不同。当我们说某种行为是错误的或者对于某个人来说是错误的,这里表达的是从行为本身的道德价值出发,我们有理由去避免这种行为的发生。但是当这种行为涉及到人与人之间的道德领域时,上述有理由去避免这种行为发生的原因不仅仅涉及到行为本身的道德价值,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作为理性的人有理由去避免被伤害。当然作为理性的人有理由避免被伤害可能有别的理由——如这个人是个科学家,这个人掌握很多技能等,但认识到人的价值在于人是一种理性主体存在才是处理人与人之间道德领域的核心。作为理性主体的人从其本身出发就有理由拒绝不正当的行为。同时,所有人都是作为理性主体存在的,个体不仅仅认识到自己作为理性主体所拥有的道德理由,还要认识到别的主体所拥有的道德理由,要从可拒绝性原则出发处理自己和别的理性主体的关系。同时,这两个领域之所以有着不同的道德理由,还在于二者所涉及道德范围不同。斯坎伦的道德契约论关注的并非是广义的道德,并非所有的被称为“道德”或“不道德”的行为都可以纳入契约主义的范围。例如,当一个不称职的家长,或者做一个不忠实的朋友,是一种道德上的缺失,斯坎伦的契约论并没有很好地解释对这些事情的谴责。它们在道德上是错误的,并不是因为它们违反了他人合理的期待[13]。再比如,同性恋也不涉及对他人的责任与义务,但仍然是一种道德上错误。斯坎伦的道德契约论中道德的范围是通常所称的“道德”的一个特殊部分,是对一个较为狭窄的道德领域的说明,它涉及的是人们之间的“责任”与“义务”,比如要信守诺言、不能撒谎、反对杀戮等,它们是调节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道德规范。斯坎伦之所以从个人理由出发理解契约主义,是由于斯坎伦将自己的契约主义限制在这种人与人之间的责任与义务领域。
在斯坎伦所规定的狭义道德领域内,不仅仅能够通过个人理由理解一项行为是不正当的缘由,还可以通过不断追问个人理由来分析某些抽象的道德名词,使得这些词语蕴含的道德意义表现得更为具体和规范。假设有准则P允许一些残忍的行为,因此我们有理由拒绝准则P,当我们寻找拒绝P的理由时,了解相关信息的个体就会区分出准则P允许的哪些行为是残忍的,这些残忍的行为所带来的可能的严重后果是什么。这些行为给某些主体带来的可能的严重后果使得潜在的受害者按照主体相涉的理由要求行为实施者去避免这项行为。契约主义者从受害者的主体相涉的理由出发,可以宣称是准则P给他们带来的可能的、具体的严重后果,使得准则P所允许的行为是不能得到合理辩护的,因而准则P所允许的行为是道德不正当的。契约主义通过这种主体相涉的理由来分析“残忍”这一抽象的道德名词,一方面保留了这一道德名词所蕴含的伦理学意义,另一方面也为这个名词提供了具体的、规范性的意义[14]。因此,当意欲从主体相涉的理由来理解斯坎伦的可拒绝性原则时,契约主义能够帮助我们理解某些行为不正当的复杂理由,这样可拒绝性原则就不是多余的,而是在判断行为不正当上起着重要的作用。
这种主体相涉的理由不仅仅可以用来反驳多余性反对,还可以用来证明契约主义作为一种实质性道德理论的优越性。后果论者通常把促进最大化的善以及将伤害降到最低来作为基本的、独立的道德准则来使用。后果论者的证明模式从根本上说是集合性的:某种确定的价值其总量要被最大化[1]230。它根据给少数人以昂贵的代价却给其他更多的人带来足够多的利益来证明其正当性。而契约主义的证明模式则充分尊重个人利益:个人要求权这个一般理由,相对于整体利益的理由,在道德论证上更强而有力,因此一项原则如果容许甚至要求人们伤害一小部分人来增进总体的利益,就是可以被合理地反对的[15]。相对于后果论,斯坎伦的契约主义的优势在于:它赋予每个人的合理理由在道德论证上具有同等程度的重要性,它避免牺牲他人的较小利益来实现最大化的利益。作为一种实质性道德理论,契约主义不是多余的。
参考文献:
[1] SCANLON T M.What we owe to each other[M]. 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8.
[2] 陈代东.略论托马斯·斯坎伦的契约主义[J].伦理学研究,2005(3):94-97.
[3] WALLACE R J.Scanlon’s contractualism[J]. Ethics,2002,112(3):429-470.
[4] CRISP R.Contractualism and the good[J]. Philosophical Books,2000,41(4):235-253.
[5] PETTIT P.Doing unto others[J]. 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1999,25(6):7-8.
[6] MCGINN C.Reasons and unreasons[J]. The New Republic,1999,220(21):34-38.
[7] BLACKBURN S.Am I right?[J]. 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1999,21(2):7-24.
[8] RIDGE M.Saving Scanlon:contractualism and agent-relativity[J].The Journal of Political Philosophy,2001,9(4):472-481.
[9] STRATTON-LAKE P.Scanlon’s contractualism and the redundancy objection[J]. Analysis, 2003, 63(1):70-76.
[10] RIDGE M.Contractualism and the new and improved redundancy objection[J].Analysis, 2003,63(4):337-342.
[11] STRATTON-LAKE P.Scanlon, permissions, and redundancy response to McNaughton and Rawling. [J]. Analysis,2003,63(4):332-337.
[12] MCNAUGHTON D,RAWLING P.Can Scanlon avoid redundancy by passing the buck?[J].Analysis, 2003,63(4):328-331.
[13] 斯坎伦.何为道德:道德的动机和道德的多样性[J].陈真,译.江海学刊,2005(3):22-28.
[14] SUIKKANEN J.Contractualist replies to the redundancy objections[J].Theoria,2005,71(1):38-58.
[15] 邓伟生.斯坎伦的契约主义与总计问题[J].世界哲学,2016(4):127-1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