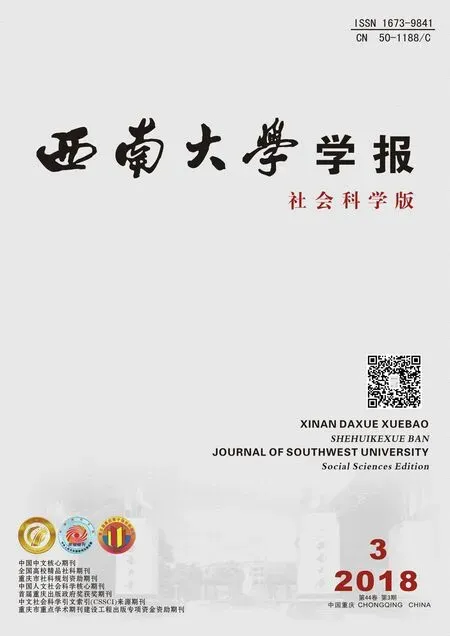农业面源污染环境税规制机制研究进展
周 志 波,张 卫 国
(1.西南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重庆市 400715;2.重庆市地方税务局 办公室,重庆市 401121)
一、环境税规制农业面源污染研究总体情况:从不对称信息取得突破
面源污染,也叫非点源污染,是相对于传统的点源污染而言的。当前,世界各国已经公认面源污染是导致生态环境恶化的一个重要原因,其危害性在某种程度上超过了点源污染,典型的例子就是农业径流中的化肥和农药,以及大城市的车辆排放等造成的污染,而农业则是面源污染的主要来源,并且对环境污染的贡献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早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欧美发达国家就已经开始关注农业面源污染问题,并设计了诸如环境税、污染排放许可、休耕补贴、污染处理处置技术、污染防治法律法规等政策工具解决面源污染问题[1]。但是,与点源污染形式不同,面源污染很难通过设计一种单一的政策工具加以有效规制,因为确定各个污染个体对环境污染的贡献度(或者说对环境质量的影响)十分困难。因此,最实用的办法就是,要么依靠调节投入、产出或技术标准等与污染变量间接相关的指标,通过一种非直接的税收(或罚款)传导机制对污染要素的投入、污染技术的使用行为进行惩罚;要么花费很高的成本安装监控设备,确保个体污染者的排放水平可以准确观测,对污染者的排污行为实施“精准惩戒”[2]。税收机制在点源污染治理领域取得了重要进展,环境税、生态税、污染税、碳税、排污税等系列环境政策工具被世界各国广泛应用,大量的理论研究和许多国家的实践证明,税收机制在规制面源污染领域具有可行性。
环境税最初被广泛应用于点源污染的防控,相关的研究也大多局限于点源污染领域。经济学家们普遍承认,诸如环境税(排污税)、可转让排污许可交易等环境政策工具,通过价格机制促进点源污染减排的能力很强并且十分有效[3]。在环境经济政策工具的共同作用下,点源污染问题得到有效控制,但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面源污染问题却愈发突出,并逐渐成为污染损害的主要来源。许多环境问题,尤其是由农业引起的环境问题,都可以归入面源污染问题[4]。农业面源污染作为面源污染的主要形式,逐渐引起了学术界和实务界的关注,特别是由于农业导致的湖泊、流域的面源污染问题,让一些学者开始思考将环境税(补贴)、罚款等在点源污染控制方面运行良好的环境经济制度移植到农业面源污染的管控实践中。实际上,自1970年代开始,一些学者开始关注污染防控中的不对称信息问题,并开始研究将环境税用于面源污染的控制[5]。
一般情况下,环境税的有效实施要求对每一个污染排放者的排污水平具有完全信息,但农业面源污染不同于点源污染的一个最大特征就是无法有效观测农业生产者个体的污染行为,污染管制机构一般只能获得关于总体环境污染排放水平的信息,而不能获知个体污染排放水平[6-7]。环境管制面临严重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一方面可能源于观测每个个体的排放水平在技术上有困难,另一方面则可能由于观测和掌握这些污染排放的信息成本非常高[8]。信息不对称问题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环境税等政策工具在面源污染防控领域的应用[9],但有关环境税治理农业面源污染的研究,最早也是从信息不对称方面取得突破的。大量文献表明,面源污染问题可以利用基于污染排放噪声观测的激励相容机制,在这一方面Holmström[10]的研究非常具有代表性。但是,Holmström建立的理论模型依赖于三个假设。首先,总的面源污染排放量可能存在一些测量误差(measurement error),但一定能够公开进行观测。这样就可以计算和征收环境税(实际上是一种排污税):每一个污染者根据监测到的排污水平,按照环境税税额标准,计算缴纳相应的环境税。第二,在选择污染排放水平时,面源污染者博弈遵循古诺-纳什(Cournot-Nash)行为模式,同时进行排污决策。换言之,面源污染者之间不存在先发优势,也不存在寡头、垄断等市场势力,他们具有同质性,同时进行决策,确定农业面源污染排放水平。第三,污染者是风险中性的。当每个排污主体都承担污染排放增加的边际成本时,环境税就是有效率的[11-12]。这样得出的结论是,即便在不对称信息条件下,规制者没有关于个体污染排放的信息,利用环境税调节面源污染是可行的,并且可以实现有效率的配置。实际上,污染者个体污染排放相关的信息毫无价值,合意的环境税制度设计并不需要这些信息,这一结论已经被很多在该领域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学者的相关研究所证明。例如,Cabe和Herriges[13]建立的静态模型,McAfee和McMillan[14]、Laffont[15]等引入逆向选择的研究,都再次验证了这一结论;同时,Lewis[16]研究了机制设计(mechanism design)在环境污染规制问题中的应用;Chambers和Quiggin[17]将这一方法应用于农业面源污染的研究中,属于该领域的开创性研究,并且验证了上述结论。此后,很多学者都循着这一方向解决农业面源污染的不对称信息问题,即环境税(或者补贴)不针对单个面源污染者个体的排放,而是根据污染者集体的污染排放总水平对每一个体征税。例如,D’Amato和Franckx[18]就专门研究了环境税(排污税)规制农业面源污染过程中寻找污染代理变量的问题。他们假设存在多个风险规避型的污染源,并设计了一种标尺竞争机制(yardstick competition scheme)规制面源污染,这种规制机制依赖于污染源的集体绩效(总体排放)和污染者的平均绩效(个体排放)之间的差异,其规制效率是否高于针对单位污染排放征收的排污税,取决于污染监测中一般随机因素协方差矩阵的结构;更为重要的是,如果污染面源数量足够多,这种标尺竞争机制通常优于线性的环境税机制。
二、环境税规制农业面源污染效率问题的质疑:个体理性的局限性、污染排放的随机性和污染主体的合作共谋
现有的大量文献表明,环境税规制农业面源污染确实有效率,并且可以通过合意的环境税机制设计实现经济效率和社会福利的整体改善。当然,也有一些先前的研究对环境税的效率问题持否定态度,这种质疑主要来源于两个方面:第一,污染主体必须清楚他们的个体排放行为对于污染排放总水平测量的影响,而排放主体众多是农业面源污染的重要特征,因而要满足这一条件就变得十分困难。我们可以将这种质疑归纳为“污染个体理性的局限性”。实际上,环境税效率低下,是因为污染者无法了解他们个人对环境监测结果进而对他们收入或收益的影响[13]*总体看来,对于诸如农业径流等造成的面源污染问题,较低的环境税可能是一种比较有吸引力的环境政策工具。但有一点必须明确,这一结论只有当规制者(政府)为污染者提供较低的环境税或设置在庇古税率水平上的排污税两种政策选择时才成立。如果政府不能为污染者提供环境政策选择,就不可能对农业面源污染者集体进行有效观测,也就无法实现环境税对农业面源污染的有效规制。。Karp[19]研究了环境税规制面源污染的额外税收负担问题,结果发现:如果规制者能够观测到单个面源污染者的排污水平,那么基于污染排放总水平征收的环境税可以实现社会最优的污染排放,但要保证环境税机制的有效性,每个面源污染者都必须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决策对总体污染排放水平的影响;当污染者对环境税政策采取策略性行为时,他们的税收负担可能会低于对个体污染排放水平征收环境税的情况,因此面源污染者更加偏好于规制者无法观测到个体排放水平的情况,即便不对称信息让规制者不得不对总体污染排放水平征税。第二,环境税一般适用于对污染排放量的随机噪声测量(noisy measurement),根据有噪声的随机测量值征收环境税,给污染者带来了风险,而这种风险会使得社会成本非常高,即便污染者是规避风险的。我们可以将这种质疑归纳为“污染排放的随机性”。从理论上讲,采用非线性激励机制能够减少对环境税效率问题的质疑,但这样的机制往往会导致自相矛盾的结果,最典型的就是最优政策要求无限处罚但处罚率为零[20]。激励机制的设计也依赖于精确的测量误差的概率分布特性,而这种特性又使得在实际操作层面十分困难。
关于环境税规制面源污染的研究,特别是证实环境税机制有效的文献,一般都没有考虑面源污染者之间的沟通协调和合作共谋因素。如果放松污染者合作共谋的假设,可能结论会有所差别,早期引入污染者合作共谋因素的有关文献,往往认为环境税规制面源污染的有效性值得商榷[21],并且合作共谋对研究结论具有关键性影响。由此引出对于环境税机制效率问题的第三个质疑理由——污染者合作共谋。实际上,放松非合作行为假设本身是否重要,与面源污染集体的性质有关联。特别是,许多农业问题涉及当地流域的污染问题,污染者之间合作共谋的方法在减少污染排放方面可能会有价值。农业生产者之间的合作是必不可少的,他们建设并保护湿地和池塘以捕捉硝酸盐排放量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例子。此外,在欧洲和其他国家有一种环境政策趋势,就是使用依赖于污染者合作的自愿协议或契约,实现污染减排的目标。从工作场所、小额信贷机构到农业环境组织的不同情境,农业面源污染者之间存在的合作都有据可查。早期Kandel和Lazear[22]的研究表明,因社会道德带来的同行压力为污染者采取合作共谋策略提供了有效的激励。De Janvry、McCarthy和Sadoulet[23]研究了污染者之间的合作共谋质量如何依赖于监管和执行成本。值得注意的是,现有的监管机构往往在社会层面和专业技术层面依赖于地理位置上较近的主体之间的合作,这实际上就是一个同行监测(peer monitoring)的制度框架。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荷兰就成立了农业合作社,以协调政府为防止过量施肥导致富营养化问题而采取的各项政策措施[3]。
有关同行监测(peer monitoring)的文献表明,当污染主体之间共享规制者(政府)不能观测掌握的相关信息时,签订协议进行同行监测就有价值[24],有利于面源污染的减排和控制。与规制者(政府)相比,污染主体在污染排放方面拥有很多的信息优势*比如,印度的许多污染工业都位于工业园区,这里的水污染具有典型的面源特征。规制者(政府)可能观察到园区边界的公共排放,但是在同一工业区内的企业在监控其他企业污染排放方面比比地理位置上相隔较远的环保机构更加方便,也更具有合理合法性。Sterner(2003)分析了印度西部古吉拉特邦(Gujarat)安格莱什沃(Ankleshwar)工业园区在园区内建立的企业自愿监控同行的效应。这个园区有400多个化工厂,安格莱什沃工业协会采用了包括提供相关信息、征收小额排污费、罚款在内的多种手段迫使会员企业清理污染,以提升工业园区的整体形象和声誉,为招商引资工作添彩。。这种同行监测的优势已被一些实证研究用于公共财产资源管理[25]。地理上的邻近有助于检测可能的共谋偏离(违约),合作也需要对不合作的违约方实施制裁的能力,否则这种合作共谋就是一种松散的、没有任何保障的“口头协议”,会对面源污染者的决策行为模式造成重大的影响,因为每一个参与合作共谋的污染者都可能为了获得额外的利益而背离“协议”。从这一点上说,将违约者排斥在共同项目(例如农业合作、专业协会、联合研究)之外的威胁可以形成一种有效的行为约束,阻止污染者对合作的偏离或者违约,保证污染者之间的合作共谋行为具有稳定性。众所周知,在重复的博弈中,如果污染主体的贴现因子足够高,诸如社会孤立(social seclusion)等可信的威胁,将有助于维持污染主体之间的合作。农业面源污染主体如果在博弈中同时决策、同时行动,也可能出现合作的结果,例如社会协作,或者合作社共享共同的生产要素。如果污染主体停止减排合作,通过使用触发策略(trigger strategy)并威胁恢复到非合作的二次博弈均衡状态,他们就可能在排放和减排方面维持合作[26]。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对合作共谋的背离无法有效观测,某些合作共谋仍然是可持续的。在这种情况下,对农业面源污染排污行为的惩戒制裁必须针对污染者集体,并且总体排放水平高于设定的某一阈值。在均衡状态下,没有人偏离设定的排放水平,但如果污染排放监测是随机的,惩戒制裁却是无效率的,这与Green和Porter[27]的研究结果吻合。但事实上,关于环境税规制农业面源污染的政策机制,多数文献采用直接对个体污染排放(或其代理变量)征税的办法,其结论大多数情况下不支持环境税机制能够有效规制农业面源污染。与此同时,由于污染者之间合作共谋可以更好地消化环境税提高带来的影响,在不完全信息条件下,这必然导致更高的环境税水平,但实践中规制者(政府)往往更愿意采取相反的政策。因此,监管者(政府)必然会采取这样一种折中的政策,即对合作共谋的污染者群体设置过高的环境税,而对不合作共谋的污染者群体设置过低的环境税,进而导致这样的结果——在污染者可能合作共谋的情况下,环境税在经济学意义上有效率的结论可能并不成立。这实际上是理论结果与实践选择之间的一种“悖论”,也是实证分析与规范分析的一种“背离”。在不预设价值判断的前提下,从社会资源配置最优的角度讲,应当对合作共谋程度高的污染群体征收高税率的环境税;但从社会公平角度这一否定的结果要求引入其他的政策工具加以配合,以更好地检视污染者群体的行为。
三、环境税规制农业面源污染研究的最新进展:合作共谋和团队绩效条件下的有效规制
早期引入合作共谋因素的有关研究表明,环境税机制的有效性严重受限于不完全信息和合作共谋,考虑合作共谋的研究一般都对环境税机制的有效性提出了质疑。但是,近些年来理论界对这方面的质疑做出了越来越多的回应,特别是引入实验经济学方法的有关研究,论证了环境税规制农业面源污染有效率的结果可以延伸到污染者合作共谋的情况下,并且在更低的环境税税率下就可以实现同样水平的污染排放总量控制[2]。在环境税规制农业面源污染的研究中,对于污染者之间沟通协调、合作共谋的关注最早源于制度经济学对集体道德风险(moral hazard)、个体隐藏行为(hidden actions)和团队绩效激励机制(collective performance mechanism)的相关研究。
集体道德风险,特别是其中个体的隐藏行为,导致个体最优行为与集体最佳行为之间存在巨大差异。在有关面源污染规制的研究中,很多文献提出建立多种工具相结合的政策体系规制农业面源污染,其中最典型的就是“两部规制工具”(two-part instruments),这样的政策工具组合一方面具有最优庇古税机制的特点,另一方面又对污染监控和政策执行具有最低的要求,但很多研究却发现激励机制的设计不当也可能引致道德风险问题。近年来Goetz和Martínez[28]等人的研究再次证实了这一问题。他们对面源污染的税收/补贴两部规制工具的设计和适用性进行了分析,并利用西班牙东北部地区的畜禽养殖数据,实证研究了最优的税收/补贴政策组合。结果发现,这种机制将税收和补贴政策结合起来,对不利于污染控制的行为征税,对有利于污染控制的行为补贴,但却导致了道德风险问题,因为污染不仅仅取决于污染投入,还与污染投入的方法高度相关。实际上,这一问题很早就引起了理论界的广泛关注,并促进了相关研究的快速发展,很多学者致力于设计基于集体绩效的激励机制,以实现集体决策和行为达到理想水平,典型的例子就是激励相容的公共产品筹资机制(incentive-compatible public goods funding mechanisms)在公共经济学中的应用[29],收入共享、强制契约和竞争性竞赛等团队绩效机制在契约理论中的应用[30]以及环境污染控制政策工具在环境经济学中的应用[31]。团队绩效激励机制的理论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团队成员没有明显的协作努力这一假设条件。但实际上,团队绩效机制往往最适合甚至实际应用在个体成员可以沟通并且合作共谋具有可能的条件下[32]。因此,无论从理论还是政策的角度讲,沟通协调对团队绩效机制效率的影响都应当从实证方面加以研究,以确认是否存在为实现某一集体结果而进行沟通合作有利可图的情况。
作为解决群体道德风险的一种途径,自Segerson[31]开始,很多经济学家都十分关注农业面源污染政策工具设计问题,这些工具通常都是基于整个污染集体排放导致的环境污染水平[32-33]。在Segerson的一般激励机制下(以下简称“Segerson机制”),如果面源污染总排放(对污染者集体的测量)超过(或者低于)预定的排放目标,那么每个面源污染者都支付罚款(或者接受补助)。这种激励有两种形式:对超标排污实施非连续但固定的罚款机制,或者就相对于排放目标的面源污染边际变化的征税/补贴机制。面源污染者的支付义务(税费负担)依赖于所有污染者的减排努力,而不仅仅依赖于其自身的减排努力,并且与随机的环境反应有关系。从理论上讲,Segerson提出的这种目标或强制契约方法(targeting or forcing contract approach),与Holmstrom[10]提出的强制契约机制类似。Shortle和Horan[34]指出,在流域污染治理问题中,基于环境污染排放总量的规制方法的最佳适用条件有四个:第一,面源污染主体数量不太多;第二,面源污染者具有同质性;第三,已有污染监测机制;第四,面源污染排放与环境损害之间的时滞不太长。然而,交易成本低、反应速度快等条件反映了理想的合作共谋的形成机制:单个面源污染者的支付义务(可能是税收、也可能是罚款),依赖于整个污染集体的减排努力,所有的污染者都有激励形成一个“减排联盟”并对减排策略达成一致意见,以减少他们的预期税费负担。此外,Hansen[3]从理论上证明,在Segerson提出的非预算平衡的基于环境污染水平的环境税规制机制中,面源污染者有激励促进集体减排,污染者有动机和理由共同做出努力,让污染排放低于目标排放水平。因此,虽然基于环境污染水平的机制可以通过将信息要求限制在监控环境污染水平而非个体污染排放水平,进而提升政府(污染规制者)的视野,但一个基本的关注点在于污染者之间的合作可能让面源污染规制机制变得无效率。当然,也有相关的研究坚持认为面源污染的规制应当针对污染者个体行为实施,而不应针对集体绩效执行。Horan[35]分析了当规制者与污染者之间存在环境关系和随机事件相关概率方面的不对称信息问题时,环境税规制面源污染的问题。他们比较分析了污染者风险中性和风险规避两种情形,结果发现最优的环境税应当针对个体污染者的排污行为征税,并且规制者应当提供其他的激励机制以保证污染者采用减少排放的生产技术。
实验经济学的发展为面源污染规制问题的研究提供了新的工具和方法[36-38]。现代实验经济学文献大致有三条脉络:一是检验个体决策理论的实验,二是检验博弈论假说的实验,三是检验产业组织问题的实验[39],而前两者都与面源污染规制问题的研究高度相关。在利用实验经济学方法研究面源污染规制问题的早期重要文献中[40-41],污染者之间通过沟通进行合作共谋的因素尚未纳入分析框架。此后,Spraggon[42]在污染者不合作共谋的假设下分析了Segerson机制的效应,Vossler等[21]分析污染者通过沟通交流采取合作共谋策略时Segerson机制的效应,在该领域具有重要影响。不过,Vossler等重点通过实验经济学的方法检验无约束力的沟通(nonbinding communication),或者说所谓的“廉价谈判”(cheap talk)对团队绩效机制的影响,结果表明沟通协调、合作共谋对于污染者集体绩效和行为有着重要影响,提高了固定罚款、税收/补贴等相关规制机制的效率却容易导致过度遵从问题。Poe[43]用实验经济学的方法,检验了在农业面源污染者可能合作的情况下,基于环境污染的规制机制的效率,结果发现环境税/补贴、环境税/补贴配合固定罚款的机制容易导致污染者的过度遵从,最终的污染总排放远远低于社会最优水平。此外,以Millock和Salanie[2]等为代表的学者,以Segerson机制为逻辑起点,将污染者的沟通协作、合作共谋因素引入环境税规制面源污染的分析框架,结果表明在污染者可能合作共谋的情况下,环境税在规制面源污染方面是有效的政策工具。总结相关文献,很多研究认为“廉价谈判”有助于排除一些令人难以信服的均衡结果[44],拓展均衡结果的集合[45],并且有利于避免出现误解或者合作失败导致的无效结果[46]。特别是基于实验经济学的相关研究表明,“廉价谈判”有助于散播有关集体最优策略的信息,增进集体成员之间的信任并改变对其他成员行为的预期,增加决策主体收益并改善其结构[47],从而让污染者之间的合作共谋更具有稳定性。但是,就沟通本身而言,其介入并不必然保证出现有效的结果,并且在某些情况下“廉价谈判”并没有任何的影响[48]。尽管在自愿公共服务筹资机制(voluntary public goods funding mechanisms)中,沟通的作用已经得到论证,但却很少有实证方面的证据表明,在一些目的在于实现理论上最优个人行为的机制中,沟通具有积极的作用[49]。实际上,在农业面源污染规制机制中,集体绩效和沟通合作就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在这种情境下,由于农业面源污染排放具有分散性,并且无法通过合理的成本对污染排放实施精准监测,集体道德风险问题是普遍存在的;特别是,由于复杂的新陈代谢机制、随机的环境因素、多样的面源污染源头等,监管机构很难通过农业生产者的投入或者土地利用情况测算其面源污染排放水平。此外,一些学者还利用实验经济学的方法研究了影响农业面源污染的因素等问题[50-51]。例如,Rong等[52]以北京市密云水库地区为研究对象,采用田野实验和问卷调查的方法分析了影响农业面源污染排放的因素,结果发现土地利用类型、降雨分布特征、农业生产活动是影响密云水库周边土壤农业面源污染物浓度的主要因素。
四、文献评述及研究展望
环境税规制污染问题的有关研究最早起源于Kneese[53]等人关于水资源问题的关注。此后,环境税的相关文献大量涌现,其理论成果在世界各国先后付诸实践,自1990年代开始的环境税改革就是理论成果转化为制度实践的成功代表。但是,大部分研究特别是早期的研究基本都只关注工业污染排放等点源污染问题,而对面源污染问题的关注不够。这可能主要源于两个方面的因素:一方面,面源污染具有不同于点源污染的特征,其分散性、随机性和不易观测性等特点使得面源污染的规制问题更为复杂,在点源污染问题的研究不够成熟的背景下,分析面源污染问题具有较大的难度;另一方面,从技术层面讲,由于不对称信息、道德风险、合作共谋、风险偏好等因素的存在,环境税规制面源污染的数理经济模型构建比较困难,即便能够建立数理模型,但模型结论可能在经济学上没有任何意义,更难以解释现实的问题,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环境税规制农业面源污染的相关研究的深入发展。直到Plott[54]关于税收和交易外部性机制的开创性研究为面源污染规制机制的构建奠定了理论基础,Segerson等学者建立了环境税规制面源污染的激励机制(即Segerson机制),有关环境税与农业面源污染治理的研究才得以迅速发展,并取得了比较丰硕的成果。
总体上看,有关环境税规制农业面源污染的研究在以下几个方面做出了较大的贡献:第一,将税收规制污染问题的激励机制由点源污染向面源污染领域拓展,并从理论上论证了环境税(排污税)或税式支出(补贴)机制对于面源污染问题有效,并在制度和政策层面具有可操作性。第二,鉴于面源污染独有的分散性、随机性、不确定性、不易观测性等特征,从不对称信息问题入手考虑数理模型构建,成功地解决了环境税规制面源污染面临的激励不相容问题,并论证了通过合理设计制度要素,环境税在面源污染治理领域具有效率。第三,随着理论研究的逐步深入,学者们将道德风险、风险偏好、合作共谋等因素逐步纳入分析框架,让经济模型更加贴近经济运行实际,并在更加贴切的假设基础上,证明了环境税是规制农业面源污染问题的合意政策工具,特别是引入合作共谋因素后,很多研究实现了面源污染者个人理性和集体理性的激励相容、经济效率和社会福利的激励相容。第四,鉴于在现实世界特别是在存在不遵从问题的地区,并不存在真实的数据表明农业面源污染者如何对环境政策机制做出何种反应,近年来有关环境税规制农业面源污染的相关研究逐步引入实验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从行为经济学和心理经济学的角度,在实验室条件下模拟环境税规制农业面源污染机制的运行情况,让研究结论更具有科学性和可靠性,并在一定程度上回应了关于环境税规制农业面源污染问题的质疑。设计得当的实验至少可以揭示人们是否认同并采取与经济学理论一致的行为,以应对这些政策激励。如果农业面源污染主体没有像经济学理论预测的那样对政策激励做出反应,那么,就应该怀疑所运用的经济理论在解释和预测污染主体行为方面的能力和有效性。正如Vossler等[21]所强调的那样,实验也可能对理论模型假设条件的适切性做出提示,并提出政策修改建议以避免该领域研究的潜在问题。
但是,现有的文献也存在一些不足和缺陷,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很多文献无法同时将产品市场和污染规制同时纳入分析框架,一般的研究都为了便于分析不考虑面源污染者产品市场结构的问题,弱化了研究结论的说服力,影响理论研究向政策实践的转化。实际上,产品市场结构(或者说产品市场的寡头、垄断等市场势力因素)、产品市场和销售收入的不确定性等因素,与政策制定者的工具选择和污染者的生产排放选择可能都高度关联,并对环境税机制规制农业面源污染的效率和机理具有重要的影响。产出的不确定性可以显著地影响面源污染排放水平,这一点是研究者不容忽视的。第二,环境税规制农业面源污染的研究从不对称信息问题取得突破,但一般的文献主要考虑纵向信息不对称(规制者与污染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而几乎不考虑横向信息不对称(污染主体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但在现实经济运行中,纵向和横向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同时存在,忽略横向信息不对称的研究结论在可靠性方面有所局限。第三,现有的研究一般假设农业面源污染者是同质的,这种同质主要包括产品同质、风险偏好同质、行为决策同质等,很少考虑面源污染者之间的异质性问题,进而让分析模型和框架更加贴近实际经济运行。第四,虽然实验经济学方法的引入让农业面源污染规制相关的研究取得了新的突破和进展,但由于这一方法对实验条件、实验设计等的要求很高,相应的研究成本也比较高,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实验经济学方法在这一领域的应用和发展。
可以大胆预测,未来有关环境税规制农业面源污染的研究将在以下几个方向取得新的突破:一是实验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和分析范式大有可为。采用实验经济学的方法,对农业面源污染者的沟通协作、合作共谋等行为进行研究,有很大的应用空间,并且可能获得一些意想不到的结果。二是内生化外生变量是该领域研究的一个重要发展方向。特别是将古诺竞争、合作共谋等一些原本假设具有外生性的变量和因素内生化于理论模型之中,可以更加清晰地认识环境税规制农业面源污染的机制和效应。三是政策机制对经济行为的“反馈效应”是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考虑环境税制度的“反馈效应”(interaction effects),研究环境税机制是否还会引致农业面源污染者行为模式的改变,以及会在何种程度上影响被规制者的决策行为。
参考文献:
[1] REVENGA C, MOCK G. Freshwater biodiversity in crisis[C]//Earth trends world resources institute: 1-4. Revenga, Carmen, and Greg Mock. Freshwater biodiversity in crisis. earth trends. Oct. 2000. 25 Oct. 2008.
[2] MILLOCK K, SALANIE F. Nonpoint source pollution when polluters might cooperate[J]. Topics in economic analysis & policy. 2008,5(1):1233-1233.
[3] HANSEN L G. A Damage based tax mechanism for regulation of non-point emissions[J]. Environmental and resource economics. 1998, 12(7): 99-112.
[4] CAMACHO-CUENA E, REQUATE T. The regulation of non-point source pollution and risk preferences: An experimental approach[J]. Ecological economics. 2012,73(15):179-187.
[5] HARFORD J D. Firm behavior under imperfectly enforceable pollution standards and taxes[J].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1978, 5(1): 26-43.
[6] XEPAPADEAS A P. Observability and choice of instrument mix in the control of externalities[J].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1995, 56(3): 485-498.
[7] HORAN R D, SHORTLE J. S. Endogenous risk and point-nonpoint uncertainty trading ratios[J]. American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2017, 99(2):427-446.
[8] WARDROPPER C B, GILLO S, RISSMAN A R. Uncertain monitoring and modeling in a watershed nonpoint pollution program[J]. Land use policy, 2017, 67:690-701.
[9] SHORTLE J S, ABLER D G, HORAN R D. Research issues in nonpoint pollution control[J]. Environmental & resource economics,1998,11(3-4):571-585.
[10] HOLMSTRÖM B. Moral Hazard in Teams[J]. Bell journal of economics, 1982, 13: 324-40.
[11] MERAN G, U. Schwalbe. Pollution Control and Collective Penalties[J]. Journal of institutional and theoretical tconomics, 1987, 143 (11):616-629.
[12] SEGERSON K. Uncertainty and Incentives for Nonpoint Pollution Control[J].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1988, 15 (3):87-98.
[13] CABE R, J A HERRIGES. The regulation of nonpoint source pollution under imperfect and asymmetric information[J].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1992, 22 (3): 134-146.
[14] MCAFEE R P, MCMILLAN J. Optimal contracts for teams[J].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view, 1991, 32(8): 561-77.
[15] LAFFONT J. Regulation of pollution with asymmetric information[C]. Nonpoint source pollution regulation: isssues and analysis. Cesare Dosi and T. Tomasi, eds., pp. 39-66. Dordrecht: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1994.
[16] LEWIS T. Protecting the environment when costs and benefits are privately known[J]. Rand journal of economics, 1996, 27(4) : 819-847.
[17] CHAMBERS R G, J QUIGGIN. Non-point source pollution regulation as a Multi-Task Principal-Agent problem[J].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59 (January 1996): 95-116.
[18] D’AMATO A, FRANCKX L. Nonpoint pollution regulation targeted on emission proxies: the role of yardstick schemes[J].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 policy studies,2010,12(4):201-218.
[19] KARP L. Nonpoint source pollution taxes and excessive tax burden[J]. Environmental and resource economics. 2005,31(2): 229-251.
[20] MIRRLEES J A. The theory of moral hazard and unobservable behaviour: Part 1[M]. Mimeo, 1974. republished in th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1999, 66: 3-21.
[21] VOSSELER C A, et al.Communication and incentive mechanisms based on group performance: an experimental study of nonpoint pollution control[J]. Economic inquiry, 2006, 44(4):599-613.
[22] KANDEL E, E P LAZEAR. Peer pressure and partnerships[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 1992, 100: 801-817.
[23] DE JANVRY A, N MCCARTHY, E SADOULET. Endogenous provision and appropriation in the commons[J]. American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1998, 80: 658-664.
[24] VARIAN H R. Monitoring agents with other agents[J]. Journal of institutional and theoretical economics 146 (1990): 153-174.
[25] OSTROM E. Governing the Commons: The evolution of institutions for collective action[M].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26] SPAGNOLO G. Social relations and cooperation in organizations[J].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and organization, 1999, 38: 1-25.
[27] GREEN E J, R H PORTER. Noncooperative collusion under imperfect price information[J]. Econometrica, 1984, 52: 87-100.
[28] GOETZ R U, MARTNEZ Y. Nonpoint source pollution and two-part instruments[J].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and policy studies, 2013, 15(3): 237-258.
[29] BAGNOLI M, MCKEE M. Voluntary contribution games: efficient private provisions of public goods[J]. Economic inquiry, 1991, 29: 351-366.
[30] NALBANTIAN H R, SCHOTTER A. Productivity under group incentives: an experimental study[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97, 87: 314-341.
[31] SEGERSON K. Uncertainty and incentives for nonpoint pollution control[J].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1988, 15: 87-98.
[32] HORAN R D. Ambient taxes under m-dimensional choice sets, heterogeneous expectations, and risk-aversion[J]. Environmental and resource economics, 2002, 21: 189-202.
[33] WEERSINK A, et al. Economic instruments and environmental policy in agriculture[J]. Canadian public policy, 1998, 24: 309-327.
[34] SHORTLE J S, HORAN R D. The economics and nonpoint pollution control[J]. Journal of economic surveys, 2001, 15: 255-289.
[35] HORAN R D. Ambient taxes under m-dimensional choice sets, heterogeneous expectations, and risk-aversion[J]. Environmental and resource economics, 2002, 21: 189-202.
[36] HEIDERSCHEIDT E, LEIVISKT, KLØVE B. Chemical treatment response to variations in non-point pollution water quality: Results of a factorial design experiment[J].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2015, 150(1): 164-172.
[37] KAPLOWITZ M D, LUPI F. Stakeholder preferences for best management practices for non-point source pollution and stormwater control[J]. Landscape and urban planning, 2012, 3-4(15): 364-372.
[38] WESSTRÖM I, JOEL A, MESSING I. Controlled drainage and subirrigation: a water management option to reduce non-point source pollution from agricultural land[J]. Agriculture, ecosystems & environment, 2014, 198(15): 74-82.
[39] KAGEL J. H. and Roth, A. E. The handbook of experimental economics[M]. 2016, Renmin university press, Beijing, China.
[40] ALPIZA F, REQUATE T, SCHRAM A. Collective versus random fining: an experimental study on controlling ambient pollution[J]. Environmental and resource economics, 2004, 29: 231-252.
[41] SPRAGGON J. Exogenous targeting instruments as a solution to group moral hazards[J].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2004, 84: 427-456.
[42] SPRAGGON J. Exogenous targeting instruments as a solution to group moral hazards[J].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2002, 84(3):427-456.
[43] POE G L. Exploring the performance of ambient-based policy instruments when nonpoint source polluters can cooperate[J]. American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2004,86(5):1203-1210.
[44] FARRELL J. Cheap talk, coordination, and Nash equilibrium[J]. Economic letters, 1988, 27: 209-214.
[45] FARRELL J, RABIN M. Cheap talk[J].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1996, 10: 103-118.
[46] AUMANN R J, HART S. Long cheap talk[J]. Econometrica, 2003, 71: 1619-1660.
[47] OSTROM E. A behavioral approach to the rational choice theory of collective action: presidential address[J]. American science association, 1997.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998, 92: 1-22.
[48] CROSON R, MARKS M. The effect of recommended contributions in the voluntary provisions of public goods[J]. Economic inquiry, 2001, 39: 238-249.
[49] DAVIS D D, HOLT C A. Experimental Economics[M].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3.
[50] MIN J, SHI W M. Nitrogen discharge pathways in vegetable production as non-point sources of pollution and measures to control it[J]. Science of the total environment, 2018, 613-614(1): 123-130.
[51] HUANG S Y, LIANG C J. A conceptual study on the formulation of a permeable reactive pavement with activated carbon additives for controlling the fate of non-point source environmental organic contaminants[J]. Chemosphere, 2018, 193(01): 438-446.
[52] RONG Q Q, et al. Field management of a drinking water reservoir basin based on the investigation of multiple agricultural nonpoint source pollution indicators in north China[OL/J]. Ecological Indicators, 2017, Available online. http://dx.doi.org/10.1016/j.ecolind.2017.02.033.
[53] KNEESE A V. The application of economic analysis to the management of water quality: some case studies[M]. Palgrave macmillan UK, 1974.
[54] PLOTT C R. Externalities and corrective policies in experimental markets[J]. Economic journal, 1983, 93: 106-1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