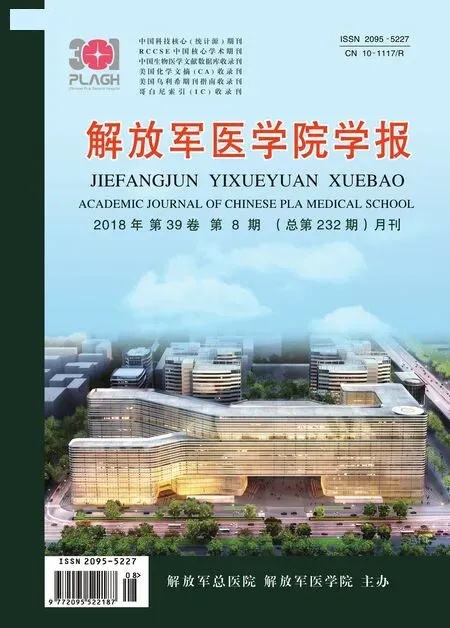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发病机制及预后评价的研究进展
陈亚东,汪建新解放军总医院,北京 00853;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警卫局保健处,北京 0007
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acute respiratory distress syndrome,ARDS)是指由心源性以外的各种致病因素所致的急性、进行性缺氧性呼吸衰竭综合征。尽管在ARDS病因和治疗上的研究有了令人瞩目的进展,但是其病死率依然居高不下[1]。ARDS发病机制复杂,致病因素众多,患者之间的病情差异非常大[2]。有一些治疗方法对于特定的患者可以取得很好的疗效,而对另一些患者却不尽如人意,如俯卧位通气策略的应用[3]。需要对ARDS的发病机制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发现患者之间的差异,找到准确的预后评价方法,才可以采取个性化的治疗方案,有效提高治疗效果。本文就ARDS的发病机制和预后评价方面作一综述,旨在为ARDS进一步的研究和治疗提供帮助。
1 发病机制的研究进展
1.1 病因学 1992年欧美ARDS联席会议(AECC)根据病因将ARDS分为肺内源性和肺外源性两大类[4]。引发肺内源性ARDS的主要病因有吸入、肺部感染(细菌、病毒、肺孢子虫等)、淹溺、有毒气体吸入、肺创伤[5];引发肺外源性ARDS的主要病因有肺外因素导致的脓毒症、重症创伤(胸腔以外)、体外循环、复苏时输液过量、胰腺炎[5]。
国内外学者发现肺内源性和肺外源性ARDS的病理生理机制存在多种差异。Menezes等[6]使用脂多糖(lipopolysaccharide,LPS)气管滴入和静脉输入制造出肺内源性和肺外源性ARDS的动物模型,并详细对比两者病理的差异。电镜观察下发现肺内源性ARDS的肺泡上皮细胞破坏和中性粒细胞凋亡,而肺外源性ARDS引起肺间质水肿,上皮和内皮层完整。Peres等[7]的研究发现,肺内源性ARDS透明膜厚而不连续,肺外源性ARDS的透明膜薄而均匀。肺外源性ARDS病理中Ⅷ因子表达减少,内皮损伤一致,而上皮完整并且细胞角蛋白AE1/AE3表达增加。临床的病理研究发现,相对于肺外源性ARDS患者,肺内源性的ARDS患者的肺部病理呈现更明显的肺泡萎陷、肺泡壁水肿、纤维蛋白沉积,只有在早期的肺内源性ARDS病理中可见胶原蛋白的数量增加[8-10]。肺内源性ARDS的病理改变主要是肺内实变,而肺外源性ARDS主要是间质水肿、血管充血以及肺泡的塌陷。PEEP会导致ARDS患者的呼气末容积增加,有助于肺外源性ARDS患者肺泡的复张、氧合的改善,而对于肺内源性ARDS患者,PEEP可能造成正常肺泡的张力过度升高,产生二次损伤。临床上可见PEEP治疗肺外源性ARDS的肺复张效果要比肺内源性ARDS更好,这一现象符合肺内源性和肺外源性ARDS的病理生理差异[11]。
肺内源性和肺外源性ARDS患者的生物标记物之间也存在明显的差异。Calfee等[12]对来自一项单中心研究的100例患者和一项多中心随机对照研究队列中的853例患者进行了对比研究。在这两项研究都发现,与肺外源性ARDS患者相比,肺内源性ARDS患者的血液生物标记物中肺上皮细胞损伤的标记物水平更高,而血管内皮损伤标记物水平更低。国内的研究也证实,患者的血清促血管生成素-2(Ang-2)水平,肺外源性ARDS组显著高于肺内源性ARDS组。患者的血清表面活性蛋白D(SP-D)水平,肺内源性ARDS组显著高于肺外源性ARDS组[13]。
1.2 遗传易感性 虽然ARDS的发作不呈家族式聚集,但其实质是一种对损伤的反应过程。临床证据表明,个人对于感染或是创伤的反应是具有遗传差异的。最初的基因学研究就是基于ARDS病理生理,聚焦于某种特定功能的遗传变异和在肺损伤反应中具有决定作用的基因,如血管紧张素转换酶(ACE)基因和表面活性蛋白(SP)。人类ACE基因包含一个多态性D等位基因,其与血浆和组织内ACE活性增高相关。研究表明,这种导致ACE活性增高的基因型在ARDS患者中表达频率更高,高于血管再通手术组的患者。这种强度的相关性,表明ACE的基因多态性在ARDS的发生和发展中起重要作用[14]。在SP-B基因密码子131的核苷酸1580上有一个多态性,在ARDS患者组中,C/T的表达有显著性差异。研究表明,该基因多态性和ARDS的易感性相关[15]。
随着研究进入全基因组时代,研究又发现了与ARDS相关的多个变异位点。Tejera等[16]进行了一项包括417例ARDS患者的单核苷酸多态性(single nucleotide polymorphisms,SNP)与ARDS发病率关系的研究。发现Popdc3降低ARDS风 险(OR值0.65),PDE4B、ABCC1和TNFRSF11A则升高ARDS风险。虽然直接原因尚不明确,但是作者认为可能是基因决定了代谢的情况从而影响患病的风险。Christie等[17]发现了一个新的创伤后ARDS危险因素基因位点,PPFIA1或liprinα,该位点影响肺损伤的机制尚不明确。除此之外还发现了158个位点可能与此有关,其中19个属于血小板反应蛋白和几丁质酶的家族,已被证明与ARDS的发病机制相关。Wei等[18]研究表明,在中国汉族人群中,一氧化氮合酶(NOS3)的单核苷酸多态性可能会改变基因表达,部分影响ARDS易感性。
Shortt等[19]对96例ARDS患者进行全外显子测序,确定了一系列潜在的SNP。其中3个SNPs(rs78142040,rs9605146和rs3848719)被证明与ARDS易感性显著相关。Kangelaris等[20]对29例ARDS合并脓毒症患者和28例单纯脓毒症患者进行比较,发现多种基因表达上调,并与中性粒细胞对感染反应相关。研究结果表明,中性粒细胞炎症反应相关通路可能与脓毒症导致的ARDS的早期发病机制有关。Wellman等[21]制作绵羊的ARDS模型,用PET检查肺部的代谢变化,同时对不同区域的基因表达进行检查,发现这些不同代谢的区域显示了基因表达的差异,其中表达变化最显著的基因是CXCL10。而研究表明,CXCL10直接导致中性粒细胞介导的肺损伤[22]。Nick等[23]首先对31名ARDS患者和19名健康志愿者的循环中性粒细胞基因组转录谱进行检测,用来描述干扰素刺激基因(ISG)表达特征,并将其分为高表达、正常表达、低表达3组,再检测120例ARDS患者的外周血中性粒细胞,发现ISG过高、过低表达的患者与正常表达患者组相比,呼吸机脱机时间、ICU住院时间、90 d死亡率等临床结果更差。
2 ARDS的预后评价指标
2.1 氧合指数 2012年的柏林标准,根据氧合指数将ARDS分为轻、中、重度[24]。对4 188例ARDS患者进行的Meta分析结果显示:轻度ARDS患者住院死亡率为27%(24% ~30%),中度ARDS患者为32%(29% ~ 34%),重度ARDS患者为45%(42% ~ 48%)。幸存者中机械通气中位时间,轻度ARDS 5(2 ~ 11) d、中度7(4 ~ 14) d、重度9(5 ~ 17) d。在一个单中心研究中,81例ARDS患者因病情进行了人工体外膜肺氧合(ECMO)支持治疗,37例氧合指数下降,44例氧合指数改善,下降组较改善组住院死亡率更高(48.7% vs 22.7%)。使用Logistic回归,氧合指数的变化是一个独立预测医院死亡率因素[25]。另一项研究中,436例接受无创通气治疗的ARDS患者,氧合指数与呼吸机支持强度和ICU死亡率相关。根据柏林标准将患者分为轻度、中度和重度3组,无创通气的失败率分别为22.2%、42.3%和47.1%。氧合指数可以有效体现患者疾病的严重程度,准确预测ARDS患者的预后。
2.2 生物标记物 在ARDS的病程中,免疫系统和凝血纤溶系统会被激活,炎症损坏肺泡上皮细胞和血管内皮细胞共同组成的屏障,包括多种以肺损伤为核心的细胞损伤途径:内皮损伤、上皮损伤、促炎损伤、凝血、纤维化及细胞凋亡。ARDS的急性期生物标记物主要分3类,一是来源于肺泡上皮细胞损伤标记物:晚期糖基化终产物受体(RAGE)、人型细胞特异性膜蛋白(HTI56)、涎液化糖链抗原(KL-6);二是血管内皮细胞的损伤标记物:促血管生成素(Ang)、细胞间黏附分子-1(ICAM-1)、血管性血友病因子(vWF);三是各种炎性因子:白细胞介素(interleukin)、肿瘤坏死因子(tumor necrosis factor,TNF)[26]。这些生物标记物都对ARDS预后评价有价值。
血浆中Ang-2可能是反映肺损伤的变化的特异标记物[27]。也有研究表明,血浆中sRAGE升高的程度与肺泡弥漫损害程度以及ARDS患者的28 d、90 d死亡率相关[28-29]。在ARDS患者中血清KL-6的升高与肺损伤及死亡率密切相关[30-31]。Chen等[32]研究发现,在脓毒症肺炎患者与脓毒症ARDS患者以及对照组之间,BMP-15、CXCL16、CXCR3、IL-6、NOV/CCN3等炎性因子的血中水平存在明显差异,ARDS患者组中血IL-6、CXCL16水平明显更高,且与住院天数和感染发生率相关。另外有一些抗炎因子也参与ARDS过程,如IL-1Ra、IL-10、sTNF-RI/sTNF-RII,但其与ARDS患者发病率和死亡率的关系还需要进一步研究。虽然许多生化指标已应用在ARDS的预后评价上,但还没有任何一个生物标记物在对ARDS预后评价中达到理想的效能。Terpstra等[33]对19个与ARDS死亡率相关的生物标记物进行Meta分析,其中IL-4、IL-2、Ang-2和KL-6这四种生物标记物的OR值最高,分别为18.0、11.8、6.36和4.29,但是纳入研究的病例数都比较少。可能是因为炎症对于内皮或者上皮的损伤在时间和空间上往往出现交叉重叠,而且生化指标物的浓度是动态变化的。目前为止,还没有一种单一的临床特征或生物标记能够可靠地预测ARDS的结果[34]。
2.3 生物标记物联合检测 联合多种生物标记物,有助于提高敏感性和特异性,获得更高的预后评价效能。Fremont等[35]研究了192例创伤患者(其中107例为ARDS患者,其余85例为对照组)的血浆标本,21种生物标记物被纳入研究范围,将其中7种生物标记物(BNP,RAGE,胶原肽3,Ang-2,IL-8,IL-10,TNF-α)联合作为诊断ARDS的依据,诊断准确率可达86%。Calfee等[36]使用潜在分层分析法(latent class analysis,LCA),对两组独立的ARDS患者队列进行研究。研究列出27个临床指标和8个生化指标(SP-D、vWF、sICAM-1、IL-6、IL-8、sTNFr-1、PAI-1、protein C),作为影响ARDS的重要变量。根据这些变量将ARDS分为两型,相对于1型,2型患者的IL-8、IL-6、sTNFr1、Ang-2和RAGE更高、休克和脓毒症的发病率也更高,PEEP的治疗效果更差,90 d病死率也更高,预后更差。该研究团队又再次扩大研究范围,加入了1 000例ARDS患者的一个研究队列,依然使用LCA方法,再次证实存在两型ARDS,并且2型ARDS的患者相对于1型患者预后更差[37]。
Wong等[38-39]采用了类似Calfee等[36]的方法,使用临床指标、生化指标、基因标记物,病死率敏感性为94%,特异性为56%,阳性预测值为50%,阴性预测值为95%;在随后的队列研究中进行验证,校正后的诊断策略敏感性85%,特异性60%,阳性预测值61%,阴性预测值85%。Maslove等[40]进行了类似的研究,通过此方法将患者分为两型,其中1型患者炎症相关的免疫调节基因表达水平更高,两型之间还存在临床及激素、神经垂体激素、肾上腺素等相关基因表达的差异。
2.4 多项临床指标联合评价 虽然联合多种生物标记物进行预后评价的准确性更高,但是许多生物标记物并不是常规检查项目,联合临床特征等项目也可以得到令人满意的评价效能[41]。Zhang[42]使用LCA方法,分析943例ARDS患者的年龄、心率、体温、收缩压、舒张压、血浆钠、碳酸氢盐、血浆钾、血清白蛋白和氧合指数,并将其分为血流不稳定组、血流稳定组和中间组,其中血流不稳定组的90 d病死率明显较另外两组高。Mikacenic等[43]联合临床特征和多种血生物标记物建立了两种预测脓毒症ARDS患者28 d死亡率的模型。Wang等[44]发现ARDS诊断后24 h内粒细胞淋巴细胞比值NLR高(>14)可独立预测ARDS患者预后不良。Jabaudon等[45]联合sRAGE和其上游基因的SNP,对ARDS的患病风险有预测作用。Luo等[46]分别分析肺内源性和肺外源性ARDS患者住院病死率的预测因素,发现虽然病死率相似,但是预测因素存在显著差异。肺以外的脏器功能衰竭与肺外源性ARDS患者的病死率相关,与肺内源性无关;感染严重程度与肺内源性ARDS患者的病死率相关,与肺外源性无关。进一步证实了两种ARDS之间病理生理机制是不一样的。
3 结语
ARDS是一种由临床症状和病理生理反应组成的一个综合征,并不是一种疾病,在临床上的表现千差万别。关于ARDS发病机制的研究已经进入新的领域,基因组学、代谢组学、蛋白组学等研究成果不断涌现。但迄今为止尚未找到一个高效能的预后评价变量。未来的趋势应是联合临床特征、实验室检查以及多种生物标记物等多个变量进行量化计算分析,以发现ARDS患者之间的差异,对ARDS患者进行精准预后评价,采用个体化治疗手段,提高ARDS患者的治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