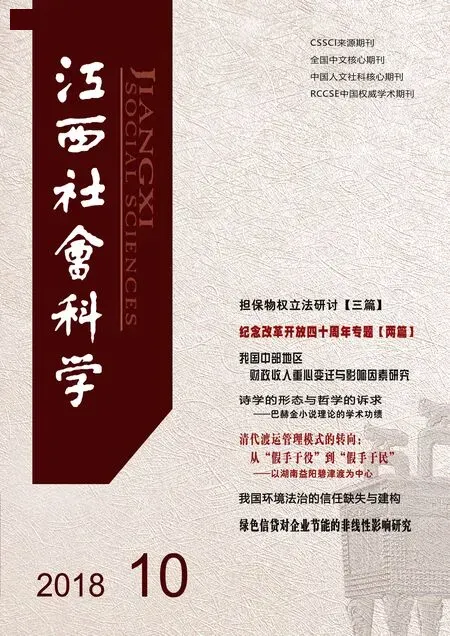中国礼貌文化研究的范式及理论建构
国际礼貌研究始于Lakoff在1973年提出的三条礼貌规则——不要强加、给予选择和友善[1]。之后,学者们提出一系列有关礼貌的语用学理论,主要包括20世纪末Brown和Levinson的面子理论[2]、Leech的礼貌原则[3]、Fraser和Nolen的“会话契约说”[4]、Fraser的“社会规范说”[5]、Aijmer的框架理论[6],以及21世纪初Spencer-Oatey的人际关系管理论[7]、Arundale的面子构建理论[8]、Locher和Watts的“关系活动论”[9]等。综观这些研究我们发现,现有的礼貌理论几乎都是由西方学者在西方文化背景下提出的,而关于中国文化中礼貌现象的研究大多集中在对西方理论的调整、修改或补充上。可以说,到目前为止,学界对中国文化背景下礼貌现象的原创性研究仍旧十分匮乏。然而,中国作为东方文明的代表,有着与西方截然不同的文化,中国式礼貌也必然有着不同于西方式礼貌的独特内涵,因此有必要对中国式礼貌的文化独特性展开专门研究,这不仅有利于深化我们对中国式礼貌的认识,也有助于促进国际跨文化交流。
此外,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尤其是21世纪以来,国际礼貌研究在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上也发生了一些转变。本文将结合这些转变探讨当前应该如何对中国式礼貌进行原创性研究及理论建构。我们认为,要深入挖掘中国式礼貌的文化独特性,需要以中国传统的礼文化为基础,用建构观的视角对礼貌现象进行审视,此外,还要特别重视汉语本族语成员的理解和判断(即交际参与者视角),具体研究方法可以采用会话分析研究方法对自然发生的真实语料进行分析。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揭示中国式礼貌的深刻内涵和独特本质。
一、以中国传统礼文化为基础
礼貌研究初期,学者们致力于提出具有文化普遍性的礼貌理论,其中最具影响力的当属面子理论和礼貌原则。面子理论认为,面子是礼貌概念的核心,所谓礼貌,就是要最大限度地降低对面子的威胁。该理论的提出基于两个普遍性假设——“面子”和“理性”:首先,个体都具有正面面子和负面面子,而且随时可能遭到威胁;其次,说话人被赋予根据交际目标选择语言策略的精确模式。面子理论问世后迅速引起强烈反响,但很快就受到挑战,尤其是该理论中礼貌的“策略性”本质和“负面面子”概念被质疑对其他文化,尤其是东方文化,缺乏解释力。例如,Ide区分了两种不同的礼貌:策略性礼貌和程式化礼貌。策略性礼貌是交际者实现交际目标的手段,与交际意图紧密相关;程式化礼貌与个体在某一等级社会中的角色和义务有关[10]。日本文化侧重后者,即判断某一言语礼貌与否要看其是否符合当前等级关系和交际情景所期待的共享规约。Matsumoto指出,日本文化不强调个体的独立性和自主权,即所谓的“负面面子”,而是强调个体在某一团体中与其他成员的关系以及被其他成员接纳和认可的程度。[11]Mao指出,由于中国文化对团体和谐的重视超过个体自由,“面子”更是一种社会现象,而非“个体的心理需求”,同时,对“关系”的强调也说明“负面面子”的不适应性。[12]与面子理论不同,礼貌原则把礼貌理解和归纳为六条准则:策略准则、慷慨准则、赞誉准则、谦虚准则、一致准则和同情准则。同样,该理论的文化普遍性也受到质疑。顾曰国指出礼貌原则并不能完全解释中国的礼貌现象。他从中国传统文化出发,对Leech提出的策略准则和慷慨准则从行为动机层和会话表达层进行了修正,提出符合中国文化的贬己尊人准则、称呼准则、文雅准则、求同准则等准则。[13]
不难发现,人们对经典礼貌理论的质疑和挑战大多集中在中西文化差异方面[14],这说明不同文化中礼貌的内涵是不同的,这使学者逐渐从寻求具有普遍解释力的礼貌理论转向对礼貌文化独特性的关注和研究。因为不同文化传统深刻影响着内部成员对礼貌的认识和理解,因此我们对中国式礼貌进行研究时,要首先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找解释的线索和资源,而与中国现代礼貌联系最密切的当属中国传统的礼文化[15],正如顾曰国所说,“现代的‘礼貌’与古代的‘礼’是有历史渊源的”[13]。
众所周知,礼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古代的“礼”是一种社会制度或一套行为法则。《礼记》谈到中国古代“礼”的起源:“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以穷,使欲不穷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是礼之所起也。”也就是说,礼起源于人类的欲望和欲望难以满足之间的不平衡,“先王”划分人与人之间的差别界限,使人的欲望不要越过这个界限而得以满足,因此“礼”也成了平乱获治之本,“天地者,生之始也;礼义者,治之始也”(《荀子·王制》)。[13]由此可见,中国古代的“礼”是维护社会等级差别的一种社会制度或行为法则。
当代中国的“礼貌”显然不能等同于古代的“礼”,但不可否认,中国传统的礼文化对当代中国的礼貌文化产生非常深刻的影响。虽然如今“礼貌已不再作为维护现行社会等差的行为法则,而是作为不分差别、供人们效仿的行为规范”[13],但和古代的“礼”一样,现代“礼貌”的关键要素之一也是“尊敬”。《墨子·经上》把古代的“礼”解释为“礼,敬也”。《曲礼上》中也有类似的论述:“夫礼者,自卑而尊人。虽负贩者,必有尊也,而况富贵乎?”同样,“贬己尊人”也是中国当代礼貌的一个重要方面,这一点不仅被顾曰国明确列为中国礼貌原则的一个准则,也得到了一些实证研究的证实。例如,对恭维言语行为进行的会话分析研究表明,“贬己尊人”的文化制约着当代中国人对恭维进行回应的方式。[16]
当然,“贬己尊人”只是中国传统礼文化影响现代中国式礼貌的一个方面,要深入全面地揭示中国式礼貌的内涵,就要从中国传统礼文化中汲取更多更丰富的营养。例如,在下面这个交际过程中出现了一种中国特有的、不同于西方的礼貌现象,要解释这种现象出现的原因,就要从中国传统礼文化中寻找线索。
A:这是给你的,我看你需要。
B:你这是干嘛?
A:没什么好东西,你就戴吧。
B:那哪行呀,这得多少钱呀?
A:不值钱,你就戴吧。
B:不行不行,我得给你钱。
A:我说了不值钱,挺适合你的。
B:真不好意思。
A:你就别客气啦。
B:那谢谢啦!
这是一个典型的中国文化背景下人们送礼物和收礼物的交际过程。A送给B一条项链作为礼物,B并没有马上接受,而是表达了拒绝。面对B的拒绝,A并没有放弃,而是继续坚持把礼物送给B,然而,B依然没有接受A的礼物,这样给予——拒绝的模式持续出现,直到A再一次坚持,B才真正接受A的礼物,并表达感谢。很显然,这一过程完全不同于西方文化中给予礼物——接受礼物并表达感谢的发展路径。对中国人而言,直接接受别人给予的礼物是不礼貌的,只有经过两到三次拒绝之后再接受才是礼貌的;对于给予礼物的人来说,在遭到对方首次拒绝时不能放弃,而要坚持,只有持续坚持到对方接受才是礼貌的。
那么如何解释中国文化中这种特有的礼貌现象呢?我们可以从中国传统礼文化倡导的 “真诚”和“平衡”两个维度去理解。对A而言,因为要表现出真诚,他必须反复多次地给予礼物,哪怕遭到B的不断拒绝。对B而言,他要确保A是真诚的才能接受这个礼物,因此他会通过反复拒绝来验证A是否真诚。同时,在此过程中,A和B都必须做出一些“平衡”。对A而言,一方面要保证这个礼物不是强加给B的,另一方面又不能让B觉得A认为他非常欠缺或想要这个礼物。对B而言,一方面要不能因为拒绝接受礼物而伤害A的面子,另一方面又不能让A觉得自己贪得无厌。正是基于以上方方面面的因素,A和B的交际过程才会出现多个给予——拒绝的回合[17]。
由此可见,中国传统礼文化为我们研究中国式礼貌提供了丰富的解释资源,因此,要对中国式礼貌进行原创性研究和理论建构,我们需要以中国传统的礼文化为基础,从中寻找中国式礼貌的历史演变线索或形成因素,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发现中国式礼貌的独特本质,才有可能提出具有中国文化独特性的礼貌理论。
二、采用建构观视角
传统礼貌研究的另一个特点是普遍采用规约观视角。总体而言,礼貌的规约观认为礼貌话语就是符合某种社会规约的话语。比如,“社会规范说”认为:“每个社会都有一套由比较明确的规则组成的社会规范,这些规则对特定语境中的行为、事态或者思维方式做出规定。”[5]符合这些规范的行为被评价为积极的,违背这些规范的行为被评价为消极的。“会话契约说”认为,交际中人们受会话契约制约。会话契约指交际中基于双方社会关系,可依据语境变化进行调整的规则、权利和义务。礼貌就是根据会话契约的条款进行的交际活动。框架理论认为,规约化礼貌的运作机制,是交际者根据储存在头脑中的现成的礼貌范式对具体语境做出反应,这些礼貌范式是交际者在与周围环境尤其是与社会语境相互作用的过程中获得的。由于礼貌范式是基于特定社会文化背景形成的礼貌形式与特定语境的对应关系,因此判断某一话语是否礼貌必须要参照特定的社会文化规约。礼貌原则的各项准则实质上也是一系列人们在交际中需要注意并遵守的社会准则。即使是面子理论也没有脱离对社会规约的观照。因为交际者判断面子伤害程度、选择礼貌策略所参照的三个变量(双方的社会距离、权势差异以及行为的强加程度)也是社会变量,需要从普遍接受的社会规约的角度来衡量。
不难看出,礼貌的规约观关注点主要在于礼貌话语是如何产出的或者说话人如何选择礼貌话语,因此是以说话人为导向的。然而,礼貌归根结底是一种存在于人们互动交往过程中的现象,没有人际互动,礼貌现象就不复存在,因此必须把互动交往过程中的所有参与者都纳入考虑范围。换句话说,我们不仅要考察说话人如何产出礼貌话语,同时也要考察听话人如何理解和判断礼貌话语。规约观的另一个问题是其所基于的编码—解码的交际观,即人们的交际过程就是说话人对其话语进行编码,听话人再对说话人话语进行解码的过程。然而,简单的编码—解码的交际观并不能解释人们互动交往的复杂过程,无法解释交际意义是如何在交际双方的互动过程中协商产生的。鉴于以上两点,礼貌的规约观视角已不再适用于新时期的礼貌研究。我们认为,要对中国式礼貌展开研究和理论建构,应该采用一种新的研究视角,即建构观视角。
建构观视角的核心思想是礼貌为交际双方在互动过程中共同建构的结果。这一新视角不再基于简单的编码—解码的交际观,而是基于一种新的交际观,即交际的联合共建模式。交际的联合共建模式认为,在交际过程中,交际双方互相制约对方对话语的理解和产出,进而共同推进会话不断展开,其共建的过程可以产生非累加的交际效果[18]。交际的联合共建模式充分考虑了交际的动态性、交际参与者的主动性,以及交际双方的协同合作和相互制约,因此更加符合人际互动交往的本质。基于这一互动的交际观,我们认为,采用建构观视角对中国式礼貌展开具体研究时,考察的内容应该是汉语本族语交际者如何在真实、具体的交际活动中共同作用、相互制约,实现礼貌的动态建构过程。具体来说,我们考察的内容不再是怎样的话语是礼貌话语,或者说话人根据什么来判断话语是否礼貌以及礼貌程度如何,而是交际双方是如何在具体会话过程中将某一话语建构为礼貌话语的。因此,礼貌不再是某一话语或行为的本质属性,而是由交际者在具体交际过程中建构起来的一种临时性特征。
例如,上例中B在第一次拒绝时说:“你这是干嘛?”如果从传统规约观的视角来看并不是礼貌的(甚至是不礼貌的),因为它既没有减少对交际对方面子的伤害,也没有增大对交际对方的赞扬,甚至起到相反的作用。然而,如果从建构观视角出发重新审视这句话,我们就会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在这个动态的交际过程中,B的话语“你这是干嘛”是在回应A的话语。由于A的行为是给予B礼物,B通过这句话执行的行为是拒绝A的给予(而不是质疑或批评A)。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别人给予礼物时要首先表示拒绝,如果立刻接受就会被认为是没有礼貌或者没有教养。正因为如此,B的话语并不是不礼貌的,而是非常礼貌的,因为B非常直接地拒绝了A的给予。换句话说,B正是通过拒绝的“直接性”把话语建构为礼貌话语。另一方面,A再次执行了给予的行为,并未对B的话语表现出任何不满,这表明A也认可B的回应是礼貌的,至少没有认为它是不礼貌的。也就是说,A通过继续执行给予这个行为(而没有挑战B话语的合适性)把B的话语“你这是干嘛”构建为礼貌话语。因此,在这个具体的交际语境中,B的话语“你这是干嘛”是礼貌的,而且这种礼貌性不是该话语的内在属性,而是由交际双方共同建构出来的。
由此可见,采用建构观视角对中国式礼貌现象进行审视,能够揭示礼貌协商的动态过程,能够得出更加客观、真实、符合交际实际的结论。
三、重视交际参与者视角
传统礼貌研究的第三个特点是普遍采用研究者视角。经典礼貌理论可以说是理论提出者基于自己对社会交往的认识和对礼貌现象的观察、思考提出的理论框架。例如,面子理论把“面子”这一概念作为阐释礼貌现象的核心,认为礼貌的本质是使用各种策略减少对面子的伤害。礼貌原则从社会基本价值观的角度阐释礼貌的本质,认为礼貌就是遵守一系列有助于人际和谐的价值观。“会话契约说”将礼貌的本质归结为人们对交际过程中各种契约、条款的遵守。事实上,这些理论无论从哪个角度对礼貌现象进行阐释,都是基于理论提出者自己的观察、判断和思考,因此不可避免地受到理论提出者“已有的内在的语言知识”[19]影响。由于社会、文化以及个体差异,很难保证理论提出者对礼貌现象的理解和判断与交际活动的参与者一致。尤其是作为大学教授的研究者大都属于中产以上阶层,他们对礼貌行为的判断难免带有自身所在阶层的烙印,因此不一定适用于大众阶层。
由于礼貌是一种文化现象,是全体社会成员共有的文化资源,因此,要研究某一社团中的礼貌现象,就是要研究这一社团的内部成员是如何共同认识和理解礼貌现象的,而不是看研究者个人的理解。因此,我们认为,要真正揭示中国文化背景下礼貌现象的本质,就要研究汉语本族语成员作为具体交际活动的参与者是如何理解交际过程中出现的礼貌现象的。也就是说,我们应该采用交际参与者视角(而非研究者视角)对中国式礼貌现象进行研究。事实上,这也是解决当前中国礼貌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促进中国礼貌研究健康发展的最重要、最关键的一步。正如文章开头所提到的,目前中国的礼貌研究仍停留在对西方理论的调整、修改或补充上,原创性研究仍旧十分匮乏,在现有研究中我们很难找到从汉语本族语成员视角出发的研究,也很难找到能够恰当解释中国式礼貌本质的理论研究。要突破目前的困境,首要任务就是要深入研究和挖掘汉语本族语成员是如何判断、理解和认识礼貌话语的。只有他们的判断才是真正客观的判断,也只有基于汉语本族语成员的共有判断,我们才有可能发现中国式礼貌的内涵,提出中国本土化的礼貌理论。
从交际参与者视角研究中国式礼貌,决定了我们首先要进行大量的实证性研究,然后才有可能进行理论建构。实证研究是自下而上的研究,即先收集、分析语料,再在语料分析的基础上总结规律;而理论研究是一种自上而下的研究,即研究者先提出一个理论,再用该理论去解释具体现象。我们之所以要先进行实证研究,是因为只有在实证研究中我们才能发现汉语本族语成员在具体的交际活动中对中国式礼貌现象的理解和判断,而只有依托这些实证研究得出的结论和证据,我们才有可能提取出中国式礼貌的内核,进而建构出能够真正解释中国式礼貌内涵的原创性理论。
从交际参与者视角研究中国式礼貌,也决定了我们进行研究的基本单位必须是由汉语本族语成员参与的完整的交际语篇,而不能是单个的、脱离语篇的孤立话语。因为只有在完整的交际语篇中,我们才有可能得知交际参与者是如何理解交际中所涉及的礼貌现象的,也只有在完整的语篇中,我们才有可能找到他们理解的证据。例如,要判定上例中B的话语“真不好意思”是否礼貌,我们就要将其放在完整的语篇中考察,而且要看交际参与者(而非研究者)是如何理解这一话语的(尽管很多时候二者的理解是一致的)。A将B的这一话语评价为“客气”,由此可见A把B的话语理解为礼貌的。在最后,B对A表达了感谢,并没有对A把他的话理解为“客气”表示异议,由此可知,B认可了A对其话语的理解,即承认自己的话语“多不好意思”就是在表达客气和礼貌。因此,我们可以说,B的话语“多不好意思”是礼貌的,而且这一结论不是基于研究者的判断,而是基于交际参与者的理解以及从交际语篇中找到的证据得出的。
从交际参与者视角研究中国式礼貌,能够尽可能排除研究者主观猜测对研究结果的影响,因此更加客观、合理,应该加以提倡。
四、采用会话分析研究方法
当采用建构观视角和交际参与者视角对中国式礼貌进行研究时,我们采用的研究方法也必须能够满足这些新视角提出的新要求。礼貌的建构观视角要求所采用的研究方法能够揭示礼貌的动态生成过程;交际参与者视角要求研究方法能够帮助研究者客观地提取交际参与者对礼貌现象的判断以及判断的依据。这些都是传统的礼貌研究方法,如语篇填充法、问卷调查、角色扮演和采访等不能达到的,因此我们提议采用会话分析这种基于自然发生的真实语料、没有理论预设、重视交际互动过程、并且能够获取客观证据的研究方法对中国文化中的礼貌现象展开研究。
会话分析是Harvey Sacks和Emanuel A.Schegloff于20世纪60年代在美国发展起来的一种社会学研究方法。它的诞生主要受到美国著名社会学家Erving Goffman有关社会秩序的思想和Harold Garfinkel的民俗方法学(ethnomethodology)的影响。[20]受前者的启发,会话分析认为人们的互动交际不是杂乱无章的,而是有内在规律和秩序的,会话分析就是对会话的内在组织结构和内在秩序的研究。受后者的影响,会话分析采用的是自下而上的归纳法,而非自上而下的演绎法。会话分析的研究目标是对人们执行行为和理解他人行为的方法进行描述,观察对象就是人们进行交际的过程本身。该研究方法反对基于假设的研究路径,因为这种先提出理论假设的研究路径会影响研究者对真实世界的观察,一些与研究假设不符的现象就会被过滤掉。相反,它采用的是在客观审视自然会话的基础上对观察到的规律进行概括的研究路径,因此是一种基于大量观察的归纳研究,而不是受某种理论假设驱动的演绎。[21]
会话分析的核心原则是会话的序列组织,这是会话分析研究方法区别于其他交际互动研究方法的根本特征之一。对会话分析而言,交际者当前的话轮受前一话轮的影响和制约,同时也影响着下一话轮的出现,因此,每一个话轮都不是孤立存在的,要理解某一话轮中话语所执行的行为,必须参考该话轮出现的序列位置。当同一话轮设计出现在不同的序列位置时,它执行的行为就会不同。[22]另外,会话分析强调使用自然发生的真实交际作为语料。它只认可通过录音或录像收集的自然发生的真实语料,不接受其他定性研究采用的语料收集方法,如访谈、观察记录、角色扮演等,因为这些方法都无法准确记录具体情境中发生的交际细节,有可能被一些理想化的形式所代替或者被研究人员人为操控,也无法真实全面地反映所观察现象的多样性和代表性,更无法像录音或录像一样回放来争取同行的审视和认可。因此,对会话分析而言,只有自然发生的真实交际才是可接受的语料来源。
为什么要提倡采用会话分析研究方法对中国式礼貌进行研究呢?第一,会话分析对自然发生的真实语料的坚持,保证了我们在进行中国式礼貌研究时,研究对象的确是发生在中国文化背景下的由汉语本族语成员所参与的真实交际活动,也可以保证我们发现的规律是中国文化背景下的礼貌规律,当某一规律不同于西方式礼貌时,我们可以判断这是中国文化中所特有的礼貌现象,因而也可以结合中国独特的文化传统对此做出解释。第二,会话分析对会话序列组织的重视可以保证我们对中国式礼貌现象的审视是动态的建构观。如上所述,会话分析认为,会话序列中的每一个话轮都既受前一话轮的制约,也同时影响着下一话轮的出现,即交际参与双方互相影响、制约对方的话语的产出和理解,这表明会话分析不仅把交际活动看作动态的过程,而且还提供了分析这种动态性的手段,因此运用这一方法,我们可以发现交际双方是如何在具体的交际活动中共同作用、相互制约,实现礼貌建构的动态过程的。第三,会话分析对序列组织的重视也可以保证我们对中国式礼貌的研究采用的是交际者视角。会话分析中对某一话轮所执行行为的判断主要依据交际对方对该话轮的理解,这一理解可以从交际对方在下一话轮的回应中看出。如果采用同样的方法来分析礼貌现象,我们就可以从下一话轮中看出交际对方是如何理解当前话轮中的话语礼貌与否的。而且,交际者对某一话轮中话语礼貌与否的正确理解、不解甚至误解都可以在之后的序列中得以展现和证实。这样,把对每一个“当前话轮”的分析综合起来,我们就可以发现在整个交际活动中,交际参与者是如何理解和判断其中涉及的礼貌现象的。
总而言之,会话分析研究方法能够满足建构观视角下和交际参与者视角下对礼貌研究的新要求,因此可以很好地用于对中国式礼貌文化的研究中。
五、结 语
在国际语用学界,礼貌研究已有近半个世纪的历史,也取得了非常丰硕的研究成果。遗憾的是,目前对中国文化中礼貌现象的原创性研究却寥寥无几,这导致我们对中国式礼貌内涵的认识还远远不够。本文主要探讨了在当前形势下应该如何对中国式礼貌进行研究和理论建构。从研究视角上说,我们应该以中国传统的礼文化为基础,采用建构观视角和交际参与者视角对具体交际活动中的礼貌现象进行审视;在研究方法上,我们提倡采用会话分析这种基于自然发生的真实语料、没有理论预设、重视交际互动过程、能从交际过程中获取证据的研究方法。只有采用客观、科学的研究视角和方法,才能得出合理、站得住脚的结论,才能真正揭示中国式礼貌的独特内涵,进而建构出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礼貌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