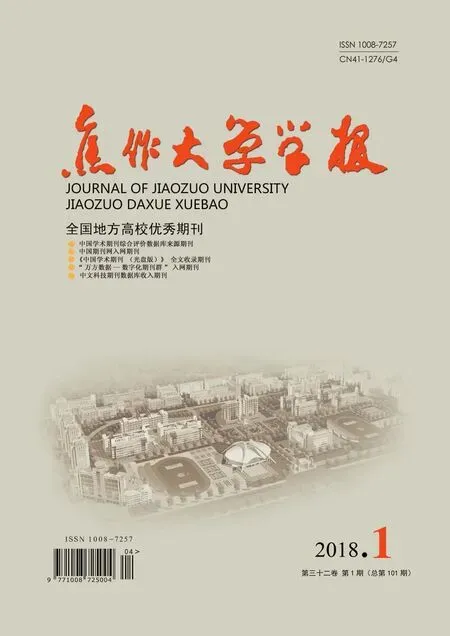基于大数据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汉绣保护研究
叶 鹏赵 跃赵敏芝
刺绣是按照预先设计的花纹与色彩规律,在纺织面料上刺缀运针、穿引彩线,以绣迹构成花纹、图案或文字的一种装饰工艺。它作为一种延续千年的古老艺术,一路伴随着中华文明的演进与发展,成为人类了解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窗口。随着社会审美和工业技术的发展,众多刺绣技艺均面临人才断档的危险。在全球化不断深化、社会经济高速发展的今天,如何运用新兴科技助力汉绣的传播和发展,推动其更好地融入荆楚现代生活和社会全面进步,还需要从新的视角对汉绣保护进行分析和研究。
1.汉绣保护的现状与桎梏
汉绣作为湖北地区传统的民间手工工艺的典型代表,其最早发源于湖北江陵[1],并在战国时期就已经出现[2]。进入21世纪以来,为弘扬和继承这项重要的地方性非遗,在湖北省政府和湖北省相关文化主管部门的联合主导下,主要采取了抢救性保护和生产性保护的方式对非遗汉绣开展了一系列保护工作。
汉绣的抢救性保护是从教育和存档两方面着手,对具有艺术价值、科学价值、历史价值而又面临传承困境的非遗进行传承弘扬和原真记录,从而保证非遗的有效传承。2008年汉绣被评为国家级非遗后,相关文化行政管理部门和文物保护部门为保护汉绣,增设以“杨小婷汉绣研究室”和“汉绣博物馆”等为代表的非遗传承基地和研究机构,使濒临消失的汉绣又重新回到了公众视野。许多刺绣爱好者通过各类培训班、短训课的方式,逐步成为了汉绣从业者。经过近十年的不断发展,汉绣在人才培养和成果积淀上均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据湖北省工艺美术大师杨小婷估算,目前,湖北省已有数十个汉绣工作室,囊括八千余名汉绣绣友,改变了以往汉绣从业者不到一百人的局面[3]。此外,各类博物馆、群艺馆、文化馆等文化机构和社会公众收藏了大量汉绣作品,以及相关的工艺技法、花样纹饰、艺术造型等文化信息,以文本、照片、视频等数字化载体在互联网上广为传播。
汉绣的生产性保护是指在不违背汉绣手工生产规律和运作方式、保证其本真性、整体性、手工核心技艺和传统工艺流程的前提下,使非遗汉绣在创造社会财富的生产活动中得到积极有效的保护。从行业发展来看,现阶段汉绣的生产性保护尚处于“店厂合一”的小作坊阶段,展示、设计、制作和销售等工作均在作坊内进行。从产品内容上来看,现阶段市售的汉绣作品在内容上反映了各个历史时期湖北文化的特征与审美,其纹样构成和色彩搭配在内容题材、艺术造型、纹型组织等工艺技法均源于客观原型和社会生活。但较为遗憾的是,从行业产值来看,作为全国汉绣制售中心的武汉,全市汉绣产业的年销售额不足500万元,与苏绣的10亿多元、湘绣的4亿多元相距甚远[4]。
通过对非遗汉绣保护工作的调研和分析可以看出,在汉绣保护过程中,政界、业界和学界已初步形成合力。但即便如此,由于全球一体化和我国城镇化的冲击,汉绣保护依旧任重而道远。具体而言,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尤为突出。
其一,文化行政管理难度日渐增加。当前,我国非遗的传承与保护主要围绕非遗代表性名录、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展开,形成了政府主导下的非遗传承与保护模式。伴随汉绣产业的不断扩张,文化行政管理部门有限的保护资金和业务能力将难以应对不断增长的管理需求。为此,基于现有海量社会信息的筛选和甄别,对亟待保护的汉绣品种和传承人实现精准保护,将成为提升政府工作效率和非遗保护成效的重要课题。
其二,社会公众参与度有待提升。群众的参与是非遗传承的重要前提[5]。比照国外相关刺绣类非遗保护项目可知,汉绣的社会公众参与程度还很低,它一方面表现为汉绣内容与社会公众之间存在审美差异,青年人无法欣赏和理解传统刺绣的文化内涵;另一方面还表现为汉绣艺人与社会公众之间存在文化代沟,艺人虽有精湛的绣法技艺,但除传统刺绣纹样外,无法充分了解社会公众对刺绣样式和内容的全新需求,从而导致绣品产销供需脱节。
其三,存量信息资源难以发挥效益。从百度搜索引擎的关键词检索结果的数量比较来看,苏绣为793万个词条、蜀绣326万个词条、湘绣429万个词条,而汉绣仅有50万个词条。造成上述结果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汉绣的发展水平相较前三者而言还处于起步阶段,另一方面则是由于设备、标准、来源和操作流程的多样性,导致汉绣数字化信息在生成、保存和传输过程中存在互不兼容的现象。如何对汉绣数字化信息的收集、整理、鉴定、保管、编目和检索提出指导性标准,引导汉绣数字化信息资源从无序走向有序是当前的一项重要课题。
综上,笔者认为可以从大数据管理和大数据规划入手,通过数字化管理、信息标准制定和数据挖掘应用的具体实施,推动我国非遗管理体系的优化与提升。
2.大数据管理和大数据规划研究进展
自2012年美国政府率先提出大数据国家战略以来,以欧盟、日本等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均相继制定了大数据战略。2015年,为落实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实施国家大数据战略”,国务院印发了《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2016年初,实施国家大数据战略被写入国家“十三五”规划纲要。同年底,工业和信息化部印发了《大数据产业发展规划(2016-2020)》,提出到 2020年,技术先进、应用繁荣、保障有力的大数据产业体系基本形成。为全面了解大数据管理和大数据规划的研究状况,笔者以“大数据管理”和“大数据规划”为关 键 词 , 在 EI、Web of Science、Taylor Francis、CNKI等数据库中进行检索,所获信息如下。
就大数据管理角度来看,近年来,大数据管理的部署范围和管理实例均呈上升趋势。2016年美国国际数据集团 (International Data Group)对724个随机抽取企业进行调查,结果显示已部署大数据并对其进行管理的项目企业占随机抽样总数的75%。从研究状况来看,在国内外学者对大数据研究方向进行探索的过程中,大数据管理的影响要素和大数据解决方案成为大数据管理的焦点。为此,国内外学者提出了大数据全生命周期管理[6]、大数据项目实施路径分析[7]等系列理论,并结合大数据应用提出了包括采集、组织、整合、分析和运行在内的管理实施办法。我国学者则多从大数据资源管理的角度着手,探索包括大数据的获取、加工、应用、产权和法规等在内的管理问题[8],以及基于国家层面的大数据管理策略[9]。
就大数据规划角度来看,虽然欧美国家率先在世界范围内启动了基于公司战略的大数据规划,但各国组织和机构对大数据规划工作的关注度仍显不足。就学界研究而言,国内外学者对大数据规划的研究焦点则多有不同。国外大数据规划研究重在实施标准和具体应用,如Biesdorf和Court提出大数据规划应匹配行业投资重点与公司业务战略,通过技术应用和数据分析平衡成本和效率之间的关系[10]。我国大数据规划研究的重点则多聚焦于国家战略和顶层设计,例如陈明奇认为构建中国特色的大数据战略及其建设路径是我国大数据研究的核心要义[11];闫建指出需从顶层设计的角度出发,构建我国大数据整体规划,并组建专门机构进行定向管理,从而实现我国大数据事业的统筹发展[12]。
结合前文分析可知,研究不断发展和流变的非遗汉绣,必须运用大数据技术在社会生活的大尺度下对汉绣信息资源进行聚合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通过汉绣管理信息系统及其算法设计,对汉绣的保护状态、保护成果和艺术发展等因素进行量化和评价,最终通过大量微观环境下的信息搜集和数据聚合,为文化行政管理部门提供宏观决策支持,并为非遗生产性保护企业和社会公众在中观上提供精准的信息支持服务。
3.基于大数据的汉绣保护机制
通过对大数据研究历程的回顾及其研究热点的分析,笔者认为,我国文化遗产保护应顺应大数据时代的研究趋势,借鉴已有大数据研究成果,探讨大数据理论方法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运用与发展。为此,应重点加强对资源规划模型、保护标准和关键技术的研究,从而应对行政管理、存量信息和公众参与三方面的挑战。
3.1 基于本体的汉绣大数据资源规划路径
随着大数据技术在社会生产生活中的不断融入,大数据作为一种重要的战略资源的基本定义已成当今社会的一个共识[13]。
笔者以现有大数据研究成果为基础,以汉绣保护实践为导向,尝试从本体角度提出汉绣大数据资源规划的研究视角和理论思路。通过目标确定、概念梳理、规划设计和实现路径四个环节,从理论和应用两个视角出发探讨了战略规划理论与信息资源规划在大数据资源规划中的可行性与适用性问题,初步形成了汉绣大数据资源规划路径。该路径从大数据技术与应用出发,为组织和管理汉绣大数据资源提供了可行思路,同时可在规划设计阶段与现有行政管理体系及其技术方法相互融合,达成较好的互动效果。大数据资源在体量 (Volume)、 效率 (Velocity)、 来源(Variety)、价值(Value)及真实性(Veracity)等方面呈现出的多V特性,决定了大数据资源开发与管理的复杂性,也为组织驾驭大数据带来了巨大挑战[14]。上述汉绣大数据资源规划模型的实施需要文化保护数据、物联网数据以及互联网大数据等多来源数据的支持,随着全社会大数据生态环境的改善和提升,大数据资源规划将推动文化遗产保护体系与社会公共大环境之间的数据流动与资源融合,从而真正发挥汉绣大数据的核心价值。
3.2 基于大数据的汉绣元数据标准集
从国际角度来看,元数据标准作为大数据应用的基础已成为共识。就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而言,一系列基于DC标准和TEI/EAD标准的专门元数据标准集已逐步建立,形成了以《文化对象编目指南》(CCO)、国会图书馆主题词表(LCSH)等为代表的国外文化遗产元数据标准集。
从国内角度来看,现阶段相关部门发布了《政府信息资源共享管理暂行办法》《大数据标准化白皮书》等若干与大数据相关的标准和文本,但并未对我国文化遗产大数据形成专门标准。究其原因,一方面是由于现行大数据标准多强调内容的通用性,尚未考虑文化遗产大数据中隐含的文化属性、保护属性、传承属性等特性要求,因而在标准拓展和细节制定上较为滞后。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在我国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过程中,形成了大量标准各异、架构多样的异构数据。如何整合大量多来源、多角度、多维度的对象内容所产生的复合型数据是现阶段我国文化遗产大数据应用的难点之一。为解决我国汉绣存量信息转化与传输的问题,笔者基于对现有汉绣数据的语义分析,以通用性较强的DC标准元数据名及标准词缀库作为基础蓝本,定义出含13个标准元数据名,包含66个元素与扩展元素的汉绣元数据标准集[15]。依托上述汉绣元数据标准集,可以实现汉绣大数据在内容和格式上的归一化,为后续数据挖掘、数据认知、数据检索和指标评价等工作打下基础。
3.3 基于K-means算法的大数据挖掘技术
从大数据角度来看,汉绣是湖北地区具有共同生活环境、生活方式与文化心理的刺绣艺人群体进行的集体创作的信息集合。利用大数据技术对汉绣信息资源开展整理、分析、储存、分发、展示等工作,通过汉绣信息在微信、Twitter等社交媒体的展示和传播,以及维基百科、百度百科等知识平台的作用,构建一个用不同语言组成、可动态变化、自由访问和群体编辑的汉绣大数据空间,进而推动汉绣的公众参与度。
通过对汉绣数字化保护成果的分析可知,现阶段汉绣信息资源主要包括以下三种类型,即结构化数据、半结构化数据和非结构化数据。其中,又以文本、图片、图像、视频等在内的非结构化多媒体数据组成了汉绣信息资源的主要部分。为处理以非结构性数据类型为主的汉绣信息资源,需要依赖以规则提取、自然语言处理、文本主题分析等在内的大数据挖掘技术。基于国内外现有的主要大数据系统设计方案的研判和分析,笔者尝试以现有非遗叙词表及本体词汇[16]为基础,形成面向汉绣保护利用的大数据应用框架。上述框架以实现功能、应用流程、技术类型和技术名称为内容主线,以结构化标注具体汉绣信息资源并进行有效组织为目标,通过标准制定、数据挖掘等技术手段,定义各种汉绣多媒体信息资源和实物载体的对应关系,实现汉绣大数据应用的落地,并对其保护现状和保护水平进行监控和评价。
在上述面向汉绣保护与利用的大数据应用框架中,K-means数据挖掘算法是对汉绣信息资源进行数据挖掘的主要工具,并为后续的数据抽取、数据评价和知识传播提供技术支持。上述技术的实现,首先是采用元数据标准对汉绣异构信息资源进行预处理并形成汉绣信息资源数据库。其后是采用K-means数据挖掘算法对汉绣信息资源数据库进行数据挖掘和模型分析,算法要点为依照自然属性、社会属性、行为属性、价值属性和影响力属性形成模型,并对数据对象进行抽取、清理、组织和集成,最后通过人机交互界面响应文化行政管理部门、文化产业行业、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和社会公众的多样化需求,进而构建完整的汉绣大数据应用方案。
[1]叶云,叶依子.论汉绣的保护与传承[J].湖北社会科学,2008(9):178.
[2]周薇,谢敏.汉绣文化的历史演进与传承保护[J].兰台世界,2015(6):28.
[3][4]张帮晋.浅析汉绣民俗艺术的产业化开发[J].华中师范大学研究生学报,2016(3):16.
[5]周耀林,程齐凯.论基于群体智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管理体制的创新[J].信息资源管理学报,2011(2):54.
[6]Siddiqa A,Hashem I A T,Yaqoob I,et al.A survey of big data management:Taxonomy and state-of-the-art[J].Journal of Network&Computer Applications,2016(71):151-166.
[7]Kemp R.Legal aspects of managing Big Data[J].Computer Law&Security Review,2014,30(5):482-491.
[8]杨善林,周开乐.大数据中的管理问题:基于大数据的资源观[J].管理科学学报,2015,18(5):1-8.
[9]于浩.大数据时代政府数据管理的机遇、挑战与对策[J].中国行政管理,2015(3):127-130.
[10]Biesdorf S,Court D,Willmott P.Big data:What’s your plan[EB/OL].[2016-12-15].http://www.mckinsey.com/businessfunctions/digital-mckinsey/our-insights/big-data-whats-yourplan.
[11]陈明奇.大数据国家发展战略呼之欲出——中美两国大数据发展战略对比分析[J].人民论坛,2013(2):28-29.
[12]闫建,高华丽.发达国家大数据发展战略的启示[J].理论探索,2015(1):91-94.
[13]周耀林,赵跃.大数据资源规划研究框架的构建[J].图书情报知识,2017(4):63.
[14]周耀林,赵跃.大数据时代信息资源规划研究发展路径探析[J].图书馆学研究,2017(15):49.
[15]叶鹏,周耀林.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元数据的创立思路与语意标准[J].忻州师范学院学报,2014(4):115-116.
[16]周耀林,赵跃,孙晶琼.非物质文化遗产信息资源组织与检索研究路径——基于本体方法的考察与设计[J].情报杂志,2017(8):107-1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