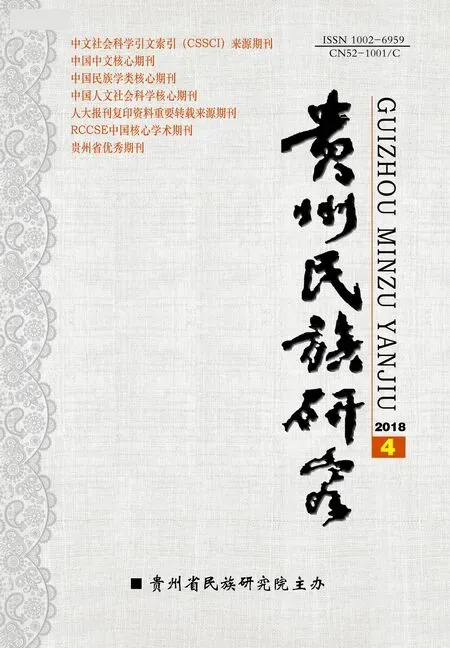从“本真”文本到“拟真”符号
——西兰卡普的当代重构研究
向思全
(四川大学 艺术学院,四川·成都 610044;湖北民族学院 美术与设计学院,湖北·恩施 445000)
一、西兰卡普在乡土语境中的“本真性”存在
“本真”作为一个哲学范畴,在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中被提出。所谓“本真”,是指不遮蔽的真实存在,即事物以其本真存在而存在。在乡土社会的语境中,西兰卡普作为民俗化的艺术,在内涵的审美价值和情感表达上是以“真”为核心。首先,“真”体现在使用功能上始终是与实用相融共生;其次,是真实地反映了人们的精神世界;再次,西兰卡普的“真”还表现在普通女性对自在生命的本真体验。因此,西兰卡普在造物层面上情感的表达是诗性的、真诚而非功利的。正如海德格尔所说“一切艺术本质上都是诗。”[1]传统西兰卡普本着“真”的精神,产生了蓬勃的生命力和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呈现出纯朴、自然的诗意境界。
(一)实用为美的本真表达
“工艺之美就是实用之美。”[2]西兰卡普诞生于日常生活之中,为日常生活所用是其发展的原初动力。土家人擅长纺织,早在3000多年前就掌握了织锦技术,从賨布、兰干细布,再到斑布、溪峒布,最后定型为西兰卡普,都始终围绕着生活的需求而展开。《大明一统志》记载,“土民裔出槃瓠,身服无彩斑衣。”据清同治年间《龙山县志》记载,“土锦五色为之,文彩斑斓可爱,俗用以为被,或为裙,或为巾。”由此可见,西兰卡普就是土家人日常生活的必需品,并且伴随着土家人的一生。小孩出生时,娘家就要为婴儿准备西兰卡普的花盖裙,功能是保暖、遮光和挡风,织锦花边的装饰要以使用为原则,多则不好用,少则影响美观;在结婚时,土家姑娘要用几年的时间亲自制作西兰卡普作为自己出嫁时最重要的嫁妆,《永顺府志》记载:“土家婚礼、过礼、女家索聘,奁资亦丰,棉被多至二十余铺。”西兰卡普的精致程度成为衡量姑娘的人品和能力的标准,同时这些花被盖会伴随他们今后的日常生活;土家女性在百年以后,还要将自己生前织得最满意的西兰卡普作为陪葬,可见对织锦工艺和质量的要求。在实用为真的原则下,西兰卡普没有过于华丽的奢靡之风,也无淫贱之型,有的只是诚实之性和优良之质,呈现出工艺实用的健康之美。
(二)精神世界的本真表达
土家族是没有文字的民族,勤劳的土家人把自己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转化成精美的装饰纹样织在西兰卡普上,形成了一部没有文字的史书,真实地呈现出土家人在各个时期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五代之前,土家族还处在渔猎时代,此时的织锦名为“賨布”,纹样以“窝毕”指“小蛇”,反映的就是土家先民龙图腾的崇拜。唐代末年,土家人结束了战乱和动荡的渔猎生活,进入了“刀耕火种”的农业生产时代。为了表达出对稳定生活的向往,便产生了敬神台,以表达对神龛上“天地君亲师”和历代祖先的敬意。因此,这一时期的织锦题材就以“神龛花”最为盛行。到了雍正十三年(1735年)实施了“改土归流”,取消了“蛮不出境,汉不入峒”的禁令后。大量的汉文化影响到了土家族地区,常见的就有吉祥文字和吉祥纹样,“福禄寿喜”、“老鼠嫁女”、“土王一颗印”等又成为织锦的流行题材。
除了随时代变化的纹样外,还有些纹样是约定俗成的,它们代表了民族的精神和信仰。如“四十八勾纹”,就是对土家部落远古蛙图腾的抽象模仿,是土家族人将母爱、多子、避邪驱疫的渴望和祈求融进蛙纹之中,通过集体意识的渗透深入到每个社会个体的意识之中,成为大家都认可的“蛙人合一”的图腾符号。还有“台台花”,由水波、菱形面纹和小船三部分构成。相传人类曾经毁灭于洪荒之年,布所和冗妮躲进葫芦得以幸存,为了延续人类,两兄妹被迫成亲繁衍了后人。土家人为了纪念再造人类的祖先,就将他们奉为傩公傩母。“台台花”就是这个故事的真实写照,水波代表洪水,菱形面纹代表布所和冗妮,小船代表葫芦。织有“台台花”的儿童盖裙就成了儿童的保护神,也寄托了土家人繁衍生息的美好愿望。抽象的纹样体现了土家人对未知自然的模仿和想象、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对民族信仰和社会秩序的遵守,是土家人精神世界的本真表达。
(三)创作主体“尚俗”的本真表达
西兰卡普源于生活,其创作主体是土家族的普通女性,勤劳朴实的民族性格和乡土化的生活体验,使其和宫廷匠人“尚雅”的风格相异,表现出明显的“尚俗”趋向,造就了西兰卡普民俗化的魅力。民俗化的“本真性”审美价值赋予了西兰卡普本真而强劲的生命力。
除了创作的题材具有“尚俗”的特征以外,西兰卡普的用色表现出明显的“尚俗”趋向。西兰卡普的用色并不是像宫廷工艺以“五色与金银之色”为正统用色,严格讲究哲学中的“五行相生”和“五方正色”与社会秩序及伦理道德的契合。而是在遵循本民族“尚黑忌白”的大原则下,使用来自自然的丰富颜色,凭着自己的审美经验自由搭配,讲究色由心生的感性体悟。“红陪绿,颜色足;兰配黄,放光芒;黑配白,那里得。”的配色口诀便反映出她们对色彩的理解。在图案创作中也表现出“尚俗”的特征。土家女性常以日常生活和自然为蓝本进行图案创作。相传,一位土家姑娘没有花样可织,坐在机头发呆,看到岩墙上开的花朵很美,就以此为图案,织成了岩墙花。其实,土家人认为万物皆有灵,一山一水有性情,一草一木栖神灵[3]。他们以栖身的世界为蓝本,创作了百余种经典纹样。具有代表性的有,以植物花卉为题材的,韭菜花、腾腾花;以动物为题材的,阳确花、燕子花、猫脚迹;以生活物品为题材的,桌子花、椅子花;以几何纹样为题材的单八勾、双八勾、四十八勾……生动通俗的纹样,反映出土家人源之自然的本真审美意识。
因此,土家女性在西兰卡普的创作中,没有遵循严格的构成章法,而是体现出民俗生活感性、随意的特点。在色彩搭配和纹样创作上,完全是凭借此时此地真实的审美经验,将自然生活升华为一幅幅形态各异和色彩不同的艺术精品。这便是土家女性对物象自在生命的本真体验,它充满了灵韵。
二、西兰卡普在消费语境中的“拟真化”呈现
“拟真”是鲍德里亚在《象征交换与死亡》中提出来的概念。所谓“拟真”又称为“仿真”,指的是一种不以客观现实为基础但又极度真实的符号生产和行为过程。自改革开放以来,物质的丰裕、经济的腾飞,促使中国表现出明显的消费社会特征。随着改革的深入,经济发展也影响到偏远的少数民族地区,西兰卡普从原初自给自足的农业时代,进入了物质丰盈且充满符号的消费社会。经济、文化语境的改变,对传统民间手工艺带来了巨大的挑战,最直接的影响便是使用功能和本真意义的丧失。如今的西兰卡普不再是土家女孩为自己出嫁倾尽全心力织的土花铺盖,其中所承载的宗教伦理、原始信仰也被逐渐淡忘。在消费逻辑的支配下,西兰卡普被资本、政治、媒体等力量所控制,逐渐异化为脱离本真的仿真“拟像”。
(一)作为商品的时尚化拟真
西兰卡普作为民间工艺产品,具有使用和交换的价值。在消费社会,西兰卡普原本具有的实用功能被现代工业产品所代替,人们对西兰卡普使用的需求转向了对其所附有的象征意义的需求。于是,资本以产业化的方式进行规模化生产,按当代的审美方式赋予它商品的意义,使其呈现出时尚化、审美化的趋势。
如今的西兰卡普早已脱离了原初精神和形式的原型,按照当代人的喜好被开发成各种旅游产品,他们以畅销为原则不惜篡改图案甚至打破禁忌,在商品的氛围中被买卖和出售。如西兰卡普中的经典纹样“四十八勾”,凭借其优美的构成形式而成为时尚的图案,出现在土家族地区的各种地方。旅游纪念品要印上四十八勾纹,舞台服装要印上四十八勾纹,土特产包装上也印上四十八勾纹,就连建筑也都用四十八勾的纹样做装饰。原本作为土家族人对生殖和太阳崇拜的纹样,在当代被简单地解构成一个纯粹的图像纹样,成为了时尚的消费符号。
抛开使用语境的四十八勾早已失去了本真的意义,其实就是对西兰卡普本真形式的浅表理解和简单复制,甚至是对复制品的复制。按符号学的观点,符号化的西兰卡普逐渐脱离本真,它既不指称现实,也不表达意义,它就是符号的简单重叠,并成为没有所指对象的时尚符号。正如鲍德里亚说所,时尚是建立在取消过去的基础之上,在时尚的氛围中,所有文化都在完全的混杂中作为仿像而起作用[4]。
(二)工艺展演的舞台化拟真
舞台化作为一种形象化的符号展示方式,对民间工艺文本来说,能够更为集中地展示其包涵的地域文化和手工技艺等符号信息,也能让消费者获得更为形象的感知和直观的体验。因此,旅游景点为了促进消费,将西兰卡普作为土家文化的代表搬上舞台,以舞台化表演的方式转化成消费文本。
如今在旅游景区和土家族的民间工艺品商店,经常会看到现场制作西兰卡普的手工艺人,她们身着现代的土家族服装,在精心布置的环境中熟练地挑花和操作织机,丝毫不被周边游客的闪光灯所影响。表面看她们足够的原生态,但从状态来看更像现代的工人,她们脸上丝毫没有劳动带来的愉悦表情,手上几乎用相同的节奏和时间完成每一行的编织。从作品来看更像机器生产,织出的花总是那几个畅销纹样和颜色,并且像计算过的一样精确和相似。这种去语境化的工艺展演看似真实,其实却并不真实。展演中机械的临摹仅仅是为了完成表演的任务,工艺制作者对西兰卡普工艺所代表的土家族女红文化缺少理解,对来自生活的经典纹样也缺少体验,以至于她们不能进入原初的诗意的虔诚状态,它实质是脱离文化背景的商业表演。
如果说制作表演还是对西兰卡普原真的模仿,那么舞台表演就是脱离了原真的拟真创作。为了进一步加强消费者猎奇和娱乐化的感官刺激,人们创作出《西兰卡普》的文化实景演出,在人造的原生态舞台中对西兰卡普的文化进行戏剧性表演。在表演中作为工艺的西兰卡普仅仅被当作是舞台中的一个元素,被随意地安排到整台演出中,甚至背离原真的文本参照,用夸张的手法加入人为的想象,呈现出华丽而震撼的效果。对观者而言,舞台呈现出来的西兰卡普,是一种没有实际意义的娱乐表演,它仅仅是打着“土家文化”幌子的一堆碎片化的符号。观者在表演中所接收到的符号信息是脱离了摹本的想象,是为了满足消费者而建构的审美化、娱乐化的拟像文本。
(三)影像建构的景观化拟真
影像作为现代都市文明的产物,是集消费与审美于一体的符号集合,是用虚拟的方式将美好的想象置于观众熟知的生活场景,通过媒体展示出的一个又一个的符号景观。地方政府为了促进文化产业的发展,推介西兰卡普文化的传播和消费,请来权威媒体将西兰卡普搬上银幕,试图在浮华的当代为人们建构出一个理想、仿真的诗意世界。
纵观从央视台到地方台的宣传片,它们通过艺术创作显得华丽而精美。画面有意拉开现实物象和审美意象之间的距离,将西兰卡普像明星般安排在精心布置的场景中,刻意突出西兰卡普在民间乡土语境中的宁静和优美。在蒙太奇手段的时空转化中,西兰卡普展现出百奇斗艳、耀眼无比的繁华景象,屏幕前的观众也对影像建构出的土家文化和西兰卡普无比向往。然而,这仅仅是在表面上呈现出的繁华景象,实质上,这种“去生活化”的景观化呈现,是对西兰卡普本真状态的遮蔽,是令民族艺术主体感到紧张的文化失去。[5]正如居伊德波所说“琳琅满目的图像和景观充斥了当代社会并前所未有地改变了当代人的生存体验和文化境遇——影像成为人们的社会关系的中介,生活展现为景观的庞大堆积。”[6]西兰卡普在影像建构的景观中,再次成为取悦消费者的仿真拟像。
三、西兰卡普的当代价值重构
消费文化终结了西兰卡普的使用功能和乡土化的审美姿态,符号意义从本真的“诗意的文本”裂变成拟真的“消费的符号”。在裂变中,西兰卡普被任意地打散、拼贴和挪用,原本熟悉的民族文化符号变得奇异和陌生,在工艺上失去了“灵韵”,在情感上失去“乡愁”,表现出明显的当代困境。然而,时代的发展是不可逆转的,我们已经不能回到原初的乡土语境,裂变后的西兰卡普必须以当代的姿态重回大众的生活,才能突破当前的困境。
(一)消费语境的使用价值重构
需求决定市场。乡土社会中,西兰卡普作为日常生活、民俗仪式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因实用而具备刚性需求。但在现代语境中,科技的发展、知识的普及以及丰盈的物质,几乎消解了它的全部功能,其象征意义也逐渐被现代文明抹平。可以说西兰卡普功能和需求的失去是其日渐式微的主要原因。
要重建西兰卡普的当代价值,就必须重新走进现代人的生活而重获需求。这就要求对传统文本进行当代改造,将传统造物思想和现代设计相结合进行“再设计”,开发出符合现代人审美和生活习惯的产品。在当代也不乏很多成功的案例,如鄂西土家族地区的刺绣企业“土司皇宫”,以千层底布鞋为原型,用传统的手工制鞋工艺和刺绣装饰,在传统绣花鞋的基础上结合现代人的使用习惯,设计出绣花拖鞋、踩堂鞋、虎头鞋等系列产品。产品既保持了传统的土家文化内涵又具有实用性,得到了消费者的认同和追捧。由此可见,对传统民间工艺的当代“再设计”具有重要意义,它不仅可以让传统文化的功能在当代得到新的延伸,而且可以让工艺重获市场的自信。
西兰卡普因纹样优美、工艺精湛具有功能衍生和再设计的条件,但当前的衍生品开发主要还是集中在服装、围巾、桌旗以及纹样和物品结合的传统层面上,与当代主题和时尚结合的系统性产品开发还有待进一步拓展。未来,西兰卡普不仅要在题材和符号上赋予传统以生命,在图案、色彩等形式上要自觉地与当代审美心理和审美经验对接,更要在产品的使用功能的维度上进行大胆的挖掘。
(二)民族符号的审美价值重构
西兰卡普的审美价值是在劳动实践中形成和发展的,它受到土家族社会历史条件、文化心理结构和特定的民族信仰的制约。审美价值和意义在历史的传承中被逐渐固定下来,且具有相对稳定的解释,如“台台花”纹样的盖裙,象征着驱赶“白虎”的保护神,作为儿童的专用品而不能随意乱用。其意义通过上千年的口耳相传中被不断地强化,是典型的强编码文本,当代人难以从中解释出新的意义。
民间工艺要在当代重获发展,一定要打破其稳定的符号审美意义,用当代的语言对其进行重构,建构出特有的解释张力。如中央美院的吕胜中教授,将传统的剪纸图案“抓髻娃娃”进行当代改造和创新,用实验艺术的手法创作出不同形式的“小红人”,从装置艺术“天圆地方”、“招魂堂”到大型行为艺术“降吉祥”,作者用后现代的表现手法加以展示,赋予了传统剪纸新的生命。人们在作品的解读中,超越了传统吉祥的审美价值,引发出对于人的当代思考,符合了当代的审美品位。这种以现代设计观念为指导对传统文化进行结合,既保留了传统工艺美的意蕴,又推动了传统工艺在当代的审美重构。
西兰卡普要在当代语境中获得新的意义,应该从审美价值的重构入手,融入现代人对传统工艺文化的体验和感悟,将传统的形式语言转换成具有现代意味的艺术形态,使之在新语境中产生出新的意义。
(三)“女红文化”的工匠精神回归
西兰卡普作为中国传统“女红文化”的典型代表,集土家女性“尚巧”的创新精神、“求精”的工作态度为一体,体现出“道技合一”的人生理想。[7]具有中国传统工匠精神心无旁骛的心态、一丝不苟的精神和精益求精的标准的价值意蕴,是维系织锦工艺千年不衰的动力和源泉,是工匠精神的典型代表。
在浮躁的消费社会,快速的生活节奏和空气中弥漫的消费气息,打破了土家族自给自足的乡土生活节奏。年轻女性把制作西兰卡普作为谋生的手段,以计件和机械复制的方式进行生产,完全没有了制作嫁妆而倾力投入的状态。商人为追求利益的最大化,将西兰卡普开发成廉价的旅游纪念品,并大量的工业化生产和低价出售。被消费社会异化了的西兰卡普不仅失去了本真的文化意蕴,也失去了手工细作的灵韵。西兰卡普以当代的姿态重回大众生活,不仅是要求新颖的设计和全新使用价值的回归,还要求“女红文化”工匠精神的回归。这不仅符合现代人对商品高品质的需求,也符“中国制造2025”的战略计划。消费语境中“女红文化”所代表的工匠精神的回归,会成为其消费群体抵抗工业文明对主题精神异化的武器。使审美主体得以在机械复制时代的平面化、快餐式消费语境中重构个体生命体验。[9]还会提升产品的品质,重拾西兰卡普乡土语境中精工精致的诗意本真。
结语
西兰卡普作为土家族民间工艺的代表,反映出的仅仅是传统民间工艺在当代困境的一个侧面。在社会语境的转变中,工业生产挤占了传统民间手工艺的生存空间,经济发展破坏了乡土社会的文化土壤,消费文化改变了人们的价值观。很多优秀的民间工艺在当代语境中,或是失传或是面临失传的危机。然而,社会的发展是不可逆转的,传统民间工艺作为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要在当代继续发展,不可能回到过去,也不能简单地陈列在博物馆,更不能人为地通过想象建构,成为虚假繁荣的文化景观。我们应该加强民族文化的认同、提升文化自信,让民间工艺真正回到民间,参与到当代人生活中,与当代的人们共同成长,在传统和当代文化的共融中进行活态的传承和发展。
[1](德) 海德格尔.人,诗意地安居:海德格尔语要[M].郜元宝,译.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5:37
[2](日)柳宗悦.工艺之道[M].徐艺乙译,广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28
[3]罗斌,辛艺华.土家族民间美术[M].湖北:湖北美术出版社,2011:42
[4](法)鲍德里亚.象征交换与死亡[M].车槿山,译.江苏:译林出版社,2012:116
[5]吴晓.民族艺术的消费社会境遇[J].文艺研究,2007,(4)
[6](德) 居伊德波.景观社会[M].王昭凤,译.江苏: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3
[7]肖群忠,刘永春.工匠精神及当代价值[J].湖南社会科学,2015,(6)
[8]俞晓群.艺术的魅力与民俗的活力——试析“女红”的当代文化价值[J].浙江社会科学,201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