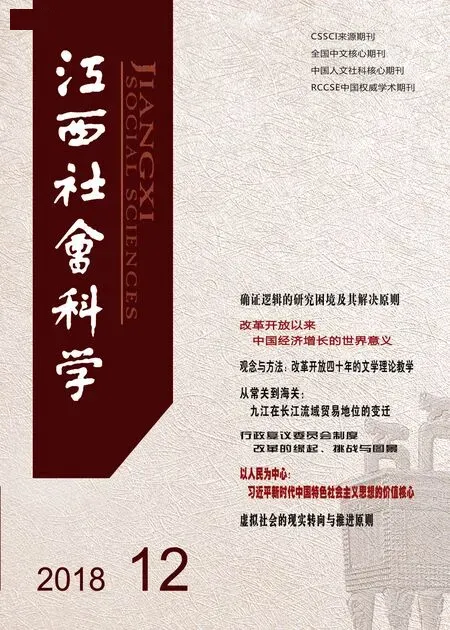汉语与英语学界中国文学研究互动的媒介与路径
17世纪以来,随着汉语与英语学界在中国文学研究领域的交流越来越频繁,两者之间的互动不断得到拓展,并且形成了具有常态性的交流互动的媒介方式和路径。从人员流动的角度来看,中英学界互动的媒介和路径主要有两类:一是留学、访学、讲学与旅学交游,二是学术移民或旅居;从研究成果的传播接受与影响层面来看,主要是学术论著译介与反馈性研究,以及国际学术会议与跨国、跨语际学术批评。
根据学界的研究,中国文学典籍在西方的译介、传播,萌芽于16世纪末的西班牙语世界,而后逐渐发展到意大利语和法语世界。英语世界中国文学的传播则兴起于17世纪,地域范围集中在英伦三岛。[1]随着英语世界中国文学研究的发展、兴盛和繁荣,在中国文学研究领域,汉语与英语学界之间的交流、互动也越来越频繁、越来越密切。17世纪至今,中英学界①在中国文学研究领域的交流越来越频繁,并形成了具有常态性的交流互动的媒介方式和路径。从人员流动的角度来看,中英学界互动的媒介和路径主要有两类,一是留学、访学、讲学与旅学交游,二是学术移民或旅居。从研究成果的传播接受与影响层面来看,主要是学术论著译介与反馈性研究,以及国际学术会议与跨国、跨语际学术批评。
一、留学、访学、讲学与旅学交游
在中国文学研究中,中英学界展开交流互动的方式与路径,首先是留学、访学与讲学。研究人员在不同国家之间的访学和讲学,带来的往往是不同国度的研究者直接的学术交流与学术思想火花的碰撞。留学方面,以哈佛燕京学社为例,该组织通过留学方式,成功地打开了中美两国文化、文学交流的大门。1929—1949年间,通过该组织来华留学的研究生、学者二十余人,其中以专治中国文学而闻名的有海陶玮(James Robert Hightower)等。而自19世纪70年代以来,到哈佛大学留学的中国学子数以百计,其中像胡适、梅光迪、陈寅恪、吴宓、梁实秋、林语堂、梅祖麟、范存忠、袁同礼等人,后来都成了中英学界中国文化、文学研究交流互动的杰出人物。梅光迪还在哈佛大学执教十年(1924—1936年,期间回国任中央大学代理文学院院长两年左右时间),讲授中国文化与文学,为美国培养了不少汉学人才。
说到留学在中英学界中国文学研究领域所起到的学术交流之作用,韩南(Patrick Hannan)的中国留学之旅是非常典型的案例。20世纪50年代中期,韩南在伦敦大学亚非学院攻读博士学位,原来选择《史记》为博士论文题目,后在指导教授西蒙(Simon)及著名翻译家亚瑟·韦利(Arther Waley)建议下改为研究《金瓶梅》。1957年,韩南获准到北京进修一年。虽因故未能在北京大学成功注册,但他在此期间获得很多珍贵的学术资源。首先就是认识了郑振铎、傅惜华、吴晓玲等韩南本人心仪已久的中国学者。其中与北京大学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专家吴晓玲的交往,对韩南的《金瓶梅》研究影响很大。吴晓玲是当时中国学界《金瓶梅》研究屈指可数的人物。韩南后来撰写的《〈金瓶梅〉的版本及其他》与《〈金瓶梅〉探源》等研究文章,多次援引吴晓玲等中国学者的观点,其影响可见一斑。而得郑振铎之帮助,韩南还得到当时人民文学出版社根据1933年影印本出版的《金瓶梅词话》一部。(因韩南研究的需要,时任中国文化部长的郑振铎,特批准把该书卖给伦敦大学图书馆一部。而在当时的中国,该书仅印刷一千部。)
学者在不同国家之间的访学与讲学,同样是开展学术交流的重要方式与路径。以斯奈德(Gary Snyder)对中国古典诗歌与诗学理论(尤其是对寒山诗)的了解、认识来说,陈世骧对其所产生的影响是非常大的。1945年起,陈世骧任伯克利加州大学东方语文系教授,主要从事中西诗学比较研究。期间,斯奈德进入该校学习中文,受教于陈世骧,并在陈世骧的指导下翻译了24首寒山诗,中国古典诗歌对斯奈德的诗歌创作和诗学观念的形成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类似的情况我们还可以从美国汉学家艾朗诺(Ronald Egan)身上看到。在一次访谈时,艾朗诺如此说道:
现在回想起来,我走上中国文学研究之路,有几个人不得不提,内心深处对他们一直充满了感激。第一个就是白先勇,他是我的中文启蒙老师。19岁那年,我还在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读大学二年级,他就送了我一本《唐诗三百首》,就是因为那本书,我一头扎进了中文世界。后来,他还专门安排我去中国台湾进修中文课程。第二位是我在哈佛的博士导师海陶玮(James Hightower)教授。他是老一辈的陶诗专家,也研究过贾谊的汉赋,从他那里我接受了最严格的古典训练,也是在他的指导下,完成了我的毕业论文,研究《左传》以及先秦的叙述形式。第三位,就是先后在斯坦福和普林斯顿任教的宋史宗师刘子健(James T.C.Liu)。我们有过长期交流,他对我的宋代文学研究启发很大。最后一位是方志彤(Achilles Fang),他和钱锺书是清华的同级同学,也是很要好的朋友。他学问极好,希腊文、拉丁文、德文、法文、意大利文都懂,但在哈佛却很不得志,到退休还是高级讲师,但他培养的许多学生,比如海陶玮都成了名教授。[2]
中国学者在英语国家的访学、讲学,在中英学界中国文学研究领域所取得的积极的交流、互动的效果是显而易见的。不论是陈世骧之于斯奈德,还是白先勇、刘子健、方志彤之于艾朗诺,其意义和价值彰显无遗。与此相应,英美等英语国家的中国文学研究者在中国的访学、讲学,同样很好地担当着学术交流、互动之功用。
浦安迪(Andrew H.Plaks)教授是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中国文学研究的舵手,长期从事中国古典小说叙事艺术研究。在其1987年出版的 《明代小说四大奇书》(The Four Masterworks of the Ming Novel)中,浦安迪从空间维度对中国古典小说叙事艺术进行了比较深入的阐释。1989年3至5月间,受乐黛云教授邀请,浦安迪到北京大学为该校中文系和比较文学研究所的青年教师和研究生开设了“中国古典文学与叙事文学理论”课程。在这次系列演讲中,浦安迪就中国古典文学空间叙事论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3]浦安迪所作中国古典文学空间叙事研究对后来中国学界的空间叙事研究影响不小。这种影响,最明显地体现在龙迪勇的“空间叙事研究”上。龙迪勇在研究中把浦安迪的《明代小说四大奇书》《中国叙事学》列为重要参考文献,并多次援引其中观点。像浦安迪这样来华访学、讲学并对中国学界产生一定影响的英美汉学家还有很多,如宇文所安(Stephen Owen)等。
随着研究者在国外留学,或是在不同国家进行访学与讲学,另一种学术交流互动的方式随之出现,那就是旅学交游。学者间的学术交游是很常见的,就中英学界中国文学研究者之间的交往来说,王韬与理雅各,赵元任与罗厄尔(Amy Lowell),江亢虎与宾纳,龙墨芗与赛珍珠(Pearl S.Buck),乐黛云与浦安迪,等等,即是对此种交流方式的极好诠释。旅学交游往往展现出研究者之间在学术思想和学术观念上最直接的接触和交流。季进所著《另一种声音:海外汉学访谈录》,其实就是该作者长时间以来与海外中国文学研究者如美国的宇文所安(Stephen Owen)、夏志清、艾朗诺等人旅学交游的成果。而以访谈的方式出现,更加突显学者之间学术研究思想上面对面的碰撞。
二、学术移民或旅居
学术移民或旅居,亦是中英学术界展开交流互动的一种非常重要的方式和路径。当中国学者移民英、美等英语国家,进入高校教师的行列,或加入中国文学研究机构,此时,两种不同历史文化语境和学术传统背景下成长起来的中国文学研究者,在学术视角、学术思想、研究方法等方面的交流、碰撞就比较容易展开。同样,英语世界中国文学批评者移居(旅居)中国,亦会出现类似的情况。而学术移民或旅居在交流互动中所取得的效果,与上述诸种方式是相似的。
20世纪上半叶,赛珍珠同家人一起旅居中国,前后长达近40年。我们所熟悉的赛珍珠,更多的是一个以中国题材进行文学创作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美国女作家,但事实上,她也是一个在中国文学(古典小说)研究上取得一定成绩的批评者。[4]自1925年起,赛珍珠先后任教于南京大学、东南大学、中央大学,与当时中国学界人士广泛接触,对中国文学的认识也深受中国学界的影响。这些学术经历,让赛珍珠对中国文化、中国文学的了解和认识,比当时英美国家的大部分研究者要更为深入。20世纪30年代,赛珍珠先后撰写多篇文章讨论中国小说,特别是1938年在诺贝尔文学奖颁奖典礼上所作的《中国小说》(The Chinese Novel)的演讲,更是在西方世界大力宣扬中国小说,让西方人认识真正的中国小说。而在当时的大多数西方学者眼中,中国小说是不入流的。当时一个学者贝克(Baker)就说,中国小说尚停留在“故事”阶段。[5]作为一个旅居中国多年的美国作家,中国古典小说批评者,赛珍珠站在西方人面前,充分肯定中国古典小说在形象塑造、语言描写、情节架构等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在很大程度上为西方中国文学研究注入了另一种声音,大不同于美国时人的新颖的认识。②
赛珍珠旅居中国的经历,使其有很多机会与中国学者直面交流,相互之间在中国文学研究问题上展开讨论。而作为一个旅居中国的美国学人,中国古典小说的研究者,当赛珍珠把她在中国文化、文学语境之中所获得的对中国文学的认识公诸英美等西方国家学者面前时,赛珍珠本身就已成为英语世界中国文学研究与中国学术界交流互动的最好、最直观的方式和媒介。
移民或旅居英、美、加拿大等英语国家的中国学者为数不少,像陈世骧、周策纵、夏志清、叶嘉莹、刘若愚、高友工、叶维廉、孙康宜等,是其中成就卓越者的代表。这些移民或旅居英美等英语国家的华裔学者,大部分在中英学界频繁走动,他们的中国文学研究成果在中英世界出版发行,他们的研究方法、学术思想、理论观点等为中英学界所认识、所熟悉。其中,有些学者的观点甚至影响到中国文学史的书写。
夏志清是与韩南齐名的对美国的中国文学研究产生重大影响的学者。作为一位留学美国并最终定居美国的中国学者,夏志清在中英学界中国文学研究互动中承担着多重角色,发挥了非常独特的作用。他的《中国现代小说史》(A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Fiction)英文版1961年在美国出版。受当时美国学术思潮特别是“新批评”的影响,夏志清在该论著中致力于“优美作品之发现和评审”,对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很多作家形成了大异于中国学界的认识和评价。且不说其对鲁迅、郭沫若、茅盾等人的评价与中国学界之间有多大的出入乃至于冲突,单是对沈从文、张天翼、钱锺书、张爱玲等人的文学史价值和地位的发掘,就对中国学界产生了巨大影响,甚至影响到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学界的中国文学史书写。正是因为留学美国,旅居美国,并最终移民定居美国,夏志清才得以受教于美国特殊的学术体制、学术语境和学术传统,从而以一种特殊的学术视角切入研究、评价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诸位作家。正是这种“异样的声音”,当夏志清的研究成果传入中国学界时,就立马对中国学术界形成了巨大冲击。所有这些,正是留学、学术移民等带来的效果。
留学、访学与讲学,学术移民或旅居,从性质上看大体相当,从它们在学术交流中所取得的效果来看也基本相似。这些交流互动的方式和路径所带来的首先是研究者在中英学界之间的流动,而随着研究人员的流动带来的则是研究方法、研究视角与学术思想、学术观念等的交流、交叉与融合,从而使中英学界在中国文学研究领域相互影响、相互借鉴,共同推进中国文学研究的发展。然而,纵观19世纪以来中英学界的交互发展历史,在中国文学研究领域,不论是留学抑或学术移民,由中入英者远超过由英入中者。个种原因比较复杂,暂且不论。
三、学术论著译介与反馈性研究
中英学界在中国文学研究的交流互动上,对研究论著的译介也是一种非常重要的路径和方式。虽然未能进行具体统计,但据笔者近年来的学术考察,对为数不少的中国学界的研究者来说(专业学者之外),他们对英语学界中国文学研究的了解和认识,很大一部分是来自中国出版发行的英语学界中国文学研究成果的中文译本。像赛珍珠、夏志清、韩南、刘若愚、浦安迪、宇文所安等人的中国文学研究著作,大都有了中文译本。像王秋桂等译韩南著《韩南中国小说论集》,沈亨寿译浦安迪著《明代小说四大奇书》,杜国清译刘若愚著《中国文学理论》(Chinese Theories of Literature),程章灿、郑学勤等译宇文所安的中国古典诗歌研究系列论著,刘倩等译孙康宜 (Kang-I Sun)、宇文所安主编《剑桥中国文学史》(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等,就是其中非常优秀的成果。特别是江苏教育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与商务印书馆,它们或出版了海外汉学译丛,或出版了海外汉学书系,或出版了海外汉学丛书,其中有不少是英语世界中国文学研究的著作。
英美汉学家(实际上是整个西方汉学界)对中国学界的文学批评基本持厚古薄今的态度,特别是对中国当下的文学批评可谓是“不屑一顾”。在美国学者编撰的《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Columbi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Victor H.Mair)和《剑桥中国文学史》这样的大部头著作中,对中国学者观点的引用大都局限在1949年之前,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则基本上没在其中出现。对于这种情形,德国著名汉学家顾彬(Wolfgang Kubin)的言论是很有代表性的,虽然他的言论在中国人看来显得很尖刻。2007年,《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对顾彬做过一次采访,其中有这样一个问题,原文摘录如下:
中国新闻周刊:你觉得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现状是怎么样的?
顾彬:太可怕。因为他们多拿“红包”来写,所以,中国评论家们的作品我们都不看。中国文学的一个问题是在评论家,他们不够认真。[6]
对中国文学批评家们来说,顾彬的话很不中听,但它却道出了一个实情:在中西学界之间——当然包括中英学界,出于诸种原因(按顾彬之论实则是学术品质与学术水准),中国学界始终处于被动的境地。就可见的现实来论,在中国文学研究上,中英学界的交流互动,中国的确一直处于输入、接受的那头。
在上述大的学术环境之下,中国学界出现了一种笔者称之为“反馈性研究”的交流互动的方式和路径。自黄鸣奋著《英语世界中国古典文学之传播》(学林出版社,1997)开启先河,中国学界涌现出一大批以英语世界中国文学传播、研究为研究对象的论文和论著。这种“反馈性研究”,能较好地把英语世界中国文学研究的历史和现状、研究方法和视角、学术思想和观念等,引入到中国学界,甚至为中国学者的研究提供了全新的参照系,很好地推动了中国学界中国文学研究的发展。但同时也存在一个致命的问题,那就是此种研究往往是自说自话,是中国学界的研究者们在唱独角戏,而缺乏真正意义上的两个主体之间的对话和交流。与此相似,中国学界大量译介、出版英语学界中国文学的研究成果,很大程度上也只是一个主体发出的行为。如何打破此种窘境,这是个重大的课题。努力搭建起交流互动的平台固然重要,而努力提高中国学术界的学术品质和研究水准,则更为关键。因为,当自身的研究不为他者所关注、所重视、所认可时,真正意义上的交流互动是无法展开的。
四、国际学术会议与跨国学术批评
通过学术会议的形式进行交流互动,这在中英学界中国文学研究领域是比较常见的。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英学界的人员流动越来越频繁,举行国际性的学术会议成为可能。在中美两国之间,20世纪80年代就连续举行多次中美文学双边会议。特别是1984年的洛杉矶会议,美国诗人金斯堡(Allen Ginsberg)和斯奈德二人专门为该次会议准备了一份“美国诗人想问中国诗人的一百个问题”,在会晤时和中国与会代表展开直接交流。1983年中美比较文学双边会议开始举行。纵览历届以来的中美比较文学双边会议,基本上都有中国文学的研究论题。而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专门以中国文学研究为主题的国际学术会议不断出现,像敦煌学国际研讨会,杜甫国际学术研讨会,苏轼国际学术研讨会,唐诗宋词国际学术研讨会,凡此种种,不可胜数。
国际性的学术会议,为不同国家的研究者进行交流提供了最为直接的舞台。在这个舞台上,不同国度的学者们可以在研究方法与视角、学术思想与观念等方面进行交流,也可以就某一具体的论题展开直面的论争,从而取得交流互动的效果。正是通过这种性质的学术会议,中英学界在交流互动的基础上不断把中国文学研究推向前进。
在众多的国际性中国文学研讨会中,国际《红楼梦》研讨会开展得比较早,影响力也比较大,在不同国家的研究者之间也起到了比较好的交流互动的作用。首届国际《红楼梦》研讨会,是由美籍华裔学者、《红楼梦》研究专家、美国威斯康星大学教授周策纵发起的,于1980年6月16日到20日在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召开,参与会议的有中、英、美、加拿大、新加坡、日本等国家的学者。此次会议,围绕着《红楼梦》的主题、艺术技巧、版本与作者曹雪芹的家世和生平等问题展开,而在这些问题上中外学者之间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像夏威夷大学马幼垣教授提交的《乾隆抄本百二十回稿的一个版本问题》一文,在会议上引来众多与会学者的关注,也在学者们之间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中国红学家周汝昌认为,马幼垣的论文应该得到重视。[7]国际《红楼梦》研讨会从北美到中国到欧洲,一直在召开;有关《红楼梦》研究的各种论题,不断在研讨会上提出并得到讨论;中、英、美、加拿大等中英学界的学者,也一直是历届研讨会的主角。通过这样的学术会议,《红楼梦》研究中出现的不同的声音不断在中英学界传播;正是中英学界发出的这些不同声音,不断促进《红楼梦》研究的发展。
针对中国文学研究中出现的问题展开跨国学术批评,不只出现在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也出现在批评者个人的具体研究之中。笔者试举两例来说明这种情况。第一个案例,中国学界对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的批评。夏著传入中国之后,由于其对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不少作家的评价大异于中国学界,很快就引来中国学界的批评。《重庆社会科学》2007年第1期发表了一篇题为《在政治立场与学术探讨之间——评夏志清先生〈中国现代小说史〉鲁迅专章》的文章。该文章从政治立场的角度出发,批评夏志清因受政治偏见的局限,在对鲁迅的评价上以政治评判代替了审美评判,从而导致对鲁迅作品的误读。[8]中国学界对夏志清的这种批评文章为数不少。第二个案例,英国汉学家、陶渊明作品翻译与研究专家戴维斯(A.R.Davis)对中国学界陶渊明研究的批评。1983年,戴维斯译注《陶渊明:他的作品及其意义》(T’ao Yüan-Ming,His Works and Their Meaning)在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在该书的卷首语和导论部分,戴维斯强调陶渊明的诗歌是个人抒情诗,基于此从而批评了中国学者在陶渊明研究时所使用的非文学标准。此外,戴维斯对20世纪后期中国学者为陶渊明撰写更为详尽、更符合现代观念的传记进行的尝试和付出的努力也作出了批评。在戴维斯看来,这些研究者的尝试和努力,一个致命的问题是缺乏有足够证据的原始材料。[9](P108-109)浦安迪对中国学界《水浒传》作者、版本等的研究所作的批评,与此相似。此类案例还有很多,不再赘述。
中英学界针对中国文学研究中出现的某一问题彼此之间展开批评论争,对于促进相互之间的交流互动意义非凡。相对于上文谈到的“学术论著译介与反馈性研究”这种交流方式和路径来说,跨国学术批评显得具体、实在。这不再是中国学界或英语世界学者的独角戏,而是两个主体之间有意识的学术探讨。当然,由于时空的局限,这种学术探讨往往缺乏时效性。像《在政治立场与学术探讨之间——评夏志清先生〈中国现代小说史〉鲁迅专章》一文的发表时间(2007)与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的出版时间(1961),足足隔了46年。
五、结 语
经历数百年的时间,通过数代人的努力付出,中英学界在中国文学研究领域展开交流互动的基础和平台才得以建立。通过留学、访学与讲学,通过旅学交游,通过学术移民或旅居,通过学术论著译介与反馈性研究,通过国际学术会议与跨国学术批评等传统媒介和路径,中英世界的专家、学者就中国文学研究展开交流互动。因受到时空差异的局限,以及上述方式和路径本身的局限性,目前构建起来的平台还不能比较及时、有效地推进中英学界展开交流互动。在传播媒介的发展日新月异的今天,我们应该在维护知识产权的前提下,积极探索建立更加迅捷、高效的交流平台,从而构建起中英学界中国文学研究领域交流互动的日常运行机制。
注释:
①中国学界与英语学界,本文简称“中英学界”。
②赛珍珠对中国小说的具体论述,参见:China in the Mirror of her Fiction,Pacific Affairs,Vol.3,No.2 (Feb.,1930),pp.155-164;East and West and the Novel,Bulletin of The American University WomenAssociation,1931;The Early Chinese Novel,The Saturday Review of Literature,No.46.Vol.7.1931;Introduction of Shui Hu Chuan,All Men Are Brothers,NewYork:The John Day Company,1933;The Chinese Novel,NewYork:The John Day Company,19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