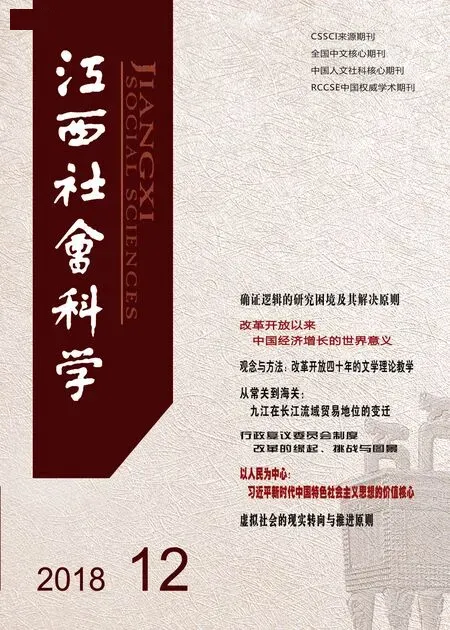跨国别生态诗学基础问题谫论
乔尼·亚当森、卡伦·劳拉·索恩伯、乌苏拉·海瑟等生态批评学者秉承生态世界主义理念,主张将比较视域引入生态批评理论研究,从多元到贯通,打破学科和国别疆域。中美生态诗学研究呈现多元行动主义特征,跨国别生态诗学建构成为本土话语与世界生态话语互鉴交融的必然选择。多元文化生态诗学使生态批评由学院派走向世界环境人文实践的第一线,为跨国别生态诗学建构提供了理论参照。
当代世界生态诗学研究出现明显的跨国别转向,比较视域成为生态文学与比较文学研究的重要视角,主要表现为生态批评理论研究的块茎性特征凸显及比较生态文学对多元民族性和跨文化性的关照。生态批评领域出现了一个有趣的微妙变化,比如权威生态批评学者斯洛维克、阿莱默、亚当森等将自己的专业领域从以往的“文学与环境”更换成“环境人文学”。[1]环境人文为自然科学和人文学者跨学科合作提供途径,以人文力量辅助科学实践,力主改变社会结构。随着生态世界主义思想盛行,中国传统生态美学开始主动搭建与西方环境人文理念的对话平台。跨国别生态诗学范式的构建有助于中西生态诗学形成对话关系,并共同参与到世界环境人文实践中来。
一、互鉴交融的中美生态批评
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生态批评家开始批判文学批评界一边倒地研究女性主义、解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的现象,呼吁进行自然导向性文学研究,倡导与人类中心义相对的自然中心主义思想。从乔纳森·贝特的《浪漫主义生态学:华兹华斯与环境传统》(1991)、卡尔·克鲁柏的《生态文学批评:浪漫的想象与生态意识》(1994)、劳伦斯·布伊尔的《环境的想象:梭罗,自然书写和美国文化结构的构成》(1995)到格罗特菲尔蒂的《生态批评读本》(1996)和乔尼·亚当森的《环境正义读本》(2002),西方生态诗学研究视角从挑战人类中心论的自然复魅研究,延展至为世界环境人文实践提供理论支撑的环境正义文化研究。生态诗学研究对象的范围从集中关注自然写作、自然诗歌和荒野小说等体裁到研究多种景观,研究对象的变化说明了“关于批评内部环境责任感的争论更加激烈,使得此运动走向一个更侧重以社会为中心的方向”[2](P153)。生态批评家逐渐意识到无人类打扰的自然荒野形式、结构和内在成分不平衡状态,“亚当森首次将环境正义思想应用到文学批评领域,标志着生态批评由园地伦理、荒野哲学向社会生态哲学转变”[3](P138)。社会文化研究视角的介入催生了众多生态批评流派,包括后殖民生态批评、环境正义生态批评和城市生态批评;生态批评家将全球化背景下的种族、性别、阶级等维度纳入生态诗学研究范畴,环境正义成为新时期生态批评的主要视角之一。亚当森、斯洛维克、索恩伯、朱莉·塞斯将自然书写与环境正义文化研究方法结合,从种族、性别、阶级层面剖析自然的多重属性,将“自然的社会属性、物质属性和价值属性纳入被殖民历史情境,研究第三世界国家与西方中心国家的对话关系对各自本土环境建设的重要作用”[4](P302)。
实际上,在生态批评学科建制之初,西方学界就很重视关于中国生态话语的研究,哈佛大学出版社先后出版《佛学与生态学》(1997)、《儒学与生态》(1998)、《道教与生态学》(2001),为后续索恩伯等比较生态文学学者的研究奠定了基础。近年来,以卡纳万·盖伊的文章《勒·吉恩的乌托邦小说中的道家、生态与世界化约》(2014)为代表的西方生态批评实践开始以东方生态理论话语阐释其本土生态文本,中国传统生态话语日渐成为西方生态批评的重要视角。2010年以来,西方至上观念开始消解,具有本土性的地方生态现象成为诗学理论研究的重要内容。比较文学研究者开始纯熟地运用比较文学平行研究、影响研究和阐发研究方法阐释不同国家或地区生态文学的世界性因素,他们“发挥自身的学科优势,从生态批评的视角展开跨文化比较研究”[5]。文学与环境研究的跨国别转向是生态批评与比较文学研究方法聚合的直观体现。随着生态世界主义思想盛行,生态批评研究对象不再局限于地区或单民族生态现象,开始影响公众意识和个人认知。索恩伯的《生态含混:环境危机与东亚文学》(2012)从比较文学视角直接引述中、日、韩等原语作品来研究东亚地区生态文学特征,标志着比较生态批评研究这一新兴潮流的兴起。
与此同时,亚太生态批评研究与西方生态诗学研究的对话关系逐步建立起来,在研究方法和对象层面实现了互鉴共通。以中国生态批评研究为例,从20世纪90年代中国学者第一代生态美学研究学者鲁枢元、王宁的研究工作至今,中国日渐发展成为环境人文研究重镇。中国生态批评批评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全球化与生态批评专题研讨会”(2001),由清华大学和耶鲁大学联合承办,标志着“生态批评”正式作为文学、文化研究术语为中国文论界所接受。山东大学承办的“人与自然:当代生态文明视野中的美学与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2005)及由北京大学承办的“生态文学与环境教育国际研讨会”(2009)标志着中国的生态批评话语渐成体系,但是,那时的生态批评研究仍停留在对西方生态话语和方法理论的借鉴层面。2010年后,中国的生态批评话语体系日臻完善,中国生态批评话语开始实现与世界环境人文研究术语接轨。2015年,由上海师范大学承办,以物质性、可持续性与应用性为主题的“环境人文学国际研讨会”标志着中国环境人文开始成为显学;值得一提的是,2019年,美国“文学与环境研究会”(ASLE)年会的主题即是关于物质性、可持续和人类纪时代的环境人文发展的探讨。近两年,中国香港日渐成为亚太环境人文研究的地缘核心,继香港大学承办“亚洲生态电影的背景化:过去与未来”(2016)国际研讨会之后,香港中文大学举办讨论组会“亚洲环境人文:生态危机与文化反映”(2018)及香港岭南大学即将承办的“国际环境人文会议”(2019)均表明亚太地区政治优势和生态文明诉求的日益凸显,东方生态美学话语相较于西方生态话语的劣势地位开始逆转。
中国环境人文兼具本土生态美学和世界环境人文实践特色,东方生态理念开始对西方环境人文思想产生“反影响”。曾繁仁、鲁枢元、程虹、赵白生、龚浩敏(中国香港)、韦清琦、陈红、刘蓓等中国生态批评家开始与西方环境人文学者合作著述。在西蒙·艾斯图克主编的论文集《东亚生态批评》(2013)中,杨金才、陈红、鲁枢元分别从文学的环境维度、本土性、美学鉴赏等视角介绍中国当代生态批评研究现状;斯洛维克主编的《生态含混、社区和发展》(2014)中,以刘彦君为代表的中国学者开始探究将环境正义视角引入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路径和方法;韦清琦、格里塔·加德的论文“跨文化女性主义伦理的研究工具”(2018)从跨文化女性主义伦理学视角探讨反种族压迫的生态女性主义策略。除此之外,美国生态批评家程佳茹将于2019年出版《中国环境人文:环境实践的边缘地带》,从跨国别视角强调中国生态批评在世界环境人文领域的重要地位。在环境正义文化研究和多元行动主义人文实践层面,中西生态诗学对话研究热点存异趋同,世界开始聆听中国声音,世界生态诗学跨国别转向呈矢在弦上之势。
二、跨国别转向的机遇及挑战
新时期生态诗学及环境人文研究在重视地方生态本土性的同时,开始超越民族与国家界线,从世界主义视角“将(美国)文化置于国际框架中,针对全球化带来环境问题提出相应对策”[6](P381)。现今世界生态诗学研究领域一改往昔白人主唱的局面,呈现多元民族文化大合唱盛景。当代中国生态美学为新时期美丽中国建设实践提供了话语支撑,美国生态批评理论研究及环境正义文化研究为环境人文实践活动提供了理论参照。中西生态诗学研究其中任何一方在理论层面取得突破,都会促成跨国别生态诗学理论建构的完善,形成明显的二律背反辩证关系。生态诗学研究从关注“环境”“生态”概念内涵开始转向对外在民族、社会生态的环境正义问题研究。世界生态诗学研究的跨国别转向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
一方面,21世纪初,亚当森的多元文化生态诗学及索恩伯的比较生态文学视角先后扩展了西方生态诗学的研究范畴。多元文化生态诗学以环境正义思想为主线,研究美国族裔文学反映的社会、自然生态现象,将西方生态批评关注点从荒野自然引至社会环境现象。“亚当森与斯洛维克、塞斯等学者将环境正义文化研究作为生态批评理论研究的重要分支,从种族、阶级、性别、殖民和自然等因素考量经济正义、社会正义与环境问题间的联系。”[7](P408)2010年后,索恩伯、海瑟等比较文学研究学者将平行研究、影响研究方法用于生态文学批评实践,将多元文化生态诗学和环境正义文化研究的疆域从美国本土扩展至东亚地区,直接引述中、韩、日等东亚文学原文,阐释东亚生态文学创作及批评实践中的生态含混现象,试图从东亚地区文学创作和批评入手研究区域文化、个体对自然及社会环境的态度。无独有偶,黄新雅基于对琳达·霍根(美)的《鲸人》、维蒂·希麦拉(新西兰)的《鲸骑士》、夏曼·兰波安(中国台湾)的《天空之眼》这三部海洋叙事文本的研究,提出跨太平洋生态诗学构想,强调“海洋本土文化在全球生态话语中重要性”[8](P114)。东西方比较文学及生态批评学者开始跨越语言障碍,研究对象的选取标准不再局限于某一地方文学。
另一方面,当下世界生态批评理论研究处于井喷阶段。生态批评理论以多极视野构成新的认知范式,具有明显的多元性及块茎性等后现代理论研究特征,被欧普曼称为“后现代生态批评”。在伊奥凡诺与欧普曼编撰的《物质生态批评》(2014)中,斯坦西·阿莱默提出的跨肉身性概念及亚当森提出的自我诗学概念等,共同颠覆了物种、种族主义的共谋关系,将文学与生态实践关系具象化,彻底拉开了将生态批评理论引导环境人文实践的帷幕。皮帕·马兰德、苏珊·海客曼等学者以本体论方法阐释物质叙事能力,将生态诗学研究推进新的发展阶段,即物质生态批评。通过预设人类和非人类物质关系,物质生态批评强调文学叙事是由故事物质(Storied Matter)集合而成的故事世界(Storied World),客观存在的物质与主观的人类经验、世界与文本形成动因式交错关系,互为影响驱动因素。物质生态批评颠覆了人类与非人类物质施事关系,揭示人类和物质互为主客现象,消解人类中心主义和自然中心主义隔阂,缓冲物种主义与种族主义之间冲突。
但是,生态诗学跨国别转向仍面临挑战:第一,全球化背景下国别间文化存在冲突,“需建构游刃于文化、经济、政治和技术中具有共同体性质的统一理论基础,催化生态批评自身的跨国转向”[9](P159)。在生态世界主义理念指导下,重视各民族本土生态话语,构建植根本土、放眼世界的生态诗学理论。第二,当前比较生态文学在比较文学阐发研究方法论的运用层面仍显片面,以西方环境美学话语阐发东方文学的批评实践远超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生态话语阐发西方文本的 “反阐发”实践。生态诗学的跨国别转向不同民族生态话语的交融借鉴,从本土文化、历史、现实角度共同为生态批评走向环境人文实践提供方法论支持。埃尔多·利奥波德曾将生态学定义为“关于共同体的科学”[10](P340)。如今,生态诗学研究兼具理论性和应用性,重视本土局部特征及不同文化间的悖谬关系研究,场域边界开始从地方扩展至全球,共谋生态共同体福祉。西方至上观念开始消解,平等对话关系日益形成,跨国别生态诗学建构时机业已成熟。
三、跨国别生态诗学理论根基及特征
新时期生态诗学研究表现出明显的跨文化和跨国别趋向,但关于其多元化的本体论立场和多样的阐释方法仍褒贬不一。欧普曼、亚当森先后以吉尔·德勒兹和瓜塔里在《一千座高原》(1980)中构建的块茎(Rhizome)模型阐释生态批评理论发展轨迹的形象:其开枝散叶的开放多元姿态下隐含着庞大集中的理论根茎,与其他生态学科理论属于变异结盟关系。植物学意义上的块茎性是指植物根茎生长现象,以确保能为繁枝茂叶茂提供充足养分。[11](P174)作为后现代思维非等级模式的一个典型隐喻,块茎性强调理论研究的差异和多样性特征,反对任何形式的总和。[12](P20)尽管生态批评博采众长的块茎性本质为人所共知,但生态批评发展至今,构建基本理论原则并探究清晰方法论体系仍显得尤为重要。
21世纪初,亚当森以环境正义理念为主线的多元文化生态诗学相关概念反思美国工具理性文化带来的环境非正义文化现象,贯通了美国族裔文学研究、环境正义文化研究及环境人文实践,使生态文学批评由学院派走向指导环境人文实践的第一线。多元文化生态诗学相关概念诸如文学观察工具(Literary Seeing Instrument)、中间地带(The Middle Place)、变革主体(Transformational Beings)、环境正义(Environmental Justice)等,可为厘定跨国别生态诗学的边界提供理论参照。
第一,文学观察工具为跨国别生态诗学确定研究对象提供了理论支撑。文学观察工具是与列维·施特劳斯和芭芭拉·巴伯科克研究神话的科学方法类似的概念,主张将区域民族传统和现实生态现象的纪事作为媒介,以“口头文学、诗歌、小说等体裁作为观察工具,考察地域文化兼具本土性和世界性叙事程式”[13](P258)。跨国别生态诗学以具体生态问题为导向,以承载特定族群故事和传说的民族叙事作为文学观察工具,追溯种族文化根源,为跨国别生态诗学从生态世界主义视角关照本土生态现象,证明生态世界主义思想与本土文学的辩证联系提供了理论依据。跨国别生态诗学以记载特定地域文化的文本为观察工具,考察不同族群、个体与环境的关系,探究不同族群、社区人们影响环境的行为动机。亚当森主持的安德鲁·梅隆基金支持的环境人文项目设立“希望警世档案数据库”,是以跨国别本土知识体系为文学观察工具,以文本想象力量推进环境人文实践的有益尝试。
第二,中间地带概念发展了范·基尼和维克多·图纳的阈限性概念,概括了族裔文学研究、生态批评与社会生态实践的交互关系。跨国别生态诗学的建构过程实质上就是中间地带概念落地生根的历程,旨在为双方搭建对话平台。范·基尼在《过渡礼仪》(1960)中将阈限性定义为跨域空间差异、超越凡俗神圣界限的状态,图纳将阈限性称为交叉融合关系,亚当森基于对西尔科、谢尔曼等印第安裔作家作品中的前景化现象研究,强调中间地带概念对环境人文实践的重要性:“固守单声部集权,以发号施令的形式号召大家采取行动注定只能产生微弱影响。我们需要学者和先锋置身种族、物种的中间地带,聆听、质询、体察不同族群和种群需求,并将之付诸实践。”[14](P156)不同群体、种族之间的交流具有模糊、混杂居间特性,通过搭建(具象化的)中间地带,将穷人、边缘族群和有色人种从某种特定权利桎梏中解救出来,使他们能够为自己发声。结合约翰·布林克奥夫·杰克森的乡土景观与精选政治景观概念,亚当森整合了普韦布洛族和纳瓦霍族争取环境正义的事件纪实,将中间地带概念上升为生态文学研究及环境保护运动的中介术语及环境正义文化研究的学科宣言。中间地带概念将跨国别生态诗学的边界具象为双边文化的交互地带,其研究目标是将“异文化”与“自文化”进行比较研究,消解对话主体因语言、习惯不同产生的临界性、异质性、混杂性和矛盾性。
第三,变革主体概念的雏形是亚当森在“为何理论不会扼杀熊的思想:厄德里奇《痕迹》中转换理念和口述传统”(1992)提出的变革角色(Transformational Characters)概念。正如人类癫狂和疯癫状态实质上是内在欲望的防御表现,“熊”具有文化交流中的种(族)群双方由于文化隔阂而将对方形象野蛮化的象征意义。变革角色超越物种、种族界限,反映出印第安文学作品与主流白人社会交流过程运用的自我心理防御策略。在跨国别生态诗学建构过程中,由于语言、文化、地方生态、经济、政治和社会状况的不同,对话双方易将对方形象野蛮化;变革主体概念为消解跨国别对话双方隔阂提供了思路。以厄德里奇在《痕迹》中塑造的主人公弗勒为例,她能够在“熊”和族群人类身份之间自由切换,无法被带入任何秩序当中,她的发肤制成的“爱药”有着令人起死回生的功效。部落族人一边将她妖魔化为狡诈的白狼,一边用同样的配方和步骤制出的药却没有“爱药”的功效,其根本原因是“不知如何(用正确语言)询问使用方法”[15](P195)。厄德里奇以“失效的爱药”来喻指不同族群、物种交流过程中语言的重要性:只有学会对方语言,才能消除误解,建构起真正意义上的中间地带。作为多元生态叙事策略之一,变革主体概念可上升至变革生态批评(Transformative Ecocriticism)的高度,将自然概念重构为由人类、非人类及介于二者之间的变革主体组成的生态整体。由生态批评家担当变革主体角色,运用文学、环境和文化研究方法,规避区域中心主义局限,建构共同的批评理论基础,“以满足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文学批评实践,探寻解决地方、国别乃至全球的社会环境及生态环境问题的途径”[14](P83)。
第四,跨国别生态诗学整合全球生态文化叙事,减少霸权论述对弱势声音的消解现象,属环境正义文化批评范畴。环境正义概念包涵人与自然他者(种际正义)、人与后代(代际正义)等多重关系,为跨国别生态诗学建构提供了研究视角。亚当森作为首位将环境正义概念引入生态批评研究的学者,通过考量西蒙·奥特斯、约翰·麦克菲、格蕾特尔·埃利希等作家文本中关于牧民、矿工的描写,揭露地域生态与现代工业景观之间的冲突,将生态批评引向更负责任的发展方向,呼吁“不再有更多牺牲”[14](P84)。环境正义为重新审视自然荒野和人类文化的关系提供了新的视角。1939年,美国为保护沙漠大角羊在亚利桑那州西南部美墨边境的尤马沙漠建立卡韦萨·普里伊塔国家野生动物保护区,区域内的图霍诺·奥德哈姆原住民部落被重新安置,“沙漠居民的迁出意味着这片达3 840平方公里原始荒野彻底没有了人类活动迹象,成为人类文化让位于自然生物的牺牲区域”[14](P16)。跨国别生态诗学追求种际间平衡共处关系,为避免陷入浅层生态学,以人类需求为尺度,对自然改造或人类绝对让步于其他物种的生态哲学怪圈寻求解决路径。相较于种际正义的研究,跨国别生态诗学在研究种族和殖民文化生态正义的霸权语境层面显现出先天优势,将南北正义视角引入了生态诗学研究范畴,辩证地看待人类中心主义和西方中心主义思想弊端。亚当森在“环境人文的根基与轨迹:从环境正义到代际正义”(2017)中,从代际正义、族际正义等跨国别视角分析电影“通天塔”(2006)中体现的环境非正义现象,将摩洛哥、日本、墨西哥和美国跨国别文化间的环境非正义现象上升至代际正义层面,为跨国别生态诗学从南北正义文化研究视角进行批评实践提供了范式。
多元文化生态诗学的以上概念厘定了跨国别生态诗学的边界和特征:文学观察工具概念确定其研究对象,中间地带概念划定其边界,变革主体概念为消解对话主体矛盾提供了思路,环境正义概念指明了未来发展方向。跨国别生态诗学不再局限于单民族生态文学现象,而是致力消弭物种、族群、国别等二元对立因素间的界线,表现出本土性和整体性特征。跨国别生态诗学始自于对生态文学文本的世界性因素的关注,但又不止于文学文本细读,在理论研究及批评实践层面汇集环境美学、环境社会学、政治生态学研究成果,表现出明显的块茎性属性。此外,由亚当森主持的世界环境人文项目在北美洲、亚洲、澳大利亚、英国和非洲设置的八大环境人文整合平台是跨国别生态诗学的实践性和现实性的体现,值得一提的是,曾繁仁、程相占等中国学者曾参与其中的亚太人文整合平台建设。可以说,植根本土环境、面向全球生态,以问题为导向的跨国别生态诗学已现雏形。
四、跨国别生态诗学建构中的中国话语
世界生态诗学研究在经历了与马尔萨斯主义、浅层生态学等思想的论争之后,又迎来理论多元论与理论一元论的质疑:海瑟(2008)和吉福德·泰瑞(2010)等学者指出世界生态批评亟待建构系统的理论框架。针对当前世界生态诗学的跨国别转向趋势,笔者尝试梳理跨国别生态诗学研究的理论基础,为整合中西传统生态文化资源、规避以西释中或以中释西的片面性提供路径,拉开中西生态诗学平等对话的帷幕。
在研究方向及空间层面,跨国别生态诗学为中国生态话语与西方诗学术语的跨国别对接提供了中间地带。生态批评与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开始聚合,中国承办的国际生态诗学会议名称流变过程也表明中国生态话语参与世界环境人文学科建构的趋势。跨国别生态诗学重视具有本土性和异质性特征的生态元素,将东西方生态诗学对话关系明确为垒筑生态共同体,构建适于各表一枝的本土生态话语对话的平台。
在研究对象及主题层面,跨国别生态诗学可将儒、道、佛、禅为代表的中国生态话语作为观察工具,以平行研究、阐发研究、影响研究方法对西方生态文学文本进行“反阐发”实践,丰富比较生态文学范畴。后续跨国别生态诗学研究可细分东西方诗学对话主题,如对乌托邦小说、科幻小说等文学体裁中生态元素的比较研究等。
在研究主体及方法层面,跨国别生态诗学明确生态批评家为变革主体,亚当森、欧普曼、海瑟、斯洛维克、索恩伯、塞斯等西方学者从环境正义文化研究视角强调以中国生态话语为代表的东方思想的重要性,以曾繁仁、鲁枢元、程相占为代表的中国学者也开始参与到世界环境人文实践中去。跨国别生态诗学建构可为后续比较生态批评研究及环境人文实践提供方法论依据。
总之,未来的跨国别生态研究以中西生态批评家为变革主体,从多元到贯通,在重视本土性生态元素研究的同时关注各民族生态文学主体间性,为环境人文实践提供方法论支持。后续生态批评理论研究可回溯跨国别生态诗学概念渊源,在此基础上展望其对世界生态批评理论对话及环境人文实践的指导意义,为实现诗意的栖居构建坚实的理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