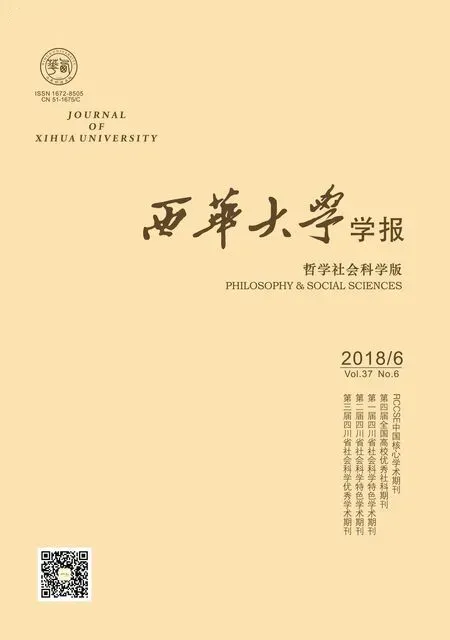从可能世界理论看迟子建《额尔古纳河右岸》对中国当代生态小说困境的突破
石访访
(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 四川成都 610064)
生态文学缘起于在世界范围内愈演愈烈的生态危机,奥尔多·利奥波德首倡生态整体主义的精神思想,而蕾切尔·卡森于1962出版的《寂静的春天》,在“改变了历史进程”的同时,昭示着生态文学的真正到来。西方的生态话语与文学在中国的译介与传播,加之中国现实的生态问题催生出中国当代生态文学,其始于20世纪80年代,以纪实型报告文学为起点,随即卷入诗歌、散文、戏剧等领域,尤以生态小说的繁荣为象。
相较于纪实型叙述对生态恶化的具象呈现与数字化展示,小说作为虚构叙述,本可以建构起一个丰富多彩的文本世界,以形象的方式论述具体生命与生态的复杂关系,使文学叙述具有跳动的生命脉搏。然而,就中国当代生态小说的现状而言,其所承载的现实社会职责与作为虚构叙述的文本体裁,却使之在一定程度上囿于“生态”与“文学”的双重困境。而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则在一定程度上显示出中国当代生态小说在困境中的发展。
一、《额尔古纳河右岸》与生态小说的“虚”与“实”
《额尔古纳河右岸》初刊于2005年第6期《收获》杂志,并于2008年获得第七届“茅盾文学奖”,以此受到更为广泛的阅读和学术研究的关注。将携带着官方意义与意识形态色彩的“茅盾文学奖”授予一部生态小说,这本身就意味着对中国当代生态小说所取得的文学成就与社会意义的认可,在这个层面上,《额尔古纳河右岸》在中国当代生态小说中具有着里程碑式的意义。
《额尔古纳河右岸》继承了迟子建惯有的“对温情生活的辛酸表达”,同时显现出书写生态、历史与文化的厚重感。本书以年逾九十的鄂温克民族最后一位酋长的女人兼任叙述者,将“额尔古纳河右岸的森林作为舞台”,讲述鄂温克民族近百年的历史与变迁。在这个意义上,《额尔古纳河右岸》成为中国第一部真正意义上书写“第四世界”的生态小说,所谓“第四世界”,由著名的土著人运动领袖George Manuel提出,用以指称那些保持着以采集-狩猎为主要生活方式,大都生活在世界边缘,游离于世界文明之外的非主流群体①,文中的“鄂温克民族”正是一种典型的“第四世界”。通过叙述大兴安岭与鄂温克族在现代文明进程中的遭遇与命运,《额尔古纳河右岸》体现出以生态反思文明的深度,从而成为中国当代生态小说的一个典型。
实际上,除却书写内容的典型以及在当代文坛所具有的里程碑式的意义,《额尔古纳右岸》更在文本叙述的层面体现出生态小说在“虚构体裁”与“现实职责”之间的张力,展现出中国当代生态小说在磨合“生态”与“文学”过程中的突破。
生态小说,归属于生态文学的门类之下,其兴起与繁荣是人类为减轻和防止生态灾难的迫切需要在文学领域的必然表现,也是文学作家对地球以及所有地球生命之命运的深刻忧虑在创作中的必然反映[1]1。因此,生态警示的社会价值自然成为其创作的目标与题旨。然而,就文本的叙述体裁而言,生态小说,作为一种特殊的小说类型,其根本的特质依然定点在“小说”的虚构性。这种虚构性叙述的文本体裁,取决于文化的程式规定,文化决定生态小说被作为“虚构”进行创作与接收,并认定其呈现一个“无关事实”的文本世界[2]65。这种“无关事实”并不是指虚构叙述的内容必然与经验世界无关,而是指这类体裁程式本身就无法对其内容提出“与事实相关”的要求。
因此,作为“小说”的虚构特质与归属于“生态”的现实指向,使得生态小说呈现出一种“虚”与“实”的矛盾,这种看似悖论的矛盾,并非源于小说形式与生态内容的错位,而是涉及到更为根本的文学虚构叙述与现实世界的关系问题。“生态”的前缀与“小说”的限定,暗示着生态小说在可能世界与现实世界之间的通达性。
依据可能世界理论,生态小说实际上可以理解为一种从可能世界出发探向实在世界以获取生态警示效果的叙述,其虚构特质与现实指向之间并非是对立的,而是任何虚构叙述共有的一种通达属性。只是这种通达性,一方面作为任何虚构叙述的共性,另一方面又在生态小说中显现出特性,从而彰显出生态小说为其自身的缘由:生态小说对实在世界的通达既是自身构筑文本世界所无法回避的叙述方式,同时也肩负着实在世界所赋予其的社会职责,通过对实在世界相关元素的通达,生态小说再现一个“可能”与“实在”混杂的虚构世界,并最终借此导向对实在世界的生态批判。
因此,从叙述学的角度来说,《额尔古纳河右岸》正是一部基础语义域立足于可能世界,而又通达实在生态元素的小说,这种通达既是“小说”作为虚构的叙述方式,又是“生态”对叙述做出的“现实性”要求。文本正是凭借对现实世界的大兴安岭与敖鲁古雅的鄂温克民族的通达,在构筑起虚构的文本世界的同时,折射出现实的生态反思。在这个意义上,生态小说并不存在“虚”与“实”的悖论,而只有坐“虚”(可能世界)探“实”(实在世界)的通达。
二、通达与生态小说的“现实性”
中国当代生态小说的产生与现实的生态危机直接相关,其以揭示生态问题,拷问人与自然、人与其他生命的伦理关系为己任,集束式地呈现在中国当代文坛,并希冀获得相应的社会关注与生态效果。这种与现实紧密连接的特质,规约了中国当代生态小说的表意诉求:力求对生态现状作“真实”的摹写,成为虚构型生态小说的叙述特质,并具象地显现为文本世界对实在世界的密集通达。
《额尔古纳河右岸》对实在世界的通达是明显的:“额尔古纳河右岸”作为情节的发生地是锚定于实在世界的现实地点,“鄂温克民族”是对实在世界的鄂温克族与鄂伦春族的通达以及乌力楞的靠老宝,还有可以看见星星的希楞柱,萨满文化与信仰,日本人的入侵与训练营,俄国商人的“安达”,日本与苏联的战争与冲突,20世纪60年代的大兴安岭开发,鄂温克人的下山定居,都是锚定在实在世界元素上的叙述。甚至是走出山林又回归山林,最终在困惑中葬身河流的鄂温克画家“依莲娜”,也是对实在世界中鄂温克画家柳芭命运的对应。这种通达显现出作为虚构叙述的生态小说与实在世界之间的“寄生”关系:“一有机会就附着在实在世界的经验关系上,但是并不是整体都浸入现实”[2]194。
对实在世界生态元素的密集通达,实际上是中国当代生态小说的共性,通过从微观的词语细节到规模较大的叙述情节,甚至是思想逻辑与宗教信仰的通达,生态小说构筑起一个具有“真实感”的文本世界,从而呈现出“现实性”的风格特征。因为“虚构的可能世界与实在世界通达关系数量越大,两者距离越近,虚构叙述的‘现实性’越强。”[2]195在这个意义上,生态小说通过对实在世界密集而近乎覆盖的通达,使文本叙述具有一种强烈的“现实感”,并希冀借此取得社会的认同与生态警示的现实意义。然而,这种“现实感”从反面来说,也在一定程度上致使生态小说陷入“有生态而无文学”的困境。
若仅就文本风格而言,无论“现实性”还是“幻想性”并无上下之分,如同纪实与虚构作为叙述的两大门类,并无优劣之分。然而问题的关键在于,文本世界是一个符号再现的媒介化世界,是一个有限度的世界,当虚构叙述中的实在世界元素过多,而形成“现实性”风格之时,其从反面而言就意味着对可能世界元素的挤压以及文学“幻想性”的降低。更为关键的是,实在世界乃是一个没有限度的世界,其细节无限饱满,文本建构起的有限世界根本无法穷尽其细节。因此,生态小说作为虚构型叙述,其基础语义域立足于可能世界,在文本世界中,对实在元素的通达不应过分地追求数量,而可能元素也应当维持一定的限度以保证虚构文学的想象特质及其审美维度。正如米兰·昆德拉所言:“小说是这样一个场所,想象力在其中可以像在梦中一样迸发”,“发现唯有小说才能发现的东西,乃是小说唯一存在的理由”[3]21。
实际上,中国当代生态小说滑入“有生态而无文学”之困境的症结以及《额尔古纳河右岸》对以往生态小说的突破正在于此,多数生态小说就通达社会现实情况的信息密度与数量级而言,并非不足,而是过度。急迫的生态危机对作为文学叙述的生态小说树立了过高的社会使命。揭示生态危机的现状、教化民众的责任,以及自身面对生态的深刻忧虑,使得生态小说的创作者迫切需要接受者的认同与社会的回应,从而对实在世界的生态境况进行过度密集的通达以求得“现实感”,却也因此压缩了可能世界的展开维度,从而无法调动充沛的想象以构筑起一个多彩的文本世界,小说作为文学的审美特质也因此流失。
其次,教师在授课过程中,要将阿姨的人生经验充分揉进来,比如,过去的人喜欢给婴儿剃茶壶盖的发型,其实背后的道理是为了保护孩子的囟门,现在的人都知道小孩子不能捂得太狠,跟民间说的“若要婴儿安,常带三分饥和寒”是一个道理。不是所有民间知识都是落后的,将老师讲授的科学知识与她们所掌握的一些生活经验对应起来,告诉她们哪些是对的?背后的道理是什么?哪些是不对的?为什么?帮助她们把已有的认知进一步清晰和升华,她们的理解会更深刻。
《额尔古纳河右岸》的文本叙述并不限于这种“求真”的书写,“可能因素”在文本世界中与“实在因素”平衡的共存:刻画在粗壮大树上的白那查山神;依芙琳哭泣时为其拭去眼泪的蛇,以及其旋转舞蹈时达玛拉借蛇之口所说出的话语;尼都萨满与妮浩萨满通灵天与地的舞蹈;伊万葬礼上身穿素白衣裳的俊俏姑娘,乃是其年轻时在山林放过的白狐狸;妮浩翻下沟谷的瞬间探出双手拦下她的黑桦树,乃是其自愿替母死去的儿子耶尔尼斯涅所化。《额尔古纳河右岸》构筑了一个实在元素与可能元素混合的文本世界,其基础语义域立足于可能世界,却导向实在世界以获得“现实感”,同时又依从“心理可能性”展开想象的维度,在可能世界元素的充分叙述中,呈现一个通达而丰富多彩的“额尔古纳河右岸”。
生态小说,就“生态”而言,社会警示与批判的现实职责使其必须与“现实”相关;就“小说”的层面而言,其所构筑的虚构世界乃是心智想象的产物,叙述只需依从“心理可能性”,就本体意义而言“无关事实”。因此,在通达实在世界以获取“现实感”与生态效应的同时,平衡可能因素与实在因素在文本世界中的数量级关系,发挥虚构叙述想象的优势,呈现小说的审美特质与诗性魅力,正是满足生态小说对“生态性”与“文学性”双重诉求的叙述方式。
三、认同效果与文化程式
中国当代生态小说所承载的社会职责以及作者深刻的现实忧虑,使得小说对“实在世界”的生态因素采取了密集式通达,并希冀借此取得叙述的“真实感”与社会认同效应。英国的福特·马多克斯·福特指出,“优秀的现代小说,追求一个共同的目标”,即“抓住读者,用一个事实将其淹没,使他意识不到自己正在读小说,也意识不到作家的存在”[4]34。这种对文学叙述的逼真性以及认同效果的追求,在叙述学中称为“浸没”。生态小说所力求的社会警示效应正是读者被叙述“浸没”后的自然结果。
问题的关键在于,对实在世界生态细节的密集通达是否真的能够取得这种“浸没”效果?换言之,生态小说叙述所追求的“真实感”,是否真的与通达实在元素的信息量成正比关系?依靠增加实在生态境况与细节元素的数量,生态小说是否便能够突破虚构叙述的体裁界限,做到“有关事实”?
事实上,通过对实在元素的通达,虚构叙述的确可以营造出文本的“现实性”风格特质。然而,“现实性”的文本风格特征与“逼真性”的文本阅读效果并不能够等同,前者是文本叙述的内在风格,的确可以依靠通达点的数量得以完成;而后者则是读者对文本的认知态度,其“首要条件是叙述文本与读者分享对叙述内容的规范性判断”[5]242,而这种规范则取决于社会文化形态。文学过程作为一种“共同体”,必须依赖这种相互关系才能存在[6]86-96。换言之,文本之隔即是“世界”之隔,虚构叙述对实在世界的通达并不能够抹去“文本世界”与实在世界的界限,也无法突破虚构叙述体裁“无关事实”的界定。叙述认同效果的取得,其关键并不在于通达实在世界的信息量,而是叙述文本与读者之间是否共享文化的程式规范。
在这个意义上,多数的中国生态小说,执着于对实在生态元素作密集通达的创作现状,压缩了其文学性与审美维度,致使其陷入“有生态无文学”的困境,即使仅就“生态”层面而言,这种密集的通达也并不能真正取得其所追求的社会认同与生态警示效果。
赵毅衡先生在《当说者被说的时候》中指出,“文学叙述,是语言符号的特殊集合,它在语言符号系统上另外附加一个构造,这个构造(叙述的文类要求)本身构成了符号体系,而这个符号体系,更需要社会文化形态提供编码与解码的转换方式”[5]247。这种文学叙述的编码与解码,依赖发送者与接收者之间共享一套文化的元语言规则。因此,作为具有现实诉求的虚构叙述,生态小说所希冀取得的认同效果,只有依靠叙述文本与读者之间文化程式的彼此契合。
然而,中国当代生态小说,其叙述背后的生态伦理思想与文化逻辑,在很大程度上移植于20世纪60年代在西方兴起的生态话语批评,其以“生态整体主义”为核心思想,即“把生态系统的整体利益作为最高价值而不是把人类的利益作为最高价值,把是否有利于维持和保护生态系统的完整、和谐、稳定、平衡和持续发展作为衡量一切事物的根本尺度,作为批判人类思想文化、生活方式、科技进步、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终极标准”[1]10。简而言之,即将人类视为生态的一部分,而不再是“万物的尺度”。这种生态整体主义思想的合理性毋庸置疑,问题在于,其在西方的提出,是建立在西方社会经过现代化高度发展之后,所做出的评判性反省,而中国的现实则正处于一种复杂的“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并置共存”的文明发展的差序格局。因此,以西方生态整体主义为思想逻辑进行书写的中国生态小说,其与中国当代现实的社会文化形态之间必然存在着错位,而中国传统的“无为”“桃源”等生态思想与中国当下的社会文化形态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
中国当代诸多生态小说中存在着的自然复魅、退守桃源、生物神化、人类恶化以及“反现代化”的倾向,都显现出小说的文本叙述的文化逻辑,与中国当下社会复杂的文化形态之间的矛盾。这种文化逻辑错位的生态小说,从根本上阻碍了生态小说在现代社会取得“浸没”的效果以及相关的现实效应,从而使得生态小说在“生态价值”的层面亦陷入困境。
这种困境反映在生态小说中,便是文本对中国现实社会的通达,仅仅停留在对生态恶化现象的平面揭示,李克威《中国虎》书写生态恶化以及华南虎面临灭绝的现实,以及引起一定社会关注的《狐啸》《狼图腾》《最后一只白虎》都不同程度上局限于暴露问题、批判现象的平面化叙述,而无法透过生态危机的现象,审视其背后的中国社会现实与文化系统。生态问题,不是生态本身的问题,而是人与文化的问题。因此,生态小说(文学)的第一要务不是对生态危机的现象做出平面化的通达,而是以通达探取现象背后的深刻的人文缘由,生态小说(文学)乃是隶属于作为“人学”的文学,而非生物学或环境学。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额尔古纳河右岸》显示出其以生态反思文化的深度内涵。文本对实在生态现象的通达,集中在20世纪60年代对“绿色宝库”大兴安岭的大规模开发:“大批的林业工人进驻山林,运材路一条连着一条出现,铁路也修建起来。在公路和铁路上,每天呼啸而过的都是开向山外的运材汽车和火车。伐木声取代了鸟鸣,炊烟取代了云朵”。“持续的开发和不负责任的挥霍行径,使那片原始森林出现苍老、退化的迹象”[7]263。林木稀疏,动物锐减,敖鲁古雅的鄂温克人被迫下山定居。相较于传统生态小说以焦灼、全面、求实的心态暴露过度开发所造成的恶化景象,《额尔古纳河右岸》则在实在元素与可能元素的混合中书写了“马粪包”的死亡:当连续的运材车接连地驶过眼前,这个鄂温克人无法控制情绪地用猎枪扫射轮胎,最终死于伐木工的拳下。被伐木工人称为愚蠢、不可理喻而“找死的野人”的“马粪包”,是最后一个以放养驯鹿为生的游猎民族的代表,其在“文本世界”的死亡折射出现实中国的景象——现代化进程对自然生态与作为“第四世界”的鄂温克民族的双重吞噬。
迟子建坦言创作这部小说是“想借助那片广袤的山林和游猎在山林中的这支以饲养驯鹿为生的部落,写出人类文明进程中所遇到的尴尬、悲哀和无奈”[8]34-35。无论是大兴安岭,还是曾生活其中的鄂温克民族,都被现代文明碾过,在自然的过度开发与生态恶化的叙述背后,是现代化进程下的中国社会复杂的文化形态以及这种社会文化因素对人与自然生态所造成的影响。正是通过这种文本叙述与接收者文化程式的契合,《额尔古纳河右岸》得以取得接收者的认同以及随之而来的现实反思。
正如乔纳森·莱文(Jonathan levin)所言:“我们的社会文化的所有方面,共同决定了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生存方式。不研究这些,我们就无法深刻认识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而只能表达一些肤浅的忧虑。……因此,在文学如何表现自然之外,我们必须花更多的精力,分析所有决定人类对待自然的态度和生存于自然环境里的行为的社会文化因素,并将这种分析与文学结合起来。”[9]1098因此,在叙述生态问题,通达实在生态元素的同时,对中国当下的社会现实与文化形态进行深刻的投射,对人与自然关系中的社会文化因素做出剖析,既是中国当代生态小说取得社会认同的根本方式,也是虚构叙述对实在世界进行通达的社会意义。生态小说也由此避免形而下的具象堆积,在深刻的通达中获得社会认同与反思的现实效果,从而走出平面化“生态”的困境。
《额尔古纳河右岸》在可能元素与实在元素彼此和谐且平衡的混杂中,构筑起了一个现实感与想象性共存的文本世界。小说在对实在世界生态元素做出通达的同时,对生态现象背后的人类文明进程与中国当下复杂的文化形态做出投射,从而超越一般生态小说暴露形而下恶化景象的“问题”机制,呈现出生态问题背后的文化逻辑。这也正是《额尔古纳河右岸》被视为文化生态小说的缘由及其深刻性所在。它代表着中国当代生态文学的一种发展路径,即契合中国文化程式的“现实性”与充沛的“可能性”并存,并以此获得“生态”与“文学”的平衡。而这一发展路径的可行性与成果则需要中国当代生态小说的创作,并给予实践。
现代社会的文化形态日渐趋于复杂,合一的程式规范已不再可能,依靠读者与作品共享规范而取得认同效果,也变得愈加困难。实际上,文学叙述的意义本不拘泥于认同效果的取得,作为虚构叙述小说其价值更不在于此。然而任何公开发表的叙述都需要承担一定的社群责任[9]98-107,生态小说更是如此,从其诞生之日起所载负的警示与批判的社会职责,促使其对现实责任的承担以及对认同效果的追求。
因此,对中国社会“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并置共存”的文明差叙格局的深刻认知,对中国当下复杂的社会文化形态的洞察,面对不可逆的文明进程,对人与生态如何共存的思考,成为中国当代生态小说走出叙述困境的根本方式,并最终获得社会认同。而在具体的文本叙述中,则呈现为立足于可能世界,对实在世界有限而深度的通达,展开想象的维度以舒展可能元素的叙述,在“实在”与“可能”的混杂中构筑起一个多彩而深刻的“文本世界”。
注释:
① 1974年,加拿大“土著人运动”领袖George Manuel提出“第四世界”的概念,至1984年,地理学刊ANTIPODE发行“第四世界”专栏,将世界范围内的“土著民族”称为“第四世界”,这一概念逐渐受到认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