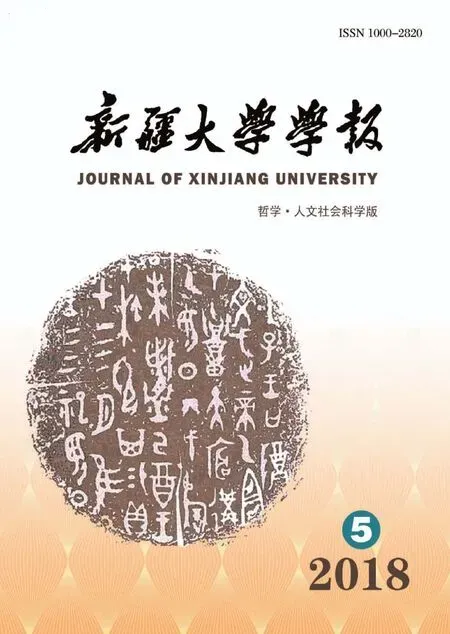唐音、宋调的离合
——论宋代闽地理学家的诗学之路*
张艳辉
(闽南师范大学文学院,福建漳州363000)
关键字:宋代闽地;理学家;唐音;宋调
宋代闽地理学大盛,有“家有洙、泗,户有邹、鲁”[1]之称。从载道南来的杨时,到罗从彦、李侗至于集大成的朱熹,闽地理学家辈出,而这些理学家同时兼具诗人的身份。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理学家的诗歌创作对宋代闽地的诗学发展起着不容忽视的作用。对于理学家的诗歌,四库馆臣如此评价:“以濂、洛之理责李、杜,李、杜不能争,天下亦不敢代为李、杜争。然而天下学为诗者,终宗李、杜,不宗濂、洛也。”[2]1737可谓确论。陈庆元在《宋代闽中理学家诗文——从杨时到林希逸》中综论闽籍理学家的诗文,而着重论述朱熹的诗文创作[3]。骆锦恋的《宋代闽地理学诗人诗歌理论与创作》则指出宋代闽地理学家以议论为诗的宋诗化的特点[4]。由此可见,对宋代闽地理学家诗歌创作的研究尚有余地。
一、北宋至两宋之交——兼具唐音、宋调时期
北宋诗坛流行的白体及西昆体在福建文人那里得到了回应,前者如邵武吴处厚,后者如浦城杨亿。而以“江西诗派”为代表的宗杜学韩的典型宋调也在宋仁宗之后确立,与江西接壤的福建或多或少受到了这一诗风的影响,例如蔡襄。但是,这一时期闽地理学家的诗歌创作却游离于两者之外,具有其独特性,代表人物有侯官陈襄、侯官郑穆、建阳游酢、将乐杨时、沙县陈瓘、剑浦罗从彦等人。
是时,闽地理学家大多强调温柔敦厚的诗教观念。如杨时主张:“为文要有温柔敦厚之气。”[5]游酢论诗以诗教为旨归:“诗之为言,发乎情也。……其要归必止乎礼义,有君臣之义焉,有父子之伦焉,和乐而不淫,怨诽而不乱,所谓发言为诗,故可以化天下而师后世学者。”[6]即便如此,理学家们并没有多少反映现实的作品,同时也并没有刻意将明理与作诗统一起来,说理不妨在文集中长篇大论,而作诗也不妨“缘情而绮靡”。因此,在诗学观念上显得比较含糊,没有明确的主张宗尚某家某派。正是因为闽地理学家在诗歌创作上缺乏主导思想,因此能够在同一个诗人的诗歌创作中具有不同风味,可以推崇李杜、韩孟,也可以模仿晚唐诗歌,当然也有与时代相应的宋诗气息。
推崇李杜者如杨时《向和卿览余诗见赠次韵奉酬》:“杜陵头白长昏昏,海图旧绣冬不温。更遭恶卧布衾裂,尽室受冻忧黎元。”《席上别蔡安礼》:“杜陵苦被微官缚,元亮今为世网撄。”杨时的崇杜,倒不见得是学习其艺术技巧,更多的是思想内容。倒是陈襄说:“老杜诗成笔力豪。”(《次韵和程少卿省宿寄齐熙业少卿》)这是指艺术性。陈瓘《呈知府司封二十韵》云:“曹刘风自古,李杜格殊伦。”将李杜并称。罗从彦的《寄傲轩用陈默堂韵》诗:“我醉欲眠卿且去,肯陪俗客语羲皇。”径直取用李白《山中与幽人对酌》之句,可见其对李白也有足够的重视。
诗歌风格类似中晚唐者,如陈襄的《和子瞻西湖寒食》:“春阴漠漠燕飞飞,可惜春光与子违。半岭烟霞红旆入,满湖风月画船归。缑笙一阕人何在,辽鹤重来事已非。犹忆去年题别处,鸟啼花落客沾衣。”声调凄婉。其他诗人如游酢的《水亭》诗:“清溪一曲绕朱楼,荷密风稠咽断流。夹岸垂杨烟细细,小桥流水即沧洲。”以及《题河清县廨》:“小院闲亭长薜萝,鹿木穿径晚径过。夕阳萧散簿书少,窗里南山明月多。”还有陈瓘的《和刘太守十州诗》:“月明偏照海边洲,绿水回环漾素秋。斗转参横群动息,桂花零落遣谁收。”也都不乏唐诗风味。
典型的宋诗风格作品如陈襄的《天道不可跻》:“天道不可跻,以其高且危。地道不可寻,以其幽且深。土圭测日影,可以分照临。桐鱼击石鼓,可以求声音。嗟夫世之人,不知方寸心。”是明显的道学家之诗,其它如《白头》《偶书》《赠禅者》《留题天游阁》都是此类。陈瓘的《了斋自警六首》其一:“本无一字尧夫易,八十一篇扬子玄。今古是非那复辨,仲尼尤不废韦编。”《杂诗》:“大抵操心在谨微,谬差千里始毫鳌。如闻不善须当改,莫谓无人例可欺。忠信但当为己任,行藏终自有天知。深冬寒日能多少,已觉东风次第吹。”几乎全部说理论道,缺乏诗味。罗从彦《自警》《观书有感》等诗从内容到语言风格与前两者如出一辙。
北宋闽地理学家的诗歌创作以杨时为代表,其《送富朝奉还阙》诗:
君不见庆历承平道如砥,驰车八荒同一轨。虏人鸱张怒螳臂,百万云屯若封豕。又不见朔方横流涨天起,腐麦蛾飞木生耳。扶携道路杂老幼,操瓢沟中半为鬼。关河日夜刁斗惊,嫚书乘驷来渝平。兵间持节得英杰,谈笑坐使羁长缨。青社环城万区屋,发廪分曹具饘粥。饥羸枯颊陡生光,丛冢不闻新鬼哭。臧孙有后天匪亲,闾门容车何足论。朅来濉上见犹子,雄姿宛有典型存。骅骝已渡渥洼水,朝燕暮越应千里。行看玉勒驾銮舆,濯足瑶池从此始。
从遣词及句法上来看,这首诗有意学习李白及杜甫;从风格方面来说,却类似韩孟诗派的奇崛诗风;同时又具有宋诗以文字为诗的特点。《题赠吴国华钓台》《赠别蔡武子被诬得释赴泉州录参》《寄练子安教授》《酬林志宁》《寄范正甫》等诗都是如此。从形式上来看,这类诗歌大多是古体诗。
杨时的律诗和绝句则多呈现唐诗特色,而无宋诗气息。如《夜雨》:“似闻疏雨打蓬声,枕上悠扬梦半醒。明日觉来浑不记,隔船相语过前汀。”再如《含云寺书事六绝句》其一:“竹间幽径草成围,藜杖穿云翠满衣。石上坐忘惊觉晚,山前明月伴人归。”纯然宋调的说理诗也不少见,譬如《枕上》:“小智好自私,小德常自足。自私开人贼,自足心有目。瑕瑜不相掩,君子此良玉。默默枕上思,戒之在深笃。”再如《初夏侍长上郊行分韵得偕字》《读东坡和陶影答形》等都是典型的宋诗风格。由此可见,杨时在诗歌创作的时候并没有刻意区分唐音与宋调,而是根据表现内容的不同调适不同的风格。
北宋至两宋之交的闽地理学家在其作品中兼具唐音、宋调,不排斥任何一种风格,也不有意推崇某种诗风,只是根据自身表达的需要阐述义理,或者抒写情怀。而时事、民生、政治理想等内容,则很少出现,似乎与其所强调的诗教相矛盾,而这恰恰说明闽地理学家将诗歌作为反映内心恬淡与自在的一种手段,诗歌的艺术性则相对淡化。这种情况在两宋之际以及南宋时期发生了很大变化。
二、两宋之交至南宋中期——宋调的形成与唐诗学观念的新变
两宋之际至南宋中期,闽地理学进一步发展,这一时期的理学家人数众多,其中沙县陈渊、沙县邓肃、侯官林之奇、崇安胡宏、崇安刘子翚、莆田林光朝、龙溪陈淳及朱熹等人有诗歌创作。这一时期闽地理学家的诗歌创作的主体风格已经转变为典型的宋调。同时,开始有意区分唐诗及宋诗风格,并且对唐代不同诗人的偏好愈趋豁显。
这一时期,闽地理学家仍然强调义理的阐发,比如朱熹就说:“今人不去讲义理,只去学诗文,已落第二义。”[7]3334又说:“不必著意学如此文章,但须明理,理精后,文字自典实。”都强调义理在文章之先,陈淳也说:“大抵穷理与做文章不同。做文章旋逐修饰,润色,惟教好看。”[8]
以诗谈理是宋代闽地理学家的共性,如林之奇的《朝乘》云:“小利专欲速,大德不踰闲。”《高竹》:“道污得夷理,物虚含远情。”等都体现出明显的语录体诗歌的特征。在这一点上,陈淳、林亦之、胡宏及等人表现得尤为明显,与其说是诗,毋宁说是“讲义语录之押韵者”。抛开这一点,即使是不谈性理的作品,闽地理学家的作品也已经形成了典型的宋调,如四库馆臣评价林之奇:“其诗尤具有高韵,如《江月图》《早春偶题》诸篇,置之苏、黄集中,不甚可辨也。”[2]1366邓肃、胡寅莫不如此。唯有刘子翚、钱钟书认为他是道学家中的诗人,较少沾染讲义语录气息,诗歌风格豪爽明朗。
由于闽地理学家多数宗尚江西诗派,因而诗论中必然提及杜甫及韩愈。如邓肃《寄张应和运副二首》其二:“桃源目断知何处,身在杜陵诗句中。”陈渊《赵元述庆得子次韵》:“贫家岂有石麒麟,说梦哦诗傀杜陵。”林亦之《奉寄云安安抚宝文少卿林黄中》:“夔子城头开幕府,杜陵诗卷作图经。”刘子翚《次韵明仲幽居春来十首》:“却忆少陵诗句好,依然云木晓香忝。”胡寅《晓乘大雾访仲固》:“原君读此一醒然,未负当年少陵句。”这种共性反映了理学家对杜诗的接受情况。
进入闽地理学家视域的,除了韩愈的儒学道统,还有诗歌。这一点在邓肃的诗论里表现的尤其突出,其《昭祖送韩文》诗:“斯文未丧得韩子,扫灭阴霾霁九州。古来散文与诗律,二手方圆不兼笔。独渠星斗列心胸,散落毫端俱第一。”推举韩愈的散文与诗歌“俱第一”;其《质夫和来》云:“作文忽慕元和格,送入贤关亲眉白。遽闻皇甫语穿天,渊源盖是退之客。”这里的“元和格”显然指的韩孟诗风。与邓肃类似,胡寅、林之奇也极为欣赏韩愈奇险的诗歌风格,前者如《清湖山大火》云:“每钦韩公观陆浑,雄词险句咻而燉。”这里的“雄词险句”指的就是韩愈《陆浑山火》。而林之奇也说:“子美正声谐韶濩,退之劲风沮金石。”[9]所谓劲风,也是就诗风而言的。
与诸家推崇韩愈奇险诗风不同的是,朱熹却说:“韩诗平易”[7]3327,又说:“诗须是平易不费力,句法混成。”[7]3328邓肃等人是基于蹈袭江西诗派而崇尚韩愈,自然从其险怪的诗风入手,朱熹则反对江西诗派,因而独从平易的角度来评论韩诗,这恰好与朱熹追求的以平淡为主的道学气息相通。
闽地理学家对李白的评价亦可关注,如朱熹说:“李太白终始学《选》诗,所以好。”[7]3326同时,朱熹认为李白诗雍容和缓,合乎道的气象。他说:“李太白诗不专是豪放,亦有雍容和缓底,如首篇‘大雅久不作',多少和缓!”[7]3325从理学家注重诗教的视角来看,邵武李吕注意到了李白诗中的讽谏意味,其《读太白集》诗云:“吾宗老太白,俊逸自幼年。……仍喜宫祠句,浑如讽谏篇。至今读青史,终始无间然。”难得的是,闽地理学家对李白的评价多基于其诗歌风格,突破了“理学”观念,如邓肃《醉轩吟》云:“渊明句法古无有,头上葛巾须瀌酒。太白毫端惊倒人,举酒望天不计斗。二子风流不可追,公作幽轩为唤回。”再如陈渊《再和时可》诗云:“应共翰林争敏捷,岂如开府但清新。”林之奇的《观澜文集》则将李杜并称:“自非业足以造游夏之渊源,辞足以发李杜之光焰。”[10]卷10
除此之外,闽地理学家也偶或论及其他唐代诗人,但大多为只言片语,不足为据。此中唯朱熹对陈子昂及韦应物的模仿及评论受人关注。朱熹在其《斋居感兴二十首序》称:“余读陈子昂《感遇》诗,爱其词旨幽邃,音节豪宕,非当世词人所及。如丹砂空青,金膏水碧,虽近乏世用,而实物外难得自然之奇宝。”朱熹以理学家的身份批评其诗缺乏世用,却以诗人的身份肯定其词旨、音节。因此模仿其作:“欲效其体,作十数篇。……然亦恨其不精于理而自讬于仙、佛之间以为高也。斋居无事,偶书所见,得二十篇。虽不能探索微眇,追迹前言,然皆切于日用之实。”而理学家毕竟是理学家,其着眼处仍然在于“精于理”,其仿作的结果也仅仅是“切于日用”而已。明人谢肇淛即说:“晦翁诗却有不著相处,然便欲以《感遇》拟子昂,终觉不侔。”[10]卷10朱熹又推崇韦应物,以为其诗“自在”,如说:“其诗无一字做作,直是自在。其气象近道,意常爱之。”[7]3327正是因为这种“自在”与道接近。朱熹本人在诗歌创作上也是从韦应物入手学习的,许学夷在《诗源辨体》中也说:“朱子幼年,五言古悉学苏州。”[11]
三、南宋中后期——“击壤派”理学诗体与唐音的合流
南宋中期之后,随着以邵雍为代表的象数之学的兴盛,诗学观念也产生了相应变化。闽地诗论家严羽在其《沧浪诗话》中称邵雍的诗歌为“邵康节体”,即典型的理学家诗体。多数学者认为,“邵康节体”逐渐演变为“击壤派”,如祝尚书《论“击壤派”》一文认为“击壤派”源于邵雍的《伊川击壤集》,形成于宋末《文章正宗》与《濂洛风雅》的出现[12]。四库馆臣却认为:“南渡以后,《击壤集》一派参错并行,迁流至於四灵、江湖二派,遂弊极而不复焉。”[2]1726以为“击壤派”的形成在南渡之后,本文采取这一论断。
无论是“邵康节体”还是“击壤派”,都是就邵雍的诗歌创作及其追随者而言的。祝尚书所提及的“击壤派”闽地理学家有两人,一为真德秀,一为林希逸。南宋中后期的闽地理学家,大多推崇邵雍的诗歌,并以其《击壤集》为诗学范式。故此,这一概念的外延应较祝尚书所言更为广泛。除上述二人,宁德陈普、莆田黄仲元、仙游王迈等人也属于这一群体。
真德秀在论及邵雍诗时说:“康节之辞若卑,而其指则源于六经。”[13]卷36认为诗出于六经为高,而邵雍诗正是源于六经。林希逸对邵雍的诗歌评价更高:“删后无诗,固康节言之。然《击壤》诸吟,何愧于古。彼其规尺,岂与古同?所以鼓吹者,同一机也。康节之后,又无诗矣。”[14]卷13陈普持相同看法:“少陵康节,信手挥洒,任意纵横,不愁浅俗,不畏讥诮,而卓绝之奇,自出其中宏大之局,自见其首尾也。”[15]在陈普看来,尽管南宋以来陈与义、陆游等人的诗歌并不因循模仿其时流行的晚唐诗风,但也不能做到与风雅同声,由此可以看出其诗学观念的核心。黄仲元则继承邵雍“以物观物”的思想:“香山老(白居易)坐东亭,以人观物,不以物观物,是时年壮气锐,犹以遭不遭为幸不幸。”[16]卷1
真德秀的诗歌创作与其诗学观相应,以阐发义理为要。如《志道生日为诗勉之》诗:“我闻洙泗言,惟仁静而寿。汝欲绵修龄,斯义盍深究。”再如《题黄氏乐贫斋》:“濂洛相传无别法,孔颜乐处要精求。须凭实学士夫到,莫作闲谈想像休”等都是如此。曾师从真德秀的王迈《和刘编修潜夫读近报蒋岘被逐》诗:“怀哉康节先生语,作事莫教人绉眉。”则直接化用邵雍《诏三下答乡人不起之意》诗:“平生不作皱眉事,天下应无切齿人。”陈普在诗歌创上与邵雍的诗歌特点一致,将散文化倾向发挥到极致。如《归去来辞》:“已矣乎曷之,予知归去兮。松菊候门而南山耸媚,花鸟欣迎而北岭喧呼。悔知非之既晚,乐成赋以归欤。”其它如《和李太白把酒问明月歌》《不饮酒歌》《劝学歌》《醉吟》均如此。由此可见,南宋中后期的理学家在诗歌创作上鄙弃文辞之美,强调经世致用,也是“击壤派”的共同特点。
“击壤派”理学家的唐诗学观念也大体一致。这一时期的闽地理学家对杜甫、韦应物、韩愈诗歌关注比较突出,如黄仲元说:“诗可学也,建安黄初暨晚唐,几千百家,独子美不可拟议。”[16]卷1陈普也以杜诗为尊:“盖其学餍经饫史,含庄咀骚,采掇菁华,材料饱足,故能兼陶杜之体。”[17]林希逸《和柯山玉上人三首》其一云:“我学老禅无长进,相逢却讲少陵宗。”究其原因,无非是“其指近乎经”。从诗歌创作上来看,虽然在诗学观上推尊杜甫及韦应物、韩愈,但这一时期的理学家并没有多少神似杜甫、韦应物诗歌风格的作品。闽地理学家的学唐并不是着眼于其艺术性,而是为宣扬道学服务,故此,无论是“理学家”诗体还是模仿唐人之作,都呈现出共同的风格特征,具有唐音、宋调合流的趋势。在这一点上,真德秀可作为这一群体的代表。
真德秀所编《文章正宗》第二十二卷、二十三卷、二十四卷选录唐诗,去取主理,遵守“其体本乎古,其指近乎经”的基本原则。由此,《文章正宗》所选唐诗,重视古体诗而轻视律诗。而从内容上来看,真德秀特别重视那些近于六经的作品。具体到所选唐人诗,有陈子昂十三首、李白五十四首、杜甫一百二十五首、韦应物九十一首、柳宗元二十首、韩愈三十首。从数量上来看,最多的是杜甫及韦应物。
陶渊明与韦应物的诗歌风格接近,因此闽地理学家大多通过韦应物习学陶渊明,比如朱熹。这是因为韦应物诗歌具有萧散冲澹之趣,具有修身养性的功能。从《文章正宗》的选诗数量上来看,真德秀的诗学思想似乎与朱熹一致,实际却远非如此。真德秀明确指出:“予闻近世之评诗者曰:渊明之辞甚高而其指则出於庄老;康节之辞若卑,而其指则原于六经。以余观之,渊明之学,正自经术中来,故形之于诗,有不可掩。《荣木》之忧,逝川之叹也;《贫士》之咏,箪瓢之乐也……予尝病世之论者于渊明之蕴有所未究,故以是质之。”[13]卷36指出渊明之辞并非出于老庄,而是出自经术。正是从这一点出发,《文章正宗》“增入陶诗甚多”,同时,韦应物及柳宗元诗歌的大量入选也就找到了根本原因。
在有限的几个入选诗人中,李白诗在《文章正宗》中占了五十四首,这与其他闽地选唐诗者不同,如林之奇《观澜文集》中只选一首。究其原因,在真德秀看来,李白的某些诗歌符合其选诗宗旨。一方面,从形式来看李白的诗歌“近古”。另一方面,真德秀并不大注意李白豪放的诗歌风格或者辞藻的华美,这与朱熹也略有不同。真德秀专注于诗歌的比兴寄托,李白“八荒驰惊飚”诗下注云:“龙凤喻君子,网罟喻祸患。谓君子幸脱祸患,将安所栖托乎。”表现诗歌讽喻之旨。
林希逸论诗亦从比兴出发,将李杜并称,他说:“班固、刘勰缀缉词章,而不达比兴,其文可考也。故露才扬已,妄致其讥,不合典雅,窃生异议。若夫俱怀逸兴壮思飞者,又肯为此言耶?是故‘虽乏谏诤姿,恐君有遗失',此杜拾遗之诗也,非骚之忧愤乎?‘仰天揽明月,散发弄扁舟',此李翰林之诗也,非骚之放逸乎?由此观之,则信乎诗家之风骨蹊径,与骚为同出也。”[14]卷8指出李杜之诗源出《骚》,达比兴之旨。又说:“吁!诗于李杜,圣矣乎!神矣乎!”[14]卷8这种诗论显然与北宋及南宋初期存在极大的差异。
四、结 语
北宋时期到两宋之际的闽地理学家并没有诗风自立的倾向,诗歌创作兼具唐音及宋调。而到了两宋之交至南宋中期,随着闽地理学的兴盛,理学家在诗歌创作上以阐述义理为主。同时,对唐人诗的评价及接受也逐渐豁显。南宋中期以后,以真德秀为主的“击壤派”闽地理学家并不关注诗歌创作的艺术性,而主要为宣扬其道学服务。故此,无论是“理学家”诗体还是模仿唐人之作,都呈现出共同的风格特征,具有唐音、宋调合流的趋势。籍此,可以看出宋代闽地理学家的诗学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