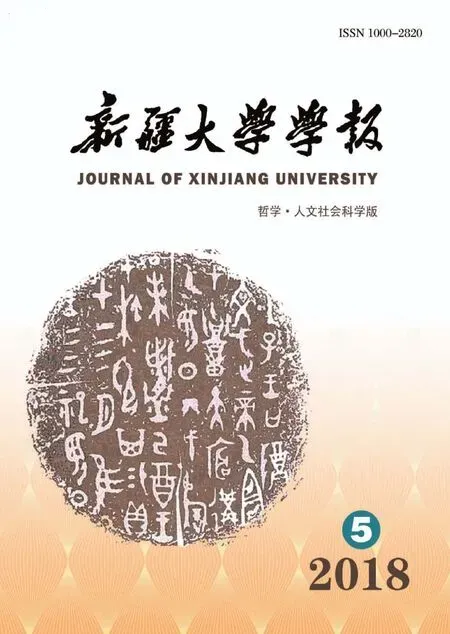从满文寄信档看“德风乌什哈达互讦案”对清代新疆吏治的影响*
孙文杰,宁 燕
(1.新疆师范大学西域文史研究中心,新疆乌鲁木齐830054;2.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档案局,新疆乌鲁木齐830002)
清朝时期,清政府根据当时新疆的历史与现实环境,采取“因俗而治”的治疆方略,“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1],这对天山南北的经济与社会发展有着巨大的促进作用。但当时的新疆也存在诸如伊犁将军与喀什噶尔参赞大臣权责不清带来的行政混乱、朝廷派驻官员与地方伯克相互勾结、官员素质较低、腐败成风等方面的吏治问题,以致在乾隆三十年(1765)发生了震惊朝野的“乌什事变”,对新疆的政治、经济等方面均造成了巨大的破坏①有关“乌什事变”的具体情形,详见拙文《从满文寄信档看“乌什事变”中的首任伊犁将军明瑞》,《新疆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1期,第66—69页。。事后,为尽快消除“乌什事变”所带来的不利影响,清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如厘清喀什噶尔参赞大臣与伊犁将军的具体职责、将喀什噶尔参赞大臣移驻乌什、制定《回疆善后事宜八条》等,这一系列措施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奠定了清政府治理新疆的基本范式②有关“乌什事变”对清代新疆吏治的影响,详见拙文《从满文寄信档看“乌什事变”真相》,《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6期,第128—135页。。
但由于受当时全国政治局势的影响,“乌什事变”后新疆的吏治问题并没有得到切实改变,又接连出现“高朴盗玉案”“经方贪腐案”“索诺木策凌盗卖盗销案”等一系列有关吏治腐败的大案。直至乾隆四十六年(1781),时任和阗办事大臣德风与和阗领队大臣乌什哈达因隙互讦而出现“德风乌什哈达互讦案”[2]卷1139,253,乾隆皇帝才连下40 多道密寄谕旨,明确要求中央政府派驻新疆官员务必严格遵守当年制定的《回疆善后事宜八条》,并在此基础上廉洁自律,秉公办事,以化人心。
“德风乌什哈达互讦案”,对清代中期以后的新疆吏治乃至清政府治理新疆方略的基本形成,都有着重大的影响。但是,传统文献如《清实录》对此却仅有片段记载,令人不知所终。基于清代国史馆所藏史料、档案写成的《国朝耆献类征初编》对该案仅有简略记载:“德风以乌什哈达东三省人,意存轻视,遇公务有意饬驳,不假辞色;以致乌什哈达不能隐忍,讦以泄忿。德风私动钱文属实,照例拟罪。乌什哈达私受皮张皆以物抵给,并非勒取;惟讦款实少诬多,应革职,发乌什边卡侍卫上效力。”[3]
通过大量从《国朝耆献类征初编》与《满汉名臣传》二书过录史料而辑成的《清史列传》[4],其卷二十七之《乌什哈达列传》相关内容与《国朝耆献类征初编》几无二致。《清史稿》卷三百三十三、卷三百四十九《乌什哈达传》对此记载则更为简单:“(乌什哈达)充授和阗领队大臣,坐与办事大臣德风互讦,褫职,效力乌什边卡。”[5]11250而传世的清代新疆方志如《回疆通志》《新疆图志》等对此更是没有只言片语,以致学界前贤先哲暂未关注至此。但是,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馆藏的大量满文寄信档则详细记载了“德风乌什哈达互讦案”的来龙去脉。作为皇帝的密寄谕旨,这些档案均属以满文记载各种事件之密寄上谕专档,又具有与汉文档案不相重复,抄载内容更多、更完整之特点,是清史研究中最为真实、原始、可靠之资料[6]册1,3。基于此,笔者不揣鄙陋,拟在《乾隆朝满文寄信档》等稀见史料的基础之上,对“德风乌什哈达互讦案”的发生以及鞫审过程作以梳理,进而对清代新疆吏治问题作个案探讨,以期为系统而又全面梳理清代中央政府治理新疆的研究进行新角位的思索。
一、“德风乌什哈达互讦案”的发生
德风,索绰罗氏,内务府满洲正白旗人,礼部尚书德保之弟。乾隆十七年(1752)进士,后历任侍读学士、日讲起居注官、翰林院侍读、詹事、安徽学政、盛京户部侍郎等职[7]。乾隆四十年(1775),时任顺天府府尹的德风,因“私委知县修理盛京官署革职,复经特恩赏给三品职衔,发往和阗效力赎罪”[2]卷994,286,任职和阗办事大臣。
乌什哈达,吉林满洲正黄旗人,以师征缅甸、金川等地军功,图形紫光阁[5]11992。乾隆四十五年(1780),以副都统职衔授为阿克苏领队大臣。乾隆四十六年(1781)八月十五日,授和阗领队大臣[2]卷1139,252。
但就在乌什哈达上任仅十一天之后的八月二十六日,时任叶尔羌办事大臣复兴向乾隆皇帝上折奏事:“德风控告乌什哈达收受阿奇木伯克迈达雅尔绸缎、皮张等物,其家人张锦禄、印务笔帖式岳克清额与妇女奸宿;乌什哈达又交年班伯克迈达雅尔捎带回京物品,乌什哈达家人赵德禄随护送年班伯克等之一等侍卫唐苏里携带物品等情。”[8]册15,587接到奏折后,乾隆皇帝立即指示乌什参赞大臣绰克托,命迈达雅尔、赵德禄等人即刻返回和阗,接受调查。但几乎就在同时,绰克托也向乾隆皇帝上折:“乌什哈达控告德风派数百民,以修万寿宫,新建房屋衙署,致误耕种;克扣官兵盐菜银两,以及其家人与妇女同宿等情。”[8]册15,587是为“德风乌什哈达互讦案”。
由于当时和阗归叶尔羌办事大臣直接管辖,职责所在,复兴在给乾隆皇帝汇报的同时,也立即奔赴和阗,拟将德风、乌什哈达二人就地免职。同时,因为八月亦为乌什参赞大臣照例巡查各城之时,复兴拟待绰克托巡查叶尔羌、喀什噶尔等地至和阗后,二人乘便会审,并将此上奏乾隆皇帝。接到奏折后,乾隆皇帝认为事态紧急,复兴一面具奏一面立即赶赴和阗处置的行为,甚为合理。同时,乾隆皇帝认为,和阗乃天山南路最要之区,关系甚要①有关和阗在清代新疆地位的重要性,详见拙文《和瑛西域著述的价值与意义》,《新疆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4期,第70—76页。。而德风、乌什哈达并不安抚民众,尽心办事,却相互指控,待复兴、绰克托审实之后,应将二人从重治罪。而且,护送年班伯克迈达雅尔起程之侍卫唐苏里应允乌什哈达家人跟随并带物来京,亦属非是。
因此,乾隆皇帝指示:“将德风、乌什哈达立即解任,所有涉案之人,逐一究审明白,秉公从重拟罪具奏,不得稍事袒护。”[8]册15,588至此,“德风乌什哈达互讦案”正式立案,在北京与和阗同时展开鞫审。
二、“德风乌什哈达互讦案”的鞫审
就在绰克托与复兴在和阗开始查案的同时,乾隆皇帝亦在北京进行思索:
乃思,乌什哈达系新满洲,素性小气图利,收受人物品等项,谅俱有之事。乌什哈达控告德风之案,朕初尚怀疑,德风果无此等之事,朕自喜焉。转而又思,乌什哈达控告德风多派数百民,借修万寿宫为名,翻建衙署房屋,致误耕田。又,其查出历年采集私藏玉石,并不办理,却招集伯克,施以恐吓,由其家人从中讨价,取银千余两及价值二三千两之物,方以息事;并举出克扣官兵盐菜银两等项[8]册15,588。
乾隆皇帝认为,如果上述属实,则德风不可与乌什哈达相提并论。因为德风不仅是包衣佐领之人、吏部尚书德保之弟,前又在顺天府府尹任上因罪加恩遣往和阗办事。乾隆皇帝认为,如若乌什哈达收受当地民众绸缎、皮张等事属实,则“新满洲素性小气图利,尚在情理之中”;而德风“阖家承恩优渥,若仍如此贪图小利,则德风之罪比乌什哈达更重矣”。同时,乾隆皇帝深知清代中期官官相护之弊,又对此加以特别指示:“对德风、乌什哈达二人,(想必)绰克托、复兴,偏袒德风。此等之事,究竟孰是孰非,朕毫无定见。……绰克托等若袒护德风,而加罪于乌什哈达,嗣后查出,朕必将绰克托、复兴二人,从重治罪。……此案务必遵行朕旨,秉公(明白)办理。不得袒护任何一方。”[8]册15,589
同时,由于乾隆四十三年(1778)发生的“高朴盗玉案”对新疆稳定与安全所造成的影响仍历历在目①有关“高朴盗玉案”的具体情形以及对清代新疆的吏治影响,详见拙文《从满文寄信档看“高朴盗玉案”对清代新疆吏治的影响》,《北方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1期,第110—114页。,乾隆皇帝认为:“(德风乌什哈达互讦)殊属骇异。伊等兄弟,皆深受皇家朕恩深重,德保在外任督抚数年,且德风从前获罪,朕并未治以重罪,却将伊视为一人才,加恩遣往和阗办事。今观乌什哈达讦告事项,几似高朴,实负朕恩。此案显系德风自知有弊,恐为乌什哈达告发,而先发制人控告乌什哈达矣。”乾隆皇帝深恐此案成为“高朴盗玉案”的再演,并且认为德风在和阗多年,必送有德保玉石、皮张等物,即便德风未曾送及德保此等物品,亦必有送与自家者。且德风控告乌什哈达,极可能会事先写信与德保相商。此上种种,乾隆皇帝认为德保不可能不知情,随下令将乌什哈达控告德风之原件呈与德保详阅,并命其对乾隆皇帝的种种疑问据实查明回奏[8]册15,589。
就在乾隆皇帝在北京鞫审该案的同时,乌什哈达又呈控德风“以库贮官钱八千余腾格,交都司张子龙放贷生息”。接奏后,乾隆皇帝大为震怒:“朕原以为乌什哈达指控德风之事,尚有疑问。今批阅乌什哈达补充陈控,乌什哈达所控情由,似皆属实。新疆地方岂可如此肆行贪婪!……若在新疆地方如此贪婪图利,肆行无忌,久之必为另一高朴,不知生出何等之事。”进而明确指示复兴与绰克托:“德风若无此等情弊,固然好。若以为乌什哈达系新满洲,而苛刻办理;德风系德保之弟,即袒护办理,而加罪于乌什哈达……一旦查出,同于德风,予以治罪。”同时,乾隆皇帝对绰克托拟先去阿克苏宴请年班伯克后再赴和阗办案的行为大加申斥,命其立即奔赴和阗,会同复兴,务必彻底审明,秉公明断,并特意交待:“朕甚挂念此事,每道谕旨,俱以六百里驰递。”[8]册15,590
随后,乌什参赞大臣绰克托在阿克苏前往北京必经之路堵截年班伯克迈达雅尔,经仔细核查后,发现其所捎带乌什哈达皮箱、包裹中并无玉石、金银等贵重物品,不过是狐皮、羊羔皮、皮筒子而已,而迈达雅尔本人所携带物品亦仅有准备觐见所贡玉器等物。但绰克托为了稳妥起见,将此结果先行上报清廷,并将乌什哈达家人与迈达雅尔均带往和阗,待审问明白再行具奏。接奏后,乾隆皇帝发现,绰克托所查获乌什哈达捎寄家中之物品清单中,仅有几种皮张等寻常之物而已,并无德风所控金银、玉器等值钱之物。而乌什哈达控告德风之事,却似件件属实。同时,乾隆皇帝在批阅绰克托奏折时又发现:“言下似有偏袒德风之意,绰克托一定厌恶乌什哈达。……绰克托先不甚提及德风,惟奏乌什哈达之事,实属非是。”[8]册15,592因此,乾隆皇帝再次明确指示绰克托、复兴,务必将该案审明具奏,断不可稍有偏袒德风之处。随后的乾隆四十六年(1781)九月十一日,提前赶赴和阗的叶尔羌办事大臣复兴,经过上下探访,侦得部分实情:
德风与乌什哈达,因言语发生口角,互生嫌隙而出首控告。……查得和阗仓库所存粮饷等项,俱与册数相符,惟空廒之中,查出私存玉石一千九百三十九块。经询问德风,称皆系历年采贡所余,俱有印册。俟绰克托到后,共同审明拟罪具奏[8]册15,594。
由此,乾隆皇帝发现,按照复兴所查之结果,乌什哈达前所控德风“私藏玉石等,由其家人私下讨价,索银千余两,又取价值二三千两之物,掩饰案情”一事,今查库中所存玉石并未动用,且俱有印册可凭。并且,又查处仓库,数目俱符。再加上之前绰克托查验结果,可见德风、乌什哈达所互控事项均属不实。至此,该案似乎进入困境。但深知清代中期官场黑暗、历来有官官相护之弊端的乾隆皇帝仍有疑虑:“复兴方抵和阗,情形大概如此,最终在于伊等秉公处理。伊二人务必秉公彻底查明,若袒护德风,而稍事冤屈乌什哈达,朕明鉴后,必将绰克托、复兴二人,从重治罪。”[8]册15,595
随后,乾隆皇帝对该案继续进行反思。他认为,该案显系德风、乌什哈达二人不合,争忿生隙,然后分别出首诬告,绰克托等人若用心秉公审讯,并非难事。因此,再次下发密旨明确指示绰克托等人:“若确有其事,亦不可因此圣旨而事消弭,务须查实拟罪。”[8]册15,598但此后的一个多月中,乾隆皇帝未接到绰克托、复兴二人有关该案之任何奏折,极为震怒,认为该案大略情形前已查明,竟拖延多日不报,显属二人有意私下消弭[8]册15,602。或者是二人彼此意见不合,或偏袒德风,或袒护乌什哈达,互相掣肘,以致拖延不决。因此,再次专降谕旨,指示二人:“绰克托即因高朴案,伊未予办理而获罪矣。此案何以如此迟滞不办?著寄谕绰克托、复兴,严行申饬外,并将德风、乌什哈达互控案,务必速行查明审理,明晰办理具奏。其孰是孰非,不得稍有隐瞒,亦不得稍存袒护之心。若再彼此掣肘,迟延不奏,朕必将伊二人从重治罪。”[8]册15,604
随后,绰克托、复兴二人经过上下访查,终于厘清案情,并据实上奏:
德风以乌什哈达系东三省之人,意存轻视,凡遇一切事务,有意饬驳,而言词甚厉,以致乌什哈达不能隐忍,互相控讦。德风私动玉石钱文,修理衙署,属实[2]卷1145,349。
(德风)将回人偷卖玉石交出之五百余腾格普尔钱挪用,私自修理衙署,又因与乌什哈达不睦,编造数款控告乌什哈达[8]册15,607。
至此,朝野震惊的“德风乌什哈达互讦案”真相终于浮出水面。但因为绰克托与复兴的多次奏折内,均未言及乾隆皇帝较为关注的“该案究系谁先控告”之问题,因此再降谕旨:“惟此案究系谁先起意,先行控告,绰克托、复兴折内,并未陈明。(或德风先控告)或德风知乌什哈达控告抢先控告,或德风即原告,(或乌什哈达知德风控告,而追控德风之处)著绰克托、复兴将前后根由查明,速行奏闻。”[8]册15,608
随后,绰克托上奏:“德风遇一切事物,不肯为乌什哈达稍留地步,以致乌什哈达不能隐忍,始将伊动用卖玉钱文,并风闻数事,开列呈控。”[2]卷1145,350但是,乾隆皇帝却从中又看出清代新疆吏治之弊病:“至德风、乌什哈达互相控告,究系谁先起意,绰克托、复兴屡次折内,均未声明。及朕询问,今日绰克托、复兴折内始行奏明。果不出朕之所料,终系乌什哈达先控告德风者。绰克托、复兴前有意袒护德风,以期平息此事,故有前奏耳。”[8]册15,608乾隆认为绰克托、复兴二人故意隐瞒谁先控告的行为,实属有意私下袒护德风之举,如不及时制止官场此风,必将致使当时吏治更为糜烂不堪。
三、“德风乌什哈达互讦案”的处置及其对清代新疆吏治的影响
案情厘清后,绰克托、复兴二人遵照大清律法以及乾隆皇帝的指示,按律定罪:拟将德风绞监候、乌什哈达以侍卫衔留于乌什边卡效力。然而乾隆皇帝在接奏后却认为:“绰克托、复兴将德风拟绞,虽不过甚,然尚不至如高朴私卖玉石肥己,于彼处正法示众也。已降旨交军机大臣等议奏。”[8]册15,608另外,乾隆皇帝认为该案在新疆绝非个例,而是代表了清代新疆官场的一种普遍病态,若不及时加以整顿,必将影响边疆的治理:
此事实属恶习,德风乌什哈达同城办事,何以不能和衷,挟嫌互控,成何事体?……新疆大臣,若皆如此,又何以集事?且为人臣者,在自己果有才能,而又得帮助办事之人,彼此和衷,自不致有掣肘,如自己才能不及,尤需帮助有人,何可轻忽相视,任意专擅耶。乌什哈达系吉林之人,若果行事不循法纪,德风即应据实参奏,乃无故轻视其人,因嫌滋事,甚属不堪。……著将此通行传谕新疆将军大臣等,办理诸事,务须和衷商榷,断不可似德风轻视乌什哈达为吉林之人,以致滋生事端[2]卷1145,349—350。
乾隆皇帝认为,此案暴露出清廷派驻新疆官员不能和衷共事的两个弊源:第一,乌什哈达出身低微,而德风则系身份显贵的包衣佐领之人。而清代自康熙以来即普遍存在贵族重出身的社会现实,这在实行军府制的新疆表现尤其明显,进而造成清廷派驻新疆官员不能和睦共事之局面。第二,德风系进士出身的文官,而乌什哈达则是没经过科举教育、靠军功起家的武官,而清代中央政府派驻新疆的同阶文武官员之间,向来互存轻视与偏见①有关清代新疆文武官员之间的互为轻视,详见李宏为《乾隆与玉》,北京:华文出版社,2013年,第402、431页。。官员之间的不睦,尤其是驻疆官员之间的离心离德,不能和衷共事,则危害更巨。因此,看到“德风乌什哈达互讦案”所折射出的整个清代新疆吏治均存有此种弊端的乾隆皇帝,希望能借此整顿新疆吏治,让他们能真正做到平等尊重、和谐共事,遂决定将此案传谕派驻新疆各地之将军、大臣,要求他们“办理诸事,务须和衷商榷,断不可似德风轻视乌什哈达为吉林之人,以致滋生事端”。
同时,又因“乌什事变”后,虽然清政府对新疆的吏治进行了种种改革,但此后接连出现的“高朴盗玉案”“经方贪腐案”“索诺木策凌盗卖盗销案”,均对新疆的安全与稳定带来了极为恶劣之影响。为加强对新疆的治理与经营,维护中国西北边境的稳固,乾隆皇帝再次下令,明确要求驻疆各大臣务必廉洁律己,秉公办事:
(乌什事变)距今已近二十年矣,现在驻扎大臣等,多未经历,且全然不知此事者,亦有之。新疆驻扎大臣办理一切事宜,理应眷念朕恩,凡事廉洁律己,秉公办理,怀柔措置,收抚下属人心。今夫素诚系前车之鉴,其丑恶行径,宜令新疆各驻扎大臣等,时刻铭记在心,以为儆戒。……著将此通谕新疆各驻扎大臣等,务令伊等遵行朕旨,廉洁自律,妥善约束下属,一切事务,秉公办理,以服人心。不可稍事傲慢,任意妄为也。将此谕旨,著饬新疆各驻扎大臣,列入交待事项,令各任大臣,铭记查照施行[8]册15,610。
乾隆皇帝认为,当初“乌什事变”后,阿桂和明瑞为祛除该事所造成的恶劣影响而制定《回疆善后事宜八条》,在阿奇木之权、格讷坦之私派、回人之差役、都官伯克之补用、伯克等之仆使、民回之居处、赋税之定额、伯克与官员相见之仪等八个方面所进行的改革[9]179—180,对天山南北地区社会矛盾的缓解、清政府在天山南北统治的巩固等方面确实有着重大贡献。
但“乌什事变”之后的20 余年,当初针对新疆吏治弊端而制定的《回疆善后事宜八条》却并未得到切实贯彻,以致又出现如今的“德风乌什哈达互讦案”。因此,明确要求驻疆各将军、大臣务必遵守此八条改革措施,一切政事,务必秉公办理。并且,为了此八条能真正得以贯彻而不致沦为虚文,乾隆皇帝专门再降谕旨,明确指示中央政府派驻疆大员必须将《回疆善后事宜八条》列入交待事项:“故降旨通谕新疆各驻扎大臣,令伊等务必廉洁自律,小心谨慎,一应事务惟当秉公办理,怀柔措置,以收服人心。毋得妄自尊大……然明瑞等当年所定八款,事隔年久,抑或俱为虚文,早已置若罔闻矣。著将此各抄一份,寄与新疆各驻扎大臣,与前旨一并列入伊等交待事项,令各任大臣铭记查照遵行,不得视为具文。”[8]册15,610
尽管以乾隆皇帝为代表的清政府对“德风乌什哈达互讦案”极为重视,仅处置此事的相关满文密寄谕旨即有数十道之多。但是,随后发生的历史事实显然也证明了清政府执法的随意性:乌什哈达“寻复起授头等侍卫、虎枪营营长、键锐营翼长”[5]11993。德风,由绞监候改为监禁,但随即就在两年后的乾隆四十九年(1784)三月,乾隆皇帝又特意降旨:“德风获罪监禁,已逾二载。伊系文职,乃与乌什哈达忿事,互相讦奏,咎已难辞,又复动用库项私盖官房,是以将伊治罪。然究与侵蚀入己者有间,著加恩释放。”[2]卷1202,78可见,随着清廷对“德风乌什哈达互讦案”调查的持续深入,乾隆皇帝自己的态度亦开始有所松动,对案件的追查有着前紧后松、随意执法之特点。
不可否认的是,尽管乾隆皇帝此次借“德风乌什哈达互讦案”对清代新疆吏治进行的整顿,虽对新疆的吏治建设有一定的积极影响,但由于当时的新疆吏治问题早已积重难返,后来发生的历史事实亦充分证明,乾隆皇帝此次对新疆吏治的整顿是不彻底的,固然也就很难真正有效。尤其是随着清政府对吏治相关问题的不断深究,特别是当问题波及至驻疆大员之时,清廷或许是出于顾忌大范围的打击可能会动摇自己的统治根基,进而会将大多数涉案官员予以谅宥,但这又最终致使清代新疆的吏治走进了一个互为因果的恶性循环之中[10]。
因为,仅仅在“德风乌什哈达互讦案”之后的乾隆四十七年(1782),新疆就发生宜禾县知县瑚图里亏空库银九万两、奇台县知县窝什浑亏空库银四万两等多件小官大贪的案件,以及随后乾隆四十九年(1784)的杨桑阿贪腐案、乾隆五十二年(1787)的魁林亏空案,嘉庆年间的喀喇沙尔多任大臣亏空库银案、奇臣贪赃案、那灵阿贪腐案……这些历史事实早已告诉我们,如仅靠皇帝的一时态度来整顿吏治,虽会对官员们能起到某种程度的威吓作用,但这也只是限于某种局部的暂时整顿。有法不依,执法不严,或者违法不究,执法随意,缺乏完善的法律制度保驾护航,又欠缺卓有成效的制度监督,清代新疆的吏治也只能是苟且不已,最终亦仅有病入膏肓这一种结局。这也正如乾隆皇帝本人在面对屡禁不止的贪腐大案时,也只能仰天长叹:“官官相护恶习,固结不解,实为可恨。”[8]册13,6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