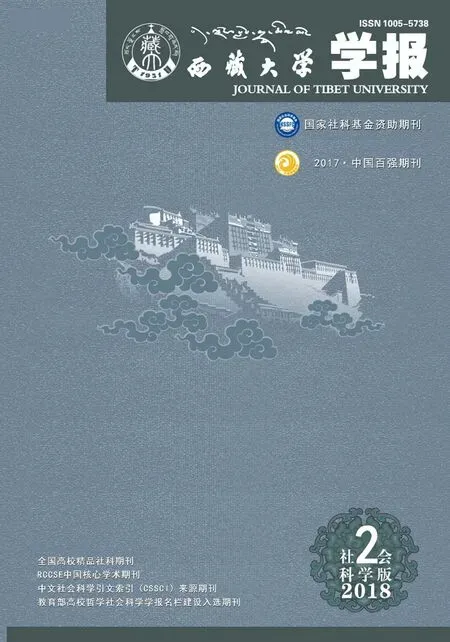从“主流话语”到“性别觉醒”
——关于西藏当代女性小说的文学转型与文化思考
马小燕
(中山大学中文系 广东广州 510275)
西藏当代汉语长篇小说肇始于20世纪50年代,形成了以男性为主的作家群,女作家仅有益西卓玛、央珍、冯良等人。21世纪以来,日渐成熟的西藏女作家创作了大量优秀长篇小说,完整地展现了西藏女性的生活状况和精神状态,重塑了女性的社会形象,表现出西藏女性把握自己命运的渴望,构成了西藏小说界的一道靓丽风景。目前,学术界对西藏女性小说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王泉在《中国当代文学的西藏书写》中认为央珍《无性别的神》在强烈的时代气息中呈现出主人公女性意识的觉醒过程,安妮宝贝、红艺、杨金花、摩卡、陈泠、江觉迟等新生代女性小说表现出了疾病的隐喻与爱的传奇[1]。徐琴在《文化身份的建构与书写——当代藏族女性文学研究》中提出,央珍、格央、白玛娜珍、梅卓、尼玛潘多、亮炯·朗萨等人的作品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当代藏族女性作家小说创作的不同风貌[2]。此外,尚无学者对西藏女性小说进行过专门研究,鉴于此,笔者希望对此有所贡献。
一、西藏女性小说的突破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西藏当代文坛出现了藏族女作家的身影。1981年益西卓玛发表长篇小说《清晨》,开启了藏族女作家从事汉语长篇小说创作的大门。1994年,央珍发表了《无性别的神》这部被誉为“西藏的《红楼梦》”[3]的长篇小说。在这些前辈作家的带领和感召下,西藏女作家的数量在21世纪呈现出迅速增长的趋势,涌现出了白玛娜珍、格央、尼玛潘多、多吉卓嘎(羽芊)、杨金花、陈泠(才仁玉真)等女作家,形成了一个以反映西藏女性生活为小说主题的女作家群体,创作出了数量众多的女性小说作品,产生了较大的社会影响。这些女性小说一改以往以男性为中心、女性为附属的主题,实现了西藏当代汉语长篇小说向女性中心的转变。
西藏女性小说的出现与现实生活中女性地位的提高密不可分。随着西藏经济社会的发展,西藏农牧区妇女也有了追求性别平等的机会,开始在西藏社会崭露头角。这种新情况势必引起女作家们的注意,并形成一种为女性代言的冲动。由于性别相同,女作家对西藏女性的生活比较了解,在创作上有男性作家不可比拟的优势。西藏以往的长篇小说多偏重于政治性、军事性、历史性等宏大主题,基本上不涉及女性的情感生活,正面人物大都是高大全式的正人君子。而随着西藏社会的发展和妇女地位的提高,人们已经厌倦了传统的小说主题,希望能够在内容上有所拓展,读者对女性文学的需求也在增加,时代呼唤能够反映西藏女性生活的文学作品,在这种情况下,西藏女性小说就应运而生了。
西藏女性小说毫无悬念地将女性作为主人公,男性多是以配角的身份出现。这样的安排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出女作家的女权主义思想,是对以往以男性为中心的西藏当代汉语长篇小说传统的挑战。益西卓玛的《清晨》[4]讲述了西藏和平解放以后,饱受头人和国民党反动派压迫的西藏农奴盼望筑路大军的到来,希望早日翻身解放的故事。虽然这部小说仍然是以军事政治题材为中心,但是也塑造出女农奴卓嘎、进步农奴白玛、解放军医生王小英等女性人物形象,她们惦记远行的丈夫和孩子,帮助受苦受难的农奴,展示出女性的柔情和母性,使小说充满了浓浓的人情味。央珍《无性别的神》[5]则完全抛弃了以男性为中心的创作手法,第一次将女性作为小说的中心进行书写,巧妙地用二小姐德吉卓嘎与女解放军的接触,实现了女性角色的对接,呼应了“无性别的神”这一题目。而《拉萨红尘》《复活的度母》《让爱慢慢永恒》《紫青稞》《西藏生死恋》《藏婚》《心印》《莲花》《天堂高度》等女性小说则涵盖了西藏女性的爱情、事业、命运、家庭、宗教等诸多主题,对藏族女性的生活进行了立体式的展示。如果说早期西藏当代汉语长篇小说中的女性是完全政治化的人物的话,那么西藏女性小说则赋予西藏女性血和肉,还原了她们的真实面貌,这应该是西藏当代汉语长篇小说的突破。
二、西藏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
在20世纪的中国女性文学中,性爱主题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都是一块无人敢涉足的雷区。女性作家一方面受到传统文化的挤压,一方面找不到自己的话语方式,性爱主题乃至性爱描写在女性作品中的缺失就是不可避免的,这种情况直到80年代以后才有所改观[6]。由于特定历史时期的局限和浓厚政治氛围的影响,以男性为主体的西藏作家们不敢触及西藏女性性生活这一敏感话题。这样一来,拓展西藏当代汉语长篇小说内涵的任务就落在了西藏女作家身上,直到21世纪以后,西藏女作家们才开始大胆地在小说中描写西藏人的性生活。
白玛娜珍的小说作品具有地域上的跳跃性和时间上的宽广度,作家没有局限在西藏的特定时空,而是在更大的场域中叙事,将落脚点放在了女性身上,在性的诠释方面进行了富有颠覆性的尝试,突出了女性“感性”的一面。在她的笔下,性成为小说中不同女性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追求性刺激,女主人公随意地和不同的男人发生性关系;看见其他人做爱也能激起她们的性趣;女性朋友间随意评论各自的性生活,而不把它当作自己的隐私。女性性生活的对象除了藏族男性以外,汉族男性也成为藏族女性人生中的重要参照物出现,但这些男性只是昙花一现,只有极少数人成为藏族女性生命中的另一半。
正如卡伦·霍尼所说,性交除了具有生物性的功能外,还有一种价值:证明自己的被需要[7]。白玛娜珍笔下的现代藏族女性敢爱敢恨,不愿意依附于男性,不甘心过平凡的生活,而是醉心于追求纯洁的爱情,追求精神上的洒脱,从身体到精神都要自己做主:她们鄙视夫唱妇随的社会规则,不能忍耐只忠于一个性伴侣,而是首先从身体上解放自己,即使已经结婚,但是只要遇到合适的男性,就可以随性而发地和对方发生性关系,满足身体上的欢愉。能够享受众多男性的爱欲,充分说明了这些女性的魅力。但是青春易逝,在厌倦这种追求肉体享乐的生活后,她们只能选择遁世,或者孤独一人生活,最终也没有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从追求家庭幸福的角度来说,这些女性都是悲情式人物,表达出西藏女性对现代生活的失望和厌倦。透过性生活的表象,以及女性性爱对象的多元化,可以看出白玛娜珍对西藏社会发展现状的忧虑,隐晦地表达出了她关于西藏在现代化进程中如何处理好经济发展与传统文化的关系,如何处理好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人们之间和平相处的关系等一系列社会现实问题的思考,表达出对藏族饮食文化、居住格局变化的担忧。
白玛娜珍的《拉萨红尘》[8]主要表现朗萨和玛雅这两个西藏女性在现代生活中的迷茫和无所适从。她们虽然从军医校毕业,但是走入社会后却找不到生活目标,玛雅和泽旦结婚,又和迪偷情,和徐楠偷欢,还在医院值班室里和萍水相逢的青年人多吉做爱,甚至利用到上海大医院学习的机会去找徐楠偷情。朗萨相对单纯一点,也先后经历过仁真群佩、觉尔玛两个男人,最后和觉尔玛去过闲云野鹤的生活。白玛娜珍把年轻女性们这种混乱的性生活归结为拉萨的巨大变化,认为是外部环境的巨大变化引起了西藏女性行为的乖张。小说的结尾,玛雅和泽旦夫妻二人一方面抨击电影画刊上的明星,另一方面两人又在夫妻生活中假扮成性工作者和嫖客,追求刺激。但是她们又非常坚决地将自己与从事皮肉生意的“小姐”区别开来,用不再穿裙子这种行为来证明自己的正经。这种矛盾的心理说明在城市中生活的西藏女性更容易受到现代潮流的影响,她们在性对象的选择上不拘一格,但是在心理上又很排斥性工作者用身体来换钱的性行为,认为这种行为背离了人性的初衷,表现出西藏女性朴素的审美观。
《复活的度母》[9]的内容比较复杂,情节设置从旧西藏延续到了现代,时间跨度很大,思考的问题也更加深邃,关照到了社会变革中人的命运、宗教的起伏和社会的发展等问题。琼芨的一生是与男人斗争的一生,先后经过了巴桑顿珠、洛桑、丹竹仁波切三个男人,生下一男一女,在与青梅竹马的丹竹仁波切承鱼水之欢后,丹竹仁波切在临别之际赠送给她一箱珠宝,但却因为佛事繁忙、信徒如众星拱月般的护卫而无法脱身,未能和意中人白头偕老。作为一个没落贵族的后代,琼芨为了和命运抗争而奋斗着,但是她的性格却使自己一次次被命运所捉弄,最终只能选择向社会屈服,转而在子女身上寻找亲情的安慰。女儿茜洛卓玛的命运却与母亲大相径庭,她生在了一个好时代,不愿意接受母亲托人安排的事业单位的工作终其一生,而是在社会上闯荡,和哥哥旺杰一起经营藏餐厅。在感情上,她先后经历了老岩、洛泽和普萨三个男人,老岩打开了茜洛卓玛的青春之门,教会了她性爱;洛泽带给她快乐和欢愉,普萨王子则给了她爱情。虽然她没有找到合适的伴侣,但是她还非常年轻,脱离了体制的束缚,有足够的时间去寻找属于自己的幸福。
三、西藏女性对幸福生活的追求
不同的女性对幸福有着不同的理解,西藏女性也不例外。对于藏北牧女来说,用一己之力将兄弟几人拢在自己身边,过着一妻多夫的生活,那就是幸福。而对于农区的女性而言,走出乡村,到县城或城市里去生活才是幸福。对于县城中的藏族女性来说,更乐于看到县城规模的扩大、人口的增加和生活条件的改善。西藏女作家们在小说中阐释了西藏女性不同的幸福观,也反映出西藏社会的巨大变化。
格央的《让爱慢慢永恒》[10]讲述了20世纪初的藏族女性追求幸福的故事,充满了忧伤婉转的悲伤情绪,女性们的结局因为跟随的男人不同而大相径庭。为了生存,玉拉被嘎朵抛弃后,嫁给了一个商人为妻,过上了安定的生活。但是当嘎朵再次出现并要求她跟他出走时,她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还是为了追求精神上的幸福离家出走,在索南旺堆的帕多庄园中谋生。因为嘎朵所管的账目出现亏空,两人又一次逃到了江孜,嘎朵加入了英国人组建的警察队伍。最终,嘎朵被同属军队的士兵杀死,玉拉变成了寡妇,她当年所追求的幸福也戛然而止。姬措姆和嘎乌·索南平杰私通后怀孕,而平杰又出家为僧,由于担心哥哥回来后嫌弃自己,她离家出走,跟着一支马帮去往印度大吉岭,在队长的帮助下安顿了下来,在那里生下孩子,给英国警察部队当佣人,被派去照顾锡金人莱顿纳上校脾气古怪的表弟吉苏亚。在她的精心护理下,吉苏亚的身体康复了,他对姬措姆产生了深深的依恋,两人结为夫妻。当吉苏亚接受表哥的邀请前往江孜组建警察部队时,姬措姆也一同前往,并在那里见到了颓废憔悴的嫂子玉拉。最终,姬措姆和丈夫离开西藏,到英国乡下以务农为生。而索南旺堆的二太太姆娣曾经是拉萨时尚潮流的引领者,被丈夫卖到了大理的妓院里,六年后,又被逛妓院的马帮队长赎了回来,最终在一个尼姑寺里出家,追求心灵上的平静。索南旺堆的三太太因为多次拒绝丈夫的求欢而被殴打,她拒绝了商人李先生的求爱,又希望嘎朵能够带她离家出走,但当她看穿嘎朵的本性后又放弃了这种想法,最终接受了李先生的爱情,跟她回到云南大理的家乡,过上了幸福的生活。这部小说将西藏女性的幸福生活捆绑在男性身上,表达出特定历史时期的女性在追求幸福之路上的坎坷和无奈。
在尼玛潘多的《紫青稞》[11]中,普村的青年男女们都不愿意像自己的父母那样当一辈子的农牧民,而是希望到城市里去闯荡,进城打工就成为他们脱离家乡的唯一途径。在这个过程中,男人们首当其冲,扮演着带路者的角色,他们带给普村的冲击首先表现在对传统婚姻形式的背叛,不愿意继续过一妻多夫的生活,而是要建立自己的小家庭。在城市里闯荡的年轻人的命运打破了普村原有社会阶层的结构,由于小儿子多吉在城市里闯荡的失败,原本处在金字塔尖的宗教人士强苏家的社会地位受到极大冲击,而旺久生意的成功,使得处在金字塔底层的“不可接触者”铁匠家的社会地位不断提高,激发了人们对金钱的向往。阿妈曲宗的女儿桑吉、达吉、边吉为了追求幸福的生活努力奋斗。桑吉为了寻找情人多吉第一次走出普村,来到城市,经过一番波折后,放弃了自暴自弃的多吉,最终和强巴结婚,留在了城市。二女儿达吉去给没有子女的二叔当女儿,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做起了生意,卖奶渣、卖酥油、开茶馆,最终和丈夫普拉分道扬镳,和旺久合作开了一家大型批发部,当上了女商人。边吉投靠二姐后,因为受普拉的谩骂和责打,愤然离开二姐,自己去闯荡生活。三个人的奋斗之路虽然充满艰辛,但是她们却通过自己的努力成功走出了农村,实现了自己进入城市的愿望,用崭新的钞票博得了普村村民们的羡慕和敬佩。是改革开放改变了人们的思想观念,为西藏的藏族女性们提供了经商的舞台,纺织氆氇、制作奶渣、酥油、甜茶和青稞酒这些西藏农牧区女性掌握的基本生活技能,却成为她们告别农村,来到城市后从事商业生产的优势。桑吉和达吉作为第一批吃螃蟹的人,抓住了这样的机会,成功在城市里立足,也获得了幸福的生活。而作为小妹的边吉因为年龄小,不谙世事,喜欢意气用事,还在社会上闯荡,继续寻找自己的幸福生活。这些女性的奋斗过程也反映出西藏城市和农村的巨大差异,农村代表着保守和落后,而城市代表着开放和机会,农村中社会地位不同的人在进入城市后,实现了原有社会地位的反转,改变了自己的命运,使城市成为农村人心生向往的吉祥之地。
多吉卓嘎以身边的女性朋友为小说人物的原型进行创作,回答了不同民族的女性在西藏这片土地上的交集和冲突,而把男性作为不同民族女性之间发生联系的桥梁,反映出不同民族的女性对心目中理想男性的判断标准,以及对爱情不同的表达方式。藏族女性被塑造为西藏传统文化的代表,而汉族女性则来自现代都市文化,对藏族男性而言,中年男性更加保守,喜欢传统的藏族女性,虽然和汉族都市女性发生肉体上的关系,但是却在心理上将其拒之门外。而青年男性则更加开放,不愿意延续父辈的传统生活,而是乐于到城市中生活。虽然他们的根在农牧区,不能违抗父亲的家长权威,和传统的藏族女性组成家庭,但是心理上却更加喜欢汉族都市女性。多吉卓嘎在她的小说作品中通过性生活的描写,来反映女性的感情生活,表达出汉族女性对自己的身体有着绝对的决定权,而藏族女性在现阶段仍然无法完全掌握自己身体的意味。
《西藏生死恋》[12]具有浓厚的藏地风情的味道,而女性对于爱情的追求和性生活的把控才是小说的重点,使小说具有浓厚的女性小说的意味。在无人区中以放牧为生的雍西没有能力拒绝不喜欢的男人的骚扰,只能被迫做影子猎队的首领姬迦的女人,她威胁姬迦时总是大喊“休想再进我的帐篷”,强调对自己身体的所有权。而深爱着公扎的女盗匪色嘎为了捍卫自己一厢情愿的爱情,竟然用刀捅了风,要用这种方法除掉情敌。最终,女性们都找到了自己的幸福生活。只有风为了追求精神上的幸福,留在错愕草原依靠绿色肉类生意为生,痴痴地等待公扎,希望能够收获属于自己的幸福生活。
《藏婚》[13]中的女主人公卓嘎是藏东结巴村的藏族姑娘,在父亲权威的安排下,按照传统习俗,嫁给了未曾谋面的嘉措五兄弟,延续着藏族一妻多夫的传统婚俗。但是她的家长嘉措却在拉萨与一个来自北京的名叫好好的汉族女人相好。这个眼神里充满忧郁的康巴汉子就这样行走在传统与现代中,在藏族女性和汉族女性的身上抛洒着自己的力量和汗水,既要当好家长,又不愿意和兄弟们分享卓嘎,还不想失去好好。卓嘎和丈夫们新娶的妻子央宗共同和五个丈夫按照祖先留下的风俗习惯生活着,只是卓嘎和嘉措、扎西、朗结在拉萨,央宗和宇琼、边玛在老家照顾父母,表达出传统生活方式和现代生活方式的融合。与卓嘎这样的藏族传统女性相比,琼宗和萨珍则显得非常叛逆,琼宗不愿意嫁给自己从未谋面的仁钦三兄弟为妻,选择了逃亡城市,使自己的父亲和未婚夫的父亲双双颜面扫地,家人也都抬不起头,却在拉萨和仁钦相识相爱。但他们的爱情没有得到仁钦父亲的首肯,这位倔强的父亲又给儿子们说了门亲事。琼宗在坚持传统文化的仁钦家人的上门辱骂和责打中失去了活下去的希望,选择自杀;而愧疚的仁钦在拉萨磕长头赎罪后又被迫回家去尽到自己家长的职责。萨珍忍受不了当尼姑的孤独和寂寞,和僧人丹增相好。面对同村人的侮辱,他们最终选择了私奔,远走他乡,在拉萨经营甜茶馆,养育了两个孩子,过着自己甜蜜和辛苦相伴的小日子。这些西藏女性的不同遭遇表明,在现代化的过程中,西藏女性已经不能对外面的世界视而不见,因为男人们往来于农村与城市之间,发挥了桥梁的作用,也将西藏女性带入到现代社会中。不管结局如何,西藏女性不但在婚前掌控自己的身体,而且在婚后也追求精神上的满足,对两性之间爱情和幸福生活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
在多吉卓嘎的这两部小说中,公扎在和风发生性关系时,喊出措姆的名字,嘉措在和卓嘎发生性关系时,喊出了好好胡诌的燕子的名字。前者表达出藏族男性对传统藏族女性的爱恋,虽然公扎退伍后成为一名公职人员,先于错鄂草原的其他人接触了外面的世界,但是他的心却没有发生变化,依然对传统文化化身的初恋情人念念不忘,反而提前退休后成为一名猎人,过着风餐露宿的复仇生活。后者表现来自农村的藏族男性对现代汉族女性的仰慕之情,虽然嘉措结婚了,但是他却不愿意担任家长的角色,在家人和卓嘎面前一味逃避,只是迫于压力,没有做出逃婚的行为,而是在拉萨和好好同居,但是他又不得不突然消失,返回农村处理家庭事务。在某种程度上,《藏婚》是《西藏生死恋》的延续,不仅保留了卓一航这个人物,而且还创造出了他的养父卓麦和卓嘎的母亲年轻时是一对恋人,被卓嘎的爷爷按照传统婚俗拆散,在儿女们的共同努力下,才将卓麦的骨灰在送走母亲的天葬台安葬,让两位有情人的灵魂结合在一起。展现出现代文明对西藏传统文化的深层次影响,也表达出西藏青年对现代生活的接纳。
结语
正如茱莉娅·克里斯蒂瓦所说:相信一个人“是女人”,几乎就像相信一个人“是男人”一样荒谬和朦胧,我对“女人”的理解是“女人”无法逾越、无法言传,存在于命名和意识形态之外[14]。西藏女性小说反映了西藏女性希望获得更大社会自由度的现实,完成了对女性肉体和精神上的双重阐释,大胆地表达出西藏女性的生理需求,发出了西藏女性不再是匍匐于男性脚下的仆役,而是自我独立的现代女性的呐喊。女性作家们表达了西藏女性追求精神满足的高品质追求,突破了以往男作家们难以深入其中的创作瓶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