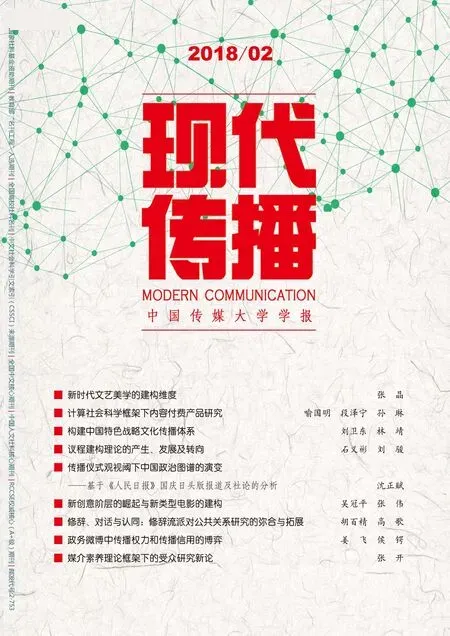元媒介与元传播:新语境下传播符号学的学理建构*
■ 赵星植
元媒介时代下所显现出来的传播与媒介内涵的双重变革,给当代传播学理论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以媒介效果为中心的经典大众传播理论并不能有效的解释传播主体在元媒体时代所发挥的强大作用力。同时,元媒介时代也呼吁新的研究路径,新的传播理论,它为当代传播学重审学理逻辑、重构理论体系带来了新的切入路径;更为传播符号学这一探究符号意义及其符号使用者之相互关系的传播学派,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
一、“元”概念:新语境下研究范畴的革新
“元-”(meta-)一般用于学科或概念名称上,意思是 “关于什么的什么”。meta-这个前缀,希腊文原是“在后”的意思。亚里士多德的文集,哲学卷放在物理卷之后,名为Metaphysics(“物理之后卷”)。哲学是对自然深规律的思考,此后meta-就获得了全新的含义,指的是对世界规律的探讨。因此,所有有关“元”的讨论,实则都是关于某个理论、术语或现象背后更深一层的层控规则之讨论。而用“元”概念来统摄新媒介语境下的媒介形态与传播活动,并非术语更替,而是表明二者在媒介技术推动下所产生的根本性变革。新的媒介形态与传播方式,呼吁传播学研究的新范式。
“元媒介”(meta-media),即“媒介的媒介”,具体是指以计算机、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等智能终端为代表,基于互联网与移动终端为一体的新传播平台。这类新媒介平台的最大特征,就在于先前所出现的所有媒介及其传播方式皆可以共存在这类平台之中,或以模拟或虚拟的形式存在于其中。换言之,元媒介时代的所有媒介类型都是原生于或寄生于元媒介家族的。如纸质媒体或者广播媒体现在寄生到元媒介中,而博客、微博以及社交网络这样的新媒体则本来就原生于元媒介之中。这就是所谓的“元”:它既与现存媒介相平行,却又不同于任何一类现有媒介①。它作为媒介之媒介,既是传统媒介在新平台进行传播的新媒介,又是如社交网络这类新媒介平台的产生之地。
有学者将元媒介形象地称为“屏幕页”(Screen Page)②。 因为诸如电脑、手机等移动终端屏幕中的几乎所有内容都是来自其他媒介,所以元媒介在内容和形式上,都是其他媒介的翻译、改制、改造③。不少学者从媒介融合的角度,讨论这类网络新媒体技术带来的变革。但笔者认为这种融合的关键并不在于媒介平台的整合,或传统媒介在融合媒介平台上发挥着各自原有的功能。而在于它以一种“再媒介化”的方式实现对现有媒介传播方式的升级,并对当前整个符号表意结构以及传播方式有着根本的影响。
元媒介既然是再媒介化的媒介,那么元媒介平台上的文本是在对上一级媒介文本的跨层次再度使用;它再现的仅仅是上一级文本的某些形式或品质,由此失去与次级媒介的直接关系,最后可能会完全抹掉原初文本的次级媒介特性,进而形成于一种高于传统媒介的元媒介体系。例如,电视媒介文本在元媒介平台再现,其视频文本的特性被保留,但其单向的传播特性已被抹去。特别是元媒介平台客户端中,实时直播、弹幕、及时转发评论等新媒介技术的方式,即便是电视这一寄生于元媒介之中的媒介文本,已很大程度上失去原本的传播方式和特性。
因此,从本质上说,元媒介的“元”在于其新的传播关系和方式的嵌入与整合。正因为它是统合次级媒介的上一层媒介,所以它必然对传播方式及其传播主体关系进行重塑。这种重塑的根本后果是整个文化社群意义编码及其组织形式的变革。元媒介形式下所酝酿出的一个全新人类传统形态正在形成,那就是“以人为中心、以连接了所有媒介形态的人类大环境为媒介而实现的无时不在、无处不在、无所不能的传播”④。元媒介位于沟通串联的核心位置,使传播在媒介汇流中成为人与社会新的连接方式⑤。
而这种新嵌入传播关系的根本,即为“元传播”(meta-communication)在元媒介平台的凸显,并逐渐成为影响媒介传播活动及其形式的主导因素。“元传播”,也即“关于传播的传播”,这一概念最早由贝特森(Gregory Bateson)提出。贝特森主要从言语交流层面指出元传播问题:“人类的语言交流不仅能够,而且一直是在许多抽象的对比层次上进行”,这实际上已经指出了语言符号交流的层控关系这一经典命题。他进一步认为,任何言语命题除用于指涉事物的实际状态,还在另外两个层面上展开。第一是把元语言信息(meta-linguistic information)引入到传播活动之中,用于指明传播内容的解释规则。第二,交谈双方也传递彼此之间的关系意义。这表明人们为了传播,不得不进行元传播活动,不仅是为了使传播的信息更加准确,更重要的是为了在传播中建构内含人际关系的交往规则。因此,元传播解决的正是“在关系之中怎样讨论关系并由传递关系意义的元传播建立关系的问题”⑥。
贝特森的研究仅在于人际传播,并指出了元传播在人际交流层面的隐匿性,“绝大部分元语言和元传播的讯息都是含蓄的”⑦,因而必须经由“语言”得以推断。然而,相较于人际传播与大众传播中元传播模式的“隐身”,元传播诸问题则是凸显在元媒介传播活动之中。换言之,元媒介中的元传播活动,不仅是传播符号意义的内部编码规则,更是作为传播活动本身参与到具体的传播实践之中。
丹麦学者延森⑧(Klaus B.Jensen)则回应了元传播与元媒介之间相辅相成的关系问题。他认为元媒介的本质特性在于,传播主体对“元数据”(meta-data)所进行的一系列元传播活动。元数据是关于任意信息的来源、特征及其轨迹,如文本的标题、关键词、索引数据等。这也使信息抓取与搜索成为可能。而元数据在元媒介的普遍化存在,使得传播者的能动作用大大增强。媒介使用者对于网页、图片的“标签”(tag)、“点赞”、转发等等,都在实际的参与到元数据的编码工作中,进而参与的是传播文本的实际创造。而传播主体在元媒介语境下,对传播符号文本所进行的符码或传播语境的重塑,实际上是“元传播”在元媒介语境中的显现。
因此,借用彼德斯(John Durham Peters)的名著《对空言说》(Speaking into the air)之标题,过去的元传播一般都消失的无影无踪(into the thin air)。但在新媒体语境下,媒体使用者则是对系统(system)言说。从时间戳(time stamps)到“emoji”表情,从搜索关键词再到社交媒体中的标签书写,传播这在元媒介中的交流与互动中,传播者时时刻刻都参与到了元传播这种编码机制中来。更重要的是,位于上一层的元传播机制,在元媒介的传播实践层面,被实时记录了下来。元传播以及符号意义建构规则,从面对面传播、大众传播时代的临时“缺场”变成了元媒介时代的时刻“在场”。这为我们从意义规则层面去探究元媒介语境下的传播规则提供了一条很好路径。
二、元媒介中的“元传播”:传播符号学研究范式的突破口
问题的关键是,元媒介语境下的元传播活动是如何进行的,且又是如何具体地影响到传播主体之间的具体传播实践的。并且,“元媒介”与“元传播”作为一对新的研究范畴,其研究路径和具体突破口在何处。关于前者,延森作了较为深刻的探讨。他的研究可以算作这一新兴课题的成果。延森认为,可根据元媒介系统与元媒介使用者对信息控制能力,以及对信息内容和访问时间的选择,把元媒介中的元传播活动分为如下四种类型⑨:
(1)审阅传播(processed communication),即系统通过个体使用者的媒介使用轨迹进行记录,为用户提供账单、系统维护、市场分析等等。在审阅传播之中,最关键的一环在于元媒介用户的“注册”(registration)这一行为。注册使得传播者的元数据得以搜集和整理,并成为下次传播活动进行的起点。
(2)推荐传播(recommended communication),即系统管理员根据不同使用者集体的传播行为的考察,以确定最受欢迎的传播行为,或者该用户群体最受欢迎的传播内容,并由此推荐给使用者集体的内容。比如,亚马逊网站所推荐的购书清单,微信与微博中的推荐文章或者推送广告,等等。
(3)迭代传播(iterative communication),即使用者以异步或同步的方式,参与到针对彼此交往或传播活动的评论、转发,甚至传播的内容的集体编辑或创作等。例如,知乎、维基百科、百度百科这样的开放编码平台中的用户参与。这使得用户不仅将自身、而且将彼此进行了编码,并整合到不同的社会关系之中。
(4)第三方传播(third-party communication),即系统把用户在元媒介中进行因为传播活动中所留下的数据信息,进行重新整合,并将其发布给如广告商、市场管理者或者政府单位等等。与审阅传播相比,第三方传播的主动权被系统所操控。
客观的说,延森从系统与系统使用者两个维度,对元媒介中四种主要元传播类型的探讨,为我们探究元媒介中的元传播形态提供了诸多启示。然而,上述四种分类仅仅说明了元传播模式在元媒介平台的技术性特性,并且这一分类还是主要在传播者视阈所进行的探究。这一分类模式并不能说明的是,作为传播主体的媒介使用者在诸种元传播活动中,对传播内容也即符号意义编码与意义规则建构,究竟起到了何种作用。
上述这种把媒介技术与传播主体能动性二元对立的方式,在当代传播学中普遍存在。如法国学者麦格雷所言,以二元论为中心的传播观实际上是把理性与技术对立起来,把人的思维与行为对立起来。他解释到,人类在世界上的行动可以参照不同的标准——如工具的、规范的、表达的——而这些标准或秩序之间实则上并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从本质上说,“人类并不是双脚站立在技术的大地上而思想却飘浮在星空中”⑩。
而笔者认为这恰恰是当代传播符号学理论可着力开掘的地方。近年来,国内一批学者开始注意到元传播问题的重要性,并主要从概念梳理,学术史脉络以及应用前景进行了讨论。但目前还鲜有研究讨论如何从元传播视角推进元媒介中的诸种传播问题方面。而传播符号学之所以可作为其突破口,是因为元传播把传播主体间的关系意义置于核心,这正是传播符号学研究的最主要内容。
如传播学家菲斯克(John Fiske)所述,传播符号学把“传播”理解为意义的生产与交换。因此这一学派的重要任务在于理解意义背后的社会文化机制或意义生产机制,并赋予接受者在意义生产过程中更加主动且积极的地位。传播符号学把信息理解为传播主体因符号而产生互动,并由此所协商的意义;因此它更加注重传播主体的互动与协商机制。
相较于现有研究对元媒介中元传播类型的技术特征及其传播过程的归纳,传播符号学更加关注的是,这些元传播模式如何建构传播符号学的意义解释框架,并且依据诸多元传播规则而建立的意义交流社群以及意义互动形式。从这一路径出发,可能更能凸显的是,媒介使用者的“元意识”在元媒介中相关传播活动中的实现及其能动作用。
从传播符号学的角度来看,“元传播”这一议题在本质上与“元语言”(meta-language)诸问题紧密相连。元语言,就是能使文本在阐释活动中显现为意义的一整套规则体系。元语言的存在,意味着整个符号体系的“可翻译性”。例如用一种语言可以对另一种语言进行解释。元语言不仅是意义实现的先决条件,元语言也是意义存在的先决条件。面对一个文本,任何阐释必须有元语言集合的支持。并且,在符号传播与表意的所有环节,都为符号意义的阐释提供各种元语言因素,参与构筑阐释需要的元语言结合。
同样,元语言因素还可以呈现于符号文本之中,由此主导着该符号文本的解释路径和意义建构规则。关于此点,符号学家雅各布森(Roman Jacobson)的“符号六因素论”说的非常透彻。他指出任何符号文本包含六个因素:发送者、文本、对象、媒介、符码与接收者。当其中一个因素成为文本的主导时,就会导向某种相应的特殊意义解释。特别是,当符号侧重于符码时,符号出现较强的“元语言倾向”,也就是符号文本自身提供相关线索来进行自我解释。
因此,所谓元媒介下的元传播活动,实为不同的元语言因素在元媒介符号文本中成为主导解释因素,而形成的偏向元语言符码建构与解释规则的各类传播活动。相应地,元媒介使用者同样会依据符号文本所显现的不同元语言因素类型,调动自身或解释社群的元语言集合,对符号文本进行解释与再传播。贝特森的元传播概念,超出了符码系统元语言,进入了广义的符号——语用范畴;因此应当结合新媒介的语用环境,对元语言的范畴进行扩容。
笔者赞同上述观点,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推进。元媒介平台中元传播议题的凸显,主要是因为诸如“注册”“标签”“点赞”“分享”“转发”等技术性因素的凸显,使得元媒介中的符号文本自涉强烈的元语言因素,引导者、媒介使用者对符号文本进行再编码以及再传播。笔者把元媒介中凸显的这类元语言因素,称为“技术性元语言因素”。在技术性元语言因素的引导下,使用者调动不同的元语言对符号文本的意义进行生产与再生产。
所以,从传播符号学的角度来探究元媒介中的元传播,是在技术性元语言因素分别与语境元语言和能力元语言之间的融合,并在此基础上展开关系意义的建构与传播活动。在这一维度上,媒介技术、语境与传播主体的关系意义被很好地拉入到了研究视域中。新技术要素促成新的元语言符码建构规则,而主体关系则在上述符码规则中得以重构与传播。
三、传播符号学视阈下元传播的三个层次与研究路径
元媒介平台的传播实践中,由于元语言特别是技术性元语言因素的凸显,使得符号文本的解释与传播呈现出强烈自携元语言因素。而这里由这类传播文本引发的传播活动,即为本文所谓的元媒介视阈下的元传播诸活动。现在要追问的是,在这类元传播活动中,传播主体是如何调动不同的元语言集合,进而展开意义的交流与互动,由此推进元媒介平台中的元传播进程的。
赵毅衡指出,实际上表意过程的所有环节,都为阐释提供各种元语言因素,参与构筑阐释需要的元语言集合。为此,他大致上把这些元语言因素分成三类:社会文化的语境元语言;文本构造的自携元语言;阐释主体的能力元语言。这一观点说明,媒介使用者可以根据不同的元传播类型,调动不同的元语言集合,进而产出不同的表意与传播方式。
然而,不同形式之间的元传播活动又是如何在元语言层面进行自由调度与操作?并且,不同层次的元语言集合在具体传播实践中会呈现出何种意义协商机制?为此,笔者从元媒介文本与元语言集合之相互关系入手,并根据皮尔斯(C.S.Peirce)的符号现象学“三性”原理,把元媒介中的元传播活动分为三个层次。相比于延森注重技术特性与传播过程的元传播四分类,笔者认为本文即将提出的三分类则侧重于传播主体间对符号文本的意义建构与互动行为。这一路径,可有效地探讨,传播主体在元传播过程中的能动因素,以及媒介、符号文本与传播社群之间的互生关系。并由此为元媒介时代的传播符号学研究提供一个可能的研究框架。
皮尔斯符号学的根基是其符号现象学的三性原理。他认为世间万物都可以统归于三个基本范畴:“第一性”是“显现性”,是由感觉之品质构成的。皮尔斯认为,“第一性”这种存在模式,即是那种任何一个事物毫不考虑其他事物之存在而如其自本然地存在(CP 1.25)。“第二性”是“实际性”,是实际经验的存在。“第二性”的最大特征即为感觉与经验之间的实际碰撞,是二元对立、冲突发生的根源。“第三性”即统合“第一性”与“第二性”的法则或规则。由此,我们可以用绝对当下的、直觉的、不做思考的感觉来描述“第一性”,用外部实在的、非理性的事实以及我们在经验中到处发现的阻力和斗争感来描述“第二性”,而“第三性”则就是在上述二者间协调并给出意义、秩序、规律以及普遍性。
根据皮尔斯的三性原理,我们可以对元媒介中的元传播模式分为如下三层,由此推导出元媒介语境下的三种主要的传播符号学探究路径:
第一层,是元传播的实际功能或技术层面。它主要是元媒介平台中元传播技术因素,给传播实践所带来的具体变革。在此层面上说,传播中的信息交流、转换或状态更替,均可以用规律和因果关系来进行解释。这类似于皮尔斯所谓的“第一性”范畴,这个层面是“由此及此”,也即A等于A,也即元传播实践模式与元媒介平台中的技术或者功能因素相对应。
在此意义上说,延森所谓的元传播四种类型都均属于这一层面。无论是审阅、推荐、迭代还是第三方传播,其前提条件就在于元媒体平台首先提供了这类特定传播模式的技术资源。由此媒介使用者才可以据此进行特定的元传播活动。例如,第三方传播与审阅传播的前提,就是元媒介平台所提供的用户注册功能,因为只有用户通过注册提供元数据,媒介系统才可能统计出用户的内容使用偏好,从而进行数据整理与预测。同样,基于媒介使用者的推荐或迭代传播,其前提是元媒介系统所提供的诸如开放元代码,或点赞功能。由此媒介使用者才可进行此功能对传播内容进行实时编码与再传播。
而从元语言与元传播之关系的角度来看,媒介使用者在这一层元传播活动中,主要是通过符号文本自身携带的元语言因素展开意义解释模式。特别是,媒介时代所特有的技术性元语言因素,为传播符号文本打上了独特的文本风格,并由此形成元媒介时代特定的符号表意与传播规律。据此,当代传播符号学在这一元传播层次上,已经开始进行了相关的探索。
这一层次的传播符号学研究主要从元媒介语境中不同符号文本形态变迁入手,探索这些元传播模式的表意形规律。这主要把传播学与社会符号学相结合。把以语言文本为中心的社会符号学理论推进到以非语言文本为中心多模态研究(multimodality),进而适应元媒介语境下符号形态的变迁以及由此带来的社会意义。
在其中,英国符号学者克雷斯(Gunther Kress)与霍奇(Robert Hodge)的贡献值得一提,他们重构了以学科交叉性为特征的符号学体系,试图去考察和解释社会语境中各种符号系统的意义生成和维系方式。而荷兰社会符号学家范·李文 (Theo van Leeuwen),则将社会符号学引入日常生活,指出不同的符号资源,通过节奏、构成、信息链接、对话等四种途径,整合形成多模态语篇与交际行为。由此,传播符号学这一理论分支的实践,经历了从符号到符号资源,从语言符号到其他非语言符号系统,从言语交际语篇到多模态语篇的发展脉络。
第二层,是元传播的社会或文化的层面,即符号再现差异与冲突的层面。这一元传播模式主要是表达传播主体间的身份与差异,是界定意义社群与社群间关系的层面,身份指向共有,差别指向等级和冲突。元媒介平台中的这一层面充分假定社群间存在对话或非绝对的冲突,而这些皆为各种社群与文化关系的基础。再此意义上说,这一层面类似于皮尔斯所谓的“第二性”,即因具体的传播与文化实践,所导致的意义交流、冲突与协商机制。
从元语言集合层面来看,这一层面的元传播模式,媒介使用者主要调动是语境元语言集合,即文本与社会发生的诸种关系,引出文化约定的对信息的处理方式元媒介技术以其终端开放性,人际交互性等特点为传播环境提供了真正的互动性和多元性,这极大促进了意义社群的聚合,以及社群与社群间意义交流的实时互动。例如,由于社交媒体中的实时集群功能,以及转发与分享功能的普及性与便利性,媒介使用者非常容易通过对特定符号文本的转发、评论与分享,依据所属意义社群的特定规则,对符号文本从元语言层面重新进行编码。这种基于特定意义社群解释规则的元传播模式,成为当今元媒介领域的传播常态。
同样,这种符号文本的再编码与再传播模式,一方面为媒介使用者提供了能及时沟通意见的公共平台,另一方面又为话语或符号冲突提供了机会。由此,符号意义在具体传播语境或传播事件中的使用与变异,也就是目前学界所提出的“后真相”(post-truth)时代的舆论失衡问题。当符号文本的述真问题以一种去中心化的方式传播,真相成为传播社群中的商议与相对共识之达成时,元传播中的社群关系变成为衡量“真相”的主导维度。因此,处理该问题的核心,是如何重建真相传播过程中的元传播关系链,进而建构以民主商议为核心的新型元媒介社群。
第三层,是元传播的创造性层面,主要是指元传播过程中所出现新的意义解释,并对之做出调整,包含创造性和可能性的层面:这是所谓“第三性”或“无限”的层面,是个体和社群之间的意义之普遍关系的层面,它的边界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创造性表达关系。这实际上已经类似于皮尔斯所谓“无限衍义”的定义。因此,在这一层面上,元传播可以是被视为一种规范的、意义机制之间的互动,显然这与皮尔斯所阐述的“第三性”特征是契合的。
这一层面元传播模式,主要调动的是媒介使用者的能力元语言。所谓能力元语言,即为解释者先天或后天在传播实践中所累积起来的意义解释框架、社会经验或者是知识储备。这一元传播层面,主要关注是媒介使用中在元媒介平台中逐渐形成的、完全基于元媒介平台的新表意方式与互动方式。作为三种元传播层面的最高级形式,这一层面的元传播活动是面向未来的,符号意义社群互动与建构的新方式。
这一层面的元传播活动,则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开掘。第一,是元媒介平台新型社群关系的建构与维持。以手机客户端为元媒介平台的社交通讯工具,正在从根本上改变着人类的日常生活交往习惯及其伦理准则。从朋友圈的“点赞”,到“分组”,再到主动“屏蔽”他人信息流,诸如这类交往方式是原生于元媒介平台的,是元传播的核心维度。它创造出与线下交往完全不同的交往规则,但却又实在地影响着实际生活中的人际关系。因此,对此类社群关系的研究,则必须要进入符号互动层面梳理,元传播活动在传递关系意义过程中,如何对传播主体的符号自我进行重构,并且如何在元语言层面建构新的关系意义解释规则。
第二,是元媒介语境下以激活元传播活动为核心诉求的符号消费与消费文化。当代社会是以追求符号价值为主的“异化符号消费社会”,符号增值速度远远超过社会物质生产的速度。这早已成为不争的事实。然而,元媒介时代的到来,符号消费的重心正在从对符号价值转向对符号所建构的关系意义。由此,广告主的诉求也正在从对消费者的说服,转向从元传播层面建构符号商品的关系价值。于是,口碑转发,分享送红包,“晒单”等成为商家的主要推广手段。与此同时,消费者也在分享过程中建构与维持自己的关系社群。并且,社会名流也在元媒介平台上,建构自身与消费者的互动社群,继而形成“商家—名流—消费者”的关系链。由此,社群关系正替代广告文案,成为刺激符号消费的主要因素。
综上,从传播符号学路径探究元媒介时代的元传播层次以及具体符号表意实践,其理论优越性是明显的。首先,传播符号学从元语言与元传播之关系入手,为元媒介技术和媒介使用者搭建起了沟通桥梁。进而为当代传播学在元媒介时代走出技术与理论二元论,提供了具体的探究方式。其次,传播符号学对元媒介时代中元传播之文化与意义社群交流机制的关注,为元媒介时代的传播学研究拓展了新的理论空间。由此,如何梳理并归纳元媒介语境下全新的意义交流与协商机制,就成了当代传播学所不能忽略的一个重要面向。第三,传播符号学关注元媒介语境中,媒介使用者之间创造性的表意模式之开掘,为元媒介时代符号消费与文化生产的研究提供了新的切入点。
注释:
①⑧ [丹]克劳斯·布鲁恩·延森:《媒介融合:网络传播、大众传播和人际传播的三重维度》,刘君译,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96-98、98页。
② L.P.Glazier,DigitalPoetics:TheMakingofE-Poetries,Tuscaloosa and London:The University of Alabama Press,2002,pp.115-119.
③ 赵星植:《论元媒介时代的符号传播及其特性》,《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3期。
④ 赵启正:《“序一:沉浸传播——新媒体时代的新概念”》,载李沁:《沉浸传播——第三媒介时代的传播范式》,清华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页。
⑤ 张斌:《屏幕研究:“元媒介"时代影视研究的融合路径》,《暨南学报》,2015年第7期。
⑥ 王金礼:《元传播:概念、意指与功能》,《新闻与传播研究》,2017年第2期。
⑦ Gregory Bateson,StepstoAnEcologyofMind.London:Granada,p.151.
⑨ Klaus B.Jensen,HowtoDoThingswithData:Meta-data,Meta-media,andMeta-communication,First Monday,vol.18,no.19,2013,http://firstmonday.org/ojs/index.php/fm/issue/view/404.
⑩ [法]埃里克·麦格雷:《传播理论史:一种社会学的视角》,刘芳译,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页。
(作者系四川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