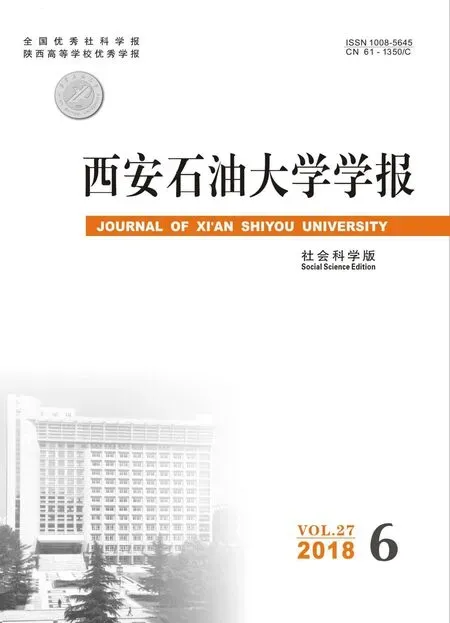主体:幻象领域与存在落陷
——《致命魔术》的拉康式解读
栾 鑫
(集美大学 文学院,福建 厦门 361021)
0 引 言
《致命魔术》是著名导演克里斯托弗·诺兰的代表作之一,改编自克里斯托弗·皮瑞斯特的同名小说。影片讲述在魔术盛行的维多利亚时代出现了两位优秀的年轻魔术师,二人本是好友,却由于种种原因互相猜忌,最终成为了势不两立的对手,他们各自费尽心机,渴望证明自己才是当时最顶尖的魔术师。而两人的竞争过程就是一出主体完成确立,并在欲望中走向灭亡的悲歌。笔者试从拉康精神分析理论的视角阐释《致命魔术》,以影片主人公为例,揭示主体确立的过程和宿命,以及主体在欲望中永恒失落的残酷事实。
1 镜像阶段:那喀索斯之影的陷阱
自我实际上是无知与误认的领域。与弗洛伊德不同,拉康对生物性的本我持否定态度,正如黑格尔所言的人是一个自然意义上的黑夜,人的开端是无,并不存在本能原欲。在婴儿阶段,婴儿不具备感知整体的能力,无法控制自己破碎的身体,并且对于被肢解的身体感到焦虑。而在面对镜中自身影像的一刹那,他发现了统一整合的形象,于是他把这个镜中的影像看作是自己本身,自我的形成在这一刻有了起点。
一个尚处于婴儿阶段的孩子,举步趔趄,仰倚母怀,却兴奋地将镜中形象归于自己,这在我们看来是在一种典型的情境中表现了象征性模式。在这个模式中,“我”突进成一种首要的形式。在与他人的认同过程的辩证关系中,“我”才客观化;语言才给“我”重建起在普遍性中的主体功能[1]90。但是,也正因如此,人在诞生之初就将自己的起源让位于他人,因为影像并非真正的自我,而是一种虚假的映像,幻象在给予自身完整性的同时也剥夺了自我的主体性,他人奴役并取代自我,于是,自我在形成之初就吊诡地走向了异化。在镜子阶段,婴儿通过身体运动来控制镜中影像的运动,在这个过程中,婴儿获得了一种对自身整体性的把握,自己的身体不再是分离的,而是具有了一个统一的形象,自我的产生正是来源于这个身体的倒影。而在这个过程中起到关键作用的正是“认同”,即婴儿认同镜中的影像就是自己,倘若没有这种认同,那么婴儿将永远无法建立起整体的自我,并且最终将在破碎的身体中走向自我的空无。然而这种“认同”也同时是“异化”的开端。婴儿把镜中的形象与自我相混淆,并且对这一形象的侵凌毫无自知,甚至把主体的地位主动让位给他者,于是自体被他者取代,最终成为了镜像。可以说,自我的出现一开始就伴随着异化。
在《致命魔术》中,波顿就是安吉尔的镜像。两人自小是要好的伙伴,一同跟随卡特进行魔术表演和学习。安吉尔是贵族出身,举止高雅,风度翩翩,并且有高超的表演天赋,但他的魔术技巧却有所欠缺。与之相反,波顿出身普通,不修边幅,醉心于研究魔术技法,有着惊人的洞察力和创造力。两人在看过中国魔术大师的表演后,安吉尔对大师变出鱼缸的神奇之举感到困惑,波顿却一眼看穿其中的玄机,可见在魔术技巧上,波顿显然是胜过安吉尔的。之后的一次魔术表演中,波顿在给进行水下逃生表演的女演员绑手上的绳结时出现失误,导致女演员,也就是安吉尔的妻子溺死,这就给两人埋下了仇恨的种子,使两人站在了对立面。对于安吉尔而言,波顿既是他的对手,同时也是他渴望成为的镜像。安吉尔虽然有着华丽的表演技巧,但是缺乏魔术创造力,因此,在魔术的世界里,他始终感觉惶惑不安。作为一个魔术师,他自身的形象是破碎的,尚不完备整一,他需要一个他者的目光来确认自身的存在,让自己魔术师的形象得到承认。
在影片中,安吉尔一直在模仿波顿的魔术戏法。在看过波顿的“移形换影”表演之后,卡特看出了其中的妙门,并且找来了酷似安吉尔的酒鬼作为替身,还原了波顿的表演,但是安吉尔坚信波顿没有使用替身,于是他偏执地追寻波顿这段表演的秘密,并且安排自己的女助手去波顿身边打探,在女助手背叛他之后,安吉尔甚至设局偷取了波顿的日记。安吉尔痛恨波顿,但他的魔术表演却始终追随着波顿的脚步,这种追随本身就是认同的体现,他认同波顿的魔术才华,并且试图占有这种才华。他渴望复制波顿的魔术,以此来构建自己作为魔术师的完整形象。实际上,波顿作为魔术师的形象正是安吉尔的镜像,他为安吉尔提供了一个统一和完整的感觉。如果没有波顿,安吉尔永远无法成为一个伟大的魔术师,因为安吉尔受困于自己的能力,无法构建作为魔术师的自我,他只能借助于波顿的形象来唤醒自身。波顿作为镜像,在两人都没有意识到的情况下,轻而易举地夺走了安吉尔作为魔术师的本质。而安吉尔的自体受到镜像的蒙蔽,带上了名为自我的假面,上演了一出那喀索斯的悲剧故事。因为这种认同实则是一出误认,拉康认为,自我是被建立在整体性与主人性的虚幻形象基础之上的,而且正是自我的功能在维持着这种一致性与主人性的幻象[2]37。自我的功能实际上是一种误认的功能,安吉尔不愿承认自己天赋上的欠缺与不足,他拒绝接受破碎与异化的真相,否认自身作为魔术师的不完整性,于是陷入自恋的陷阱中去,迷恋上水中完美的那喀索斯之影,而那个理想之影正是波顿的形象,安吉尔却并不自知,反而视其为自身镜像,视其为理想自我,这就注定了安吉尔的悲剧命运。在这种无意识的自欺中,借助波顿的形象,安吉尔达成了自身的统一,却是在出离自身的位置上离奇地获得了主人性,这一错误也导致了安吉尔真正主体的永恒失落。拉康认为,异化恰恰就是“存在的缺失”[2]39主体的异化并非是自身的异化,实际上,自身在自我的确认中缺席了。安吉尔渴望成为的伟大魔术师实际上并非他自身所愿,他自身在追逐理想自我的道路上是不在场的,波顿的形象正像一个诱饵,在安吉尔自我建构的舞台上表演了一出致命魔术,使他以虚假的镜像为中心,以回归他者的形式步向了背离自我的道路,而安吉尔与其说是受到蒙蔽,不如说是由于不愿承认破碎的真相以及自身的缺席,从而心甘情愿走进了假象所制造的骗局,由此,异化构成了主体,他者取代自身而占有了自我的席位。
而那个成为安吉尔理想之影的波顿,自身也陷入到了镜像的困局。波顿在参透鱼缸魔术的秘密之后,他领悟到了魔术的终极奥义是“牺牲”。于是,他牺牲了自己的人生。为了保证换影移形魔术的秘密永远不被知晓,波顿制造了一个惊天骗局。法隆与波顿本是一对孪生兄弟,二人都醉心魔术,因此甘愿为魔术牺牲自己一半的人生,他们轮流扮演道具师“法隆”与魔术师“波顿”,交替接受台下观众的喝彩与掌声。甚至两人的生活也交织为一体,他们同时扮演着波顿家庭中的丈夫和父亲的形象,于是波顿的妻子在丈夫的忽冷忽热中逐渐疯狂,最终走向了自我毁灭。波顿与法隆以极其典型的形式向我们展现了镜像的事实,兄弟二人互相以对方为镜像中的自己,“波顿”这个魔术师的形象实际上是二人在镜中发现的那个拥有整合性的理想自我。兄弟二人都被这一形象所占据,可以说,镜像是毫不费力地侵凌到主体内部的,因为主体无法承认自身被他者抢占,他一旦承认这个残酷的事实,承认自己只是他者的幻象,那么就会把自己暴露在无的陌路之上。于是,在对镜像顽固与偏执的忠诚里,兄弟二人甘愿步入离奇的生活之中。
不仅如此,在主体看似欣喜的自我构建里,实则暗藏着无法规避的危险性。由于受到整合状态的镜像的诱惑,自身在一种毫无知觉的情况下将主体的地位让位于掠夺者,并且终身背负着掠夺者给自己的命运刻下的印记,虽然自身对此无能为力,但是被侵害的愤怒却会一直延续下去。在电影中,安吉尔虽然将波顿视为理想自我,但他也一直试图破坏波顿的事业,甚至最后将波顿陷害入狱,把他送上了绞刑架。实际上,这正是安吉尔被波顿这个掠夺者夺走了自己想象中的理想形象的幻象而愤怒的表现。波顿是一个可见的外部的掠夺者,于是安吉尔将自我内部斗争延伸出来,对波顿展露出攻击性,主动挑起了一场你死我活的较量。镜中之像在用迷人的假面把安吉尔装扮起来的同时,给予了他完整而永恒的形象,他被这个完整和谐的形象所迷惑,欣然接受了在他者形象中体验自己的宿命。然而这个看似和谐的图式中也暗藏着矛盾,安吉尔所认同的理想自我的形象终究是一个他者的形象。由于认同机制,他受困于这个他者的形象,受他支配,任他摆布。安吉尔从波顿这一幻象中消解了自身破碎性的恐惧,但一种新的危险正对他虎视眈眈,他不得不眼睁睁看着自己的主体地位拱手于他人。被剥夺了自身主人权利的安吉尔是如此愤怒,于是他将所有攻击的矛头都指向了波顿,这个曾经给予了他理想化统一形象的魔术师,此时已经成为剥夺他主人地位的掠夺者。而这种斗争的终结是以撕裂自我作为句点的。影片的结尾处,波顿兄弟中的一人被绞死,终结了二人奇妙的共生,而活下来的“波顿”又枪杀了安吉尔,这是一首他者最终获得胜利,占据了主体地位的凯歌,“波顿”与安吉尔通过具像化的方式,向我们展示了镜像阶段的残酷事实,这种自我的内部纷争被扩展到外部,演绎了一出厄洛斯与塔纳托斯的跷跷板游戏。
2 能指:存在与意义的乖离
我们看似是在自主地使用语言,但实际上却是被语言所操控,被符号吞噬,成为被他者言说的存在。由于语言先于主体而存在,主体为了加入与他人的契约关系,不得不让自身被符号化。在镜子阶段,主体被他者侵凌,成为了缺失的存在。为了摆脱无的烙印,能指成为主体寻求意义的场域。在影片中,魔术师在首次登台表演之前都要为自己取一个艺名,安吉尔使用了亡妻给他取的名字,即“伟大的丹顿”,在获得这个名字之后,安吉尔完成了从学徒到魔术师的转变。这种转变不仅仅是安吉尔外在身份的转变,同时也是他精神世界的变革,是他自我认知的一次更新,而促成他内在转变的动力正是来自能指。安吉尔渴望成为真正伟大的魔术师,试图在“伟大的丹顿”这一名讳中确认其自身,摆脱虚无的本质,但拉康认为,能指本身也是虚无的东西,它无法作为呈现意义的符号而存在,反而是对主体本原性缺失的一次误答。能指把主体的身份指认抛向未来,在可能性上给予主体一次建立意义的期待,“伟大的丹顿”并不能赋予安吉尔一个指向当下、指向本质的存在之证明,在这一能指的代理下,安吉尔自身并未被赋予任何形式的实际内容,二者仅仅凭借某种契约关系而联系,并非是具有同一性的东西。安吉尔将自身的空无暴露在符号之下,试图用能指覆盖被他者消除的自身,但实际上却一直占据了能指发挥其效果之位置,主体仍然未能也永远不会成为其自身,反而借助能指再次消除了自我的痕迹,将自己引渡到了远离自身之场所。
与笛卡尔所云的“我思故我在”不同,拉康认为“我于我不在之处思”。“思在”是主体确认自身的过程,按照拉康主体消灭的公式的结果,主体成为了被能指所代理的事物,在自身被消灭后,被一分为二的切割开来,其一是由于能指出现而被打开意义缺口的空无之物,其二则是被能指符号化的表象之物,这样一来,主体成为了“无”的存在,成为了被他者入侵并消除之存在。其意义恰巧位于远离存在之地,主体自身之存在被排斥在意义之外,换言之,主体的存在由于被他者抢夺而被动消解了自身的意义。正如变成普通带子的莫比乌斯环,存在与意义被拉康还原为无法共存的两个平面。在《致命魔术》中,安吉尔把实体赋予了并不存在的自己,即“伟大的丹顿”,沉醉于自己舞台上精彩绝伦的表演,在观众的凝视与喝彩中感到愉悦和满足。而在波顿的设计下,安吉尔的替身被发现,魔术表演失败,其演艺生涯跌至低谷时,这种能指所填补的意义缺口在此被打开,安吉尔又一次不得不面对自身空洞的存在。实际上,安吉尔作为一个魔术师,他在观众面前必须总是作为一个被消除的符号,而绝对不能使自己的存在暴露出来。安吉尔魔术表演的秘密,即自己的酒鬼替身必须被永远隐藏起来,才能完成表演,赢得观众的喝彩。而当舞台上出现了自己的替身,安吉尔的戏法被识破,不能呈现于世的东西裸露出来,“伟大的丹顿”指向未来维度的期待也就此被消解,安吉尔作为该符号来行动的自己被迫消失,其自身真正的存在被迫显现出来。由于这一经历是以失去意义为代价的,安吉尔不得不又一次面对裸露的自己,他试图遮掩,但进退维谷,于是,在主动放弃自己存在的过程中,安吉尔背负起了追寻他人之宿命。他盗取了波顿的日记,来到了特拉斯的实验基地,希望再次取回作为魔术师的意义。
主体通过被能指言说,到达意义世界,将其存在的空洞表面覆盖上意义,也就是说,主体的存在与意义必须永远不能同时呈现,主体所追逐的意义是以遮蔽自身存在为代价的。当主体开始思考自己的存在时,其存在就会被意义置换。于是,拉康将“我”分裂为“我思”之我与“我在”之我。“前者是在未来的可能性中给予没有之物的我,而后者则是执着于现在此地的‘有’的我。”[3]141影片中,安吉尔和他的替身们将这两个我具像化地展示出来。安吉尔借助特斯拉的机器,在一百场表演中不断制造替身,而这些替身又通过将本体杀死来完成魔术。在每场表演中,都存在两个安吉尔,一个是将要被杀死的本体,一个是完成魔术的替身,前者作为“我在”之我,其存在是在聚光灯下被彰显出来的,是被观众的目光定格在正在进行着的表演中的“有”之我。因此,为了达到魔术表演的“化腐朽为神奇”,将主体推向意义世界,“我在”之我必须被“我思”之我,即替身所取代,也就是将“有”的存在消去,让主体自身存在的空洞再次打开,在此基础上才能将自身被消除而残留下的痕迹交给未来,通过指向可能性的维度,从而暂时平息主体对于存在与意义的无休止的执着。
3 欲望:主体的永恒失落
在主体思考自身缺失了何种东西的过程中,存在与意义背道而驰。主体为了填补被消去的存在,必须寻找某种替代物,而这其中的必然性就是以欲望作为推力的。也就是说,当主体失去自身最初的存在之时,欲望也就随之诞生了,来自未来的虚无之物的召唤催生了欲望。主体渴望取回缺失之物,但缺失之物是永恒失落的,是不可复制之物。要想达成欲望,主体只能将没有之物通过符号化的方式刻进未来,欲望就在一个又一个对象的转接中徒劳地运作,获得一种间歇性的接近满足的状态。安吉尔的欲望发端于妻子的离世,妻子虽然是一个外部的他者,但她也是安吉尔经过外部世界认同所产生的自身的一部分。在妻子为安吉尔取名为“伟大的丹顿”那一刻起,妻子的形象与艺名这一能指紧密相连,被书写进安吉尔的内心世界。于是,当妻子意外溺死之后,安吉尔感到的悲痛是从内在生发出来的,外部的逝者对应的是安吉尔自身丧失的某一最亲密部分,而这种丧失同时也是“伟大的丹顿”这一意义开始彰显的先兆。事实上,安吉尔的妻子是一个必然要消亡的存在,在她与艺名符号关联的那一刻起也就注定了二者的不可共存,只有当妻子的存在成为空无之时,“伟大的丹顿”才能作为意义来填补安吉尔自身的空洞。因此,妻子的离世成为安吉尔自身最初的缺失,而之后安吉尔为了填补这一缺失,不得不持续替换欲望的对象,从迷人的女助手到波顿的魔术戏法再到特斯拉打造的魔术柜,安吉尔试图在这些一个接一个的对象中满足自身的欲望,然而却永远无法达到目的。
拉康所言的欲望与需求有着本质的区别。生物性的需求可以通过获取某一对象而得到满足,而欲望却永远无法得到满足。其原因就在于欲望的对象并不是现实中的某一具体事物,而是对他者和他者之欲望的欲望。首先,由于主体不具备言说自己的能指,因此主体作为一个缺失者只能混淆自我与他者,通过他者的欲望来寻找自身欲望的对象。但是当主体从他者之欲望中获悉了自身欲望时,主体又渴望自身的欲望得到承认,渴望被他者所欲望。[3]154-162波顿与安吉尔的斗争也凸显了这一欲望辩证法的本质。二人互相在对方的欲望中被告知了自身的欲望,而在点燃了自身的欲望之火后,二人又期盼能被对方承认,成为被对方嫉妒的魔术师。于是,他们之间以互相成为欲望对象为目的的战火愈演愈烈。然而二者无论如何都无法向对方让步,因为这场斗争的前提是二人以对方为欲望对象,因此,一旦得到了欲望对象的回眸与承认,那么欲望对象将沦为败者,而作为获得承认的胜者所得到的是没有价值的胜利,因为自己所渴望的对象此时已经不再具有被欲望的价值。换言之,主体在自身被承认的那一刻也同样遭到了否认。这是二人无论如何都不愿看到的,因为只有对手仍然保持着不可战胜的姿态,主体才能在渴望被欲望中充满力量地生存下去。因此,这场战争最终走上了以消灭对方为终点的悬崖,安吉尔的死亡为这场永远不能结束的斗争画上终止符。其次,他者和他者之欲望的真实对象永远处于缺失的位置,这也就注定了主体欲望的快车只能驶向空无的目的地。然而欲望之所以成为欲望也恰恰是因为欲望对象的永恒缺席,主体通过不断地追寻,试图接近欲望的客体,但这种努力终究是徒劳的。受到驱力的指挥,主体陷入了西西弗斯的悲剧命运之中,在永远无法得到满足的循环中重复运动[4]7-8。因此,安吉尔不断寻找的替代物永远无法真正使自身得到满足,因为欲望是在“无”的平面上的,欲望永远是与缺失相联系的。因为欲望的对象是空无之物,是永远无法企及之物,所以欲望指向的并非目的,而是过程本身。安吉尔和波顿对于魔术终极奥秘的追逐如同阿喀琉斯对乌龟的追逐,主体不断靠近客体,但客体永远都可望而不可即,二人为了魔术费尽心力,甚至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但始终无法达到自己所追求的魔术境界。实际上,完美的魔术根本不存在,“最伟大的魔术师”这一能指本身就不具有确定意义,它是在能指的维度上相对于其他“魔术师”而存在,而能指并不指涉主体自身,只能是主体自身被消除的痕迹之代理,因此一旦失去了其他能指作为参照,其本身也就丧失了意义。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二人之间的纠缠并不指向结果,而是指向斗争行为本身。换言之,正是二人的交锋为欲望的延续提供了一个具体场域,使得主体的追逐行为获得一个外在的合理之证词。而追逐之物本身则是镜中月,是影子之影子,永远无法企及。但这种不可即性又恰恰是催生欲望的动力,二人在欲望中欲望,在不断求索的过程中体验快感的同时也走向灭亡。
4 结 语
《致命魔术》就如同拉康精神分析的现实图解,通过安吉尔和波顿的魔术斗争,具像化地向人们揭示了主体确认自身的艰难过程。主体通过镜像来确认自身,却被他者侵凌奴役,开始走向他者取代自我的宿命,而在能指的代理下,人之虚无本质也愈发明晰,主体的存在与意义成为了无法共存的两个平面。在欲望的话语机制下,安吉尔和波顿的缠斗从外部世界进入了主体内部,而主体之欲望永远无法得到满足,只能在不断追逐中走向灭亡。在这个意义上,《致命魔术》超越了诺兰其它影片,具有了更加深层次的内涵,因为它不仅揭示了欲望的不可满足性,同时也展示了主体之必然消亡的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