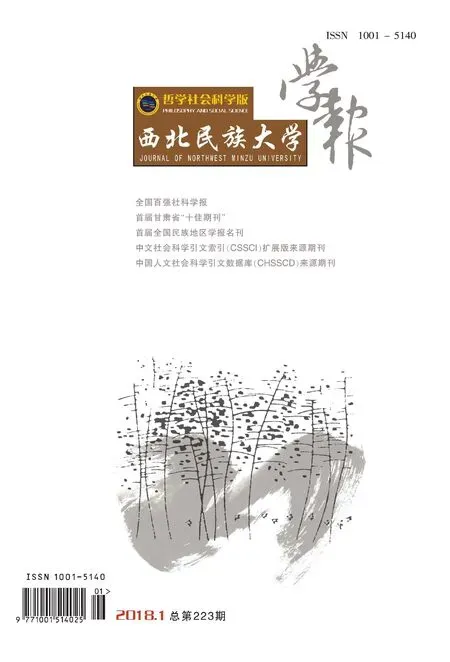类主体视阈下少数民族国家认同的历史维度
王德民,徐黎丽
(1.安徽师范大学 历史与社会学院,安徽 芜湖 241000;2.兰州大学 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甘肃 兰州 730020)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有深刻的复杂性,难以获得根本性同一。当前“台独”“藏独”“疆独”等各种民族分裂势力猖獗,这其中固然有盘根错节的诱因,但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矛盾对立也是显而易见的。本文基于类主体理论,企划与构建少数民族国家认同的历史维度。
一、类主体视阈下的认同与国家认同
人类作为整体是一种“类存在物”。“类”是对同类事物的抽象概括,与其说它是一种实体,不如说它是一种关系。人类的存在依赖于自身的实践活动。“通过实践创造对象世界,改造无机界,人证明自己是有意识的类存在物,就是说是这样一种存在物,它把类看作自己的本质,或者说把自身看作类存在物。”[1]人类通过实践,其主体性不断得以演进与发展。
(一)人的主体性演进:从主体到类主体
文明伊始,人类混沌未开,主客不分,没有主体意识。古希腊文明确立了主客相分的主体意识,但这种主体意识只是对象化的。尽管对象化的“主体—客体”思维模式催生了科学思维理性,但也带来了工具理性。以主体性的立场去考量主体与客体、精神与自然、形式与内容,不可避免形成了理性的独断。“主体—客体”思维方式最终不利于对主体自身的把握与彰显。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肇始了人的主体性觉醒。“‘我’成了别具一格的主体,其他的物都根据‘我’这个主体才作为其本身而得到规定。”[2]存在者之存在是从作为设定之确定性的‘我在’那里得到规定的,“自我”成为建构全部存在的第一根据。因循主体性的“自我”意识,借助启蒙运动成长起来的德国古典哲学更深刻地探讨了“形而上学、认识论、逻辑、意识、自我、主体与客体的同一、自然与精神的一致性等多种问题”[3]。康德论证了作为现代性基本原则的理性与自由,将时空的先验感性、范畴论的先验知性、辩证论的先验理性,都归结为“自我”和“自我意识”的展现。黑格尔的绝对理念或具体概念亦是“自我意识”客观化和绝对化的辩证运动的整体过程。
然而,随着“自我意识”成为保证其他一切存在者存在的最终依据,“自我”就转变成了实体化的主体。主体作为“实体”拥有削平一切异质性和差异性的绝对权威,构成了人的知识、人与世界及人与人关系至高无上的尺度与标准,“自我”也就成了“唯我”。“唯我”意味着人的主体性的过度膨胀,由此也带来了主体性困境,体现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就是人类借助科技进步与社会生产力提升,越来越呈现出对自然的“占有”与“征服”,“人类奴役自然,为了满足自身的需要来改造自然,结果是自然界越来越多地遭到破坏”[4];体现在人与人的关系上就是“唯我”造就了排斥他人利益的个人,这种单子式的个人将他人作为满足自己私利手段的客体,人与人之间难以做到有效的平等交流与理解。
如何超越“实体化”的主体,根源仍在于对主体性“自我”的透视与理解。胡塞尔提出了经过“先验还原”的“先验主体”,但他同时指出作为“先验主体”的主体意识不是孤立的,是主体与他人主体交往形成的。“我就是在我自身内,在我的先验还原了的纯粹意识生活中,与其他人一道,在可以说不是我个人综合构成的,而是对我来说陌生的、交互主体经验的意义上来经验这个世界的。”[5]海德格尔深刻地指出,笛卡尔虽然提出了“我思故我在”,但“我在”的本真意义仍然在他的视野之外,“他在这个‘基本的’开端处没有规定清楚的正是这个思执的存在方式,说得更准确些,就是‘我在’存在的意义”[6]28。对应“我在”的本真意义,海德格尔提出了“此在”,揭示了“此在”的生存方式是“在世界之中存在”。“此在”是面向未来展开的,是一种可能性存在,作为主体性的“自我”是与世界相互渗透的。“人并不是从他的孤独自我透过窗户去看外部世界,他本已站在户外。他就在这世界之中,因为他既生存着,他就整个地卷入其中了。”[7]由此,人与世界“一向总已经”处于内在的统一和融合之中。
胡塞尔的交互主体性消解了主体性“自我”的封闭性,开启了自我与他人之间认识论上的联系。海德格尔的“此在”更内在地揭示了我与他人之间的共同存在,“此在的世界是共同世界。‘在之中’就是与他人共同存在。他人的在世界之内的自在存在就是共同存在。”[6]137“此在”的存在论意义使个人不再与他人分离,超越了个人的主体性,生成了主体间性,使个人由单子式的主体走向了类主体。
(二)类主体与国家认同
类主体是类本位状态下的主体,它既具有丰富的个体独立性,又蕴含着不同个体的统一性、聚合性与凝聚性。类主体体现着存在哲学的生存论视角,一个具有主体意识的自我,并不是纯粹个人的事情,因为“这种存在的主体性从一产生就已经是一个主体际性”[8]。类主体所具有的“主体际性”既不是群体本位中超越个体之上、存在于个体之外的那种实体性“大我”,也不是个体本位中彼此分离的单子式“小我”,而是“大我”的整体性与“小我”的个体性的有机统一。换句话说,类主体已将个人存在纳入他人本质,他人的存在也纳入了自己的本质,类主体是一切丰富性个体的整体性统一。
类主体揭示了人与人之间的共在性,超越了主体与客体关系的模式,升华了个体生命之间的主体与主体关系。类主体是主体性在人与人之间关系上的本质性表现。人在“主——客”关系中表现出来的主体性是单子式的,是异化的主体性,而类主体使个体成为真正的主体,也使主体性避免走向三个极端,即“以自我为中心的占有性个体主义;以统治自然为目标的人类中心说;不包含交互主体性的单独主体性”[9]。类主体消解了主体在客体面前的霸权,消除了主体对客体的统治与支配,使个体成为具有丰富个性的自由人,又在人与人之间生成一种自由联合的类共同体。
从一定意义上讲,认同是一种主体性体现,是主体如何确定自己在时空的存在。“个人的自我认同是多重性的,在个人与社会互动的过程中生成。”[10]国家认同亦可视为主体与国家的关系。有学者认为,国家认同是“一个人确认自己属于哪个国家,以及这个国家究竟是怎样一个国家的心灵性活动”[11],可以视为一种主体性心理。还有诸如“国家认同是指公民对国家的政治权力和权威的认同”[12];是“一个国家的公民对自己祖国的历史文化传统、道德价值观、理想信念、国家主权等的认同”[13]。这些都是主体将国家对象化了,国家成为个体主体认同的客体。另有一种重要观点认为,国家认同“不仅是一种国家意识或国家观念问题,而且是国家建设本身的问题”[14],因为国家认同是人们对其存在其中的国家的认可和服从,“人是国家的主体,建设国家;国家最大限度地满足人生存与发展的基本需求”[14]。此种观点揭示了主体与国家的生成关系,看到了国家内在孕育的主体性力量。
从类主体视角看,国家认同被视为类本位中主体与国家的生成关系,国家是群体意义上的类主体。“每一个自我——主体和我们所有的人都相互一起生活在一个共同的世界上,这个世界是我们的世界,它对我们的意识来说是有效存在的,并且是通过这种‘共同生活’而明确地给定着。”[15]类本位中主体与国家的生成关系是每个自我即主体所共有的世界,国家认同是以交互主体的存在为前提的,国家转化成为反映主体间或主体际关系的共同主体。“个体之主体性只有在共体主体性里才成为现实的东西;共体主体性也只有在众多的个体主体性发挥中才成为现实的东西。”[16]国家认同所构成的生成关系中,作为共同主体的国家需要提供基本的权利和自由,以使与之共存的个体主体性得到充分保障与发展;另一方面,存在其中的个体也需要意识到自己的类主体身份,能够相互尊重、相互协调。国家作为由个体主体组成的共同体,与各个体主体一道共同塑造不断生成中的国家认同。如此的国家认同既存在几乎可以视为无限的可能性,而其中的许多也已经或正在转化为现实性。
二、少数民族国家认同的类主体身份构建
倘若将多民族的中国视为群体意义上的类主体,少数民族无疑成为存于其中、具有类本位性质的个体主体。从历时性维度看,多民族中国的发展历程实质上就是中华民族的形成过程。尽管“中华民族”作为自觉的民族实体是近代以来出现的,但“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几千年的历史过程所形成的”[17]。从类主体视角看,作为生存主体,中华民族从“自在”到“自觉”的转变是漫长历史过程累进的结果,是一种“能在”。“能在就是如其实际上存在着的那样存在的此在向来为其故而存在的东西。”[6]223中华民族作为“能在”,既揭示了其自身“向来为其故而存在”的实际形成历程,也昭示了少数民族国家认同所孕育的无限可能性及其转化的现实性。
古代中国肇始于尧舜禹时代的“部族国家”,后经夏商周时期“华夏民族国家”的演变,再发展为秦汉以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18]。在此历史阶段,民族关系处于“天下观念”与“大一统”思想的笼罩中。“天下观念”是一种复杂的价值系统,“天下”与“四海”“九洲”相列,与“国家”高度重合。不仅如此,“天下观念”寄寓了“天意”,是远超乎国家观念的政治、文化理念。“大一统”思想是天下观念的进一步发展,承载了“九洲攸同”“万国为治”的政治愿景。古代中国的民族关系以“华夷之辨”“用夏变夷”为特征,深潜于其中的国家认同被遮蔽了,以“华夏”为标志,少数民族的类主体性潜质获得朦胧发展。在与汉民族的互动过程中,有些少数民族被“汉化”了,另有一些少数民族则反客为主,以争“中国”、争“正统”的表现形式建立了强大的王朝政权,如以契丹族为主的辽朝、以蒙古族为主的元朝及以满族为主的清朝[19]。这不仅使少数民族形成了“中华民族”的类主体潜质,也促进了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
近代中国是民族国家确立的时期,也是中华民族由“自在”向“自觉”转变的重要阶段。列强入侵,国内各族民众陷于内忧外患境遇,亡国灭种的危机意识促进了民族觉醒,“振兴中华”“中华一体”逐渐转化为少数民族的类主体意识。新中国成立后,在宪法上规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各民族共同缔造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确立了少数民族的类主体地位,“民族区域自治”进一步提升了少数民族的主体性。
综上可以看到,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与中华民族的发展内在同一,且与少数民族的类主体身份高度相关。近年来民族问题的产生,除了国外分裂势力干涉、地方民族主义高涨等外部因素,根本原因仍在于少数民族成为中华民族类主体身份的弱化与缺失。经济发展、增强公民权利等措施可以提升少数民族的主体性,但也应同时兼顾族际间的协调,注重强化少数民族的类主体意识,关注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否则,少数民族主体性的过分膨胀反过来亦会产生民族分离倾向。
三、少数民族类主体身份与中华民族认同的历史维度
中华民族作为生存主体,其形成、发展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少数民族作为中华民族的一员,拥有中华民族的类主体身份,其对中华民族的历史性认同也是多维度的。
(一)中华民族认同的历史时空维度
历史时空维度涉及历史时间与空间。少数民族既有自己的成长史,亦有融入中华民族的发展史,这种历史过程以历史时空为前提条件,是一种“曾在”。“曾在”不是纯粹消逝、过去了的东西,而是“还存在并活动着,但却是以其本己的方式活动着”[20]。少数民族与中华民族共同关系的整体性,是在历史时空中展开的主体生命和经历关系的整体,既有少数民族自身的族群记忆,亦有融于中华民族、与其他民族互动的历史记忆。“时空就是属人的、社会的时空,只是在不同的讨论语境中表现出不同的社会规定性。时空具有测度性(测度时空)和价值性(价值时空)的双重规定性。”[21]有意义事件组成的时序表征具有空间特性,有意义事件构成的历史认识是通过主体内在的时空观念确认加以紧密联系的。胡塞尔认为,“不能根据‘客观时间’——即根据实在事物在空间中的运动——去把握时间,而应根据时间对象在意识之中的显现,根据主体自身的体验去把握时间,即所谓的‘内在时间’才是原初的时间观念”[22]。以“疆域”观念为例,少数民族对中华民族的认同,一方面带有自身族群的地域观念,另一方面又蕴含中华民族核心地域的历史时空变迁。“中国的中心区域是很清楚的,那是融汇了各种胡汉血脉的‘中国’。”[23]作为个体主体,对族群地域的认知会产生诸如“故乡”“故土”的依恋。作为类本位中的主体,对中华民族核心地域历史时空的感知,会赋予其国家人文情怀,因为核心地域的历史时空变迁,恰恰与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先辈人物有种种关联,也恰恰是在历史变迁的种种关联中产生了诸如民族习俗、社会传统、生活方式等,由此构成国家认同的情感基础。
(二)中华民族认同的历史理解维度
在生存论意义上理解就是人类生命本身原始的存在特质。“习俗、传统与相应的自身未来可能性的具体联系是在理解本身中得以实现的。”[24]少数民族的类主体身份与中华民族是统一体,或一种关系,在这种关系中同时存在少数民族对中华民族认同的历史理解。历史理解主要聚焦于中华民族特质及个体民族之间的多元交流、对视与沟通,构建多民族共存的历史时空场域,铸造国家层面的民族融合与理解。中华民族的长期发展形成了超越少数民族个体的共享“场景”与文化传统。“民族的认同和共同体是由‘此处的感觉’和‘主格我们的感觉’构成的,前者源自在一个地方的共同居住,后者来自群体的团结和共有属性。”[25]中华民族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各民族相互吸纳、交往与融合,历史理解塑造了各个体民族的交互主体性,强化了少数民族与中华民族内生性的整体融合,并塑造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共享记忆与文化。
(三)中华民族认同的历史评价维度
在过去、现在、将来的时间序列中,生存论把将来置于首位。“将来使此在的存在成为可能。所以,生存性的本来意义就是将来。”[26]114将来伸达并供呈曾在,重演是曾在的本真样式。“重演自然包含着对曾在此的本真生存的敬畏,但这同时又是对自由生存所具有的唯一权威的敬畏,对生存可重演的诸种可能性的敬畏。”[26]146少数民族融入中华民族的重演,既有中华民族发展的整体立场,更有少数民族的生存立场,这其中就有了相关的生存意义与评价。少数民族对中华民族认同的历史评价维度,既要着眼于长时段的中华民族整体发展,也要考虑特定历史境遇的少数民族生存发展。就此而论,少数民族融入中华民族的历史进程,少数民族与汉族、各少数民族之间不是抑制、同化、占有的关系,而是交流、互融、共存的关系。少数民族的生存是一种积极主动、没有异化的存在。“在没有异化的主动中,我体验到自己是自己活动的主体。……我的活动是我的力量和能力的表现,我、我的活动和我的活动结果合为一体。”[4]78由此,少数民族融入中华民族的历史活动,既有体现中华民族的类主体性,也有体现少数民族自身的生存主体性,两者统一于少数民族对中华民族认同的历史建构。比如,宋辽金元是少数民族主体性活动交融的凸显时期,这一时期契丹族建立的辽、党项族建立的夏、女真族建立的金、蒙古族建立的元,都体现了自身民族的主体性活力,也都对中华民族的整体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各民族政权又在推动边疆地带发展、活跃亚欧经济文化交流等方面起到了中原王朝难以取代的积极作用。”[27]少数民族不仅凭借迁徙、贸易等活动强化了民族交融,还以对峙、战争等形式塑造了自身生存的主体性,更深层地促进了中华民族的内在融合,生成少数民族的类主体性。所有这些都内显“澄明”于少数民族对中华民族认同的历史评价之中。
[1]中央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237.
[2]海德格尔.海德格尔选集(下卷)[M].上海:三联书店,1996:882.
[3]叶秀山,王树人.西方哲学史(第六卷)[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6.
[4]弗洛姆.占有还是存在[M].李穆,译.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5.
[5]胡塞尔.胡塞尔选集(下卷)[M].上海:三联书店,1997:878.
[6]德格尔.存在与时间[M].陈嘉映,王节庆,译.上海:三联书店,2006.
[7]威廉·巴雷特.非理性的人——存在主义哲学研究[M].段德智,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230.
[8]大卫.M.列文.倾听着的自我[M].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7:134.
[9]郭湛.主体性哲学——人的存在及其意义[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239.
[10]乔治·H·米德.心灵、自我与社会[M].赵月瑟,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136.
[11]江宜桦.自由主义、民族主义与国家认同[M].台北:扬智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12.
[12]陈茂荣.论“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J].学术界,2011(4).
[13]贺金瑞,燕继荣.论从民族认同到国家认同[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3).
[14]林尚立.现代国家认同建构的政治逻辑[J].中国社会科学,2013(8).
[15]弗莱德.R.多尔迈.主体性的黄昏[M].万俊人,朱国钧,吴海针,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63.
[16]杨金海.人的存在论[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5:248.
[17]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2:3.
[18]王震中.国家认同与中华民族的凝聚[J].红旗文稿,2016(1).
[19]瞿林东.历史文化认同与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第一卷)[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13:6.
[20]海德格尔.面向思的事情[M].陈小文,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15.
[21]王林平,高云涌.时空二元论的理论困难及其解决出路——对国内有关马克思社会时空观研究的前提批判[J].哲学研究,2013(8).
[22]塞尔.内在时间意识现象学[M].杨富斌,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13.
[23]葛兆光.殊方未远:古代中国的疆域、民族与认同[M].北京:中华书局,2016:24.
[24]伽达默尔.诠释学Ⅰ:真理与方法[M].洪汉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376.
[25]拉彼德,克拉托赫维尔.文化和认同:国际关系回归理论[M].金烨,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181.
[26]陈嘉映.海德格尔哲学概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
[27]邓小南,李华瑞.一个“生于忧患,长于忧患”的朝代[N].光明日报,2017-01-0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