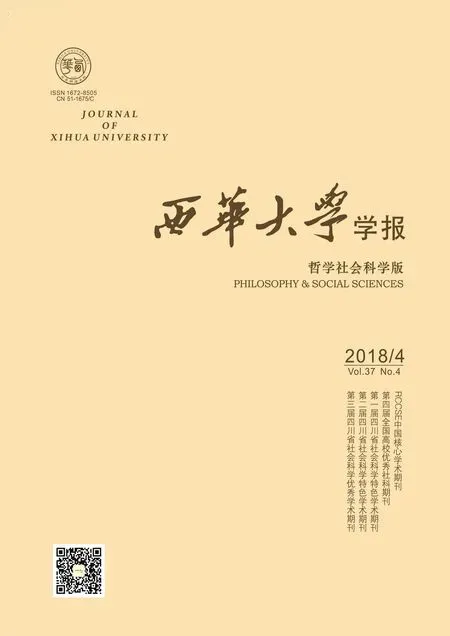古代都江堰岁修制度
——从《秦蜀守李冰湔堋堰官碑》说起
彭邦本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四川成都 610044)
世界上很多古老的文明都曾有过著名的大型水利工程,但很多工程已在历史的长河中陆续湮没消失了,而矗立于世界东方、中华大地的大型综合水利工程都江堰,却跨越了2000多年的漫长曲折历程,其不仅是人类公认的伟大文明遗产,而且至今仍充满蓬勃的生命力。都江堰从古至今始终保持青春活力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其拥有一整套一以贯之、日臻完善、博大精深、充满科学与人文精神的岁修制度。下面谨结合传世文献的丰富记载和近年来出土的古代碑刻等文物考古资料,对之进行一些初步的探讨。
一、考古资料反映的早期岁修
都江堰的岁修形成于何时?由于都江堰历史悠久,早期传世文献缺略,这一问题至今未得解决。笔者认为,对岁修制度的起源和形成,比较合理的解释应是,在建堰之初即已经起源,至迟在汉代即基本形成。首先,都江堰的工程模式和技术手段,决定了它每年洪水过后,堰体都会受到一定损坏,河道必然发生推移质砂石的淤塞,因而必须定期每岁修治;其次,修治的时间只能在冬春之际;第三,秦以耕战立国,汉承秦制,以秦汉政府对都江堰的高度重视,即便在平常的情况下,也决不能让都江堰陷于瘫痪,因而必然在秦汉之际就形成了初步的岁修制度。以上所论,固然合于逻辑,亦非毫无根据,但终究缺乏坚证,仍属推论。所幸近年来都江堰渠首外江河床陆续有重要考古发现,尤其是出土的石刻铭文,为我们探索这一问题提供了新的可能。
众所周知,“深淘滩,低作堰”,是古代都江堰岁修制度流传至今的六字金诀。据明代蜀中著名学者杨升庵的《金石古文》中著录的《秦蜀守李冰湔堋堰官碑》,其六字诀文字作“深淘墠,浅包鄢”,并谓“其文字又简古如此,真异人哉”。王文才先生《校勘记》指出,李冰湔堋堰官碑“历代无著录,此碑乃明正德时得于湔堋堰水中,传为秦刻,恐未必然,疑亦唐时之物。杨慎始录其文,李调元《蜀碑记补》转载之”[1]47。按六字诀《水经注·江水》轶文作“深淘潬,浅包鄢”,其字与碑文均甚简朴,颇具古风,应不晚于汉代。
下面谨结合近年出土的东汉建安四年《郭择赵汜碑》等资料的记载,进一步分析讨论。《郭择赵汜碑》云:
(建安)三年□□□间,择、汜受任监作北江堋,堋在百京之首。冬寒凉慄,□刃□□□,不克□□。时陈溜高君下车,闵伤犁庶,民以谷食为本,以堋当作,□□□兴□公,掾史都水郭荀任臿,杜期履历平司;择、汜以身帅下,志□□□,□□作堋。旬日之顷,堋鄢竟就备毕。[2]9-10
从碑铭叙事顺序推测,郭择、赵汜受任监作北江堋之时,应在蜀郡太守陈溜高君“下车”亦即上任之前。碑铭云“冬寒凉慄,□刃□□□,不克□□”,虽有数字之迹漫漶不清,然通览上下文,其寒风如刀刃刺骨,因而不能顺利施工之大意还是清楚的。“高君下车”履新之后,鉴于天气严寒,工程艰难,且“闵伤犁庶,民以谷食为本,以堋当作”,因而增派掾史都水郭荀、杜期加强对此次冬季修治北江堋的领导工作。接下来由于“掾史都水郭荀任臿,杜期履历平司;择、汜以身帅下,志□□□,□□作堋”,可谓上下齐心,众志成城,因而“旬日之顷,堋鄢竟就备毕”。从碑铭全文可知,建安三年和四年冬春之际的此次都江堰修治,并无水灾背景的记载,可知是为一次正常的岁末修治,而且是在新的郡守上任之前即已经开始,足见应属按程序依例开展的工作,证明其时岁修确已经成为制度或惯例。
都江堰渠首工程地处岷江出山口甫入平原之地,江水由深山峡谷中的激流立转为平原上的缓流,每岁均有大量砂石沉积,尤其是卵石等大粒径推移质在渠首鱼嘴一带大量堆积,容易很快造成渠首工程的淤塞①。这样的大型无坝引水工程必须以岁修为制,按时清淤淘河,方能持续运转,因此,冬季岁修之制必然在工程建成之时即已初步形成。秦人素有冬季由政府主导进行水利修整的制度,青川县郝家坪秦墓出土的秦《为田律》关于冬季“十月为桥,修波(陂)隄,利津梁”的明确规定,十分清楚地反映了这一史实。由此可见,都江堰工程的岁修制度,应在建堰之后不久即已经初步形成,并为汉代所继承和完善。
都江堰岁修制度,指的是每年冬春之际枯水时节对都江堰工程进行系统维护、修治和必要的更新,由此形成的全社会官民同遵共守的传统制度,包括在每岁进行维修的基础上,复有每隔数年的大修,或针对具体情况进行的特修。
中国古代地方上的重要水利工程的兴建维修,历来有由政府主持进行的传统。《郭择赵汜碑》铭文就揭示,汉代对都江堰水利工程的维修,政府依制要直接领导管理,对口的政府职能机构的官员即郡县的都水掾和都水长。这与秦汉传世文献中地方上水利政务的主管职能机构是都水的记载吻合,形成较为充分的印证。不仅如此,《汉沈子琚碑》铭文亦反映,蜀地其他重要的水利工程的修治,同样要由都水掾、水曹史等负责水政的官员领导②。值得注意的是,1974年3月都江堰渠首外江河床出土的东汉李冰石像铭文云:“建宁元年(168)闰月戊申朔廿日都水掾尹龙、长陈壹,造三神石人。”反映了都水官员对都江堰的管理,不仅包括工程技术层面的水利事务本身,而且包括每年对李冰等神圣偶像的祭祀活动,进而包括负责祭祀偶像和祠庙的监造修缮。
此外,从政府层面看,除开郡县政府水政机构都水官员的专业管理,都江堰工程的岁修尤其是大修或特修,官府往往还要另外派员监作,以加强领导管理。如从《郭择赵汜碑》可知,郭择赵汜是以“太守守史”的身份受命监修都江堰工程的③,说明至少东汉时期重要的岁修,如大修,还往往要临时加派另外的官员,以加强领导和监管。
最后,《郭择赵汜碑》铭文还反映,都江堰岁修的管理主体分为两级,一是郡县都水机构,主要发挥统筹领导的管理职责;二是地方政府下属的堋吏(或曰堰官)机构,其作为专职的日常管理者,在岁修中须要发挥具体组织为数众多的“作者”亦即役夫施工的领导作用。须要指出的是,《郭择赵汜碑》铭文中的堋吏不止一人,说明当时堰官是通过其领导下的专职机构来对都江堰进行管理的。其后诸葛亮“以征丁千二百人主护之,有堰官”[3]766,同样反映了早期堰官管理的系统化趋势。宋元以后尤其是明清时代都江堰专职管理机构的演进,莫不反映了这一性质特点。堰官或曰堋吏机构,其任务首先应为组织实施岁修,同时自然还包括古堰运转的日常维护管理。
二、科学合理的岁修准则
岁修工程需要有科学的准则程式作为施工的规制依据。史载都江堰岁修最早的水则依据,是由李冰制定的。《华阳国志》记李冰“壅江作堋”后,乃“于玉女房下白沙邮,作三石人,立三水中,与江神要:水竭不至足,盛不没肩”[4]202。白沙邮位于故白沙镇,在都江堰上游白沙河、古湔水入汇岷江交汇处。1959年岷江山口兴修紫坪铺电站,白沙镇已由白沙河口右岸移迁左岸。上引文“立三水中”,《水经注》作“作三石人立三水中”,三水应指岷江干流及湔堰所分内外二江。石人早已不存,然所谓“与江神要:水竭不至足,盛不没肩”,显系当时希望的正常水位范围。可见矗立于三条河渠中的石人,不仅起着测量水位的水则作用,而且与岁修淘挖河床深浅的准则直接相关。学者或以为石人之足与肩之间的高度,应该是当时湃缺(溢流堰)的堰高[5]100,可为一说。
唐五代以后,用于度量水位的都江堰渠首江岸水则应已形成。《宋史·河渠志》载:
离堆之趾,旧鑱石为水则,则盈一尺,至十而止。水及六则,流始足用,过则从侍郎堰、减水河泄而归于江。岁作侍郎堰,必以竹绳自北引而南,准水则第四以为高下之度。江道既分,水复湍暴,砂石填委,多成滩碛。岁暮水落,筑堤壅水上流。春正月则役工浚治,谓之穿淘。[6]2398
这是都江堰离堆古代已有水位刻划,相当于今日水文站水尺水则的最早记载,距今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考虑到都江堰已逾千年历程,岁修之制亦已久成传统,联系涪陵白鹤梁长江最枯水位石刻题记已早至唐代宗广德元年(763)二月等资料④,则以上“旧鑱”云云,说明“鑱石为水则”,应非宋代发明,确实由来已久。侍郎堰、减水河相当于今内江飞沙堰、人字堤溢洪道,北宋时规定其堰顶平水则第四划,并明确要求每岁对“砂石填委,多成滩碛”的河道“浚治”“穿淘”,充分揭示其岁修已有“深淘滩、低作堰”之旨,这同样也应是由来已久的传统准则和规制。自《史记》有《河渠书》,《汉书》有《沟洫志》以后,正史中从《宋史》始有《河渠志》得以系统记载了都江堰枢纽结构、渠系分布、灌区管理,尤其是关于岁修制度的资料,而此前则因史书体例而失载。考虑到唐五代四川社会稳定,经济文化繁荣,深淘低作之准则必已久为定制。
水则作为测量水位、岁修淘河的准则,其后一直成为传统。宋元时期的水则位置均在今三道崖附近,只是相较宋代水则共十划,元朝水则仍以尺为度,但已经增加为十一划。至明代万历时,水则下移至宝瓶口内江左岸与离堆相对的位置,水则已为二十划,一说二十四划,依然每划一尺,沿用至今。
岁修淘滩作堰严格依则进行,反映了自古以来“深淘滩、低作堰”的深刻理念,此六字被先民奉为治堰岁修的金诀。关于这六字诀,文献多有记载,且都归于李冰所创。《元史·河渠志》载,“北江稍东为斗鸡台,台有水则,又书‘深淘滩,高作堰’六字其旁”。文中“高作堰”之“高”字应为引述笔误,元代揭傒斯《大元敕赐修堰碑》(又名《蜀堰碑》)作“低”,甚是。其文云:
北江少东为虎头山,为斗鸡台,台有水则,尺为之画,凡有十一(一作“十有一”)。水及其九,其(一作“则”)民喜;过,则忧;没其则,则困。乃书“深淘滩,低作堰”六字其旁,为治水之法,皆李冰所为也。[2]192-196
“深淘滩,低作堰”六字诀究竟起于何时?至今未有定论。学界大致形成了三种观点。(1)秦蜀守李冰建堰之时。依据是杨升庵《金石古文》所收的《秦蜀守李冰湔堋堰官碑》即已有“深淘墠,浅包鄢”[1]39六字遗则,因而建堰之初即已有岁修制度。(2)始于南北朝。依据是明代曹学佺《蜀中名胜志·四川》卷六引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江水》轶文云:“李冰作大堰于此,立碑六字曰:深淘潬,浅包鄢。”⑤潬、鄢为滩、堰古字。(3)始于宋朝。依据是《宋史·河渠志》正式出现的都江堰岁末修治“穿淘”之说:“岁暮水落,筑堤壅水上流,春正月则役工浚治,谓之穿淘。”民国《都江堰水利工程述要》亦载:“宋开宝五年壬申,重刻‘深淘滩,低作堰’六字诀于灌口江干。”⑥综考三说和各方面的资料,第(3)说显然失之过晚。前已指出,《秦蜀守李冰湔堋堰官碑》简朴的古风提示其应为秦汉遗物,因而笔者认同《蜀中名胜志》所引《水经注·江水》轶文的史料价值,既然如此,就只能认为其佐证了第(1)说所谓六字诀为李冰遗则的观点。而第(2)说亦失之拘谨,且逻辑上略欠周延。就史料考订的角度而言,古籍的成书年代与其所引史料的年代应有区分,后者往往比前者早,因而不宜一概以前者定后者,既然《水经注·江水》轶文云“李冰作大堰于此,立碑六字曰:深淘潬,浅包鄢”,则应考虑结合史实背景取后者。从战国晚期都江堰创建以来,该堰一直沿用下来,如无切合水、地之宜的科学岁修原则,实难如此。
六字金诀结合水则的应用,成功地解决了古代岁修难题。根据《宋史·河渠志》,渠首内江工程主要由鱼嘴、侍郎堰(飞沙堰)、宝瓶口等设施构成。为了保证将内江引水量控制在所需范围内,内江河道之底的高程和与之相应并建在冲槽上的侍郎堰(飞沙堰)顶的高程,都必须结合水则高度加以合理确定。如河道底的高程越高,则侍郎堰越高,也就越易被冲毁,导致内江之水顺冲槽尽归外江,使宝瓶口几无水可进,形同虚设。这个千古一以贯之的问题,只能在岁修时按“深淘滩、低作堰”的“穿淘”金诀来科学解决。
所谓“深淘滩”,就是要在每年冬天岁修时深挖河道,清除淤积的砂石,使内江河道断面得以保障稳定的江水过流断面,具体即要达到《宋史·河渠志》所谓“水及六则,流始足用”的标准⑦。所谓“低作堰”,具体到侍郎堰(飞沙堰),就是堰顶的相对高程必须适度,以免过高则影响到溢洪排砂的效果。《宋史·河渠志》对此指出:“水及六则,流始足用,过则从侍郎堰、减水河泄而归于江。”因此,“岁作侍郎堰,必以竹绳自北引而南,准水则第四以为高下之度”。亦即侍郎堰(飞沙堰)顶的高程应以渠首江岸水则的第四划为准。这种“用绳牵平测量,以定淘挖深浅之准”的传统办法,直至清末光绪三年(1877)丁宝桢大修都江堰时仍在沿用。
为了确保“深淘滩、低作堰”的准则得以切实贯彻,除了将这六字金诀刻石垂示,并“鑱石为水则”外,历代还采取了多方面的技术手段和措施。
明曹学佺《蜀中名胜记》谓“都江口旧有石马埋滩下”,以之作为岁修时淘滩深度的标准。清代道光年间,成都水利同知强望泰岁修时曾挖出两个石兽,或即所谓石马。又相传古人为标志淘滩清淤应及层位埋有铁板,明代正德年间的四川水利佥事卢翊就曾在岁修时,淘滩“深及铁板”。埋藏于河道的石马、铁板,应是明代甚至更早时期,人们为岁修淘滩深度设置的标尺。由于岷江洪水湍急,古人设置的标志物常常被冲失或淤埋,反映了先民为实现科学岁修的艰辛曲折。明朝万历四年(1576),正式在凤栖窝底埋下铭有“永镇普济之柱”六字的卧铁一根。后也被冲失,清代又加以补铸。乾隆三十一年(1766),为防止卧铁被再度冲失或淤埋不见,遂以铁链缚所埋铁柱,并在上方立碑以标志卧铁所在。道光二十年(1840),强望泰在宝瓶口后的三泊洞上游挖沟时发现万历四年铁柱,将之重新埋回凤栖窝清代铁柱旁。同治三年(1864),成绵龙茂道观察何咸宜又补铸一根刻有“缵绪贻则之柱”六字的卧铁,与前此两根并埋于凤栖窝。光绪十年(1884)再度冲失一根,为解决卧铁淤没难寻问题,水利同知庄裕筠遂在凤栖窝崖壁立碑,铭文注明“卧铁在此崖下”,且碑与卧铁高差33米,平距7米。民国时期,又补铸卧铁一根,并在三根卧铁旁设置铜标,高程海拔726.02米(比飞沙堰低2.05米);铜标上方浇筑混凝土标准台,台分五级,每级高0.4米,台顶高程海拔728.07米,相当于飞沙堰顶部高度。这就最终基本解决了都江堰岁修淘滩作堰的高度标准问题。
鉴于“深淘滩,低作堰”岁修治堰思想的重要性,清同治十三年(1874),灌县知县胡圻将其总结为三字要诀,铭刻于灌县二王庙:
六字传,千秋鉴。挖河沙,堆堤岸。分四六,平涝旱。水画符,铁桩见。笼编密,石装健。砌鱼嘴,安羊圈。立湃缺,留漏罐。遵旧制,复古堰。[7]271
光绪三十二年(1906),成都知府文焕进一步修改之,并且也铭于二王庙壁:
深淘滩,低作堰,六字旨,千秋鉴。挖河沙,堆堤岸。砌鱼嘴,安羊圈。立湃缺,留漏罐。笼编密,石装健。分四六,平涝旱。水画符,铁柱见。岁勤修,预防患。遵旧制,毋擅变。[7]271
除了千古相传的六字金诀外,先民在每岁修治都江堰的历程中,还总结出了另外一些重要准则和理念。如光绪元年(1875),成都水利同知胡均所撰著名的八字格言:遇弯截角,逢正抽心。这同样是千百年来都江堰岁修在疏浚河道方面的宝贵经验总结,具有很强的科学准则指导价值,因而被镌刻在二王庙壁,一直为世人所会心赏析。同样被尊为八字格言的还有:乘势利导,因时制宜。此为清人吴涛所撰,也镌刻在二王庙壁,从更为富于哲理的高度,深刻总结了都江堰工程两千多年来的科学和人文理念,无论对岁修治堰或理世治国,均颇具启发意义。
三、约定成俗的岁修时序
自古以来的都江堰岁修,均有严格的时序习俗和制度。对此,前人所撰《天时地利堰务说》有云:
由此而推修堰之法,以及水性、节令。如每岁修堰,必在立冬后者,何也?盖此时天寒水冻,江流渐消,庶可淘滩、作堰。须先筑土堤埂一道,以逼江水南行。挖淘工及有半,又外筑砂堤埂一道,抽换土埂。至冬至时而山谷点滴细流,凝聚成冰,且雨雪尚积山谷,不能入江,正是挖淘用工之际。至若夏秋所淤塞沙石,挖淘一尺,得水一尺。深淘至交春时,堤埂水面要比堰底高五尺,堰底比堤埂水面低五尺为合法;如开堰放水,至惊蛰节,水还消尺余,确不误事;此“深淘滩”之法也。竹笼砌鱼嘴分水处,要比水面高五尺,渐至离堆山脚高一丈为合法;堰长百丈,长则能截春夏水入堰;低则能泄夏秋野水还大江;此“低作堰”之法也……。
盖六字心法,久治久验,全在以惊蛰节间河水消定为凭。但月有闰余,节令有迟早不等,务必乘时……。窃以日月经天,各有度数;堰水灌溉,亦有画则。果能开堰修淘,能以顺天地之造化,合水性之消长,按节令之气候,用工深淘、浅筑,则水满田渠,农民庆欣。[2]666-667
此文作者不详,初见于清代乾隆时期都江堰二王庙道士王来通编著的《灌江备考》一书,冯广宏先生认为该文当即王来通自撰,可备一说[2]667。文章从天地阴阳之演化顺逆立论,充满了传统的文化意味,而其对都江堰岁修时序安排的阐述,则显然是历代经验的总结,具有很强的科学性和可行性。具体说来,清代以来岁修的时序,严格按照节令安排如次:霜降节祀神下杩,以内江导流,开始截断外江;小雪淘挖外江河床;至立春,外江穿淘结束,开始放水导流,转而截断内江,穿淘内江河床;到次年三月清明节,岁修工程完成,复开内江放水,并举行开水典礼,由成都知府和主管水利官员(民国时期则由四川省主席和建设厅长)主祭江神和李冰。清代的这一“修堰之法”,不仅与“水性、节令”相关,且因冬季农闲便于征集组织足够的役夫而切实可行。
四、沿革成制的工役组织
征集组织役夫进行都江堰等大型水利设施的岁修工程,秦汉以降与国家劳役制度密切相关。秦自商鞅变法以来,实行小家庭编户政策,严禁“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以扩大国家的赋役收入;又实行“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的政策,即以免除徭役来奖励耕织成绩突出的编户齐民。徭役或简称役,涉及“戍、漕、转、作”等方面⑧,即戍边、漕运、转运和大型公共工程造作,后者包括皇帝陵寝、城郭宫室、道路桥梁的造作,也包括修治堤防沟渠以至农田水利设施。秦并巴蜀后,也将上述制度、法令和政策推广到了巴蜀,青川县郝家坪秦墓木牍《为田律》即反映了这一史实,其文云:
以秋八月,修封捋(埒),正彊(疆)畔,及癹千(阡)百(陌)之大草。九月,大除道及除郐(浍)。十月,为桥,修波(陂)隄,利津梁。[8][9]
以上律令所提到的工程,按国家规定,均由编户齐民承担劳役完成。秦始皇兼并天下后,由于大修骊山陵墓和驰道、直道,并在关中、关外大造宫殿,史称“一岁力役三十倍于古”[10]1137,急政暴虐,终致灭亡。
汉代徭役制度规定,成年男子每年要在本郡服役一个月,叫作更卒或卒更,属于近役;不服役者则以两千钱代役,叫作践更,政府以之雇人充役。此种以钱代役之制,叫做更赋。承担国家大型工程力役的役夫或曰役者,史籍中称为“作者”。如《史记·秦始皇本纪》即称建造阿房宫的役夫为“阿房宫作者”。《郭择赵汜碑》铭文,亦径称建安三年冬天承担都江堰岁修工程的役夫为“作者”,并记其中单是次年出资建碑歌颂郭择、赵汜功德的“作者”就有“赵□卿、郑□□、□彦□、苏子卬、□定卿、杨叔财等百余人”[2]9-10,足见这次岁修役工人数众多,亦证明“作者”乃秦汉时期徭役制度一以贯之的术语。
魏晋南北朝时期,在国家赋役制度下,蜀地政府承担都江堰维护修治工作的役制仍一以贯之,然亦有所变革。如《水经注·江水》即记蜀汉丞相诸葛亮高度重视都江堰的“农本国资”地位,特别“以征丁千二百人主护之,有堰官”[3]766。在每年依制岁修的基础上,又建立一支由兵丁组成的专业队伍常年四时守护,实为加强管理的重大举措。或以为这些兵丁亦要承担岁修力役,可备一说。不过,这出于所处时代条件的特殊措施的形成,绝非偶然。都江堰渠首工程所在,历来是控扼四川盆地尤其是成都平原与川西高原少数民族地区的军事要地⑨,诸葛亮此举,可谓一举两得,兼收军事战略和水利维护之功效⑩。从《郭择赵汜碑》可知,岁修时役夫人数众多,这必然涉及征集和管理等一系列问题。其间的细节因史籍失载,已难稽其详,但必与其时国家户口徭役制度直接相关,则是无疑的。综合传世和出土文献,这些由国家机器的郡县乡里地方机构征集的劳动力,从郡内不同居住地来到都江堰后,应是在都水官员和“堰官”或曰“堋吏”的组织领导下,有序地进行和完成岁修工程。
隋唐时期,继续实行汉代以来以向政府纳钱或物代役的制度。隋朝沿用北魏以来的租调制,租调数量和农民服役时间均有减轻,并规定“民年五十,免役收庸”,即交纳一定的绢代替服役。唐代的租庸调制,规定“有田则有租,有家则有调,有身则有庸”,具体即每丁每年要向国家纳粟二石,叫作租;纳绢二丈、绵三两或布两丈五尺、麻三斤,叫作调;服役二十天,曰正役。不服役者每丁按每天纳绢三尺或布三尺七寸五分的标准,交足二十天的数额以代役,叫做庸,或曰“输庸代役”,政府另外征人代役。秦汉以来的这种代役制度,在政府组织的大型工程中一直延续下来,唐五代之后保存较多的都江堰水利体系岁修工程史料中多有反映。
宋代文献中,都江堰修治的役夫人力组织也有了一些新的变化发展。如宋人张君房《云笈七签·道教灵验记》即记载,其时都江堰岁修,“赋税之户,轮供其役”[2]77,修治工程采用的是按户分段包干具体工程任务的办法,这种岁修役法的改革,有利于提高工程的效率。另一方面,有关资料显示,这些轮役的“赋税之户”一般是都江堰水利体系覆盖范围内亦即受益地方的农户,因而这种劳役又属于古代近役,役者“籍(名籍)在修堰之内,邑吏底名分地以授之,自冬始功,讫年而毕”[2]77。另一宋人冯伉《移监离堆山伏龙观铭并序》亦有类似记载:“每岁孟春,役徒万亿,太仓为之给粟,长吏为之监工。”[2]111岁修工程浩大,以至出现“永康军岁治都江堰……吏盗金,减役夫”[11]8757的违法腐败事件。
元代沿袭了这种由都江堰灌区农户承担岁修工程之役的传统,并以驻军参与其事。对此,揭傒斯《大元敕赐修堰碑》铭记佥四川廉访司事吉当普至元元年(1335)大修都江堰时曾叙及此制:“初,郡县及兵家共掌都江之政。延祐七年(1320),其兵家奏请独任,郡县乃以其民分治下流诸堰,广其增修而大其役,民苦之;至是复合焉。”又记其时都江堰岁修云:“有司岁治堤防百三十三所,役兵民多者万余人,少者千人,其下犹数百人。人七十日;不及七十日,虽事治不得休息。不役者三日一缗。富屈于资,贫屈于力,上下交病。会其费,岁不下七万缗。毫发出于民,十九藏于吏;概之出入,不足以更费。”⑪针对“水失其道、民失其力、吏乘其弊”“上下交病”的状况,佥四川廉访司事吉当普“征工发徒,以至元改元(至元元年,即公元1335年)十有一月朔,肇事于都江堰”。这次大规模治理都江堰水利体系,集中于“要害之处三十有二”,重心是渠首工程,开工早于往年。其余暂未施工者,“若成都之九里堤,崇宁之万工堰,彭之堋口、丰润、千江、石洞、济民、罗江、马脚诸堰,工未及施而诏,亦责长吏及农隙为之”。由于工程浩大,“是役也,石工、金工皆七百人,木工二百五十人,徒三千九百人;而蒙古军居其二。粮为石,千有奇;石之材取于山者,百万有奇;石之灰以斤计,六万有奇;油半之;铁六万五千;麻五千撮。其工之直、物之贾以缗计,四万九千有奇,皆出于民之庸⑫,积而在官者,余廿万一千八百缗,责灌守以贷于民,岁取其息,以备祭祀,若淘滩、修堰之共。仍蠲灌之兵民常所徭役,以专其堰事”⑬。
明朝伊始即“加意水利”,但也加重了巴蜀地区的水利工程差役。嘉靖《四川总志》卷16《成都府·水利》载都江堰灌区岁修时,“每岁冬春之会,令得水州、县与军、卫、屯、所,共役人夫五千”[2]237。可见平均每年兼用民夫、兵丁就达到五千人之多。成华九年(1473),四川巡抚都御史夏埙巡视都江堰堰务,认为“远人赴役不便”,改行新法,因而专由郫县、灌县抽调劳力承担堰务,而二县的“杂派科差,均摊得水州县。(郫县、灌县则)专备工料,以供堰务”[2]237。其后正德十五年(1520)四川水利佥事卢翊继续采取按田产摊派劳役的办法,“下令以粮三石,派夫一名,分八班,凡八年一周”[2]237。此种按田产摊派劳役的办法,形成了固定的岁修劳动力组合,有助于岁修工作的进一步制度化。
清初巴蜀政局大致稳定后,都江堰岁修工程恢复,仍沿袭明代以来按田产摊派劳役之制的传统。顺治十八年(1661),巡抚佟凤彩在上疏朝廷的奏章中提出,“欲为永久计,必行令用水州县,照粮派夫,每年淘浚,庶民不忧旱,而国赋渐增矣”[12]。次年亦即康熙元年(1662),渠首工程恢复,正是此制已行之证。据康熙二十年(1681)温江知县王日讲《水利详文》所载灌县验申“前事”申称,“都江大堰乃成、华、温、郫、新、双、崇等州县用水之源,兵民命脉,国赋根本,每年年前雇夫,自正月初一日,各县典史、堰长督夫到工,兴修至清明工峻”[13]。按照其制,不仅灌区各县典史、堰长督夫到工,而且往往县长也亲自率属下役夫到场处理堰务。该制规定,渠首工程役夫数额为“大修额夫一千零八名,小修额夫三百三十六名”,但因“其时民田未经丈量,仅计块出夫,灌、温、郫、崇、金、成、华及新都、新繁,共计八百三十名。咸以用水之多寡,为出夫之标准”。康熙四十八年(1709),针对“川民不知亩法,向以块计,故都江堰功按田派夫,不无畸轻畸重”之弊,加以大修费用不足,官府遂“易派夫为折银”“每夫一名,折银一两”“得水州县,照折有差”[14]。雍正七年(1729),巡抚宪德上疏:由于川省“田地向来不知亩数,惟有计块出夫。今丈量已竣,亩数可稽,若仍以田块较算,不无大小悬殊之别,实属不均”,应“计亩出夫,随时修筑”。建议将各地摊派劳力改为摊交水费,由当地收款后雇工代役,并在次年即正式施行按田亩得水先后分级征收水费的制度。
上述都江堰渠首工程岁修之制,可谓全川水利岁修范例。都江堰外江堤堰如石牛堰的岁修,即由崇庆、灌县居民承担,清人陈梦雷《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载:“居民计粮出夫,分工修浚。”[2]313各地民堰大抵如此,并延续至晚清民国时期。
五、多源多样的经费渠道
古代都江堰等巴蜀水利工程岁修等建设的经费,大致有四个来源:政府财政拨款;专门税捐(专项赋税);民间自筹;个人捐款。
都江堰作为大型水利工程,其创始修建以至岁修经费的一个主要来源,即政府拨款。政府拨款又分中央和地方财政两个渠道。唐以前都江堰工程建设、维修方面国家府库开支的记录失载,但政府拨款的存在毋庸置疑。唐代高骈在成都修筑罗城,该城既是军事防御工程,又是大型水利设施,与都江堰水利系统密切相关,甚至本身就是该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用工和经费开支浩大。唐僖宗就曾下《赐高骈筑罗城诏》指出,整个工程总共“役徒九百六十万工,计钱一百五十万贯;卓哉懋绩,固我雄藩,罄府库之资储,舍阴阳之拘忌;但为国计,总忘身谋;并无黎庶之怨嗟,不请朝廷之接借”[2]55,足见财政开支之巨。然从诏文中“不请朝廷之接借”之说可知,这笔巨大的经费,全出自地方财政。北宋冯伉《移建离堆山伏龙观铭并序》亦记,都江堰岁修“每岁孟春,役徒万亿,太仓为之给粟,长吏为之监工”[2]112。“太仓给粟”云云,提示宋代对都江堰的修治中央财政似亦有支出。元代灌州也曾实行以贷款于民所获利息,用于都江堰岁修的制度。明代堰工开支政府亦有投入,史载“或支官料”[15]2245。清朝政府财政对都江堰岁修的开支有进一步扩大。明清之际巴蜀长期战乱,导致都江堰荒废于草莽之间,尽管封疆大吏高民瞻、佟凤彩均组织岁修,灌区各县亦纷纷进行修治,但限于财力经费不足,一直难复昔日之功效。康熙十九年(1680),杭爱以都察院右副都御使出任四川巡抚,鉴于“此堰废弛已久,往岁修筑,仅以草率从事,故有历三春而水不至田,农人悬耒太息者。遂于是岁(康熙二十年)孟春,发帑金四百,遴委通判刘用瑞、游击钟声,往求离堆古迹而疏浚之。比至,果于榛莽中得离堆旧渠,砂石淤积久矣。盖历年堰水,惟从宝瓶口旁出,非离堆故道也。禹主治水,行无所事,李冰岂独不然?违其道而治之,毋怪乎用力艰而决防屡告耳”[2]721-723。杭爱这次下决心大规模修复都江堰,使“民得耕稼以有秋,官吏相与庆于庭,士农相与歌于野”,所用经费,即出自国库。乾隆六年(1741),四川巡抚硕色奏请都江堰水利工程岁修经费由国库开支,获得批准。由此“堤岸、闸坝等工,俱动正项银粮。从前捐输各项,自乾隆元年为始,一概革除。都江堰所有计亩均摊,尽数豁免”[2]391。然至乾隆末年,官拨经费款已经入不敷出,初由盐茶道给予补助。到嘉庆二十四年(1819),四川总督蒋攸铦呈请征收灌区各县义仓租谷(堰田收入),“以备堰工不敷经费”[16]287;并由用水各州县捐助竹粮银730两。此后每年岁修“或加银六七两至百余两不等”[14]。各县所交谷价银除支付岁修经费外,至道光二十八年(1848),余款所储已至银9500余两,并用此前以之生息所获息银3720两作为岁修补贴,因而从此年开始免除各县堰工银两;并将嘉庆二十五年(1820)以来征用的济田租谷归还各县[17]114。
不过,无论中央或地方的财政支出,归根究底还是来自民间交纳的赋税。地方政府投入的经费,甚至本身就以工程受益地区的水利专门税捐(专项赋税)为主构成。宋代大观二年(1108)七月诏曰:“蜀江之利,置堰溉田……然岁计修堰之费,敷调于民。”[6]2398随着宋代吏治逐渐腐败,“永康军岁治都江堰,笼石蛇绝江遏水,以灌数郡田。吏盗金,减役夫”[11]8757。这是官员用减少役工吃空缺的伎俩贪污工程款(也可能是“敷调于民”的民间款,但已变为公款)的记载。上引大观二年七月诏令亦指出,地方政府负责岁修“工作之人并缘为奸,滨江之民困于骚动”,因而严令:“自今如敢妄有检记,大为工费,所剩,坐赃论。入己,准自盗法。许人告。”[6]2398
蜀地编户齐民承担修堰赋役之制,由来已久,前蜀杜光庭《道教灵验记》即谓:“赋税之户,轮供其役。”[2]77至于充当地方政府岁修工程经费的专门税捐(专项赋税),宋人有明确记载。南宋范成大《吴船录》曰:
李太守疏江屠龙,有大功于西蜀,祠祭甚盛,岁刲羊五万。民买一羊将以祭,而偶产羔者,亦不敢留,并驱以享。庙前屠户数十百家。永康郡计至专仰羊税,籍羊税以充。甚矣,其杀也![2]177
范成大淳熙二年至四年(1175—1177)任四川制置使,以上引文即其淳熙四年五月从成都离任时,出发西行至都江堰的纪行文字,记载可靠而权威。其时祭祀李冰父子刲羊之税为数甚巨,不仅“永康籍羊税以充郡计”,以至有过“吏颇侵盗”遭致罢免的记载[2]188。羊税不仅成为政府财政的重要来源,且杀羊祭祀李冰父子尤其是被高度神化的李二郎,已不仅仅是民间信仰活动,而是北宋以来政府管理都江堰水利事务之每岁重要内容,并成为后世传统。北宋著名大臣石介《记永康军老人说》对此有详细记述:
有灌口祠,其俗事之甚谨,春秋常祀。供设之盛,所用万记,则皆取编户人也;然官为之聚敛,盖公私受其利焉。民苦是役,过于急征暴敛……国家尝大酺(祭祀二郎神诞辰),而永康屠羊豢豕之家,尤苦其役。盖官以峻刑急责,而强取其利……及是复酺,公(永康判官刘随)先言屠人,出公帑钱平易之。是年,屠人乐输。公初出帑中钱也,有司执之以为不可,公斥之,独行;朝廷亦不问……鲁国石介闻是说,起而舞曰:夫严先配庙,尊圣人也;斥灌口祠,禁淫祀也。[2]124-125
可见宋代崇德庙(今二王庙)供奉李冰父子的春秋常祀当时即已为“国家大酺”,祭祀典仪极盛,史称“万羊之祭”[2]185。北宋欧阳忞《舆地广记》云:“蜀李冰作大堰,以溉诸县……蜀人德之,立崇德庙祀之,蜀人奉祠,岁刲羊以数万计。”[2]184南宋初年曾敏行《独醒杂志》也云:“有方外士为言:蜀道永康军城外崇德庙,乃祠李太守父子也……祠祭甚盛,每岁用羊至四万余。凡买羊以祭,偶产羔者亦不敢留。”[2]162
到元代,根据前述揭傒斯的《大元敕赐修堰碑》文,民间交纳的都江堰水利体系岁修专项赋税数量亦甚巨:“会其费,岁不下七万缗。”具体征收办法是“人七十日;不及七十日,虽事治不得休息。不役者三日一缗”。《元史·河渠志》的记载与此略有出入,曰“不役者,日出三缗为庸钱”,总数则同为“岁不下七万缗”。其明确指出,岁修征费如此巨大,“而利之所及,不足以偿其费矣”。可见国家征收的岁修专项赋税给当时民间造成的经济负担不轻。前述《大元敕赐修堰碑》还记载了元顺帝元统二年(1334),佥四川廉访司事吉当普大修都江堰,其时灌州“民之庸积而在官者”已达二十五万余缗,吉当普此役工程空前浩大,共花费四万九千余缗,余款“廿万一千八百缗”贷民之息,可“以备祭祀,若淘滩、修堰之共”。这笔日后用于祭祀李冰父子和淘滩修堰的官款,考其源,仍是产生于灌州老百姓“专供堰事”这一近役的代役钱——所谓“民之庸”的利息。
明代地方水利所需经费、人力和工料的来源,前后并不统一,“或役本境,或资邻封,或支官料,或采山场,或农隙鸠工,或随时集事,或遣大臣董成。终明世,水政屡修”[15]2245。但在都江堰灌区,如前所述,明初以来仍实行“每岁冬春之会,令得水州县与军卫屯所,共役人夫五千,竹木工料记田均输”。至成华九年(1473),四川巡抚都御史夏埙“以远人赴役不便,又将郫、灌二县杂派(一作泛)科差,均摊得水州县,专备工料,以供堰务”[2]237。其后正德十五年(1520),四川水利佥事卢翊继续采取按田产摊派劳役的办法。四川的上述新法,实际上已经开了晚明“一条鞭法”将税粮和力杂差役全部计亩征钱、折办于官的先河。
清初以降,都江堰岁修工程仍沿袭明代以来按田产摊派劳役经费之制的传统。顺治十八年(1661),巡抚佟凤彩提出,“行令用水州县,照粮派夫”。康熙四十八年(1709),官府遂“易派夫为折银”“每夫一名,折银一两”“得水州县,照折有差”[14]。雍正七年(1729),巡抚宪德建议将各地摊派劳力改为摊交水费,由当地收款后雇工代役。由此次年即行按田亩得水先后分级征收水费。总体而言,计亩分级摊交水费的办法,比起更具人身强制性质的计亩派夫服役,相对减轻了农民的压力和负担,是一个历史进步。上述都江堰渠首工程计亩分级摊交水费的岁修之制,亦影响到巴蜀广大地区民堰的岁修。诸民堰的岁修,一般由用水农户推举或轮流担任的堰长、沟长负责主持,按堰规调集劳力,摊收水费。
巴蜀地区除都江堰这样的大型水利设施作为国家或政府工程,往往由灌区尤其是受益民众以计亩摊收等方式征集解决经费问题外,农村大量的小型农田水利设施,则多由民间筹集资金、工料来兴修和维护。如史载唐代“眉州通义郡青神县,大和(828—835)中,荣夷人张武等百家请田于青神,凿山酾渠,溉田二百余顷”⑭。此种情况,历代均有。又如光绪《射洪县志》载:“乾隆庚午、辛未间(1750—1751),有乡民杨荛、冯栋等跨岗之西而东穿一石洞,欲引水灌田,以力匮则止。乾隆二十五年(1760),邑令何辰劝民捐资,督工横凿岭腹,导溪水以达于坝,分左右支,左支灌太和镇北杨村坝、纳镇坝田二千四百余亩;右支凿石开渠引灌谢家坝田六百余亩。是堰之成,众捐银一千三百余两,各田户计亩出银一千七百余两。”[18]92
普通民众的经济能力一般均很有限,因而地方上捐资兴修水利者,多为大户或乡绅。清代王泽霖《新开长同堰碑》铭云:“乾隆除,吾灌自玉堂场抵太平场,沿山皆旱地。十九年(1754),王来通等五人相度地势,于横山寺凿崖开渠三年,南达石崩江,置闸引水,命曰长流。后经履勘,于乾隆二十三年讫二十九年(1758—1764),续开至太平场下长生宫后,更号同流,合名长同堰,灌溉所及不下一万亩。是堰由二王庙道士王来通规划,县人艾文星、张金倍、王大舜、刘玉相各捐银五百两以为工费。”⑮捐资建长同堰的艾文星等五人,显然都是颇具实力之大户,而规划此堰的道士王来通对清代灌县一带水利亦颇有贡献。无独有偶,据乾隆《双流县志》,清初顺治年间,双流县三圣寺大朗和尚亦托钵募化,自双流金马河上游温江县左岸引水开渠百余里,自流灌溉温江、双流、新津三县之田六万八千余亩,史称大朗堰。乾隆《彰明志略》亦记清代彰明县(今江油市的一部分)有“姚济堰,明成化年间,本乡举人、云南楚雄推官姚本仁致仕后开修”。又如清代三台县“惠泽堰在县之南明镇,与绵属之马嘶渡毗连。乾隆十九年(1754),郡守费元龙、绵州牧罗克昌详请兴修,工巨费繁,历久未就。绵州诸生熊绣暨子飞龙、升龙捐资万余,独力垫修,至三十一年,工始克成,记灌涪绵二属田万六千五百余亩”[12]。
地方官中亦历来不乏捐资兴修水利设施者。如史载北宋哲宗年间的崇宁司里张唐英,就曾“独立捐金”修堰,溉田达数千亩,人称“司里堰”[19],传为美谈。再如元代吉当普大修都江堰之前,就有灌州判官张弘“请出私钱,试以小堰。堰成,水暴涨,堰不动”[2]192,为下一步大修提供了依据。另据康熙《成都府志》,清初战乱,都江堰多年失修,“顺治十六年(1659),巡抚都御史高民瞻、监军程翊凤合文武捐银二千两,雇募番倮修筑开浚,暂资灌溉”。又清朝大邑知县“黄藜,字天阁,福建平和人,康熙庚午举人。四十二年(1703),知大邑。邑旧有堤堰三十六座,导水灌田,常资修浚。藜于春作方兴,几捐俸亲督堰长,预期修筑。终藜之任,秋成无歉”[12]。嘉庆《四川通志·堤堰》亦载:“永济堰在射洪嘴,乾隆九年(1744),遂宁知县田朝鼎捐资创建,约灌杨渡坝田二万余亩。”[12]
需要指出的是,民间捐资兴修的水利工程,因年代久远以后,常常由于种种原因,民间财力不济,遂转而由政府接手维修扩建。如清代崇庆州“黑石河大堰,原系民间自淘挖,往返百里,劳苦备臻”。雍正初年,田廷锡任知州,“为民请命,遂如都江诸堰,一例给帑官修”[12]。又如民国《三台县志·堤堰》记:“永成堰在县东北涪江之滨,清乾隆二十六年(1761)创开于县民陈所伦,灌溉数年,老君溪山泉穿渠堰废。嘉庆十五年(1810),邑令沈绍兴议修复……历百有余年至光绪二十九年(1905)天旱,以工代赈,发帑万金,循古迹而上至绵界麻柳林筑新口,引渠长六十五里,横出山溪九,灌溉涪江左岸涪城、小围及老马渠诸坝田三万四千亩。”又如前引清代二王庙道士王来通规划、大户出资兴建的灌县长同堰,“溉田三万余亩,后以用官工经费岁修,改称上、下官堰”[20]。此种历史现象,反映了中国古代中央集权大一统帝国制度下,民间社会在面对自然环境长期复杂沉重的压力和挑战历程中,相对于国家和政府的强势而表现出的自身力量的不足和脆弱。
综上所述,从传世文献、近年出土的考古资料和都江堰本身的工程模式、建堰材料可以推知,大型水利工程都江堰的岁修应于建堰之初即已经起源,而且在历史上形成了颇为完善的岁修制度及其执行机构,包括系统、完备的准则程式、时序组织以及经费、工料的划拨征集、规划开支等等,充分反映都江堰不仅在工程模式、水文明理念等方面堪称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典范,而且在组织、制度层面同样为世界留下了极为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
注释:
① 根据20世纪40—90年代的长时段测量资料,由于岷江上游河谷经常发生山体崩塌和泥石流等缘故,导致岷江上游平均每年的悬移质、推移质分别为845万吨、150万吨左右,河床质卵石粒径一般为124—248毫米,最大达800毫米,而其大粒径的推移质在河道出山口的都江堰鱼嘴一带大量堆积,因此,定期清淤历来为都江堰岁修工程的主要任务。
② 《汉沈子琚碑》又名《绵竹江堰碑》,绵竹江堰地属广汉郡绵竹县,系绵水(今称绵远河)上的堰渠。详见(清)常明等修:《四川通志·金石》,清嘉庆二十一年刻本,第2128页。
③ 该碑自身全名为“建安四年正月中旬故监北江堋太守守史郭择赵汜碑”,参见冯广宏主编《都江堰文献集成·历史文献卷(先秦至清代)》,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2007年,第9—10页。
④ 涪陵长江江心水下岩盘白鹤梁上有石刻双鱼,其侧石刻题记云:“(唐代宗)广德元年(763)二月,大江水退,石鱼见,郡民相传丰年之兆。”此为历史上关于长江最枯水位的最早明确纪年题刻。另乾隆《巴县志》所载《碑目考》:“重庆汉江水底,石盘上碑形天成,见则年丰,一名雍熙碑,一名灵石,汉晋以来皆有石刻,非江水枯涸极,不可得见,见则年丰。”雍熙碑在重庆朝天门嘉陵江、川江汇口脊石上,则为时更早。
⑤ 该材料散见于明人曹学佺所著《蜀中名胜志·四川》卷六《成都府》六《灌县》引《水经注》轶文。该文不见于今本《蜀中名胜志》。
⑥ 该句见于民国四川省水利局编《都江堰水利工程述要》,但此句原文出处不明。
⑦ 到元代,《元史·河渠志》指出:“北江稍东为虎头山、为斗鸡台,台有水则,以尺画之,凡十有一。水及其九,其民喜,过则忧,没其则则困。”“水及其九”,则进入内江的流量既能充分满足成都平原生产生活用水需求,又不至于导致洪涝,这需要每年冬天严格依深淘低作之则进行岁修。清乾隆王来通辑《灌江备考》中载:清明作秧田时,水淹至五、六划;立夏、小满,成都州县普遍插秧,水淹七、八划至九、十划。根据1949年以来的实测数据,内江断流最低水位为水则五划;灌区扩大后,春灌用水增多,春水十三划流始足用,十六划为洪水警戒水位,灌区河堰即须准备防洪。
⑧ 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纪》载:“关东群盗并起,秦发兵诛击,所杀亡甚重,然犹不止。盗多,皆以戍、漕、转、作事苦,赋税大也。请且止阿房宫作者,减省四边戍、转。”中华书局,1959年,第271页。
⑨ 早在四千多年前的宝墩文化时期,其地上、下芒城的两座古城遗址就以双重城壕为特征,提示其具有强化军事防御的特质,与宝墩文化其余诸城形成对比。
⑩ 其后都江堰一带也常驻军队,并参与岁修等工程。如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74载宋代其地因“正控两山六州军隘口”,先后为永安军(乾德四年,公元966年)、永康军(太平兴国三年,公元978年);《元史·河渠志·蜀堰》亦载元代伊始,这里亦行“郡县及兵家共掌都江之政”;明代也常以军队参加都江堰岁修工程。
⑪ (明)宋濂《元史·河渠志》据揭傒斯《大元敕赐修堰碑》铭写成,其文此处亦为:“会其费,岁不下七万缗,大抵出于民者,十九藏于吏。而利之所及,不足以偿其费矣”。参见《元史·河渠志·蜀堰》。
⑫ 《元史·河渠志·蜀堰》作“铁六万五千斤,麻五千斤。最其工之直、物之价,以缗计者四万九千有奇,皆出于民之庸”,其文是。
⑬ (元)揭傒斯:《大元敕赐修堰碑》铭,载冯广宏主编:《都江堰文献集成·历史文献卷(先秦至清代)》,巴蜀书社,2007年,第192—196页。本处引述时标点有所调整。
⑭ 见(宋)欧阳修:《新唐书·地理志》。清代嘉庆《四川通志·堤堰》亦云:“鸿化堰在(青神)县北十五里,唐初(按当为唐后期)张武等所开。”
⑮ 转引自四川省水利电力厅编:《四川水利志》(第一卷)(内部资料),1989年,第8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