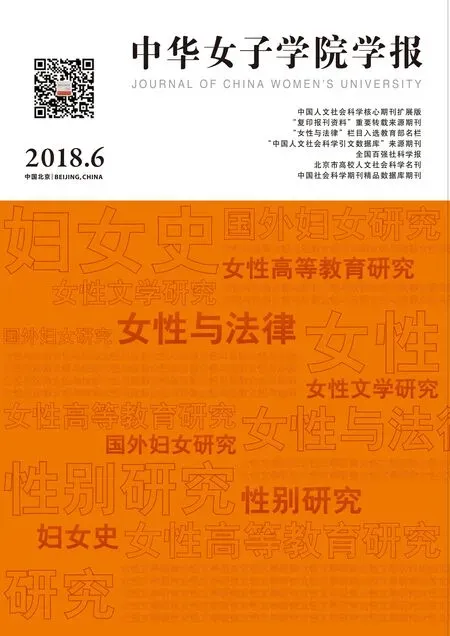简·奥斯丁及其家人的择偶观
龚 龑
在《英国的家庭、性和婚姻》中,历史学家劳伦斯·斯通指出,1500—1800年间,英国的家庭生活发生诸多变化:从最初“开放的世系家庭”(1450—1630),经历了后来的“家长制核心家庭”(1550—1700),最后又发展成为“封闭的小家庭”(1640—1800),也就是现代家庭的前身。在这一变迁中,情感因素,如所谓的“情感个人主义”,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大致而言,到了英国18世纪晚期,无论农村地区的乡绅儿女,还是城市里的有产阶级子弟,都能够比较自由地选择配偶,而不必听命于家长的意志;即便在某些贵族家庭,双方当事人对感情的考量,也不亚于对金钱、地位和权力的权衡。本文以简·奥斯丁家族的择偶实例来验证一下斯通的说法,并结合相关传记材料来推测奥斯丁的婚恋观。现实生活中,择偶实践所涉内容颇为广泛、繁杂,本文主要考察其中的两个重要方面:第一,撮合婚姻时,最终的决策权究竟取决于父母,还是子女?若两者都参与其中,那么这样的决策权在父母与子女间该如何分配?第二,择偶的主要动机是什么?为了方便分析,不妨将其分为两类,利益取向型和情感取向型。前者是指主要为了巩固家族的社会利益或者自身的经济地位而缔结婚姻,而后者是基于对对方的人品、心理素质等方面的了解,经过一段时期相处后才决定组合家庭。
一、作为“准乡绅”的奥斯丁家族
斯通论述的时段太长,而且涉及各个社会阶层,有时作者也不得不承认,现代早期英国的择偶情况非常混乱,难以归纳。[1]287-288本文有意锁定某一具体阶层,并将时段压缩至18世纪和19世纪之交,大致相当于英国小说家奥斯丁的生平,也就是1775—1817年。斯通的史料多取自当时的贵族和乡绅(Gentry),谈及性行为时,大多个案均围绕着贵族家庭展开。贵族和乡绅都拥有地产,但数量有别,此处不必赘言。在18世纪,贵族和乡绅占英国人口的比重较小。[2]228严格地说,奥斯丁家不能算入其中,或至多算是乡绅的底层。斯通在论述中还采用了其他表示阶层的术语,比如地主(Squirarchy),有产阶级(Propertied Classes),中等阶层(Middling Ranks),甚至资产阶级等,这些分类也不足以精确界定奥斯丁家的阶层归属。有学者认为,那些仅次于乡绅的社会阶层,不妨叫作“准乡绅”(Pseudo-gentry)。[3]“准乡绅”算得上乡村里的精英人士,但基本上没有自己的地产,或者地产寥寥可数,不会超过50英亩。他们持有固定职业,如国教的神职人员(教区长、牧师、代理牧师等),或者律师、医生以及现役军人等。奥斯丁的父亲资助两个儿子到牛津大学读书,手头宽裕时还一度购置了马车等,这些基本达到了普通乡绅的消费水平。法国大革命前后,英国社会正在逐步降低乡绅阶层的门槛,让更多有产者加入精英群体,以调整社会分层,缓和阶级矛盾。
斯通提及了诸多乡绅家庭择偶的个案,但限于篇幅,不够具体。本文以奥斯丁家族为进一步补充,不仅希望揭示此阶层的某些婚恋观念,还想指出,当时亲族联系的重要性,并没有如斯通所说,逐渐下降且主要限于近亲的范围。[1]124-129不必说贵族、上层乡绅家庭,即便是“准乡绅”的奥斯丁家庭,也离不开一个四处弥漫的关系网络的强有力支撑。小说家的父亲乔治·奥斯丁(1731—1805)出生于一个外科医生家庭,在70余年的生涯中,成功地为子女在“准乡绅”的世界里谋求到稳定的地位。家族关系,尤其与之相连的恩庇体系,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弗兰西斯·奥斯丁(1698—1791)是此家族中一名热心的律师,为侄子乔治·奥斯丁的前程精心谋划,劝他放弃学徒,先去汤布里奇语法学校就读,然后转入牛津大学。乔治·奥斯丁获得了圣约翰学院的奖学金,为最终通往教会的大门初步铺平了道路。堂兄托马斯·奈特(1701—1781)通过广泛的人脉关系,出资为刚刚毕业的乔治·奥斯丁确保了两份圣职。[2]还是通过熟人引介,乔治·奥斯丁娶了李氏家族的卡桑德拉(1739—1827)。这家人拥有较高的社会地位,是奥斯丁家族所不能企及的,日后为奥斯丁兄弟姐妹的发展都发挥过不小的作用。奥斯丁的大侄子,也就是日后《简·奥斯丁的回忆录》(1869)的作者,最终继承了李氏家族的部分产业,更其家族名为奥斯丁-李(Austen-Leigh)。
奥斯丁夫妇共育有六子两女。一个儿子患不治的残疾,终生被寄养在附近村民家里,本文不予讨论。奥斯丁的三哥爱德华(1767—1852)最幸运,过继给了奈特夫妇的儿子(小奈特夫妇无子嗣),成为大庄园的主人,算得上是没有头衔的贵族。当然,按彼时的协议规定,他得正式改姓奈特。奥斯丁母亲认为,爱德华是个“天生的商人”,乐见这个儿子前程似锦,改姓根本算不上什么。[4]18后来,奥斯丁姐妹经常远道探望爱德华一家,入住肯特郡那幢颇为气派的古典豪宅,过一段上流社会的日子。1809年,爱德华将所继承另一处产业的小部分,即汉普郡的乔顿乡舍,分派给母亲和两个姐妹居住,这就是今天奥斯丁故居和纪念馆的所在地。
奥斯丁的大哥詹姆斯(1765—1819)继承了大部分家产,并追随父亲的步伐成为神职人员。二哥亨利(1771—1850)的职业生涯最为丰富多彩,从军和经商等都曾尝试过。凭家族关系,他在牛津郡捐纳了一个中尉的军衔,兼任该地兵团的财务出纳员。[5]84退役后,靠整个家族筹款一万英镑作股本,亨利与先前的战友合伙在伦敦开办了一所小银行。银行业在英法战争期间一度繁荣,但1815年英法战争结束后,大范围的经济萧条突然而至,诸多小型银行岌岌可危。亨利从爱德华处又筹措了一万英镑,竭力支撑生意。银行最终倒闭后,他才死心塌地、规规矩矩当了牧师。也就是说,奥斯丁家有三个成员在教会里谋生。由于农业革命和圈地运动,农村地区的什一税明显增长,牧师的地位在18世纪末有所上升。[6]18许多牧师热心农事,撰写农业报告,有的甚至成了农艺学家;某些牧师担任治安法官,代理地方政府的职能。在某种意义上,牧师们算是现代公务员的前身。[7]17
与奥斯丁年龄最接近的两个兄弟,是四哥法兰西斯(1774—1865) 和唯一的弟弟查尔斯(1779—1852),他俩都在少年时代就加入了皇家海军。1792年法兰西斯擢升为上尉,曾巡航东印度群岛,并在中国待过一段时间;查尔斯服役于“独角兽”舰,曾俘获过两艘法军船只,这些细节在奥斯丁的小说《劝导》中曾间接提及。他们最后成为小有名气的海军上将,法兰西斯还获得“爵士”的荣誉头衔。英法战争导致了英国军队数目不断扩大:海军人数从战前3万人增长至1810年的14万人,陆军从4.5万人骤升至1812年的25万人。[8]海军军官若捕获敌军战舰,就可以因分享战利品而致富,对中等阶层子弟而言,一度成为炙手可热的职业选择。牧师和军官是当时乡村社会里两个重要的职业群体,可以说是19世纪英国中产阶级的前身。奥斯丁家族的经历,是“准乡绅”阶层全面兴起中的一幕,是极具典型意义的社会现象,值得认真研究。在本文考察的这一历史时段,英国社会发生了较大的社会和地理流动,这必然改变准乡绅阶层的构成和规模,并使得此阶层的子弟与其家族、邻里的传统关系松弛开来,进而改变他们的职业、择偶观念等。
二、奥斯丁兄弟的择偶
大致而言,在奥斯丁家族的择偶上,取决于父母而不考虑子女意见的情况几乎没有。爱德华的婚姻稍微特殊些,虽然排行老三,他是兄弟六人中最早结婚的。如前所述,他自幼过继给奈特家族,不仅完成了大学教育,而且有机会到欧洲“游学”。[5]70诚如斯通所言,大家族要权衡政治、经济地位的巩固,不得不考虑门当户对。1790年,在肯特郡的邻居中,爱德华结交了布鲁克爵士,看中了这个家族年仅17岁的小女儿伊丽莎白(1773—1808),并于次年成婚。布鲁克爵士共有三个女儿,均就读于“伊顿女校”(Ladies Eton)。爱德华和伊丽莎白共育有11个子女,奥斯丁姐妹终身未嫁,经常到哥嫂家尽“未婚姑妈”(Maiden Aunt)的义务。
作为长子,詹姆斯会感受到压力,他获得了大部分财产,其婚姻选择对家族的未来很重要。如果两个妹妹嫁不出去,他有义务承担一定的生活费用,甚至得长期照料她们。1792年,自牛津大学毕业后,詹姆斯赶赴所属教区就任助理牧师,在当地结识了马修将军(1728—1805)。马修将军终生行伍,参加过英国反对北美独立的战争,曾兼任格林纳达地方行政长官,积攒了不少资产。此时,马修将军已经回国,购置了一座私人宅邸(Manor House)。将军的二女儿安妮(1759—1795)年近30,比詹姆斯大5岁。按当时的平均结婚年龄推算,这差不多是她最后的择偶机会。詹姆斯爱慕对方的大家闺秀风范,两个人很快就开始商定婚事。最初,马修将军夫妇并未相中这个助理牧师,但出于对女儿的关爱,同意了这门亲事。[3]71-72这桩婚事主要由子女来决定,当然子女本人也必须考虑双方是否门当户对。马修将军承诺,每年为女儿提供一百英镑的“零用金”(Allowance)。[5]72在18世纪的婚姻协定中,像这样的零用金发放,一般要明文指定,以保障女方婚后的基本权益。安妮生有一女,1795年因病去世,马修将军继续支付这笔零用金,并表示主要用于外孙女的抚养和教育等开支。在洛克和卢梭思想的影响下,18世纪的欧洲儿童开始被认为是“纯洁无辜、有待造就”之物,他们的感受、需求和愿望,也逐渐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9]41-48文化市场上的各类玩具、书籍和教育用具等,都直接以儿童为对象。此时,中等家庭不再把孩童送往别人家里做学徒。
妻子去世后,詹姆斯准备续弦再娶,而此时奥斯丁的二哥亨利也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这给我们一个机会来看看奥斯丁家的“自由恋爱”。哥俩迷恋同一位表姐伊莱莎(1761—1813),并在他们的期刊、书信文字中流露出争风吃醋的心态。奥斯丁的姑妈曾因家境贫寒,不得不远嫁某东印度公司的医生,1861年她在加尔各答生有一女,就是奥斯丁家未来的“海外表姐”。这位姑妈与首任印度总督黑斯廷斯颇有交情,经她联络,黑斯廷斯的儿子一度交由奥斯丁父母照顾。后来黑斯廷斯赠予伊莱莎一万英镑,这可是一个大数目。伊莱莎主要在法国接受淑女教育,骑马、跳舞、弹竖琴,样样精通。她不时寄信给英国乡下的表亲,大谈巴黎趣闻、精美时尚等。在母亲和朋友的劝说下,伊莱莎先是嫁了某个法国贵族,生有一子;后来,这位丈夫在法国大革命中被处决。自此,伊莱莎带着儿子穿梭于巴黎和伦敦之间,时常参加中上流社会的晚宴,频频约会、出游,过着“喧闹的生活”。[10]45-47伊莱莎好虚荣,但自信、积极,乐享生活。最终,她选择了颇具绅士范且浪漫多情的亨利,放弃了一本正经的牧师詹姆斯,她在书信中多处表示不喜欢牧师职业。詹姆斯后来娶了邻村的老朋友玛丽·洛伊德(1771—1843)。得知此一消息,奥斯丁母亲乐不可支,立即给这位尚未过门的新娘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我和丈夫希望,你将接受我们的至爱,一想到不久你即将成为家里的儿媳,我们感到莫大的满足。”[5]99
“海外表姐”曾给奥斯丁家带来了不小的“动荡”。1795年,亨利第一次向伊莱莎求婚,遭到拒绝。也许为了摆脱对表姐的迷恋,1796年初,亨利一度与玛丽·皮尔森订婚,后者是格林威治海军医院某军官的女儿。亨利甚至得到了对方的小画像,并自豪地向父母展示。从书信看,奥斯丁的母亲暗自高兴,以为这一下总算摆脱了伊莱莎,毕竟她比亨利年长近10岁,还带着一个儿子。此时,奥斯丁恰好跟亨利造访伦敦,近距离目睹了皮尔森小姐的芳容,她写信提醒姐姐:“如果皮尔森小姐跟我回家,请小心,不要期望她太美。……咱妈肯定会大失所望,我看过她的小画像,和本人压根不像。”[5]97
或许就在这期间,伊莱莎对亨利又发起了一轮情感攻势,亨利竟然终止了和皮尔森小姐的婚约。这可是件大事,有悖于当时的乡规民约,甚至给双方家庭带来一些闲言碎语。从现有证据看,这主要是亨利本人决定的,奥斯丁父母并没有干预。其实,奥斯丁母亲对伊莱莎从未说过一句好话,对于他们的结合甚至不乏微词,但这些统统无济于事。1797年12月26日,伊莱莎给自己的教父写信:“我已经同意和表弟奥斯丁中尉结婚了,……他收入充裕,心地善良,通情达理,对我痴情不渝,对我儿子,也关爱有加,他赞同我对自己财产的处置,毫无私念,尤其这一点,我不得不答应他的求婚,两年来我一直拒绝。”[3]105所谓“财产的处置”,是指同年八九月间,伊莱莎提取了属于她、但暂由乔治·奥斯丁等人共同托管的基金(约一万英镑),并完全归她自己掌管。18世纪的英国妇女,尤其寡妇,采取婚前将财产交与数位保管人的预防措施,原则上,未来的丈夫不容易动用此款项。另外,从亨利和伊莱莎的婚恋也可以看出,追求现世的欢乐和幸福,已经成为18世纪英国中等阶层结婚的主要心理动机。他们相信,获得属于自己的快乐,也有益于公共福祉。难怪当时的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宣称:个人利益的追求,如果能自由合理地进行,将促成一个自我调节的良性市场,而社群的经济利益和福祉,也会随之最大化地被确保下来。
按斯通的说法,婚姻最自由的是幼子,他们自己做决定,只把决定的结果告诉父母。1803年7月,奥斯丁的四哥法兰西斯抵达肯特郡的海边小镇,指挥当地的海防部队,由此结识了吉本森一家。这家的大女儿玛丽(1785—1823),金发碧眼,性格开朗,富有活力。两人很快开始谈恋爱,并于次年正式订婚。[3]139-1401804年,奥斯丁的弟弟查尔斯负责大西洋沿海地区的巡航,保证中立国家(尤其美国)不与法国进行贸易往来。在百慕大驻扎时,查尔斯认识了当地的首席法官埃斯顿先生,并通过他认识了范尼·帕尔默(1790—1814),也就是这位法官的小姨子。查尔斯和范尼于1806年春订婚,次年结婚,当时女方只有17岁。[5]161哥俩都是通过书信将择偶的结果告知父母。
奥斯丁兄弟在择偶时,都会考虑友谊、情感等因素,在相处一段时期后,基于对对方的道德、心理等方面的了解,进而决定组合家庭。需要指出的是,即便以这样的情感动机为主导,审慎的态度(尤其关涉经济条件、家庭出身等问题)始终是不可或缺的。不妨说,奥斯丁父母的价值观早已被子女所接纳,即便他们不参与,后者也会较为自觉地从门当户对的家庭中选择合适的伴侣。
三、奥斯丁姐妹的择偶
女性在择偶时往往处于弱势,她们唯一可靠的未来,在于是否能确保一桩满意的婚姻。奥斯丁家属于乡绅的底层,詹姆斯继承了大部分家产,奥斯丁姊妹俩几乎没有自己名下的嫁妆。大约于1792年,奥斯丁的姐姐卡桑德拉(1773—1845)与儿时的伙伴汤姆·福勒(1765—1797)订婚,福勒曾经是奥斯丁父亲为增加收入而在家里招收的学生。[5]81这对恋人没有多少财产,但当事人和双方家长似乎并不介意。从亲属克雷文伯爵那里,福勒得到了威尔特郡阿灵顿教区的牧师职位,但这还不足以让这对情侣举办婚礼并维持像样的生活。1795年,克雷文伯爵请福勒充任随军牧师,跟他前往西印度群岛。福勒接受了提议,希望能积攒一笔充足的结婚基金。他也预估到漫长海上航行的危险和西印度群岛的炎热气候,同年10月出发前,福勒立下遗嘱,若有意外,未婚妻可以受领自己的全部积蓄(约一千英镑)。[5]91一年后,这位随军牧师在圣多明各死于黄热病。从各种证据看,日后似乎没有人可以在奥斯丁姐姐的感情中取代福勒;奥斯丁家人也逐渐意识到,卡桑德拉宁愿单身终老,将注意力完全投放在直系亲属身上。随着母亲年高岁长,卡桑德拉不仅承担了大部分家庭责任,还频繁造访肯特郡,照料爱德华不断增长的家庭;姐妹分开时,卡桑德拉总要及时答复奥斯丁的信件,帮她排解各类难题。卡桑德拉从未婚夫那里获得一千英镑遗产,这意味着她有了一定的经济基础。
奥斯丁父母往往授予青春期子女相当大的约会自由,如谈话、跳舞等。在当时,乡镇中的舞会、联欢会,往往是青年男女交往的场合,还有各郡的巡回审判、年度市集或赛马大会等。奥斯丁和汤姆·勒弗罗伊(1776—1869)就是在村里举办的舞会上相识。勒弗罗伊来自不太富裕的爱尔兰家庭,兄弟姐妹一大群,而父亲已经退役。勒弗罗伊有个亲戚较富裕,看重侄子的才分,资助其完成大学教育并为他规划了未来的职业,希望“有一天出人头地,再来救助其他的家人”。[5]92勒弗罗伊在都柏林三一学院表现出色,但身体欠佳,1795年底来汉普郡度假,顺便拜访这里的叔婶,然后去伦敦进修法律。他和奥斯丁就这样不期而遇。在20岁的奥斯丁眼里,这个小伙子“十分绅士、帅气、令人开心”。卡桑德拉不知从何处听到妹妹和勒弗罗伊调情的风言风语,写信告诫妹妹,要她注意言行。奥斯丁根本不当回事,“我们一起跳舞、闲坐,举止之放纵,言谈之惊人,你尽可想象”。[11]2不久勒弗罗伊去了伦敦,两人了断了任何往来。后来,勒弗罗伊完成在伦敦的法律见习,回到家乡娶了一位富有的爱尔兰小姐,最终晋升为爱尔兰高等法院王座庭的庭长。传记学者指出,勒弗罗伊叔婶对两个年轻人的交往颇为担心,毕竟勒弗罗伊是未来的“家庭顶梁柱”,学业未完成,而奥斯丁也没有多少嫁妆,为阻止日久情深,不妨先采取果断措施拆散他们。[12]154不过,这完全是来自男方家庭的干涉,奥斯丁的这位“白马王子”显然感受到了家族长辈的压力。“嫁妆制”在罗马社会就颇为盛行,历经中世纪,到了维多利亚时代依然生机勃勃。与那些比自己社会地位低下的人群联姻,时人称为“下嫁或者下娶”(Marrying Down),不仅贵族对此怀有恐惧感,乡绅和城市资产阶级也同样耿耿于怀。
两年后,这位勒弗罗伊婶婶另作打算为奥斯丁做媒。她邀请当时还是剑桥大学学生、后来成为牧师的布莱克奥(1771—1842)来家里访问,为两个年轻人营造见面的机会。她已经向布莱克奥说明,奥斯丁是一位值得考虑作为合适妻子的人选。布莱克奥脾气温和、心肠不坏,但为人自负,大声说教,这让奥斯丁惊讶不已。在致勒弗罗伊婶婶的信中,布莱克奥表达了对奥斯丁的殷勤之情。奥斯丁似乎看透了对方,在信中写道:“相较于他此前的举止,这封信理智有余,爱意不足。我挺满意。我俩的交往,会顺顺利利进行一阵,然后就自然而然地终结了。我们很快就会对彼此没有感觉。他最初的好感,纯属因为对我一无所知。这样的好感,除非一辈子再也不见我面,否则难以维系。”[11]19看来,奥斯丁对未来配偶的举止、人品等,均有一定的要求。得知侄女安娜订婚后,奥斯丁赶紧给姐姐写信:“可叹的是,双方的品位极不同,让人有些忧虑:男方讨厌聚会,而她(侄女)却很喜欢。另外,男方脾气古怪,而她情绪易变,这也不太妙。”[5]204
1801年,奥斯丁父母做出一个重大决定:离开家乡,领着两个女儿定居巴斯。对此,学者给出的猜测都与奥斯丁日后的文学创作相关,其实可以换一个角度考虑奥斯丁父母的决定。此时,这对姐妹都未出嫁,奥斯丁已经26岁,几乎逼近适婚年龄的上限。在伦敦和巴斯,人口流动较快,社交机会颇为频繁,这为男女缔缘提供了必要的场所。伦敦和巴斯是当时最大的全国性婚姻市场,潜在的配偶人数远高于其他地区。[1]317或许,奥斯丁父母认为,两个女儿的择偶不必仅仅局限于本阶层或本郡。1801—1805年间,奥斯丁曾陆续寓居巴斯,也频繁造访伦敦。她的另一段“自由恋爱”,恰发生在1801年夏天的旅行中。奥斯丁父母带着两个女儿前往德文郡,在那里结识了一位年轻牧师,后者来此地探望以医生为职业的兄长。据说,奥斯丁对此牧师印象极佳,甚至坠入爱河。不久,奥斯丁一家却收到了这位牧师的讣闻。奥斯丁过世多年后,姐姐卡桑德拉对家族中的晚辈提及了这段海边恋曲。[13]63
奥斯丁有一位求婚者哈里斯·比格-威瑟,是她家多年的朋友。比格-威瑟是自己家族的财产继承人,他的三个姐妹都想极力促成此事。1802年12月,旅行中的奥斯丁姐妹来看望比格-威瑟一家。有些出乎意料,这位比格-威瑟突然提出求婚,最初奥斯丁接受了,但仅隔一夜她就反悔了。对此奥斯丁本人从未给出任何解释,多年后,她的侄女卡洛琳推断,比格-威瑟家境优裕,两家交情深厚,况且对方真诚求爱,奥斯丁心头不免一热。卡洛琳写道:“那些房子和财产,毫无疑问是属于他(比格-威瑟)的,但这些东西不能改变其人。”[5]137这位比格-威瑟身材魁梧,但长相、举止不佳,曾患有口吃,比奥斯丁小5岁,两人并无情感基础。或许奥斯丁是出于家庭责任感,为了生活有所保障而一时允婚。奥斯丁拒绝如此“有利的婚姻”,事后自然引来了大哥和大嫂的啧啧埋怨。奥斯丁最终放弃此一婚姻,更多的是考虑自己的个人感受。坚持个人拥有某种程度的行动自由权与内在信仰权,这也是英国新教价值体系的应有之义,小说家奥斯丁还经常被称作是“牧师的女儿”。27岁的奥斯丁不会不知道,一旦拒绝这桩婚事,就意味着与“为妻为母”的传统角色渐行渐远了。卡洛琳对此赞叹道:“我一直都因为姑妈的勇气而尊敬她。我想,大多数年轻女子仍然相信,先结婚再培养情感也无妨。”[5]138某现代传记作家如此评论:“大多数女人会毫不犹豫地接受,她们相信,婚姻需要的是安全感而非爱情,但奥斯丁拒绝这么做,她宁愿成为自己思想和行为的主宰。”[12]183另外一个“简迷”学者也感叹道:“自此,不会再有什么降临到奥斯丁这个女人的身上,从现在开始,她的历史将属于艺术家奥斯丁的。”[14]130
若要窥测奥斯丁的心迹,她给侄女范妮的两封书信算是不可多得的“物证”。范妮年幼丧母,自15岁起就成了家里的女主人,料理家务,照看十几个弟弟妹妹。奥斯丁对姐姐说:“她(范妮)几乎就像咱们的妹妹。我从没想过,会有一个如此重要的侄女。”1813年,奥斯丁和范妮逗留于伦敦,她见过范妮的追求者约翰·普伦特里,“一个英俊的年轻男人,有着安静的、绅士般的举止”。范妮也曾向姑妈透露恋情,但到了1814年11月,她感到自己的感情变了,写信给姑妈,探寻自己变心的原因。
奥斯丁全力为男方辩护:“他的处境、家庭和朋友,他的人品,心地善良,讲究原则,志虑忠纯,性行淑均,你知道,这些具有怎样的价值,这些,你知道,是最重要的。……这样一个年轻人,品质如此卓越,你与他,在爱情中一起成长,多么令人称心如意。”[11]292-293这种典型的情感取向型择偶动机,更渗透在奥斯丁的小说中。奥斯丁一再奉劝自己的读者在伴侣身上寻找诸如善良、理解力强、脾气好、为人和悦等品质,难怪读者会将她的小说当成现代婚姻指南。在这番劝导的最后部分,奥斯丁补充道:“话虽至此,我还要告诫你,假如不是真喜欢他,不要接受他。什么都可以忍受,没有情感的婚姻,却不能。”[11]292-293
对姑妈的劝导,侄女反复揣摩,心神难宁。事后,奥斯丁也有所不安,而且,她从范妮的回信得知,男方刚进入林肯律师学院读书。在第二封回信中,奥斯丁突然调转了劝导的方向。
现在,令我疑虑的是,一旦你们私订婚约(无论语言上挑明,或两人心有默契),将对你产生怎样的不利。…… 我担心的是,这种默许的婚约,充满了诸多不确定,难保何时才能兑现。等他经济独立,可能还需要好多年。你对他的情感,现在就结婚,或许尚可,但不足以让你一直等待。……一想起,你到现在为止,还没有结识几位男士,而且,将来还极有可能(我现在依旧相信,你能)真心爱上一个人;只要想一想,下来的六七年,你的生活会充满多少婚姻的诱惑(这几年,最容易产生儿女私情),我真不敢指望,以现在不温不火的情感,你就对他以身相许。没错,你也许不会再吸引另一个像他一样的男士了。可是,假若真有这样的男士,且对你更有深情,在你眼里,他就会显得更完美。[11]298-299
在这两封信中,奥斯丁的态度看似矛盾,其实背后的主导精神是一致的:认真对待婚姻中的个人感受和未来幸福。这种审慎的态度,有时变得近乎是一种“算计”。这位范尼最终拒绝了对方的求婚,直到30多岁她才结婚。有数据显示,18世纪英国中等阶层中,呈现出“结婚年龄较迟”的趋向。某种程度上,这种晚婚现象和审慎的态度有关。就物质层面而言,要在正式步入结婚礼堂前累积必需的经济资本,奥斯丁姐姐和福勒推迟他们的结婚显然有这方面的考量;就精神层面而言,要仔细衡量哪一个选择会带来更多的快乐和幸福。此处强调奥斯丁姐妹的审慎,自有一种特殊的历史语境需要强调:18世纪英国中等阶层的女性一般都不参与社会劳动和生产领域。直到19世纪中期后,随着近一个世纪的工业化浪潮之拓展和纵深,英美国家的妇女地位和自我意识才发生较为显著的变化。恪于形势,她们不可能像今天的女性一样追求婚姻平等,完全从情感的角度出发来选择配偶,本文所谓的“情感取向型”当然是相对而言的,奥斯丁姐妹的审慎态度也是不言而喻的。可以说,只有当就业、保险、金融市场以及其他各种现代市场机制健全起来并取代了传统家庭、社会关系的经济交易功能之后,婚姻和家庭的基础才能更多是感情而非利益,个人是为自己而不再是为别人而存在。对于今天的读者来说,一旦没了感情,婚姻的基础就丧失了,离婚是合情合理的选择,而在奥斯丁的年代,离婚几乎是不可能的,结婚就意味着终生的选择。
四、结语
由奥斯丁家的情况观之,在撮合婚姻时,最终的决策权基本上取决于这个家庭的子女,他们只是把决定的结果告诉父母。就动机而言,奥斯丁家族在择偶时首先考虑情感因素,相处一段时期后才决定是否要组合家庭。当然,涉及经济状况或社会地位时,审慎的态度也是不可或缺的。这样的择偶实践和观念,与奥斯丁家族的“准乡绅”地位极有关系。婚姻观念的转变与整个社会、经济和文化体系等都息息相关。本文试图以奥斯丁家族为例,来勾勒18世纪和19世纪之交英国“准乡绅”择偶的某些具体历史语境。当然,那是一个社会流动性较强的年代,即便同一社会阶层的婚恋观念也存在相当差异,况且,每个家庭选择婚姻伴侣的情境都会因时因地而有所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