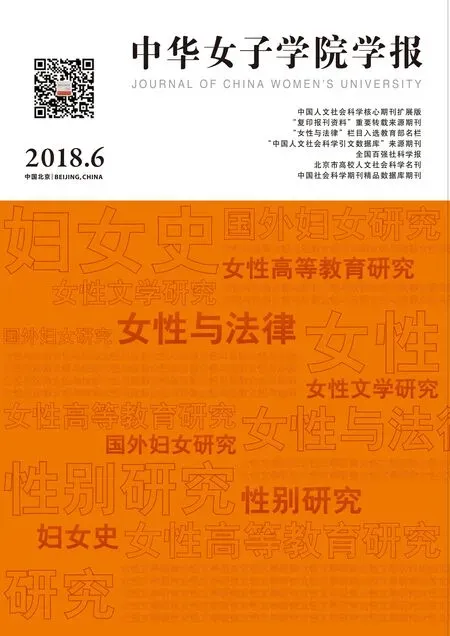印尼华文女作家袁霓的本土书写
马 峰
在印尼,袁霓是极具影响力的客家籍华文女作家。她不仅是印尼华文文学(简称“印华文学”)的引领者,还是印尼客家社团的重要领袖。她1955年生于雅加达,1966年因苏哈托政权全面封闭华校而失学。自20世纪90年代起,印尼文化环境逐渐开放。1998年12月22日,印尼华人文化界人士共同成立“努山打拉之光基金会(Yayasan Budaya Harapan Nusantara)”属下的“印华作家协会”。从创会至今,她一直担任该会主席,更对新生的作家团体充满信心:“我们希望通过文化和艺术的桥梁,达到和印尼兄弟民族间的友好和谐;用我们热爱的华文文字抒发我们的思想感情,也用我们热爱的印尼文文字写作和翻译。”[1]东瑞称其为“乱世涌现出的女闯将”,作为事业型的女性,她的可贵与奉献除了个人的创作,就在那种为整个印华文学发展的全情关怀和贡献。[2]559-563印华作家协会是印尼本土最大的文学团体,在组织文学活动、作家交流、创作比赛、出版书籍等方面都发挥了核心作用。
印华文学的发展有其特殊性,1966年至1998年的华文断层期对作家的创作产生极大影响。袁霓在接受访谈时表示,当时印华作家都会取材于当地社会,反映当地社会现实,也关注下层民众的苦乐,只是不敢深入批评,更不敢批评政府政策。[3]另一方面,官方的政治高压也激发出作家们潜在的社会参与意识。慕·阿敏认为,作为反映现实生活、促进族群融洽团结和推动社会进步的文学工作者应有时代使命感,印尼华人写作者应立足本土,描写具有本土气息的作品。[4]11既要表现本土社会,又对政治有所顾忌,于是“温和的本土书写”便成为印尼华人写作者的重要手段,这种倾向在女作家中尤为明显。温和的书写策略表现为温和的笔调、温情的主题、和谐的追求。从题材内容来说,作品多描写日常的人情世故,包括爱情、亲情、友情、乡土之情等;涉及政治与族群议题时,多采用迂回手法,较少直接的伤痕揭露与批判,多寄望于彼此理解、和谐友善等美好理想。袁霓著有诗合集《三人行》、短篇小说集《花梦》、诗文集《袁霓文集》、双语诗集《男人是一幅画》、微型小说集《失落的锁匙圈》《雅加达的圣诞夜》等。概而言之,她善用情理交融的笔调去书写印尼华人生态。既有个人的情感抒发,又有对社会的理性思考。她拥有感伤与悲悯的女性情怀,也不乏审视与批判的敏锐眼光,呈现出丰富的情感世界与广阔的本土社会图景。
一、从诗意爱情到伦理批判
袁霓的早期诗作富有青春气息,洋溢着爱情的浪漫与感伤,交融着离别、守望、苦涩、期待等各种情感。《三人行》出版于1996年,是她与茜茜丽亚、谢梦涵的诗歌合集,也是三人共同的初显峥嵘之作。印华前辈作家严唯真在《序》中对此赞誉有加:“印尼华人女诗人出诗集,在印华文学史上是首创,袁霓的诗笔直指现实的社会百态,剖析人生,她的诗善恶分明、人情味浓酣,能体味到华人的凝聚力。”[5]1-3她以诗意的想象去抒怀,以诗化之笔去涂抹本土华人的情感空间,尤其以柔情笔调吐露出印华女性的爱情观。《怀想》恰似一首缠绵的爱情小夜曲:
夜……
神秘、温柔、安详
没有着落的心
慢慢飘荡……飘荡……
收不拢的眸光
迷迷茫茫
在那遥远的“多伦多”
是否有人知道——
在这椰风蕉雨的千岛上
有个少女在引颈遥望
涂满相思的一片芭蕉叶
放在安卒的海湾
要他载上我浓浓的怀想
流向流向那遥远遥远的地方[5]79
诗人直抒胸臆,满怀相思之情,同时又以地名标示出雅加达少女对多伦多恋人的痴情。对爱情的思索,更有种岁月沉淀后的清醒。
这种爱情的浪漫格调同样表现于她的早期小说中,《花梦》是她的第一部小说集,从书名便可窥探其爱情主题。作者曾说自己爱做梦,而小说集的同名篇正是花季少女的梦,青春萌动的初恋散发着纯真无邪。“不管如何,我还是会永远怀念他,怀念他的人,他的微笑,他的沉默,也怀念那一段甜美的日子,那一段花梦——菩提花盛开,青藤缠绕,草儿青翠,黄菊摇曳,蒲公英飘飞的梦。”[6]28故事发生于雅加达,莱蒙是荷兰混血儿,虽然“我”和他错过姻缘,但是却留下难忘的回忆。从另一层面看,传统的华人家庭对异族混血儿有潜在的排斥,在华人的文化观念中,跨族群婚恋显然被视为异类,这也导致此类恋情的苦涩收场。《缘》《伞》等则有出人意料的缘分,营造出温馨而幸福的爱情。这些作品的共同点是感情的纯真,都对美好爱情执着而向往。
如果说作者在早期主要倾向于纯真爱情的书写,那么21世纪以来则在婚恋主题的转向中增添了反思的沉重感。在陈喜儒看来,她的小说多以爱情、婚姻、家庭为主题,探索爱情和生命的意义,反映印尼华人社会在传统和现代交织中的复杂心态。[7]2010年《失落的锁匙圈》面世,她勾勒出广阔的社会生活画面,其现代手法渐趋多元,这也是印华女作家的第一部微型小说集。[8]2013年,再度出版微型小说集《雅加达的圣诞夜》。小说的题材广阔,将历史的记忆与现实的人生交融,通过匠心独具的构思、巧妙睿智的结尾、灵活多变的叙事艺术淋漓展现。她一般先从爱情及婚姻写起,随后转向复杂的社会层面,最后往往以亲情篇章来结束。其中,爱情题材占比最大,在细腻手法中凸显深刻,纯真与苦涩、忠诚与背叛、虚假与真挚、辛酸与慰藉相交织。她寓理于情,描绘出真假善恶交融的“爱情辩证法”。有论者称她的爱情小说体现了现代人在浮华尘世中对真情的渴望,形成呼唤、寻觅真情的意蕴。[9]同时,她善于挖掘人物内心的细微处,对女性爱情心理的把握十分出色,对情感纠葛的呈现出神入化。
爱情有纯情之美,当然也少不了怨恨伤楚。母女爱情调包的畸恋在《圆不了的月》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呈现,小说恰似优美的散文诗,女主人公伤痛的心境又赋予景物丝丝凄美。美梦惊醒,从夕阳到黑夜,从橙红的天网到漆黑的心网,极富张力的语言与细腻的心理刻画相结合,让爱情的伪善与亲情的虚假原形毕露,倾诉心被吞噬的伤痛与梦被撕裂的悲哀。作者描写爱情,也不时掺入对社会的反思。在《半包瓜子》中,一段羞涩的回忆引出一段伤痛,纯真与执着的爱令人动容。将回忆与现实交错,历史的伤痛与青春的无虑交融。
三十多年前,他正当年少,她也正年轻。一九六六年九卅事件,苏哈托夺取旧政权,全印尼笼罩在白色恐怖中,华校被封闭,每个正当求学的孩子都彷徨无措,不知道学校会不会重新开放,不知道他们是否从此失学?爸爸妈妈为他们请来了老师补习功课,期望有一天,学校重开时,课程不会被拉得太远。这个期望后来落空了,他们那个时代的孩子,除非转读印尼校,从此没有再进学堂的机会。[10]31
这是印尼华人由威权政治所分隔两地的情缘,从雅加达到广州代表了华侨与归侨之别。从懵懂少年到已届中年,算是从爱情到友情的升华。文中以第三人称“他”“她”来叙述,并无真名实姓,实则隐喻了印尼一代华人的普遍遭遇。作者不只关心华人族群,也描写印尼本土族群。《猎物》表现原住民的爱情,丽娜“背叛”了男友,表现出爱情抉择的心酸与痛楚。从彼此相爱到大义灭亲,爱国的理智战胜个人的情爱,寄予着印尼和平稳定的社会理想。
从爱情到婚姻家庭,需要男女双方的同心协力,更需要真诚的责任心。袁霓书写婚姻故事,探讨家庭伦理,体现出一种忧患意识。“作家不仅仅对色彩斑斓的婚姻家庭悲剧进行描写和揭示,而且着力凸现作品中人物内心世界和性格的复杂性;更重要的是这些小说灌注了作家对印度尼西亚华人婚姻家庭状况的忧患与反思。”[11]307-308《短讯》《情敌》都是夫妻恩怨情仇的纠结,精妙构思与形式创新相结合,婚姻在殿堂与地狱间徘徊。夫妻间信任与沟通的缺失,给了爱情挥之不去的阴影。爱情的阴影随之催生出种种罪恶,导演出猜疑、背叛、仇恨的家庭悲剧。有的则以细腻心理抒写婚外恋的迷失,《跪》充满对负心男人的谴责。故事在雨中来去,大雨曾让他们喜结姻缘,同时也浇灭了她的梦。雨水的姻缘与崩溃,泪水的感激与忏悔,每个人的跪各具嘲讽意味。是宽恕还是无奈,是赞佩还是嘲讽?无不让人反思,伤痛真的会“春梦了无痕”吗?在这些作品中,女性往往成为受害者,作者一方面赞赏女性的勇敢离婚与坚强自立,另一方面又希望两性在精神上的理解与关爱。对婚姻的深情关注,进而深层剖析其悲剧的根源,这是对夫妻和睦的真情呼唤,而两性的和谐婚姻更需要精神上的彼此关怀。
二、亲情的自我观照与超越
印尼是礼教习俗浓厚的国度,而华人族群也有其传统的伦理准则,这种双重传统势必影响本土女性的主流价值取向。有论者讲道:“印尼华人妇女,一般都很少对传统的这套规则有反抗的激情,她们认为一切也许是天定的。男人比女人强,所以女人在心理上扫除了障碍,甘愿依附丈夫和家庭。”[12]这种说法当然有失偏颇,有着刻板的两性对立之嫌。袁霓身为印华女性,她选择的是温情而不是对抗。她重视家庭亲情,对丈夫、子女也有较强的依恋,但依恋不等于失去自我的依附,而终极追求的应是家庭和睦。她对家庭倾注的是一份炽热爱心,也是夫妻相互扶持的责任心。
从作者的自我观照来看,她的散文以记事性为主,主要取材于现实生活,并记录自己真切的所见所闻所感。因为记事性的特质,其散文具有很强的故事性。于是,她常忽略散文与小说的界限,产生“散文小说化、小说散文化”的混融。《祖母》《生命无限美好》《一盏青灯伴古佛》便可同时归入散文与小说。从另一角度看,这种体裁的混搭在印华文学作品中颇为常见,算是印华作家同质化写作趋向之一,即遵循主题的现实性。袁霓善于从现实中汲取素材,注重对华人日常生态的表现,尤其是家庭亲情的描写。1987年,她恢复写作后的第一篇文章是《把成就献给您——母亲》,对含辛茹苦的母亲,她满怀一颗感恩的心。该作也是其文集的首篇,真诚的关爱,浓郁的情义,为全书铺垫了一层温情的氛围。其实,早在20世纪70年代,她就具有温情的关怀意识,有对癌症病人的怜悯,有尊老爱幼的传统美德,也有童年的美好记忆。其中,《祖母》一文声情并茂,文中不时穿插俗语、民谣,富有天真童趣与生活气息。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人生阅历的丰富,她的关怀面更趋广泛,有对珍贵友情的赞扬,有对职场的感怀,还有佛教的超然洒脱。
作者以精细之笔勾勒亲情的酸甜苦辣,其亲情题材浓郁厚重,并不局限于单一亲情,而是将其放到印尼社会背景中予以铺展。有家庭辛酸的情感抒发,有现实社会的伤痛苦难,也有人生命运的清醒反思。她关注沉重的社会敏感问题,敢于触摸历史伤痕,剖析下层人的苦难根源,进而反思社会的弊病。《达尔梭的遭遇》倾吐的便是经济危机、排华暴乱、国家动荡给人精神与肉体的多重创伤。
他忽然明白政治的残忍,上层人物玩弄的政治牺牲品是什么都不懂的下层人民。他不知道那些死去的人都是些什么人,也许是屋主,也许是来抢劫的那些暴民,但是,他深深明白一点,政治的混乱,是国家的苦难,更是他这一类下层人物的苦难。[13]70
建筑工人达尔梭是普通民众中的一员,当看到1998年“五月暴乱”时被烧毁店屋里的骷髅惨状,他感到震惊而痛心。他的家庭生计因国家动乱而面临窘境,他的彻悟正是本土下层民众的呐喊心声,而集体的伤痕记忆也被一再唤起。袁霓在亲情书写中融入族群对照,流露出超越华人族群的关怀意识。
对华人家庭,她在同情之中又有批判。《求神》在浓厚的生活情趣与华人传统习俗中展开,在雅加达著名的金德院,拜佛的轻松与阿婆伤痛的沉重对比,充满对人生的无奈慨叹。命运的凄楚,求神的苦衷,恰是尊老养老的社会问题,对华人抛弃父母亲情之举暗含批评。对于原住民,袁霓揭露恶习之中,也不乏同情。《母亲》讲述梦境与现实的惊悚,惊悚之中加入玄幻,孩子的梦与母亲的驱魔,儿子精神分裂变成吃人恶魔。叙述者对人物心理进行了深层透视,以母亲的愁苦、担忧、隐痛、疑惑、不安、释然的心理流动贯穿故事。比起纯粹的华人、原住民的单一族群故事,不同族群间的交流显得更为重要。《叔公》刻画了原住民的浪子回头,叔公名叫“江湖”,是华人家庭领养的原住民孩子。他年轻时痞性十足、无恶不作,后来转性变得富有义气。在印尼,华人与原住民之间难免有些抵触情绪,华人的自尊优越感往往看低异族,原住民则排斥华人是寄居自己国家的“外国人”。随着相互的交流、理解与信任,彼此间多了尊重,由此也趋向亲情式的族群和谐。
在亲情题材中,作者也深度雕琢出本土底层民众的苦涩和艰辛的生命历程。《祖母口中的祖父》宛如一曲清新的笛韵,遥远温馨的回忆悠扬而至。祖父勤劳俭朴、事业有成却壮年早逝,祖母的辛酸委屈在字里行间倾诉,却又洋溢着往昔的幸福和骄傲。祖父跨山涉水、漂泊南洋的传奇印证了离散华人的艰辛创业史。祖母则代表了中国传统妇女的典型,充满母性的亲情包容,更有坚韧持家的自立性,而海外华裔族群的繁衍生息无疑正得益于此。《上报》则是对底层原住民的苦难缩影,小说将现实与回忆交叠,展现法蒂玛一天的盼望等待。她一生有过四个丈夫、十二个子女,最后却连唯一的女儿也要失去了。女儿去沙特阿拉伯做女佣,因遭受虐待而犯上精神病,这是印尼外劳的悲情写照。心理透视法表现了母亲的无望等待,最后在绝望中眺望,冷静叙述浓缩了人生的悲苦。在这一对母女的苦难背后,其实也影射了印尼底层妇女的恶劣处境。由于原住民生活的相对落后,原住民妇女的思想更为保守,其遭际比华人妇女更为艰辛,而女性的命运及其地位改变显然需要更多的社会参与以唤醒群体的觉悟。对原住民的传统女性而言,在男权束缚与宗教制约下,女性意识的成长显然还有漫长的路要走。
三、社会生态的族群言说
袁霓具有浓重的现实情怀,不仅观照华人生存状态及心理,也对印尼社会现实、族群和谐以及下层小人物进行多重审视。作者描写的是华人族群的个体,其实也是对华裔、侨生、归侨群体的代言。在散文的日常生活记述中,她不只是个体言说,对华人族群的群体生态也有深入的观察。在华人群体中,从血统分,有纯正的华裔,也有混血的侨生;从地缘看,有本土华人,也有北归中国的华侨。《片片竹叶青》借粽子品味亲情,竹叶裹糯米含着长辈的爱心,而香叶裹白米则是风俗的变迁与同化。雅加达华人的“娘惹粽”口味已与祖宗秘方大相径庭,他们虽然保留传统的端午节习俗,但是孩子们却不了解纪念屈原的来龙去脉,隐含着华人文化在本土的失落。在印华几代人身上,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已走向本土变异。[14]《温家的婚礼》特别关注印华侨生群体,颇为细致地描绘了丹格朗小城的侨生婚俗。据说,他们的祖先在明末清初避祸南来,虽早已同化于当地民族,但依旧持守唐山祖宗的传统习俗。
我看着他,心里不胜嘘唏。住在大城市里的华人,随着西方文化的入侵,虽然会写会看中文字,但是多数都不想再保留华文名,而宁愿取英文名或印尼名。可是住在偏僻乡下的这一群传了一代又一代的华裔,不会看、不会写,甚至不会讲华语,他们的皮肤因为种田时风吹日晒而黝黑,他们和原住民通婚,脸型已经被同化到大概只有在眼睛部位才能看出一点华人的影子,但仍然一代又一代地沿袭祖宗留下来的风俗,虽然他们不明白那都是什么意思。[15]32
侨生,此处特指华人男子与原住民妇女通婚的后裔。侨生是华印两族的共同血脉,更是文化混血的典型,娘惹纱笼、Cokek舞蹈、贴对联、凤冠霞帔、对襟唐装等所隐含的是中华文化与本土习俗的多元交融。
印尼由多元族群组成,除了华人群体,作者也接触到诸多原住民。此类故事勾勒出族群和睦的美好图景。《无名英雄》即是对伯苏嘉迪救人义举的赞美,他住在雅加达渣望芝里翁河畔的违章建筑中,当洪水泛滥,平凡的城市贫民却表现出无私无畏的英雄气魄。伯阿宗与伯苏嘉迪,都是信仰伊斯兰教的原住民,从“解禁节”“真主”等细节便可知晓。他们是善良的穆斯林,虽然身处社会的贫下层,但是同华人雇主之间却毫无隔阂。作者还表现出华人的民间团体对疾苦贫民的关怀,对人民幸福、族群和谐、国家安定充满期望。当前,印尼华人习惯称其他族群为“友族”“兄弟族”,而很少用“异族”“土著民族”等称呼,其实这是一种友善的族群平等意识。她书写族群题材,并没有鼓吹迎合的矫揉造作,而是水到渠成的坦荡情怀。人性的真善美超越了种族身份的界限,彼此之间达致平等、尊重、理解、信任、赞赏与关爱,表征着族群和谐的理想图景。
在诗歌创作中,她寄心于身边的人情世事,不乏浓郁的感性基调,又以理性的思维去审视。这种悲天悯人的视角,有宽泛的关爱之情,也有真切的本土意识。诗人身处复杂的商场,对人性的虚伪有深刻体会,满怀批判与反思。她广泛关注印尼的社会生态,《最后一滴鳄鱼泪》从皮革制品写到眼前的石鳄鱼,又联想过去的鳄鱼园及将来的大商场,所感怀的是人类文明对自然生态的破坏,这是环保意识的突出体现。本土关怀意识在《我曾经是一棵大树》与《奥奇》两首诗中更为明显,二者都采用借物喻人的手法。前者以“大树”引发参观养老院的感触,老人们有难以抚慰的孤寂,“宁愿被雕成不讲话的木偶/放我在家里一个不被注意的角落/也比被抛弃来的好受”;后者以“奥奇(Ojek,载人三轮车)”承载车夫的辛酸,“沉思、喘息、挣扎、无奈、叹息、哀怨”传达出生命的苦痛。诗人关心雅加达的老人问题及贫民窘境,更深层则是对印尼弱势群体的关爱。此外,诗人以象征隐喻抒发心志,具有梦幻性与模糊性的诗便属此类。《男人是一幅画》是双语诗集,也是印尼语文坛与华文文坛双向交流的催生物。诗人向印尼主流文坛袒露心声,对敏感问题的揭露表现出无畏的气魄。她以同名诗作为书名,或许别有寓意,“纵横交错的创伤”是气势磅礴的油画,而男人的坚韧也可视为华人族群的品格象征。同样,《寄生藤》《掌纹》都是对离散族群的命运思索,永恒的身份象征让族群遭受不尽的苦难,隐寓了华人族群在本土的悲惨遭际。与之相比,《气氛》与《忌辰》则是对更为血腥的排华暴乱的伤痕书写,前者描绘暴乱前夕“整个社会已经酝酿着一种让人不安的气氛”,后者满怀悲情地悼念那些勇敢的英魂与枉死的冤灵。《气氛》写于1998年3月12日,不久“黑色五月”便笼罩着华人的家园。
一只战栗的小鹿
穿过利如刀削的流言
在草木都已变兵的
空间里跳跃
避过蛇的影子
却又担心杯里的弓
是埋伏的定时炸弹
随时爆炸
也许早就爆炸了
看不到战场
却有战争
听不到枪声
却有血流[16]104
每当印尼发生社会暴乱时,华人就如同被猎捕的无辜“小鹿”。在恐惧与忧患的气氛围困下,一切都变得风声鹤唳、草木皆兵,而一触即发的血腥场景则成为永不消弭的创伤梦魇。袁霓描写华人的族群境遇,并不是“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式的复仇心态,而是要寻求华人族群的合理生存空间。《凝眸处》是该诗集的终篇,她以“椰林”“大海、波浪”的远景隐示理想的升起。理想应该有特殊的意涵,小到自我的追求,大到华人族群的期盼,再到人类的和谐,不同的视角则有不同的阐释。诗人凝眸远眺,其理想追求给当地华人以极大的鼓舞。
在小说中,袁霓面对纷杂的社会,或点名道理,或引人深思,切中肯綮地雕刻善恶众生相,一针见血地抨击社会弊病。她以警世之言惩恶扬善,不乏悲天悯人之心;以幻境之语讽喻现实,足见济世救人之切。她善于将上层社会的伪善与下层社会的辛酸相对比,善于以小题材见大道理,善用讽喻手法发人深省。赵朕认为:“她不再满足于从熟悉的环境中发掘创作题材,以抒发自己的所感所悟所怀所念,而是以积极的姿态介入社会,讴歌真善美,鞭挞假丑恶,由此不难看出她旨在匡正扶危、涤荡世俗的努力。”[17]《丰收》的喜悦让冯子诞“一夜之间变成了一个响当当的名人”,成名之后却为玉米大丰收所累,省长夫人秘书、警长夫人、人协代表、乡长纷纷来电讨要玉米,官僚的惠顾让丰收成为苦恼。结尾的“因为丰收”四字发人深省,“丰收大赚钱”变成幻想,最后落得不想搞农业了。小说通过丰收的苦涩,成名后的疲于应酬,再现了一场民与官的“暗战”,而官员的腐败由此可见一斑。
作者长期生活于雅加达,对城市生态有着细致观察,因此深刻展现出大都市的复杂多面。《“爱她死”后的梦坠》表现推销员的都市梦,李有恒的爱情幻灭也是“首都碰运气”的梦想幻灭。故事明线是爱情的追求,实则揭露城市的阴暗面。
他住在一个三教九流聚集之地,聚赌的有之,老千有之,夜蝴蝶也有之,好人家也多;三层豪华住家旁边是摇摇欲坠的破屋,印尼人华人毗邻而居,富人穷人共用一条坎坷不平、坑坑洞洞的路,整个区域卖小食的到处都是,垃圾乱丢,不通的水沟上面浮着丢弃的不溶的塑胶袋,原本就黑的脏水变得越来越黑,走过去有一股垃圾发霉的臭味……[18]123-124
雅加达是龙蛇混杂的大都市,贫富差距悬殊,环境污染严重,社会秩序混乱。最后,主人公选择逃离肮脏的城市陷阱,重回自然纯朴的农村,这种城市的灰暗场景无疑是批判性的。《雅加达的圣诞夜》则双线并行,一条是爱情婚姻的插曲,一条是对宗教和谐、信仰自由的期盼。当宗教极端分子疯狂袭击基督教徒时,连正在教堂里举行结婚仪式的新人也不能幸免,歹徒们竟堂而皇之地公然抢走了结婚戒指。这里的“新人”暗指华人基督徒,新娘在幸福时刻突遭洗劫,其惊恐之余的和平呼唤也就更具人性的冲击力。在自称宗教多元自由的国度里,圣诞夜就像赶赴战场,随时都会有生命危险。基督徒如同义无反顾的勇士,而宗教极端分子则变成嗜血的刽子手,其潜在的宗教关怀与宗教批判不言而喻。排华暴乱、宗教纷争留给印尼华人太多的恐惧与伤痛,主人公在回味友情中祈求导人向善的宗教融合。此外,在诸多篇章中,作者无不充满对社会动乱、不良风气的批判与思考。当然,她对华人族群也痛下针砭,历史的惨痛与时下的笙歌对比,人们对名利的迷恋令人瞠目,也暗讽华人对排华事件的遗忘。华印两族在同一片土地上生存繁衍,华人族群的南洋创业之路充满坎坷,而下层原住民的生活也遍布辛酸苦楚。她不断进行族群书写,展现出一种超越种族、关怀本土的人道胸怀。
四、结语
袁霓是印尼较为多产的华文女作家,其创作题材包罗万象,既有贴近本土气息的民众生活呈现,又有对人类生存状态的跨族群、跨国界的反思。她尤其善于调度爱情、亲情及社会主题,爱情恰如复调音乐,多声共奏成爱的交响乐;亲情宛若生活佐料,搅拌出酸甜苦辣的五味瓶;社会好似炽热熔炉,铸炼涤荡着心灵的多棱镜。[19]她对假恶丑的披露让人略感低沉,对真善美的探讨令人重拾温情。三大主题交相辉映,在对人生境遇与人性善恶的普遍审视中建构出印尼华人复杂的本土面向。同时,她对作品的语言及形式要求严谨。她的诗歌情感浓烈,既有优美的语言与浪漫的情怀,又有素朴的语言与阅世的沉郁。她的散文常伴温情,以女性的柔情去观察,以真诚的胸怀去感悟。她的小说格调多元,自然流畅的叙事中略显沉重,细腻含蓄的语言中突显质朴,跌宕起伏的情节中蕴蓄深刻。总体而言,其创作具有情理兼备的特质,以情见长却又情中寓理、理中含情。既有个体心路历程的内在探视,又有关怀社会疾苦的外在视野。对个人情感的深入,突显出女性的细腻,对社会人生问题也有深邃的审视。社会人生的苦涩,敏锐的心灵视角,精雕细刻的笔法,都令人回味反思。她以开阔的视野着笔,以历史记忆为底色,以社会现实为主色调,以人生苦难为配色,以悲天悯人的情怀勾描出广博的印尼华人生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