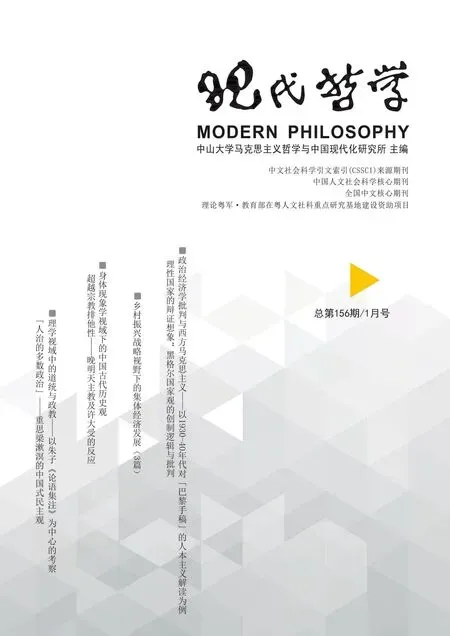最后的神的面目
朱清华
海德格尔后期关于最后的神和诸神的论述引起了广泛兴趣,一方面因其深奥难解,另一方面因其在海德格尔后期思想中占了极为重要的位置。研究者都试图透过海德格尔艰深的描述来把握海德格尔所说的神是什么及其思想意义。海德格尔协会(Martin Heidegger Gesellschaft)2016年年会(奥地利维也纳大学)所讨论的主题之一就是海德格尔与神学的关系,在会上Ingeborg Schüβler、Istvn M. Fehér、Günter Pöltner、Helmuth Vetter等学者从不同角度论述了海德格尔的神。*其中Ingeborg Schüβler教授的报告《观看、全能与暗示:海德格尔论上帝问题》论述了海德格尔的最后的神和上帝(作为存在者的最高根据)、基督教的创世神的对抗。(参见王宏健:《2016年海德格尔协会年会纪要》,首发于公众号“大道不离万有”。)在关于海德格尔的“神”的研究文献中,有人强调海德格尔的神的非神学意义和神对此在的促成作用。例如,Figal强调《哲学论稿》和《存在与时间》的内容承接和联系,提出最后的神是给出理解者,是此在和存在的时间-空间,通过神,此在在自由中成为自身*Günter Figal, “Forgetfulness of God: Concerning the Center of Heidegger’s Contributions to Philosophy”, in Companion to Heidegger’s Contributions to Philosophy, C.E.Scott, S.M. Schoenbohm, D. Vallega-Neu & A.Vallega eds.,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01, p.206.;认为最后的神不会以任何个别的形式显示自身,不会成为一个宗教信仰的中心。Crownfield也强调神在自我-决断中的位置,神是超出自我决断的赠予和要求。*David Crownfield, “The Last God”, in Companion to Heidegger’s Contributions to Philosophy, pp.213-228.Polt认为海德格尔提出的诸神以及最后的神是“民族性的来源”。*[美]波尔特:《存在的急迫》,张志和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年,第305页。他们都淡化了最后的神和诸神的神学意义,而强调在提出众神和最后的神之际,此在的成己就有了一个上限,或者说获得了一个来自超越的力量的规定,即它的成己之路不再只靠自己的力量,还有一个在上的超越的力量可以诉求。孙周兴的论述大概可以归为此类。*孙周兴:《后神学的神思——海德格尔〈哲学论稿〉中的上帝问题》,《世界哲学》2010年第3期,第44—54页。有的学者则强调最后的神的神学特征,例如Seidel认为海德格尔的最后的神出自谢林“最后的神”,甚至是将谢林思想转化的结果。*Seidel, “Heidegger’s Last God and the Schelling Connection”, in Laval Théologique et Philosophique 55, No.1, February 1999, pp.85-98.林子淳认同Seidel的观点,认为海德格尔深受谢林神学影响,最后之神可能反映了海德格尔的基督论,所担负的是“道成肉身”教义,即最后的神是存有的本现;但他也指出不能直接将二者等同,因为海德格尔最后的神的提出,是为了进入另一个开端服务。*林子淳:《“最后之神”即海德格尔的基督?》,《世界哲学》2015年第1期,第62—71页。另外,Paola-Ludovica*Coriando, Paola-Ludovica, Der letzte Gott als Anfang: Zur ab-gründigen Zeit-Räumlichkeit des übergangs in Heideggers “Beiträge zur Philosophie (Vom Ereignis)”, Munich: Wilhelm Fink, 1998.、D. Vallega-Neu*D. Vallega-Neu, Heidegger’s Contributions to Philosophy: An Introducti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03.、Richard Rojcewicz*Richard Rojcewicz, The Gods and Technology-A Reading of Heidegger,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Albany, 2006.等都对海德格尔的神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那么,对海德格尔的“神”这个异常晦涩的概念应当如何理解?海德格尔的“神”是什么?神和人是一种什么关系?
一、最后的神不是基督教的上帝
海德格尔所说的神因其难以正面描述,往往只能从否定方面被把握,所以他关于神的观点常常被称为“否定神学”*马利翁(J.L.Marion)也将海德格尔放在狄奥尼索斯-埃克哈特大师神秘主义否定神学传统中。关于否定神学,参见Flight of the Gods-Philosophical Perspectives on Negative Theology, eds. Ilse N.Bulhof and Laurens ten Kate, Fordham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2000.。本文也首先从否定方面对海德格尔的神进行论述。海德格尔所说的最后的神显然不是基督教的上帝。《哲学论稿》对“最后的神”最先表明的,就是“最后的神完全不同于曾经的那些神,尤其是基督教的上帝”*Martin Heidegger, Beiträge zur Philosophie (Vom Ereignis)(GA65), Vittorio Klostermann, Frankfurt am Main, 1989. S.403.,这就开门见山地把最后的神和基督教上帝区别开了。上帝已死,根本无力承担海德格尔赋予神的任务。他在多处文本反复批评包含在形而上学史中的基督教的上帝。在他看来,基督教的“上帝之死”是必然结局,是形而上学史发展的结果。传统的形而上学同时是存在论、神学、逻辑学*参见[德]海德格尔:《形而上学的存在-神-逻辑学机制》《同一与差异》,孙周兴、陈小文、余明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Die Onto-theo-logische Verfassung der Metaphysik(1956/57)”, Martin Heidegger, Identität und Differenz, Vittorio Klostermann, Frankfurt am Main, 2006.,这三者是一体的。由于形而上学首先是存在论,它将存在作为奠基性的观念,对存在者的存在的论述有两个向度:一方面它是那最先的、最普遍的,另一方面它是最高的、最终的。从第一方面来说,存在就是逻辑学的最根本原则和论证的出发点;从第二方面来说,存在是形而上学上的最高存在者。上帝同时作为最高的和最终的存在者、根据以及最终因、自因,所以在形而上学历史中,存在论、逻辑学与神学不相分离。但海德格尔认为,形而上学忽略了存在论的差异,所探讨的主导问题是“什么是存在者”,而没有思考存在自身。*Martin Heidegger, Beiträge zur Philosophie (Vom Ereignis)(GA65), S.6, 12, etc.上帝被分解(Austrag)出来,成为存在论-神学-逻辑学的最终因的和最高根据,是一切存在者的存在根据,那祂自己也不免成为一个特别的存在者。这个贯穿形而上学史的上帝见证了形而上学的兴衰,并随着形而上学走向终结,而被宣称“上帝死了”。 在海德格尔看来,上帝之死并非人们经常认为的那样,是无神论以及虚无主义的开始,反倒是虚无主义的自我呈现。形而上学的本质就是虚无主义的,它既不思存在,也无诸神临在。这种虚无主义一向被基督教的上帝所掩盖,而上帝之死将这种虚无展示出来。海德格尔甚至提出,上帝不是刚刚才死了、死于现代,而是两千年来神都已经不在场。虚无主义是欧洲的历史基本运动,也是被欧洲所决定的世界历史的基本运动,是西方民族命运的不为人所知的推动力。*[德]海德格尔:《尼采的话“上帝死了”》,《林中路》,孙周兴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第232、234页。以虚无主义为其本质的形而上学注定发生超感性世界的崩塌,包括上帝、道德法则、理性权威、文明、文化等的崩塌。对基督教上帝的信仰丧失,只是其中的一个结果。
近代以来,上帝和教会的权威被“理性”和“良知”代替,超感性的领域被“历史进步”代替,永恒幸福的彼岸目标被尘世幸福代替,似乎一种新的思想模式已取代了旧的神创论模式,但实际上这一切都没有脱出旧有的世界构造和存在者的等级模式,只不过换了名称而已。海德格尔指出这个旧的模式是在形而上学的开端处早就被柏拉图所确立的泛希腊-犹太世界基本结构。*[德]海德格尔:《尼采的话“上帝死了”》,《林中路》,孙周兴译,第234页。这个换汤不换药的架构,虽然到了尼采才喊出“上帝死了”的哀鸣,实际从开始就已经离弃了诸神,离弃了存在。在尼采那里,“上帝”指的是基督教的上帝,而“上帝死了”是说那个超感性的、约束性的世界丧失了,柏拉图以来形而上学的理念世界不再有效了。但是海德格尔认为,事实上,形而上学的“上帝”的位置没有阙如,而是被“主体”所替代。形而上学的那种神学-存在论-逻辑学结构也没有随着上帝之死而丧失。主体性的本质规定是“表象着的主体保证其自身,并且始终也保证它所表象的东西本身”*[德]海德格尔:《尼采的话“上帝死了”》,《林中路》,孙周兴译,第257页。,从而真理成了确定性,确定性具有可靠性的特征。这种可靠性靠数学观念的清晰性、明确性来保证。因此,数学和计算成为真理的衡量标准。在以计算和机巧(Machenschaft)为特征的现代,真理不复是存在的真理。海德格尔断言:还有几百年机巧将会洗劫地球,使之荒芜。*Martin Heidegger, Beiträge zur Philosophie (Vom Ereignis) (GA65), S.408-409.
海德格尔认为,西方思想的崩塌是存在离弃的结果,其表现就是诸神的逃离,在现代这种从存在的连根拔起却被“人的重现发现”所掩盖*Martin Heidegger, Beiträge zur Philosophie (Vom Ereignis) (GA65), S.118,119.。人作为主体是脱离上帝的控制而自我裁决的“自由人”,通过科技的“进步”,人的控制力变得强。但人自身却是大众化的、无根的,松松垮垮,精神贫困。人无能于思考,无能于真理。所谓“进步”只是存在的离弃的加深和增长。
二、人的本质和神性
诸神逃逸被海德格尔看作是存在离弃的标志,人也因此失去根基。问题是:为什么人必定需要神?在人的生存中,神有怎样的位置?在海德格尔那里,存在的本现与人的本质的确立跟神的召唤密切关联。他一再指出传统对人的定义(即人是理性动物)是一个谬误,原因之一是这个定义将人规定为某种实体,赋予人既定的本性。而他认为人除了生存外,没有其他本质。人是自由的,自由是一切根据的根据,由此可以说人是无根据的(Abgrund)。*Heidegger, “Vom Wesen des Grundes” , in Wegmarken, Vittorio Klostermann, Frankfurt am Main, 1976, S.174. [德]海德格尔:《论根据的本质》,《海德格尔选集》,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第207页。不过,展露在此在面前的是命运带给它的、它作为被抛的东西的那些可能性。这是有限的选择可能性,而非萨特所说无限的可能性。不能将人归为理性动物的另一个原因是:在从动物出发对人进行规定时,在范围上已经画地自限,将人跟动物划归一类,然后将人再区别出来,对人的研究也最终归为生物学、人类学的范围。而在他看来,虽然人和动物在肉体上最接近,但从存在上人更接近于神。*Martin Heidegger, “Brief über den Humanismus”, in Wegmarken, S.326.神一直和人的“本真状态”或“人的本质”的奠基关联在一起。神就在存在的真理的奠基中运作,作为召唤者,作为逝经(Vorbeigang)者。人和神的本现都来自存在自身,来自存在的真理,所以必须从人-神关系而非人-动物关系来规定人。
在海德格尔那里,人的本质同“家”和“家乡”有难以割舍的联系,一方面是此在本质的无家可归状态,另一方面又要返乡和回家。《存在与时间》强调人本质上是无家可归的。在家状态(Zuhause-sein)只是常人在平均日常状态的安然自信,沉沦于世界中如同在家一样。畏将这种假象粉碎,此在失去熟悉的“家”,顿觉骇异惊恐,流离失所。人在畏中骇异于这种不在家(Un-zuhause)*Martin Heidegger, Sein und Zeit, Tuebingen: Max Niemeyer Verlag, 1960. S.188;[德]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庆节合译,北京:三联书店,1999年,第217页。,这是寻求本真存在的开端。此在更加源始的现象是无家可归状态(Unheimlichkeit),而非在家的平安宁静状态。在家状态反而是无家可归的一种变式。因而,在沉沦日常操劳的在家状态中,总有无家可归状态在威胁着,它在最无关痛痒的处境中升起。此在在操劳中总是力图逃避这个无家可归状态,逃进常人状态中。而畏总是要打破它的宁静,将带它到自己面前。*Martin Heidegger, Sein und Zeit, S.189;[德]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庆节合译,第218页。在对无家可归的强调中,海德格尔试图说明人的本质和人的生存不受任何预定的实体决定。人是自由的,虽然这种自由令人惊怖,如同遭到流放。不过指出人本质的无家可归状态并非最终目标,海德格尔的目的是要为人找到真正的家,即人的立足之处。“只有那种存在者,它作为将来的(zukünftiges),也同等源始地是曾在的(gewesend),才能把继承下来的可能性承传给它自己之际接纳本己的被抛状态,为‘它的时代’而瞬间存在(augenblicklich sein für ‘seine Zeit’)。”*Martin Heidegger, Sein und Zeit, S.385;[德]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庆节合译,第435—436年。此在的立足点就是其被抛其中的历史(Geschichte),这里的历史主要指涉民族历史。此在通过对历史之曾在的重演,在决心中传承下、选择出那些使得本真生存可能的可能性,也就是将自己交托给了自己,从而拥有他本己的命运。此在决断之根基就来自这里。在这个本质立足点,人不再如同浮萍一样处处是家而处处不是家,不再流转于常人。
海德格尔在后期与前期一样仍讨论“无家可归状态”,但是从存在历史角度来谈的。自第一个开端之后,存在离弃日益深重,上帝之死更敞明了那种虚无。思想在形而上学之存在遗忘中挣扎,在机巧为本质的技术时代,已经面临极大的危险和困境。在这个时代,诸神逃逸。处于存在离弃这种最大的困境(die Not)中,是最深重的无家可归。在作为存在离弃的拒绝中,此-在(Da-sein)被迫回到自身,接受自己在存在历史中的天命。因此,后期海德格尔除了揭示人的日益深重的无家可归状态,还强调“还乡”,并且显然更关注的问题是何处是人的“家乡”、人如何“还乡”。海德格尔说需要回到西方的天命去找到人的本质。“人的未来的天命就在于,人要找到存在的真理中去而且要走到找存在的真理的路上去。”*[德]海德格尔:《关于人道主义的书信》,《海德格尔选集》,第384页。所谓西方的天命,海德格尔指的是西方在存在历史中现在所处的存在遗忘状态和将来有可能的承担起人类克服存在离弃,过渡到另外的开端的使命。这个使命尤其是荷尔德林的“同胞们”德国人的,“以便德国人从命定的归属于各民族的关系中与各民族一同变成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德]海德格尔:《关于人道主义的书信》,《海德格尔选集》,第382页。。人的天命便是在存在的真理中驻足,从存在历史而言,人的驻足之处是存在的天命,回归到存在的近处,就是回到家乡。人真正的本质或者本真性,就是进入存在的真理,看护存在。除此之外人无本质,是一无所有的赤贫。*[德]海德格尔:《关于人道主义的书信》,《海德格尔选集》,第385页。
那么,人从何处获得进入存在的真理的力量?易言之,人成其本质的尺度是什么?在机巧的时代,尺度败坏为数学和数字的度量。一切存在者之存在皆从数学获得其存在性。一切对象皆从数字被表象。人自身作为统治者、支配者自身却失去了尺度,唯有从尼采所依据的“动物性”或黑格尔所依据的“理性-意志”来规定和衡量。海德格尔认为,真正的尺度是诗人荷尔德林所把捉到的,乃是从神而来的尺度。“神本是人的尺度。”*[德]海德格尔:《人诗意地栖居》,《海德格尔选集》,第472页。神能够作为尺度,乃因神源自存在,出自居有(Ereignis)。神有其神圣性和神秘性。神作为尺度,意思是这个不可被认识者保持为不可被认识者,处于一种揭露活动中,让被遮蔽者看到,但不是作为完全的、脱离了遮蔽的东西被看到,而是将其保护在遮蔽之中同时让人看到。神在天空中,而人在大地上,同时在天空之下。在海德格尔看来,这不仅仅是人的地理位置,而且是人本质的维度——人需要从大地和天空同时获得其存在尺度。作为在大地上的,人是有死者,人承担起他的死亡;作为在天空下的,人从神获得尺度。*[德]海德格尔:《人诗意地栖居》,《海德格尔选集》,第471页。
神是那在亲熟的东西中陌生的东西,也是诗人在作诗中所召唤的东西。*[德]海德格尔:《人诗意地栖居》,《海德格尔选集》,第476页。诗人能够从神获取尺度,他的作诗活动就是从神“采取尺度”,诗人借神性度量自身。*[德]海德格尔:《人诗意地栖居》,《海德格尔选集》,第472页。海德格尔所说的回到家乡,承担起被抛状况,或承担起存在离弃的困境,都是指人获得本质,获得其命运,为命运所把握,或者说被存在所派遣。只有能胜任这种困境的人才有命运,才能经验到作为命运的存在。命运是半神的存有(das Seyn der Halbgötter)。*Martin Heidegger, Hölderlins Hymnen “Germanien” und “Der Rhein”(GA39), Vittorio Klostermann, Frankfurt am Main, 1999. S.179.海德格尔所谓的只有诗人能够“采取尺度/丈量尺寸”,就跟他说诗人是“半神”一样。半神的内在特征是绽出地进入神和人的存有的中间,嵌回到家乡大地,解放其中统治性的力量。所谓半神不是神,也不是完全的人,海德格尔称之为超人的存有(Das übermenschliche Seyn),其本质是承担起我们的被抛状况,揭示出困境,并胜任这种困境。在这个承担(Leiden)中,存在作为命运被敞开。*Martin Heidegger, Hölderlins Hymnen “Germanien” und “Der Rhein”(GA39), S.175.半神作为海德格尔的超人,正是那些以作诗、运思等方式打开澄明之境的人。在他看来,人需要先被存在抛进存在的真理,绽出地生存才有可能有最后的神和诸神进入澄明,但并不能保证他们会出现。唯有等待最后的神的召唤和拯救,才能摆脱存在遗忘状态,回到家乡。总之,神是人得以被派送存在的命运的中介,人藉由神而成为此-在,即存在的真理在此本现。
三、存在历史和神的面目

神的形象既然是不可视见的神秘,其降临就不会是跟人面面相觑的直视。海德格尔用逝经(Vorbeigang)来描述神的到场,提出逝经是诸神在场状态的方式(das Vorbeigehen ist die Art der Anwesenheit der Götter)*Martin Heidegger, Hölderlins Hymnen “Germanien” und “Der Rhein” (Winter semester 1934/35), S.111.;同时用诸神的逃离或到来(die Flucht oder die Ankunft der Götter)这样的说法;称最后的神在暗示中本现(Wesung im Wink)*Martin Heidegger, Parmenides(GA54), S.12,409.,最后的神的“最伟大的接近”作为拒绝(Verweigerung)。这些说法的共同之处是,神的显现不是现成的在场。波尔特(Polt)指出,“逝经”这种说法和尼采有关,即“查拉斯图特拉逝经我这里”;但其更深来源是旧约《圣经》,即“神在其荣光中‘逝经’摩西,但摩西不能直接看神的面容,因为那意味着死亡”*[美]波尔特:《存在的急迫——论海德格尔的〈对哲学的献文〉》,张志和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年,第301页。,同样神伴着烈风、地震和火逝经了以利亚。波尔特正确地指出,上帝间接地展示自身,在人和神之间有某种接触,但我们永远无法表象或者考察他。海德格尔的神跟上帝一样地逝经人,并不表明他的神是基督教的上帝,不过他提到在源始的犹太教中和耶稣的布道中的神是他所说的神的“曾在者”(das Gewesene)*Martin Heidegger, “Das Ding”, in Vortr?ge und Aufs?tze (GA7), ed. F.-W. von Herrmann, Vittorio Klostermann, Frankfurt am Main, 2000, S.185.。
海德格尔既用神(der Gott)也用诸神(die Götter),还用最后的神(der letzte Gott)这样的表达方式,在数量方面,既有单数也有复数。他提出神的数量并不是个问题,无论是单数的神还是复数的诸神,都不能做量化的理解。用单数的形式,神用以表述海德格尔所说的神性,所以他也用神圣者(das Göttliche)、神性的(das Götthafte)来称他所说的神*在Parmenides(GA54)中多有这样的用法。;而他用复数对应的是“基础与去基础的内在丰富性”*Martin Heidegger, Beiträge zur Philosophie(Vom Ereignis)(GA65), S.411.。最后的神和诸神虽然在神性上没有差别,但海德格尔按照存在历史给了属于他们的不同的历史阶段*Martin Heidegger, Über den Anfang (GA70), ed. F.-W. von Herrmann, Vittorio Klostermann. Frankfurt am Main,2005, S.65.。按照他的存在历史,第一个开端及其作为形而上学的历史已经到达终结,必将开启另一个开端。现在所处的是过渡阶段,即对形而上学的克服和向另外一个开端跳跃的阶段。第一个开端处有希腊的诸神。伴随着形而上学的历史的开展并走向终结,诸神逃逸,随之而来的是无神状态(Götterlosigkeit)。无神状态并不值得人欢欣鼓舞,也不是人摆脱神权统治后获得自由,而是人已经进入了最深重的存在离弃状态,有待开启存在历史的另一个开端。在跳跃入另一个开端之前的过渡阶段中,只有最后的神的召唤让人出离存在遗忘的困境。海德格尔称,最后的神是为了存有之本质的发生而来,祂开端性地本现作为开端的存有,而最后的神的召唤是“居有活动神秘的来袭和逃离”(Anfal und Ausbleib)*Heidegger, Beiträge zur Philosophie(Vom Ereignis)(GA65), S.406, 408.。由于最后的神产生自对真理的存有(Seyn der Wahrheit)的拥有,所以最后的神也是开端的神*Martin Heidegger, Über den Anfang (GA70), S.131.,祂唤起人向着另外一个开端。基督教因为拒绝了存在而拒绝了神,而海德格尔的最后的神丢弃了形而上学的造物主本质,祂却因此更具神性。*Martin Heidegger, Über den Anfang (GA70), S.132.最后的神在过渡时期中是独一无二的,具有唯一性,因为这是存有通过最后的神而有“独一无二的切近”*Martin Heidegger, Beiträge zur Philosophie(Vom Ereignis)(GA65), S.412.。而在另一个开端中,海德格尔又用诸神来表述神,“诸神被分配进神性中,人被分配进人性中”*Martin Heidegger, Über den Anfang(GA70), S.157.。在过渡阶段,那作为神性的曾在者,无论是在希腊人那里的诸神还是在预言的犹太教、耶稣布道中的神,虽然已经不再(Nicht-mehr)在场,但是同时也是祂们的神性之“未被耗尽的本质的隐蔽的到来”的一种尚未(Noch-nicht)。*Martin Heidegger, “Das Ding”, in Vorträge und Aufsätze (GA7), S.185.如果是这样,那么对曾在的神的重演就是对未来的神的接近。
四、神和半神
海德格尔所说的神不是存有(das Seyn),不是某种存在者,也不是神化的人。*Vallega-Neu也强调这一点。参见[美]瓦莱加-诺伊:《海德格尔〈哲学献文〉导论》,李强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31页。神显然不是任何存在者,即使是最高的存在者都不是,所以与基督教的上帝有质的差别。海德格尔的神也不是基督教上帝那样的完满的存在,不缺乏任何存在,相反,他的神需要存有,但是神有所需要、有所缺乏并不降低神的伟大。在海德格尔这里,存在比任何神都更具开端性(Das Sein ist anfänglicher denn jeder Gott)*Martin Heidegger, Über den Anfang(GA70), S.64.。在神和存在的关系中,最后的神来自存在的居有(Ereignis),是居有“迟疑着的拒绝提升”,也就是一种拒绝(Verweigerung)。这种拒绝不是单纯的不在场,而是在拒绝中已经有着居有发生,是一种最高的赐予的方式。在存在离弃中,存在显示为拒予,而最后的神显现的方式首先是拒绝显现。这是神对人的最极端的遥远。人认识到这个困境和这种遥远,恰恰是由于听到了神的召唤,所以这种遥远同时是对神的独特的切近。最远和切近同时在一瞬间发生。在存在的拒予中,以暗示的方式,最后的神降临。为此,人需要做到两件事:一是经受住作为拒绝的存在的居有,二是让存在者如其所是地显现。*Martin Heidegger, Beiträge zur Philosophie(Vom Ereignis)(GA65), S.411, S.412.由此,大地得到拯救,世界焕然一新。
神不但需要存在,也需要人,只有人的建基才把真理庇护进存在者中。神的历史需要人来保存。说最后的神或诸神在存在和人之间沟通二者,或者说它是存在自身“道成肉身”*林子淳:《“最后之神”即海德格尔的基督?》,《世界哲学》2015年第1期,第62—71页。,都有很大的解释空间。但是基督和最后的神之间仍有本质区别。海德格尔的神所做的不是救赎,将人作为罪人、低下的存在物,让人屈服于神才能得救。在他的神中,此在没有被压低,而是被提升到它的自由的奠基中,置身入存有之中。海德格尔明确说,诸神对于人“不是救赎,不是压低人”*Martin Heidegger, Beiträge zur Philosophie(Vom Ereignis)(GA65), S.413.,存在之居有发生在神和人的斗争中。神和人之间的关系并非仅仅是听从,而且还是斗争。在天、地、神、人共同构成的游戏时空中,神、人、存在者整体才都各得其所地本真存在。
这个居有事件在决断(Ent-scheidung)中发生。在《存在与时间》中,面临虚无的惶恐畏惧,决断打开了一个空间,从而完全摆脱常人状态。在后期,决断(Entscheidung)首先是属于存在自身的运作。Ent-scheidung表示的是分离、分开,是存有的本质中心(Wesensmitte),即存在自身在最中心处就是分开、分离。在分开中,打开一个敞开域,这个敞开域就是澄明之境(Lichtung),也是居有活动(Er-eignung),是人对存在的归属,同时人成为存在的真理的奠基者。在存在的中点处打开一个游戏时空(Zeit-spiel-Raum)。通过分开,才有了人-神的分离和人对神的归属,人被神占有。在这个敞开域中,存在者整体被放入决断。这种决断从存在对人的派送而言属于天命,而对人而言就是承受天命做出决断。这种决断或者朝向历史,或者丧失历史。海德格尔称,所谓历史即大地和世界的斗争,这种斗争的实施方式出于居有的召唤,其样式是最后的神的召唤。这种决断朝向历史的方式,必须是对最后的神的归属样式。神的暗示是“最短的、最陡峭的道路”*Martin Heidegger, Beiträge zur Philosophie(Vom Ereignis)(GA65), S.96, S.408.。最后的神的暗示涉及诸神的“来临和逃离的来袭和缺席”,也就是关于另一个开端的开启。
Figal对最后的神和诸神的理解是深刻而有见地的,认为海德格尔最后的神不会以任何个别的形态显示自身,也不会成为一个宗教信仰的中心,最后的神是那种让人理解此在和存在的敞开的时间、时间-空间的东西,祂让人经验时间的统一,统一起这个敞开域。此在从对自由的把握而被奠基,它既非只相信自己的理论,也非仅仅依赖于一个在上的超越的能力。*Grünter Figal, “Forgetfulness of God:Concerning the Center of Heidegger’s Contributions to Philosophy”,pp. 207、208.Figal点明了神在人在此-在中奠基中的作用。在笔者看来,海德格尔的神的确有其神圣性。神不仅是促使人为存在所居有的一个力量,而且以其神秘和令人惊异的面目启示人,这种神秘如同宙斯在天空发出的霹雳给人带来敬畏*在《巴门尼德》中,海德格尔描述了宙斯发出的霹雳和真理女神的形象。。但这种神圣者又跟基督教的上帝完全不同,和“道成肉身”的耶稣也有本质区别。海德格尔说神给出尺度,而诗人“采取尺度”, 诗人如同“半神”一样。同样运思者、艺术家、政治领袖等也可以成为这样的神和人之间的中介。*Martin Heidegger, Beiträge zur Philosophie (Vom Ereignis) (GA65), S.302. Da-sein之“Da被经受,以各自的庇护真理的方式——思的,诗的,建筑的,领导的,牺牲的,受难的,欢呼的。”神通过诸如诗人、哲学家、政治家等给出尺度,他们承担起了存在的天命,为此-在建基。在人的本质中,为存在所具有,被神所召唤,就是这种作为“半神”的“此-在”。这些少数人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庇护了真理,由此成为历史性的。同样,“民族”也来自神的尺度。海德格尔强调,他所说的民族不是人类学上的某个族类,而是说他们都属于存在自身。*Martin Heidegger, Beiträge zur Philosophie(Vom Ereignis)(GA65), S.96.
结 语
海德格尔自早期就对神和神性的主题充满兴趣*陈治国曾对海德格尔早期的神学解构进行论述,朱松峰也对海德格尔早期思想与基督教的密切关系进行了论述。(陈治国:《海德格尔的形而上学解构与神学的三重关系》,《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5期;朱松峰:《早期海德格尔论原初基督教》,《南京社会科学》2009年第10期。),对神和神性的思考跟他不同时期思考的重点问题密切关联着。在后期,海德格尔关于“最后的神”的论述同存在历史以及此在的建基和人的安居密切相关。最后的神在存在离弃的困境中对人发出召唤,拒绝作为存在自身的本现的方式,是最后的神对人召唤的方式。最后的神是存在历史从第一个开端到另一个开端的过渡中的神,就是那个能够救渡处于极端困境中的我们的神。神还以诸神方式临现。海德格尔说诸神是曾经的诸神的变形,应当指第一个开端处诸神的复活。他们是赫拉克利特在烤火炉旁共在的神,是人安居之神,也是在人“归乡”之后的“家乡”的神,在此处,大地和天空、神和人在一个时间-空间的敞开之域中交相映射。在存在的真理之思中,在筑基中,神在。人对神是倾听、不计算,为神所占有,被神所用*Martin Heidegger, “Von den Göttern gebraucht”, in Beiträge zur Philosophie (Vom Ereignis)(GA65), S.87.,同时和神在斗争。易言之,在海德格尔看来,“未来者”的生存必定与神同在。人的本质中有神性才得其所哉。
海德格尔的神不是有神论,也不是无神论,总之,不是神学上的神。他将神与人在存在的本现中以特别的方式结合起来。他对神的存在和神人关系的描述为我们打开了一个新的视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