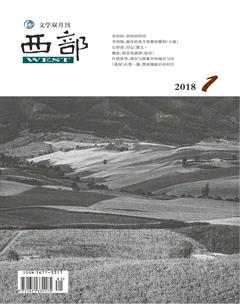回忆降临的黑夜
赵嘉竑
回忆是架构文学故事的一种流传已久且非常重要的手段。到了二十世纪,诸如普鲁斯特等现代作家在作品中对回忆的形式进行了精微的描述。马尔塞蘸着茶水的玛德琳蛋糕已经成了谈论非意愿记忆的经典意象。而到了石黑一雄笔下,事情全倒了个个儿——故事成了探讨回忆本身的手段。
这位日裔英国作家曾在访谈中表明,记忆、人们如何利用记忆才是他真正感兴趣的议题。所谓的英国历史、日本历史是他选择來呈现记忆这一主题的时空节点,对历史或现实世界的准确呈现并非他所努力的目标,甚至在他看来也非虚构文学之目的。在《被掩埋的巨人》里,他写道:“每段私人关系和社会关系中,总有黑暗、不为人知的记忆,在当时被刻意隐瞒或埋藏,但何时回忆、是不是该回忆,这是重点所在。”这似乎可以看作石黑一雄对自己所有作品的一个总结。
《黑夜降临后的村庄》是石黑一雄发表于2001年的一部短篇小说。在这部作品中,作者似乎有意剥离故事的具体历史与社会语境,以便更直接地切入记忆这一主题。直到阅读过半,读者才知道主人公是在加拿大的某个小村庄中,而这仅仅是个无关紧要的信息。不同于《远山淡影》里处于核爆阴影中的日本长崎或是《长日留痕》里二战硝烟中的英国贵族宅邸,这部短篇小说的背景设置更贴近于卡夫卡的风格,漆黑的夜色仿佛吞没了一切具体的线索,我们唯见寥落的人物穿行在深不见底的记忆中,不时踩中过去时光那将熄未熄的星火。
主人公弗莱彻在不停地周游旅行后回到年轻时曾生活过的村庄,虽是故地重游,但经历显然称不上温馨。夜色正浓,灯光昏暗,小巷逼仄又曲折,满身疲惫的他在此完全摸不着方向,没有什么近乡情怯,没有什么还乡断肠,哪怕是物是人非也没有,所谓故地对于如今的弗莱彻来说已经是一个完全陌生、异己的世界。
弗莱彻的叙述一早就明言自己过去在村庄的非凡影响力,他遇到的第一个村里人——年轻女孩向他发出邀请也确证了这一说法。读者们由此便好奇主人公过去究竟有着怎样的风云历史,他的记忆成了吸引读者继续阅读的一个悬念。当他终于进入老居民彼得森一家的屋子,注意到那个他曾经卧躺、阅读、聊天的角落,读者预计“弗莱彻风云史”的帘幕就要拉开了。然而事情并非如此,我们的主人公冒冒失失地跑去那个角落睡起了觉。睡眠断断续续,没有任何有关往昔的记忆入梦,读者只“听见”彼得森一家围在炉火边的低语。一个女人终于结束了弗莱彻的假寐,并称他毁了自己的一生。回忆的叙述开启,却不是关乎弗莱彻的辉煌历史:女人记得自己过去年轻貌美(尽管如今也自以为风韵犹存),记得自己对弗莱彻的崇拜,记得他们过去的性爱经历,但唯独没有说起弗莱彻何以毁了她的一生,她只是对弗莱彻如今近乎流浪汉的状态表达出不满,这似乎给她过去的盲目又带来了一重耻辱。至此,读者对主人公过去历史的期待依然没有得到满足,反而感到疑团越来越大:一个“名人”,有些风流韵事总是可以理解的,而从已知信息来推测,这极有可能又是一个始乱终弃的老故事,但女人语焉不详,弗莱彻对此又仿若失忆,读者们就只能希望接下去的情节能够顺带完整揭示出这段恋情的来龙去脉。新的“冲突”随即出现,弗莱彻因他自己臆想的这家人的忌惮和敌意而愤怒离去,决定接受女孩的邀请去年轻人的村舍同他们聊天。冲突带来了叙事的转机,又加强了弗莱彻是个重要人物的印象,读者们似乎可以预见到弗莱彻在一群年轻人渴慕眼神的注视下对自己过往徐徐道来的场景。但此时出现了一个罗杰·巴顿,这个弗莱彻的老同学与他聊起青年时代,虽说是有关过去的记忆但却是校园霸凌的陈词滥调,与读者们所期待的那种“影响力人物”的传说相距甚远。巴顿拖慢了弗莱彻的步伐,最终使他跟丢了那个女孩。于是在小说的结尾,巴顿领他到村庄的广场上,让他在这寂静的黑夜中等一辆据说总是带来欢乐的大巴,它将载着他去到年轻人的村舍。这辆大巴最终是否会到达读者们不得而知,但是他们所期待的弗莱彻的风云历史已无疑是没有着落了。
其实读者一早就落入了石黑一雄设好的陷阱。他善于使用漫不经心、絮叨徐缓的语言在不经意间设置悬念,操纵读者的期待。如在《远山淡影》中,悦子的大女儿安子为何自杀,作为叙述者“我”的悦子如何从日本来到英国都是读者期望解开的疑问,但悦子却只顾言说旧友佐知子和其女儿万里子的故事,读者为了获得前两个问题的答案而不得不忍受悦子对故友无休无止的回忆。直到书页所剩无多,读者感到悦子母女身世解密已希望渺茫时,石黑一雄才轻轻一笔,留下了悦子和佐知子似是同一人物的暗示。类似的技法在石黑一雄风格迥异的《家庭晚餐》《伤心情歌手》等作品中一再出现,因此,其作品从表面看来清风徐来、水波不兴,实则暗潮汹涌而别有深意。在《黑夜降临后的村庄》中,这种技法更得到强化。石黑一雄一开始在情节层面设置给读者的阅读期待直到小说结束时都没有被实现,这就造成阅读后的不满足感,它促使读者再次审视文本,以此来揭示和强化主题层面上作者对读者的期待,也即是说,小说表面情节的展开怪异地与母题相分离,而正是这种分离使得有关母题的讨论得到强化。对弗莱彻的青年时代的回忆并没有形成一张覆盖全篇的罗网,等着聆听故事的读者不免会失望,而这种无法全然把握记忆的失落感正是石黑一雄为读者设置的深入记忆世界的起点。他并不着意写一个关于某个人过去历史的跌宕起伏的情节故事,他以这个有点没头没尾的故事带出的是自己对于回忆这一母题的思考,并希望读者也参与到这种反思之中。在石黑一雄看来,欧洲文学尤其是英美文学,总是十分重视情节,但他所仰慕的俄国作家契诃夫的短篇却给了他勇气和信心来坚持这种慢速叙事、弱化情节的风格。
在《黑夜降临后的村庄》中,作者尽管采用了自己惯常使用的第一人称视角,但有关那段年轻岁月的记忆并不仅仅由叙述者一人诉说。对同一段时期,不同人物有不同的说法,而作为这段历史的中心人物的弗莱彻也对不同的记忆表现出不一样的态度。女孩所代表的村庄年轻人虽然不是那段岁月的亲历者,但却自称是专家,他们将那段历史设想为激动人心的经历。他们认可弗莱彻作为重要人物的说法,却又让不怎么重要的大卫·麦格斯受到同等的待遇,弗莱彻颇享受年轻人的恭维,但也不满麦格斯也能和自己平起平坐。而彼得森家的女人则只记住那段悲伤的情事,认为它造成了持久的伤害,弗莱彻作为当事人却辩称自己完全不记得这回事了。罗杰·巴顿则已经乐于接受他被弗莱彻所欺凌的那段回忆了,他的成长使他坚信自己后来有力量胜过他,他曾崇拜弗莱彻,之后则对其轻蔑,如今已经原谅,而弗莱彻却对他吹嘘自己年富力强的回忆不怎么感兴趣。对弗莱彻本人来说,他在故人的刺激和鼓动之下回忆起的往昔是一段勇担责任但却无法避免错误的经历。经由这些细小的记忆碎片我们无法拼凑出过去历史的全貌,就连弗莱彻的形象也是指向领袖和混蛋这样的两个极端。石黑一雄有意将记忆的事实层面给略去了,记忆远不止是某时某地的某人某事,它被取舍、剪裁、修正,它带有强烈的情感和价值判断,它支撑着我们成为如今的自己。
当弗莱彻与彼得森家的女人对峙时,女人耿耿于怀过去的枉费痴心,而弗莱彻却是揪住她声称自己那时知道争论的答案这一“错误”不放,两人的对话似答非所问,但弗莱彻对女人爱抚的意会与抗拒却似乎泄露了萦绕在他内心的不安。弗莱彻对自己造成的情感伤害选择性失忆,却承认过去的确犯有过失,但辩解那是自己在努力承担责任。他的认错和追悔更像是一种策略性的回避,以对小错的接纳来逃脱更为沉重的罪名。总体而言,弗莱彻只记取那些有利于自我形象塑造的记忆。他对仰慕自己的年轻女孩表现出虚荣的谦逊,但却极力修正她对麦格斯重要性的看法,这种踩低不得不说是对他自己过去形象的一种捧高。而当他遇上罗杰·巴顿,那个他过去欺凌的对象,他马上就记起了学生时代的种种,不过在巴顿一方看来,自己彼时只是个好欺负的受气包,不可能在弗莱彻的记忆中留下痕迹。弗莱彻仍旧以过去的眼光打量这位老同学,他将自己往日的暴力行为解释为为了巴顿能变得强大的好意,所以他同样以一种虚伪的强者对弱者的关怀来解读岁月刻在巴顿身体上的痕迹。不过,随后弗莱彻对巴顿所引发的怀旧之情显然产生了态度上的转变。这种转变开始于巴顿对弗莱彻离开以后的记忆叙述,他讲自己如何变得强壮,如何看透了弗莱彻的真面目,现在又如何温情地原谅了一切,巴顿甚至因为弗莱彻近似流浪汉的状态而怜悯起他来。巴顿的追忆令弗莱彻强烈地感到自己今不如昔的落差,他们之间的强弱对比竟奇特地颠倒了过来,于是他对那段校园岁月的记忆又抗拒了起来,希望能够更换话题。
石黑一雄在此是以一种卡夫卡式的反讽来刻画弗莱彻这一人物,而这种讽刺又被他迟缓的笔调控制在一种相当有节制的程度之内。一开始,弗莱彻就被年轻人期待为一个“指引者”,而小说的后半部分,他亦努力赶往年轻人的村舍以便给予这种指引。而实际上,弗莱彻这一夜的奔波都受到别人的指引,女人指引他回忆自己的情感,女孩指引他去往温暖舒适又欢迎他的村舍,罗杰·巴顿指引他回忆校园时代,指引他前往村庄广场——那是小说开篇他想要前往的地点——并在他心中种下了新的憧憬。与这些指引相并行的,是弗莱彻有意无意对某些记忆的回避,只不过他的逃避和游荡一次次被偶遇的回忆所改变方向,但兜兜转转他最终回到了“原处”。弗莱彻倾向于以一种永不停息的变动来拒绝一些令人不安的回忆。而当那一切又不可避免地“回到”他身边,他只得以对下一站的虚无缥缈的期许来聊以自慰了。石黑一雄的叙述恰好印证了本雅明的这句话:“一个经历是有限的,无论怎么样,它都局限在某个经验的领域;然而回忆中的事件是无限的,因为它不过是开启发生于此前此后的一把钥匙。”即便是我们选择压抑与遗忘的记憶,都将在我们的抉择中投下阴影,“过去的某些事情最终会回到你身边”。当然,石黑一雄并没有苛求他的人物。在避重就轻的记忆抉择背后,弗莱彻以一种苦行式的周游弥补过错,其动机虽然大致源于他对难以接纳的记忆的逃避心理,但其中又未尝不包含着几分不自觉的自惩意味在里面。石黑一雄同样安排弗莱彻意识到,对记忆的压抑并不能完全消除它的影响,他就那么鬼使神差地走进一家看似毫无印象的村舍,而这正是他往昔度过快乐时光的房子。那些美好的旧时辰正如同这暗夜之中微弱的火光,能够带来醉人的暖意。
石黑一雄借《黑夜降临后的村庄》这样一个晦涩不明、躁动不宁又充满疲惫的古怪故事,向我们揭示记忆或遗忘对我们自身的意义。记忆的显现、隐没与编造,都在帮助我们维系自身身份的完整性,它可能缓解当下境遇所带给我们的心酸,抑或可能使痛苦加倍;它潜入我们关于未来的梦,在暗中指引我们随意的抉择;它带着强大的情感力量沟通起我们过去的个体经验与未来的可能性。一定程度上,我们保留了怎样的记忆,决定了我们成为怎样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