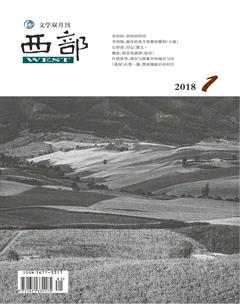阅读加缪
远人
探索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主题
在加缪唯一的短篇小说集《流亡与独立王国》中,排列第二的《反叛者(混沌的头脑)》最令人惊心动魄。该篇叙述方式完全不同于小说集首位的《不忠的女人》,倒和萨特认为“也许是最精彩也最费解”的《堕落》类似。小说通篇采用内心独白的方式,在独白中,加缪又不忘意识流的手法,这就使这篇小说从头到尾,在语言上充满扑朔迷离的气息,也造成小说的晦涩难懂。奇特的是,读完这篇小说,令人难以喘气的压抑感和震动感却久难消散。
早在《流亡与独立王国》出版前六年,加缪就发表了引起他和萨特从志同道合走向唇枪舌剑的决裂之作《反抗者》。加缪在正文开篇就给“反抗者”下了一个定义:“反抗者是什么人?一个说‘不的人。然而,如果说他拒绝,他并不弃绝;这也是一个从投入行动起就说‘是的人。一个奴隶,他在以往都听命于人,突然他认为新的指令无法接受。”
面对“反抗者”的释义,我发现它同样可以成为《反叛者(混沌的头脑)》的精当注解,因为小说主人公恰恰是“以往都听命于人,突然他认为新的指令无法接受”的一个自命为“奴隶”的传教士。
传教士的自白一开始就令人感到毛骨悚然,“……自从他们割掉我的舌头之后,不知怎的,另一个舌头不停地在我脑子里运转。”小说的第一个悬念立刻出现,“他们”是谁?“他们”为什么要割掉“我”的舌头?无论从哪方面看,割掉舌头的刑罚都极为残酷。身为传教士的“我”犯罪了吗?他又究竟犯了什么罪?
“我”没有直接——至少没有即刻告诉我们他犯了什么罪,竟至遭受割舌之刑。相反,“我”的独白很快绕过自己的肉身苦痛,谈起“父亲很粗鲁,母亲暴躁,喝葡萄酒”,谈起“冬天漫长,寒风凛冽”,使得“我”“突然想摆脱这一切”。从这里来看,“我”的童年过得极不如意,幸好一个每天照料他的神甫将其引向天主教。在年少的“我”的眼里,“天主教便如旭日东升一般光明”,于是,修道院接受了“我”。不经意间,“我”的独白又突然回到舌头被割的此时此刻,“我”疯狂地想“杀掉自己的生父”,即使“他已死了多年”。另外,“我”还几乎按捺不住地渴望“杀掉那些传教士”。
童年没有得到幸福,未必会让一个人就想要杀掉父亲,“我”在修道院学习多年,应该——事实上的身份也早是一名传教士。难道宣扬上帝与爱的传教士会对同行起杀心?
“我”立刻交代,之所以要和修道院的神甫以及“他的师长算账”,是因为他们“都骗了我”。神甫们是不是真的欺骗了他?又是何时何地欺骗他的?如果说宗教的目的是感化人,是将人牵引到上帝身边,那么宗教的目的就难以说是欺骗。对传教士来说,他们无不以为自己是上帝在尘世的代言人。他们要宣扬的是上帝之爱。在所有神学家那里,上帝之爱是没有欺骗的爱。小说中的“我”究竟感觉自己在哪方面被骗了?
“我”的独白没有逻辑可言,也难怪加缪要在题目中附上“混沌的头脑”为副题。“我”的头脑又未必真的混沌,该说清楚的地方还是说得清清楚楚。他对神甫们咬牙切齿,是因为他们建议“我”到“野蛮人的国度”去。他应该前往那里传教,开化当地人的头脑,启悟当地人的智能。神甫甚至告诉“我”,到野蛮人的国度之后,他应该告诉他们什么是“主”。按《圣经》的说法,“你打他的左脸他便伸出右脸”,神甫甚至鼓励“我”接受当地人的侮辱,以便让他们得到切实的证据。这些鼓励让“我”不以为然,他自认身体壮实,一些侮辱又算得了什么。“我”的想法甚至是“最好来揍我,往我身上吐唾沫”。修道院院长由此认为,“您也还有善良之处嘛”。这句话读来不无揶揄和反讽意味,以致“我”承认,从修道院学来的那一套只是让自己明白,“我”不过是一头“头脑聪明的骡子”。这头骡子坦白了自己念经时的偷工减料,即便如此,还是想要“树立榜样,树我自己,好叫人人瞻仰;在对我景仰之余,他们就服膺将我教化成材的教理,并以向我致敬表达对主的爱戴”。
这句话让我们能够体会,“我”未必会成为真正虔诚的传教士,因为“我”首先想到的是自己而不是上帝被人“景仰”。即使希望受教人“表达对主的爱戴”,也得通过“向我致敬”的环节。促使“我”跃跃欲试的,不过是让自己成为“主”的化身。于是,“我”果真出发前往野蛮人的国度。按康德的说法,野蛮人就是没有知识的人。在“我”的亲身体会里,野蛮人不仅没有知识,还确凿无疑地认为“他们是坏人”。正因为他们是“坏人”,所以才需要“我”去教化。于是,“我”“越过阿特拉斯山脉、高原和沙漠”,来到一座叫盐城的沙漠之城。 “我”刚到盐城,遭遇的当头一棒就是向导的偷窃,还被他狠揍得“耳角血流不止”,导致“我”想到的不再是“给对方打了左脸还伸出右脸”,而是“躲起来,是得躲起来!趁一切搞乱之前,先躲起来再说”。
盐城没有可以躲起来的地方。城在沙漠,“一切都是白花花的”,没有雨水的干旱天气使这里“热浪飙升,空气简直像一锅热汤……天空发出经久不散的轰鸣声,像烧红了的铁皮”,更无法忍受的是,那些野蛮人“一刻不停地盯着我。我经受不住逼视,呼吸益发急促起来。终于号啕大哭起来”,最后,“我被拉到了偶像之家”。
偶像并不是某个人。野蛮之地也会有野蛮之地的权威象征。在天主教徒眼里,野蛮之地的偶像不过就是该下地狱的异教徒形象。当“我”在四周都是盐墙的偶像之家待下之后,几天里唯一的食物就是野蛮人扔到地上的“一勺污水加粮食颗粒”。白天大门紧闭,夜晚没有灯光,连时间也无法计算。“我”不知道究竟过了多少天才大门打开,一群野蛮人拥着一位头发蓬乱、戴着面具的巫师进来。一个野蛮人首先“无动于衷地拧住我的下嘴唇……叫我跪下,弄得我嘴边鲜血淋漓……然后转身与别人汇合……眼睁睁看着我在毫无遮阴之处痛苦呻吟”。没有审判,也没有提问,更没有什么对话,一场对“我”的折磨立刻开始。野蛮人首先给“我”灌下一碗喝下后脑袋就痛得像着火的黑汤,然后将“我”剝光衣服,剃掉毛发,用油净身,接着就是用盐水浸过的绳鞭抽打脸部。当“我”转过头去,立刻就有“两个女人揪住我的耳朵,将我的脸凑近巫师的鞭子”。被打得遍体鳞伤之后,这些野蛮人才“扶起我”,强迫“我”去瞻仰“斧头似的双重脑袋,如蛇一般扭曲的铁鼻子”的偶像。“我”在绝望中发现,自己不仅无法在这里进行传教,还得“命定为它效劳、对它顶礼膜拜”,而“我”果然也“记忆丧尽,认真向偶像祈祷起来”。
“我”的这一行为令人惊心动魄。一个从小接受天主教信仰的传教士居然在自己的肉身痛苦和自由受到的胁迫下开始向异教徒祈祷。盐城在沙漠,这一地点能使人体会,加缪渴望将耶稣在沙漠面对的苦痛与诱惑暗示出来。如果“我”果真信仰坚定,那么痛苦就能够忍受。不论“我”是不是能挺过难关,更大的痛苦又接踵而来。在被偶像主宰的、说不清来龙去脉的漫长日子过去之后,巫师和野蛮人带进来一个“几乎赤条条的”女人。似乎巫师想用女人来诱惑传教士,传教士果然上当,当他走近与女人交媾之时,“一只有力的手紧紧捉住我的下颚,另一只手掰开我的嘴,把我的舌头拉出,拉得直流血。我大约像杀猪般尖叫。就在此时,一把利器(真是锐利!)从我的舌头划过”。割舌的刑罚就这么触目惊心地完成。一种“撕心裂肺的剧痛”使“我”觉得死亡都是值得“庆幸”的。“我”没有死,相反有种“新的仇恨在我心中燃起”。“我”没说是什么仇恨,我们看到的是,当“我”发现偶像“还在原地”时,忽然对偶像“不仅是祈祷,而且是笃信他,同时否定了这以前我所信仰的一切……他就是力量和权威……他就是主子、就是唯一的主,他的天性当然就是邪恶,从来没有什么善良的主子”。
小说最尖锐的张力就此出现。这一惊心动魄的精神冲突令人无法不想起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中探索的“致命问题”。伊凡向弟弟阿辽沙抬出的“宗教大法官”犹如一场痛苦的鞭打。它蕴含在伊凡讲述的一个个冷酷故事当中,其中某个故事讲述一对夫妻因为怀抱许多人都有的虐待小孩的习性,居然疯狂地向五岁的亲生女儿施加五花八门的虐待手段,当棒打、鞭抽、脚踹也不能满足他们扭曲的心理之时,竟在天寒地冻的冬夜将小女孩关在厕所,然后责怪她夜间不说自己要大小便,那个母亲就将小女孩的屎涂在她脸上,还逼着小女孩将屎吃掉。
伊凡冷酷地质问阿辽沙:
你明白这种荒唐事情么,我的朋友,我的兄弟,我的虔诚驯服的小修士?你明白为什么要有这样的丑事,它是怎样造成的吗?有人说,没有这个人就不能活在世上,因为那样他就会分辨不出善恶。但如果分辨善恶需要付这么大的代价,我们又要这该死的善恶干什么?因为我们全部的认识也不值这婴孩向“上帝”祈求时的一滴眼泪。我不说大人的痛苦,他们已经吃了禁果,那就随他们去吧,让魔鬼把他们捉去就是了……
伊凡灌输的分辨善恶的代价让阿辽沙感受到难以忍受的内心折磨。阿辽沙最终能抵抗这一思想风暴,也许还在于他没有亲身经历那些痛苦,哪怕后来的弑父事件来临,阿辽沙也没经受自己的肉身磨难。在加缪这里,善恶的颠倒能如此自然地在传教士身上出现,唯一的缘由,就在于本性不够坚强的传教士因为一种无辜的惩罚而动摇了对上帝的信仰。信仰的动摇极为可怕——当“善”走向消失,紧接着的“恶”将发动怎样的攻击就难以预测了。在信仰崩溃的传教士眼里,“善”变成永远不可企及的梦想,“恶”却可以达到它的顶峰,建立起自己摸得着、看得见的统治。更可怕的是,传教士开始觉得自己从前信仰上帝时是奴隶,如果自己“也满怀恶意,就不会再当奴隶”。于是,被“恶”控制的传教士在“学会了向‘仇恨的不朽灵魂跪拜”之后,弄来一把步枪,一门心思地想要“杀掉自己的生父”和“杀掉那些传教士”。
传教士将想法立即付诸实行。他取到枪,在沙漠的一块岩石后潜伏好几天。当他看见新的传教士骑着骆驼到来,就立刻一边“赶快将子弹上了膛”,一边疯狂地向偶像祈祷,“希望侮辱多多益善,希望仇恨统治一大群受难者,希望恶人成为永远的主子,希望那王国终于到来”。传教士的内心完全被邪恶控制,他明知道自己是在“向憐悯放枪”,是“对着无权威及其慈悲”放枪,还是瞄准新来的传教士“放了又放”。他看着人跌倒,看着“骆驼朝地平线狂逃”,这一结果使他笑得“前仰后合”。当中枪的传教士在“黑袍下扭动身子,他微微仰头,一眼看见了我”时,“我”的感觉是自己虽“身陷囹圄”,但“我可是他至高无上的主子”。于是,在疯狂的谵念之下,“我”举起枪托,打在这个传教士的脸上,甚至感觉自己是打在“善”的脸上。
在世界文学史上,这一残忍的行为几乎只被陀思妥耶夫斯基触及过,在伊凡的冷酷独白中出现过。当它来到加缪笔下,作为读者的我们不可能不被这一主题震惊。它不是一个简单和例外的主题。这一主题就掩藏在人性的深处。不是每个作家都能进入这一深处,更不是每个作家都有能力来表现这一深处。人性之恶总会在某个时段奔涌。上帝宣扬善,是尘世的恶太多。加缪创作这部小说时,他已经经历了历史上最为疯狂和血腥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也正在经历冷战的恐怖对峙。对熟读陀思妥耶夫斯基著作的加缪来说,不可能放过陀氏借伊凡之口说出的那句“这大地太需要荒诞了。世界就建立在荒诞上面,没有它世界就会一无所有”的冷酷之言。令人恐怖的是,它又恰恰是真实之言。惩恶扬善是所有人的美好愿望,生活中不计其数的事实又总是恰好相反地表现为惩善扬恶。
人性真的如此之恶吗?陀思妥耶夫斯基不给出答案,加缪也不给出答案。或许,善恶的分辨取舍,从来就取决于人的一念之间。“我”对传教士的枪击引来“一群黑压压的飞鸟”般的野蛮人。他们“一把抓住我”,“我”突然明白,野蛮人对“我”施加折磨和刑罚,居然是因为“我”孤身而来。此刻的枪声却让他们害怕会引来“驰援的大兵们,怕他们冲向圣城”。“我”终于发现,那些自以为掌握真理的野蛮人无法头顶“信仰的骄阳”。他们用“黑色的面纱遮住明朗的欧洲”不过是“将我钉上十字架的一击”。这一击的确可以考验受难者的信仰是否坚定。
发现巫师们的“恶”并非来自信仰之后,“我”的善念再次复活。当“我”在沙漠中睡一夜后醒来,看见“曙色微露”的“第一道阳光”,立刻感到“那是为其他活人来临的又一天”。太阳的出现意味上帝的来临,“我”仿佛听到了有什么人在说话。说话声甚至清晰得让“我”能听明白,“假如你愿为恨和权而死,谁将宽恕我辈?”于是,“我”在近乎神启的瞬间发现,“不停在我脑子里运转”的“另一条舌头”居然说的是“勇敢些,勇敢,勇敢啊”。不论这是不是上帝的声音,我们还是要问,人性真的足够“勇敢”吗?“万一我又弄错了呢?”这一疑问不觉间又在“我”的脑中盘旋,紧接着,“请助我一臂之力”的祈祷让我们能够体会,这一次,“我”的祈祷终于回到信仰身边。它吻合了加缪毕生主张的地中海思想——明知世界冰冷,也要尽力燃烧。
我的确发现,阅读这篇小说,不止是阅读世界的冰冷一面,同时还在阅读最残酷的一面。我没去考证加缪是不是基督徒,他身体力行的,往往又是最崇高的悲剧——不仅通过这篇主题堪称伟大的小说,还通过他的一生。
永难摆脱的生活凡庸
稍稍回顾十九世纪的法国文学会发现,司汤达笔下的于连,巴尔扎克笔下的拉斯蒂涅、吕西安,雨果笔下的冉阿让、郭文,大仲马笔下的邓蒂斯,左拉笔下的艾蒂安等人物,无不充满超群的个人魅力。似乎在那些小说家笔下,充满激情又将激情引向某个高度的人物才值得他们精心塑造。到二十世纪,普通人成为小说家们关注的对象。古典小说家们并非没有塑造过普通人和小人物,只不过,他们往往将那些小人物搁置在具有时代感的背景之下,似乎没有这一背景,人物的命运就不好解释。
塑造小人物,加缪不是第一个,却是写得极为深入的一个。他在短篇小说《无声的愤怒》中刻画的依瓦尔等人物让我们感到,他们与时代没什么关系,仅仅是个人性格才导致他们面向命运的叹息。
依瓦尔是一个工场里的制桶工。该身份容易让人想到,巴尔扎克笔下的葛朗台也是箍桶匠,读过巴尔扎克小说的会知道,葛朗台的精明强干令每一个读者都不敢低估。如果我们在生活中遇上葛朗台这样的角色,只怕难逃他“钢铁般的利爪”狠抓。依瓦尔只是逆来顺受的工厂工人。小说出场时,依瓦尔对隆冬“明晃晃的太阳”和“海天一色”的景致都“视而不见”,只是“费力地骑着自行车”前往工厂,他腰间挎包的午餐盒里,塞有妻子费尔嫩德做好的粗制面包。
依瓦尔已经四十岁。加缪告诉我们,从二十岁开始,依瓦尔都这样每天前往工场。二十岁和四十岁的区别太大。二十岁那年,还是单身汉的依瓦尔不仅“看海看不厌”,还“酷爱游泳”,每个周末都是在海滩度过。和费尔嫩德结婚并有了孩子之后,他的周末不再是用来度假,而是“在制桶厂加班”,星期天还得“为私人干零活”。似乎在深入生活之后,消逝的不仅是青春,还包括某种内心的东西。唯一没变的,是依瓦尔“仍旧爱海”。每天他都在平台上看落日,穿着费尔嫩德给他“仔细熨烫过的干净衬衫”。奇怪的是,依瓦尔虽感惬意,还是“不知自己是喜是忧”,他总觉得自己还在“耐心等待”,但“自己也不甚了解等待什么”。
二十岁的青春容易让人感受尚在远方的生活吸引而勃发激情,这股激情的延续或会将人带往渴望的某种高度。当依瓦尔四十岁仍然在工厂做工时,不仅激情消退,还觉得自己四十岁就已老成了“古人”。这种近乎颓丧的心态决定了依瓦尔的生活。
这一天,依瓦尔觉得“去工厂的路从未显得如此漫长”,原因是他们罢工失败。工厂老板拉萨尔拒绝了工人们的要求,继续罢工的前景不妙,工人们不得不复工。包括依瓦尔在内的所有工人都事先明白,这次罢工无非是“出出气”,因制桶业受到“造船和运油卡车威胁”,拉萨尔的生意已经不太好做。当工人们决定罢工时,拉萨尔只说出“去留自便”的生硬之言。对依瓦尔来说,他们实际上不可能离开工厂,“有手艺没饭碗”的前景等于将自己逼入绝境。
小说容易让人想起左拉的《萌芽》。左拉同样描述了一次罢工事件,他笔下煤矿工人的罢工是因为劳资双方尖锐对立。无产者与资产者具有历史意味的抗争使左拉将小说写得气势磅礴,犹如史诗。在加缪笔下,拉萨尔是老板,谈不上剥削工人,因为子承父业,拉萨尔“早就认识几乎所有的工人”。拉萨尔和工人们相处融洽,为人也“十分和气”,工人们罢工,更多的是拉萨尔“碰上了难题”。对一个老板而言,工人们罢工相当于造反,不论他和工人们多么熟悉,还是不见得欢迎工人们前来复工。依瓦尔和所有同事都一声不吭,都“对自己的敢怒不敢言极为恼火”。
拉萨尔走进作坊后,没有人搭理老板。拉萨尔主动跟工人招呼,后者也自顾干活。拉萨尔质问工人们这种态度有啥用,回答他的还是作坊里铁锤和电锯的声音。工人们选择了复工,对自己的失败又感到沮丧。拉萨尔是罢工的赢家,没变得趾高气扬。加缪也没有借助这种冲突,在小说中去刻画道德甚或阶级意义上的好人和坏人,他只写某种生活的某个截面。作为“存在主义”的代表作家,加缪写的仅仅就是“存在”。
拉萨尔将依瓦尔和另一个工人叫到办公室。进去之前,他们听到拉萨尔婴孩的哭声,还听到拉萨尔“不好再请医生”的嘱咐。这个细节表明了拉萨尔的困境。所以,办公室的谈话不会有什么结果。小说设置的情节始终枯燥,唯一增加的信息就是拉萨尔的女儿病了。
加缪的笔尖始终集中到依瓦尔身上。读者看到他“一直弯腰驼背,脸朝着手中的刨具”。疲乏感将依瓦尔彻底控制了,正值四十岁壮年的男人,居然觉得自己“年事渐高”,觉得“凡是劳动四肢的活计,最终受到诅咒,并成为死亡的前奏……对那些凭空赞美体力劳动的人,自己实在是不知其所云”。
这些“不祥之念”使依瓦尔感觉“体力劳动日艰”。然后发生的事是拉萨尔女儿病情加重,工厂工头出去请医生。依瓦尔对拉萨尔女儿的病情不加评论,只是将消息传开,工人们过来听了听,然后又重新各就各位干活。大家似乎都在观望什么,又没有什么值得观望,既然复工了,不管他们是否愿意,该干的活都得干。依瓦尔心情仍很难过。他本想说点什么,却无话可说,他唯一渴望的只是回家,“重见费尔嫩德和儿子,重登平台”。这个被生活打磨的男人意气消沉,或许依瓦尔不是因为复工才感到消沉,从他觉得自己变成“古人”那一刻起,依瓦尔就不再有年轻时的激情和向往。
加缪似乎想拖延小说节奏,当工人们下班之后,他不厌其烦地描述他们如何停下机器,如何熄灭火堆,如何进入更衣室,其他人如何清扫现场,在淋浴时如何不再有众人开玩笑。依瓦尔没想叫住任何一个同事,甚至没有洗澡就更衣,和大家道过晚安之后,就急急走出,找到自行车,当他“一跨上车,便又感极度疲惫”,他还是“骑得很快”,路上还想起拉萨尔女儿的病情。我们或能体会,依瓦尔的生活中实在没什么值得书写。老板女儿的生病也成为他生命中一件可以时时想起的事情,这也只能说他无法在工作中再找到其他重要的东西。
回到家时,依瓦尔的儿子正在翻阅画报,妻子费尔嫩德很自然地问他今天是否顺利,依瓦爾还是一言不发,径直去洗衣房冲凉,然后坐到平台上眺望。海面还是像二十年前一样,对他有充分的吸引力,他的内心完全不复当年的冲动感受。令人疲惫不堪的感受不可能让人再做出不顾一切的决定。当费尔嫩德在他身边坐下后,依瓦尔将这平淡无奇的一天情形告诉给了她。依瓦尔比任何人都明白自己生活就处在一个无意义的状态。唯一剩下的感受,就是他凝望大海时涌起的隐秘情绪,该情绪导致小说的结句几乎突如其来,“他想望着青春复来,费尔嫩德也姣好如初,那么他俩必定会远渡重洋的”。
当整篇平淡乏味的小说写到末句,才令人突感一股锥心的刺痛。这当然不是加缪的强行所为,这句表面上尚有激情,实际上不再可能实现的话正是无数人的想法。谁都想青春重来,让自己有更好的选择。人真的有选择吗?就依瓦尔来看,他和所有人一样,都有过激情充沛的青春:在他酷爱游泳的青春时代,他身下的这片大海不就对他发出过召唤?他在海滩散步之时,海洋的对岸不就曾吸引他的目光?他初识费尔嫩德之时,费尔嫩德不正是如花似玉的锦瑟之年?这一切当然能够肯定,他缺乏给自己开创未来和独自打开生活的勇气,这不是依瓦尔一个人缺乏的勇气,而是无数人——如拉萨尔工厂的所有工人们都缺乏的勇气,所以,他们所有人都留在了工厂,他们“出出气”的罢工也就只可能以失败告终。
小说最后也蕴含一个问题,如果此刻的依瓦尔尚在青春,他会真的携费尔嫩德远渡重洋吗?我觉得不会。加缪这篇小说令人震动,就源于所有人都有过这样那样的渴望,生活本身的凡庸又让他们不知不觉选择了屈从。摆脱凡庸,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即使每个人都渴望有属于自己的强者幻想。真正成为强者的只是少数,生活给绝大多数人的,只是随波逐流的点滴。这些点滴构成无数人日积月累的一生。依瓦尔在品尝这种点滴,我甚至忽然肯定,他每天坐在平台上眺望黄昏和大海,不过是给自己重复一种虚幻的安慰,它不可能变成实实在在的现实。沉沦幻想是无数人的行为,人摆脱不了比人更强大的现实,幻想也就注定成为虚幻。用加缪的哲学术语来说,这一沉沦的虚幻不过是人在生活中面对的“荒谬”。如何面对“荒谬”,加缪的回答是扛起“荒谬”。但屈从生活之后,无数人扛起“荒谬”的勇气也不见得拥有。这恰恰是依瓦尔的悲哀,也是人最大的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