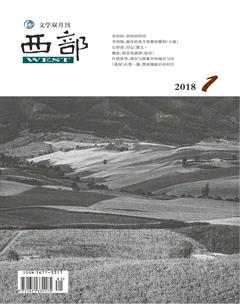青蛙·蚯蚓·壁虎
安宁
青蛙
雨水好的夏天,每天傍晚,都会听到蛙鸣。有时候是孤独的一只青蛙,有一声没一声地叫,不知是太闲了,还是在梦境之中忽然受了惊吓。有时候是一声紧跟着一声,像雨天屋檐下的雨滴,因为密集便连成了线。还有时候,是一群青蛙的聚会,在潮湿的草丛里,商量好了似地亮开了嗓门,开始无休无止的大合唱。那歌声有很强的穿透力,连夜空里的星星都好像给震动了,隔着湿漉漉的榆树叶子看上去,星星犹如大地这片舞台上的灯光,在夜幕下泛着朦胧遥远的光。草丛里的青蛙歌唱的时候,池塘边的也跟着附和起来,还有院墙根下某个落了单的家养的青蛙,或者在田地里走丢了的某一只,听闻这一场盛大的演唱会,全都兴奋起来。于是歌声便从黄昏一直持续到深夜。可苦了那靠声源近的人家,一整夜翻来覆去无法安眠,以至于最后气得骂娘,爬起来,到院子里站着听那蛙鸣,直到天边亮起,濡湿了脚,才一脸困倦地回屋再睡。
很少有人会将青蛙的叫声当成悦耳的歌声,尽管青蛙是在借这样聒噪的歌声求偶。雨天来临之前,它们是多么快乐啊,情不自禁地手舞足蹈起来,一定要用呱呱的叫声来动员身边的同伴们,美好的雨天就要来了,为什么不一起唱歌跳舞庆祝呢?雨天里,人只会待在家里,看着大雨着急。青蛙却在水塘里兴奋地跳跃起来,有时候它们也会跳到大大的荷叶上去,丝毫没有避雨的意思。它们蹲踞其上,想要告诉每一个人,它们感谢这一片苍茫的雨雾,不仅带来了它们赖以生存的潮湿的天气,而且提供了源源不断的食物,此时草丛里的虫子们开始大量繁殖,还有什么比日日饱餐更让它们觉得幸福的呢?
不管歌声怎样,至少青蛙的样子还是不让人那么厌烦的。比起它们的本家蟾蜍来,青蛙简直可以称得上是可爱的。好歹,青蛙绿色的外衣要比土黄色的衣服好看,人偶尔踩到也不觉得心惊。倒是蟾蜍,趴在土溝里,跟泥土混为一色,很容易让人在耧草或者耧树叶的时候,一下子碰到,它们黏湿且长满疙瘩的皮肤,吓得碰到的人尖叫起来,甚至还会神经质地以为那黏液是有毒的,一遍遍清洗双手,即便洗干净了,心里的膈应还是要许久才能消除。不过老人们则认为碰到蟾蜍是吉利的,因为月亮不就被称为蟾宫嘛。据说蟾蜍是美丽的嫦娥变的呢,只是为什么仙子一样美好的嫦娥会被变成如此丑陋的模样,就不是我们小孩子能够理解的了。但有钱人家的条几上,还是会有一只吐着舌头的蟾蜍,那舌头当然不是白吐的,上面永远会有几枚铜钱,预示着财源广进、多子多福。
蟾蜍是沾了仙气的,青蛙可是地地道道的人间的产物。小孩子们嫌弃蟾蜍丑,不愿意玩弄它们,怕沾一手的黏液,于是去寻青蛙开心。雨后的水坑里,到处是跳跃的青蛙。即便是泥地上,也随处可见。它们一蹦一跳地横穿大道,朝湿润且多昆虫的田地里蹦去。捉一只青蛙几乎是毫不费力的事,随便走到一株大树下或者水塘边、田地里、沟沿上,都会遇到一两只,正鼓着圆圆的大眼睛,瞪着人,本想要唱歌的,却又惊恐地止住了。看见小孩子笑嘻嘻地弯下腰来,它们立刻感觉到了正在逼近的危险,后腿一蹬跳了出去。但人多么狡猾啊,另外一个小孩子早就在对面守着了。一只想要逃命的青蛙,很快落了网。
玩弄青蛙,当然都是男孩子们的游戏。他们有数不清的把戏来折磨可怜的青蛙。比如将青蛙翻过身来,白色的肚皮朝上,而后用木棍不断地敲击,直到那肚皮不知是不是因为气愤而鼓胀起来,看上去很是滑稽可笑,施虐的男孩们才会住了手,捉起青蛙两条细长的后腿,扔进对面的水池里去。那青蛙已经被敲得奄奄一息,在水池里依然翻着白色的肚皮,那眼睛也还是大大地瞪着,似乎有死不瞑目的愤怒与忧伤。而施虐的人,则因了这劳动成果,哄然一笑,四散开去。
也有天不怕地不怕的男孩,将铁丝穿过青蛙的身体,放在火上烤,一直烤到那肉里焦外黄、散发着诱人的香味,再洒上一些盐,而后毫无忌惮地吃起来。不过敢吃青蛙的孩子并不太多,所以那个大胆的男孩也便有了第一个吃螃蟹的人的英勇与豪迈,走到哪儿都会有人问他:青蛙的肉是什么味道的?香不香?嫩不嫩?吃了能长生不老吗?他也就新闻发言人一样,处处向人描述青蛙肉质的鲜美和难忘。说得多了,大家便有些不相信他,觉得这孩子是在夸张,哪有什么动物的肉比得上牛肉好吃呢。当然,村子里吃过牛肉的人也不太多,大致是有钱一些的住户才能吃得起,而且那也是在年节时才能够享用,并非可以经常吃到。但那孩子还是坚持着,蛙肉的确是世界上最好吃的肉,不信的话,他可以烤了给每个人尝尝。当然没有多少人愿意去吃青蛙的肉,想想就让人浑身起鸡皮疙瘩。
人不喜欢吃青蛙,牛也一样。所以男孩们就恶作剧一样地,为了让牛觉得恶心,用叶子或者青草包住一只活着的青蛙,丢到牛的嘴里去。那从未吃过荤的牛,忽然间觉得嘴里有一股怪味,不由得咧开嘴,试图将青蛙吐出来,无奈那青蛙吓坏了,不知道怎么才能逃出去,左冲右撞中,一不小心,便蹦进了牛的喉咙里,葬送了性命。围观的小孩子们见恶作剧成功,全都哈哈大笑起来,直吓得那牛不知道怎么办好,焦躁地踱着步,又扯下一大把草来吃进肚子里去,似乎想要借此清除掉那青蛙带给口腔的怪味。
更残忍一些的男孩将青蛙捉住后用针扎住四肢,而后对其进行剥皮手术。那皮还要剥得完整无缺,不能出现断裂或者破损。负责剥皮的孩子不是来自屠夫家,就是天生有做屠夫的基因,一起帮忙的小孩子们都吓得发出嘶嘶的声音,好像自己身体里被扎了很多根针,或者有人拿了刀子剥着自己的皮,因此觉得疼痛难忍;同时心里对那主刀的“大夫”又生出满满的仰慕和惊骇,不知他怎么能忍受那些湿滑的液体和蛙血的腥气。对于旁观的人,这一场“屠杀”在心里留下的印记很久都不能消除,每次见到夏天的青蛙,都会想起这一场事故,心里不自觉地收紧了,手也下意识地按着小腹,好像疼痛的伤疤再一次揭开来。
这些沾染着血腥味道的游戏,也只有男孩才会乐此不疲,女孩子则害怕青蛙这样柔软的小动物,别说去“谋杀”,就是碰到都会觉得恐惧。所以男孩们最喜欢将青蛙放到漂亮女生的铅笔盒里,看她一声尖叫,花容失色,会有捉弄了自己喜欢却得不到的女孩子的快感。但当青蛙还是小蝌蚪的时候,几乎每一个女孩子都会温柔地去河边捉两三只小蝌蚪,回家来用罐头瓶子养着。小蝌蚪大约是我见过的水里最可爱的小生命了,比鱼还要动人。它们黑色的拖着一条细细尾巴的圆圆的身体,像极了一个动听的音符或者春天落在电线上的燕子。当它们在河中欢畅地游动时,那轻微的水声,如果放大了,一定是叮咚叮咚响着的世间最美妙的乐声,而很多的小蝌蚪在水里酣畅淋漓地游来游去,就是一首旋律跌宕起伏的大合唱了吧。
我喜欢在放学后去河边坐上一会儿,看那些初夏的小蝌蚪们欢快地游来游去。有时候它们会游到我裸露的脚边来,用柔软的脑袋“亲吻”一下我的脚趾,而后又倏忽而逝,混入无数的蝌蚪之中,让人寻不到它究竟是哪一只。有时候我会想,女大十八变,为什么这么可爱的小蝌蚪长大以后不会变得漂亮一些呢?比如像翩翩起舞的蝴蝶,有着优雅外衣的七星瓢虫,或者一尾穿了鲜亮的红色裙子的金鱼。总之不要有那么突兀的眼睛,怀胎十月般的大肚子,枯树枝似的脚趾和毛球一样绿色皮肤上的小疙瘩。我当然想不明白造物主的决定,只能为此叹息,就像为童话里被女巫变成了丑陋青蛙的王子惋惜一样。
我养的小蝌蚪,没有等它们长出腿脚或者尾巴消失,要么就因忘记了换水喂食而不幸死掉,要么就是我太恐惧它们在一夜醒来后变成了绿色青蛙的模样,而将它们重新还给了池塘。我不知道它们的妈妈在哪儿,或者蝌蚪们也找不到妈妈了,只能独自在水中觅食,一天天长大。大人们还说,青蛙从来不知道珍惜自己的孩子,它们甚至会一转身,就将蝌蚪当成了晚餐吞进肚中。啊,就连蝌蚪自己也会将死去同伴的尾巴吃掉!这听起来有些骇人,我一遍遍问母亲,为什么青蛙会吃自己的孩子。母亲没有读过书,说不出来,被我问得烦了,便拿起笤帚疙瘩要打我屁股,我吓得转身就跑出了家门,一边跑一边想,母亲如果再狠一点,会跟一只青蛙一样,也把我给吃掉的吧!
母亲有没有在我梦里变成一个吃人的母夜叉,我已经完全不记得了,但是靠近村头池塘的老李家却被青蛙给“报复”了。老李的媳妇在一连有了五个闺女后,终于生下的一个儿子,却是个哑巴!老李找了会算命的嬷嬷,问她为什么老天爷这么不公,偏偏给他们家断子绝孙。嬷嬷烧了纸钱,又将一碗小米蒙上布后倒扣在地上,不停地说着什么。最后,布揭开来,发现正对着门外池塘的方向缺了一个小口。嬷嬷便说,你一定对池塘里的青蛙做过什么坏事吧?老李终于想起来了,三年前下大雨,池塘里忽然间涨满了水,还有不知是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满满的青蛙,整日整夜地呱呱地叫著,让他心烦,为了睡个好觉,他将一瓶农药倒进了池塘里。青蛙的叫声终于少了,可是却没想到,他生下的唯一的儿子也没了声音。
村里人都相信是老李将蛙神给得罪了,而他的哑巴儿子也不敢靠近池塘,尤其在夏日的傍晚青蛙开始大声歌唱的时候,池塘边的人总能听到老李呵斥儿子的声音。儿子当然是听不到的,可是他看见老李脸上的愤怒,还是会忽生恐惧,乖乖地离开这给过他诅咒的池塘,咣当一声将铁门紧紧地关上。
也是因为这个哑巴,此后村里的大人们再看到男孩子玩弄青蛙,比如剥皮、开膛破肚、砸青蛙、将它们当成石头扔来扔去,就会愤怒地呵斥,并丢下一句恐吓的话说,小心明天青蛙报复,将你们这些兔崽子全变成瞎子、瘸子和哑巴!这一句话果然管用,那些“凶手”全都讪讪地住了手,看着被砸得没有多少力气的青蛙,慢慢地爬到池塘里去,消失在一片茂密的水草里。
我不知道那些捉弄青蛙的男孩们,在夏日的梦里会不会见到没了皮的血淋淋的青蛙愤怒地瞪视着他们,并因此吓得大哭起来,但我却一直怀疑,老李家的哑巴儿子,或许是童话里的青蛙王子投胎到人间,专门护佑村里青蛙的吧。
没有人提及这个话题,大人们讳莫如深。我们小孩子也终于对一只青蛙生出了畏惧。
蚯蚓
夏天的时候,下过雨,庭院里积满了水,通往巷子口的垄沟一时间忙不过来,那水便打着漩漫溢开来,有的积在梧桐树的树坑里,有的聚在香台底下,有的滞留在猪圈鸡窝旁。我拿着小棍子,将浅浅的垄沟里平日堆积的泥沙、树叶或者瓦块等垃圾全都清理出来。这样疏通一番后,雨水便欢快起来,汩汩地朝墙外流去,半小时后,院子里便现出昔日清洁的模样,而从松软的泥土里,一定会有许多条蚯蚓,爬到地面上透气。如果不是这一场大雨,它们大约要一辈子待在温暖的地下或者庄稼、野草的根须里,无休无止地睡下去。
我其实是有些怕蚯蚓的,因为它们长得像小小的蛇,但又因它们着实没有小蛇那么可怕,至少是在我完全可以控制的领域内,所以,我和所有的小孩子一样,喜欢拿一个细细的草茎将它们挑起来,放到干燥的沙石路上,看它们笨拙地扭动着身体,一伸一缩地朝某个方向慌张地乱爬。如果它们爬得足够得快,就能很快消失在某片泥土里。如果动作慢上一拍,就有被旁边冲过来的公鸡一口啄进肚子里去的危险,被人踩断一截身体的致命一击。大街上还有许多小男孩专门以断掉蚯蚓为乐的;因为听说蚯蚓断了一半后,两端各自还会长出新的蚯蚓来,出于好奇,也出于恶作剧,他们将蚯蚓从水里或者淤泥中捏出来,直接用尖锐的小木棍切断,再笑嘻嘻地看着那两部分怎样生离死别地各自愈合。
当然很少会有小孩子耐心地观察断掉的蚯蚓如何成长为两条新的生命。乡下永远有比这更新奇的事情等着他们去做。而我,则害怕观看这样残忍的断体游戏;就像每次来乡下“耍把戏”的马戏团,为了挣钱,总有个十二三岁的小男孩被当场卸断了胳膊(脱臼),以便博取同情的泪水和更多的收入。而我,就在那恐惧的一刻,从人群里快速地挤出去,一路飞跑着回家,似乎再晚一步,马戏团里那个心狠手辣的卸胳膊的男人就会将我也拉进去一起卸了。我想如果蚯蚓也有灵魂,它们会不会在断体的那一刻,像个孩子一样内心满是无力逃脱的惊恐和绝望。据说,蚯蚓是有心脏的,如果正好切到它们的心脏,就会两边同时死去。那么一个有心的生命也一定跟猫狗一样,是会哀哀地在地上,抬头仰望着不可一世的人,求他们放过自己的吧。
没有谁会想到这些,一条蚯蚓,不过是不值一提的蚯蚓罢了。在乡下人的眼里,生命只是人本身而已。不,即便是人本身,也不怎么值得提及。那些生孩子就如葡萄一样一大串的父母们,就好像生的是猫猫狗狗一样,任由小孩子们在庭院内外奔来跑去,至于他们是会砸死一条狗,还是虐待一只猫,或者被什么人给揍了一顿,都不在父母的关注之内。小孩子们也不会要求太多,只要在众多兄弟姐妹们之间能够好好活着,有口饭吃就可以了。没有被人给予过太多宠爱的孩子,自然不懂得怎样呵护别的生命,哪怕只是一条微不足道的蚯蚓。它们是怎么消失掉的呢,又去往哪片泥土,没有人知道。地上的人照例过自己的凡俗日子,而泥土下的它们照例为庄稼疏松着泥土,生产着肥料,吞吃着残渣。没有人关心这个地下王国有怎样的生活。人们在刨地挖草的时候,常常会与它们碰面,也不过是陌生人一样看一眼就各自走开了。人不帮蚯蚓回归原位,蚯蚓也不惹人烦厌地爬到脚面上去,让人起鸡皮疙瘩。蚯蚓只与泥土和植物的根系发生最亲密的关系。它们透明柔软的身体像弹琴的手指一样,有节奏地快速伸缩着,没有什么东西能够阻挡住它们的道路。我总怀疑《西游记》里的土行孙是根据蚯蚓虚构的。当然像蚯蚓一样能出入地上地下的动物有很多,它的本家长兄蛇就是其中之一。我天生好奇,喜欢去抠地上大大小小的土堆,小的会抠到蚂蚁、蝉、蟋蟀、地老虎等稀奇古怪的小虫子,大的则会抠到老鼠、蚯蚓或者是蛇。相比老鼠,我还是更害怕蚯蚓和蛇。蛇其实不会轻易碰到,而且它们体型细长,很容易看到。但蚯蚓则不同,它们跟泥土几乎一样的色泽,一不留神就会在一把抓起的泥土里碰到它们柔软湿滑的身体,甚至捏到它们的脑袋;而此时,我唯一会做的,便是一声尖叫,一扬手,将蚯蚓飞快地扔出去。
蚯蚓当然是田野里最无害的生物,它们既不会咬人,也不会袭击人,而且还是药材。村里的中医药铺里,有放中药的一格一格的小抽屉,上面写着“地龙”的,就是干了的蚯蚓。有患支气管哮喘的老人,买回去研成碎末,日日冲服下去,据说有很好的药效。我总觉得害怕,觉得那人肚子里会重新长出一条蚯蚓。
母亲却完全不顾及我的恐惧,为了她养的那一院子的鸡们能多下些鸡蛋换油盐酱醋,非让我和姐姐去田野里挖蚯蚓给鸡改善生活。我只能提起两个罐头瓶子,跟扛着锄头的姐姐一起出门,朝蚯蚓最多的那片梧桐树林走去。《红楼梦》里林黛玉扛着锄头是去葬花,我和姐姐则是很不唯美地去挖蚯蚓。不过树林里的天地,在夏天的正午也自有一种幽静之美。知了的叫声有些乏了,听上去便有些遥远。偶尔有鸟粪从头顶落下来,啪嗒一声滴在一片树叶上,随后便许久都没有声响,只听得见我和姐姐踩在潮湿腐烂的枝叶上发出的啪嗒啪嗒的寂寞的声音。不远处的沟渠里有水哗哗地流淌。鸟雀也午休了,偶尔一只淘气,不肯睡去,忽然从一个枝头飞到另一个枝头,总会吓人一跳。阳光间漏下来,洒在细长的草茎上,有风吹过,那里便像一小段明亮的梦幻的时光在轻轻跳跃。
如果不是姐姐用锄头在潮湿的地面上扒开腐烂的树叶,沉迷于这静寂时光里的我几乎忘记了自己是来做什么的。树叶下是另外一个小却复杂的王国,屎壳郎、毛毛虫、蚂蚁、飞虫都聚集在那里,自得其乐。再往更深处挖掘,就会看到蚯蚓。越是湿润的、肥沃的、腐烂树叶堆积多的地方,越会挖到更多的蚯蚓。姐姐负责在疏松的泥土里挖掘,我则将挖出来的劳动果实捡到罐头瓶子里去。我从来不会用手去抓,而是用细细的木棍把蚯蚓挑到瓶子里去。那可怜的蚯蚓根本来不及逃走,就成了瓮中之鳖。
辛勤劳作两三个小时,我们就可以收获两罐头瓶子的蚯蚓了。相比姐姐,我当然是清闲的,所以有时候她在前面当挖掘机,我则优哉游哉地采摘红的蓝的黄的野花玩。树林里花草多极了,我可以采摘到足够多的花,编织成一个漂亮的花环,戴在自己的脑袋上臭美。母亲嫌麻烦,从来不给我留长头发,甚至有一年因为我身上生了虱子,她又懒得天天帮我捉,一气之下给我剃了光头!啊,我就这样顶着光秃秃的脑壳,天天在学校里接受别人的嘲笑,最后我固执地在大夏天戴了一顶冬天的帽子去上学。那真是有些屈辱的时光。我在树林里戴上漂亮的花环,自得其乐。姐姐只顾着翻找蚯蚓,没时间给我白眼,除非她喊我很多声,我都不搭理她,她才会气呼呼地过来打我后背一下。
我这样沉迷在想象中的世界里的时候,竟然没注意地上的罐头瓶子被碰倒了,蚯蚓争先恐后地逃离了牢笼,等姐姐发现这一意外事故的时候,蚯蚓已经跑得七零八落。我怕回家挨母亲臭骂,只能硬着头皮用手迅速地将蚯蚓们抓回瓶子里去。这简直太可怕了,好像手里抓了一堆刚刚出生的小蛇一样,滑腻腻、软绵绵的,我全身鸡皮疙瘩都起来了;又像半夜里遇了鬼,而且那鬼还是在你的背后,伸出一只白森森的爪子来,你汗毛倒竖,却不敢回头看一眼。
等我回来的时候,姐姐已经收拾好了东西,要打道回家了。我编好的花环,被姐姐随意踩踏一番后早已失去了初时的灵动。我知道即便姐姐没有故意踩上一脚,我也不敢拿回家去,因为怕她告状说蚯蚓被我放走了一半。一路提着两小罐蚯蚓,有些提心吊胆,不知道前面一声不吭气呼呼走着的姐姐到了家里怎么跟我算账。瓶子里的蚯蚓拥挤在一起,发出沙沙的响声,好像暗夜里的蚕,听起来有些孤独。我恨不能自己变成一条蚯蚓,混迹在模糊的群体里,分不清哪一个是我。
好在,母亲总是忙着做晚饭,没有功夫听姐姐汇报挖蚯蚓的战绩。她不过是匆匆扫上一眼,说一句倒给鸡吃去吧,便忙着搅拌玉米粥去了。鸡像是听懂了母亲的命令,原本已经在窝里懒洋洋地准备休息了,这时候呼啦一下子全围了过来,眼巴巴地瞅着我瓶子里的蚯蚓。我小心翼翼地掀开鸡网,将蚯蚓快速地倒在地上,而后连瓶子也不想要,就盖上了鸡网。母亲眼睛厉害,喊一句,快将瓶子拣出来,拉得上面全是鸡屎,下次怎么用?!我只好重新将胳膊伸到鸡网里去,拽出瓶子来,无意中将一个想要逃回瓶子去的蚯蚓给拉了出来。但一只母鸡眼尖,趁我不备,将脑袋伸出鸡网来。只是那母鸡没啄准,落在了我的手上。我一声大叫,哭着向母亲告状,不想却被母亲一通臭骂,骂我办事不利索,真是笨到家了,被只鸡欺负。
我悄无声息地走到院子的一个角落里,蹲在一棵梧桐树下。暮色已经浮上来了,邻居家的女人也在骂自家的孩子。我觉得有些孤独,好像那一只被鸡漏掉啄食的蚯蚓。我很想知道那一只蚯蚓去了哪里,却又懒得动弹。抬头看看天空,月亮已经升上来了。那只蚯蚓在月亮底下会迷路吗?这个问题,我想到快上床的时候,但终究没有想出答案。
村南头的大水塘里,一到下雨就涨满了水。小孩子一个猛子扎进去游泳,男人们则坐在水塘边钓鱼。他们都是有备而来,早早地派遣女人去捡拾一小罐蚯蚓,而后搬着马扎,拿着鱼竿,带上自家小儿,去了村头。水塘边早就集聚了一群人,女人们抱着孩子看跃上水面的鱼,鸽子一样叽叽咕咕地点评水里扎猛子的男孩子里谁家的儿子屁股大,小鸡鸡也长;又顺便指挥自家男人,将鱼钩上的蚯蚓投放到哪儿去,才能让鱼顺利上钩。如果蚯蚓被鱼偷吃了,女人会失望地喊叫起来,抱怨男人手笨。那坐在马扎上钓鱼的男人听了,当然不舒服,骂一句娘,让女人回家待着去!女人一撇嘴,人群里丢一句,我看你今天就是把蚯蚓全喂了鱼,也别指望能钓上一条来!男人听了愈发烦躁,顺手操起旁边盛放蚯蚓的罐头瓶子,啪一声丢进水里去。那瓶子在水里浮了一会儿,蚯蚓们则纷纷借此爬出来,而后一条一条飘向水塘边去;过了片刻,水漫进了瓶子里,咣当一声,那瓶子沉了底。只有蚯蚓們在水里起起伏伏,终于一点点靠近了岸边的水草,艰难地爬了上去。
水塘边的人看着,觉得这一场夫妻之间的争吵没有扩大,实在无聊,于是再随便瞟一眼那些不知所踪的蚯蚓,还有怎么也不肯上钩的鱼,便彼此说着闲话散去了。
我拿着小棍,试图将被水草拦住的一条蚯蚓救上岸来,却不小心差点滑下水去。我在惊吓中发了一会儿呆,起身跺一下发麻的脚,也跟着走开了。
那只缠在水草上的蚯蚓,究竟怎么回到泥土里去的呢,我始终不知道答案。
壁虎
天气暖和起来以后,院子低矮的土墙上,猪圈的顶棚上,石头缝里,房间的角落里,屋顶大梁上,甚至睡觉时的蚊帐上,随处可见到长相不那么讨喜的壁虎。在黄昏的时候,我搬开一块石头,无意中看到趴在地上的灰色壁虎,常会吓一跳。那只壁虎也好像受了我的惊吓,一时间愣在原地,不知该朝哪儿去,片刻后,它才回过神来,消失在一堆乱石瓦块中。
乡下管壁虎叫蝎虎子,大约觉得它们跟蝎子屬于长相骇人的物种。五月端午的时候,虫子纷纷出洞,家家户户要驱“五毒”,这五毒里,除了蛇、癞蛤蟆、蝎子、蜈蚣之外,还有攀爬高手壁虎。在自家院子里,其余四个“毒虫”并不太常见,至少不会明目张胆地四处乱爬,所以属于不轻易扰民的类型。但是壁虎从来不知躲避人,它们似乎很喜欢跟人一起居住。石灰腻成的墙上,挂着晒干的辣椒啊、豆角啊、丝瓜啊之类吃食,壁虎也自由自在地穿梭其中。当然,它们只在黄昏抵达之后,借着夜色自由穿行。夜晚,院子里的灯一打开,如果哪面墙上没有十只八只壁虎在寻觅食物,人反而会觉得奇怪,甚至有一点寂寞,好像庭院里缺少了一些生机似的。
大约是天天与壁虎见面的缘故,所以虽然不喜欢这小虫的长相,但是我也没有怕到一定要消灭它们的地步。况且,壁虎是吃蚊子的高手,即便被大人灌输了不知有无根据的壁虎尿液有毒的观念,但还是跟壁虎保持着互不干涉的态度。况且,它们的皮肤软软的,样子也有些像长了四肢的蛇,我避之不及,又怎么会故意地去招惹它们?
无事可做的傍晚,我会坐在院子里,一边拍打着蒲扇,一边看墙上的壁虎陆陆续续地出来觅食。壁虎的脚像吸盘一样,可以紧紧地吸附在任何物体上,这让它们看起来很像武侠电影里飞檐走壁、无所不能的英雄。每次看到它们在墙上如履平地一般地爬来爬去,还时不时地探出脑袋来将半空里的蚊子瞬间吃掉,但自己从不会掉落下来,我便心生羡慕,想着如果自己也可以这样爬到邻居家墙头上去,看一眼家家户户在做什么,或者在静夜里偷听隔壁胖婶绵绵不绝地大骂,再或爬到高高的屋顶上,看看万籁俱寂的深夜里月亮上到底有没有嫦娥和玉兔,那该多好!
壁虎当然不会理会我的胡思乱想,它们是这个世界上最专注的捕食专家,它们不需要阳光的温暖,也不需要人类的打扰,只要有蚊虫存在,恰好没有瓢泼大雨,便是好年景了。为了一只蚊虫,它们可以一动不动地在黑暗的墙壁上或者屋檐下趴上许久。我半夜起来撒尿,经常会看到壁虎屏气凝神地在纱窗上趴着。当然,也可能已经不是最初我上床睡觉时见到的那只,因为它们长得如此相似,很少有人能够区别出这一只纱窗上的壁虎跟另外一只矮墙上的壁虎有什么不同。人也没有这样的闲情逸致去跟一只壁虎逗趣。因为人总是想,与其那样无聊,还不如去跟村南头的铁蛋兄弟干上一架。乡下的人不能闲着,一闲着就觉得无趣,总是要找些不相干的什么人道些家长里短才好。
壁虎就不一样了。人害怕壁虎,壁虎也恐惧人。人觉得壁虎长相瘆人,又丑,看见了总要绕道而行或者嗤之以鼻地叫骂几句。人们丝毫不觉得它们捕捉蚊虫对人是有益的。壁虎也怕面目狰狞的人。看人们在院子里为柴米油盐的琐事争吵,或者毫不留情地拿着笤帚疙瘩追打光屁股的小孩,将原本可以安静的庭院弄得鸡飞狗跳,它们便怕,急忙地爬到更高的墙壁上,躲在一处电灯昏黄的光线照不到的阴影里,悄无声息地等待院子里的波澜慢慢平息,重新回归静寂。
公的壁虎是会叫的,静夜里仔细听,从墙角处会传来“唧唧唧”“吱吱吱”或者“嘶嘶嘶”的声音,类似于蟋蟀的鸣叫,但又不尽相同。不过除非求偶或者受到攻击,它们基本上会无声无息地待着,不给人增添任何的麻烦,更不会像人恶意揣测的那样,爬到人的衣服上或者后背上去。大多数时候,人与壁虎还是能够和平共处的。即便它们偶尔爬到卧室里,挂在蚊帐上,也很快在人的吼声里,迅速地消失在橱柜后面或者人永远无法抵达的角落里。
我总怀疑壁虎是被孙悟空之类的神秘人物给施了妖法,将图画书里南美雨林中的食人鳄鱼像金箍棒一样缩小了,扔到了我们乡下来。好在它们体型很小,不至于吃人,所以我才能安全地坐在院子里,看它们目不转睛地捕捉蚊虫。我还怀疑它们身上有一种甜蜜的味道,否则怎么会吸引那些会飞的蚊虫傻乎乎地靠近它们?当然,它们也会自己爬到靠近灯光的屋檐下或者电线杆上,尽可能地离蚊虫近一些。可是,一个不会飞翔的小动物,想要捕捉有翅膀的蚊虫,多少还是有些难度的。它们又没有我们小孩子常用的捕捉蜻蜓或者知了的网,单凭一条长长的小细舌头倏地一下伸出来,就能黏住那飞翔的蚊虫,这功力实在比武侠电影里的英雄们厉害多了。就连我们人,也没有壁虎能耐大,捕捉蚊子全靠喷药,或者挂起蚊帐隔绝。壁虎可是要靠捕蚊虫为生的,如果没有一点真本事,怕是活不过一个夏天就饿死了。
但有时候夜晚站在墙根旁,无意中半空滴下湿漉漉的水珠来,我还是充满了恐惧,不知那水珠到底是不是壁虎的尿液,因为大人们都说,壁虎的尿有剧毒,滴到哪儿哪儿就会溃烂。村里的老人们还讲故事吓唬我们小孩子说,很久很久以前,也是夏天的傍晚,一个女人给自己家的两个孩子洗澡,旁边桌子上有一杯白天喝剩的茶水,孩子们口渴,女人顺手拿过茶水来给他们喝了。片刻之后,两个孩子就消失不见,而盆里的水则变得又浑又腥……我给硬生生地吓住了,甚至一到夏天,连放在外面杯子里的水都不敢喝,怕一不小心自己便化成了一摊脓水,连点骨灰都不留就平白无故地从人间蒸发掉了。
那滴在我手臂上的水珠,到底没有将我的胳膊废弃掉,但我还是一遍又一遍地用肥皂和泥巴清洗手臂,直到胳膊被我搓得像一根红萝卜,我才努力说服自己,那毒液应该被我阻挡在了皮肤外。可是自此看到壁虎,就离它们远远的。那些无虫不捉的男孩子们也很少会大胆地捕捉壁虎,大约也是怕自己溃烂而死吧!我想壁虎一定很喜欢这个虚构的故事和关于它有剧毒的流言吧,因为如此,它们反而可以过逍遥自在的无人打扰的生活。
当然还是会有胆大不怕死的孩子,拿了小棍,在壁虎经过时猛地在尾巴上一击。那壁虎受了惊吓,竟然断掉尾巴,迅速地逃到砖缝里去。那条可怜的尾巴,则在原地骇人地蹦跳几下,才慢慢平息下来。最终,壁虎尾巴当然不会像我们担心的那样,诡异地钻入某个人的耳朵里去。据说,壁虎慢慢会长出新的尾巴,但我还是会想,它会不会思念过去的那一条尾巴呢?在没有尾巴的这段日子里,它会不会嫌弃自己的样子?别的壁虎看见了它,会不会嘲笑它?如果它是一只正在恋爱中的壁虎,那更让人觉得悲伤,不知道另外一半会不会因为它身体的缺陷而掉头走开,不管那一只壁虎嘴里衔了多少美味的蚊虫献给它的爱人。这样想想,人才是最无情的,一个恶作剧却可能让一个壁虎的生活发生扭转性的巨变。
同一条巷子里祥子的奶奶却是不怕壁虎的。她几乎每天都要吃掉几条壁虎!这听起来有些可怕,但却是千真万确的。我是很喜欢祥子奶奶的,她总是笑眯眯的,看见我们小孩子,就从孙子开的小卖铺里偷一粒糖出来,给我们吃。对,她每次只偷一粒水果糖,而后剥开鲜亮的糖纸,放在已经快掉光牙齿的嘴里,咬成几瓣,分给我们吃。因了这点很快就化掉的甜味,我们对祥子奶奶充满了好感,觉得她是一个好人。
可是好人总不像故事书里写的那样会有好报。祥子奶奶得了癌症,癌症当然是会死人的,大家纷纷前去探望,人多嘴杂,不知谁说了一个从哪儿听来的偏方,壁虎是可以治疗癌症的。说者不过是出于安慰,随便说一下罢了,但听的人却上了心。不知道是祥子还是祥子奶奶先动了这个主意,总之,不久之后,我们每天就可以看到祥子在傍晚拿一罐头瓶子,守候在巷子的墙根旁边,等着捕捉壁虎。
祥子那时候还没有娶上媳妇,所以他一个人想捉到几点就捉到几点,丝毫不用担心回家晚了会挨媳妇一顿臭骂。我猜想整个夏天祥子因此被蚊子喝了很多的血。为了不弄断壁虎的尾巴,他每次都小心翼翼地用大的网罩将壁虎套住,而后用手指将其轻轻弹到网罩上,再迅速地放到罐头瓶子里。听说,壁虎一定是活的、完整的,才会对癌症有效。我始终不知道祥子究竟是怎样将壁虎洗干净了,放到馒头里蒸熟了,给奶奶吃的。难道那壁虎不会跑掉吗?难道祥子不怕壁虎的尿液有毒吗?难道祥子奶奶吃壁虎的时候不会呕吐吗?难道那壁虎吃到人的肚子里不会死而复生吗?难道死亡比吃壁虎这件事还要可怕吗?啊,人得有多么大的勇气,才能将这么恐怖的壁虎给吃下去啊!
我每天爬到平房上去,或者在祥子家门口徘徊,却始终没有弄清楚祥子究竟是怎样把壁虎蒸熟,他的奶奶又是怎样一条条地吃了一个夏天的壁虎,以至于我们巷子里的壁虎慢慢地减少,祥子要去另外的胡同里寻找。我只知道,祥子奶奶自此很少出门,偶尔拄着拐杖在巷子里走上一圈,小孩子们总会躲得远远的,好像她浑身都爬满了骇人的壁虎;又好像她已经是一块腐朽烂掉的肉,发出让蚊虫趋之若鹜的臭味,而壁虎也因此慢慢爬滿她的身体。
第二年夏天,祥子没有出门捕捉壁虎,祥子奶奶没有熬过当年的冬天。巷子两边的石灰墙上,又开始有三三两两的壁虎在黄昏的时候出来寻找食物,或者想念去年夏天断掉的半截尾巴。
只有在壁虎爬到蚊帐上,我睁开眼睛无意中碰到它们并发出一声分贝很高的尖叫时,母亲才会骂我几句,一个蝎虎子,有什么好怕的?!人家祥子奶奶还吃过上百条呢!我不敢再出声了,并不是怕母亲骂我,而是忽然觉得,那壁虎好像化成了祥子奶奶,隔着蚊帐,探头看着我,依然是笑眯眯的,露着为数不多的牙齿。
我蜷缩成小小的一团,又轻手轻脚地拽过枕巾蒙上了眼睛。
我不想打扰那只通了人性的蚊帐上的壁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