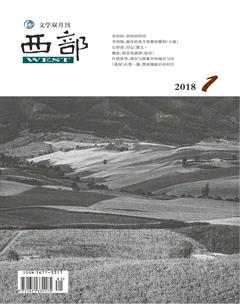驿道上的过客
洪忠佩
从来没有走得这么难。我觉得我不是在前行,而是在后退——向着山村时间与空间的后面退,那样急切与刻不容缓,生怕去晚了,前方山村的人和事就不见了。在我眼里,驿道与村庄不仅有一根流转的连线,还有当下一个难解的死结。
一
走进大秋岭已近腊月,绵延的山峦曾有过怎样憾人的秋色,在我心中仍然是个谜。据说,大秋岭“以山势秋秋跄跄,腾骧磊落而名”,那应是秋天山野色彩很有气势的一种飞跃与奔腾吧。古时,山村能够想到这样句子的人,想必是喝了不少墨水的。
大秋岭上的猫儿刺(枸骨)是青的,草却枯了,枫香的树叶落了地,而黄枝(黄栀子)、罗英(金樱子)黄的红的吊在枝头,特别醒目。许是脚步声惊扰了茅丛中的雉鸡,扑地飞出一群。远处,分明有一只白色的锦鸡在林间慢悠悠地散步。麻雀与黄瓜鸟(绿鹦嘴鹎)更是热闹了,一路都是它们灵动的身影。麻雀和黄瓜鸟个体不大,声音也细碎,但欢快地啄着虫豸的神情是一样的。
跨在路上的半山亭,已经塌了一半,破败得不成样子了,横梁露着半截,椽都断了,瓦砾满地都是,亭顶现出一片天光。即便这样,亭内的光还是有明暗。半山亭,原本是供过往路人歇息的场所,显然,这样的功用已经不复存在了。
这,只是山岭的荒僻吗?
不尽然吧。
山风吹来,阳光滤过树叶,蜿蜒的石岭一路光怪陆离。脚踩在枯叶上,沙沙地响。徒步上岭,讲究的是脚力与耐力。我的脚步是缓的,不疾不徐,这样走似乎特别适合徒步驿道。山岔口岭洞(永济洞)的出现,尤其是洞壁上刻着的《永济洞记》,着实让我心生欢喜。“婺北六十里,有大秋岭,延山里而峻,行者饮倦。其北麓有大小二洞,不可以涉。先是灵泉公伐石为桥,岭之头筑洞……于佑于佑于兴公,素知为纪其长岁月,以徽其济之永也。”《永济洞记》是一位名叫汪夫卷的人在万历甲戌年(1574)十月撰的,记的是先祖灵泉公与兴公建桥筑洞的事迹。
在此前,有多少人读过这样的文字呢?
遗憾的是,我读到的是风化的版本。这沉静辽阔的山野,还有多少人和事在风化?我无从查考写《永济洞记》作者的生平,他应是山野村庄文字优秀的代表。
实际上,永济洞不是从山体穿过的,而是用青石卷砌的,整体的样貌像城门洞,抑或关隘,洞顶却长满了免枧(檵木)、栲树、栎树、荷树(木荷)以及黄檀。《永济洞记》上说,北麓有大小二洞,可除了岭洞(永济洞),另外一洞却不知所踪。在徒步大秋岭前,对面山从港头至大汜的斑竹岭我穿行了,没有发现青石卷筑的岭洞,一路上只有三座路亭(其中两座亭顶已经坍塌)。
顺着永济洞下,是去汪槎的山岭,横过洞口,拐弯,则是通往大秋岭村的小径。其周边呢,有“罗岭十八肩,肩肩叫黄天”的说法,可见岭的陡峭与村民出行的困难。我对肇奇兄说,既然徒步在大秋岭,何不去大秋岭村中走一遭呢。
山嶺与小径,似乎是埋在大秋岭村的伏笔。能够听到狗吠与鸡鸣,贴在山上的大秋岭村就展现在眼前了。与周边的港头、汪槎、大汜相比,六十多户人家的大秋岭村格局显得小了。村舍倚着山,板壁的,砖墙的,混搭在一起,有的木柱作撑,屋底直接是空的,而有的前屋二楼几乎与屋后的路面齐平。然而,大秋岭村的始祖在明朝末年从庆源迁到这里时,对村庄布局是否是同样的构想呢?他们很难想到一脉相衍,村庄几百年后会如此拥挤。
或许,高耸的香樟、枫香,开凿的石池以及废弃的石础、石磨、陶罐是村庄最初的遗存。
一间小得不能再小的阁楼,一块水泥板连接路面,柜台也没有,货在木架上散堆着,这应是我看到的最小的百货店了。店门敞开,店的主人却不在。
偶尔,我在村巷里遇到了两个上山砍柴的妇女,其中一个是早年从汪槎嫁到大秋岭村的,她的三个子女都在外地打工。家里有女人,锅灶就不会冷。在村口的池塘边,我还遇到了年过八旬的詹树庆老人,他挑着一担粪,应是刚刚从菜园归来。
逼兀,局促,迟暮,倦怠,缺少人气,是我对大秋岭村的第一感觉。詹时女老人的喘息与她拉手锯的声音一样,时断时续。她坐在门前的木凳上,艰难地锯着毛竹当柴火。老人说,儿子在外地打工,自己病了,媳妇只好回来照顾她。去县城住了几天医院,好点就回来了,能够动就做点事,儿子媳妇养家糊口不容易。一顶毛绳帽遮住了老人的脑袋,她抬头的时候,我看到她浑浊的双眼含着泪水。
嚇呼,嚇呼,手锯能够锯断毛竹,却锯不断老人的孤独。老人撩起布满油渍的围裙擦了擦眼泪,无奈地叹了口气。
巷口老屋的砖墙,倒了一截。那豁口,一如老人残缺的牙床。
二
皴裂的手指,有三道血红的伤口;裸露的手背上,也有了细微的裂痕。老人不管不顾,还是若无其事地背起塞满了萝卜菜(萝卜缨子)的菜篮,佝着身子走了。狭长的田埂,瘦小的身体,让装满萝卜菜的菜篮更加臃肿。
如此仓促的相遇,还没容我打听老人的姓名与年纪,老人就走远了。她那皴裂的伤口,让我感到了来自山村寒冷的尖锐。
村,建在山坳拱起的地方,塘窟的村名也恰如其分。三四十户人家,圈在一块土坦周边,倒也密集,好比是大家冬天里围着火炉盆烤火。土坦上堆满了杉树圆木,还有竹筛竹盘里晒着的番薯干(红薯干)。向着村头的平鼻岭走,山坡地上是高矮不一的茶园。像天外的“飞来石”,一块巨大的山石斜斜地耸立在路边(约莫有两层楼那么高,六十度倾斜)。挨着巨石,还有村民传说的“仙人洞”。民间道听途说的神话故事多了去,还是村民老张的一句话实用,“仙人洞”呀,是村民上山躲雨的地方。
老张在平鼻岭驮树,正好在“飞来石”旁歇气。六十三岁的他,从山上驮来的杉树圆木大约有一百三十斤左右。他的腰与肩膀混淆了他的年龄。
虽然是冬天枯水季节,山涧里依然淌着水响。陡,是平鼻岭的标志。石韦、矮脚茶(平地木)、络石藤(络石)、石林珠(铁角蕨)、箬皮(箬叶)、猴狲刮屁股(鸡血藤),随着岭边石缝长。一个六七岁的小女孩,拖着两根刀柄粗的杂树棍,一脚深一脚浅地迎面走来。
我问她,怎么不放在肩膀上驮。
她仰着红扑扑的脸,羞涩地应道,驮不动哩。
在城里的孩子觉得书包与课业负担重的时候,山里的小孩已经跟着母亲上山驮柴了。
这,便是城乡孩子的差别之一吧。
岭边的杉树林,密而直,根根都是一梢线。林中的杉树,大的都可以取材做房屋的木柱了,小的还只有木笐般粗。越往上,灌木、乔木混杂,落叶的、常青的都有。在密林中的岭上绕来绕去,真的有点像上山的蛇行。
山脊上的石亭,从挂在亭壁上的“功德排(牌)”上看,还是八年前村民自发修缮过的。按照婺源的民间信仰,石亭中设有神龛,供奉地方菩萨——泗州大圣。不知是何缘故,神龛在修缮时散失了。我由此想到在下港头关帝庙前一位村民磕头作揖的样子,我问他拜的是什么菩萨,他摇摇头,转身走了,留给我只是一个躬身的背影……与亭相连的石屋,早已塌了。据说,石屋曾经住着一位姓张的烧茶人,于是便有了石屋茶亭的来历。亭边的石井被枯叶堵了,但还可以看到水痕。如果时间退回五十年前,石屋有人施茶,石亭有人歇脚,还有人在亭中背起行囊继续上路。
而消隐的,只是亭中的烧茶人吗?
在这样的山野石亭之中,恍惚时间是静止的。亭前,立着一块青石的山林禁碑。那碑上的年代,是我未曾到过的。因此,青石的石碑给我展现的不仅是风雨剥蚀的一面。
我翻过平鼻岭,是要去石屋坑村—— 一个落在安徽休宁地界,从婺源甲路与清华迁去的村庄。在石屋坑村,一口纯正的婺源话,是村民最好的胎记。
三
雨雾。丛林。荒径。
落叶与腐殖土厚厚的一层,一径往上都是野猪经过的痕迹。横亘路边的原木、树兜,长出了一朵朵的菌类,像开在树兜原木上的花朵,红的鲜润,白的纯净,让徒步的路上有了活脱脱的喜感。背风向阳的坡地上,还有穿山甲挖出的新土。老齐一边走一边琢磨,总觉得不对劲,他掏出手机给新岭下村的老张打电话,说山路有岔口,像是迷路了。老齐是西源茶坑人,在石峡林做茶多年,曾好几次带我进山访古,去寻找西源村庄的历史积层,但遇到这样的情形还是头一次。老齐觉得冒着雨雾走了这么长的山路,找不到青石洞(永新亭),总是歉疚。是呀,当年广为人知的“大路”,怎么就逐渐被人遗忘了呢?
原准备从朱家村进坞上岭去紫云亭与天竺庵,在朱家祠堂门口被村里老人劝住了,说是雨雾路荒,进不得山,于是改道走了新岭。出乎意料的是,新岭也荒得够呛,狗脊、贯众、悬钩子、牛郎挡(南五味子)、芭茅、荆棘、络石藤(络石)以及蜘蛛网交织一起,每走一段都是对步行者勇气与毅力的考量。麻雀、长皮鸟(寿带鸟),还有雉鸡喳喳咕咕地叫得欢,它们像山涧里潺潺的流水,只听见声音,却很难看到它们的踪迹。新岭建有岭脚亭、岭脊亭、腰亭三座石亭。岭脚亭的“助银碑记”上,依稀能够辨出俞姓和胡、王、金姓捐银人名以及“清乾隆十三年(1748)吉旦”等字樣。在遥远的年月,新岭岭脊亭是由思溪村“思本堂”买下岭上的山场,把林木的收入用来作为住亭人员烧茶的支出的。为了烧茶方便,岭脊亭边还专门凿了“冷水窟”(一眼泉)。而这些,都像山径一样荒芜了。往山上走,个别路段还残存驿道的痕迹,有的路段直接被土石覆盖了。檵木、枫香、栗树、楮树、栲树、枞树,共同组成了山路边的林相,偶尔还夹杂在几株梧桐与柽籽树(油茶),交合、遮蔽。天阴,雾重,荒径在树林里穿行,前方仿佛幻境。有青石板的台阶,长出了苔藓,缺失了青石板的土路,有腐叶覆盖。尽管小心翼翼地走,还是感觉到滑。空气中除了雨雾的气息,还有腐殖土的气息。惊喜的是,走在这样的山林中,飘飞的落叶美得叫人咂舌,黄色的、红色的,缓缓地飘落,宛如蝶影。迷惑与幻觉,是我在林中穿行时首先想到的词汇。
九里岚培十三弯是一个笼统的说法,其分别与秋口梓槎、浙源沱口、清华大坞交界,山与山之间都有古驿道相连。驿道三五里之间,建有路亭,路亭中设有神龛,大多供奉的是婺源的地方菩萨——泗州大圣。相传,泗州大圣是婺源乡村的地方菩萨,护佑着一方山乡的平和与安宁。神龛简朴,只在一块青石上刻有“南无泗州大圣尊神之位”的字样。七转八转,终于找到了藏于山体用平整的青石砌起的青石洞,殊异的是,神龛中供奉的是一尊石雕的佛像,神龛上刻着“阿弥陀佛”。西源,是一个民间信仰多元的地方,土地庙、社公庙、关帝庙、晏公庙。还有一个村庄不仅有太尉庙,而且直接用太尉庙作了村名。所有这些,都应是山村人精神取暖的地方吧。据说,青石洞的佛像早年曾经被邻村的一位篾匠偷去卖了。结果呢,篾匠的精神失常了。后来,村民想尽办法才把佛像请回了青石洞。祖祖辈辈居于山村的村民,在一尊佛像上找到了一份心安。长在青石洞洞顶的树木,根裸露着,洞前有青石堆起的半截石墙,好比是村庄老屋的照壁。我与老齐站在洞口的雨雾中,静默不语。
在西源的村庄,我在水口看过许多庙,也看到了禁示碑、养生碑、桥碑、孤魂总祭碑,不去想村庄的历史过往都难。譬如,太尉庙既是庙名亦是村名,我觉得很难理解。太尉的官衔可上溯到秦汉,为正一品。而偏远的西源山村,怎么会与太尉有所关联呢?据说,太尉庙供奉的三尊神像是父、子、孙三代太尉,村名也因此而来。令人疑惑的是,婺源村庄为何仅此一村有太尉庙,父、子、孙三代太蔚又是何许人呢?历史上,确有“杨氏一门三太尉”——东汉文学家杨修的曾祖父杨秉、祖父杨赐、父杨彪——东汉延熹五年(公元162年)杨秉代刘炬为太尉,熹平五年(公元176年)杨赐官拜太尉,献帝时杨彪授太尉之职。那遥远的年月,杨氏与此地有何勾联,又遗存怎样的基因,却不知端倪。锁口潭的晏公庙,在婺源乡村也是个特例。晏公(晏戍仔),明代玉封为“神霄玉府晏公都督大元帅”,在民间被奉为一方水神。晏公庙在什么年月,又是怎样的际遇落户西源山村呢?从胡家村进长田坞走长田岭,路边一块风化的断碑引起了我的兴趣。石碑是光绪元年(公元1875年)冬月重修长田岭刻的,依稀可辨出刻录的是坞头、胡家、西源村民的捐款人名。长田岭最初的建设年月已经无从知晓了,还好,让我找到了一块一百多年前重修长田岭的断碑,一如让我看到了久远年月民间精神的标本。
相对而言,长田岭比新岭要完整些,岭的宽度也不一样。只是,一路湿漉漉的,落叶太厚,稍不注意,脚下就打滑。在岭腰的地方,耸着坟冢,坟的规模较大。一位在山地里睡熟了的人,他(她)的墓碑不会长高,而坟周边的芭茅与杂树会长。没有看到墓碑,也不知道埋着的是哪一个村的先祖。墓的主人经年在这里看着岭守着山,他(她)是否会孤独呢?会生起这种荒诞的想法,我自己也觉得莫名其妙。老齐告诉我,从长田岭岭脊岔口转下山,还可以走到他的村庄——茶坑。一路走来,只有这一句,老齐的话语说得十分肯定。横过岭脊,密林的路边有路亭,虽然不知道亭名,但亭还是修得比较讲究的:三方亭墙都是用青石垒砌的,青石与青石之间没有任何黏合剂,却平整妥帖。亭只有人字披的梁,盖鳞瓦,却没有柱。亭内靠石墙的两边,设有石块与圆木搭起的木凳,简易、实用。尽管如此,给人的感觉还是一种衰败与荒凉。围着岭脊的路亭转,我没有找到建亭人的踪迹,只在亭内看到了“泗州大圣”的神龛。在这样的山上,隐匿的只是建亭人吗?
雨雾飘忽,根本打不开视野,即便站在山脊,也看不到九里岚培十三弯的轮廓。山野寂寥,雨雾中伫立着我与老齐,还有落寞的路亭,高耸的枞树、栗树、栲树、枫香。
四
塔岭,僻远、隐秘,自古是进出婺源的五条通道之一。五岭分别是如今在安徽休宁县境内的新岭,婺源县境内的羊斗岭、塔岭、对镜岭与芙蓉岭。“山水吾州称绝奇,间生杰出当如之。不行天上五岭路,焉识人间二程诗。”早在元代,诗人方回在《寄还程道益道大昆季诗卷》中就提到了五岭。清代经学家、音韵学家、皖派经学创始人江永(婺源人),还将婺东一带的燕子岭、回头岭、谭公岭、对镜岭、芙蓉岭连成一副饶有趣味的地名对子:“燕子回头见洋际,谭公对镜望芙蓉”……沿着青石板砌起的石岭上塔岭,两边依次是茶树、柽籽树(油茶树)、毛竹、野藤、杉树、灌木。令人讶异的是,石壁上野趣天然的“牛鼻像”还没有看到,一匹牛犊竟横在岭上,茫然而无辜的样子,不知它是在寻找茅草,还是找不到回家的路。我从牛犊眼前或身后绕过,它犹犹豫豫的,一动都不动。走过路边的石亭,涧底就有了潺潺的水响,石板路也缓缓地平了。跨涧的永安桥只有一拱,青石砌成的,规整、平实,石缝里长满了石韦与青藤。紧贴桥边,有一棵不知名的小树,叶面有一层隐隐的霜白,枝头长着小巧圆实的果,样子甚是惹人喜爱。
青山相峙,涧底幽幽。远远地,瀑布从山崖上跌落,形成粗长的白练,在阳光下银光闪烁,如凝滞一般。俗话说,有瀑就有声。然而,我与山崖上的瀑布相隔的距离实在太远了,只见其景而难闻其声。沿途的山涧,清流见底。经过水的冲刷与荡涤,山涧石床呈现着原始的面目,光洁、圆润,没有丝毫的苔藓。临近公济桥的地方,有一片相对阔些的坡地,中间是涧水,水边有落光了叶的柳树,有枯了叶的芭蕉。边上,还有一个小木棚。棚是木板与树皮搭成的,看去有些破败了,没有栅栏,木门虚掩着,门内仿佛有关不住的古意。本想沿着荒芜的小路去木棚探个究竟的,但看到路口有一根干枯的树枝拦着,便打消了念头……木棚的主人在山中是种树、守山,还是狩猎?我是住在文字里的,而曾经住在木棚里的又是谁呢?
石板路伸了下腰,就有一阵阵隆隆的轰鸣声传来。到了一拱的梯云桥,百丈冲瀑布便一览无余。瀑布源于山涧的水流,从山崖交汇的岩口一泻而下,水流呈扇形散布,急切、汹涌,热烈而饱满。奔泻的水冲入龙潭,似带着水的呼啸之声。扎根于崖缝的免枧(檵木),在飘起的水雾中摇曳,找不到静止的机会。
冬天能够有这样的水量,是得益于这漫山遍野的阔叶林吧。
云梯依山势而盘旋,一转一折,向着山的深处蜿蜒。青石板的台阶,台阶边的石护栏,对于开山辟路的先人来说,是一个历史性的叙事。据传,云岭的路面和石栏杆是上溪村程兆第出资修建的。程兆第的母亲经常去齐云山进香,需要途经此地。程兆第看到此处山坡陡峭,路人难行,便下决心修建梯云桥与云岭。由于修建云岭的工程量大,上溪村蛟池寺僧人诚一也加入募化出资,才使云岭得以修复……从溪头上溪村到安徽交界的塔岭村,有十里左右青石铺就的驿道,还有七座石拱桥宛如隐形的路标,路依山势,桥随涧跨,把山水与村落景观链接其中。叮叮当当的凿石声,早已远去,山里只有寒冷的风还在漫游。伫立梯云桥时,我想,即便當地人,也无从知晓个中隐姓埋名的出资建设者有多少。
在这样的山中,我找到了向往的原生地带。石拱的园口桥,卧波于双溪合流处,桥的规模大于一路上的石拱桥。据说,过桥随山路翻山而下,走东流岭、对镜岭,可以到达婺源的龙尾砚(歙砚)产地——砚山村。我曾站在砚山村口想象一位姓叶的猎人,在唐开元时的龙尾山山溪捡到第一块砚石的情景,如果换成其他人,会对“美人面,婴儿肤”的龙尾砚石无动于衷吗?“新安出城二百里,走峰奔峦如斗蚊。陆不通车水不舟,步步穿云到龙尾……其间石有产罗纹,眉子金星相间起。居民山下百余家,鲍戴与王相邻里。凿砺磨形如日生,刻骨镂金磨石髓……不轻不燥禀天然,重实温润如君子……不为金玉资天功,时与文章成里美……”遥想江西诗派的鼻祖黄庭坚当年从歙州出发,以一首《砚山行》对龙尾山进行了观照,四十二行的诗境里,有采石制砚的繁盛,有砚石质地的坚润,还有砚石纹理的妍丽。隔着八百多年的时空,我无缘与诗祖擦肩,只好与他相向而行,走进了塔岭的腹地。我之前去砚山村时,比黄庭坚要幸运得多,路不算难走,还走过了村口的复兴桥,而他是“陆不通车水不舟”。黄庭坚远道而来,不是为了写一首《砚山行》的,而是作为一名官员去督制贡砚……
看到水口高耸繁茂的香樟、枫香、槠树、红豆杉,就意味着要进塔坑村了。塔坑建村于明朝末期,先有江姓迁入,继有毕姓迁入。村庄倚山而建,错落有致,中间有一条岩石裸露的水坑。一路走来,我只遇到一位挑着竹筛与火桶去溪头卖的中年妇女,还有两个去上小学的学生。
竹与木横在水坑上,就成了晒场。竹叉竹笐上晒着的腊肉、火腿,飘逸着浓郁的山村人家生活气息。在我看来,这腊肉、火腿的浓香是对村庄在外打工人员的一种召唤。姓毕的老人说,他们再不回来,家中杀年猪帮衬屠夫抓猪脚的人都没有了。老毕吐了叼在嘴上的烟蒂,神情茫然,他有一手桶匠的技艺,现在却没人请他箍桶了,左邻右舍和邻村村民都买塑料桶、塑料盆过日子。
我虽然是第一次到塔坑村,但这样远离尘嚣的山村似曾相识,却又无法具体到哪一个村庄。从塔坑往前走,便是通往安徽的羊斗岭了。颇有意味的是,一块民国二十三年(1934)九月立的赣皖界碑躺在塔坑一家村民的门口,成了日常的洗衣板。尽管久经时光浸泡,风雨漂洗,但碑石上的字迹依然清晰。
抬头,我的目光碰到了屋檐下一个空空的燕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