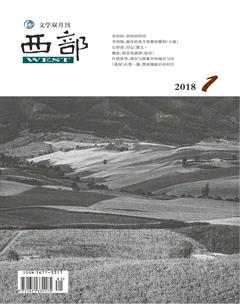布恩山的日出音乐会(外一篇)
骆娟
两千两百零八
清早起床,第一件事是看天气,打开窗户,一股清凉湿润的空气和满眼的星空扑面而来——是晴天,运气真好!
夜雨似乎剛停歇不久,楼外的棚檐上还有水珠掉落的嘀嗒声。为了轻装速行,我搁下手杖,只背了被我塞在背包里委屈了好多天的单反相机,打亮头灯,顶着细细的弦月和灿灿的星光出发了。
进入布恩山的林中小路后,我的身旁渐渐汇集起陌生的队友。黑暗之中,附近的山色和树林都无法看清,只是感觉到并不宽敞的山路蜿蜒而升,大家有序地排着队向上而行。在脚步和登山杖交错的声音中,偶尔传来人们短促的呼吸声和低低的交谈声。空气中是雨后的潮湿以及密集丛林散发出的气息。看不清山景,我跟在陌生徒步者的队伍中,踏着头灯打在石阶上的光亮向上,同时和着自己的脚步数数。大约走了一个小时,我一步不落地数到了两千两百零八步,到达山顶——Poon Hill。
这就是大环线上传说中的布恩山吗?
在上山路上一直低头行走,此时放眼,方能看到星空。只见布恩山上方的暗蓝色夜空似边沿微微低垂的穹幕,山峦的起伏又为这夜幕添了柔美的线条。三千两百米的海拔高度让它在数座世界高峰的拱卫中,像一个小小的平台。而从大环线和小环线汇集到格雷帕尼镇的人们,已经陆续蜂拥到这个平台上。
东方蒙蒙发亮。我们面前环列着的山峰,可以辨识的有鱼尾峰、安娜普尔纳Ⅰ峰、安娜普尔纳南峰、道拉吉里峰和尼日吉里峰。也许是因为一路上都在雪山之间行走,乍一看到群峰耸立在眼前,竟先会去想着对应它们的名字以及分辨它们的七千米或八千米级海拔位列。
可是,我们来到此处,真的是因为记住了这些雪山的名字和海拔高度吗?
队友们也陆续到达了布恩山顶,十几个人一撒进平台上的人群中就看不到了。大家各自寻找着合适的角度和位置,有的攀上平台中间的铁塔观景台,有的架好三脚架和相机,有的用手机拍摄或者自拍着,有些队友簇堆谈天,有的情侣依偎取暖,也有几个像我这样没头没脑地在人群中四处溜达的。呵,在黎明即将揭幕之前,我有些迷失的感觉——我们,这么多人到这里来做什么?
脑中一片空白,裹紧了衣服站在人群中,呆呆地望着轮廓愈加清晰的雪山。如果说那是梦境,那是因为我从未想象过它此刻的样子。如果说那不是梦境,那是因为我们竟然又与他相遇——人群的拥挤中,一个戴着头灯的老人在我面前转过了身。
是我们一直挂念着的老捷克!我们竟然还能再见,竟然离得这么近。我们开心地笑着,这一刻,天有多遥,地又有多远呢!
我们需要圣殿
站在布恩山顶上,一路急行上山的气息渐渐平缓下来,心也终于松弛而宁静了。斗转星移间,东方呈现出淡淡橘色,守候在布恩山上的人群渐渐停止了躁动喧杂。所有的人,我身边陌生的情侣、各色人群,包括我,都静静地望向远处——那里不是地平线,却是日出时分的山冈。
山冈上满是阔叶林,此刻山脊在逆光中伫立着一排树木,每棵树的挺拔树干和交错枝叶都有着人工刻绘的绝妙,树荫缝隙间透过的光影也有着精微的细节。整面山谷还在混沌的暗沉之中。
这是一场日出音乐会吗?
站在布恩山的这个平台上,我突然闪过了这样的念头。
这多像一场美妙乐章的开篇序曲呵——当光亮逐渐聚集在雪山的峰尖,朝阳的一侧闪闪发光,宛如第一节低缓而深情的曲调,它是这个最接近神灵的国度为平淡时光最隆重的揭幕。那一瞬间,停滞成永恒不变的节律,而神圣感自苍凉空间升腾弥漫,世间所有都沉浸在上苍的眷顾之中。
不久,篇章翻动,山顶的积雪在晨风中轻轻扬起,聚成旗云展动不停。而天空中增添了更多丰富的色彩,云霞的绚丽和雪峰的灿亮,山谷中由暗及明呈现的浓绿以及映照在布恩山这个平台上暖暖的橘黄色光晕,让我们与周遭的所有一起沉浸在日出之美中。
它不只是世界高峰的日出,不只是喜马拉雅山麓的日出,不只是大环线或者布恩山的日出。不只是这些呵,它还是天空中每一缕浮云的日出,是山坡上每一株树木的日出,是草地上每一粒露珠的日出,是村落里每一个沉睡的人的日出。它还是加德满都山谷中的神庙殿堂和生活其间的人群的日出,是巴德岗、帕坦、博大拿的日出,是杜巴广场、孔雀窗、野鸟和猴群们的日出。
是的,不只是这些,它还是我们跨过的每一条河流的日出,是我们经过的每一个村庄的日出,是我们看过的每一道瀑布的日出,是我们深深浅浅的每一个脚印的日出。
日出仍在继续,它将更深厚的吟唱呈现给了山坡上的树木、灌丛、野花和蒿草以及能够覆盖到更广阔天际的方向,也同时唤醒着我们心中积蕴的更多美好感受。
在朝向道拉吉里群峰的山坡边,摆着两张条椅。那是专门给我们这些风尘仆仆徒步而行的游子准备的。此时,它旁边的树丛上,挂满了人们敬献的经幡和鲜花花环,而那椅背木条上,还悬垂着大颗的水珠,像是五线谱上的乐符,在间歇中缓缓地落下。
坐在那张长椅上,寒意彻骨,风声入耳,我的手冰凉,心却像有火在燃烧着。这日出,让我意识到,此刻守候在布恩山上的所有人,都并非遥途远路上寻花观景的过客。这一程人生苦旅对自我与精神的琢刻,与此刻造物主勾勒河流、描绘山川的过程无形之中相契合。
当我们眺望雪山和云层的高远,俯瞰山谷和湖泊的宁静,倚靠在树木和石头上休息,追拍着猛禽和岩羊时,我们所身处的自然其实都始终密密关联着,包括我们自己,也正是它的一分子。否则,为何我们如此迷恋这世界上所有与美有关的事物,那些深深根植于我们内心的东西,始终都在左右着我们的灵魂和精神,让我们一刻不停地向往并寻找着这似曾相识而浑然一体的关联。
是它,让我们的身体变得透明,盛放着山野的芳香和冰雪的纯净,让我们的心为大自然的壮美而悸动、震颤。我想起约翰·缪尔曾说过的那句话:“我们离不开食物,也离不开大自然的壮美。我们需要乐园,也需要圣殿。”他是我最喜欢也最信服的自然圣徒。是的,正如他所说,我们,人类,不仅仅是自然的欣赏者、追慕者,享受着大自然的灵光与圣境,也体会着人世间的赞美和欢乐,并能够将所有美好和热爱传递下去。我们也是真正的自然之子呵,如一滴水珠,如一片草叶,如一缕阳光,与万物同享于此的幸福。
两个小时后,光线转为平淡,却将温暖给予了这片空地。作为最后一批离开布恩山的日出观光客,我们穿越密林山径,狂奔下山。
我不知道
这一天的下山路与从陀龙垭口降落到穆格迪纳特有得一比,是两千两百多米海拔的急骤下降。不过,与我们那一日奔向新大陆一般的踌躇满志相比,大环线真正意义上的最后一程让我们走得有些恋恋不舍。
我们与小环线上行的人流交错而过,不断地见到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当我们一步步远离已经熟悉的山谷和河流,那些山间的梯田和田间的屋舍仍然闪亮在正午的阳光中,在雾霭游移中眺望到的对面山谷,更显出亦真亦幻的味道。
看着那些一步步向后退去的老杜鹃树林、叮当铜铃和路边放学少女漆黑的眼眸,都像依然有不绝于耳的乐曲声在山谷间回响。我的气息也随着云端的雪旗而震颤,随着瀑布的飞泻而奔涌,随着溪涧的曲折而婉转,随着翠鸟的鸣叫而轻灵,我听见自己心底里发出的一声轻轻叹息。它是那么微弱,像我已经老迈到无力跋涉。
此刻,复又回归到亚热带植被的穿行中,我被高海拔落石砸伤的腿,因受寒而疼痛的胃,被晒伤的脸颊和干裂的嘴唇,它们全都成为我心情低落的印记,也全都成为我情怀激荡的明证。它是时间,是我们深深沉陷着的时间,它也是过往,是我们默默目送着的过往。
在我的身后,队友牧民哥正吹着口哨学着鸟叫轻松地走着,他惟妙惟肖的拟声让我总觉得真有一只鸟在身后。在我面前的山路上,一位母亲头顶着一大包由山下驮来的物品,艰难地攀登在陡峻的石阶上,她的孩子—— 一个长得像极了母亲的男孩,也顶着一个小包袱跟随在后。他们的身后是架设在河道上的铁制吊桥,是凿通在山间的简易道路,是开设于转角处的客栈和商店。
更远处,则是整整齐齐不浪费一块空地的梯田,是晾晒于地头的豆类和垛放于田间的稻谷,是灶间的火和端在手中的食物。在我们所经过的每一段路程上,都并非空虚而深长的秘境和仙域,都包容着的最真实的人类生存。
这里的人们,与冰川切削着的山体,风沙磨蚀着的崖壁,流水冲刷着的岩石,一样存在,一样承受着自然的塑造,也获得着自然的庇护。而我们,在敬畏山川河流的时候,也在学习用同样的敬畏面对这里的人群。
在频频下落的数千级石阶上,大家都说膝盖要走冒烟了,走冒烟了吹灭了再冒烟。据说几公里之外就有公路了,在那里可以搭到车到达那亚布尔(Nayapul)的中转站,再转车前往博卡拉。数月前我们还十分陌生并心怀忐忑的安娜普尔纳大环线——世界第一徒步线路,就这样将要顺利完成了。回望着重重山岭,我恍惚又恍惚,这一路的豪迈迈、悲壮壮、乐颠颠、惨兮兮要如何表述呢?而我所拍到的这些,又哪里能有我亲眼所看到的美那么多呢?
在那树下坐一坐
在海拔的不断下降中,云层越来越浓厚,我们也好像从云端而再次落入幽谷。在急速回转的石板路上,不断出现着我们曾经看到过的那种花树。
花树,高大的树干上满是盛开的粉色花朵,虽然是那么温婉浪漫的花姿,却在它挺拔粗壮的护佑中恣意怒放。在游移的云层和变幻的光线中,眼前的这些花树又开始展动着奇幻的树影,我几乎想要卸下所有的背负,扔下手中的相机,只为了在那树下坐一坐。
就在我小心地在耸立的石径上向下挪动脚步,同时心绪纷乱地不时停步四处眺望时,看到了几个队友停在我前方的陡坡下。如果没有他们的等候,我恐怕没机会停下来了。
大家聚在一起。我们所停步的拐角处,是一棵以极为盛大之势开放的花树,一座石质的休息台正好搭建在树下。就在这棵树下,牧民哥帮我拍下了几张合影。照片上,除了我和队友们,还有我们的尼泊尔背夫南米德普、柔桑、勾唐、拉仁。大家衣服的色彩是最自然的蓝、绿、黄,每个人面对镜头都笑得很灿烂,这种自然、灿烂和其中包含着的真诚、友善,与我们作为背景的那棵花树和它后面的整座山谷都十分契合。
我相信,未来的旅途,无论是无边的荒野,还是浩瀚的山峦,只要一想到这张照片上的笑容,所有关于大环线的往事便会盈满心间,就像这棵大树上盛开满枝的花朵,始终都会那么鲜艳如新。
再一次,远远眺望
还是这一天。最后一程,如果它在整个大環线上最像一个梦的话,那我宁愿我的讲述时断时续,让这梦时醒时回味。我们从落满花瓣的石径连续下行,勾唐依然陪着我,队友南哥带着几个队友边骂边追赶前方疯狂赶路的领队,希望可以慢些走,但前队的节奏就像是在下坡路上滚动着的轱辘,根本慢不下来。
从南哥的对讲机里传来领队零红蝶的呼叫,再过一座桥就结束这段折磨人的石板路了。我站在山边,一次又一次眺望着对面山谷的梯田,它们在光线的游移浮动中正显示出越来越丰富的层次。
很快就要过桥走进这片梯田了,我们将要进入它田间的小路,经过它开着鲜花的人家和正在收割的稻田,就让我站在这里,再一次远远眺望这无边的山野,然后深深地呼吸着,走进它的光影之中。
在路上开始遇到逆向而来夹杂着更多中国队友的队伍,他们都是选择小环线去往布恩山看日出的。一些刚刚投宿客栈的人们新鲜地在村里逛来逛去。看到同胞我们总感觉亲切,不由还会时时像在大环线上相遇外国友人那样,说一句Namaste,但似乎我们是从无人区直直进入了菜市场,无人在意也无人感知到来自雪山的激情。
所幸,在原计划下山的路程中,公路又向前延伸了。我们到一个村子附近,恰好遇到两辆刚到的越野车,领队立马决定包车。虽然人多,但按当地的乘车习惯,大家还是全都挤坐进了车里,背夫们和行李则上了车顶。
山路的颠簸是我们在几程搭车路段已经熟悉的。我挤在前座上,时时被颠到司机身边。他挂挡的时候总会碰到我受伤的腿,可是在山路上的激烈狂颠和窗外风景,早已经让我抛开了腿上的刺痛,尽可能随着这车的颠动调整身体的摆幅。看到路边飞舞着的纯黄、纯蓝色的蝴蝶,心又回到初上大环线的日子里了。
呵,我想,这些路边飞舞的蝴蝶,夜幕背后的满月与星光,山峦重叠的雪岭冰川,它们知道我的感受。此时,极目山谷,我们的来踪与归途自云中一路绵延。如果我们走过的是一路坦途,如果从不曾有尘埃与雨露,如果我们永久地相伴在一起不会说出告别,那么,这所有的遇见里,我还会有那么多、那么复杂而难以自抑的感动吗?
从那亚布尔转车,领队说让背夫米勒提前帮我们租了一辆豪华的大巴,让大家舒舒服服进博卡拉。果然是足够舒服,我一个人坐了两个位置,歪靠在车窗前,身体深陷进座位里。阴云浓郁,有要下雨的迹象。在我们的回望之中,所有的雪山、丛林、梯田和我们走过的那条叫大环线的路,渐次陷没。
这些留在路途上的星光和泪水,在十数天的时间和海拔急升骤降的奔行中渐渐聚拢,成为我们心里盈盈闪动的一泓清澈水面,如镜,映出的容颜,那般熟悉。在梦幻与现实交接的路上,浓雾满山,我喃喃自语,是我们,在一起,曾经与神共舞,心醉而神迷。
这是终点吗?
下午四点多,抵达博卡拉。
站在宾馆过道的长廊下,看着傍晚的天色和高大芭蕉树叶间交错的天空,我还没有从一路徒步行走中回过神来。这是终点吗?
还在恍惚之间,却见到背夫勾唐来找我。看着他的手势和一些能听懂的单词,我明白了,原来他是来告别的,他和南米德普几人要赶去搭车回加德满都。过节了,他们想要早点和家里人在一起。我与他告别,目送他离开。想起他路上一直对我说的、我唯一能记得的话——Slowly,心里有一些难过。还有背夫南米德普、拉仁、南米色仁,我想,我会一直记得他们的名字,并且祝福他们凭自己的努力获得更好的生活和快乐。
背夫领队米勒在我们到达博卡拉后,就在宾馆遇到了另一批要去小环线的中国徒步客,恰好他们正在寻找向导和背夫,当即谈妥,次日就再次出发进山(此后,在微信上,我们看到米勒进山带队徒步的照片,多数陪同的都是中国客人。生活不易,我们为他的成长感到高兴,但用一句中国老话说,也愿他能好自为之)。
等我们一行人落座在兰花餐厅,点了满桌的肉菜,开启了庆祝大环线顺利完成的啤酒和二锅头时,一场大雨急骤地落下。它来势猛烈,如河水自天而倾,显得有些惊悚夸张。我们站在门口,透过兰花餐厅廊下的那串红灯笼发出的幽光,看着如注的雨帘。一个光头长须的老外坐在靠窗的位置上,这个单身吃客在我们看起来有些诡异。
这异国的店铺之中满是中国元素,餐厅里放着央视的节目,音响里是周杰伦、周华健、张学友、张宇的歌声,但幽幽的光亮之中,影影绰绰地,却让人觉得,像是走进了《丁丁历险记》的片场。
巴拉加,峭壁上的村庄
壁画般陈旧的色调
因为路线变化空余出了时间,领队决定安排大家在马南休整一日。这一天,队友们有在牦牛客栈晒太阳、看书喝茶的,也有攀登刚嘎普尔纳冰川,顺路去看小冰湖的。利用这意外而来的闲暇,我和队友跑焦去拜访了巴拉加(Braga)村。
在我们沿大环线前来马南的道路旁,半个小时路程之外有几处人家和小商店,还有我们去年曾疯抢过的西点房。但是跨过一道水渠,踏着沼泽和草甸缓缓东行,却很快走进了另一个世界——这便是传说中有着九百年历史的巴拉加古村,它似乎遗落很久,无声无息。
在这片海拔四千米地带高耸的山崖下方,形成了天然的环形峭壁,又延伸为缓慢下降到马斯扬第河左岸的山坡。巴拉加村分为两片,居高临下坐落在环形峭壁及周围,北片村落较南片村落更为集中庞杂,背倚陡峭山崖,山脊线崎岖蜿蜒,村落中的房屋群密集簇拥,远看去村子就像紧贴在峭壁之上,但这风化严重的峭壁确是它踞高坐守的安全屏障。
巴拉加村子岩壁上方约高出一千米的山顶上,是一片季节性的牧场,还有一座被称为克衣且湖(Kicho Lake)的小冰湖。我们来到巴拉加村的同一时间,米勒和几个背夫也徒步从村子后山攀上山脊,走三个小时路程去往这个小冰湖。那里是观览安娜普尔纳Ⅲ峰和刚嘎普尔纳峰的绝好视角。
在巴拉加附近,还有米拉日巴(Milarepa)修行洞,这位十一世纪的苦行者,被尊为藏传佛教密宗。我曾在去甘南旅行时,到过合作的九层佛阁——供奉着一千尊米拉日巴像的米拉日巴佛楼阁。巴拉加附近的修行洞便是米拉日巴在喜马拉雅山脉的深谷幽壑中修行的所在。传说他在此处修密宗瑜伽长达九年,终日以荨麻为食,身体发肤全部变成绿色。对于一个修行者而言,无论是在幽深的佛殿,还是高耸的危崖中,他终日趺坐,不为外物所动摇。他是在试图穿透时光的玄机,将自己灵魂的光亮照映在更高處吧?那么他一定会看到山脉高高在上的灵魂,森林茂密繁盛的灵魂,那灵魂,也在一朵微小却盛开的花里,或者一缕盛满尘埃却仍然灿烂的光芒中。
我们离开大道,向山前走去,在地势明显上升之后接近了村子。一棵老树旁的白塔和长长的转经廊提示了我们进村的路口,落叶铺满地面,散养的牛犊随意卧着。屋后的山坡上有带着孩子背拾石块的妇女,还有背负着木料走来的男子。村口渠边有洗衣的老妇,村前的草甸上还有捡拾牛粪的女人。阶梯状的山崖高处,有正在修建的房屋,后来才听说,那将是巴拉加村的第一家客栈。
在偏北处的高崖上,一座藏传佛教寺庙成为这个村子最醒目也是最重要的建筑,它红白相间的颜色和庄严耸立的形制,在周围错落的灰色石制平顶房屋和插在各家屋顶随风飘舞的经幡间,显得深邃而神秘。据说如果遇到那位带钥匙的神秘守门人,就可能有机会进去参观,前提是必须要带上头灯或者手电。虽然我们没有这么幸运,但站在高耸的大殿外,可以想象在殿内阴暗的光线中,那些金佛、雕像、面具、唐卡都蒙着尘埃,但那奇特的魅力定会让人生出无限的敬意。
我们攀上崖壁高处,俯瞰着这个村子。山崖上纵横着风蚀雨淋的沟壑,深绿、褐红的灌木凌乱地附着地表,错落修建着的房屋挤挤挨挨,屋顶都非常干净平整。因为多数房屋都是二三层楼,低层的楼顶搭建着棚檐,远望便像一片由密集洞穴组成的巨型堡垒。巴拉加古村正以壁画般陈旧的色调展示着始终在岁月深处无以言说的神秘。
相比邻近的马南,巴拉加的清幽和僻静使人如置身世外。走在空落的巷道中,我们无从询问,单单那灰暗粗陋的石墙中镶嵌的木窗,那精美的雕刻和古旧的气息,就完全可以为它所承载的时间代言了。
村里大约有超过一半的房屋都已废弃,有的用粗铁丝从外面胡乱拴死了院门,有的不仅上锁,门外还抵着大石块。一些人家院墙上都有堆垒整齐的木柴,全是被阳光晒成深褐色老柴的,必然是已久无人居,而那些在老柴上方垒摞着新柴的人家,屋外便晾晒着衣物,置放着物品,偶尔有人在房顶走动,显示出生活的气息。
这些房屋群落密集,簇拥在狭窄曲折的巷道高墙下。窗户都开设在高处,但屋顶却很平坦宽敞,除了晾晒衣物、搁置物品,它最大的作用还是当地人聚集社交的场所——站在自家屋顶上就可以和邻居聊天了。很明显,巴拉加村有一种半是废墟半鲜活的味道,但每家屋顶都竖立着经幡,风舞幡动,使得整个村子依然为一体。
背牛粪的女人们
巴拉加的村民虽然牧放着牲畜,但是他们也延续着农耕社会的形态,相互依靠,合作劳动。这种互助合作的关系可以较好地利用劳动力,完成简单生活的必需环节。他们从有限的耕地获取简单的食物,并用牦牛和牛奶、毛制品换取所需的粮食和生活用品。劳动的分工在家庭中很简单,男人放牧、耕作或从事贸易,女人打理餐食,并做一些拾粪、背柴的劳动。在这些地方,人们为了生存而形成了密切的联系。他们悉心维系,相互依存地生活着。城市人群中相处所存在的痼疾和沉疴,在这稀薄的空气中无法存留。
在村中一家院落外,我们遇到三位背篓劳动的妇女,她们要将畜圈内的粪土装满背篓,运送到别处。同行跑焦围在她们旁边问长问短,很有些跃跃欲试想要参加劳动的意思。棚圈并不宽敞,只有一个狭窄的通道。妇女们细心地将黑色的粪土装满背篓,还使劲在顶上多培一些,以便有最大限度的背负。
她们大方地将一个装满粪土的背篓摆在跑焦身后,将负重的宽布带套在她的头上,两个人扶着背篓让跑焦起身,却发现她根本无力支撑起这个重量。她们帮着跑焦费劲站起身来,她摇摇晃晃将背篓中的粪土都洒到身上了,妇女们都笑个不停。这个在户外软硬不吃我行我素的女汉子,就这样发现自己也有玩不转的时候。
我们进了在高坡上眺望观察时注意到的一户人家。这家的屋顶晾晒着衣服,并有人走动。走进院子,只见房屋底层存放些草料、杂物,墙角旮旯里整齐地堆放着柴火。但我发现这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屋外的院墙上堆的都是齐整的长条柴火,而院内墙角的则是被截断成小节的,而且都是弯曲的细树枝。不知在当地人的意识里,是不是把柴火也当成自家的财产,摆出去示人的都是齐整漂亮的部分。
我们通过一个用树干掏成的梯子爬上了这家的二层起居室,狭小的露台被阳光晒得暖暖的。男主人叫保门斯英,他六十多岁的老母亲坐在阳光下,手里持着转经筒,神态安然。
保门斯英说,这个村子里现在大约有二百五十口人,以前住着的很多人都搬走了,有的去了博卡拉、加德满都或者其他地方。一些经济条件较好的人家孩子都被送去博卡拉上学。还有一些孩子在村子附近的一所小学上学。他的女儿看起来大约六七岁,一个人坐在厨房灶旁的地铺上,旁边放着点零食,守着一台很小的电视,正看得津津有味。
虽然房间里只有从门外照进来的光,屋中的陈设也是藏区最常见的——摆挂了满墙的生活用品,房梁上挂着一些风干肉,但是从孩子的脸上却能看出与城市生活环境优越的孩子一样的满足和享受感。在沿途村落中与这些孩子们的交流,让我觉得,源于山野生活的许多观念和传统,他们对于幸福的设定非常纯粹。山野生活的自由无羁、充足的阳光和简单的需求,这些都成为最基本也最重要的快乐的实质。
在走出保门斯英家院门时,我们遇到了一位顶着背篓回家的妇女,原来是帮跑焦学习背粪的妇女们当中的一位,她竟然是保门斯英所说在外劳动的妻子。这让我们有种见到亲人的感觉。
短短的时间,在这个村子里,我们竟也被当地人之间密切而单纯的关系所感染,如同与她们有了血脉之间的牵系。人性中最本质的东西无须刻意挖掘,本来就存在。即使蒙上生活的尘土,也会因微笑和友善而映射出深厚的情感。对周遭万物的友善,对生活现状的平静,这也许是一种喜马拉雅山野以及所有僻远地域人们平实生活的真实境遇所展示的内涵吧。
坎多提玲的家
我们又去到了另一户人家,爬上二楼之后,一个小女孩迎了过来。她有着单纯的、甜甜的笑脸。我们用简单的英语向她们表明来意——无非是路上与当地人交流时重复的那几句:“我们来自中国,很喜欢尼泊尔,我们正在进行安娜普尔纳大环线徒步,昨天到达马南,我们将要去往陀龙垭口。”这几句简单的介绍,女孩和她神情温厚的母亲都表示听懂了,尤其是听到“安娜普尔纳”“陀龙垭口”这些关键词时,她们都表情郑重地发出表达认同或是敬佩的感叹词。女孩还时时向她的妈妈做着翻译,后来我们得知,她在博卡拉上小学二年级,假期回家来了。
女孩名叫坎多提玲,十岁。母亲名叫宾巴特芒,四十四岁。宾巴特芒面色恬静,略有些与她年龄不太相符的苍老,但身上散发的母性气息使人感觉亲切。她一直坐在烧着木柴的灶台前,端开煮饭的锅,烧了茶给我们喝。接过配有牛奶和黄油的热茶,我们很快就熟络起来。坎多提玲与新疆农村的孩子没什么区别,有着小女孩天性中的单纯、好奇,又非常活泼大方,虽然在语言交流上还有很大障碍,但是我们彼此间都感觉很亲切。
我和跑焦都想尽办法表达着自己的想法,坎多提玲也忙不迭地向我们展示她的书本,介绍她的学习内容,指着她作业本上未抄写完的尼泊尔雪山作业,念出道拉吉里峰、鱼尾峰等等。当我们问起她的家庭成员时,她立刻拉着我们指点着墙上贴着的几张照片,并且尤其重点说明她在博卡拉工作的叔叔曾经去过北京。在我们再三示意后,这个活泼的女孩略带羞赧地唱了一支英文歌《Little Star》,恰是我們也都熟悉的《小星星》,我和跑焦也用中文跟着她一起唱着,感觉更亲切了。
看到宾巴特芒在做午饭,我们很想尝一尝,实际上我俩原本就打算在巴拉加找家当地人混个饭吃。宾巴特芒始终笑容可掬,她忙着给我们盛米饭和咖喱,坎多提玲带我俩在门外用水壶洗了手,于是我们便端起铜盘像当地人一样用手抓着吃起咖喱饭。除了为咖喱饭配的酸奶,还有小碗的酸奶糌粑。看着我们不知如何下手的窘态,坎多提玲端起一个小碗,用手将酸奶糌粑团成小块,放进嘴里,示意我们学着她的样子。
红茶、咖喱饭、酸奶、糌粑,我们一一品尝,继续比画着聊天。宾巴特芒在灶前忙碌着,一直用疼爱的眼神看着女儿跟我们聊天。当坎多提玲向她翻译我们说的话时,她总是看看女儿再看看我们,会意地点着头。我想,在这样一户喜马拉雅山野人家里,当我和跑焦与宾巴特芒母女坐在一起喝茶、聊天,说着一些彼此能简单理解的话题,从她们的笑容中得到鼓励,让自己平时拘谨、敛静的性格也奔放活泼起来,这本就是旅途和山野的魅力所在吧。
坎多提玲告诉我们,她的爸爸去外面放牦牛了。夏天,她家的牧场就在后山的小冰湖附近——为了说清这段话,她拉起我离开厨房,又爬过两道木梯上到她家最高的房顶,给我们指着屋后山坡上的经幡塔和更高的山顶。我明白,她的意思是那里是通往小冰湖的路,我隐约在山坡上看到米勒他们返回的身影。
因为一直在摆满炊具的灶房待着,我对坎多提玲说想去参观她家的其他房间。她找了好几把钥匙之后,打开了旁边的一间屋子。这是一间佛堂,靠墙供奉着佛像,几个铜碗里盛着清水和粮食作为供品,还摆放着酥油灯盏和熏香。
在这里,当地人的生活与村口的神龛、转经墙、玛尼石、屋顶上的经幡以及家里的佛堂和供奉,都已经成为一个复杂的杂合体。看着坎多提玲的大方单纯,我只是肃立在一旁,并没有随便进入。这是一个家庭中最隐秘的角落。这里的供奉,对于长居此地的人来说,已经成为一种超越精神层面的朴素内容。
完美的下午
坎多提玲告诉我们,她的父亲在河滩的牧场上。我们想请她带路一起去看看,宾巴特芒起初拒绝了这个提议,但坎多提玲向母亲不停撒娇,表示自己很想跟我们一起走,母亲不再犹豫就把孩子交给我们这两个陌生的外国人了。
我和跑焦带着坎多提玲在草滩上游荡着。草滩太大,我们没有找到她的父亲和她家的牦牛群。牦牛们在草甸子上四散觅食,两个姑娘忙着将捡到的牛粪扔在身后的筐里,她们弯腰起身,双手熟练地将捡起的牛粪从头顶扔进筐中,不停动作着。
随着日光西斜,风带着雪山上的寒意从我们耳旁低低掠过。坎多提玲坐到一块大石头上,目光时时围绕着在草滩上拍照的我和跑焦。如同我们认为这片地方所有的一切都是新鲜的那样,在她的世界里,我俩也带给她无限探究乐趣的。
在与我们目光相对时,坎多提玲会抿嘴歪头一笑。这笑容似对家人那般亲切,也似草木的自然摇曳。于我们而言,宇宙的无限、地域的延展和人类生活与共存的现实,无一不是我们日复一日所感受到的内容,无论多么晦涩难解的内核或者喧嚣嘈杂的表象。坎多提玲和她的家人们朴实无华的生活细节,本身就是人世间存在的灵动和洁净,这一切都无需驾驭和掌握,顺其自然就足够了。
这是一个完美的下午。巴拉加村对面马斯扬第河畔的草滩上,天气晴朗,安娜普尔纳Ⅲ峰和它旁边的刚嘎普尔纳峰耸立在蓝色的天幕中,峰峦、冰川、雪脊、山壑、森林直至下方山谷里的草甸,都一如千年地沉寂着。阳光缓缓移动,在这静美无边的空间中,过往无痕,唯留暮色苍凉且温暖。
身处自然的奇妙和宏大之中,我们所有的想象力都得到了无限的延展,好奇心也得到了更多的满足,同时也使我们想要看到更多更纷繁之下的真实与宁静。在这些遥远的时空中,生活本来的样貌并没有在万事万物之中隐匿,只是我们总是没有足够的视野。
把坎多提玲送到回家的路口后,我们回返马南。眺望危崖下的巴拉加村,晚霞正将灿烂的光泽涂抹在这个古村的每一个角落,又缓缓移动留下越来越多的阴影在崖壁下方,村里的人们也都停止了一天的忙碌。
暮色深重,寒意浓郁时,月亮和星星渐渐显映在微暗的天幕上。此時,在查梅,我们曾经路过的大镇,驮帮和商队都在歇脚的客栈门前卸驮准备过夜;在吉雅鲁,那个壮汉老板又迎来了一批费力爬上这个山顶藏寨的徒步客们;在陀龙垭口,一天中正、反向穿越的人们都抵达了宿营地,垭口茶房的老板也已经锁门下山了。在更远一点的格雷帕尼,徒步客们坐在客栈的平台前,面对云雾山间,憧憬着布恩山新一天的日出。
而在我们的身旁,雪山放射着幽幽的光亮,山脊在阴影的上方呈现着柔和的曲线,天空渐次变得色泽深重,像一床厚厚的被子盖在山谷上方。夜幕降临之后,一切都沉入了睡眠,只有星空在灿灿闪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