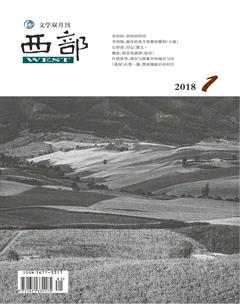所有的黑夜都是黎明
陶群力
现在可真叫安静。远远望去,村子里那些屋子静静地卧在坡上,炊烟也是静静的,在半空中一动不动,云呢,依偎在它们身旁,也静静的。土地、庄稼和家畜们也安生下来,就连崖下的那条白沙河也只是发出轻微的汩汩声。他把蹲成磨盘似的身子挪动了一下,过了片刻,又挪动了一下。许是蹲得久了,或是天空中飞鸟的哀鸣声将他从沉思中唤醒。怎么说呢,随着年岁一日一日地增长,心思也多了起来,心思重,且心结解不开的时候,他便会来这个崖边坐坐,好像来这儿待上一阵儿心里便会好受些。
想起德清那个家伙,心里就堵得慌。混蛋。他在心里骂着这个弟弟。
早晨起来,他给德清打电话。还是不通,说拨打的用户已停机。“停机,停机,停个锤子。”他对着那个黑色小盒子似的家伙嚷嚷。一连几天,他给这家伙打电话都是这样。现在若能够着那张脸,他真想扇他两巴掌。德清最后那次来电话,说:“哥,实在脱不开身啊。公司里有那么多事务要处理,娘你就多替我担待担待了。”德清在电话那头等着哥哥骂他两句,停了许久,说:“钱,我会汇来的。”“嗯?娘是我一个人的娘?不是你的娘吗?你就一辈子也不要回来。”德清在那头还在解释,他就把电话摔在了地上。
这会儿有股风刺啦刺啦地刮到他身上,山风微凉,他颤抖了一下,想,若是这从东面吹来的山风再烈些,或许就能将他如树叶那般刮到山崖下,那样自己就可以安安静静地躺着,再也不用去受活。天空忽然黯淡了片刻,又一下子亮起来,太阳如同一个匆匆往家赶路的老人,摇摇晃晃地朝山脊落下,白色的云、黄色的云、红色的云、紫色的云像一匹匹呼啸的天马,迅疾而来,狂奔而去。
这德清,说句良心话,还是蛮孝顺娘亲的,对我这个哥也是感激和回报的,从山顶下来的时候,他心想。明天得好好张罗张罗戏班子的事儿。他抹了把被山风吹出的眼泪。
“五一”前,德清来电话,说他想家了,“五一”想抽空回来一趟。他没好意思说也想哥来着,只是问:“哥,你身体还好吗?”德清告诉他,这次要带新女朋友一块儿回来,到时候,他要请城里的戏班子来村子好好热闹热闹。德清还说:“请戏班子的时候,就说钱是你出的。”他开玩笑地问德清:“别是你那新女朋友肚子该下崽了吧?” 他这个弟弟没让他少操心,结婚离婚再结婚,好像是一场快乐的游戏。钱,真是好家伙。估摸是遇到难处了。什么难处呢?啊?你有什么难处呢?他边走边想着,喃喃自语。过了野猪林,有条岔道,从这儿可以绕道通往石背坑村。入秋后,河里的水浅,最深的地方也就齐脖子,小时候,他喜欢在那儿戏水玩耍。白沙村与石背坑村隔河相望,看上去很近,抬抬腿,抓住天上的云就能跨过去;但大山很神奇,这近,是一种虚幻,是一种阔大疏朗吧。他想去那儿看看玉琴,也不知怎地,他觉得自己从那天起就变得年轻了,真的,年轻了许多,让他有了欲望、冲动、念想!这种感觉,他弄不明白是不是邪恶龌龊?但这些天就是特别想她,想看看她的眼睛,摸摸她的手,或者就和她背靠背看日头下山,看松鼠从他们身旁窜来窜去。想着这些,眉毛结成了细绳子。他抬头,天已经黑了下来,有几颗黄色的星星在松树上张望。明天再见吧?就不能等上一天?他叹出一口长气。
戏班子的车在山坳处捣鼓喇叭的当口,他正靠在大樟树下打着盹儿,仿佛是飞来的炮弹,把他整个身子猛地给弹到半空中。还好,魂儿还在。恍惚记得梦里自己在白沙河里先是追逐着那条满身斑点的桃花鱼,追着追着,桃花鱼变成了玉琴,玉琴柔软地摆动着雪白的身子,那身子真是好看,像一截长长的藕,动一下,停一下,可他使了吃奶的劲也追不上她。他环顾四周,看到“独手龙”在向他招手。他咧咧嘴,用袖子抹去哈喇子,一边挠脑壳,一边张着大嘴,说:“艺术家辛苦了,辛苦了。”独手龙将墨镜摘下,把深灰色的呢子风衣抖一抖,说:“去你妈的,艺术家?!还艺术大师呢!”
“包叔,我的弟兄在闹情绪呢。”有个胖子擂擂肚皮。
“情緒?什么情绪?”他不解地问那胖子。
独手龙说:“胖子,你个饿鬼,还抗议呢你!”
“进村,进村,”他说,“东西有你吃的,都给备着呢。”走了几步,回转身,忽然想起了什么, “‘牡丹红呢?”他伸长脖颈,往人堆里瞅瞅说。
胖子嬉皮笑脸地说:“泉水叮咚,泉水叮咚。”
众人哄笑起来:“泉水呀泉水,你到哪里去?弹着琴弦流向远方……”
“说啥子嘛。”他嘟嘟囔囔地看着这些人问,陀螺似地转了几个圈,朝四处张望,看到山毛榉林子里走出一个披着红色长大衣、黑发飘飘的女子, 是“牡丹红”。他啐了口唾沫,说:“一帮坏人。”大家跟着他一路笑着上岭。现在他家院场一定挤满了人,他想。或许是激动,也可能是今天的太阳喜欢在他身上抚摸吧,他紫红色的脸上像涂了一层山茶油,泛着光。老远,他就听到了他家的“两头乌”气场十足的狂吠声,那声音带着一种炫耀。快到院子的时候,那条狗蹿了出来,将两只前爪搭到了他的裤腰带上。院子里的那棵香泡树下已经摆放了四张八仙桌,玉琴臂弯里挎着一个竹篮,身子一欠一欠地从篮子里往外掏着什么。
玉琴回转身,正好与他的目光相对,问:“戏班子来啦?”声音很甜,也很火辣。
他没想到玉琴看他的眼神如此大胆,就像是他家的堂客。他搓着两只手,眼睛盯着玉琴说:“来啦,来啦。”他把戏班子迎进堂屋里,他说先歇歇,中午喝点酒晚上演戏的时候就有力道吊嗓子了。堂屋收拾得干干净净,桌子上放着几个大碗,围成一个圈,碗里装着花生、紫皮番薯、芋头、栗子、玉米,看上去煞是可人。客人们只消看它们一眼,就会明白这是个殷实、和美的人家。客人们闹闹哄哄地说笑着,开始感慨起来,说还是山里好啊,什么东西都是绿色食品,说要是有钱了,就来山里买块地,过神仙一样的日子!
玉琴说:“这简单啊,那就和我家换个地方呗。”她那狐狸眼像在说“也别等有钱了”。独手龙说:“山里空气真没得说啊,看看,嫂子那皮肤真是水灵。”
德明拿眼斜睨玉琴,玉琴脸上红一块白一块的,他觉得心头里有种柔软的东西跳了一下,又跳了一下。
戏文还没开唱,那些秋虫啊蚂蚱啊早早地躲到了草丛、玉米秸垛里。狗儿们趴在院场里喘着粗气,舌头伸伸,“呜吱”两下,便垂下脑壳眯上眼。山里人看戏,图的是热闹。“干吗要这样呢?”德明朝狗儿们剜一眼。戏班子演戏,当然是唱、念、做、打,锣鼓镲钹齐齐地上阵了。演什么剧目好呢?大伙儿叽叽喳喳的,好像是商量,却是干仗的架势——有人嚷嚷说:“先来段婺剧《打金枝》。”“规矩也不是不可改的,”德明说,“与时俱进,与时俱进。今天先来个歌曲《好日子》!”下面就有人悄悄议论开了,说:“看样子这家伙真的要当村长了。”还没等开唱,好像虫儿们狗儿们也听明白了,一起齐声唧唧汪汪的,真是热闹啊!喧腾鼓噪了一阵子便安静了下来,他们也知道什么是适可而止、适合时宜,他家院子外的场地上围满了看戏的人。戏开始前,娘问他:“今天是什么日子,吵吵嚷嚷的?”他说是个好日子呗。他娘说:“你搞什么鬼名堂?”“要娶媳妇了呗。”德明晚上喝了点苞谷烧,借着酒劲说:“给你娶个狐狸精样的媳妇?”出房间的时候他问:“娘,要不也抬你去院子外看戏吧?”他娘白了他一眼说:“过一天少一天了。不去。”当戏文演到《合珠记》,牡丹红唱着“更鼓初敲月儿上树梢,时逢佳节月色分外皎”时,他胸腔里好像有许多虫子在撕咬着,有东西要翻腾上来。恍恍惚惚中他听见有人在议论,好像是在说白沙村与石背坑村合并的事情。
“谁出的钱多,就选谁当村长。”龙四爷爷用榆木拐杖戳着地砖说。
“不会来事儿的,也选他当?”
“德明他书读得多,弟弟现在是大老板了。”有个小马头鬼嘘嘘地吹着口哨说。
天空中有几颗小星星拽着长长的黄色尾巴从夜色中划过,煞是好看。他想起了那天,也就是从信安城里回来的那个夜晚。夜也是如此的皎洁,月牙儿倒挂著,在路过野猪林的时候,黑黢黢的,月儿和星星靠得很近,有几只蚂蚱扑腾到他们脸上和怀里。玉米灌浆了,黑绿黑绿的叶子摇出一闪一闪的光来,甚是妩媚婀娜。
“赶场脚啊?看你脸上都成花猫了。”玉琴在他身边喘着气,胸脯耸得老高,“有鬼追我们吗?”玉琴拉着他的手说。
“天快下雨了。”他急促地缩回手,好像玉琴的手是一条冰冷得让他起鸡皮疙瘩的蛇似的。
“累了,走不动了。”玉琴蹲下来,娇嗔地说,“要不你背我走吧?”他白了她一眼,拔腿就走。人的一生,是不是命中注定,他不知道,他也不相信上帝总是用他的那双眼睛在看着芸芸众生。不过,他相信一切皆有缘,因果互生。林子里忽然响起窸窸窣窣的声音,片刻,就传来一阵呼哧呼哧的声响,他迟疑地回身的时候,玉琴忽然环腰抱住了他。
月光皎皎,空气里有淡淡的松香脂的气息吹到院场里。他好像闻到了玉琴身上的香气。
多年之后,当他离开白沙村去了信安城,在水亭门外自己的修鞋摊子上再次见到玉琴时,他仍能清楚地记起来,在那个落满“太阳雨”的燥热的下午与玉琴在信安城相遇的那个“纪念日”。德清“五一”没回来,却没食言,将钱给汇了来,说是请戏班子的事就放到中秋吧。德明原本打算在“五一”那天就去城里给独手龙说道说道,他可丢不起这张脸啊,也顺便给他这个发小带点土特产,算是赔罪吧。可乡下人总是操心、谨慎地过着日子,有什么比得上伺候庄稼重要呢?一忙活,这就拖到了双抢之后。那天,小福田电三轮载着他绕着城里的马路慢悠悠地转了两圈,他一点儿也没让电三轮歇下的意思。看这架势,倒像是旅游观光。开小福田的那个瘦猴小子有些沉不住气了,板着脸说:“喂喂,到底哪儿下啊?”他也不答话,口里叼着烟,喷那小子一口,像是莲花吐蕾。
“不给钱你吗?”他有些生气,脸上的麻子亮闪闪的,“还叫我大伯呢。嗯?瓜娃子?”
“摆谱?还没当村长吧?有钱了你就钱大爷啊?”
瘦猴瘪瘪嘴,拿一双鼠眼斜吊着看他。瘦猴眼光里带有挑衅的味道,现下村子里都在传要与石背坑村合并的事。
“咚——”他把拳头抡圆了挥过去。
两人扭作一团。后来,雨就哗哗地落了下来,再后来,玉琴就从拐角处逼仄的弄堂里走了出来。
玉琴将两人拉开,说也不怕城里人笑话?他记得那天回去的路上,玉琴板着脸说:“龙四竹多大啊?与小辈计较,不怕村里人嚼舌头?”他“啊啊”地张着嘴,想说“瘦猴这青沟子该扇两巴掌”!玉琴开玩笑笑着问他:“包老师也会文攻武卫啊?”
“包老师?”他迷糊了。
“黑夜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来寻找光明——”
玉琴说:“包老师咋忘了你写的诗歌?那个时候,我们背地里都说你是个诗人呢。”
“憨包儿,还诗人?”有好看的音符在麻脸上跳跃。
他红了脸拍拍脑壳儿说:“傻脑壳,那是顾城写的。”
看着眼前的高楼,他发呆了。这些水泥“疙瘩”怎么也像田里的庄稼会自个儿生长似的,一个比一个长得高大、粗壮。上回来,这里的楼盘还只是一片小树林子似地挤挤挨挨的,现在,自家的楼房被那些巨兽吞噬了,房子也长腿了么?
这次去信安城,一来呢,是想看看房子装修的进展;二来呢,是联系戏班子的事情。房子是德清大学毕业后买的小二居室,后来德清去了南方,房子就一直空着,德清说过好多回了,房子归他,让他和娘搬来住,说该享享福了。他明白是德清想弥补他的“牺牲”,他也曾有过搬到城里住的意思。让他想不通、料不到的是,母亲死活不肯从山下搬到城里来。母亲说死也要死在白沙村,城里的房子闭气,像个鸟笼子。想起这事,他便会骂自己太窝囊,太没主见。有一回,母亲在酣睡的呓语中大小便失禁,将棉花被子弄得到处都是“黄金条”,他心里正窝火来着,没处出,家里那条“两头乌”汪汪蹿过来,被他一脚踢到门板上半宿都喘不上气来。他也弄不明白,早些年母亲是信佛的,后来怎么就信了耶稣?母亲阖上眼叹口长气说:“上帝的眼睛在看着我们。悔改吧,不要再犯了。”
兄弟俩一个叫德明,一个叫德清,父亲的用意都明明白白地写在上面。小时候,母亲说他是“葡萄秧,苦瓜命”。龙四竹的话就如同把他那早已结痂的皮又给撕开了一层。当年,父亲由于“历史问题”下放到这个村里改造,后来,父亲再也没走出白沙村半步。他和德清是孪生兄弟,弟弟打小就身体羸弱,有哮喘,病恹恹的,书也没他念得好。兄弟俩长得一般模样,外人是分辨不出来的。高考那年,母亲说,就当是做件善事吧——兄弟俩换了准考证,弟弟就上了大学,成了“凤凰”。也算应验了母亲给他算的“八字”。一语成谶啊。
夜晚的山村空气里氤氲着湿润的潮气。
他摇晃着回到屋里。院场里一片叫好声,大概是牡丹红又唱了一出新曲儿吧。母亲估计早就睡着了,房间里传来鼾声,灯却亮着。他想进屋去和母亲说说话,但说什么呢?他想和母亲唠叨唠叨戏班子的事儿,然后呢,再和母亲说说德清的事情。母亲现在话越来越少了。他在母亲的床沿边坐下,自言自语,那样子似对母亲耳语,他想告诉母亲,说请戏班子的钱是德清出的,他记得母亲曾经是喜欢看戏的,可是那个年代哪来的钱去城里看戏?那时候,从山里到信安城来回得花一天多的时间,再者,父亲也不愿去那个地方,好像那个地方是黑暗的地狱之门。再小的时候,他们还住在信安城,父亲常常会带上母亲、他和德清去戏院看戏,那会儿城里人说成是电影院。有时候在家里,父亲喝多了酒,就会“吼吼吼”地来段“变脸”……许是酒劲上来了,他竟然起身将母亲的身子转了面向,说他打算过些日子就请人向玉琴提亲。
“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母亲忽然睁开了半瞎的眼睛,咕哝着混沌不清的声音说。他吓得逃出屋子。
好像起风了,玻璃窗被一下一下地摇动着,院场那边喧嚣起来,大概是散场了吧,他想。后来,就听见有哔哔剥剥的响动,酒也醒了大半,支起耳朵,坐起听听,原来还是风,抬眼看窗子,月光在窗棂上跳跃奔跑,屋子里有水一样的东西四处盈盈地流转漫延开来,窗上满是生动摇曳的树影。
月亮又大又圆又白。他看着月亮下面升腾着一团团黄色红色绿色的火焰,月亮发着惨白的光,模模糊糊地看不见边缘,好像有只绿头红嘴蓝眼的大鸟在上下盘旋啼鸣,一个人头马面虬髯及至双肩的巨兽,伸出舌头,舔着雪白的獠牙,狰狞地看着他。母亲的房门敞开着,有一束奇异的、金灿灿的光环笼罩在母亲的头顶,她模样怪异地划动着干枯、瘪塌的手。咦,母亲看起来比往常高大多了,脸上泛着神奇的光晕。屋子里摆放着一只巨大的银色烛台,墙上有个裸着身子的大胡子男人张开两臂……母亲在桌旁立定,回过头朝他看了一眼,嘴唇好像鲨鱼似地翕动了几下,不知是不是在唤他。平时母亲做祷告,会让他先将自己搀扶坐起靠在床头,然后撵他出去。他很紧张地望着母亲,母亲将烛台移至面前,捧起一本厚厚的泛黄了的书:“我们从尘土中来,也都归于尘土,祝福是主的……”他看见母亲的嘴里飞出一只只吟诵着欢乐颂、扑扇着的翅膀上缀有蓝宝石红宝石的鸟儿。后来,母亲的房间门“啪嗒”一下好像被风给带上了。那些鸟儿长长的喙衔着的彩色纸片上,写满了密密匝匝的蝌蚪蚯蚓样的文字,飞往一个幽深的山洞里,山洞里长着奇异的树木,开着芬芳艳丽的花朵,树木上结满红红绿绿的果子,有个虬髯很长面貌模糊的人,闭目盘腿坐在一块巨大的圆石盘上,身边围着一群貌若天仙的曼妙女子,还有两个年轻伟岸赤裸着身子奇丑无比的仆人……有只红喙的鸟凶猛地朝那人扑去,那个人抬头的瞬间,他喊了声德清。他又做梦了。
他醒来的时候在床上盯着天花板愣了好一陣子。
他下意识地朝母亲的房间看去,门关得严严实实的,屋里没有一声响动,他想过去看看是不是该换尿不湿了。
他起身披了件灰色夹克衫去了灶房。肚子这会儿咕噜咕噜地响。真的是饿极了,早上只扒拉了一碗稀粥,午饭和晚餐,肚子都让酒给占领了地盘。
灶房里亮着灯光。咦,咋回事?怎么会有人呢?“啪——”好像是碗盘落在地板上的声音。他晃晃脑袋,揉了揉眼,玉琴正弯腰去拾碎片。
看到他,玉琴的脸倏地红了。他愣了一会儿回过神,目光像一只惊鹿撞在玉琴的身上。
“包老师——”玉琴低声嗫嚅道,她刘海上的几绺发丝湿漉漉地黏在额头,有些凌乱。她羞涩地看着他,两只手不停地摩挲着,表情有些发窘。他心突突地跳着,有些恐慌,难道自己真的在迷乱中做了糊涂事?“玉琴,”他醉眼惺忪,拉过她的手低声说道,“我欺负你了?是不,玉琴?”“真的,我可不能伤害你的。”他嗡嗡地说着,肩膀一抖一抖的。
“是我心甘情愿的。”玉琴胸脯一起一伏,鼻子“咻咻”地喘着气,她羞涩地靠在德明身边坐下。窗外月光朗朗,银白的月光从玻璃窗上倾泻进来,玉琴的鼻尖上沁出细细的汗珠,闪闪烁烁,黑亮的大眼睛里汪着一泓潭水,眉毛像含羞草似地舒展开来。简直就是圣母玛利亚!母亲咋就说玉琴长着一张狐狸精的脸呢?玉琴娇羞地看着他,目光生动、绚烂、缠绵。窗外,树影婆娑,如蝴蝶黏在窗上;灶房里水呼噜噜地响着,空气里散发着麦秸秆的味道和枇杷花的香气。还是玉琴打破了寂静里的沉默,她问他:“还记得当年在镇上当代课老师的事吗?”
“哦,哦,”他已经走神了,眼睛里流露出紧张、诧异,有些不明白这个时候她怎么会提及这个,“好多事情记不得了,”他有些尴尬地说:“头疼得厉害。想睡了。”他摇了摇头,闭上眼。
“还写诗歌吗?”玉琴好像打开了话匣子,说是还记得他在学校给她们念那首“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来寻找光明”时,他脸上的痘痘都在跳动着。“你知道同学们背地里怎么说你?她们说,包老师身上的每个细胞都是诗的音符,诗的元素。还有——”她停了下来,狡黠地看着他,说,“你猜猜,还说什么?”德明转过身来,讶异地看着眼前这个曾经的学生,感觉自己真的是对生活中的许多东西麻木了,疏忽了,原本自己强烈追求的理想、人生信念,还有自己为之癫狂发烧的诗歌早已从血液里找不到了踪迹。他叹了口气,捋了捋脑门,说:“想起来了,你那个时候好像也挺喜欢看诗,还问我借过几本诗集呢。”他还想说,有本他很稀罕的诗集被她借去没还给他,让他后悔了好长一段时间。不过他不好意思没说出来。“难道你也有当诗人的念头?”他问。她咯咯地笑了起来,身子前仰后合地像一棵在风中摇摆的小树,说:“包老师满脑子都是诗歌,确实是少一根筋啊。”“诗的脓包。”她诡谲地吐出舌头做了个怪动作说,“还记得吗,学生给你取的绰号?”她有些亢奋了。“还记得那个夏天吧,学校组织我们去白沙河水库劳动,挑石头,运沙子,我的小白鞋给磨破了,伤心地哭了,怕回去挨父亲的打。后来,你偷偷地塞给我一双新的鞋子。真的,包老师,我一辈子也不会忘记那个夏天!”她的眼里闪着莹莹的光,有一串火苗在往外蹿,她的身子好像也要冒出灼人的火焰。她轻缓地将头靠向他的肩膀。他缩紧了身体,往边上挪了挪,月亮明晃晃的,好像也开始在燃烧了,灶台上茶壶嘘嘘地响了起来,他能听见自己的身体庄稼般在拔节,抽穗,噼里啪啦地炸裂开来。他感到羞愧难当。许多往事从他记忆的河床下如海藻般浮游上来。有那么片刻,那个扎着两个羊角辫、羸弱瘦小的、长着一双黑黑的大眼睛的小姑娘,快要将他脑子给塞住了,浮起,落下。那条“两头乌”忽然蹿了进来,“汪汪”地朝他瞪着眼珠子。
从广东回来后,他昏睡了整整两天。在广东的那几天,他感觉到自己是一台快要熄火了的发动机,他始终憋着劲儿,好像是在用一只阀门控制着液体的流量,控制自己的情绪,呼吸,或者说是血液的流动。那天,在去车站的路上,捧着德清的骨灰盒,他边走边骂:“这个混蛋德清,就是死,也该回到白沙村里来死,安安静静地死。他就不知道什么是客死他乡?”后来,刮起了一阵大风,他从小到大也没遇到过这么大的风。风是阴冷的,像无数把黑色的刀子,他摇摇摆摆走着,恍惚中感觉自己被风吹了起来,在一幢幢楼宇间飘荡,飞过高山、河流、峡谷,然后又被风给猛地一掼,从高处坠下,下面是黑黢黢的幽深无底的世界。他是下午回到村里的。村子静静的,留守在村子里的年轻人这会儿恐怕都窝在家里打麻将来着,到了冬天,山里的人好像就没事儿可做了。有几个上了年纪的老人聚拢在一起,在屋檐下抱拢着手,眯眼晒着太阳。他从坡地上走回场院的时候,那些人眼睛忽然就睁大了,好像是接收到了无线电信号,目光像锥子似地瞅着他。许是他们已经听说他家出了大事儿了。他们的眼神是迷离的、空洞的,看不出目光里有关切、同情,德明感觉他们是在询问德清给村子里的那笔赞助费是否会泡汤?德明后来回味之前做过的那个梦,他想,生活真是一个充满无数隐喻和荒诞的世界,梦里,德清白发苍髯的面目,难道不是在向他暗示?去广东那天,他并不知晓会是这个让他措手不及无法想象的结果。当时,那边来的电话里只是告诉他德清出事了,需要这里去人协助处理。平日里,母亲的生活起居都是自己来照顾的,他担心这趟出门母亲会不习惯他人来料理。出门的时候,他也没给母亲说德清出事了,只是说要出趟远门。现在院子里真是安静,那只“两头乌”趴在树下,眯着眼静静地晒着暖阳,也不敢黏他,好像也知道主人家出大事了。枇杷树上,一棵棵小果子探出了青色的脑袋。阳光在树叶间跳跃,有两只雀儿在叽喳地梳理着羽毛。太阳照在他的身上,有点扎眼。昨天母亲的气色不错,瘪塌下去的脸颊比先前看上去要丰润些,午饭比往常多吃了一小碗。而他只是扒了幾口,实在寡味。母亲问他德清可好?他支支吾吾地嗯了声。他听见骨头在嘎嘎裂开的声音。他有些纠结,该如何对母亲说德清的事呢?记得父亲死的那天,母亲哭得昏厥过去,好几天不言语。晚上,做好晚祷,母亲卧靠在床头,床头柜上那盏灯照着,让她的脸明暗交错。母亲实在是老得不成样了。
“德清的事情处理完了吧?”母亲问,她捋了一下眼睑,说,“生,是肉身无奈地依附于它物,死,是灵魂主动地寻找永恒的安息。”
“娘——”他哽咽着,“德清,他,他……”母亲凝视着手中的念珠,说:“你也累了,去睡吧。”母亲转动着琥珀色的珠子,嘴微微翕动。
这天的太阳真是让人伤感,那条“两头乌”眼里也悲悲戚戚的。他抱起狗儿,用嘴蹭着他的嘴巴、鼻子,再蹭身子、脖颈,鼻涕挂了它满身,皮毛上亮莹莹的。他想,如果,当初去念大学的是他,而不是德清,那现在他的生活图景会是什么?他眯起眼看着这四周,阳光落下来,把房子、树木、院场笼罩成雾蒙蒙的一片,让他有种恍若隔世的感觉。泪水开始泛滥开来。他想痛痛快快地大哭一场。
新村长的任命公布了。
村里也就开头几天热闹了下,议论、传言了一些小道消息,如同沸水,最后一样会冷却下来。在村头的道上,龙四爷说:“失望吧?也真是可惜了。”“可惜个卵。”他心里骂道。他淡淡地一笑,对于这个结果,他也并未放在心上。就像是看一场毫无悬念的电影,他认为这是意料之中的。村长这个职位,他根本不稀罕。
腊月二十三,他又去了玉琴家。之前他去找过玉琴几回,门上都是一把黑色大锁,闪着铁青色的光。德明心里空落落的,好像是还能闻得到玉琴身上的味道,却触摸不到她的脸。这会儿,院子的木篱笆斜斜地敞着,院墙上的几缕草枯萎着,有颓败之象。他想,玉琴会去哪儿呢?为啥就不辞而别?
村子可真叫安静。几只鹭鸶在白沙河上觅着食,偶尔,竹林里传来斑鸠的啁啾声。坡地的田垄里,麦苗、油菜有一拃高了。这天傍晚,从玉琴家回来,他给独手龙打了个电话,说他想约他和牡丹红方便的时候吃顿饭,谢谢他们的关心。独手龙说:“别什么都憋在心里,过去了,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他很想对他说:笑话!有什么会想不明白的,我们活着,也仅仅是一粒微尘,活着,也只是肉身存在。
“嗯,嗯。放心,”风有些大,他用衣服遮挡住手机话筒,说,“是的,所有的黑夜都是黎明。”他哈哈大笑起来。他想,这么夸张的笑会吓坏了人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