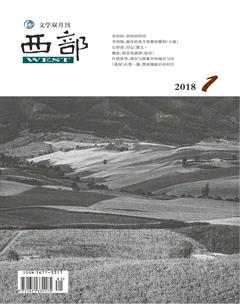失语
曾楚乔
我是在汴京城外见到子厚的。此前我并不知道他就是大名鼎鼎的张载。他戴着一顶破旧花边狐皮帽,乘着一架破马车,吱呀吱呀地响在汴京城外往西方向的官道上。天空沉暗,似乎要落雪,北风呼啸,偶尔能听到孤鸦的低鸣。赶车的年轻小伙子是张载的外甥宋京,只见他神情哀戚,一副忧心忡忡的样子。
这是宋神宗熙宁十年冬天一个寒冷的早晨,子厚,也就是张载,再一次辞官西归,和前次辞职不同,这一次他是病退。
这架破马车跟随张载多年,从嘉佑二年张载进士及第荣归横渠时开始,这马车就没有停止过服务。现在,这马车已经残破不堪,换过的车轴亦不堪重负,摩擦声如风烛残年老人的呻吟,让人担心随时都有可能咔嚓一声就寂灭。原来的实木顶蓬现已穿了好几个洞。从车里仰面看,可以看到灰沉的天空。此前还有窗布,但最近不知被何人割走,只得临时从破旧的衣衫上剪了一块粗布用绳子绑着两边,扯成一个奇怪的多边形。寒风从外面灌进来,撩开狐皮帽的一角,于是我看到了子厚瘦得只剩下骨头的脸。也许是两腮陷得太深,所以显得颧骨奇高。要不是那双深邃的眼睛,真让人疑心那是一具历经千年而不腐的干尸。
只有那匹馬显得雄壮有力。子厚十分喜欢这匹马。它原是天水守将吕大防微仲的坐骑,去岁子厚曾与微仲一聚。子厚原来那匹老马把主人送到目的地后,竟倒毙于军营前。两人煮酒夜谈,相见甚欢。所谈宗旨自是无不知则无知,有不知则有知。子厚还记得,后半夜时他和将军到营房外巡查,兴之所至,子厚不由得吟起子瞻词: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豪气还在,唯人已垂垂老矣!后来,子厚试图拉开一把硬弓,但最终只拉开一半,一阵咳嗽便如战鼓擂鸣般滚滚而来,顿时惊起了守夜的士兵,远远传来他们的呼喝声。
子厚其实喜欢军营生活,他恋恋不舍,也念念不忘。国家安危,匹夫有责,何况子厚。临别之际,微仲亲自把他的坐骑牵到子厚跟前,深深一鞠:“与君一席话,胜读圣人书,子之所见,世罕有其匹。此地一别,不知何年才能见君一面。微仲无以相赠,特以坐骑相送,略表寸心。”
这真是一匹雄壮有力的马。子厚没有推辞。他一下就喜欢上了这匹马。他不断地抚摸马的身体,又抱着马头亲热一番,闻着马儿喷出腥热的气息,他本想作诗酬谢,但脱口而出的却是:“我喜欢这匹公马! ”
可惜壮志未酬,却要战马送归。没有人前来相送,只有嘚嘚的马蹄声响在西去的官道上,子厚难免倍感寂寞。
前面是个拐弯,道路开始收窄。隐约有马蹄声传过来。宋京并不在意,他现在最为担心的是舅舅的身体还能不能支撑到长安,到了长安就离家不远了。现在还有好远的路程呢,手上的银子不多,万一途中出些差错,他都不知如何是好。所以舅舅的每一声咳嗽都能让他的心一阵紧揪。
当宋京看到那架豪华马车突然逼近时,心里一惊,本能地收紧缰绳,但对方的车子却直冲过来,把他们的马车撞翻在路边。马车当场就断了一条顶蓬的横梁,马在那一刻也脱了缰。子厚被掼出车外,他的身体本已极度虚弱,肺病把他折磨得有气无力,如此剧烈的冲撞让他差点儿背过气去。
好久,才听到一声悠长的咳嗽,像深水里一个水泡,从子厚的肺里缓缓冒出来。胸部的剧痛让子厚无法说话。
宋京也摔得不轻,但他顾不得自己,赶紧扶起咳得面红耳赤的舅舅,掏出他自己用的手帕要给舅舅擦去嘴角上的血迹,被子厚竹枝一样的手挡住了。子厚爱洁。他不能容忍一条别人用过的肮脏手帕伸到自己的嘴边。宋京呆了呆,赶紧从舅舅怀里掏出他平时用的手帕来,擦干血迹,又拍净他身上的泥土。宋京正想扶子厚坐起来,身后一声暴喝让他不得不回过头来。
一个胖子站在他们身后。一身绸缎长袍,一看就知道是汴京城里最好的出品。胖子站在子厚和宋京的面前并不说话。说话的是站在胖子身后一身管家打扮的中年男人。
“嘿!不想活了?敢挡我们大爷的车。知道我们大爷是谁吗?你到汴京城去问问,我们赵五爷的名号……”
中年管家还想多说几句威风话,但赵五爷挥了挥手,他立时闭嘴,垂手站到一边去了。
“看看少爷是否受惊了。”赵五爷说话声音不大,但他说的话就像一道命令,管家当即一路小跑着过去了。
子厚当然知道赵五爷,不过从未谋面。据说此人和皇家沾亲带故。本是做珠宝生意起家,现今富甲京城。最近赵五爷给他的大儿子赵欢捐了个小官,在殿前司都指挥使手下做事。
子厚不屑与商人交往,他不知道这赵五爷是啥脾性,但见对方气度不凡,说话不像平素见惯了的那种有钱人颐指气使的样子,心里略为宽慰。子厚心里奇怪怎么在这里碰上他。其实也不奇怪,前段时间,赵五爷带着小儿子外出游玩,今晨才回来,不想在临近京城却凑巧撞上了子厚的马车。
赵五爷看着地上的子厚,见他一副寒酸相,皱了皱眉,嘴角动了动,但还是不置一词。此时,管家喘着粗气来到赵五爷的身边,汇报情况:
“少爷无大碍,在玩斗鸡呢。他还说,我们的马没有人家的好看哪。马车也没大问题,只是一块窗布给撕破了,”
“好。你留下来代我处理。我和少爷坐别的车先回京城。”赵五爷打了个呵欠,也不问地上子厚的伤势如何,便转过身,慢条斯理地和他的小儿子上了另一架马车。
管家在子厚和宋京两人身边转了两圈,说:“我们的窗布破了。”宋京不明就里,回答说:“我们更惨,我舅舅摔伤了,车顶的横梁也断了一条。”
“你们?我可不管!”管家说。
“你想怎么样?”宋京这话一出口,就觉得有点儿气短了。
“你们撞了我们赵五爷的车,得赔。”管家说。
“明明是你们撞我们,怎么说……”宋京话还没说完,听到他舅舅沙哑的声音说:“赔他。”
听了舅舅发话,宋京也不与对方争辩,回头去找包袱。银子都在包袱里呢。他明白舅舅的意思,不要惹麻烦,尽早起程。一块窗布不值多少钱,虽然手头银子有限,但赔一块马车窗布的钱还是有的。
拿到包袱的宋京说:“好吧,我们赔你一块窗布,你说要多少钱?”
“这可不只是一块窗布的事。这块窗布是连着车门的,要换,得整块车门一块儿换。”管家说话的口气有点儿像赵五爷。
坐在地上的子厚听了,不由得抬起来头来。他发现管家正一脸笑容地望着他,那神情仿佛是他多年的朋友,他们正在交流着学习《易经》的心得。子厚心里一沉。多年在朝做官的经验告诉他,越是这样的人越是不好对付。
果然。
管家接着给他们开出了车门和窗布的价格。当子厚听到对方说一共是三百一十八两五钱时,一阵咳嗽突然袭来,让他差点儿喘不过气来。别说三百两,就是零头十八两五钱,他也拿不出来。
“你抢钱啊?”宋京气得脸都歪了,这孩子一生气脸就开始变形,生生歪向一边。
“嫌贵?你去打听打听,我们赵五爷家的东西哪一件不是宝贝?你来看看,这门是用什么木材做的,这是正宗的占城黄花梨,我告诉你们,这么一小块单是运费就值一百两。我们五爷家这个算是最便宜的了。”管家满不在乎地说。
子厚颤巍巍地从地上站起来喘着粗气说:“载没钱……”一口痰迅速又堵上来,他又开始不绝声地咳。
“再没钱也得赔,是吧?我一看这位老先生就是位仁义的人,讲信用的人,也是识货的人。”管家阴笑起来。
“你这是敲诈!”宋京忍不住吼了一句。
“你这说法要戒。五爷估计不爱听这样的话。”管家仍然一口有钱人的腔调,仿佛他就是赵五爷了。
“你知道他是谁吗?你读过《正蒙》吧?读过《易说》吧?他就是我朝的栋梁张载。”宋京说。
“你就蒙吧。小伙子,你吃大蒜了,口气挺大的呀。撞坏了我们五爷的马车,管你是东良还是西良,是张再还是李再都得赔。”管家并不买宋京的账。
“吾,吾确乃子厚。”子厚终于说了句完整的话。
“那好哟,就当你是子厚吧,我说你现在都国家栋梁了,何至于要赖这区区三百多两银子呢?这跟你平时所倡导的可是两回事呀。”管家这一番话让子厚的脸立时变成了猪肝色。
“汝,怎能说吾赖,吾,吾怎能赖汝?”子厚气得连话也说得结结巴巴起来。
“好,好,你不赖,那你赔呀。”管家见他气得脸都赤了,有意逗逗他,“想做圣人啊,那就要付出点代价,要不谁都能当圣人喽。”
子厚颓然坐下,强忍住喉咙里一股往上翻的腥气,断断续续地对宋京说:“银子,给,罢了。”
宋京叫了一声:“舅舅!”
“给。”子厚说。
“不——”宋京看到舅舅已闭上了眼睛,便明白不给是不行的了。舅舅的脾气他是知道的。
但是包袱里那点银子还不够人家塞牙缝。管家连看也不看一眼宋京递上来的银子,就又笑了,笑得一脸富贵气:
“又耍滑头了吧?小伙子,你逗我玩来着?我们五爷打发乞丐也不止呀。你们把我当乞丐了啊。”
“放下。”
宋京手里捧着银子正不知如何处置,听到子厚的分咐,如释重负地把银子放到地上。他回到子厚的身边坐下来,心里五味杂陈。他跟着舅舅求学多年,从未遇上如此难堪之境。当真是虎落平阳被狗欺哪。一个小小的管家就如此嚣张了,那些有钱人岂不更是无法无天了。世风日下,有奶就是娘,面对如此世道,舅舅怎能不心痛,那简直是在他心口捅上一刀呀。想到这里,宋京不由得落下泪来。
“莫哭!”
宋京一惊,望了舅舅一眼。子厚仍然在闭目养神,神情肃穆,不由得让人起敬。宋京收了泪,自己好歹也算子厚半个学生,不能丢他的脸。
正僵持间,远处一阵马蹄声由远及近。转眼之间,几匹快骑便来到他们的面前。管家一见为首者,当即作揖施礼,向来人问好:“子盼兄,别来无恙?”
听到子盼两个字,子厚突然睁开了眼睛。陆子盼,这个汴京城里最强势的地痞恶霸,据闻门下走狗达万人之众,连开封府都惧他三分。早在神宗五年,子厚就建议要铲除这些地痞恶霸的势力,无奈应者寥寥。朝廷似乎也无暇及此。他心里暗暗叹息,看来自己这把老骨头是回不到横渠了。子厚已经做了最坏的打算。
事实上陆子盼没有子厚想象中横蛮凶残,相反他更平易近人也比管家更好说话。当他知道事情的原委,尤其当他知道眼前坐在地上这个干瘦的老头儿就是大学问家张载时,居然给子厚施了一礼。子厚坐在地上,以他的为人,本来是准备还礼的,他挣扎了几下,无奈没能一下子站起来。在陆子盼的周旋之下,管家居然放弃了索赔。当真是太阳从西边出来了。
子厚望着陆子盼绝尘而去的背影,不由得苦笑了起来。他远没想到,如此巨大的索赔案,竟不用官府,直接在一个地痞三言两语之下就化解了,而且不用赔一两银子。他终于松了口气,但内心却更为沉重。
子厚让宋京收好银子,准备整装出发。突然听到管家一声惊呼,他寻声望去,只见微仲送给他的那匹公马此刻正趴在赵五爷那匹母马背上日得正欢!管家拿着马鞭,狠命抽了好几鞭,才把这对野合的露水夫妻分开。各自拿好了缰绳,管家一脸严肃地对子厚说:“你老是学问家,又是道德家,你也看到了,这已经不是一块窗布的事了。五爷那边我怕是不好交待了。”聽了管家这番话,宋京一下子就白了,他拿着缰绳的手微微地发抖。
“吾能自律,亦能律人,唯不律于畜牲。”子厚嘴里虽然如此说,但他心里也没有底,明摆着是自己的马日了人家的马,这道理上就亏了。而且这还不是赔钱就能解决的问题。
怎么办?仨人你眼望我眼,一时都愣住了。一块窗布事小,陆子盼就能解决。但这种事如何解决?当真是令仨人头痛。
“这关系到五爷的面子,还是等五爷亲自来处理吧。”管家也觉得事态严重了,不敢擅作主张。
双方一时僵在那里,谁也拿不出办法来。他们争论的中心从畜牲渐渐转向了人。管家认为这是一起蓄谋以久的强奸,是对五爷极大的侮辱。于是争论开始升级,他和宋京展开了一场人身攻击。他骂宋京是个十足的流氓,而宋京则回敬他是个想立贞节牌坊的婊子。双方你来我往,异常热烈。这个过程子厚不发一言。他坐在地上,只感到寒风剌骨,他很想让宋京把马车扶起来,让他坐到马车里去,但他插不上嘴,只好由他们争。
很明显,这样等下去或者争论下去对子厚相当不利,他的身体支持不了那么长时间的等候。我有心帮帮子厚。
顺便说一下我的身份。我是风流底市的一名警察,一名上了十年班的老警察。我知道我的到来对任何人来说都是突然的,我自己也说不清楚是怎么回事,反正是在执勤过程中瞌睡了一会儿,醒来就到了汴京。我刚好是整个事件的唯一目击者。我走到子厚和管家跟前,向他们各自敬了个礼。他们对我的敬礼十分不解,见我衣着奇特,管家便问:“你是子盼兄的人?”也许陆子盼手下多奇人异事,所以管家有此一问。我说我不是。
“所为何来?”
“为调解来。”
管家不由得从鼻孔里“哼”了一声。我知道他心里不屑,但我不介意,仍然提出我解决问题的方案。方案中最关键的一环便是换马。如此既解决了五爷的面子问题,又解决了子厚西归路上的交通问题,可谓皆大欢喜。我一边说,一边暗里观察管家,发现管家在暗暗点头。其实我也帮他解决了一个难题,要知道也正是他的失职才导致五爷的母马被日。所以当我一说完,管家便表示同意。子厚虽然心痛将军那匹良马,但他也想不出更好的解决办法来,只能首肯。
这件事至此总算有个了结。子厚的马虽然被换了,事实上他并不吃亏。母马说不定就此怀上了,明年要是能生下一只小马驹他就赚了。按理他应该高兴才是,但子厚脸上一点儿也看不出高兴的表情。上路的时候,子厚终于问我了一句:“子因何窥得管家欲谋吾马?”
“我并没有看出他想要你的马。”我说。
“为什么你一说换马管家就同意了呢?”宋京道。
“我是本着解决问题而来。我是从管家的切身利益考虑,试想,五爷如果知道了这件事,管家能逃避责任吗?他巴不得换马呢。何况赵五爷的小儿子还十分喜欢你们的马,如此一来,他回去后又立功了。”我答。
我听到车里的子厚“噢”了一声,恍然大悟的样子。好一会儿,子厚才又问:“子操何业?”
“警察。”
车厢里便不再有言语。我跟宋京说我身上没有银子,没法儿活,要求路上有所照顾。宋京请示子厚,半晌,车厢里传来一声:“可。”于是我坐到宋京的左边,一边看他驾车一边和他嗑话。我由此得知,宋京还没有成家。他还不想成家,张载的学问他连皮毛也没学到。他想成为舅舅那样有学问的人。我对他也不由得肃然起敬。一路上我得以分食他们一早就烙好的大饼。那大饼真香,是真正的麦香。
车到洛阳,我见到了传说中的二程,即程颢和程颐兄弟。子厚虽然是他们的表叔,但对他们兄弟也很尊敬。他们仨人谈了半夜,子厚只字未提路上遇到的事情,临睡前他却跟他们兄弟说:“载今遇一奇人,本有所得。唯病之故,恐再难著书立说,此乃载生平憾事也。”
翌日起程,二程本有银子相赠,但子厚坚辞。出洛阳城不久,我就发现了一只奇怪的鸟,外表似鸡,但比鸡漂亮不止十倍,其鸣声高吭,响彻云霄。它跟着我们,在马车上空一路飞翔。我问宋京,宋京也不认得。忽听车厢里传来一声叹息:“其声孤清,必凤凰也。载恐难及故里矣。”
果然不久后,子厚的病便开始加重,大咳过后往往见血。大饼已经无法下咽了。他现在只想喝一碗热热的小米粥。但我们身处荒郊野岭,远近并无村落,实在是一粥难求。也许天不绝子厚,走了约五里许,近黄昏时竟然在路旁得见一户人家。宋京决定借宿于此。
屋里只有两个男人,一大一小,大者年近五十,小的约莫十七八岁,显然是父子俩,不见有妇人。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猎户。只是这猎户委实贫穷,用家徒四壁来形容也不为过。唯一让人觉得还算财产的便是屋前木桩上拴着的一头瘦毛驴。房子是用木材搭起来的。屋顶是一层接一层的茅草。日子久了,雨水能渗到屋里来。屋子中央用三块石头架起了一只瓦锅,我们到时刚好闻到了小米粥的清香。主人对我们的光临热情有加,不但让子厚喝到了小米粥,还让出了屋里唯一的床。子厚推辞不过,夜里邀我同睡,我躺在他的身边却睡不着。那父子俩吃过晚饭后就不见人影了。为了安全起见,宋京把马车赶到屋里来,他就睡在马车上。
天亮时,父子俩捉回两只野鸡。儿子冻得满脸紫红,仍兴高采烈地生火煮水杀鸡。做父亲的也不闲着,不知道从哪儿弄来一抱干草,小心切碎后便拿去喂马。看得出这人是爱马的,他望着马儿那热烈的表情就像望着自己心爱的婆娘一般!
我们在这里住了整整三天。三天里,子厚不但每顿有小米粥,还有野鸡汤喝,加上休息得好,子厚的病居然大有起色,面色红润了不少,精神也好了起来。看来他缺的是营养。三天之后,子厚便思着还乡。父子俩也不挽留,不过孩子的父亲却提了一个颇令子厚为难的要求。
他想要那匹马。
子厚感激这父子俩的热情招待,可是没有马,他怕回不到故乡。子厚有些犹豫。对方见他犹豫,便提出用那头毛驴来换。
“先生可以骑毛驴,毛驴虽然慢些,但它走得稳,对先生的病体大有好处。”
儿子及时的帮腔让子厚无法拒絕。宋京虽然觉得不妥,但子厚话已经说出口,也不好反悔了。子厚便索性连马车一并送给了猎人。父子俩自然感激万分,一直送我们到森林的边上,才喜滋滋地返回。
从公马换成母马,又从母马换到毛驴,子厚思忖着下一步会不会换作步行呢?这个还真的不好设想。
令子厚感到高兴的是,头顶上空那只凤凰一直跟着,我们走到哪儿它便飞到哪儿,从未离开过。我们走进森林不久,那只凤凰又引来了另一只,一只跟着一只,最后来了数不清的一群。它们在空中上下翻飞,鸣叫声响彻森林。
我很兴奋,从来没见过这种传说中的吉祥之鸟,我猜想,碰上了吉祥鸟,此后的路途应该是顺风顺水了。
我高兴得太早了。
我们还没有走出森林,就碰上了一伙强盗,为首者骑着一匹大白马,威风凛凛地拦住我们的去路。宋京早已吓得面无人色,子厚也不知道如何是好。秀才遇着兵,有理说不清,更何况是强盗。子厚知道多说无益,只有等着挨宰的份了。
强盗自有强盗的规矩。他们要我们把身上所有的银子全拿出来,连同毛驴,一同交到他们的手上。这个过程如果有丝毫怠慢,他们就要剁掉我们的双手,挖去我们的双眼。宋京也不等子厚的指示就赶紧解下包袱,拿出寥寥可数的几粒银子准备送过去。在要不要把毛驴也牵上这个问题上,宋京有些犹豫,毕竟舅舅还坐在毛驴上,所以他只能悄声征询子厚的意见。
“莫。”子厚说。
“要剁手挖眼呢?”宋京说。
子厚已经闭上了眼,不再回答。宋京只好拿着银子送过去,走到一半,听得强盗的暴喝:“你不想要手了?把毛驴一起牵来!”宋京就站在那里左右为难。紧接着啪的一声响,宋京的脸上立时现出一条鲜红的鞭痕来。
我忍无可忍,拔出手枪,照着那匹大白马就是一枪。大白马应声倒地,坐在马上的为首者也跟着滚落地上。所有人呆若木鸡,包括子厚。忽然人群中发一声喊,所有强盗顿时四散而逃,顷刻便不见了踪影,只留下那匹大白马,倒在地上,鲜血汨汨地流。我们头顶上的那群凤凰也为枪声所吓,飞得老高,只是一会儿后又飞下来在我们的头顶上空盘旋。
“你这是啥武器?威力这么大?”上路时,宋京跟在我身后终于忍不住地问。
“手枪。”我说。
“啥枪?”他似乎不明白。
我做了个扣扳机的手势,然后说:“十丈之内如中要害,无论人畜必死无疑。”
我以为子厚肯定会问我这武器如何制造之类的问题,但奇怪的是,子厚并没有,他只是呆呆地望着我,嘴里发一种类似凤凰鸣叫的声音,但没有凤凰叫得响亮。宋京觉得奇怪,他走到子厚身边,轻声相问,但子厚依然如故,甚至连看也不看他一眼。后来子厚终于不叫了,他一路沉默,一直快到临潼,我才发现子厚竟然失语了,也就是哑了。我暗暗心惊,担心是自己那一枪把子厚吓哑了。到了十二月二十五日,我们行至临潼住进了馆舍,我才发现子厚并不是为我枪声所吓。
一进入馆舍,子厚就抓住我的手,在我的手心里缓慢地写字:
“载无别求,唯望子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如此载当瞑目。”他写得很慢,生怕我不认得字,一边写还一边用目光询问我是否明白。他热切地望着我,干瘦的脸慢慢活了,眼神里仿佛有一种清可见底的纯净。我心里一酸,在他的手心里写了三个字:“我懂了。”
我再也忍不住泪水,任其汹涌而下。子厚见了,又在我手心里写了两字:莫哭。忽然间,子厚的目光变得炯炯有神起来,脸上呈现一片红光,我以为他的病好了,心里一阵欢喜,却不知这竟是回光返照。
天黑时,子厚又让宋京给他准备一大盆热水,放到院子中央,他光着身子躺在木盆中沐浴。后来,水渐渐冷了,子厚又让宋京给换了一盆。洗了两个时辰,子厚才起来穿衣,他只喝了一碗白开水,没有吃晚餐便就寝了。子夜时分,凤凰群集馆舍上空,彻夜鸣叫。
翌晨,子厚死。一场大雪终于来临。纷纷扬扬的大雪让宋京一筹莫展。他没有哭,只是跪在子厚的床前。三天里只吃了一只烧饼,他手里的银子根本就买不起一具棺木,更谈不上为舅舅风光大葬。我见此情境,悄然走出馆舍,找到一个当铺,我想把这唯一值钱的枪给当了。我在当铺里开了第二枪,结果这把跟随我多年的枪终于换回一两八钱银子。
这点银子也不过杯水车薪,刚好够我们的住宿费。我无可奈何,唯一能做的,就是静静地守在子厚的遗体旁,默默地向上苍祈祷。所幸的是,三天之后,子厚的门人从四面八方纷纷赶来,才得以买棺成殓,护柩回到横渠。
据史料记载,张载临终时,只有一个外甥守在身边。其实史料记载有误,他临终时不止外甥一人,最少还有我,我亲眼目睹了子厚从失语到死亡的整个过程。我至今还记得,他执着我的右手,在我手心里郑重其事地写字的情景。
有人大声喊捉贼,我为喊声惊醒。我习惯性想拔出手枪,却发现枪不见了。环顾四周,发现自己又回到了现实,回到了车水马龙的都市,还流了一地口水。我这才知道刚才自己瞌睡时做了黄粱一梦。只是梦中所见,仍然历歷在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