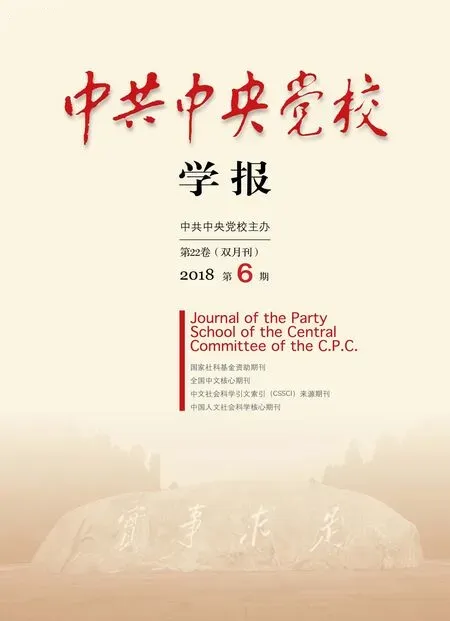中共党内关于政权阶级构成认识的整合(1921—1925)
——以“平民”概念演变为主线
周家彬
(中国人民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海淀 100872)
1923年中共三大提出了“平民政权”的口号,这是中共建党初期非常重要的政治主张。目前学术界对“平民政权”的研究大多着眼于中共三大党纲草案的相关论述,认为“平民政权”即是包括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农民阶级与工人阶级四大阶级的联合政权①参见于化民:《国民革命语境中的中共政权口号及其阶级意蕴——兼与〈从“平民主义”到“革命民众政权”〉一文商榷》,载《中共党史研究》2016年第11期;吴志娟:《中国共产党早期对民主革命认识的日趋深化——以中共一大到三大的政治口号演变为视角》,载《中共党史研究》2011年第12期;赵崇华:《建党初期中国共产党“平民政权”口号的提出及演变初探》,载《西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2期。。实际上中共党内对“平民政权”的认识存在较大的分歧。陈独秀主张通过国民革命建立四个阶级的联合政权,瞿秋白则认为应在未来的政权中限制资产阶级的地位。许多学者已经注意到陈独秀与瞿秋白在政权思想上的分歧,但研究的侧重点主要在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上。相比之下,对于1920年代前中期中共党内围绕“平民政权”特别是未来政权中阶级构成以及资产阶级地位问题的分歧,现有研究关注较少。本文试从中共对“平民”概念认识的历史演变入手,阐述建党前“平民”概念的分化,建党初期中共对“平民”的认识和第一次国共合作前后党内围绕“平民”产生的认识分歧以及对“平民政权”的差异性理解,以此展现中共党内关于政权阶级构成认识整合的复杂历史过程。因中共党内相关认识的整合完成于1925年10月中共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因此本文的研究主要集中于1921年至1925年。
一、“平民”的两种概念
民国时期知识分子对“平民”内涵的理解经历了一个变化过程。“平民”概念流行之初主要指与政治上处于特权地位的官宦相对的黎民百姓。随着社会主义思潮的兴起,“平民”概念发生分化,产生了反抗资产阶级压迫的新内涵。中共创建前后对“平民”的认识已经包含了劳资斗争的内容,并将之纳入早期的革命运动。
“平民”或“平民主义”最初传入中国时,主要强调对政治特权的反抗,例如《东方杂志》1907年曾刊登《论平民主义与国家主义之废兴》一文,将“平民主义”等同于卢梭等思想家提倡的民主价值和共和政治[1]。一战后,人们开始重新审视“平民主义”。受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其内涵逐渐向经济和社会等领域拓展,由原先只反对政治特权发展为反对政治、经济等各方面的特权。“平民”的内涵也发生分化:一部分人坚持将“平民”限制在反抗政治特权的范畴之内,如1918年9月16日《申报》刊载的《四十年后之新世界,法国之平民主义》一文继续坚持政治平等是平民主义的“根本要义”,赞扬议会等代议机关在维护民意方面的重要作用[2]。更多的人则开始将视角从反抗政治特权转移到反对经济方面的剥削和不平等,响应当时社会主义思潮的传播,使“平民”成为工人、农民等政治、经济均处于弱势地位的社会底层群众的代名词,“平民”出现新的内涵。如沈泽民将“平民”等同于“贫民”,《平民》周刊曾将“平民”视为“劳动阶级”,《少年中国》所载《少年中国之创造》将“平民”界定为“劳农两界”,无政府主义者将“平民革命”的矛盾既指向了政治特权阶层也指向了资本家。对这些人来说,“平民”主要是工人、农民和城市贫民等,资本家是“平民”的对立面[3]。
对于“平民”内涵的变化,20世纪初人们早有系统性的认识。如1922年《民国日报》副刊《平民》登载之《平民主义底潜势》一文指出,中世纪时期,“平民”相对应的是国王、贵族等特权阶层,其产生之初旨在破坏封建制度、贵族制度,追求政治上的平等地位。近代以来,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资本家掌握着越来越多的资源成为抗争的主要对象,“平民”的概念也发生转移,逐渐包括反抗资本家的内涵。作者认为俄国十月革命正是“平民”反抗的结果[4]。
将资产阶级视为“平民”对立面的情况在早期共产主义者中非常普遍。瞿秋白认为,“平民”“便是劳工和农民,乡村的和城市的小资产阶级”[5-1],李大钊也曾强调“平民”与资产阶级的对抗。1919年,李大钊发表《庶民的胜利》一文,其中“庶民”即是“平民”的别称。针对资产阶级剥削问题,李大钊指出“凡是不作工吃干饭的人,都是强盗”,因此庶民的胜利包括政治与社会两方面,政治方面是专制的失败与民主主义的胜利,社会方面是“资本主义失败,劳工主义战胜”,即劳工通过国内革命改造依赖剥削的资产阶级,“使一切人人变成工人”,消除劳动者与资本家之间的差异[6]。
许多早期的共产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的接触稍晚于李大钊,但在1920年前后也纷纷将“平民”视为与资产阶级对立的底层群众。如1920年5月高君宇在《“五月一日”与今后的世界》一文中提出世上“有‘治者’和‘被治者’的阶级,又有‘资本家’和‘劳工’的阶级”,“几千年来的平民,都囚在治者和资本家的铁锁底下”,“五一运动的呼声,是劳工在资本家压制的底下,要求翻身的呼声;也就是平民要‘复权’的一个记号”[7]。显然,高君宇此处所谓之“平民”既有反抗政治特权的内涵也有反对资产阶级的内涵,“平民”所指并非黎民百姓而是底层群众。又如1920年初,恽代英在《再驳杨效春君“非儿童公育”》一文中批评当时的法律制度是“供权贵资本家掠夺压迫平民之用”,也将“资本家”视为“平民”的对立面[8-1]。
开展劳资斗争是中共初创时期的重要活动。1920年11月,上海共产主义小组起草《中国共产党宣言》,声明中国共产党的理想是将生产资料收归公有、废除私有制,当下“第一步就得铲除现在的资本制度”,为此中共必须组织和集中无产阶级的势力,“从资本家手里获得政权”,“将这政权放在工人和农人的手里”。在共产党组织的发起阶段,早期的共产主义者就明确提出学习“十月革命”,革命对象直指资产阶级[9-1]。一大召开时,中共继承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相关思想,在其纲领中提出“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等主张[9-2]。
在此背景下,中共党内对“平民”内涵的认识比较统一,将资本家视为“平民”对立面的观点普遍为大家所接受,就连曾经将“平民”理解为黎民百姓的党员也逐渐接受新的内涵。陈独秀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1919年5月,陈独秀于《山东问题与国民觉悟》一文中还在沿用“平民”最初的内涵,认为平民主要由“学界、商会、农民团体、劳工团体”构成,号召“平民征服政府”[10-1]。这里的“平民”仍侧重于反对政治特权、追求政治民主。但随着陈独秀加入共产主义运动,其思想也发生变化,开始强调经济、社会层面的阶级对抗,提出政治是社会进步的工具,“最进步的政治,必是把社会问题放在重要地位”,将对平民主义的理解推向经济、社会层面[10-2]。1920年5月,陈独秀在南洋公学的演说中指出,“十八世纪以来旧的政治已经破产”,仅仅强调民主、共和等民主政治制度的时代已经过去,黎民百姓反抗封建特权的政治斗争要让位于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运动,中国处于由资产阶级执政向无产阶级执政转变的过渡阶段[10-3]。同年9月,陈独秀在《谈政治》中明确提出,“少数游惰的消费的资产阶级,利用国家、政治、法律等机关,把多数勤苦的生产的劳动阶级压在资本势力底下,当做牛马机器还不如”,为改变这一情况,无产阶级要夺取政权,“自己站在国家地位,利用政治、法律等机关,把那压迫的资产阶级完全征服”[10-4]。
中共创建前后,“平民”逐步被纳入共产主义运动的范畴,平民教育便是一例。1920年,杨明斋在《新青年》发表《苏维埃的平民教育》一文,认为苏俄的阶级教育就是平民教育,其重要内容为消除阶级、性别等种种差异和界限,实现工学结合[11]。同年,恽代英在《平民教育社宣言书》中指出,“平民学校是专为贫苦无力量读书的人设的”[8-2]。显然此时的平民教育针对的就是工人等底层群众。1922年初,中共在上海创办平民女校,专门针对家境不优的人士开办,学员除了半工半读外,主要的社会活动就是参加工人运动,实际上成为中共培养妇女运动力量的学校[12]。陈独秀将平民教育视为“改造社会底重要工具之一”,“资本社会里贵族教育制造出来的人才,虽非原料,却是商品”。陈独秀认为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才能真正实现教育平民化,但也希望在“资本制度之下能有少数的学校倾向平民主义”,让“平民女校作一个风雨晦冥中的晨鸡”[10-5]。李达在《平民女学是到新社会的第一步》一文中也表示期望通过平民女校为“无钱无势”者提供受教育机会,力求“不分贫富不分男女都受平等教育”[13]。
二、党内认识分化与两种“平民政权”思想
随着国共合作方针的确立和国民革命口号的提出,中共党内部分人将“平民”诠释为国民,恢复“平民”以反抗政治特权为核心的内涵,使之重新等同于黎民百姓。但仍有部分人,特别是当其论述政权问题时,坚持将“平民”阐释为一个包含劳资对抗的概念。
当国共合作的策略出台后,特别是国民革命的方针确立后,中共对“平民”的界定开始发生变化。一些之前将资产阶级排除于“平民”之外的人,又开始将其纳入“平民”范畴。如陈独秀表示“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若失了资产阶级的援助,在革命事业中便没有阶级的意义和社会的基础”。在阶级斗争方面,陈独秀一改先前的观点,认为“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分化,尚未到截然分离的程度”,二者之间的斗争并不激烈[14-1]。1923年4月,陈独秀在《怎么打倒军阀》一文明确将资产阶级纳入“平民”的范畴[14-2]。此时资产阶级回到“平民”中,“平民”的内涵又逐步向黎民百姓靠拢。目前学术界关于国民革命前后中共党内将“平民”视为国民或黎民百姓的研究较多,本文将论述的重点放在党内的另一种认识上。
另有部分人虽然认同国共合作推行国民革命的策略,呼吁全体国民反抗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但涉及革命理论,特别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关系、革命胜利后的政权阶级构成等问题时,依旧将资产阶级排除在“平民”之外,使用“平民”一词表达对资产阶级的警惕和遏制的态度。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就是瞿秋白。在起草中共三大党纲草案时,瞿秋白提出“中国资产阶级大部分依赖帝国主义的列强或军阀,极易妥协而卖平民”[5-2]。1923年9月,在《自民治主义至社会主义》一文中,瞿秋白对“平民”的定义借鉴了列宁《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以下简称《两种策略》)中有关1905年革命动力的描述,认为“平民”即“劳工和农民,乡村的和城市的小资产阶级”[5-3]。又如1924年1月,瞿秋白在《中国革命史之新篇》中指出,“政权落在少数资本家手中,试问资本家能代表人民不能?”,并表示资本家将“牺牲多数人幸福”“出卖中国”“自私自利剥削平民”。这也证明对于瞿秋白而言,“平民”不包括资产阶级,且明显带有遏制资产阶级的意味[5-4]。
“以革命的方法建立真正平民的民权”是由瞿秋白写入中共三大党纲草案,但其表达的思想与瞿秋白的原意大相径庭。在三大党纲草案的文本语境中,“平民”是包括工、农、小资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在内的整个国民的联合体,这是和瞿秋白的认识相悖的。中共三大党纲草案有几个问题值得我们注意。第一,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政治组织,其党纲草案在诸多重大问题上反映的应当是当时党内的主导性意见,并不一定是起草人本人的意见。第二,当时党内的话语权主要掌握在陈独秀手中,陈独秀对草案修改的幅度较大,虽然“以革命的方法建立真正平民的民权”这一句话得以保留,但其含义已经发生实质性的转变。关于修改过程,瞿秋白在《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一文中曾指出,三大党纲草案起草后,“独秀同志又修改了再付印的”,“‘无产阶级应参加国民革命,取得政治的地位,以至于革命领导权’一层意思,完全抹杀,变成废纸”。无产阶级领导权相关表述的修改影响到了政权思想的论述。据瞿秋白回忆,其在三大党纲草案中提出的“真正平民的民权”就是“劳动平民之革命民权独裁制”。但经过修改后的草案则丧失了与资产阶级斗争的内容,有关政治的内容沦为与一战前“平民主义”所宣扬之民主、共和无异。因此瞿秋白认为“第三次大会时的党纲草案,在现在看起来简直是不值一笑,很幼稚的”[15]。第三,1923年5月,瞿秋白于中共三大之前曾撰写《〈新青年〉之新宣言》一文,断言“资产阶级其势必半途而辍失节自卖”,流露出对资产阶级的不信任和警惕,强调“中国的真革命,乃独有劳动阶级方能担负此等伟大使命”[5-5]。1923年9月,瞿秋白又于中共三大后撰写《自民治主义至社会主义》一文,明确提出学习列宁《两种策略》中以工农民主专政遏制资产阶级的政权思想[5-6]。从上述两篇文章可以看出,瞿秋白在中共三大前后对资产阶级的态度是一致的,断不会在中共举行第三次代表大会时发生背离并在两三个月后又恢复原来的观点。经陈独秀修改后的党纲草案未能获得共产国际批准成为中国共产党正式的党纲,在共产国际眼中草案“错误百出”,“靠这样的纲领,党不能生存”,“提这样的要求,党不可能在反对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派的斗争中动员广大群众”[16]。这也从侧面证明经陈独秀修改后的党纲存在许多问题。
在对国民党的认识方面,瞿秋白曾将国民党称作“平民的政党”“代表大多数平民的利益而奋斗的政党”,而又把新三民主义称作“现实的革命原则”,学者可能据此认为瞿秋白将资产阶级视为“平民”的一部分。其实,1924年2月瞿秋白于《国民党与下等社会》一文中提出“革命党必定是代表下等阶级利益的政党”,其所谓“革命党”的参照对象是“欧美各国的社会党”“俄国的共产党”,社会党与共产党“大多数是工人或贫农”。对瞿秋白而言,只有当国民党代表“下等阶级”利益时才能称之为“革命党”。而所谓“下等阶级”“二三十年前,大半是游民,是苦人,没有受教育的机会”,“近年以来,中国的下等阶级里,因中国经济的变动,亦发现许多城市工人”,所以“下等阶级”主要指的是工人、农民等底层群众,“平民”的范围也可想而知[5-7]。瞿秋白曾表达了对新三民主义的认可,但瞿秋白对新三民主义的认识有其自身的特点和偏重,他认为新三民主义作为“平民意志的结晶”,是“农民、工人反对地主、资本家的意志之表现”,其思想处处流露出遏制资产阶级的思想[5-8]。
在对阶级关系的认识上,瞿秋白曾在《孙中山与中国革命运动》一文提出,“所谓平民,也还包含了利益相反的种种阶级”,但这所指的并非是国民革命中的“平民”,乃是瞿秋白用以形容辛亥革命时期同盟会反抗清政府时期的“平民”。当时所谓“平民”包括“游民的无产阶级”“半欧化的知识阶级及军官”“大商阶级”(包括士绅式的资产阶级和侨商及买办阶级)和“城市及乡村的小资产阶级”(包括小商人和农民),其内涵接近于全体国民。这正印证了本文第一节所述一战前国人对“平民”的认识。当然,也正如上文所述,“平民”的概念随后发生了重要的分化。瞿秋白认为,辛亥革命成功后“民族革命的主体——中国平民,经过了阶级的分化”,“一部分士绅式的资产阶级结合了军阀阶级,侨商中的买办阶级也早已退出革命的战线”,“只剩得大多数的小资产阶级——全国的小农、小商人,客观上十分需要彻底的民权主义的革命”,“游民无产阶级”开始分裂。“中国无产阶级”逐渐登上了历史的舞台,“而且是革命运动的领袖阶级”。国民革命开始后,“革命的主要阶级是大多数的贫苦的平民”,现在“真正能代表中国民族的无产阶级,真正能彻底革命的阶级,此后足以领导大多数农民群众及一切贫苦的平民——游民无产阶级,积极的实行革命,反对一切士绅阶级、买办阶级的反动势力,扼制资产阶级性的妥协政策,直接打倒帝国主义及其工具之军阀买办阶级”[17]。可见,瞿秋白认为“平民”的概念已经发生变化,转向了工人、农民等贫苦的底层群众,再次印证了上文所述“平民”概念演变之过程。
国共合作新策略的应用,改变了中共对“平民”这一概念的理解和使用。对于陈独秀等人而言,“平民”逐渐等同于国民,等同于黎民百姓;但对于瞿秋白而言,资产阶级虽然也是国民革命的参与者,但仍需时时警惕,并未改变建党初期对“平民”的理解。党内围绕“平民”问题的分歧是由中共革命策略的剧烈转轨引发的。
对于三大提出的“平民政权”,中共党内有两种不同的认识:部分人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视为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即资产阶级是主体、工农小资产阶级为辅助,在革命胜利后的政权设计上自然以资产阶级为主导;部分人则从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的关系出发,认为无产阶级也能领导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并认为其前途将是直接发展为社会主义革命,因此在未来政权的阶级构成上强调无产阶级领导权和对资产阶级的限制。
第一种政权思想的主要代表人物是陈独秀。在接受国共合作的策略后,陈独秀认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主体是资产阶级,没有资产阶级国民革命便会失去社会基础,中国工人阶级不仅数量少而且政治觉悟也不高,许多人“思想还完全是宗法式的”,“懂得什么是共产主义,什么是共产党的人则更少”,因此对工人运动的发展并不十分乐观,强调国民革命成功后“共产党才能取得基本的发展”[18-1]。在陈独秀眼中,国民革命成功后是资产阶级掌权,要建立一个涵盖工、农、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四大阶级的民主政体,工人阶级和共产党只有在资产阶级掌权、资本主义获得大发展后才有可能夺取政权。在经陈独秀修改后的中共三大党纲草案中提出的“平民政权”所指的就是四大阶级联合政权。
但事实上,合作关系与权力分配是两个不同的问题。大革命初期,党内一部分人虽然没有发展出系统性的统一战线理论,但也已经意识到“统”是为“战”服务的。例如瞿秋白曾指出“加入国民党是我们自己组织起来,并不是国民党利用我们”[5-9]。在瞿秋白的“平民政权”思想中,“平民”的概念已明显带有限制资产阶级的意思,“劳动平民之革命民权独裁制”的阶级主体主要包括工、农、小资产阶级。在许多中共领导人看来,资产阶级作为无产阶级的天敌,必须加以限制。瞿秋白并非党内唯一呼吁限制资产阶级的人,蔡和森、恽代英等人都有着相似的主张。如蔡和森就认为资产阶级“自身将负经济掠夺与背本媚外的两重怨毒,结果只有迅速的激起无产阶级革命”[19-1]。1923年6月,恽代英在《中国社会革命及我们目前的任务》一文中指出,“吾人取加入民主主义联合战线政策殊有意义”,统一战线的主要目的不是让国民党消化共产党或是让资产阶级俘虏无产阶级,“此举只认为我们借此改造民党”,“因以握取政权,为无产阶级专政树立确实根基”[20-1]。1924年3月,在《何谓国民革命》一文中恽代英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他认为无产阶级“将成为革命的主要军队”,“商人是外国资本家的支店经理人,他们自然对于革命最为反动”,因此提议对于资产阶级“稍加裁抑”。国民革命的结果不是立即实现公有制,但要“将租税加重到资产阶级身上,他们的事业,亦必须受国家的管理与干涉,有时甚至于为国民的利益,须酌量没收一部分财产”[20-2]。
三、“平民”概念统一与政权思想的整合
随着群众运动的发展,陈独秀逐渐转变对资产阶级的态度及对“平民”概念的认识,认为资产阶级妥协性将制约革命的发展,重新强调“平民”中劳资对抗的内涵。中共对“平民”的认识再次统一,党内的政权思想也逐渐统一到“革命民众政权”的旗帜下。
陈独秀与瞿秋白等人政权思想分歧的关键在于对无产阶级力量的判断。陈独秀认为无产阶级发育不完全,力量弱小,瞿秋白则从国际共运的角度肯定无产阶级的力量与中国革命的前途。例如瞿秋白指出虽然中国“无产阶级很少很幼稚,大半不脱宗法社会思想的遗毒”,“然而资产阶级之弱更甚于劳动阶级”[5-10]。中国“因阨于帝国主义之故,自然当与世界的无产阶级革命相融合而为一”[5-11],中国革命已经是十月革命开辟的世界革命之一部分,中国站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立场打击帝国主义势力,从而支援先进国家反对本国资本主义的斗争。其他国家特别是革命已经成功的苏维埃俄国,反过来也会支援中国革命。瞿秋白正是从世界革命、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角度考量中国革命的力量:虽然中国工人阶级并不是非常强大,但中国共产党“并非仅仅代表国内六十一万的工业无产阶级而存在”,“假使仅仅有此,他早已不存在了”,国际共运中世界其他国家的无产阶级将帮助中国革命,“辅翼其幼稚的无产阶级”[5-12]。因此中国革命必须时时注意阶级斗争,“为劳动平民的利益,而应用之于实际运动”[5-13]。简而言之,对瞿秋白而言,中国革命不仅有国内无产阶级的力量,更有世界无产阶级做后盾,中国革命将直接从国民革命发展成社会主义革命,中间不应插入资产阶级掌权的阶段。无论这个观点正确与否,共产主义运动确实构成了瞿秋白考量政权问题的一个重要基点。
大革命初期中共选择暴动这一革命方式也对瞿秋白等人的政权思想产生了影响。在选择暴动作为革命方式的背景下,中共所指的“政权”指的是全国性的政权,而非局部的政权。在这一点上,党内思想是一致的。如陈独秀曾批评国民党忽视群众运动,“占据一隅之地,养数万军队”的革命方式是“此路不通”[14-3]。蔡和森指出“革命党不拿政权则已,要拿便要拿一个全的”,“部分的政权,不仅于革命无益,而且有害”[19-2]。张国焘也曾批评国民党的军事运动“只图占领一二省组织一个所谓革命政府”,“把全中国的革命变成南方局部的革命”,认为国民党应集中精力发动群众运动,组织一个全国范围的群众性政党[21]。暴动这一革命方式有两个重要的特点:第一,要求有充分的群众动员,因此耗时很长。北伐之前,中共党内许多人认为国民革命胜利将是很久以后的事情,无产阶级有充足的时间培育自己的力量。第二,革命胜利与否、政权落入谁手取决于民众力量,民众的觉醒是国民革命的关键。例如蔡和森认为中国革命并非仅仅用武力完成统一、建立中央政府那么简单,而是要在民众觉悟的基础上创造新的政治局面,中国所需要的“不是武力的统一,但是革命的统一”[19-3]。中共还曾批评孙中山幻想通过弥合直系、奉系、皖系和西南诸省之间的分歧实现统一,认为此种未建立在民众运动基础上的联合只能说是“半封建半民主的局面”,“必须用革命手段根本破坏旧军事组织,由民众武装去解除旧支配阶级——军阀的武装”[19-4]。而群众运动恰恰是中共的专长。暴动的这两个特点为无产阶级主导未来政权提供了理论上的可能性。
陈独秀对国民革命以及阶级关系的认识随着群众运动的发展逐步转变。1924年9月,在商团事件前后,陈独秀对资产阶级的态度日益消极,更加强调工农阶级的重要性,提出“劳资两方面的利益绝对冲突,只有一方面退让,而无调和的可能”,支持工人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斗争[14-4]。五卅运动之后群众运动的快速发展使得陈独秀的转变更加明显。1925年9月,在《本报三年来革命政策之概观》中,陈独秀强调资产阶级之妥协使国民革命“大受打击而陷于停顿状态”,今后革命继续向前发展有赖于“中国工农阶级的组织得到更大的发展自由”[14-5]。同年11月陈独秀又在《中国民族运动中之资产阶级》中鲜明地指出中国的资产阶级“已是全世界反动的资产阶级之一部分”,“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资产阶级不革命”这一公式“又在中国民族运动中证实了”[14-6]。此时党内争取无产阶级革命领导权的呼声很高,就连被视为右倾代表人物的彭述之也于1924年开始强调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水火不容,“中国的资产阶级中反革命的成分居多,而革命希望的很少”,无产阶级“一方面须极力领导国民革命,推动国民革命到底;另一方面又须准备将来之无产阶级革命”[22]。
1925年10月,陈独秀在中共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上提出国共两党由党内合作改为党外合作,中共脱离国民党独立发展的问题[23]。虽然大会否定了陈独秀国共分家的建议,但大会通过的《中国现时的政局与共产党的职任议决案》(以下简称《议决案》)对政权进行了新的规划,党内两种政权思想实现整合。《议决案》指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分化日益明显,资产阶级“不但反对无产阶级而且背叛民族革命”,革命动力除无产阶级外仅有其同盟者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革命联合战线自然也仅包括三个阶级,所要建立的“革命民众政权”已将资产阶级列为限制的对象。此外《议决案》还提出,“国民党中的资产阶级代表发生相当的反动”,这一部分已不再被视为革命的合作对象,继续合作的对象是除反动派以外的国民党,即代表“城市小资产阶级和一部分农民”的国民党。《议决案》中也出现了“力争平民政权”的内容,这时所谓“平民”指的是工、农、小资产阶级组成的“革命民众”,已经具备了鲜明的阶级对抗的思想,与三大所谓“平民的民权”有天壤之别[9-3]。共产国际方面对中共“有产生左倾的危险”的忧虑从侧面证明了这一变化[18-2]。
此后,陈独秀在《孙中山三民主义中之民族主义是不是国家主义?》(1926年5月25日)、《打破“民族的巴士的狱”》(1926年5月30日)、《平民之不平》(1926年6月16日)、《平民的中日亲善》(1926年6月23日)、《论国民政府之北伐》(1926年7月7日)等文中,将“富绅”“巨商”“有财产之人”“大资产阶级”等排除在“平民”概念之外,认为“平民”遭受资产阶级剥削和欺骗,逐渐将“平民”与工农等底层群众画上等号[24]。受此影响,中共中央文件中“平民”的内涵也逐渐统一到工农等底层群众上[25]。陈独秀对“平民”内涵的认识经历了数次反复,在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前后由侧重反封建政治特权的黎民百姓转变为既反政治特权又反经济压迫的底层群众,国共合作初期又由底层群众转回黎民百姓,五卅运动后再度将资产阶级排除在外,转回底层群众。陈独秀认识的复杂变化是1920年代党内政权思想剧烈转轨的缩影。
北伐使得政权问题由理论研讨转向实际操作,中共五大正式提出“工农小资产阶级的民权独裁制”,这是对“革命民众政权”思想的进一步发展。相比“革命民众”,“工农小资产阶级”显然立场更加鲜明,所指也更为明确。
结语
1920年代初,党内熟知列宁主义革命理论的瞿秋白提议学习《两种策略》之工农民主专政思想,强调“平民政权”对资产阶级的遏制。而陈独秀则将“平民政权”视为资产阶级领导的各阶级联合的政权。随着陈独秀等人转变对资产阶级的态度,双方观点逐渐趋同。1925年10月中共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后,“平民”概念又逐步统一,党内政权思想也在会议提出的“革命民众政权”思想中实现整合。共产国际希望中共继续保持与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因此对中共日益激进的政权主张最初并不支持。1926年初,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六次全会通过的《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反对中共在政权设计中将资产阶级排除在外[26-1]。直到同年年底召开第七次全会,共产国际才提出建立“无产阶级、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革命联盟民主专政”,正式认可中共的“革命民众政权”思想[26-2]。由此可见,中共在大革命中已经开始对中国革命开展较为独立的探索。但一方面受到共产国际的影响,另一方面由于自身的不成熟,中共虽然明确了政权中无产阶级的领导地位和对资产阶级的限制,但对于在实践中如何实现无产阶级的领导权缺乏科学而系统的认识。在提出无产阶级领导权后很长一段时期内,中共仍将国民党视为国民革命的领导者,未能明确共产党对革命和政权的领导权。而中共自身与国民党的关系逐渐由融合转变到联合,作为无产阶级领导权执行者的中共始终无法掌握对国民党的领导权,这使得无产阶级领导权的实现缺乏基本依托和可行路径。例如陈独秀在《我们现在为什么争斗?》等文中否认中共与国民党争夺领导权和政权的可能性,认为共产党执政不会发生在国民革命。陈独秀“二次革命论”的形成在一定程度上正是受到了党的领导权问题的影响,因而在一定时期内陈独秀一面强调无产阶级领导权,一面却对国民党做出种种妥协与让步。这并非陈独秀一人之过,在共产国际强调国共合作的大背景下,中共很难突出自身的领导权。即便中共五大宣布,“工人阶级在国民革命运动中站在最主要的地位上”,“已取得斗争的领导权”,提出“工农小资产阶级的民权独裁制”[27],但与此同时在政党问题上,共产国际和中共仍未放弃争取国民党左派的希望,甚至继续坚持“增强国民党作为国民革命领导者的权威”[28],以至于中共在土地革命战争初期打出的依旧是国民党左派的旗号。从问题的提出到理论的完善,从理论的探索到实践的应用,革命理论的形成是一个极其复杂的历史过程,1920年代中共对政权阶级构成认识的分歧与整合只是这种历史复杂性的冰山一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