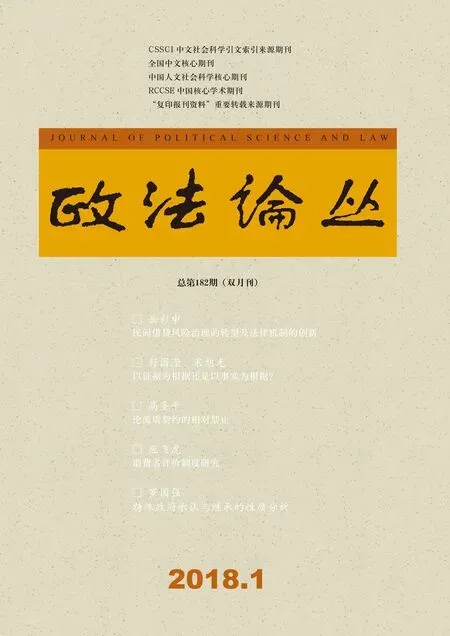实用主义刑法修正的进化论观察*
王强军
(南开大学法学院,天津 300350)
社会依赖通过各种手段强迫或鼓励民众去遵守规则,而其中最为熟悉也最为有效的就是刑法。通过刑法可以宣告某些行为是犯罪行为,能够确认道德边界行为,能够给犯罪人准确的报应。[1]P46刑法客观上确实能够起到这些实用的价值和功能。法律具有实用性本质上无可厚非,因为法律的本质就是为人们的交往建构规则,同时为裁判行为提供规范和标尺。随着社会发展提出修正刑法的要求是正常且正当的。没有人对政府和国家应当预防和惩罚犯罪的义务和功能提出疑问,但宪法层面上的问题是:国家是否应当保证公民不会被认定为犯罪?很多社会公众都会存在以下两方面的误解:第一,联邦政府对于刑法的发展具有首要的责任;第二,刑法条文越多越发达,社会公众就会更加安全。[2]P546社会公众存在偏差的刑法观念和刑法扩张的本性遇到了社会治理手段弱化的时代,就必然会催生实用主义刑法修正的兴起和泛滥。
一、实用主义刑法修正的表现
刑法原本应当有自己在法律体系中的定位,这种定位就是不应当过度使用,而应当较为矜持、严肃和理性。但是,当下的刑法却被过度使用并强调实用性。尽管刑法在性质上属于部门法,具有实用性是其特征和本质,但是,刑法还是应当具有不同于其他部门法的内在特质:那就是应当在惩罚犯罪时具有理性。而我们当下的刑法修正已经背离了这一基本准则和精神。当今世界对于安全的需求持续上升,犯罪和对犯罪的恐惧成为当代社会的标志,原本是“善良公民自由大宪章”的刑法正在受到对于安全的追求的挑战。我们所说的与犯罪行为作斗争,说白了主要是依靠刑法,也即是刑罚惩罚。[3]P182具体到立法和司法过程中就是,立法过程中刑法调整范围的扩大、社会治理过度刑法化、刑法从注重惩罚犯罪转向预防犯罪、从注重事后结果惩罚转向事前风险防控;在刑事司法过程中,对于刑法解释过度强调实用主义,将刑法作为一种为了达到实用效果而通过法律解释的方法达到目的的工具。
比如,当环境出现问题时,我们增加和调整有关环境的犯罪;当社会公众对出行安全有较高的呼吁时,我们修正涉及公众出行安全的罪名,包括增加盗窃罪的扒窃、入户盗窃等类型,包括增设危险驾驶罪,而且危险驾驶罪的范围从《刑法修正案㈧》到《刑法修正案㈨》实现了行为模式的扩容;当社会中“医患纠纷”突出时,我们将“医闹”行为入刑,在扰乱社会秩序罪中明确进行列举;当社会中出现恐怖袭击,为了应对恐怖主义的阴影,我们增设了有关恐怖活动的犯罪,而且将惩罚的时间提前,将预备实施恐怖活动的行为认定为犯罪;针对当前社会诚信缺失,欺诈等背信行为多发,社会危害严重的实际情况,为发挥刑法对公民行为价值取向的引领作用,《刑法修正案㈨》进行了如下的修正:一是,修改伪造、变造居民身份证的犯罪规定,将证件的范围扩大到护照、社会保障卡、驾驶证等证件;同时将买卖居民身份证、护照等证件的行为以及使用伪造、变造的居民身份证、护照等证件的行为规定为犯罪。二是,增加规定组织考试作弊等犯罪。将在国家规定的考试中,组织考生作弊的,为他人提供作弊器材的,向他人非法出售或者提供试题、答案的,以及代替他人或者让他人代替自己参加考试等破坏考试秩序的行为规定为犯罪。三是,增加规定虚假诉讼犯罪。将为谋取不正当利益,以捏造的事实提起民事诉讼、严重妨害司法秩序的行为规定为犯罪,等等。
不仅我国的刑法修正如此,国外也存在实用主义刑事立法的情形。在美国,一旦出现相对较为严重的社会问题,唯一的途径就是国会迅速通过一项法案来惩罚这种行为。绑架了查尔斯·林德伯克的儿子从而促成了《联邦绑架法》;由于对于马丁·路德金和罗伯特·肯尼迪等人的谋杀是通过枪支实施的,于是就导致了《枪支管控法案》,等等。国会制定和通过刑法法案如同打开的水龙头中的水一样哗哗流个不停。国会在2000年到2007年间通过了将近450个新罪名,平均是每周一个罪名。[4]P725可见其对通过刑法实现社会治理的依赖性和迫切性。
在德国,为了贯彻纳粹的战争经济政策,战争时期纳粹德国的经济刑法把刑法适用的范围扩大到了极点、把刑罚规定严厉到了极点、同时把刑法的使用灵活到了极点。纳粹不仅在经济管理的各个环节都规定了对违法行为的惩罚,而且通过制定适用范围广泛的犯罪构成,来扩大刑法的适用范围。从而让经济刑法发展成为一种最经济的具有管理功能的手段,因为如果不这样,在控制与监督社会与经济方面,就需要建立其他费用昂贵的强大的管理制度。[5]P102在笔者看来,这些刑事立法和刑法修正都出于实用主义思维,强调通过刑法解决社会中的现实问题。
过度依赖刑法去完成某些社会管理工作,比如利用刑法强化道德引领、提供社会服务和避免其他部门法的压力,被证明在功能上是无效的,实际上也造成了非常大的障碍。[6]P17桑福德·卡迪什教授曾经指出,我们应当警惕刑法的过度适用,也就是过度犯罪化。我们不应当通过刑法来提升道德信仰(比如将家庭乱伦、堕胎、赌博、吸毒、卖淫等行为犯罪化),刑法也不应当用来提升社会和商业服务(比如将醉酒行为和空头支票行为犯罪化),刑法也不应当为了控制社会秩序的安全而赋予警察特殊的权利(将流浪行为和不符合秩序的行为犯罪化)。[7]P719
犯罪是一个很复杂的社会现象,这也就意味着导致犯罪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所以,刑事政策就应当在犯罪初始形成阶段、发展变化阶段以及惩罚报应阶段都有所介入,在各个阶段配合紧密的刑事政策在预防犯罪效果上会更加有效。[8]P1271而不能一味强调某一阶段或某一过程,更不能单纯强调通过刑罚的惩罚,不能简单将刑事政策理解为通过刑法与犯罪行为作斗争。如果刑事政策过分强调预防犯罪依靠刑法这种较为单一的工具,就会阻碍政府采取其他更好的措施来完成两项事情:第一,减少或限制犯罪发生原因;第二,采取措施对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进行很好的管理,从而为有可能实施犯罪的人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从而减少犯罪的发生。[9]P169
二、实用主义刑法修正的危害
尽管犯罪和罪过多种多样,但是犯罪行为、反社会行为、变态行为等都是那些不同于常人的人实施的。所以,社会预防、个人矫正、社会改革三位一体才是预防犯罪的根本。另一种说法就是,犯罪都是那些具有特定特征以及社会性格的人实施的。所以,犯罪的预防措施就是对这些个体进行干涉,大体的方式有两种:在个人成长过程中的教育和训练,尤其是在少儿时期应当避免犯罪信息对个人的影响。从这个角度讲,预防犯罪应当是所有社会措施的“组合”共同来消灭犯罪发生的根源,从而避免初犯和累犯的发生。[9]P170
而当下的社会已经将刑法从一种后卫变成了前锋,无论是遇到何种社会管理方面的问题,都希望刑法能够发挥相应的冲锋陷阵的功能。这些表现包括对于醉酒的管理、对于考试秩序的管理、对于各种证件的虚假使用问题、各种行政责任的问责问题,等等。在人们的心里已经有一种根深蒂固的情结,那就是能够用刑法遮掩一切制度的漏洞。
因为,人们对于罪恶认识的最终惩罚后果就是刑罚处置。人们习惯于通过“短、平、快”的方式实现因果报应,而并不注重对导致违法行为的原因进行分析,也就不注重对相关社会制度的建构。比如,中国“危害食品安全行为”刑事规制体系呈现出主要依赖刑法典对特定危害行为设置罪名、核心犯罪行为属于“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公民的生命、健康安全价值并没有置于首位、实行“严打”刑事政策、鉴定制度不完备等特征。理想的情形应当是,立足于危害食品行为的现状,在与《食品安全法》的衔接中,兼顾实体和程序,构筑科学全面的刑事规制体系。[10]P128而制度建构不科学、权力不能得到有效的控制和制约,利用权力所实施的犯罪就不可避免,这一点我们在反腐败的整体工作中得到非常好的印证。对于腐败行为,我们当下选择的方式是法律反腐和重刑反腐,但我们现在已经认识到法律反腐和重刑反腐并不是最佳的方式,真正能够遏制和预防腐败的一定是制度的设计和建构,也即是“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如果我们仍然继续片面看到或过度强调刑法在反腐过程中的实用效果,那么就会南辕北辙、舍本逐末。
刑法修正过度实用会导致社会治理的弱化,而且会阻碍社会的发展。行为人实施了犯罪行为就应当受到刑罚惩罚,但前提是行为人应当清楚构成犯罪的标准是什么、界限在哪里?刑法的初衷是为了惩罚社会所认为的值得谴责的行为,也即是违背道德规范的行为。这些行为之所以构成犯罪,是因为他们行为本身的错误性,比如谋杀、强奸、抢劫。但是近些年来,刑法已经扩张到那些行为错误并不是因为行为本身的错误,而是一种法律的禁止。也就是说,这种错误是立法机关基于社会公共利益和行政管理的需要而设计出来的违法行为,而这些基于公共利益和行政管理需要所创造出来的犯罪也称之为“公共福利犯罪”。[11]P85所以,刑法在对某一行为犯罪化时,必须对以下三个问题进行衡量和判断:第一,法律制定出来是为了规范人们的行为,还是用来被违反的(laws are made to be broken)?第二,是否遵循危害性原则?是否存在只要你的行为不伤害别人的利益,那么你的任何行为都是被允许的;第三,获取经济利益的手段除了辛勤的劳动,没有别的其他或正确或错误的途径。如果认为上述三点不是社会公众尊重法律的根本,那么,我们只能认为社会公众尊重法律的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义务。[12]P1067
预防犯罪是每个国家刑事政策的主要内容之一。相应地,基于预防犯罪的需要也就会将某些预备行为等认定为犯罪,从而预防犯罪的刑事政策也让增加犯罪成为可能,同时也逐步增加对犯罪进行辩护的障碍。在许多国家,行政执法机构也正在承担主要的预防犯罪的角色和功能,因为司法机关的许多由执法机构来贯彻实施的制度促成了许多犯罪的成立。这些行政机构一方面能够制定更加容易执行和符合行政管理需要的政策,同时他们也可以设定足够的便利来推动他们政策的执行。[9]P168而行政管理对于行政违法和刑事犯罪界限的调整,客观上就会导致刑法的实质性修正,从而让行政权力的行使呈现出实质刑法化的特征。
在行政机关监管权力实质刑法化的情形下,原本就已经非常脆弱的行政违法和刑事犯罪的标准更模糊(blurred),尤其是公司犯罪(也即“白领犯罪”)。如果刑法的手臂过长,就会导致公司考量一个较好的商业决定是否会被充满野心和广阔犯罪视野的检察官认定为犯罪行为?如果公司犯罪的标准不明确,那么将会对公司的创新行为造成灭顶之灾,尤其是公司的创新行为。因为,如果一个创意或概念是超越当前的模式和概念的,如果公司考虑到这种行为具有受到刑罚惩罚的潜在风险,那么,公司就会搁置或扼杀这种创新的念头。这种搁置和扼杀创新的念头必然会阻碍公司的发展,阻碍公司在全球市场中的竞争,而只能注重国内法律的规定,着实是一种“削足适履”。[13]P1
而且,主观罪过的难以确定性和客观行为的特殊性决定了刑法将公司违法行为认定为犯罪应当更加谨慎。并不是说刑法不能介入公司违法犯罪行为,而是说,我们应当认识到通过刑法预防和惩罚公司犯罪的有限性。即便允许刑法对公司违法行为进行惩罚,也应当对于公司犯罪的主观罪过和客观行为进行有别于普通自然人犯罪的研究。唯有如此,我们才能确定刑法在公司犯罪的预防和惩罚中起到了真正的角色和作用,同时也确实解决了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14]P123
一个国家过分重视刑法在国家管理和治理过程中的作用,正像一个国家过分重视暴力在国家管理和治理过程中的作用一样,是社会政治文明程度不高、当政者对管理手段自信不足、整个社会环境依恋暴力和准暴力为倾向的明显表现。[15]P4从社会角度看,刑法过度介入社会治理,将导致社会治理手段简单化和弱化,而通过刑法的社会治理更说明政府的管理能力低下。因为,民法发达才是一个国家法治发达的标志和象征,刑法发达反而是一个国家法治不发达的标志和象征,刑法越发达说明国家的治理手段越匮乏。
三、实用主义刑法修正与刑法进化关系的分析
在某种意义上,法律是价值选择的理性化和制度化安排。人类社会交往的理性化程度是随着社会结构和社会需要的发展而不断提高的。需求的多样化必然表现为权利种类和内涵的多样化,这就要求人们对权利背后的价值有一个共同的认识,并通过民主立法程序作出理性的选择。[16]P25按照推动刑法进化的源动力不同,刑法进化可以分为外在需求和内在驱动两种情形下的进化。所谓外在需求,是指刑法所服务的对象——社会状况发生了变化,调整社会关系的外部需求呼唤刑法进行调整。所谓内在驱动,是指在刑法基本精神和原则的推动下,刑法从不成文到成文、从野蛮到文明、从残忍到人道逐渐进化的规律。基于社会发展外部需要推动的刑法修正也应当符合刑法进化的基本规律。
犯罪是特定的社会和法律系统中的产物,反映了特定时间和特定地点的利益结构,以及责任分配和安排。刑法是基于限制国家刑罚权恣意发动而出现的,刑法进化的基本规律必然是要注重对公民自由的保护。如果刑法修正违背这一基本规律,我们就会看到,为什么将犯罪的责任归咎于特定的犯罪人,而没有将其归咎于解释和适用刑法的社会、法律和政治生态?是什么原因以及在什么条件下公民会被采取强制措施并进入刑事诉讼程序?为什么我们社会中构成犯罪的往往是那些社会经济或其他方面处于弱势的青年或其他群体?在没有理解这些问题以及决定犯罪化的强大的力量之前,我们不可能真正理解刑法的社会意义。[17]P16
在法律进化的过程中,对于法律进化的路径和目标,大体上有这样两种思路:一种是自然法,一种是制定法。所谓自然法,就是按照法本身应当具有的理性、经验进行构建和发展;所谓制定法,就是按照社会结构的特定情况,根据治理社会的需要而构建相应的法律。无论是自然法路径还是制定法路径,可以看出,刑法进化的基本趋势可以体现为以下五个方面:从不成文法走向成文法;从罪刑擅断走向罪刑法定;从残酷走向人道、从野蛮走向文明;从重刑化走向轻刑化;从模糊走向精确。
刑法产生的初期是为了遏制罪刑擅断而出现。但是,刑罚权天然所具有的惩罚冲动决定了其不甘心受到约束,这种试图冲破约束的做法就是在刑法条文中留下足够的能够肆意发动刑罚权的空间和可能,所以,法条相对来说非常的模糊和笼统。这种模糊性和不精确性给刑罚权的滥用提供了空间,但是随着刑法的发展和进化,刑法逐渐地走向精确。
刑法修正也应当符合上述基本精神,犯罪的发生需要具备逻辑上的三个要素:犯罪人、被害人和不充分的控制机制。所以,我们刑事政策的制定也应当从上述三个要素出发,解决以下四个方面的问题:第一,减少犯罪的社会危害;第二,减少犯罪控制的成本;第三,分配这些成本;第四,以公平的方式实施上述行为。[18]P77在上述刑事政策的制约之下,我们才能确定科学的刑事立法和刑法修正的原则以及步骤。
比如,有学者指出,一项刑事立法应当按以下五个步骤展开审查:(1)目的是否具有合理性;(2)刑罚是不是达到合理目的的有效手段;(3)是否存在替代刑罚的手段;(4)利用刑罚保护法益的同时可能造成何种损害;(5)对相应的犯罪应当规定何种刑罚?[19]P88唯有进行了上述五个方面的全面审查之后依然认为应当进行刑法修正,此时的刑法修正才能做到既实现法益保护,又符合比例原则要求。
而实用主义刑法修正既不能实现刑法的进化,也不能实现社会治理的科学化。非但如此,还会导致整个社会对于刑法的迷恋和崇拜,从而导致社会治理过度刑法化。而社会治理过度刑法化又反过来会弱化社会规范、社会制度和其他部门法实现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实际上,民事制裁措施往往被认为比刑罚惩罚更有效,倒不是因为民事诉讼对于证据和规则的要求比刑事诉讼宽松,而是,当行为人面临着失去他们的金钱、财产、生意或谋生之道时,可能要比面对一个较低可能被指控刑事犯罪,他们有可能更加愿意遵守国家的非刑法法律法规。而且,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较高,相应地被定罪的概率就比较低。所以,行为人往往会感到侥幸。而且,即便是检察官的起诉达到了证据标准,也有可能被法官判处一个较低的刑罚,而这种刑罚可能还没有根据民法进行的制裁严重。[20]P221
比如,1899年的《河流和港口法案》被认为是美国第一部关于环境犯罪的制定法。因为它将违反规定向通航的河流中排放废物规定为一种轻罪。但是,美国国会最初制定和通过《河流和港口法案》的目的并不是为了保护环境,而是为了预防河流污染对于国内商业的影响。随着对环境监管法律的通过,19世纪八十年代将环境犯罪从轻罪升级为重罪。结果是,在19世纪八十年代,我们看到了环境犯罪的多个第一:第一次根据环境法的重罪起诉;第一次根据联邦量刑指南对于环境犯罪的监禁刑。但我们同时也看到,对环境问题是否需要刑法介入存在非常大的争论:有人提出对主观心理非常复杂的违反环境法的人进行刑事处罚是否适当?也有人提出对环境犯罪的主观心理要求标准过低,已经接近于严格责任。尤其是当公司的高管被指控对公司实施的违反环境法的行为承担责任时。[21]P1224除此之外,刑罚作为惩治生态环境犯罪的手段,其功能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因为,即使完全彻底的刑事制裁也不可能从根本上消除危害生态环境的犯罪。只有通过对环境犯罪人进行刑罚处罚的同时判处辅助措施,才能有效修复损害以达到更好的惩治犯罪、保护法益的作用。[22]P117
所以,当我们在决定刑法化和犯罪化的边界以及范围时,立法机关必须充分考虑各方的利益,包括被害人、加害人和社会大众。避免对刑法的滥用和不正当使用,防止刑法成为管制机制(policing mechanism)。[23]P387而且实用主义刑法修正非但不能推动刑法进化,相反会阻碍或降低刑法的科学性。有学者就指出,美国刑法的修正加速了美国刑法典退化的步骤和进程,这种退化可以从几个方面得到证明:第一,刑法修正受到特定利益群体的游说(special-interest-group lobbying)。刑法修正过程呈现出非常明显的源源不断的“人造或设计出来的犯罪”,而且很多犯罪并不是必须的。比如,有些州的刑法中有盗窃罪,结果在修正过程中又规定了特殊的盗窃罪;有普通的故意毁坏财物罪,结果在修正过程中又增加了针对图书资料、动物设施等的毁坏财物罪等等。第二,热点事件——政治反应的恶性循环。一些犯罪甚至一些严重的犯罪危害公众的利益,而立法机关感觉他们应当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应当对相应的行为有所反应。即便已经有相关的犯罪规定和惩罚相应的行为,立法机关也认为应当回应公众对相应问题的认识。这种设计出来的犯罪,对于整个社会来说,不仅是不需要的,而且会对刑法典的实际运行造成极其严重的伤害。[24]P171
四、刑法修正、社会变化、刑法进化的内在统一
社会肯定是逐渐发展变化的,在社会基础发生变化的前提下,刑法进化无时无刻不在进行,实现社会发展和刑法进化和谐统一的桥梁就是刑法修正。换句话说就是,刑法修正是实现社会发展和刑法进化的纽带。如果刑法修正契合社会发展和刑法进化的客观需要,那么,就会实现三者的完美统一和内在协调,从而共同促进并向科学化的方向发展。相反,如果刑法修正没有契合社会发展的需要和遵守刑法进化的规律,表现出一定的激进或保守,就会让社会秩序和规则出现混乱并阻碍社会进步,让刑法进化出现短暂的停留,甚至倒退。所以,刑法修正应当注重于社会发展和刑法进化的内在统一。
比如,随着计算机的普及以及计算机犯罪的增多,刑法必须应对这种现实需要。德国于1986年公布了两部打击经济犯罪的法律,由这两部法律规定的计算机刑法条文基本上至今仍然有效。欧洲范围内,有关计算机和网络刑法的规定比较重要的两个立法文件是2001年11月23日欧洲理事会颁布的《关于计算机犯罪的公约》和2005年2月24日欧盟理事会颁布的《关于攻击信息系统的理事会协议框架》。[25]P422这种随着新兴事物的出现而增设的犯罪,是我们必须应对的,比如计算机、人工智能等等。
再比如,对于著作权的刑法保护,虽然频繁的修法是不符合法律明确性与可预测性要求的,但是,对于著作权犯罪的刑法条文而言,自1997年颁布至今一直没有修改,即使现在修改,也谈不上频繁修改。并且很多新型的犯罪行为不断出现,司法解释在立法空白严重的情况下,能力是有限的,不能指望其解决所有问题。因此,如前所论,以立法的方式填补侵犯著作权的行为方式之漏洞迫在眉睫。[26]P35
但一些“新形式”的老问题就需要我们动用司法的智慧进行处理。比如反恐问题,有些国家的恐怖活动预防和惩罚并不是通过增加新的恐怖活动犯罪来实现的。因为有学者就提出过专门的反恐措施并不需要也不正当。原因非常简单,因为很多恐怖活动犯罪行为也都是刑法已经规定的普通犯罪。在澳大利亚,反恐行为所涉及的行为都已经被刑法典规定为犯罪,这些普通的犯罪包括谋杀、绑架、袭击、严重的伤害、劫持航空器等等。所以我们可以说,恐怖主义犯罪等于是给普通犯罪重新贴上恐怖的标签。二者区别就在于动机不同或规模不同,但并不能改变行为本身的性质,甚至也不应当影响行为的量刑。[27]P21所以,没有必要单独针对恐怖活动犯罪规定新的犯罪。同时,对于某些犯罪的高发性或严重性,也并没有必要通过刑法修正进行调整。比如,贪污罪、受贿罪是一种自然犯,任何人都能认识到其违法性。不断提高其犯罪的数额标准,只能使国家工作人员对自然犯的违法性认识更加模糊,反而不利于预防犯罪。[28]P6
而对传统法益新的表现形式和内容,并没有必要进行刑法的修正,只需要对传统法益的内涵和外延进行符合时代的解释即可。生命、身体、自由、财产、名誉等由刑法保护的法益,可谓传统法益,但是,传统法益的内容并非一成不变。在网络时代,一些新的法益会不断出现,但这些新的法益与传统法益具有同质性,因而使传统法益的内容会不断扩大。其中,部分新的内容通过解释路径就可以与传统法益一样受到刑法的保护,部分新的内容则需要修改刑法予以保护。例如,在网络时代,出现了大量的虚拟财产,在我国刑法关于侵犯财产罪的规定没有区分“财物”与“财产性利益”两种行为对象的情况下,只需要通过解释路径,就可以将虚拟财产解释为财物,从而保护虚拟财产。[29]P80并不需要专门针对网络财产的刑法修正。
如果前面所述的计算机和恐怖活动还只是局部和零星的社会问题,刑法可能还有足够的理性来应对,那么对于宏观的社会结构或社会环境,刑法可能就会背离社会发展的现实和刑法进化的内在规律。一旦我们采取广泛的刑法概念,那么就会将建立在主观犯罪意图基础上的刑法成为不可能。在过去20年里,公共秩序领域的疯狂立法活动已经证实了这一预言。公共秩序犯罪不仅改变了基本自由(表达自由和结社自由),传统关于刑法边界的认识也正在被反恐立法和其它民刑法混合的立法所挑战(1997年的“保护免受骚扰法”、1998年的“犯罪与骚乱法”、2003年的“反社会行为法”)。[15]P130再比如,对于环境生态犯罪,刑法作为保护包括草原生态在内的自然环境类法益的最后一道屏障,理应将其作为环境保护法律体系的组成部分,使之更好地发挥应有之功效。刑法从预防的角度出发,应该使刑罚相对于企业来说具有足够的威慑力,而从惩治的角度来看,也应该做到罪责刑相适应,同时也要重视恢复被企业行为破坏的草原生态。[30]P143我们唯有充分认识到刑法功能的必要性和使用上的谦抑性,才能切实发挥刑法的功能。
在我们国家,刑法修正面临的最大社会背景问题就是:我们是否已经或即将进入风险社会,是否需要刑法应对这种变化。可以说,论证刑法修正、社会发展和刑法进化的关系问题,必然不能回避刑法如何应对风险社会的问题。因为风险社会是对社会发展阶段的一种整体认识,如果我们承认了风险社会的存在,那么其对刑法的影响将是全方位的。如果刑法修正不能在刑法进化的约束之下理性对待风险社会,那么刑法将会出现根本性的变革。
实际上,我们当下的绝大部分的实用主义刑法修正已经是在风险社会理念的裹挟下进行的,或者说我们刑法修正已经被风险社会的理念所占领。要实现刑法修正在刑法进化规律的制约下理性应对风险社会,我们必须解决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第一,风险社会是否是一种真实的社会状态和社会结构,我们是否已经具备了风险社会的特征;第二,风险社会背景下的风险是否需要刑法进行应对;第三,如果需要刑法应对风险,刑法进化的客观规律对刑法修正有何限制和制约。
首先,需要分清我们是否真的进入风险社会。如果我们当下的社会确实具备了贝克所说的风险社会的特征,就说明我们决定刑法的社会基础发生了变化,刑法进行修正就是建立在对社会结构和社会状态准确认识的基础之上。但风险刑法理论最根本的谬误在于,未全面了解贝克的反思性现代化理论,因而对风险社会理论的理解过于肤浅和狭隘,更多地是根据“风险社会”的字面含义,将其理解为“有风险的社会”或“风险增多的社会”,这完全背离了风险社会理论的精髓。尤其是,它未能明确风险社会的风险与传统社会的风险之间的“世纪性差别”,曲解了风险范畴的真实含义。对于风险刑法论者而言,风险社会理论的最大意义,可能只是激活了“风险”这样一个词汇。它恰好迎合了当前普遍存在的焦虑和不安的社会心理,于是,所有的问题都被装入了“风险”这个时髦的“筐”里。[31]P76除此之外,我国刑法学界所热衷讨论的风险社会,直接继受自贝克的学说,然而,与社会学中的讨论不同,我国刑法学界对风险社会理论基本上流于形式的、狭隘的甚或是望文生义的理解,并未从现代性的角度加以展开。无论是支持者还是反对者,都没有将它当作解读社会转型的一种普遍的社会理论。这样的误读不仅在相当程度上扭曲了风险社会理论本来的面目,也直接影响到人们对风险概念的正确理解。[32]P60所以,基于预防风险的实用主义刑法修正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其次,要分析我们是否需要刑法来应对风险社会。基于刑法是控制风险的工具以及所具有的防范风险的功能,用刑法前置化来防范风险还是有一定正当性和必要性的。然而,在肯定刑法在某些领域可以将处罚时间前置化的同时,也不应忽略刑法谦抑性的基本精神。在我国,社会转型与社会风险交织在一起,社会风险陡增,但越在此时越是要理性看待刑法应对。事实上,当前我国所谈的很多风险,仍然属于传统刑法的范畴,甚至许多风险后果的酿成与制度、规范的缺失、监督力量的薄弱有直接关系;当前发生的各种犯罪现象,也属于传统的犯罪现象,传统刑法的治理方式并没有明显不适应。之所以风险刑法的概念开始流行,主要的缘故不是风险需要新刑法方式来控制,而是在制度失灵的情形之下将刑罚手段敬若神明,寻求另外一种刑法的庇护。[33]P133
而且对于风险的预防和规制,我们还不可回避地要面临和解决错误的否定(false negatives)和错误的肯定(false positives)。比如,出于反恐的需要,而将准备实施恐怖活动的行为也认定为犯罪,而行为人是否具有实施恐怖活动的风险就存在错误的肯定和错误的否定的风险。错误的否定是指,如果我们错误地认为一个人没有危险,但实际上他实施了恐怖行为;错误的肯定是指,如果我们错误地认为一个人有实施恐怖行为的危险,但实际上他是无罪的。如果我们错误地认为一个人不需要预防性措施但他实施了犯罪,那么这种错误是明显的,因为,可以通过行为人实施的犯罪进行数据上的证明;但是,如果我们错误地认为一个人具有实施危害社会的危险进而对其采取了预防性司法措施并最终定罪的话,但实际上行为人并不会实施危害行为,这种错误是不可见的,甚至永远不可能知道。[34]P505换句话说就是,基于风险预防和控制,我们采取刑事处罚早期化的显性失败就是依然有恐怖袭击事件和危害公共安全的犯罪行为的发生,而刑事处罚早期化的隐性失败就是我们基于刑事处罚早期化而错误将原本没有危险的人而定罪判刑的数量。所以,运用刑法来预防和规制风险是存在很大风险的,甚至有可能大于风险本身。换言之,运用刑法预防风险才是我们当下社会最大的风险。
最后,我们来看刑法进化的规律对于刑法应对风险的制约。实际上,风险刑法理论并没有指出风险社会中的风险如何进入刑法视野的适当路径,而是将两者的连接建立在风险社会与风险刑法都采用的风险这个内涵漂移与外延模糊的词汇之上,这是一种虚幻的联系。[35]P110在风险社会下,我们的刑法经历了非常大的膨胀,包括危险驾驶罪、污染环境罪、网络环境下的寻衅滋事罪,等等。这种观念的存在和强化还会导致对风险控制的提前,从而导致刑法保护的提前,而刑法保护的提前肯定会加大对某些原本不构成犯罪行为的处罚。
而且这种刑法保护的提前并不是一个相对孤立问题,而是一个系统问题,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1)当下的刑事司法证明过去发生的犯罪事实都非常困难,更何况对于未来一个人会实施什么行为的预测,这不是困难有多大的问题,而是完全不可能。如果我们接受了预防性刑法和风险刑法,那么客观上就会接受一个较低标准的证明标准。我们对于已然犯罪的证明标准要求达到排除一切合理怀疑的程度,而如果我们对于预防性刑法的证明标注也是排除一切合理怀疑的话,那么这些预防性措施将无法实施。如果我们降低了预防性刑法的证明标准,我们也就是提高了刑事司法错误的风险。(2)刑法惩罚行为人的构成要件要求具备客观行为和主观方面的有机统一,也就是行为人要有实施犯罪的自由意志。而在预防性刑法的情形下,我们只是基于行为人未来可能实施某些违法行为,并不考虑他的自由意志,而且不考虑他是否存在行为选择的自由意志。(3)如果允许政府对行为人未来实施的行为进行预防性司法措施的话,那么,出现基于种族、宗教、性别等选择性司法将不可避免。在对已然犯罪进行处理时,选择性司法已经非常严重,对未然犯罪进行惩罚时,选择性司法将会更加疯狂。(4)缺乏对于预防性措施实际执行效果的客观衡量标准。“更加安全胜过道歉”的理念将会不可避免地导致基于恐惧而扩张预防性刑法措施。(5)我们并不单单是不能清楚预防性司法的实际效果,更为关键的是我们有可能会对预防性司法有一个系统性和全面性的曲解。
在刑事立法层面上实现了刑法保护提前,那么必然会波及和影响到刑事司法,这样一来就会将原本不构成犯罪和不作为犯罪处理的行为都作为犯罪。如果激进的刑法立场一旦形成,再加上刑法本身扩张的本性,再想对刑法进行控制,将刑权力关进笼子里则将非常困难。立法机关需要权衡的是,如若将某种行为规定为犯罪,所保护的法益与可能造成的法益侵害相比,孰轻孰重?如果将某种行为规定为犯罪所造成的法益侵害大于其所保护的法益,立法机关就不得将这种行为规定为犯罪。所以,法益衡量是法益保护原则的最重要内容之一,司法机关在适用刑法时,立法机关在制定刑法时,都需要进行法益衡量。[17]P93
立法机关不能仅仅出于减轻公诉机关的证明责任、克服形式预备犯的证明困难、消除处罚形式预备犯的形式合法性危机的实用主义考虑,而不加选择地将犯罪预备行为任意拟制为实质预备犯。一个理智的、审慎的立法者,必须始终平衡刑法干预的必要性与谦抑性。根据现代刑法的辅助性法益保护机能定位,视防止对重大法益的侵害风险由间接而抽象的危险发展至直接而紧迫的危险的风险控制需要,斟酌决定是否确需将本身已经显现对重大法益的抽象侵害危险的实质预备行为例外地拟制为独立的实行行为。否则,就可能在实质预备犯的形式合法性的外衣掩护下,堂而皇之地、不当地前置和扩大预备行为的刑罚处罚范围。[36]P176
结语
社会发展过程中必然会出现各种“新型问题”、“新兴问题”,而解决这些问题考验着每一个国家和每一届政府。理性的思路应当是首先通过道德规范、社会规范、社会制度进行处理,制定规章制度和行为规范,而且允许上述规章制度和行为规范“试错”,给它们充分试错的机会。只有这些制度和规范不能解决和遏制社会中出现的新兴问题时,我们才能动用刑法进行预防和惩罚,而且动用刑法也并不是直接进行刑事立法,而是应当首先通过现有刑法的合理解释进行预防和惩罚。只有现有的刑法规范不能预防这些新兴行为时,我们才可以通过刑法修正案的方式进行刑法修正。如果刑法扩展到惩罚单独的罪恶意念或极小可能的危害行为的话,刑法就已经超越了它应当被接受的角色定位,就会呈现出不公正性和难以实现相应的效果,自然就会失去其信誉和仁义性。[37]P226所以,刑法只有在最需要进行惩罚和威慑的地方出现时才是最正当的。
[1] Mary M. Cheh, Civil remedies to control crime: Legal issues and constitutional challenges, Crime Prevention Studies, volume 9 (1998).
[2] Johns. Baker, JR, Jurisdictional and separation of powers strategies to limit the expansion of federal crimes, American university law review,[Vol. 54].
[3] Anabela miranda rodrigues, Criminal Policy: New Challenges, Old Ways,Cahiers De Défense Sociale Bulletin De La Societé International De Défense Sociale Pour Une Politique Criminelle Humaniste,2003,No30.
[4] Paul J. Larkin, JRPublic choice theory and overcriminalization, Harvard Journal of Law & Public Policy [Vol. 36,No. 2].
[5] 王世洲.德国经济政策与经济刑法、经济犯罪互动关系研究[J].中外法学,1999,6.
[6] Sanford H. Kadish,The Crisis of Overcriminalization, Am. Crim. L. Q. 17 (1968).
[7] Sanford H. Kadish, More on Overcriminalization: A reply to professor Junker, UCLA L. Rev,19. 1971,.
[8] Carla Monroy,The incidence of the criminal policy in the conformation of the public space, A: Virtual City and Territory. "Back to the Sense of the City: International Monograph Book". Barcelona: Centre de Política de Sòl i Valoracions, 2016.
[9] Zhaleh Mahmodi, Mohammad Ali Heydari, A case study of Criminal policy in Prevention of Crime , Adv. Environ. Biol., 8(1), 2014.
[10] 王娜.论危害食品安全行为的刑事规制——以上海“福喜事件”为切入点[J].上海政法学院学报,2016,1.
[11] William L. Anderson and Candice E. Jackson, Law as a Weapon: How RICO Subverts Libertyand the True Purpose of Law, The Independent Review, v. IX, n. 1, Summer 2004, ISSN 1086-1653.
[12] Jonathan Jackson, Ben Bradford, Mike Hough, Andy Myhill, Paul Quinton and Tom R. Tyler,Why do people comply with the law? British Journal of Criminology, 2012,52,p1067.
[13] Dick Thornburgh,Overcriminalization: Sacrificing the Rule of Law in Pursuit of “Justice” heritage lectures,No. 1180,Delivered October 6, 2010.
[14] Mark Fenwick,Corporate Wrongdoing and the Limits of the Criminal Law, in Facing the Limits of the Law,2009,P123.
[15] 杨兴培.公器乃当公论,神器更当持重:刑法修正方式的慎思与评价[J].法学,2011,4.
[16] 季晨溦.民意沟通:公共理性的司法构建基础[J].政法论丛,2017,3.
[17] Lacey, Wells and Quick, Reconstructing Criminal Law: Text and Material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18] Kauko Aromaa, Responsible criminal policy / Crime and criminal policy, Kriminologijos studijos 2014,1.
[19] 张明楷.法益保护与比例原则[J].中国社会科学,2017,7.
[20] PAUL H. ROBINSON AND MICHAEL T. CAHILL, LAW WITHOUT JUSTICE:Why Criminal Law Doesn’t Give People What They Deserv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6.
[21] David M. Uhlmann, environmental crime comes of age: the evolution of criminal enforcement in the environmental regulatory schem,Utan law review,no4,2009.
[22] 张霞.生态环境案件中恢复性司法应用研究[J].政法论丛,2016,2.
[23] Vera Bergelson,book review:The Boundaries of the Criminal Law, Crim Law and Philos (2013) 7.
[24] Paul H. Robinson, Michael T. CahillCan a Model Penal Code SecondSave the States from Themselves? Ohio State Journal of criminal law [Vol 1 2003].
[25] [德]埃里克希尔根多夫.德国刑法学:从传统到现代[M].江溯,黄笑岩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
[26] 刘邵彬,张晓伟.著作权犯罪若干问题探讨[J].上海政法学院学报,2016,2.
[27] Gregory Rose and Diana Nestorovska ,Australian counter-terrorism offences: Necessity and clarity in federal criminal law reforms , (2007) 31 Crim LJ 20.
[28] 张明楷.贪污贿赂罪的司法与立法发展方向[J].政法论坛,2017,1.
[29] 张明楷.网络时代的刑事立法[J].法律科学,2017,3.
[30] 于雪婷,刘晓莉.草原生态刑法保护下的企业刑事责任论[J].政法论丛,2017,2.
[31] 南连伟.风险刑法理论的批判与反思[J].法学研究,2012,4.
[32] 劳东燕.风险社会与变动中的刑法理论[J].中外法学,2014,1.
[33] 孙万怀.风险刑法的现实风险与控制[J].法律科学,2013,6.
[34] David Cole, The Difference Prevention Makes: Regulating Preventive Justice, Criminal Law and Philosophy (2015) 9,P505.
[35] 陈兴良.风险刑法理论的法教义学批判 [J].中外法学,2014,1.
[36] 梁根林.预备犯普遍处罚原则的困境与突围——《刑法》第22条的解读与重构[J].中国法学,2011,2.
[37] PH Robinson , A Theory of Justification: Societal Harm as a Prerequisite for Criminal Liability,Ucla L.rev, 1975,[vol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