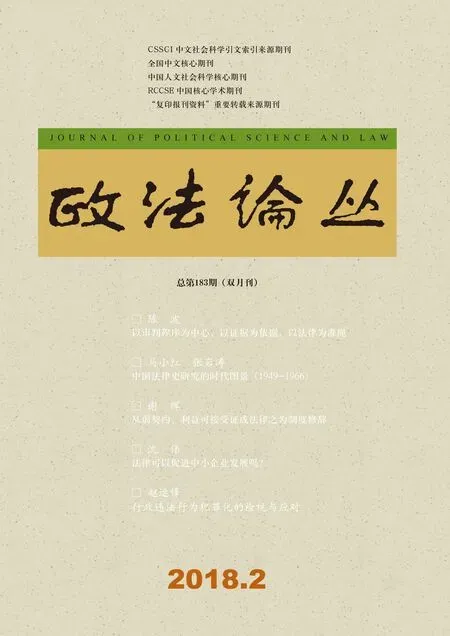为权衡理论辩护*
雷 磊
(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北京 102249)
一、引言:权衡及其争议
法律原则的典型适用方式是权衡。因为作为最佳化命令,原则要求其内容在相对于法律上与事实上可能的范围内尽最大可能被实现,并能以不同的程度被实现。[1]P75[2]80事实上的可能涉及的是对实现原则之手段的选择,它所要回答的问题是,采用何种事实上的手段才能在尽可能满足一个原则的同时不过分地损害另一个原则。而法律上的可能涉及的则是原则间的比较,它所要回答的问题是,在事实条件和手段既定的前提下,应该优先实现哪个原则的内容。或者说,在个案中,哪个原则更有分量,更有实现的重要性。事实上的可能性意味着要符合适切性原则与必要性原则;而法律上的可能性则意味着要符合狭义上的比例原则。[1]P100[3]P297而狭义上的比例原则,涉及的就是通常所说的“权衡”。
针对权衡,学者们提出了大量的反对意见。这些反对意见可以被划归为不同的层面,①其中最主要的批评来自于两个层面:一是对权衡本身的批评。它认为,作为方法的权衡是一种非理性的过程。[4]P296[5]P445,460权衡无法以理性的方式来解决案件,而只是一种专断的修辞游戏而已。权衡将使得法律适用者可以首先做出一个主观判断,然后借助于权衡来证成这一判断,因而会危及法律裁判的客观性。这可以被称为“方法论上的反对意见”。二是对权衡所应用的领域的批评。由于原则权衡理论最广泛的应用领域是基本权利领域,它认为权衡有可能造成对基本权利的不当限制或减损,甚至“正当限制基本权利”的观念本身就存在问题。②这可以被称为“基本权利教义学上的反对意见”。要指出的是,这两种反对意见是不同的:相对而言,前者更为根本。因为即便能证明权衡并非适用于基本权利领域的恰当工具,也并不一定意味着权衡本身就是不理性的。本文要反驳的,是更为根本的方法论上的反对意见。
首先要指出,权衡的理性并不意味着绝对的正确性,而只是意味着可检验性,即基于每一个参与者都必然以理性的方式赞同之标准的可检验性。[6]P50可检验性蕴含着可证立性,即通过理性程序产生之结果来证立。我们将先来阐明权衡证立结论的基本形式,或者说形式结构问题(第二部分)。对于这种形式结构,论者们提出了两大类反对意见,我们将分别予以具体回应(第三、四部分)。最后给出结论(第五部分)。
二、权衡的形式结构
权衡只是一种论证形式,它的作用在于使得产生于特定前提的论据之间形成理性关系。而在具体个案中,一个具体结论的理性或正确性既取决于产生它的论证形式,也取决于论证所采纳的前提。而前提的理性取决于实质论证,与论证形式或者说权衡的理性并不相关。权衡的形式结构包括权衡法则,以及在此基础上的重力公式。
(一)权衡法则
1、权衡法则的表达
权衡法则构成了作为权衡程序之基础的理性标准,从这一法则出发可以推导出重力公式,而重力公式的结果则为论证负担提供了依据。权衡法则脱胎于德国宪法法院的“个案法益衡量”思想。后者认为,抽象的原则/价值冲突需要被处理为具体案件中现实的法益冲突,裁判者要通过考量不同法益受到保护及遭受损害的可能情况,决定相关原则适用上的优先性。这一思想可以被分解为这样几步:首先,依据基本法的“价值秩序”,判断所涉及的一种法益较其他法益是否有明显的价值优越性。如,相较于其他财产性法益,人的生命或人性尊严无疑有较高的位阶。其次,一方面考量应受保护的法益的重要性和实现程度;另一方面,假使某条原则或某种利益必须作出让步,那么考量其受损害的程度如何。最后,考量损害如何最小化,以贯彻衡量之际的比例原则——为保护某种较为优越的法价值须侵及一种法益时,不得逾越达此目的所必要的程度。这说明目的与手段间应有适切的关系。[7]P279,285,286
个案法益衡量思想导致了狭义比例原则的产生。狭义比例原则对作为最佳化命令之原则在法律上可能的范围内尽最大可能被实现的要求:在两个原则Pi与Pj发生冲突时,由于一个原则的适用是以消耗另一个原则为基础的,所以必须在它们之间划定一条合乎比例的分界线。对这条分界线的确定导出了“权衡法则”,它可以表述为:
一个原则的不满足程度或受损害程度越高,另一个原则被满足的重要性就越大。[1]136
换言之,必须比较Pi受侵害程度的高低与Pj重要性程度的高低,若Pi受侵害程度的越高,则Pj的重要性程度就应当越高。如果Pi受侵害程度已经提高,但是Pj的重要性并未因此得到提高,那么对Pi的限制就是缺乏正当理由的。如,“责任自负”原则(Pi)受侵害的程度越高,实现对于行人“人身安全”(Pj)保护的重要性就应当越高。假如侵害到达某个点(如发生交通事故时“机动车负全责”),行人的人身安全不仅没有更好地得到保护,反而更有失去生命的危险,③则不应对Pi做这样的限制。可见,权衡法则的功能在于在具体案件中证立对不同原则重要性程度或受侵害程度的判断,并从中得出其理性。这里存在这么一条有效的法则:权衡的理性取决于其权衡对象之与个案相关的分量及其关系的可能性。因为假如无法区分某个侵害的强度,那么权衡怀疑论者都提出的反对意见就是合理的。
2、度量化问题
侵害强度或重要性程度要进行度量化处理。受侵害程度的基本形式由三个阶层组成。这对应于阿列克西所称的三阶度量化。[8]P74这一三阶度量化所包含的受侵害程度是“轻、中、重”三种度量值,分别以l、m、s来表示。[9]P777[10]P136阿列克西以经验性/描述性以及规范性的理由来支持这一三阶层的实质度量化处理方法。[1]P151他从联邦宪法法院的两个判决,即烟草案判决(Tabak-Entscheidung)④与泰坦尼克判决(TITANIC-Entscheidung)⑤中推导出了这三个值。借鉴联邦宪法法院在这两个案件中的经验性考量与规范性考量,阿列克西试图寻得对相冲突之原则的侵害强度或重要性程度加以理性判断之可能的证明。[9]P776[10]P574f.实质度量化的另一个视角涉及对于在程度分级过程中确定的“值”的数学展示。但要注意的是,数值只是展示出了论据,却无法取代论据。麦考密克曾指出,论据不可能像实质对象那样具有分量。[12]P186话虽如此,但用数字来展示证立某个原则之呈指数式上升的受侵害程度的论据还是可能的。这里涉及的并非是法律的数学化,而是以有序和清晰的方式来描述相冲突之原则的相互关系。
但迄今为止依然没有解决的问题是:我们是应当用一种基数次序抑或序数次序、连续的/无限的抑或有限的/分散的、算数式的抑或几何式的序列来展示这些论据。这是权衡之参数化和度量化问题。这一问题涉及用以表达相冲突之原则之受侵害程度或满足之重要性程度的合适次序。这一应当,它可以是基数次序或者序数次序。基础次序的基础理念在于定义固定的评价层级,借助于此可以构造出一种优先次序。“当某个刻度的数字被归于某些‘值’(前者表达出了后者的次序或其分量)时,就出现了一种基数次序。人们可以想象,‘值’的次序可以通过一个刻度的数字,从0 到1,来表达。”[1]P139但这一次序并不容许参数化,因为它缺乏一种可以清晰适用的计量单位。[13]P83由此一种从固定量化概念出发的权衡参数化就是不可能的。相反,一种序数次序并不以任何固定的评价层级为前提。对它来说,重要的只是:优先性程度是可以确定的。“一种序数次序的要求没有(像基数次序)那么高。它只是要求在有待归类的‘值’之间确定更高价值(优先性)和同等价值(中立性)的关系。”[1]P139由于权衡的目标在于借助于粗糙的刻度来确定相冲突之原则之间的与个案相关之优先关系,所以这一关系只需通过序数次序来表达就可以了。对于序数次序而言又存在两种度量化的可能,即一种连续的/无限的度量化以及一种有限的/分散的度量化。无限的度量化容许作无穷的进一步细分。虽然这是可想象的,但一种拥有无限层级的度量化无法被运用于法律论证。与此相反,有限的或分散的刻度可以表达出法的有漏洞的结构(开放结构)。就像前面已经说明的,这一分散的刻度由三个程度构成,即轻、中、重。它可以展示出重力公式(见下文)之结构内部相冲突之原则的相互关系。此外,尚需澄清实质度量化的第三个视角,即待权衡之“值”的数学化展示如何进行。对此既可以进行算术式的序列,也可以进行几何式的序列。阿列克西认为应当拒绝算术式的序列,因为由此产生的相邻值之间总是恒定的距离无法把握相冲突之原则间指数式上升的受侵害程度。阿列克西更偏向于几何式的序列,因为在这种序列中,相邻值之间的距离是不断上升的。这就表达出了这样一个事实:当侵害强度不断上升时,原则将越来越具有力量,而这与边际效益递减率是相应的。[9]P785因此,数学序列和分散刻度由这样三个值构成:轻:2°,中:21,重:22。
由此可知,在权衡中待权衡之“值”的参数化和度量化遵循的是一种序数次序,它要借助于有限的或分散的刻度来实行,要借助于一种几何式序列来表达。它展示出了权衡之理性的核心,也构成了后文中对不同反对意见进行反驳的基础。
(二)重力公式
重力公式是将权衡法则展示为数学化的商公式。它构成了权衡的形式结构,从中可以推导出权衡程序的理性。这意味着,权衡的理性一方面基于重力公式,另一方面基于其“值”的理性之上。重力公式表达出了在三阶刻度中被置入的“值”的相互关系。从这一商运算中得出的结果构成了待决案件中呈现之情境之下的原则的具体分量,它可以被表述为Gi,j。重力公式可能仅涉及两个相冲突的原则(基本形式),也可能涉及两个以上相冲突的原则(扩展形式)。
1、基本形式
无论是在基本形式还是扩展形式中,都需要来确定相冲突之原则与个案相关的分量。从根本上说存在着三对变量,它们处于商公式的分子和分母之中,即受侵害程度、抽象重力以及经验性前提的确定性程度。[9]P787在两种形式中,重力公式的核心都在于确立受侵害程度Ii和受侵害程度Ij之间的比例(商)。所以我们首先要来考察重力公式的第一对变量。这是重力公式的核心关系,即原则Pi的受侵害程度Ii与相冲突之原则Pj之满足的重要性程度Ij之间的相互关系。它可以就被表示为:
这里的操作可以被分为三个步骤:第一步,确定Pi之不满足程度或受侵害程度;第二步,确定与Pj相冲突的原则Pi之满足的重要性程度;第三步,将第一步确立的受侵害程度与第二步确立的重要性程度相互比较,确定Pj的重要性程度是否足以证成对Pi之受侵害程度。首先,由于Pi的受侵害程度总是与具体情形C相关联的,用“IPiC”来表示受侵害程度,简写为“Ii”。其次,相冲突之 Pj的重要性程度同样与具体情形C中相联系,我们标识为“WPjC”。但Pj的“重要性程度”与“受侵害程度”之间事实上存在着可转换关系,因为权衡法则只涉及两个相冲突的原则,因此在具体情形C中,如果不实施侵害的Pi措施(即保护Pi)就相当于侵害了Pj,而Pj被侵害的程度也就相当于Pj的重要性程度。因此“WPjC”可转化为“IPjC”(简写为“Ij”),这样度量就等同了。再次,为了对两者进行量化比较,用前面所说的“三阶度量化”来表示“IPiC”与“IPjC”,即“轻”(l)、“中”(m)、“重”(s)三种度量值,⑥或用几何序列的值2°、21、22来代入。
重力公式中采纳的第二对变量是所谓的抽象重力。某个原则Pi的抽象重力是Pi相对于另一个原则的与任何情形的情境都无关的分量。[9]P778就这个变量而言存在着意见分歧,因为原则是否可能事先就拥有特定的、与个案相关之情境无关的分量,这是有争议的。⑦这似乎会带来这样的问题,即使得权衡去语境化,而导向一种普遍主义的判断。这又会带来这样的结果:权衡只表达出了法律体系中唯一正确的道德价值(尽管它通过权衡表现出来的)。如果从这样一种法律体系——它将某些价值预设为必要前提,如人的尊严——的角度出发,那么很清楚的是,这些原则的抽象重力要比其他原则更加重。⑧例如,我们可以此方式论证道,在一些法律体系中,生命权的抽象重力就要比其他权利(如一般行动自由)来得高。[9]P778而在另一些法律体系中,情形却有可能相反。抽象重力使得特定的政治考量可以来影响重力公式。但另一方面应当看到,相冲突之原则的抽象重力在权衡中发挥作用的场合是比较罕见的,因为相冲突之原则通常情形中具有相等的抽象重力。如果抽象重力相等,那么它们就彼此中和。相反,如果它们具有不同的分量,那么平衡就将被打破。[9]P777f.我们可以将原则Pi的抽象重力表示为“Gi”,而将相冲突之原则Pj的抽象重力表示为“Gj”。这两个变量的“值”同样要借助于三阶度量化来确定,即轻、中、重。据此,重力公式就将具有如下形式:
重力公式的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变量是这样一些前提的经验确定性或认知确定性⑨——这些前提是关于支持相冲突之原则的有待判断的措施的。经验性前提之确定性的相对化是Ii和Ij的基础,它们将通过所谓的“第二权衡法则”或者说“认知性权衡法则”得以实现。它可以被表述为:
对一个原则的侵害程度越大,这种侵害所需前提的确定性程度就必须越高。[9]P789⑩
第二权衡法则和第一权衡法则在重力公式中是并行的。重力公式的第三对变量是否仅限于作为相冲突之原则的基础性前提之受侵害关系的经验确定性,抑或也要将规范性考量包含进来,这是有争议的。本文的立场是,变量“S”不限于经验性前提的确定性,也必然涉及规范性前提。据此,变量“S”要被理解为认识论变量。变量S的可能值也要借助于三阶度量化来分殊。阿列克西认为,存在三个认识论度量,即“确定的”、“可成立的”、“非明显错误的”,并分别赋予“20、2-1、2-2”这样的递减式几何级数。这三个度量涵盖了从一种高层级的认知确定性一直到认知确定性非常低的层级。认知性前提的确定性在重力公式中通过第三对变量来展示。作为原则Pi之基础的认知性前提的确定性程度被命名为Si。另一方面,作为原则Pj之基础的认知性前提的确定性程度通过变量Sj来表达。因此重力公式之基本形式的完整表述就是:
在上述公式中,如果Gi,j>1,侵害就是不合比例的;如果Gi,j≤1,侵害就是合乎比例的。当然,权衡的理性不只是依赖于用“值”来表示被指陈的分量,且以重力公式的形式使之处于相对化关系之中。推论图式的理性在根本上也取决于这样一个问题:它是否与本身可以被证立的前提相联结。[14]P18这意味着,对权衡之理性问题的回答不仅要在权衡的形式结构中去寻找,也要在其实质论据中去寻找。有待权衡之前提是正确的,这一主张当然包含着一种正确性宣称。这必须通过商谈来证成。这说明要想否认权衡的理性,就必须同时否认理性商谈之可能。权衡只是一种论证形式,它的内部理性存在于重力公式和三阶度量化之中,而其前提的理性则取决于商谈,无论是法律商谈抑或是通过“特殊情形命题”相联系之普遍实践商谈。普遍实践商谈受到权威性裁判的限制,后者具有初显的优先性。[15]P403f.
2、 扩展形式
重力公式的扩展形式适用于两个以上的原则发生冲突的情形。将多个原则包含进重力公式的每一方同样意味着需要有更多的变量来表示所有其他原则的受侵害强度、它们的抽象重力以及它们的认知性前提的确定性程度。如果要顾及到所有相冲突之原则(不仅包括侵害其他原则的原则也包括受其他原则侵害的原则),那么重力公式的扩展形式就具有如下形式:
但以何种方式将这些变量归于这些原则依然是个有争议的问题。此外,对重力公式进行扩展时还有这样一项困难的任务,即如何来把握所有可能的侵害强度、抽象重力和认知性前提。“问题在于,这能否通过构造积累效应在重力公式中发生。最简单的版本或许是一种直接的叠加式积累。”[9]P791现在的问题是,在重力公式的结构中可以积累的是什么?按照阿列克西的观点:“积累性的原则不能存在实质上的交叠。它们有待最佳化的对象必须是实质上相异的。即存在这样一条规则:异质性是叠加式积累的条件。”[9]P792但这一条件在大多数情形中都不会出现,因为原则之间多少都存在交叠的情形。因此,为了能够把握住多于两个的原则之间的冲突,仅仅基于异质性对原则进行叠加式积累是不够的。由此,我们还需要其他论据来使得叠加式积累成为可能。此外,可能在某些情形中涉及同一基本权利主体的不同基本权利,或者相反,可能涉及不同基本权利主体的同一种基本权利。前一种情形要求对相对于同一归责主体之原则的侵害强度进行简单的叠加式积累,后一种情形确定同一个原则之受侵害分量的手段。侵害强度的叠加式积累只是在前一种情形中是可能的,而在后一种情形中则不是。但这并非论文的重点,在此不再赘述。
那么,权衡是一种理性的方法么?对此最主要的批评可以被归为两大类,一类批评指向的是权衡本身的非理性主义,另一类批评指向的则是权衡要素的不可通约性。接下去我们将分别对这两者予以回应。
三、权衡本身是非理性的?
非理性主义批评有三个变种,即狭义上的非理性主义、主观决断主义与修辞主义。其中狭义上的非理性主义批评构成了迄今为止对权衡最强烈的反对意见,也在其他反对意见的论证过程中扮演着基础性的角色。[14]P14
(一)狭义上的非理性主义
哈贝马斯在区分规范与价值的基础上,反对将权衡视为原则的理性适用过程。具体来说,他将原则理解为价值或者说伦理性规定。这些伦理性规定可以借由重要性尺度进行归类,它们构成了一种客观价值秩序,这种价值决定可以回溯到“利益权衡”中去。[4]P255, 309ff.原则作为价值意味着它们应当尽可能被满足。但不同的满足程度并不存在于规范-价值原则自身,而要到它们之外去寻找。这意味着,法益权衡(价值原则的权衡)显现出一种目的论的性质,即一种目标导向的权衡。所有这一切都导向了一种关涉个案的具体化价值实现。[4]P310所以,将法律原则重构为价值的结果是导向了对存在于外部的特定目标的获取。由此,作为价值原则的基本权规范丧失了它们的义务论性质,而获得了一种目的论性质。有效规范要无例外且平等地向其受众施加了一种行为义务,它就只能被理解为二值即“有效”与“无效”的效力语句。规范不能依据偏好被相对化,只能要么有效、要么无效。相反,价值以特定人群之价值的阶层化为前提,因此价值及其重要性程度取决于它们被认可的社会情境。价值确定的是一种优先关系,它说明特定利益要比其他利益更加吸引人;因此我们可以或多或少地赞成评价性语句。[4]P311如果说价值可以鉴于其目的论性质发生冲突(这一点在多元社会中是很常见的)的话,那么规范就不一样了,它们必须尽可能彼此处于一种融贯的关系之中。规范与价值之间的差异可以借由它们的适用方式来鉴别。在某个规范和某个价值那里,特定行为之正确性的确定方式是不同的。价值确定的是对于个体或个体所属群体而言好的事,而规范确定的是特定有效之法秩序内对于所有个体而言正确之事,后者与个体或个体所属的群体是否赞成规范无关。只有这一点才展现出了实在法的本质。所以,如果将基本权利重构为价值原则,就会剥夺其义务论性质。而一旦它丧失了义务论性质,它就也会丧失其拘束力。价值原则的适用只取决于法律适用者的主观价值尺度,确立相冲突之原则在具体案件中的优先性就必然是在一种非理性和主观的过程中被证立的。由于对此并没有理性标准,所以权衡要么是任意的,要么是依照惯常标准和优先次序未加反思地运用的。[4]P315ff.
可见,哈贝马斯反对将权衡的基础在于这一命题:法律原则与价值是同一回事。在此意义上证明,为确立个案优先性而进行的原则权衡中的评价具有主观性。但原则理论同样将原则视为规范的一种类型。作为规范,原则就具有义务论的性质。除非证明,将规范划分为规则和原则是不可能的,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证明原则只具有评价性。哈贝马斯其实是将法秩序理解为仅由规则组成,这意味着规范不能以不同的程度来实现。它们只能以涵摄的方式来适用。但这样一种体系观念并不是对法律体系的正确反映。当然,哈贝马斯的批评部分最核心的地方在于并不存在权衡的标准,即不可能理性地来确定原则的实现程度。对于这一反对意见,我们可以指出,原则是可以借助于前面提到的三阶度量化以不同的程度被实现的。从而有可能来比较原则的受侵害强度与实现的重要性程度。权衡的理性就在于理性证立某个原则的受侵害程度或者说重要性程度。就像阿列克西所说的,可证立性虽然并不等同于可证明性,但它蕴含着理性,从而蕴含着一种位于确定性和任意性之间的客观性。[14]P19因此,权衡的理性就在于其结构,也就是来自于权衡法则、重力公式(也包括碰撞法则)。
(二)主观决断主义
从狭义上的非理性主义批评可以导出主观决断主义的批评。其代表施林克同样认为,权衡或狭义上的比例原则是一种非理性的适用过程。他将权衡视为一种为基本权利施加限制之不必要的和危险的手段。权衡的危险性在于,它允许宪法法院依赖于高度的主观性,这使得自身的前见和利益在证立这些限制性理由之受侵害程度或重要性程度的过程中悄悄潜进来。狭义上比例原则的检验过程最终只能借助于检验者的主观性,权衡在方法上和教义学上没法令人满足地克服狭义上的比例原则,最终只能决断式地来操作。[16]P462[5]P460ff.此外,权衡也是不必要的,因为只要借助于适切性原则与必要性原则就足以对限制性手段和追求的目标之间的合比例检验予以实施了。因此,和比例原则只来自于达成被追求之目标的手段理性。为了证立这一命题,施林克运用了预测决定与价值决定之间的区分。预测决定指涉表达未来之现实的命题,这样一种预测命题在未来被证明为真或假。相反,价值决定涉及某个对象相对于其他对象的优先性。这种以价值为基础的决定既不可能为真,也不可能为假。预测决定与价值决定都可能被最佳化。通过对当下与过去所发生之事的经验性评价,人们可以对未来会发生什么作出可靠的预测。由于预测决定以对当下和过去的事实为基础,所以它具有客观性,而价值决定仅以赞成或拒绝为基础,所以它总是主观和任意的。在施林克看来,比例原则完全由预测决定组成,它们在具体案件中可以被证明。因而只有适切性和必要性这两个子原则才能被视为预测决定。权衡或者狭义上的比例原则具有评价的性质,所以必然是主观的。所以广义上的比例原则要限于适切性原则和必要性原则,因为这一原则既不需要评价,也不需要额外的权衡。如果并非如此,合比例性检验就将丧失其客观性。[5]P458总之,由于其高度的主观性以及之于基本权利适用的不相干性,权衡要从合比例性检验中排除出去。
对于施林克的观点,我们可以指出,适切性和必要性这两个子原则在疑难案件中并不足以来建立基本权利之间的优先关系。施林克的模式从根本上预设的是借助于规则来解决的案件。施林克认为在疑难案件中必须保障最低限度的基本权利地位。[17]P93基本权利最低限度之地位的确证在所有相冲突之基本权利那里都要被采纳,而不必动用权衡。施林克自然是想通过回溯到最低限度之地位的观念来避免权衡。他认为,要进行的不是权衡,即确定相冲突之原则中的哪一个在具体情境中具有优先性,而是确定相冲突之原则的绝对本质内涵,为的是随后回归到必要性检验。只有借助于必要性检验才能确定,在解决案件时何种绝对本质内涵能起关键作用。但殊值疑虑的是,基本权利之最低限度地位的确证是否可能脱离开权衡而获得成功。其实在施林克的模式中,权衡被转移到了必要性检验之中。[18]P100, 132这一认识与施林克的论证存在明显矛盾。如果在必要性检验中进行的是绝对本质内涵的比较,那么这一检验涉及的就不再是预测决定,而是关于相冲突之基本权利的绝对本质内涵的价值决定了。至于他所主张的权衡的非理性,我们照样可以用反驳哈贝马斯的论据来予以反驳,因为两者都认为权衡不存在客观标准,从而权衡必然是决断是的或者说任意的。但就像已经说过的,权衡的理性来自于它的结构。如果要否认这一点,施林克就必须证明,权衡的结构并不允许对于相冲突之原则的受侵害强度和重要性程度作出理性判断。遗憾的是他并没有这么做。
(三)修辞主义
修辞主义的批评内在地与狭义上的非理性主义的批评相关。修辞主义批评说的是,权衡是一个空洞的公式,它被法官用来证立任意的决断。相应地,权衡被认为只是一种辩护技术,它遮蔽了作为其基础的主观价值判断。作为一种修辞公式,它为使用它的“演说家”省却了论证的力气。[19]P382对原则(权利、法益)的称重、比较和最佳化建立在法官看来合理的论据之上,其中法官的主观评价扮演着重要角色。因此,整个权衡的结构及其所谓的理性不外乎是一种隐喻。[19]383权衡的修辞效果不仅在于遮掩有缺陷的证立,而且也使得司法机构变成了政治机构,其代价是立法权的丧失。法官原本应当接着制定法去思考,但通过权衡他却通常不再在政治考量之外去继续思考了。[20]P172权衡由此就变成了一种权力的手段,因为权衡与比例原则都无法在高度的政治水准上得到控制。最终法治国就转变成了权衡的国家。[21]P639总的来说,修辞主义批评将涵摄视为一种无法进行理性证立的“魔咒”,认为它对于法的安定性和民主法治国而言是个威胁。[22]P905
修辞主义的批评是空洞的,因为它批评的对象并不清晰。权衡的结构,即重力公式,本身并不是非理性的。这在对哈贝马斯所提出的反对意见进行反驳的过程中就已经证明了。权衡 并不是一种修辞公式,它是一种论证结构。这意味着它并非空洞的公式,而是一种形式结构。“比例原则为此提供了结构,即如何作出信息充分且无偏私的裁判行为。它是一种形式性的分析框架,引导法官如何去组织和评价相冲突的事实主张(它们关涉法官被要求去审查的法律)。”[23]P98
综上,权衡并非是非理性和多余的规范适用方法,它的理性来自于其结构。但权衡可能因为引入非理性的前提,而在其结构中导致非理性的结果。所以,非理性的问题更多是与论证的质量而非与权衡本身相关。
四、权衡的要素是不可通约的?
所谓“可通约性”,指的是两个或更多的对象之间鉴于共同标准的可比较性。据此,假如两个或更多对象之间缺乏这种共同的标准,那么它们就是不可通约的。[24]P278就像拉兹所指出的,假如A和B中既非其中一个比另一个要好,也非两者拥有同等价值,那么它们就是不可通约的。[25]P322在许多学者看来,权衡理论以有待权衡之原则之间的可通约性为前提,如果不解决这一前提性问题,那么诉诸于权衡法则和重力公式就将是不当结论。依照不可通约命题,相冲突之原则并不存在可比较性,因为不存在对原则之优先关系予以证立的共同标准。因而将不可通约之两个原则相互权衡必回然导致非理性的结果。下面我们来处理两种比较有代表性的不可通约性观点,即缺乏比较中项与特殊主义。
(一)缺乏比较中项
阿列尼科夫于1987年发表的名文《权衡时代的宪法》中对美国法院所运用的利益权衡方法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他在反对意见中并没有提及像狭义上的比例原则、适切性原则和必要性原则这些实际上是由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发展出的检验准则,但他反对意见的核心的确指向了不可通约性问题。在他看来,权衡在内部结构上的问题在于缺乏一个可以对彼此冲突之利益进行评断和比较的标准。当相冲突之利益可以彼此比较时,就像苹果与橙子可以相互比较时,就需要有第三方要素能以无可置疑的方式并依循清晰的规则来表达出苹果和橙子的“值”。这意味着,阿列尼科夫并不认为待权衡的利益本身是不可比较的,而是认为缺乏对相冲突之利益的“值”进行比较的共同标准。苹果和橙子可以被置于一架水果天平之上,或者被分配给每磅数美元的价格。真正的问题在于如何获得这架用以将它们的“值”转化为通用货币以便加以比较的天平。因为它必须来自于法官的个人偏好之外。[26]P972-973所以,阿列尼科夫其实并不反对将一个原则的受侵害强度与另一个原则被实现的重要性程度进行比较的可能,他所质疑的是存在一个比较中项。[27]P442缺乏比较中项带来的危害是法律适用者的个人利益会悄悄潜入权衡过程之中。此外,他还担心一种主观价值尺度会掏空判例制度,因为不存在清晰的标准,就无法为普通法院、立法、官员、律师和当事人提供行为方向的指引。[26]P973阿列尼科夫认为只有草构出另一个不受法官个人利益影响的价值尺度,才能解决这一问题。所以问题就在于,这样一种价值尺度大体面貌如何。美国最高法院的做法是诉诸于诸如历史、有效的社会成本或者某种利益的具体分量等标准。此外,也有可能鉴于相冲突之利益实现特定宪法或非宪法目的的能力,将某种价值归属于它们。但阿列尼科夫确认为这些东西并没能为值得希求的外部价值尺度提供决定性的标准。[26]P974-975这意味着,不能将任何这些标准算作是比较中项,它们无法完成在权衡过程中将某种价值归属于相冲突之原则的任务。最后,他总结认为,权衡就是某种黑匣子,在其中相冲突之利益的分量是依据直觉和隐蔽的方式来分配的。
综上,阿列尼科夫最主要的反对意见在于,不可能对某个原则(利益)的受侵害程度和相对立之原则的满足程度进行比较。所以智利学者乌尔比纳主张,不可通约命题反对的是对不同选项之特殊类型的评估,也即是典型的量化评估。[28]P582但是应当看到,阿列尼科夫在证立他的命题时肯定是抽象于利益冲突的具体框架(在其中冲突得以发生)之外了。当他说,如果不存在确定侵害强度的标准,就不可能对两种利益加以比较时,他说的并没有错。但很显然,这一确定每一相冲突之原则受侵害之“值”的标准或比较中项,不外乎是宪法本身。权衡涉及受侵害程度和重要性程度,对它们的比较不可能独立于冲突发生的语境,而总是要考虑到比较的框架,即宪法。最终宪法就成为比较所必需的标准。当然,人们会对什么是有效的宪法权利和宪法原则这一问题发生争执。在我看来是有效或值的保护的东西,与他人对于同一对象的判断并不必然一致。 而一旦放弃了共同观点,不可通约性就会马上成为现实。[29]P11因此,只有谈论的对象并非法律原则,也即是外在于宪法的利益时,阿列尼科夫的观点才是正确的。但是权衡将宪法视为借此来解决之利益冲突的比较中项。因而并不会出现阿列尼科夫所声称的不可通约性的危险。如果关于基于宪法之正确性的理性商谈是可能的,那么共同的观点也是可能的。取向于这一调整性理念——基于宪法的正确性——的商谈也将变成现实和理性。[27]P442实际上,其实阿列尼科夫反对的并不是比例原则,而是法官将权衡用于为自己主观和任意的裁判辩护做法。他的反对意见针对的并不是权衡的机构和理性,而是将它作为为非理性之裁判辩护的手段。所以,他的错误其实与哈贝马斯和施林克等人一样,在于将本不可能从其内部结构中推导出来的特征强加给了权衡。
(二)特殊主义
莫尔索对于权衡结构的批评可以分作三部分:对某种抽象位阶化的批评、对三阶度量化之客观性的质疑,以及对权衡特殊主义的反对。前两个部分涉及重力公式中之原则的不可通约性,而第三个部分则涉及作为权衡之基础的策略,即解决现在和未来之原则冲突的策略。这三方面的批评拥有一个共同的论点:不可能在具体个案中表述出理性的判断,以便也能适用于未来的情形。因为原则权衡时不存在客观标准,所以不可能为未来可适用之案件创设客观的权衡标准。第一部分批评涉及所谓权衡所必须的抽象阶层化。依照莫尔索的看法,权衡要求对基本权利排出抽象的优先性尺度。这样一种优先性尺度可以从这一点中推导出来,即对权利(如人的尊严、生命权或一般人格权)进行权衡是必要的。问题正在于对于比较这些权利而言某个尺度是不可能的,因为不存在理性的标准能够让我们推导出,比如生命权是否比人的尊严更加重要,或者身体健康是否比劳动自由具有优先性。因为原则的抽象重力独立于每一个具体的情境,所以必须事先就确定每一个基本原则的抽象重力。此外,也必须要有一种尺度,以使得对权利之抽象重力的确证和展示成为可能。[30]P414不存在这种客观优先性的尺度总是暗含着对有待权衡之原则的抽象重力的质疑,即对基本权利之抽象优先性尺度的质疑。存在这样一种尺度将意味着某些基本权利比其他基本权利拥有更大的抽象重力。其结果是,某些基本权利与其他基本权利相比属于更高位阶的范畴。从而权衡就只是一种确定某个基本权利是否属于更高位阶之范畴(鉴于具体案件的特殊情境可以超过某个位阶更低之范畴的基本权利)的手段而已。莫尔索的这种重构并不吻合权衡的本质。权衡以抽象优先关系之不可能为前提。权衡理论的确指涉抽象重力,它是一种既不考虑受侵害强度也不考虑满足之重要性程度的变量。抽象重力在重力公式中表达的是一种在论证所发生的特定政治框架内相冲突之原则的分量的变量。特定的政治框架在这里尤为重要。例如生命权的抽象重力在民主法治国家中就有可能有别于在神权国家之中。[31]P202将抽象重力引入重力公式之中的目的在于对待权衡之原则的相对关系加以补充。在大多数情形中,这一分量可以彼此抵消。假如如此,它们在权衡过程中就不发挥什么作用。所以,莫尔索反对抽象阶层化的意见是没有根据的,因为权衡本身总是以对相冲突之原则在具体案件中分量的确证为前提。而大多数时候两方原则具有同等重要性从而彼此中和,所以抽象重力并不发挥作用。
第二部分批评涉及权衡过程中客观性的缺失。当关于同一对象之相异判断彼此重叠时,客观性就出现了。其前提为存在借以作出理性判断的共同标准。在权衡过程中,这一标准就是三阶度量化。如果三阶度量化无法得到理性证立,那么就可以推知权衡是非理性的。在莫尔索看来,只有当三阶度量化显现出像在确定矿物质的莫斯硬度时采用的划痕测试法(借此根据其硬度对矿物质进行分类)的结构时,它才可能是理性的。矿物质的硬度允许我们来确定一种序数式的刻度标尺。但就对基本权利的侵害而言却不存在任何方法可以用来与“划痕测试法”相比。我们没有能力去清晰地确定,借助于何种特殊的特征将(对基本权利的)限制称为是轻的、中的或重的。[30]P415三阶度量化涉及相关原则的受侵害强度以及相冲突原则之被满足的重要性。这一三阶度量的值可以从具体的案件情境中推导出来。例如在泰坦尼克案中,“天生的杀人犯”这一表述对人格权的侵犯鉴于具体案件的情境被归类为轻的。但一个恰当的问题在于,这一论点如何得以证立。对这一问题的回答要在对权衡要素的实质论证中去寻找。实质论证不外乎是法律商谈。法律商谈本身基于三个基本条件之上:制定法、先例和法教义学(特殊情形命题)。[32]P375ff.对受侵害程度或满足之重要性的证立要根据实践论据来进行。这类论据通常位于法律商谈之外,而要回溯到普遍实践商谈中去。权衡之三阶度量化的理性就在于在普遍实践商谈中作出关于特定对象之理性判断的可能。谁想要否认三阶度量化以及权衡的理性,谁就必然要否认在普遍实践商谈中作出理性判断的可能。
莫尔索第三部分的批评涉及的不是权衡的结构,而是其用以解决原则冲突的策略。他区分了具有特殊主义性质的法律原则和具有普遍主义性质的道德原则,并提出了这样一个命题:权衡的方法论策略在解决原则冲突时必然蕴含着一种特殊主义策略。他将法律论证中的特殊主义理解为这样一种观点,它解决原则冲突的策略依赖于具体的案件情境。此外,他认为特殊主义方法的结果具有适用于未来案件的可能。与特殊主义观念相左的是普遍主义的观念,其在法律论证中以涵摄为代表。莫尔索将涵摄重构为一种解释过程,其中具体案件事实被涵摄于一个普遍情形的构成要件之下。恰恰是这一特征使得特殊主义的权衡模式有别于普遍主义的涵摄模式。但在莫尔索看来,这两种模式都是有缺陷的。此外还存在第三种可能,即具体主义的观念。这一模式试图在两个极端之间开辟一条中间道路。具体主义的观念容许将权衡理解为限于涵摄的一个步骤。此外,这种涵摄的构成要件存在于他所称的范式情形之中。范式情形来自于普遍的商谈情形,展示出的是这样的情境,其中能够澄清一个原则为何分量要重于另一个原则。[33]P40ff.这意味着,它们是一种“论题”,后者告诉我们,一个法律原则为何以及在何种情境中可以被另一个法律原则所“遏制”。根据具体主义的观念,权衡只能够作为先于涵摄发生的步骤。应当指出,莫尔索将权衡与特殊主义模式相挂钩的做法并不正确。在他看来,特殊主义的权衡策略只能提供适用于具体案件的办法,权衡的结果用以解决未来的案件。这一主张与权衡的结构和性质并不吻合。权衡由三个部分组成,即权衡法则、重力公式与论证负担。其中论证负担的起点是碰撞法则。碰撞法则以条件式优先关系为前提,它不仅适用于具体案件,而且也适用于未来的案件,只要相似的事实出现。这意味着,论证负担要求,如果法律适用者想要做出一个不同的判决,就必须对这一判决进行证立。所以我们不能主张说,权衡只适用于具体案件,而从中产生的条件式优先关系无法适用于未来的案件。因此,权衡并不对应于莫尔索所说的特殊主义模式。权衡在解决原则冲突时追求一种特殊主义的策略,并不意味着权衡不具有有别于道德特殊主义的属性。这样一种差异恰恰在于有利于早先作出之判决的论证负担。
至于所谓的具体主义解决办法,即将权衡视为涵摄之先在步骤的观点,则并无新意。每个权衡都以两个涵摄开始并以一个涵摄结束。[27]P434所以莫尔索说的是权衡理论已经说过的东西,他的反对意见也是多余的。莫尔索称为范式情形的,不外乎是作为基于权衡之条件式优先关系之基础的要素。莫尔索的命题只是证实了权衡理论之碰撞法则和论证负担已经说出的东西。因而,对权衡之特殊主义的反对意见也将落空。权衡涉及的是一种理性的过程,它追求特殊主义的策略,但它并非像莫尔索所主张的那种原本意义上的特殊主义(道德特殊主义)。具体主义的追求也被证明不过是一种冗余的提法,因为权衡已经包含了它的内容。
五、结语
只要法律原则作为司法裁判之依据的地位不受质疑,权衡就是不可避免的,也就构成法律推理的一种基本方法。这种方法的理性主要体现在其形式结构方面,即权衡法则及其基础上的重力公式之理性。无论是非理性主义的批评还是不可通约性的批评都没有根据,都建立在对作为理性论证形式之权衡的误读之上。因为权衡仅仅是一种论证形式,它既需要有内部证成的结构,在运用时也需要有外部证成的实质论据。权衡的内部证成形式就是重力公式,就像司法三段论或演绎是涵摄的内部证成形式一样。权衡之外部证成的任务则在于确定待权衡之原则的具体分量,这要通过个案中的法律商谈和普遍实践商谈来完成。它无法在一般方法的层面上得以辩护,也与作为方法之权衡本身无关。因此,权衡本身是一种理性的论证过程,只是在运用于个案时需要与具体的实质论据相结合。
注释:
①阿列克西曾将对原则理论的反对意见归纳为七组(参见[德]罗伯特·阿列克西:“理想应然:为法律原则理论辩护”,载氏著:《法:作为理性的制度化》,雷磊编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12年版,第178-179页)。除第一组“规范理论上的反对意见”外,同样适用于对权衡理论之反对意见的分类。
②例如参见陈景辉:《比例原则的普遍化与基本权利的性质》,《中国法学》2017年第5期。
③因为交通肇事逃逸普遍发生以及由于对死者的赔偿远少于对伤者的赔偿,因此对于肇事者而言,撞死受害者反而可能是最为有利的选择。
④BverfGE 95, 173.
⑤BverfGE 86, 1.
⑥还可以将三阶度量值进一步细化,区分为“轻轻”(ll)、“轻中”(lm)、“轻重”(ls)、“中轻”(ml)、“中中”(mm)、“中重”(ms)、“重轻”(sl)、“重中”(sm)、“重重”(ss),并分别用来对这九阶度量进行赋值。参见Robert Alexy, Die Konstruktion der Grundrechte, in: Laura Clérico und Jan-Reinard Sieckmann (Hrsg.), Grundrechte, Prinzipien und Argumentation, Nomos 2009, S.17.
⑦反对性意见参见Nils Jansen, Die Abwägung von Grundrechten, Der Staat 36 (1997), S.43ff.
⑧但也有人,如勒尔,就认为权衡视角下的“称重”迄今为止并没有成功地找到普遍的主体间标准,参见Klaus F. R?hl und Hans Christian Röhl, Allgemeine Rechtslehre, 3.Aufl., Köln 2008, §31 V.
⑨阿列克西一开始的表述是“经验性前提的确定性”,但后来将它修正为“认知性前提的确定性”。这一修正的结果是使得第三对变量不再限于经验性前提,而也将规范性前提包含了进来。最早作这一修正之处是阿列克西2002年关于《基本权利论》(英译本)的“后记”之中(Robert Alexy, Postscript, in his A Theory of Constitutional Rights, Julian Rivers tran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414-425.),但2003年发表的重要论文“重力公式”中却没有在符号使用上顾及经验性认知裁量和规范性认知裁量的区分,直到2014年的一篇回应性文章中他才明确进行了区分使用(Robert Alexy, Formal Principles: Some Replies to critic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nstitution 12 (2014), p.514.)。
⑩在此表述略有改变,将“基本权利”变为“原则”。
参考文献:
[1]Robert Alexy. Theorie der Grundrechte [M]. Frankfurt a. M.: Surkamp, 1986.
[2]Robert Alexy. Zum Begriff des Rechtsprinzips [A]. Werner Krawitz, Kazimierz Opa?ek, Aleksander Peczenik, Alfred Schramm. Argumentation und Hermeneutik in der Jurisprudenz [C]. Berlin: Duncker & Humblot, 1979.
[3]Robert Alexy. On the Structure of Legal Principles [J]. Ratio Juris, 2000, 13.
[4]Jürgen Harbemas. Faktizit?t und Geltung [M]. Frankfurt a. M.: Surkamp, 1994.
[5]Bernhard Schlink. Der Grundsatz der Verh?ltnism??igkeit [A]. Peter Badura, Horst Dreier. Festschrift 50 Jahre Bundesverfassungsgericht, Bd.2[C]. Tübingen: Mohr Siebeck, 2001.
[6]Jan-Reinard Sieckmann. Probleme der Prinzipientheorie der Grundrechts [A]. Laura Clérico, Jan-Reinard Sieckmann. Grundrechte, Prinzipien und Argumentation [C]. Baden-Baden: Nomos, 2009.
[7][德]卡尔·拉伦茨. 法学方法论[M]. 陈爱娥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8]Robert Alexy. Die Abw?gung in der Rechtsanwendung [J]. Jahresbericht des Institutes für Rechtswissenschaften an der Meiji Gakuin Universit?t, 2001, 17.
[9]Robert Alexy. Die Gewichtsformel [A]. Joachim Jickli, Peter Kreutz, Dieter Reuter. Ged?chtnisschrift für Jürgen Sonnenschein [C]. Berlin: De Guyter, 2003.
[10]Robert Alexy. Constitutional Rights, Balancing and Rationality [J]. Ratio Juris, 2003,16.
[11]Robert Alexy. Balancing, constitutional review and representation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nstitution, 2005, 3.
[12]Neil MacCormick. Rhetoric and the Rule of Law [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13]Martin Borowski. Grundrechte als Prinzipien [M]. 2.Aufl. Baden-Baden: Nomos, 2007.
[14]Robert Alexy. Die Konstruktion der Grundrechte [A]. Laura Clérico, Jan-Reinard Sieckmann. Grundrechte, Prinzipien und Argumentation [C]. Baden-Baden:Nomos, 2009.
[15]Robert Alexy. Die Doppelnatur des Rechts [J]. Der Staat, 2011, 50.
[16]Bernahrd Schlink. Freiheit durch Eingriffsabwehr-Rekonstruktion der klassischen Grundrechtsfunktion [J]. Europäische Grundrechte-Zeitschrift, 1984, 1.
[17]Bernahrd Schlink. Abwägung im Verfassungsrecht [M]. Berlin: Duncker & Humblot, 1976.
[18]Virgilio Afonso Da Silva. Grundrechte und gesetzgeberische Spielräume [M]. Baden-Baden: Nomos, 2003.
[19]Wolfgang Gast. Juristische Rhetorik [M]. 4.Aufl. Heidelberg: Müller, 2006.
[20]Walter Leisner. Der Abwägungsstaat [M]. Berlin: Duncker & Humblot, 1997.
[21]Walter Leisner. Abwägung überall - Gefahr für den Rechtsstaat [J]. Neue Juristische Wochenschrift, 1997, 10.
[22]Fritz Ossenbühl. Abwägung im Verfassungsrecht [J]. DVBL, 1995, 1.
[23]David Beatty. The Ultimate Rule of Law [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24]Virgilio Afondo Da Silva. Comparing the Incommensurable: Constitutional Principles, Balancing and Rational Decision [J]. Oxford Journal of Legal Studies, 2011, 31.
[25]Joseph Raz. The Morality of Freedom [M].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86.
[26]Alexander Aleinikoff. Constitutional Law in the Age of Balancing [J]. Yale Law Journal, 1987, 96.
[27]Robert Alexy. On Balancing and Subsumption. A Structural Comparison [J]. Ratio Juris, 2003, 16.
[28]Francisco Urbina. Incommensurability and Balancing [J]. Oxford Journal of Legal Studies, 2015, 35.
[29]Robert Alexy. The Reasonableness in Law [A]. Giogio Bongiovanni, Giovanni Sartor, Vhira Valentini. The Reasonableness and law [C]. Dordrecht: Springer, 2009.
[30]José Juan Moreso. Alexy und Arithmetik der Abw?gung [J]. ARSP, 2012, 98.
[31]Carlos Bernal Pulido. The Rationality of Balancing [J]. ARSP, 1996, 92.
[32]Robert Alexy. The Special Case Thesis [J]. Ratio Juris, 1999, 12.
[33]José Juan Moreso. Ways of Solving Conflicts of Constitutional Rights: Proportionalism and Specificationism [J]. Ratio Juris, 2012, 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