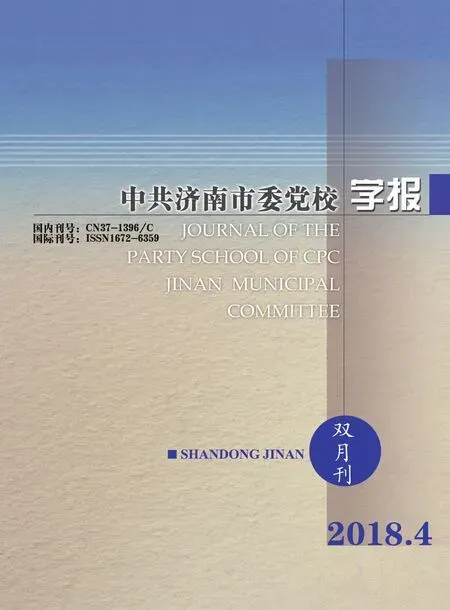道咸间词人对“词史”特质的自发建构
段小敏
清词到了道光、咸丰统治时期又一次印合了乾隆诗人赵翼“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的这两句诗语,涌现出一批堪为清词发展到晚末之际略添神采的“词史”之作。[1]这些词作为后人研究清史提供了可资“论世”的史料,另一方面,就词学批评来说,此类词作的出现正是道咸词人对“词史”特质的自发构建。
一、道咸“词史”之作的内涵
“诗史”是中国古代文学批评领域的一个专有名词,第一次把“诗史”当作一个诗学概念来使用的是晚唐的孟棨。宋人诗话中普遍出现“诗史”,并把其创立为一种崇高的诗学理念,敬献给诗人杜甫。沿着“诗史”的批评思维,在词学批评领域也出现了“词史”批评概念。清初的陈维崧首次明确将“词史”概念放在与“诗史”相同的地位。道咸“词史”即是道咸年间写出了一批具有“词史”内涵的词人词作。在《清代“词史”概念的演变与辨析》一文中,作者提出对“词史”作品的认定要符合“时代”、“时事”、“时情”三个观点。时代是指词作者需经逢乱世或遭受世变,而且置身其中;时事指词作能够反映当时时事,并有一定的政治批判色彩;时情,指词作中寄寓忧国忧民的感慨。[2]“词”之所以具有“史”的特质,是因为“词史”之作表现了重大的社会变迁,反映了在重大变动面前,社会各阶层人民情绪的波动。“词史”之作应该是一批立足于广阔时代背景,词中隐含时事并寄寓词作者一定感慨的作品。
道光以后,清朝的政权统治愈加腐败,阶级矛盾、民族矛盾频发并且日益尖锐,严峻的形势迫使文人们不得不把目光更多的投放在国家大事上,这个时期词的创作也因此出现了新的面貌,一批具有“词史”特质的作品接连问世。清代道光(1821-1850)、咸丰(1851-1861)统治时期,发生了中英鸦片战争、金田起义、太平天国运动,清王朝面临着兵连祸结的局面。而道咸时期短短40年间的社会动荡和时代危机感与安史之乱、宋元、明清易代相比,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一时期不论是以“民族英雄”名世的方面大臣邓廷桢,林则徐,还是“仕途失意”的底层文人蒋春霖、周闲等人,皆成为了这场历史浩劫的见证者。面对社会矛盾集中爆发,内外交困的局面,道咸间这些词人就结合当时的社会背景,借用词体的形式表达自己忧国忧民的心情及个人身世的流离之感。这一类作品在广阔的时代背景之下对时事真实反映,对时情真实表达,无愧于“词史”之作。
二、道咸年间词人对时事的真实反映
道咸时期的一批词人以自觉的史鉴意识承担起了传达历史、承载历史的文学使命,自发的创作出一批客观真实的再现当时社会氛围,呈现道咸时期知识分子精神面貌和心理状态变化的作品。道咸年间发生的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使身处其中的词人尤感危机深重,如贵为朝廷大臣的邓、林二人,他们在词中寄寓了自己的忧患意识,对道咸年间的时事作出真实的反映。
(一)道咸大臣词
邓廷桢,字维周,号嶰筠。江苏江宁县人士。道光时官至两广总督,鸦片战争爆发后曾与英军交战六次。邓廷桢工于词作,著有《双砚斋词》和《词话》。林则徐,字元抚,号石麟,又别号少穆。福建侯官人士,著有《云左山房词》,道光时两次身居总督高位。他在广州领导了历史上有名的“虎门销烟”运动,在中国近代史上以民族英雄身份而为后人所熟知。林则徐与邓廷桢两人关于时事唱和的词作收录在《邓林唱和集》中。邓廷桢感于鸦片之祸作了《高阳台》,来表达他的忧愤之情。词一开头就以“鸦渡冥冥,花飞片片,春城何处轻烟?膏腻铜盘,枉猜绣榻闲眠。”两句点出鸦片之祸甚深。全词语言简练、直接,斩钉截铁,表露了邓廷桢作为大臣忧心国事的情怀。林则徐作《高阳台·和懈筠前辈韵》以和。词起首以“玉粟收余,金丝种后,蕃航别有蛮烟。双管横陈,何人对拥无眠。”对应邓词点出鸦片之祸。
道光十九年九月四日,英军和清军在九龙半岛附近海域发生了一场海战,史称“九龙之战”。其后旧历中秋节当天,邓廷桢、林则徐和水师提督关天培由虎门搭船到沙角阅兵,当晚三人一起登沙角炮台望月。几日之后邓廷桢就作了这首名为《月华清.中秋月夜,偕少穆、滋圃登沙角炮台绝顶晾楼,西风泠然,玉轮涌上,海天一色,极其大观,辄成此解》的词作赠给林则徐。词开头以“岛列千螺,舟横万鹢,碧天朗照无际。不到珠瀛,那识玉盘如此。”两句描绘了虎门海口中秋夜景的壮丽,以“秋霁,记三人对影,不曾千里”做结。邓廷桢在词中联想到虎门所面临的紧张军事形势,用“元规啸咏”的典故以“庾亮”自比,展现了他保卫祖国山河的气概和理想。林则徐则作了《月华清·和邓蠕筠尚书沙角眺月原韵》回赠邓廷桢。林词以“穴底龙眠,沙头鸥静,镜奁开出云际。万里晴同,独喜素娥来此。”写激战过后的沙角海面十分平静,词人此刻的心情想必也宽慰了许多。词中“问烟楼、撞破何时,怪灯影、照他无睡。宵霁。念高寒玉宇,在长安里。”几句则写词人想到国家还有鸦片之祸尚待扫除,自己只能寄希望于朝廷能用治世之才来打破僵局,还生民健康的体魄和精神。
邓廷桢和林则徐同为清朝的方面大臣,目睹了国民遭受鸦片的祸害,痛心疾首。他们忧心家国大事,以国家安危为己任,时时表现出心怀天下生民的胸襟和气度。他们抓住词这种具有特殊美感的文体,抒发了自己忧国忧民的情怀。邓林二人的创作自发构建了道咸年间的“词史”特质,他们的词作以鸦片战争为时代背景,抒发了作为方面大臣的忧患意识。
(二)周闲的军旅词
道光二十年在浙江定海发生的两次血战,是鸦片战争烽火在东南沿海的进一步蔓延,也承载了广大将士誓死抵抗帝国主义侵略的光辉事迹。张宏生的《清代词学的建构》一书提到了“鸦片战争前后的爱国词”,认为《鸦片战争文学集》中欠缺对有关词作的收集和整理。除却对词体本身的偏见外,鸦片战争时期的文人对此时期时事的表现较少采用词的方式,相关词作少,不成气候。另一方面,在这一时期很少有词人像邓、林二人写出具有大的时事背景别有风格的词作。周闲的《范湖草堂词》就是表现浙江定海两次血战少有的军旅题材作品,足见其弥足珍贵。
周闲,字小圆,号存伯,别号范湖居士,浙江秀水人士。所著诗词文大多已毁于战乱,今仅存诗文各1卷,词3卷。他存世的《范湖草堂遗稿》多有表现军旅生活的作品,对当时军人的日常生活做了刻画和揭露。周闲诗古文词书法丹青皆有造诣,所存词3卷,就是他于役浙东时期的作品。
清道光二十年农历六月和次年农历八月在浙江定海英国远征军和清军发生了两次血战,周闲在他的词中都有记述。他于役浙东前线时年21岁左右,他的《月华清·军中对月》开篇云:“毡幕天晴,牙旗风静,枕江营垒初暮。”这一句用“毡幕”、“牙旗”、“营垒”三个军中特有的景象生动的勾勒出词人所处的环境。周闲又用“悄不闻夜鹊,更无芳树”来描绘军中的肃杀凄清,词人当时对月的心境可想而知。身处于兵荒马乱的军营之中,周闲没有寻常时刻赏月的兴致,只能联想到“网遍帘尘”的景象。周闲的这首《月华清·军中对月》,反映了词人在军中感受到的荒凉氛围和他军中对月的悲慨心绪。词人表现海陆军事活动的《水龙吟·渡海》,词云“海门不限萍踪,危樯直驰东南去。”词人面对“浪叠千山”的大海,不由得心境壮阔起来,油然生出保卫国家海域的热切愿望。词人同时也感到迷惘和忧心,词中“茫茫绪”、“遥指虚无征路”又表现了他惶惶不安的思绪。
周闲词中记录了他在前线的生活,展现了战前生活的实景图。《忆少年·夜抵上虞驿》开篇用“今宵尘骑,今宵风露,今宵山驿”三个“今”字点明此次夜里的军事行动十分紧迫。寒夜行军,自是顾不得霜寒露重,因此“笼鞭趁塘路,照朦胧月色。百里郊原霜气逼,送行人、鬼磷吹碧。”词写出了兵士在寒冷的深秋月夜行军的孤寂冷清。而《征部乐》描写的则是军中生活的另外一种景象,充满词人昂扬的斗志。“笑七尺、换得征衣,会办今年杀诸贼。”词人展现了军士渴望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和精神饱满的士气状态。
周闲于丹青上也颇有造诣,读他的词读者可以凭借想象勾勒出一幅幅战时的真实场景。如《沁园春·大宝山朱将军桂祠堂》“记衔杯虎帐,横腰剑绿,谈兵马矟,拂面旗红”以色彩之间的对撞描摹沙场上那一幕幕震撼人心的场景。这首词的基调是悲慨的,周闲以战场生还者的身份凭吊战亡的故友。曾几何时,他们“樽俎曾同”,也“誓共扫东南海上烽”,那时他们未曾想到天人永隔。如今故友亡去,战事又“旗鼓难逢”,词人心中感慨万千、五味杂陈。
周闲作为一名在军中实际生活过的词人,在词中真实记录自己的前线生活,为我们展现了一幅幅生动的军中实景图,为我们全面了解当时东南海战提供了重要的文字资料。他的词作,同样是道咸“词史”特质得以自发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道咸年间词人对时情的真切表达
蒋春霖身为传统文人,无法置身于社会动荡之外,加之他作为词人敏感、细腻的情感,使这种“词史”特质的文学性书写也就更加真切感人。和邓廷桢、林则徐、周闲一样,经历过道咸时期巨大历史浩劫的蒋春霖也自发地拿起词笔来书写“词史”。词人面对国家遭受罹难所抒发的感情,是文人责任感和使命感的真切表达。
(一)有“词史”之誉的蒋词
蒋春霖,字鹿潭,江苏江阴人士。著有《水云楼词》2卷,补遗1卷,一生穷愁落魄,抑郁不得志。他善于抒发怀抱,加之遇上伤离悼乱的世道,因而感慨深重。蒋春霖是道咸时期成就颇为杰出的一位词人,清徐珂在《近代词话》中对常州派的后七家做了评价,对蒋春霖尤为推崇。“七家中莲生、海秋、鹿潭之作,大都幽艳哀断,而鹿潭婉约深至,流别甚正,家数颇大,人推为倚声老杜”。[3]词论家已经发现蒋词中的“词史”特质,并且给予了高度肯定。吴梅认为:“洪、杨之乱,民苦锋镝,《水云》一卷,颇多伤乱之语,以南宋之规模,写江东之兵革,平生自负,接步风骚,论其所造,直得石帚之神理。”[4]蒋词写出了道咸间太平天国运动下的人民和传统文人的心绪变化,这在道咸间的词坛上,十分难得。
蒋春霖对道咸间“词史”特质的书写,立足于道咸年间的时代背景,又有他作为文人群体中的一员面对社会动乱所流露出的无限感慨。清咸丰三年三月太平军占领了金陵城,洪秀全改金陵名为“天京”,将其定为太平天国的京都。蒋春霖的《台城路·金丽生自金陵围城出,为述沙洲避雨光景,感成此解。时画角咽秋,灯焰惨绿,如有鬼声在纸上也》就是以当时称为金陵的南京被攻克的事件为背景,于次年秋写成的。“惊飞燕子魂无定,荒洲坠如残叶”刻画了金陵城中的危机感和紧张的氛围。词虽然以金陵城陷这一事件为背景,但是全词无一字是具体叙事,词人重点表现的是金陵被围城内人心惶惶、不知所措的局面。蒋春霖通过一系列感觉的描述传达出金陵城内的讯息,在词的结尾以“险梦愁题,杜鹃枝上血”来言说他心中无尽的感慨。蒋春霖还作有《木兰花慢·甲寅四月,客有自金陵来者,感赋阕》一词来抒发他的感慨。咸丰四年(即洪秀全定鼎天京金陵的第2年),蒋春霖从金陵来客的口中得知一些城内的光景,于当年4月写成此词。“破惊涛一叶,看千里、阵图开。正铁锁横江,长旗树垒,半壁尘埃。”开篇写“阵图”、“铁索”交待当时形势紧张,江上和岸边都军阵森严。文人们往日流连的秦淮院宇,也早没有了昔日的喧嚣,只有“几星磷火”还在或明或暗地闪着,让人惊疑那还是往日楼阁上的灯火。“安排多少清才。弓挂树,字《磨崖》。”可以看出战乱对文人的冲击较大,文人们只有“谁倚莫愁艇子,一川烟雨徘徊”来消解自己内心的苦闷。
蒋春霖的《水云楼词》在动乱时代的背景下抒发了词人切身的生活感受。蒋春霖词中的大量篇章,真实形象地展现了鸦片战争与太平天国运动期间的历史画卷,多维度、多层次地刻画出特定环境中的传统文人的忧世心态,更加突显出传统文人在时代波动下的形象,具有十分丰富的认识价值。蒋词写作及表达上的特点,正契合了“词史”的内涵。他在经历社会动荡后自发写出的这些作品,使道咸年间“词史”特质得以进一步建构。
(二)道咸年间其他词人的“词史”之作
与蒋春霖交好并彼此唱和的词人里也有写出道咸时期特有的时代氛围的“词史”之作,如杜文澜。他字小舫,浙江嘉兴人士。他曾参与咸丰兵事,写出不少抒发自己内心感慨的词作。《己未除夕》写于咸丰九年的除夕之夜,此时正是清军与太平军作战形势较为紧张的时期,杜文澜时任通州分司。词开篇“凄凉断角,吹残戌,匆匆复送今夕。”以“断角”、“残戌”烘托出苍凉之感,词人的内心沉重凄凉。结尾两句“猛听荒鸡,定惊起、江湖倦客。念家山,铁甲未解泪满臆。”词人流露出对鞍马劳顿生活的倦怠之感和渴望有朝一日能够解甲归田的向往之情。《八声甘州·淮阴晚渡》词云“问堤边瘦柳,春风底事,减却流莺?十里愁芜凄碧,旗影淡孤城。”连年的战乱已经让词人心生厌倦,在词中他以一句“空剩平桥戍角,共归潮暗咽,似恨言兵”直白的表达了自己心中厌战的情绪。结句“还飘泊,任王孙老,匣剑哀鸣。”战乱以来词人漂泊、孤寂的境遇不由得“匣剑哀鸣”。
与《水云楼词》相比,差强人意的还有薛时雨的《藤香馆词》。薛时雨,字慰农,一字澍生,安徽全椒人士,著有《藤香馆词》,他的词反映了战后荒凉破败的景象和清朝被殖民化的惨痛事实。他的词《多丽》写道“更惨绝、千堆白骨,滞魄永难醒。空携得、一樽浊酒,浇上孤亭。”词中抒写的是一片凄怆的情景,从萧索的景象描写中可以感受到词人内心对眼前“千堆白骨”的悲慨之情,他留下的是“一行泪雨”,更是万般怜惜、无限心酸。《望海潮·舟泊黄浦》写词人荡舟在气势磅礴的黄浦江上,他眼中的黄浦江如“巨壑腾蛟”一般瑰丽壮观。但是,气势如虹的黄浦江未能抚慰他“念苍茫身世”的忧思,外国侵略者的狂妄,本朝统治者只求苟安的情形,词人以一句“算汉家长策,只是和戎”表达了他的愤懑和无奈。面对“水驿驰轮,楼船激箭,海门百道能通”的局面,词人只能以浊酒自慰“聊把黄金买醉,歌舞向西风”。
邓廷桢、林则徐作为朝廷大臣,他们的词作格局和周闲、蒋春霖、薛时雨等人相比要壮阔许多。不管是对时事的直面抒写,还是以曲笔传之,道咸间的这些词人都在一定程度上以倚声之道反映了时代的陵替轨迹,从而构成了一条“词史”之路。
四、道咸间词人对“词史”特质的自发构建
道咸间词人对“词史”特质的文学性书写,是作为文人自身责任感和使命感的展现。邓廷桢、林则徐、周闲、蒋春霖、薛时雨等一批词人借助词体抒发家国忧患的感情,他们的创作行为受到时事的巨大影响。对于道咸间的“词史”特质构建来说,这一批词人的创作实践直接促成了其形成。道咸词人对“词史”特质的构建是自发的,家国感情自然抒发的结果。自身没有意识到他们这种巨大时事刺激下的词创作行为会对构建一种词学批评理念产生影响。
就文学方面来说,具有“词史”特质作品的出现,不仅完善和增加了词的功能,同时兼具有“词”和“史”的美感。“词史”类作品承继了词体“极命风谣里巷男女哀乐,以道贤人君子幽约怨悱不能自言之情”的婉约之风,[5]具有史书注重记录功能的特点。“词史”的出现一方面对于促进清代词学的研究大有裨益,另一方面,也可以完善清代词学批评体系。从社会学角度来看,一部文学史实际上是一部文人心态史。道咸“词史”可以说是一部道咸词人的社会史和心态史。道咸间一批词人对“词史”特质的自发构建直接促成了道光、咸丰两朝“社会生活史”和“社会心态史”的完整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