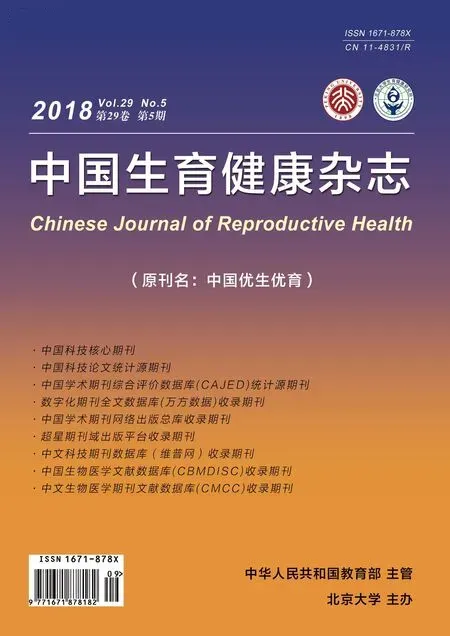卵巢癌形成、诊断及治疗的研究进展
周琳 何秀萍
卵巢癌是女性生殖系统最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发病率仅次于宫颈癌和子宫内膜癌[1],但是其死亡率最高[2],因为早期卵巢癌的临床症状并不明显,待确定诊断时已是晚期。近年来随着紫杉醇联合铂类化疗、腹膜内化疗和降低风险的手术,上皮性卵巢癌的疗效获得了改善,但由于化疗耐药性的产生,总体五年生存率未见明显提升[3]。研究发现家族史和遗传因素是卵巢癌致病的重要高危因素,近年来发现的卵巢癌易感基因包括BRCA1(breast-ovarian cancergene1)、BRCA2(breast-ovarian cancergene2)、Lynch、RAD51C、RAD51D、BARD1(BRCA1-associated RING domain protein 1)、MDM(murine double minute)家族等[4],目前该领域的重点是探讨癌症形成和发展的机制,为卵巢癌的早期诊断提供依据,解决化疗耐药性并开发新的治疗方法。
一、卵巢癌的类型
近几年对于卵巢癌来源的研究倾向于卵巢表面上皮来源,具有形态学变异性,目前认为有五种不同的“组织型”:高级浆液(high grade serous carcinoma,HGSC),透明细胞(clear cell carcinoma,CCC),子宫内膜样(endometrioid carcinoma,EC),低度浆液性(low grade serous carcinoma,LGSC)和粘液性癌(mucinous carcinoma,MC)。研究认为卵巢癌主要分为两个亚型:I型和II型[5]。I型卵巢上皮性癌包括低级别浆液性癌、低级别子宫内膜样癌、粘液性癌、透明细胞癌及移行细胞癌,其发生往往经过“良性-交界性-低度恶性癌”这种肿瘤发生模式,临床上生长缓慢,多局限于一侧卵巢,预后好。例如,低度浆液性肿瘤产生于KRAS(kirsten rat sarcoma viral oncogene)和BRAF9(B-Raf proto-oncogene9)等途径中积累突变的良性浆液性囊腺瘤或Müllerian囊肿[6]。另一方面,II型卵巢上皮性癌包括高级别浆液性癌、高级别子宫内膜样癌、未分化癌和癌肉瘤,与I型卵巢癌不同,其侵袭性高,进展迅速,发现时往往已有盆腹腔的广泛扩散,其分化差,并且在卵巢内一般见不到早期病变[7]。
二、卵巢癌的形成和转移的机制
1.卵巢癌的突变
癌症基因组图谱研究了316个原发性浆液性癌标本,发现所有标本中检测到TP53突变,在20%中检测到BRCA1和BRCA2突变(体细胞和生殖细胞)[8]。大多数肿瘤的特征是全基因组不稳定性,DNA测序技术的最新进展已经在卵巢癌中鉴定出另外的突变,包括BARD1,BRIP1,CHEK2,NBN,PALB2,RAD50家族、MDM家族和NF1[4]。由于这些基因参与DNA修复,患有卵巢癌的女性以及其家族成员患有其他癌症的风险较大。诊断为HGSC卵巢癌患者20%的可能性具有遗传性BRCA1或BRCA2突变,而具有EC或CCC的患者与子宫内膜癌或结直肠癌的患者有相似的罹患Lynch综合征的风险[9]。
2.卵巢癌的转移机制
卵巢癌极易发生转移,常见转移到大网膜。转移途径包括(1)血液途径[10]:Sood等人研究,选15对并连体小鼠模型,腹膜内注射肿瘤细胞到“宿主”小鼠,发现一半的联合“客体”小鼠有网膜或肠系膜转移。当癌细胞注射到宿主卵巢或脉管系统中时,肿瘤细胞也到达客体小鼠,进一步发现转移细胞上调表皮生长因子受体家族基因,特别是ErbB3(epidermal growth factor receptor3)的表达,并且靶向ErbB3与小干扰RNA的表达显著抑制肿瘤大网膜转移[11]。近年来对于血管内皮生长因子的研究从未停息,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EGFvascular and endothelial growth factor)为特异的内皮细胞有丝分裂素,通过其特异性受体(VEGFRvascular and endothelial growth factor recepter)介导,在卵巢癌的发生、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最终导致恶性腹水的产生。卵巢癌发生、转移机制分子水平的测定,为卵巢癌的诊断、靶向治疗和预后提供依据[12]。(2)种植途径:卵巢癌细胞通过脱落到腹腔,然后附着于附近的组织(例如网膜)而转移[10]。Lengyel等人研究显示网膜脂肪细胞通过上调脂肪酸结合蛋白4(fatty acid-binding protein4,FABP4)的表达促进转移到大网膜,FABP4在脂肪细胞-癌细胞界面处表达显著,缺乏FABP4的小鼠的肿瘤转移显著低于FABP4正常的小鼠[13]。不同类型卵巢癌中,转移路线有所不同,肿瘤的侵袭和转移是一个复杂的病理生理过程,不仅涉及肿瘤细胞之间、肿瘤细胞与宿主细胞之间的相互作用,而且还涉及许多生物活性分子之间相互调控机制。近几年研究发现多种分子机制参与卵巢癌的转移过程,例如:物理学流动学说,机制金属蛋白酶(matrix metalloproteinase,MMP)家族,白细胞介素,血管生成素,骨膜蛋白(periostin,PN),E-钙黏素(E-cadherin,E-cad)等。总之,关于卵巢癌的转移机制目前国内外尚未达成理论的统一,这也说明了转移机制仍是需要进一步研究和探索,而这一问题的解决必将为攻克卵巢癌这一难题提供强有力的理论支持,为广大卵巢癌患者带去福音[10]。
3.肿瘤细胞和微环境
突变不仅取决于肿瘤本身,也可能取决于肿瘤微环境包括:细胞内基质、细胞外基质、间皮细胞、成纤维细胞、内皮细胞、血液和淋巴管、神经、免疫细胞和脂肪细胞的混合物。细胞突变取决于肿瘤微环境的两个标志:基质侵入、转移和血管发生。为证明基质有助于肿瘤转移,许多研究者正在开发体外方法来研究肿瘤细胞的相互作用,并通过靶向肿瘤和/或微环境相互作用来确定抑制转移的策略。这些方法包括三维基质、癌细胞球体和共培养的间皮细胞(网膜的第一层)与癌细胞[14]。在球状体的研究中,Davidowitz等人发现上调上皮间质转化的转录因子,能更好地清除间皮细胞,而不上调间皮细胞表达[15]。对于血管生成,Sood等使用异种移植方法来模拟当患者停止服用抗血管生成药物(如贝伐单抗或帕唑帕尼)时发生的情况,他们发现具有丰富血液循环的小鼠的肿瘤重量较大,肿瘤增殖标志物增多,肿瘤细胞凋亡水平下降。[16]因此,对于肿瘤微环境的研究能更好地了解卵巢癌的发生和转移。
三、卵巢癌的诊断和预防
临床上卵巢癌的诊断主要通过妇科盆腔检查,血清CA125、人附睾蛋白4(HE4)等标志物检测,超声、CT、MRI等影像学检查,以及这些检测手段的联合应用,但这些检测手段在卵巢癌的早期诊断及病情监测中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因此,卵巢癌的早期诊断和预防需要不断探究。
1.早期卵巢癌的筛查
卵巢癌患者早期检测无有效的筛选试验,虽然已经开发了一些方法来检测早期卵巢癌,但是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U.S.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FDA)最近发布了一项声明,建议不要在普通人群中使用作为筛选卵巢癌的工具[17]。例如,FDA已经批准了OVA1测试用于卵巢癌高灵敏度测试,效果优于活检或手术检查,即使辐射测试结果不能表明是否罹患恶性肿瘤。OVA1卵巢癌定性血清测试将五个免疫测定组合形成一个单一数字评分系统。试验表明,符合下列条件的妇女:病人18岁以上,卵巢包块需要进行手术,病人尚未由肿瘤学家检查都可以用此测试盒进行检查。[18]。但是这些试验被证明敏感性或特异性差,导致不必要的干预(65-97%的筛选阳性妇女接受手术干预实际上没有癌症),或者不能减少卵巢癌相关死亡率[17,18]。
2.高危患者的特殊考虑
携带特定遗传突变的患者需要筛选,因为一般群体中卵巢癌的终生风险为1.3%,但在BRCA1和BRCA2突变携带者中可以高达40-60%[19],在Lynch综合征突变携带者中为10-15%[5]。由于在多基因组中确定了其他高危突变,我们可能能够识别更多的高危患者。
3.高风险预防研究进展
携带高风险突变的妇女建议进行降低风险的双侧输卵管卵巢切除术(risk-reducing salpingo-oophorectomies,RRSO),BRCA1年龄为35至40岁,BRCA2年龄为40至45岁。因为切除卵巢可能导致绝经期的早期发作,心脏和骨骼健康的风险增加,以及对生活质量的其它损害,对于立即去除输卵管(输卵管切除术)但延迟卵巢切除术(卵巢切除术)方法正在研究[20]。比较RRSO与输卵管切除术延迟卵巢切除术的风险,结论是,即使最初的输卵管切除术没有降低卵巢癌风险,卵巢切除术的五年延迟将分别将BRCA1和BRCA2突变的卵巢癌的发生率增加4.1%和1.8%。Kwon等人创建了一个模型,比较BRCA1和BRCA2突变携带者分别在40岁时RRSO、40岁时输卵管切及50岁时的卵巢切除的成本和收益[21]。尽管RRSO在40岁时在成本和总体预期寿命方面更有效,但是输卵管切除术加延迟卵巢切除术患者有更高的生活质量和预期寿命。
4.高危患者的激素药物
已行双侧附件切除术的患者较早出现更年期症状如性功能障碍、性欲低下等绝经期症状,最近的一项文献综述评估了RRSO患者BRCA突变的激素治疗的安全性[22],发现外源性激素治疗能缓解更年期症状,同时不增加乳腺癌的风险,但没有足够的证据表明增加卵巢癌复发的概率。
四、卵巢癌的优化化疗和开发创新化疗
在卵巢癌中或其他癌症中,化疗耐药性是常见的。为了确定基因耐药,Patch[9]分析了92名HGSC患者的全基因组序列分析特征突变,并在所有样品中发现TP53突变,但在化疗耐药患者中仅发现了较少的遗传改变,包括BRCA1和BRCA2中的种系突变的应答,促凋亡基因FOXO1和BCL2L11中的突变,以及增加的编码细胞药物外排泵的ABCB1的表达[22]。了解卵巢癌的基因突变,能更好的应用于卵巢癌的临床治疗,寻找克服化疗耐药性的途径。
1.优化化疗
2017年4月下旬,美国肿瘤综合协作网(National Comprehensive Cancer Network,NCCN)公布2017NCCN《卵巢癌临床实践指南(第一版)》。新版指南诸多更新源于2017年3月中旬在美国召开的美国妇科肿瘤协会(SGO)妇科肿瘤年会。增加1个上皮癌一线静脉化疗方案:卡铂AUC 5+聚乙二醇脂质体多柔比星30 mg/m2,每4周1次,共6 疗程。增加了新辅助化疗内容:(1)常用的静脉方案均可以用于间歇性减瘤术(IDS)前的新辅助化疗,也可以用于IDS 后的辅助治疗。(2)在IDS 前使用包含贝伐单抗的方案必须慎重,因为可能会影响术后切口愈合。(3)新辅助化疗和IDS 后使用腹腔化疗方案的数据很少。IDS 后可用静脉化疗,也可选择腹腔化疗,除了可选择GOG 172 推荐的腹腔化疗方案外,卡铂也可以用于腹腔化疗,方案如下:第1 天:紫杉醇 135 mg/m2>3 h 静脉化疗(IV),卡铂 AUC 6 腹腔注射;第 8 天,紫杉醇 60 mg/m2IP。(4)推荐至少6 疗程化疗,包括IDS 后至少3 疗程化疗。癌肉瘤(MMMT)、透明细胞癌、黏液性癌和交界性、低级别(G1)浆液性/子宫内膜癌样癌均可以参照高级别浆液性癌的腹腔化疗(IP)/IV方案。复发后化疗如患者对紫杉醇过敏,可考虑用白蛋白紫杉醇。新增黏液性癌复发化疗方案:(1)氟尿嘧啶(5-FU)/四氢叶酸/奥沙利铂±贝伐单抗(2B类证据)。(2)卡培他滨+奥沙利铂。
2.开发创新疗法
纳米颗粒技术是一种很有前途的方法,通过其引入治疗剂量和最小化脱靶效应。在一项研究中,研究人员使用纳米脂质体颗粒靶向化疗药物的细胞挤压的细胞膜的转运,这种方法能够恢复体外和体内的紫杉醇敏感[23]。最近证明,来自天然存在的纳米颗粒在体外和体内与紫杉醇组合时改善凋亡和抑制肿瘤生长。另外有治疗靶向周围肿瘤基质的希望,例如,研究发现胎促分裂素通过刺激单核细胞的抗肿瘤蛋白TSP-1(凝血酶敏感蛋白-1)的周围释放,来抑制铂抗性PDX模型中的转移[24]。
3.FDA批准的药剂
Olaparib是一种多核糖聚合酶(poly ADP-ribose polymerase,PARP)抑制剂,于2014年被批准用于BRCA1/2突变患者,该患者接受过3次或以上的化疗。贝伐单抗是血管内皮生长因子抗血管生成的,2014年也获得FDA批准,用于复发性铂类耐药患者与紫杉醇,拓扑替康或聚乙二醇化脂质体多柔比星的组合。目前正在研究许多其它靶向治疗剂,包括另外的PARP抑制剂,抗血管生成剂,酪氨酸激酶抑制剂和免疫治疗剂。在美国妇科肿瘤协会年会上,卵巢癌靶向治疗的内容占了很大部分。三个主要针对BRCA1/2突变的PARP抑制剂奥拉帕尼、尼拉帕尼、雷卡帕尼是本次会议的热点,也均已被FDA批准上市。
五、总结
目前,手术治疗是卵巢癌的主要治疗手段,术后辅以化疗、放疗等综合治疗,早期(FIGOI、II期)卵巢癌实行全面分期手术,晚期行肿瘤细胞减灭术。目前术后化疗药物多采用铂类为基础的联合化疗,其他治疗方法目前临床应用较多的是细胞因子治疗,分子靶向治疗作为卵巢癌的辅助治疗手段,已呈现出一定的临床疗效,但是,手术治疗无法清除全部癌细胞、术后化疗耐药以及化疗药物不敏感都是需要解决的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导致卵巢癌的复发率增高,患者生存率下降,所以,进一步研究卵巢癌的形成、转移机制,针对其完善诊断、治疗方法及改善预后是将来的研究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