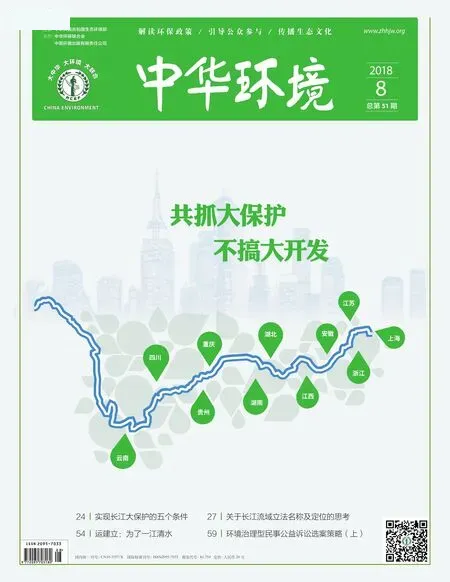关于长江流域立法名称及定位的思考
文 邱秋
长江保护立法的定位应当是实行流域治理的综合法,统筹长江流域保护和开发、利用的综合决策,以法律的方式为长江经济带实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战略目标提供系统的顶层设计和制度创新。
随着长江经济带建设的不断深化,长江流域立法正在快速步入国家立法程序。长江保护立法的焦点逐渐从为长江立法的必要性转向如何为长江立法。“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已深入人心,长江流域立法的名称为“长江保护法”具有合理性,其定位应为流域综合法,在新时期生态文明建设整体性、协调性思维下,解决长江流域的突出问题,以法治手段为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提供顶层设计与制度创新。
长江流域立法的定位之困
长江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长江流域是我国最大的流域,承载着4亿多人的生存发展,战略地位十分突出,但流域开发利用和保护的问题也特别突出。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水利部及其长江水利委员会就开始着手研究关于长江保护的流域立法问题。30多年来,在学术界和实务界的不懈努力下,对长江流域立法的法理基础乃至条文起草开展了广泛的研究,这些积累与成果为长江流域立法从理念走向立法实践提供了良好的前期基础。随着长江流域生态保护问题的日益突出,社会各界、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关于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为保护长江立法的呼声已是一浪高过一浪。特别是随着长江经济带的高速发展,三峡工程、南水北调、西电东送等重大工程的实施和运行,长江的保护、开发和利用成为关系国家发展全局的重大战略,长江的重要性、复杂性和特殊性日益深入人心。目前,长江流域立法的条件和时机逐步成熟,正在迅速进入国家立法程序,立法研究的重点也逐步从为长江立法的必要性转向如何为长江立法。
如何为长江立法首先涉及的就是名称与定位问题。鉴于长江生态的极端重要性,党中央、国务院多次明确,长江经济带建设,必须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战略定位,长江生态环境只能优化不能恶化,涉及长江的一切经济活动都要以不破坏生态环境为前提。2016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重庆主持召开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高度强调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要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2018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长江时再次明确指出:“不搞大开发不是不要开发,而是不搞破坏性开发,要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强调新形势下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关键是要正确把握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总体谋划和久久为功、破除旧动能和培育新动能、自我发展和协同发展的关系。加强改革创新、战略统筹、规划引导,以长江经济带发展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长江流域立法应当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战略定位业已形成共识,这既缘于长江生态的严峻性,更为党和国家关于生态文明建设和长江经济带建设的国家战略所确认。在为长江立法的相关研究中,这部流域立法的名称经历了由“长江法”到“长江保护法”的变化。早期关于长江流域的立法研究,多采用“长江法”的名称;2016年以后,随着“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理念的提出和深入人心,“长江保护法”的名称逐渐成为主流。例如,2016年10月,水利部就如何贯彻落实《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纲要》、共抓长江大保护时明确提出,要加快长江流域立法进程,抓紧制定并推动出台“长江保护法”。目前,国家立法机关采纳“长江保护法”的名称具有更大的可能性。有的观点认为,既然要“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长江流域立法不仅在名称上应为“长江保护法”,在内容定位上也不宜规定长江流域的开发、利用。长江流域立法的内容究竟是仅仅定位于单一的“保护”法,还是综合性的“开发、利用与保护”法,尚未完全明朗。
长江流域水事立法的割裂之痛
在长江流域立法研究中,无论是早期的“长江法”,还是后期的“长江保护法”,其法律性质均属于针对长江这个特定流域的流域立法。流域生态系统具有高度整体性和相互关联的自然特点,决定了流域管理的综合性,以及对生态系统整体性规律的遵循。但是,长期以来,我国在水事立法中已经形成了水资源、水环境与水生态相割裂,水资源开发、利用与保护难以实现综合决策的既有格局,长江流域亦饱受水事立法的割裂之痛。
调整长江流域的水事立法众多:在国家法律层面主要有“涉水”四法,即《水法》《水污染防治法》《防洪法》《水土保持法》,国务院层面有单项立法《长江河道采砂条例》,在部委层面制定了《长江干线水上交通安全管理特别规定》,在长江流域层面有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制定的《长江流域省际水事纠纷预防和处理实施办法》等;在长江的子流域层面有《太湖流域管理条例》等,长江流域所在各省(市)还制定了大量的地方水事立法。不同的层级、不同内容和不同指向的水事立法共同指向长江时,仍然未能管好长江,根本原因在于,长江的开发、利用和保护处于割裂状态,这些立法对长江流域的管理均是碎片化的,导致长江保护所需要的上下游、左右岸,以及水资源、水环境和水生态的整体性难以得到保障,甚至还存在诸多的立法冲突、立法重叠和立法空白,难以形成流域治理的合力。中央环保督察所反映的长江流域水生态系统碎片化导致的水污染问题,如江汉平原水网密布,但上下游各自为政、建设各类涵闸、水坝上万座,水系长期被人为割断,水资源、水污染纠纷不断,则是现行碎片式立法的典型“后遗症”之一。
长江流域是世界水资源开发、调度频率和强度最高的流域之一,居民对生态资源的生存依赖度极高。因此,在长江流域实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面临巨大的挑战。一方面,长江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宝库,生态安全不仅是长江流域经济社会发展最根本的基石,也是中华民族生存发展的重要支撑;另一方面,随着国家“一带一路”战略和长江经济带建设的实施,长江流域的功能日趋复杂,“黄金水道”与生态保护之间的竞争加剧,利益冲突不断升级。长江航运货运量居全球内河第一,依托“黄金水道”,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是党中央作出的重大决策,是关系国家发展全局的重大战略。长江经济带覆盖长江流域11个省市,是长江流域最发达的地区,也是全国高密度的经济走廊之一。早在1995年,其人口密度、经济密度和人均GDP就分别为沿江九省市的1.6倍、2.3倍、1.4倍,是全国平均水平的4.5倍、6.2倍和1.4倍,是我国综合实力最强,战略支撑作用最大的区域之一。因碎片化而缺少合力的现行水事立法,难以支撑流域“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急迫需求。据包存宽等统计,在十一五、十二五期间,长江经济带生态文明建设绩效整体下降。2018年6月,审计署对长江经济带11个省市“2016年至2017年生态环境保护相关政策措施落实和资金管理使用情况”的审计结果也表明,在中央“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的要求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取得了一些成效,但也存在以小水电过度开发为特征的开发管控不够到位,生态修复未达预期,污染治理还存在薄弱环节,以及生态治理资金大量结余等问题。
“长江保护法”应定位于流域综合法
在“全国性水事法律—流域性水事法律—地方性水事法律”三个层面的水事法律体系中,流域立法属于中观层面的立法。制定“长江保护法”,需要在复杂的水事法律体系中找准流域立法的定位。
习近平2018年4月考察长江经济带发展时指出,“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不是不要大的发展,而是要立下生态优先的规矩,倒逼产业转型升级,实现高质量发展。可见,“共抓大保护”中的保护,不是与“发展”相割裂的“保护”,而是“保护”前提下的“发展”,以“保护”来引领长江流域经济转型与社会和谐发展。同样,如果仅仅从字面上理解“长江保护法”,因循旧有的对长江流域的开发、利用和保护活动分别立法的碎片式立法模式,制定一部以污染防治为主的狭义的长江流域立法,既背离流域立法的本质,又不能解决当前长江流域所面临的紧迫的保护问题。“长江保护法”的定位应当是实行流域治理的综合法,统筹长江流域保护和开发、利用的综合决策,以法律的方式为长江经济带实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战略目标提供系统的顶层设计和制度创新。
长江流域涉及1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12个行业部门,长江流域以水为纽带,连接上下游、左右岸、干支流,形成经济社会大系统,涉及水、路、港、岸、产、城和生物、湿地、环境等多个方面,是一个整体;长江流域是复杂的巨型流域,上、中、下游情况各异,地方和部门利益关系错综复杂,流域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多种功能,以及依附其上的多元利益关系冲突极为普遍,需要协调。制定“长江保护法”,探索长江流域以生态文明建设引领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新途径,实现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必须坚持流域立法的整体性和协调性,跨区域、跨部门统筹考虑,以专门的法律来统一协调长江流域的保护、开发和利用问题,特别是要将水资源、水环境、水生态统一治理。
中国尚没有一部法律层面的专门性流域立法,制定“长江保护法”是一项开创性的研究。一部法需要有所为有所不为,“长江保护法”定位为流域综合法,其主要内容应聚焦于以下方面:
第一,长江保护中的流域性问题。长江流域是巨型流域,支流众多,江湖关系复杂。“长江保护法”应着力解决涉及全流域的重大问题,如长江流域水安全问题、省界断面水污染问题等。长江流域的区域性涉水问题,原则上应由区域立法规定。
第二,长江保护中的法律冲突、重叠与空白问题。“长江保护法”不是打碎既有的水事法律体系,另起炉灶,而是寻找现行立法中的冲突、重叠与空白之处,予以统一和协调,如流域水资源综合利用的法定顺序。国家和地方层面的水事立法已解决的问题,不必在“长江保护法”中重复规定。
第三,长江保护中的制度实效性问题。长江保护中的诸多乱象,并非因为缺少相关法律制度,而是现行水事立法过于原则,操作性不强,导致制度的实施效果不佳。“长江保护法”应把制度的“管用”“好用”作为立法的基本追求,在系统梳理和调研现行制度立法实效的基础上,为提升这些“僵尸”制度的法律实效提供操作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