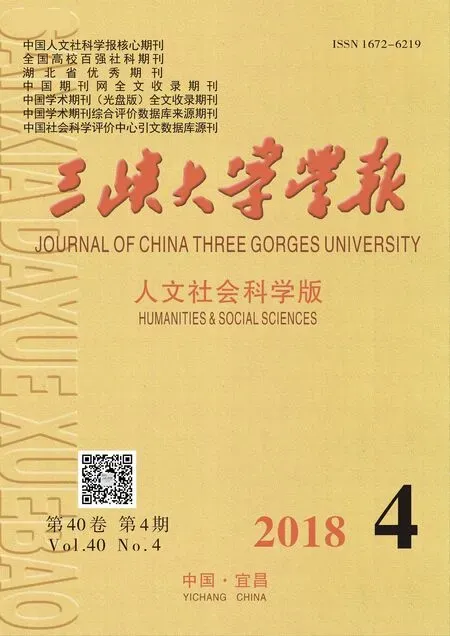作者意图、文本意图与文本阐释
刘月新,阜士亮
(三峡大学 文学与传媒学院,湖北 宜昌 443002)
张江先生在《强制阐释论》中对当代西方文论强制阐释的弊端进行了系统清理和批判,引发了理论界的热议。他在《“意图”在不在场》中进一步申明了作者意图在文本阐释中的重要性,这个意图不仅牢牢控制着作者的创作过程,而且规定了读者的阐释路径。作者意图决定了文本的内容与价值,文本决定了读者阐释的路径和目标,作者、文本与读者之间是线性的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本文认为,作者、文本与读者之间不是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而是有着复杂的转化调节机制。作者在创造文本的过程中,在表现对象、潜在读者、艺术惯例以及话语机制等因素的影响之下,超越固有的创作意图,生成文本意图。读者在理解文本的过程之中尽管会受到作者意图的影响,但主要是以文本意图为依据来阐释文本。意图不是隐含于文本之内的稳定不变的常数,而是在作者、文本与读者之间流动的变数。
一、作者意图
张江先生在“强制阐释论”系列论文中并没有对作者意图进行明确的界定,从他的论述中可以推断,他所理解的作者意图是指作者的创作动机、创作目的、艺术构思以及所要表达的思想情感。这一意图清晰而明确,既决定了文学创作的过程与结果,又限定了文学阐释的路径和范围。暂且撇开文学阐释不谈,仅仅就文学创作而言,这一观点并不完全符合文学创作的实际,既没有认识到作者意图的复杂性,又忽视其他因素对文学创作的影响。谁都不能否认,文学创作发端于作者的意图,没有意图就没有创作。但有意图是一回事,意图是否明确又是另一回事。从文学创作实践来看,有些作者的艺术思维偏于理性,能够按照自己的目的、计划去创作,将创作意图体现在文本之中,如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的鲁迅、茅盾、刘震云就属于此类作家。刘震云对鲁迅的创作思维与小说特点有较为准确的概括,他说:“鲁迅是个伟大的作家。像他那么严厉、尖刻、咄咄逼人者,在中国历史的文人中还没有过。……但鲁迅又是一个与他的思想解剖力相对而言艺术感受力不太丰厚的作家,他小说的艺术感染力主要是通过作品的思想内涵散发出来的。我们只能看到寒冬中几株秃枝桠的杨树。鲁迅小说的色彩可是有点单调。……鲁迅的小说中人物关系及发展走向历来是单线。它从来不纷繁复杂。它一直在追踪和表达着鲁迅所要表达的思想。”[1]112鲁迅是一个善于理性思考的作家,他的小说冷峻凌厉、思想深刻,给读者以思想的启迪和震撼。偏于理性思维的作家常常表达对世界的认知,在描写对象时善于以简洁白描的语言抓住对象的特征,直抵对象的本质,舍弃了对象的多样性与丰富性,限制了读者丰富的想象与情感体验,为读者提供了认知世界的角度。但不能就此认为文学创作就是作家思想的直接表达。鲁迅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的思想是从生命体验中生发出来的,他的创作既是一个思想探索的过程,也是一个寻求生命突围的过程。如果鲁迅的创作仅仅是某种固有思想的表达,其作品必然会苍白贫乏,丧失艺术感染力。
与此相反,那些偏于感性思维的作家对自己的创作意图并没有明确的意识,常常表达自己的审美感悟和情感体验,或者是表达自己对生活的感性认识,这些内容并没有上升到理性认识的层面,而是表现为某种趣味、感觉、情绪、情调和氛围。刘震云说:“如果我们把鲁迅的小说与沈从文的小说放到一起读,我们就会发现这是气质、个性、对文学的认识和出发点完全不同的两类作家在创造艺术时所表现出的差异。前者深刻、单调,后者柔弱、丰厚;前者的贡献主要在认识,后者的贡献主要在艺术。”[1]113刘震云所说的“丰厚”与“艺术”,是指沈从文的小说描绘了一个气象氤氲、丰韵饱满的艺术世界,揭示了审美对象多方面的意义,具有浓郁的审美氛围与艺术情调,给读者绵长悠远的艺术回味,不以思想的深刻性见长。
文学史上不少经典之作都是在作者意图不明确的情况下创作而成的,作者事先没有清晰的创作计划,也不明确自己笔下形象的意义,而是受到某种兴趣和情绪的推动进入创作过程。俄国小说家冈察洛夫将创作分为自觉和不自觉两种类型,他说:“我只是在完成了自己的作品,与它们相隔了一段距离和时间以后,才十分明了它们的含义、它们的意义——思想。……我在描绘的那一会,很少懂得我的形象、肖像、性格意味着什么,我仅仅看见它活生生地站在我面前……”[2]144-147不自觉的作家常常受到想象和情感的支配,他们所创造的形象和画面仅仅表明自身,其中所包含的意思有赖于批评家的发现,别林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就是这样的评论家。冈察洛夫的创作说明了一个基本事实,即作者的创作意图是复杂的、多层次的,不是所有的作家都有明确的创作意图,也不是所有的作家都能按照意图严格控制创作过程与结果。英国的布拉德雷说:“诗不是一个早已想好的清晰确定的事物的装饰品。它产生于一种创造性冲动,一种模糊的想象物在内心躁动,想要获得发展和得到确定。如果诗人早已准确地知道他要说的东西,他干吗还要去写诗?……只有当作品完成时,他想要写的东西才真正呈现出来,即使对他自己来说,也是如此。”[3]170文学创作既是作家表达思想情感的过程,也是作家认识和深化思想情感的过程。如果一个作家对自己的意图已经有清晰明确的认识,解开了思想情感的疑惑和困境,可能就不会去从事创作了。
学者袁渊在《试论作者意图与阐释标准》一文中指出,张江先生观点的片面之处在于将作者看作是一个理性主体,这个主体能够控制自己思想情感与行为方式,忽视了现代西方哲学对传统理性主体的批判。这一分析是有道理的。作者意图并非单一的理性结构,而是一个包括情感、想象、无意识等丰富内容的多维立体结构。文学创作不能缺少理性的引导,但情感、想象与无意识等因素常常突破理性的限制,使创作呈现出一定的随机性和偶然性。文学创作的奇妙之处在于,它虽然发端于作者意图,但却常常超越作者意图的控制,并非所有作者对作品产生的过程以及意义都十分清楚,也不意味着作品就是作者意图的直接表达。如果文学创作的一切都在作者意图的掌控之下,文学创作与撰写学术论文就没什么区别了。
二、文本意图
既然张江先生将文学创作看作是作者意图的实现过程,那么文本意图与作者意图之间就具有直接对应关系。在这一问题上,张江先生的观点与赫施的观点基本一致。赫施提出了“保卫作者”的口号,认为文本的意义就是作者意图的体现,文本阐释的最终目标就是把握作者的意图,哪怕是作者的无意识意图。他说:“‘无意识含义’这个概念一般是指作者未注意到的含义,但是,这个含义仍存在于作者精神的另一个区域中,也就是说,存在于作者精神的潜在区域中,通常人们称之为无意识区域。”[4]63我们并不否认文本体现了作者意图,但如果将文本意图直接等同于作者意图,就将问题简单化了。我们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来认识:
第一,从文学修辞学的角度看,从作者到文本有一系列转换的中介机制。美国叙事学家韦恩·布斯在《小说修辞学》中提出了“隐含作者”的概念。他发现自福楼拜以来的欧洲现代小说奉行客观化叙事原则,改变了传统小说讲故事的叙述策略,采用客观化的“显示”方式,消除了作者主观评价的痕迹,作者似乎从小说中消失不见了。布斯通过大量的文本分析,认为这是现代小说家使用的一种叙述策略,小说文本中仍然有作者的身影存在,他将这个作者称为“隐含作者”。“隐含作者”是隐含在作品内部的作者,和实际作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他是作者的“第二自我”,是作者在作品中的“替身”。布斯指出:“‘隐含作者’有意无意地选择了我们阅读的东西,我们把他看作是真人的一个理想的、文学的、创造出来的替身;他是他自己选择的东西的总和。”[5]84实际生活中的作者是一回事,隐含作者又是另一回事,不应将两者混为一谈。以色列的理蒙-凯南说:“隐含的作者是在作品整体里起支配作用的意识,也是作品里所体现的思想标准的根源。他和真实作者的关系被认为有很大的心理复杂性。”如果要将“隐含作者”与真实作者和叙述者区别开来,“就必须把隐含的作者的概念非人格化,最好是把隐含的作者看作一整套隐含在作品中的规范,而不是讲话人或声音(即主体)。”[6]156-168“隐含作者”既不是实际的写作者,也不是一个可以发出声音的叙述者,而是隐含在作品中的思想与意义。它是通过作品的整体设计,借助所有的叙事要素无声地控制作品,引导读者的阅读。“隐含作者”这一概念的提出是有意义的,它既承认了文本意图与作者意图的关联,又说明了文本意图与作者意图的区别。
第二,从文学语言学的角度看,要看到一种语言的意义与作者使用这种语言所要表达的意义的联系和区别。两者之间相当于索绪尔所说的语言和言语的关系,语言是言语的基础,言语是语言的运用,当作者使用一个词语去表达一种意义时,必须依赖于这个词语本身的意义限定。反过来说,词语的意义同样也依赖于该词语在使用中的意义衍变。文本意图与作者意图的关系也是如此。我们不否认文本意图中包含了作者意图,但由于语言本身的惯性以及历史文化传统的积淀,文本意图通常会大于作者意图。因此,我们在阐释文本意义时,既要研究作者对词语的特殊用法,又要考察词语的惯常用法及其背后的历史文化背景,发掘作者尚未意识到的丰富内涵。我们还可以进一步从诗歌语言与科学语言的区别来看待这一问题。按照保罗·利科的观点,诗的语言与科学语言都来自于日常语言,但两者的指向与效果大相径庭。科学语言要消除歧义,要使一个符号只具有一个意义。而诗歌语言“在于保护我们的语词的一词多义,而不在于筛去或消除它,在于保留歧义,而不在于排斥或禁止它。语言就不再是通过它们的相互作用,建构单独一种意义系统,而是同时建构好几种意义系统。从这里就导出同一首诗的几种释读的可能性”[7]301。科学语言是信息的传达,是指向经验世界的工具,目的是帮助我们认识物质世界的规律,诗要通过语言的特殊构成创造一个独立自足的艺术世界,唤起读者丰富的感受和体验,而不仅仅是传达某种信息的工具。在众多的文学语言中,诗歌语言虽然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但其他的文学语言也会产生隐喻或象征效果。从这一角度看,文学文本的意图一般会大于作者意图,为读者的阐释提供了较为广阔的空间。
第三,从文学社会学的角度看,作品的形象体系常常使文本意图大于作者意图,这就是吕西安·戈德曼所说的,作品的客观意义大于作者的主观意义。戈德曼反对结构主义封闭的意义观,认为作品是一个指向社会现实的意指性结构。在他看来,文学作品不仅仅是个人意愿和情感的表达,即使是十分个人化的作品,其背后所隐含的都是作者所属群体的价值观,都具有指向社会与时代的意指性。意指与意识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意识植根于语言,具有自觉性,而意指可以先于语言而存在,常常是非自觉的,是主体对外界的一种感受与反应。意指比意识更具有原初性,虽然不能用语言明确表达,但却包含着意义。“人类的一切行为都是个人或集体主体的回答,这种回答的意图构成使既成形势向主体所希望的方向变化,因此,任何行为,任何人类的事实都有一个意指的特质,这种特征并非总是明显的,而研究者应该通过自己的工作使之明朗。”[8]64文学作品作为一个意指性结构,其客观意义可以超越作者的意识或意图而存在,“一个作者的意图和他认为他的作品所具有的主观意义,并不总是和作品的客观意义相吻合。”这又可以分为两种情况,一是作者的主观意图受到现实环境的制约,难以在整体上把握社会历史的特点与发展趋势,但由于作者丰富的艺术感受力以及作品的意指性结构,它的形象世界可能以多种方式与社会现实发生关联,产生丰富的客观意义,而作者本人对这种关联缺乏自觉意识。二是文学史上有许多作家由于作者受到思想的局限,往往对其思想与创作意图中最具有价值的部分并不看重,反而强调那些即将被时代所抛弃的部分。“研究者只有把一部作品重新置于历史演变的整体中,把作品与整个社会生活联系起来,才能从中得出客观意义,而这种意义甚至常常是作品的作者很少意识到的。”[9]8无论是作者意识到的主观意义,还是作者没有意识到的客观意义,都应该联系作品所产生的社会历史环境来阐释,而不能仅仅从作者的个人经历和主观意图中去寻找。
美国的H·G·布洛克对文本意图与作者意图之间的关系有较为辩证的理解,他说:“虽然艺术品有表达的意义,同艺术家的‘意图’有因果关系,但它仍然有着自己独立的存在。这与艺术家本人的思想和愿望是两回事,但又与它们有关系。一旦艺术家将自己的意图体现于一个适用于公共交流的表现形式中,该意图便变成艺术品的一部分,成为公共财产。”[3]353文本阐释不能不顾及作者意图,但又不能拘泥于作者意图,要将文本置于它所产生的社会、文化与文学背景之中,阐释其丰富的意义。
三、文本阐释
基于对作者与文本、作者意图与文本意图之间的复杂关系的认识,我们认为很难建构一种大一统的、涵盖一切的文本阐释模式,应当根据作者、文本、世界与读者之间的具体关系而建构不同的阐释模式。从总体上看,文本阐释发生于读者、文本、作者与世界之间,但当面对不同时代、不同类型与不同风格的文本时,四者之间的关系会有所不同,读者会采用不同的阐释策略,相应地会产生几种不同的文本阐释模式。
首先是作者与文本互证的阐释模式。这种模式是将与文本有关的资料,如作者的创作心理、文本的创作背景、作者对于文本意图的介绍与文本联系起来考察,从中推测出作者的创作意图。我们反对将文本意图简单地等同于作者意图,但在有些情况下,文本意图与作者意图有较为直接的关联,如鲁迅、茅盾、张贤亮那些理性思维较强的作家,他们常常能够按照事先设计的意图去组合文本的艺术结构与形象世界,将创作意图体现在文本中。读者在阅读这些文本时,通过外在意图与文本内在意图的相互参照,与作者的理解达成共识。关于《灵与肉》的意图,作者张贤亮说过这样一段话:“《灵与肉》的主题是描写一个大资产阶级家庭出身的青年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社会这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通过了严酷的劳动,在精神上如何获得了劳动人民的感情和树立坚定的社会主义信念,在肉体上如何摒弃了过去的养尊处优而适应了比较贫困的物质生活的。……《灵与肉》是一支赞美劳动、特别是体力劳动、体力劳动者(里面的主角都是这样的人)的赞歌。”[10]有读者将《灵与肉》的意图概括为爱国主义,其根据是主人公许灵均在历经艰难困苦之后,依然留在草原的怀抱,没有跟随父亲到美国去享受奢华的物质生活。但从小说描写的社会背景、故事框架以及创作背景来看,作者对意图的概括更符合实际。小说包含的爱国主义感情并不能作为小说的主要意图而存在。童庆炳先生将这种阐释模式称为作者改造读者,作者将读者的阐释思路纳入创作思路之中。这类文本常常属于篇幅不大的写实之作,有着十分具体的形象体系与时空架构,叙事不够饱满圆润,读者一旦进入文本之中,解读思路将会受到作者意图与文本解构的制约。如果读者试图从其他角度切入文本,将会遭遇文本的抵制,导致误读的发生。
其次是艺术惯例与文本互证的阐释模式。阐释者在不知晓作者的创作心理、文本的创作背景与作者意图的情况下,就只能通过其他更为间接的方式来阐释文本。英国美学家安娜·谢泼德认为,在一个文本遭遇几种不同阐释的时候,阐释者为了证明某一种阐释的有效性,就需要参照作者意图,而在不知道作者意图的情况下,就需要借助“属于同一种风格的其他艺术作品,由同一位艺术家创作的其他作品,第一批观众的期望……”[11]139来间接推断作者意图。了解属于同一种风格的艺术作品就是了解与这件艺术作品有关的艺术惯例,考察这件艺术作品对艺术惯例的遵循与突破,衡量该艺术作品的意义与价值。如有研究者在研究弥尔顿的《利西达斯》时,不仅追溯到古典先驱——古希腊摩斯科斯、忒奥克里托斯以及古罗马维吉尔的田园诗传统,而且将它与锡德尼、斯宾塞、莎士比亚开创的英国田园诗传统联系起来考察,以此说明弥尔顿在运用和改造这种传统时表现出来的独创性,加深对作品的欣赏与理解。
考察一位艺术家的其他作品尤其是同一时期的作品,对于认识艺术家某一作品的意图也是有帮助的。莎士比亚研究专家德里克·特拉沃西在《莎士比亚:最后的阶段》中认为,《佩里克利斯》《辛白林》《冬天故事》与《暴风雨》是莎士比亚在1609到1611年间创作的传奇剧,这些传奇故事总是发生在一个幻想的神奇环境中,主人公先遭受苦难然后获得幸福,往往依靠一些偶然因素甚至魔法等超自然的力量化解矛盾,敌对双方互相宽恕,互相和解,最后获得完满的结局。它们在主题和表现手法上具有相通之处,构成了一个严密的艺术统一体,可以彼此说明对方。
“第一批观众的期望”是指与创作者同时代的接受者的期待视野,它对作者的创作行为可能会产生直接影响。尧斯与伊瑟尔的接受美学认为,接受者的期待视野不仅对接受过程产生影响,而且直接作用于作者的创作过程。如莎士比亚不少戏剧中的人物沉溺于由双关语和斗嘴构成的争论中,最典型的就是《第十二夜》中的费斯特与《皆大欢喜》中的塔奇斯通这两个人物。这些场面对于现代观众来说相当枯燥乏味,甚至不可理解。但莎士比亚时代的观众喜欢这些场面,为了迎合观众的喜好,作者在戏剧中设计了双关语和斗嘴的场面。安娜·谢泼德认为,为了真正理解莎士比亚戏剧的这一特征,批评家不得不置身于莎士比亚戏剧第一批观众的位置上,了解他们的社会背景、思维方式、政治态度、宗教态度和艺术趣味,从中抽象出一种期待视野。“第一批观众”并不能等同于具体的观众,而是批评家为了理解作品在各种文献以及当时流行的艺术惯例中概括出来的理想观众。“如果我们把第一批观众的期望考虑在内,那么那些使我们困惑不解的特征——诸如我所提到过的那些存在于莎士比亚的戏剧之中的说双关语的场面——就时常可以得到说明。”[11]144-145观众的期望并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由艺术惯例与时代的艺术趣味塑造而成的,它潜在影响作家的艺术创作行为。
同一种风格的其他艺术作品、同一位艺术家创作的其他作品以及第一批观众的期望都是艺术惯例的具体体现,可以作为作者意图的间接证据,阐释者能够从中建构出一种阐释模式,并将作品纳入这一模式之下,做出顺理成章的阐释。乔纳森·卡勒将这种阐释称为“吸收同化”或“归化”,他说:“所谓把某一事物吸收同化,对它进行阐释,其实就是将它纳入由文化造成的结构形态,要实现这一点,一般就是以被某种文化视为自然的话语形式来谈论它。……使一部文本归化,就是让它与某种话语或模式建立关系,而这种话语或模式,从某种意义上说,本身已被认为是自然的和可读的。”[12]206-208所谓“结构形态”、“话语”与“模式”都是指被传统所认可的文学惯例,如文学体裁、文学类型与风格类型,阐释者只有将文本纳入特定的文学惯例之下,才能理解其意义和价值。
再次是寻找象征意义的阐释模式。这种阐释模式所面对的主要是那些具有象征与哲理意味的作品。这类作品虽然有具体的写作背景,叙事和抒情也有具体的针对性,但运用了象征化与意象化的表达方式,转实成虚,叙事和抒情达到了哲理的高度,读者可以从作品的现象层入手解读其多层面的象征意义。比较典型的案例是对海明威《老人与海》的解读。海明威创作《老人与海》就是为了“描写一个人的忍耐可以达到审美程度;描写人的灵魂的尊严”。童庆炳先生就是从这一角度解读的,他认为:“这篇老渔夫捕鱼的故事寓含了深刻的哲学意味。它写出了人的倔强,又写出了人的屈辱。人活着就要奋斗,顽强地奋斗。即使受到屈辱也还要奋斗。人就要这样,明知不可为而为之,这才是真正的人生。”[13]248这一解读比较接近海明威的原意。乐黛云教授从中解读出了5个不同层面的意义:(1)与穷困挣扎的忧患和痛苦;(2)揭示了宇宙万物之间相互杀戮的残酷关系和生存斗争;(3)勇敢地面对失败,在失败面前百折不挠;(4)“自我求证”的模式;(5)“自我求证”的失败。这种解读远远超越了作者的意图,但都是从作品的叙事层面发现的意义,其中“自我求证”与“自我求证”的失败是作品的象征意义。老渔夫不惜冒着生命危险去深海捕鱼,既是生活所迫,更是为了证明自己是一个合格的渔夫。他千辛万苦捕获的大马林鱼被鲨鱼蚕食得只剩下白森森的骨架,丢弃在海边任凭风吹浪打,竟然被人误认为是鲨鱼的骨架,暗示他“自我证明”的失败。人生活在世上总是在不断地证明自己存在的价值,但由于人与人之间的隔膜,这种自我证明最终都会归于失败。这种解读遵循了由实转虚的阐释路径,阐释者从作品的现象层面入手,概括出隐含在作品内的原型,抽象出作品的象征意蕴。这种意蕴抵达了形而上的高度,是对人生终极问题的把握。
最后是寻找客观意义的阐释模式。读者在阐释过程中,不关注作者的创作意图(即使在知道作者意图的情况下),而是将作品置于其所产生的社会历史环境与文化文学语境中,挖掘隐含在作品之中的客观意义。诚如戈德曼所说,文学作品是一个指向其社会历史环境的意指性结构,由于作者思想认识与思维结构的局限,在创作过程中对自己作品形象体系缺乏深入认识与整体把握,只是将自己的艺术感受与感兴趣的生活呈现出来,其客观意义常常需要批评家来认识和把握。文学批评史上这样的经典案例不少,如杜勃罗留波夫对“奥勃洛摩夫性格”的阐释就堪称典范。杜勃罗留波夫认为:“冈察罗夫才能底最强有力的一面,就在于他善于把握对象底完整形象,善于把这形象加以锻炼,加以雕塑。……所以冈察罗夫在我们的面前,首先就是一个善于把生活现象的完整性表现出来的艺术家。”[14]184-188冈察罗夫完整地呈现了奥勃洛摩夫这一形象,这一形象的思想意义是巨大的,其意义在于揭示了俄罗斯社会生活中广泛存在、且被前代作家所描绘过的“多余人”的生活状态。普希金、莱蒙托夫、屠格涅夫等作家都刻画了不同时代“多余人”的形象,随着俄罗斯社会生活的变化,“多余人”呈现出新的特征。冈察罗夫的贡献就在于完整把握了“多余人”的时代特征,这就是彻头彻尾的懒惰和冷漠,丧失了思考能力与行动能力,对一切事物都缺乏兴趣与热情,标志着贵族阶级生活方式彻底的腐朽和堕落。乃至于冈察罗夫说奥勃洛摩夫是他和杜勃罗留波夫共同创造的,作者创造了这一形象,而批评家创造了形象的意义。这样的典型案例还有戈德曼在《隐蔽的上帝》中对帕斯卡尔与拉辛作品宗教内涵的阐释,揭示了隐含在作品结构中宗教信仰与世俗生活之间的价值冲突。
从以上归纳的四种阐释模式来看,有的阐释模式偏重于作者意图的追溯,有的阐释模式偏重于发掘文本的象征意义与客观意义。这说明文学阐释不能不顾及作者意图,但又不能拘泥于作者意图,那些深刻的文学阐释常常会拨开作者意图的迷雾,将作品置于更为宏大而复杂的背景中,探寻其丰富与深刻的客观意义。回到张江先生所讨论的“意图在不在场”的问题,我们认为张江先生的失误在于他将作者意图看作隐含在文本内的一个固定不变的要素。这个要素贯穿于作者、文本与读者之间,成为维系三者的一条线索。从阐释学的角度看,这个稳定不变的意图并不存在。首先,作者意图在创作过程中会发生变化,有些创作甚至并无明确的创作意图;其次,文本意图不直接等于作者意图,常常会大于作者意图,甚至与作者意图发生分裂;再次,读者在文本中把握的意图也不等于文本意图,而是对文本意图的阐释。因此,意图不是一个稳定不变的要素,而是一个流变的过程。如果文本阐释的目的仅仅是还原作者意图,不考虑文本特殊的话语机制和读者的阐释活动,就可能会使文本阐释流于简单化。
参考文献:
[1] 刘震云.读鲁迅小说有感:学习和贴近鲁迅[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1(3):112.
[2] 冈察洛夫.迟做总比不做好.古典文艺理论译丛(一)[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
[3] H·G·布洛克.美学新解[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
[4] 赫施.解释的有效性[M].北京:三联书店,1991.
[5] 韦恩·布斯.小说修辞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
[6] 理蒙-凯南.虚构叙事作品[M].北京:三联书店,1987.
[7] 保罗·利科:言语的力量:科学与诗歌.西方二十世纪文论选:第三卷[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
[8] 吕西安·戈德曼.马克思主义与人文科学[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89.
[9] 吕西安·戈德曼.隐蔽的上帝[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8.
[10] 张贤亮.牧马人的灵与肉[N].文汇报,1982-04-18.
[11] 安娜·谢泼德.美学:艺术哲学引论[M].艾 彦,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
[12] 乔纳森·卡勒.结构主义诗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
[13] 童庆炳.文学活动的审美阐释[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2.
[14] 杜勃罗留波夫.杜勃罗留波夫选集:第一卷[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